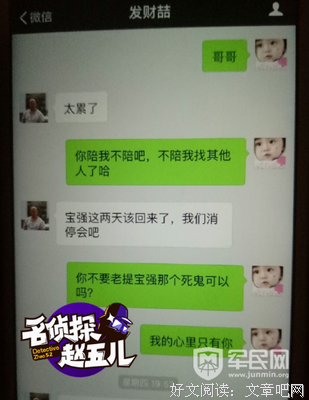记录习俗就是记录我们的存在
打开电视,看到“纪实”频道介绍藏传史诗《格萨尔王传》。专家介绍,这部史诗,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有英雄史诗的文学性,同时兼有介绍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的价值。人们在传唱的过程中迢递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与文化。听了,心里不免有所触动。
想起最近听高晓松《2018晓说》里和马伯庸一起谈长安,说到马伯庸的小说写唐代的长安详尽细致——不知道是不是说的《长安十二时辰》?我不太看马亲王的作品,有时候觉得他的推理分析很有意思,但是对其准确性心里总不是很踏实。也联想到《红楼梦》对于人物服饰、器具、饮食、礼仪的详尽描写,觉得文学其实也还有传承日常文化细节的作用的。我们民族的文化细节一点一点被磨灭掉,是不是也跟我们的文学不喜欢忠实地描摹生活细节有关系呢?现在古装影视作品里,吃个饭动不动五两十两银子,不论哪个朝代手里拿着折扇,怀里揣着银票,服色斑斓,款式新潮,随意至极,长此以往,今后的孩子大概是不会知道他们的祖先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了。
我的祖父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职业,就是用纸捻帮人装订簿册。按我们老家的话说是“纸笔点(店?)官(倌?)”是不是兼具开蒙的责任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在他生前我也没有兴趣去打听这样的细节。后来查了不少资料,才知道用纸捻装订书籍也是一种传递了很久的书籍装订办法,以前书本簿册不易得,裁好了毛边纸,让人装订一本簿册带去学堂作为练习本来用。可惜,这个纸捻怎么捻,又怎么装订,现在是都不得而知了。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日常的习俗和传统里有着很深的民族的心情和态度,甚至我以为,除开了具体的饮食男女之外,是不存在抽象的民族文化的。
读日本作家小川糸的《三茶文具店》,读到关于吊唁信的写作时,作者这样写道:“我用比平时更淡的墨写完吊唁信。之所以要用较淡的墨,是代表因为过度悲伤,眼泪滴落砚台,而让墨色变淡的意思。”以前依稀也听一位老先生说过,但是见诸文字的就很少了,是读了这段文字才唤起了自己对这个习俗的记忆。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大概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风俗本是中国人的习俗。至于在吊唁信里不能出现“此外”、“又及”,不需要在收件人下方写“亲展”,不需要在信的末尾表达敬意之类,大概对不少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但是,如果看王羲之《姨母帖》,似乎可以推想,日人的书信习俗是隐中我们的旧俗的。
现在为了图简便快捷,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我们首先觉得可以放弃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习俗和技艺。这里面固然是有很多迫不得已的地方的,当然也有不少并不符合人性与文明发展的趋势而需要摒弃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对于自己民族的生活传统放弃得太过随便轻佻,是不是会把我们民族内核的一些东西也丢弃掉呢?而最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就会渐渐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呢?我年末的时候看俄罗斯国家芭蕾剧院演出的《胡桃夹子》,其中有体现“茶”的特点的中国舞曲,既简陋又滑稽,全不像表现“巧克力”的西班牙舞曲那样特色鲜明,看来老柴对于中国文化也没有什么鲜明的感觉,心里自然就不免怅然。我们老是说自己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但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生活却又那么简陋寒碜。比如,中国也算是一个饮食大国,但是就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很不讲究,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宴会,就像是一群野蛮人的狂欢,完全看不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所应该有的仪式感。
以前我们生活得太苦了,顾不着讲究,大凡贫弱的民族,如果又没有宗教,一定是简陋寒碜的。后来我们又热衷于闹革命,一切过去的东西都是牛鬼蛇神,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样那样的一折腾,仅存的那一点点东西也就荡然无存了。现在我们一切向钱看,那些少慢差费的东西,自然不入法眼,即便偶尔有些关注,也是看看有没有商业上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简陋寒碜,是怨不得别人,全都因为我们自己。但我所担心的,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色与个性的消亡。一个民族的消亡,非人种之灭也,实文化之湮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