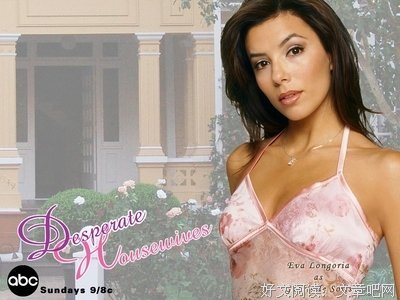《三件事》好看吗?经典影评10篇
《三件事》是一部由Кира Муратова / 琪拉·穆拉托娃执导,Сергей Маковецкий / Леонид Кушнир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件事》影评(一):關於中文譯名和影評引子
◆文/熊仔俠©
之前豆友Nova曾經翻譯了一篇關於齊娜·穆蘭托娃(Kira Muratova)的外語文章《荒蕪影像》。誠然,“荒蕪影像”一詞是對齊娜·穆蘭托娃電影最高度,最濃縮的概括。根據Jane Taubman的電影叢書系列《KINOfiles Filmmakers' Compaion》中的第四本《Kira Muratova》的目錄,齊娜·穆蘭托娃的製作電影的階段可以分為6個階段,分別爲:“奧德薩時期”,“鄉村情景劇時期”,“探索未知時期”,“蘇聯解體前後時期”,“電影《三件事》時期”以及“烏克蘭製片時期”。而Janes Taubman僅憑齊娜的一部《三件事(Три истории)》就單獨劃分出一個階段出來,可見這部電影在齊娜創作生涯中的重要地位。筆者觀看完該片以後,也有一種別樣的感覺——《三件事》可以成為齊娜電影之中最不晦澀,最不荒蕪的電影,哪怕齊娜的各種電影表現手法和處理手法依舊保留下來。另外,這部電影也曾經獲得柏林金熊獎提名。這意味這什麽?一向以來,齊娜·穆蘭托娃在電影節中從來就不是炙手可熱的關注對象和影評的寵兒。無疑,《三件事》看出了齊娜在自己電影創作中的革新和思考。而獎項提名也不過是一種最表層的體現。
本片的中文譯名正是筆者翻譯。電影原名叫《Три истории》。按照俄文的翻譯,也就更直接了當——《三件事》。之所以要使用這個譯名的原因,其中一方面是由於電影是由《鍋爐房6號》、《奧菲利亞》以及《小女孩與死亡》三個獨立,毫無關聯的故事所組成。故稱“三件事”。另一方面,這部電影在類型上可以廣義地歸入“犯罪電影”,因為這是一部講述“施害者”和“受害者”的故事。齊娜也承認電影受到《低俗小說》的影響及啓發。但是從更加人文,文藝的角度去看,這是一部講述“冒犯”和“衝突”的電影。本來筆者意欲將電影的中文名譯為“事不過三”或者“三件小事”,只不過前者“譯不對題”,後者則是偏向了“受害者”一方。爲什麽這麼說?因為電影中的三個獨立故事中的“受害者”都犯下了促使“施害者”對其進行殺害的“罪行”,而自己對“罪行”本身也是毫不知情,不甚了了甚至理所當然。對於“受害者”來說無疑是“一樁小事”。相反,對於“施害者”來說,那是滔天之罪。正如Janes Taubman提出的“Crime Without Punishment(無罰之罪)”一樣,“施害者”宛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罪與罰》的拉斯科納夫一樣“替天行道”,不需受到任何譴責。所以筆者以“三件事”為中文譯名,一方面”,“受害者”視“事”為“小”,體現出另一方面“施害者”視“事”為“大”。這方成故事的衝突。
至於談論到這個“電影《三件事》時期”齊娜·穆蘭托娃在電影上的處理手法和表現手法的話,筆者在這裡略帶提及(日後將有更為詳細的介紹與剖析)。比起齊娜在蘇聯末期製作的電影《衰弱癥》所散髮出來的“超級現實主義”(姑且可以理解成“蘇俄黑片”),在《三件事》中,齊娜更加靈活地對電影內容上採取“現實主義”化,而在電影形式上採取“失實主義”化。而這裡的“失實”是相對于“現實”來說的:
之所以“現實”,那是齊娜在電影創作上一直沿襲下來的風格。她的眼光更加專注到生活里人物的行為,語言和事件本身上去,只是在每部電影中“現實程度”有所不同。譬如正如上文提到的《衰弱癥》一樣。齊娜在該片把現實主義提升到巔峰的程度,讓觀眾目不暇接之餘,又會同患衰弱。而在《三件事》里有所不同的是,“現實”再不是統領全片的要素,它退居到“內容”層面上去。
之所以“失實”,那也是齊娜在電影創作上一直沿襲下來的風格。在她的電影里,演員的演出幾乎都是動作誇張,表情誇大,行為怪異,多少有點傾向“荒謬戲劇”的風格。而在電影聲音處理上,對白內容誇張而離散,演員說話速度極快,往往對白成為其次要素,其他“話外音”(諸如吵雜聲,動物叫聲)等反倒“喧賓奪主”。在鏡頭的處理上,齊娜傾向于用長鏡頭鏈接上下劇情,達到承前啟後的作用。往往,這種長鏡頭極富象徵意味和美感。還有,齊娜也喜歡使用“讓觀眾感到視覺不適”的運動鏡頭。最後,在剪輯上,齊娜更是跳躍式剪輯的常客。就拿《三件事》為例,電影中上一個鏡頭和下一個鏡頭之間的剪輯顯得粗糙和生硬,甚至會讓觀眾誤以為是“影片質量問題”。而這一切(演出,聲音處理,鏡頭處理,剪輯)都是齊娜對“現實主義”的“失實處理”。這也就更能好好地理解齊娜電影中“荒蕪”的精髓。因為她一直在探討一個問題——“要是電影在電影院放映的時候,無人觀看會是如何一副光景?”
當然,這也是筆者就《三件事》所作的引子,僅僅是個開頭。筆者也為對這部電影的字幕進行翻譯。同樣也會參考David Gillespie的《Russian Cinema》中的《The films of Kira Muratova,P92~P102》以及上文提及的Jane Taubman的《Kira Muratova》中的《Crimes Without Punishment:Three Stories[1997],P77~P89》的相關內容,以為觀眾和讀者呈現更為明朗和容易理解的電影《三件事》……敬請期待。
《三件事》影评(二):《三件事·奧菲利亞》:謀殺母體的二重奏
◆文/熊仔俠©
比起和《鍋爐房6號》的男主角謝爾蓋·馬科維斯基的首次合作,齊娜和自己的幾位“御用女演員”麗安娜塔·立蒂維諾娃(Renata Litvinova)以及納塔莉亞·布茲科(Natalia Buzko)的合作就顯得更為信手拈來。加之,齊娜在自己電影中對女性角色的描寫從來就占了絕對的位置。也不難怪《三件事》中的第二部份《奧菲利亞》成為電影中最長的一部。而電影的主題也回歸也到前前作《感傷警察》上去。那便是“母體的拋棄(Maternal Adandonment)”。只不過,齊娜爲了要突出《三件事》的核心主題“罪”,她就用“謀殺”這個劇情去構建起她的《奧菲利亞》。
電影一開始就是一個平靜的衝突。由納塔莉亞·布茲科飾演的孕婦塔利亞在醫院墮胎。她本來就覺得這是一件無傷大雅的事情。結果,由麗安娜塔·立蒂維諾娃飾演的婦科護士奧菲卻前往塔利亞的病房不斷追問。奧菲之所以對塔利亞墮胎一事介懷良久,是因為奧菲本來就是一個被人拋棄了的孤兒。在她心裡一直對“母體”有著強烈的復仇意識。而這就是電影一開始的衝突所在。只不過齊娜並沒有提前將動作的衝突放到最開頭,反而運用了語言上的衝突提前鋪了一個小墊。與奧菲的內心不同,奧菲的外表則是一個潔淨女神的化身,既不愛男人,也不愛女人;既不愛小孩,也不愛人類。一時,她是身穿白衣的醫護天使;一時,她則是穿上紅裙的高貴女性。而“白”和“紅”也就奠定了奧菲的外表和內心。
奧菲本來只是想過來打聽塔利亞的情況。誰知道被男婦科醫生(由Ivan Okhlobystin飾演)纏上。在“產房醫療工具圖”,“西斯廷聖母畫像”和“腦部解剖圖”跟前,男婦科醫生不斷用語言勾引奧菲,為的也就是求得一露水之情。只不過,奧菲遲疑不答應。下班之後,男婦科醫生於是窮追不捨,一直跟隨著奧菲來到了奧德薩的海濱。齊娜藉助運動鏡頭和場面調度,在廊柱的行間中再次編導出男女主角語言上的互諷和衝突。值得一提的是,電影所取景的地方——奧德薩海濱正是當年愛森斯坦拍攝《戰艦波將金號》的取景地。儘管男婦科醫生百般哀求,但是奧菲卻回頭去跟蹤塔利亞。劇情就在這裡慢慢走向小高潮,齊娜的電影元素開始呈現。
奧菲一路上跟蹤著塔利亞。穿過人群,穿過小山丘,穿過古建築,奧菲在塔利亞小便的地方小便了。隨即奧菲跟上了塔利亞,把她帶進了一個過道里,並且用自己的絲襪將其勒死。在謀殺塔利亞的時候,奧菲莫名地獲得了性高潮。這無疑是將她心裡對“母體”的仇恨最大化了。因為她本來就無法原諒塔利亞的墮胎行為。在奧菲跟蹤塔利亞的過程里,不能看見《衰弱癥》的眾多元素再一次搬上屏幕。正如筆者剛才提到的“公眾小便”,以及人際之間無處不在的臟言猥語,齊娜再一次給“公眾社會扇了一記耳光”。齊娜並沒有對現實社會作出太多的美化,反而用極為現實的手法表達出來,多少會讓人有點不適。
就在奧菲殺死塔利亞之後,給醫生打了個電話之後便“單身赴會”與其發生了關係。就在鏡頭轉向第二天清晨兩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之前,齊娜別出心裁地創作了兩組極具詩意的鏡頭。第一組鏡頭是一隻女性的食指在螺旋石柱上畫圈(一共畫了4次)的長鏡頭。石柱的螺旋紋理象徵女性的輸卵管和卵巢,而食指則是象徵母性和生命。而第二組鏡頭則是齊娜對醫生朋友的美術工作室的鏡頭描寫。一方面齊娜將比較多的筆墨聚焦到工作室裏面的概念主義繪畫中,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人為創造光源和調節光暗,交錯主次聲音的方式對工作室環境作出特寫。兩個鏡頭之後,便是奧菲從醫生的赤裸之身掙扎了出來,與其進行了“無愛的對話”。那時,奧菲方才發現自己的手袋落在了塔利亞的手上,於是在一條狼狗(齊娜的電影元素,最後一篇影評將詳講)帶路之下重新拿回了手袋。
回到醫院的奧菲進入了檔案室找到了自己親生母親伊萬諾夫娜的下落。正因為當年伊萬諾夫娜的拋棄,落得奧菲心身首創。而奧菲對自己的母親搜索枯腸的目的也就是復仇和謀殺。於是乎,奧菲來到伊萬諾夫娜的家裡,故意敲打門窗引起自己母親的注意,只可惜伊萬諾夫娜無趣搭理。齊娜通過鏡面反射和奧菲的特寫組合,將伊萬諾夫娜的懼怕和奧菲的復仇心切作出了一個平行描寫。儘管奧菲被拒之門外。但是到了第二天,伊萬諾夫娜居然穿著跟奧菲一樣的服飾,梳著一樣的髮型,牽著拐杖,拿著《哈姆雷特》前往了碼頭。就在奧菲跟隨其後之際,一位老人對著樓上另一位“老老人”喊話。在兩位老人的喊話中不難得知其倆的母女關係。個中的重複不斷的關懷問話也成為了奧菲和自己母親的一種對比。這也為劇情的展開起到了推進的作用。
就在伊萬諾夫娜在碼頭讀書的時候,心存殺意的奧菲突然顯得孩童,不斷問起母親的事,又偎依其旁,跟她不斷暗示自己就是當年的孤兒。只不過伊萬諾夫娜的無情和忽視,導致了自己最後的被殺。奧菲故意把自己母親的拐杖藏起來。正當倆人談及“奧菲利亞溺死之淒美”的時候,奧菲終於把自己的母親推下水中,後者最後溺水而亡。而奧菲拿起打火機焚毀了自己母親的檔案的時候再一次獲得性高潮。就在離開碼頭的時候,奧菲順手把拐杖給了兩位盲人。齊娜所安排的這個結局便是向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中的一句“In Our Age The Mad Lead The Blind”遙相呼應。第二部份由此結束。
之所以說《奧菲利亞》是謀殺母體的二重奏,簡而言之,是因為電影中存在“兩次拋棄,兩次謀殺,兩次性高潮”。上文也就層層分析,不難思考。
《三件事》影评(三):《三件事·鍋爐房6號》:男知識份子的暴行展覽
◆文/熊仔俠©
齊娜·穆蘭托娃的電影創作理念中極具爭議的一個理念莫過於“正常男人的缺席”(The Absence Of Normal Man;Man Without A Capital "M")。這裡的“缺席”並不是意味著鏡頭前面男演員的缺失。“缺席”可以理解為齊娜電影中男人的無能,癲狂,濫情等消極形象,簡而言之——男性道德形象的缺失。在齊娜前期的電影中,譬如《漫長的告別》中則是將“缺席”用“男青少年的叛逆”演繹了出來。這還算是合情合理。但是自《衰弱癥》之後的電影,齊娜逐步把在蘇聯“父輩電影”中的正面男性形象瓦解。結果在電影界中引起了爭議。不少業內人士稱齊娜是一個女權主義電影工作者,企圖用電影去抹黑男性形象。而齊娜對此的態度也相當的有力度——“我以前在想,將電影劃分為‘男性電影’和‘女性電影’不僅僅是‘人為的自作聰明’和‘謬誤’,現在我更覺得這是最愚蠢至極的做法!”而《三件事》中的第一部短片《鍋爐房6號》則是齊娜“正常男人的缺席”這個理念運用得最為坦白,最為直觀,最為純粹的作品。下面,筆者將會逐一剖析。
《鍋爐房6號》的劇情一點也不複雜,正如筆者在前兩篇影評中提及過一樣,短片的劇情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丹尼爾·哈爾姆斯的小說《老婦人》都有異曲同工之處(當然,齊娜也是從陀的作品中獲得靈感)。電影的男主角有兩位。男一號名叫Tikhomirov(“Tikh”在俄文中意為“安靜”,“mir”則是“平和”)。他的飾演者則是新俄電影界裏面的知名男演員謝爾蓋·馬科維斯基(Sergei Makovetsky)。一如謝爾蓋在《彼得堡異人寫真》和《烈日灼人2》等電影中的“神經刀”演戲風格,他在《鍋爐房6號》之中的演出更是和齊娜癲狂的拍攝理念完美組合起來。正如短片一開頭,Tikhomirov一邊聽著大象的叫聲,一邊歇斯底裡地疑神疑鬼;一邊看著孔雀開屏,一邊神經兮兮地模仿。這些細微的神經質動作無疑為他後來在鍋爐房向自己的舊同學Gena交待自己將女鄰居歌喉一事埋下了伏筆。而男二號則是方才提到的Gena。他與身為職員的Tikhomirov不同,他是一個底層的鍋爐工,終日創作未來主義的詩歌。值得一提的是,飾演Gena的男演員是一個名叫Leonid Kushnir的非專業演員。當然,這也是齊娜對演員苛刻之餘又特殊的“混合”癖好。
不管是現為職員的Tikhomirov,還是淪為鍋爐工的Gena,他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正如Tikhomirov在片中發牢騷“我現在活得像個多餘人”一樣,這裡無疑是齊娜對后蘇聯時代社會的映射。在蘇聯解體之後,大量的知識份子下崗失業。相反,冷血兇殘的俄羅斯黑手黨則是招搖過市,大開殺戒。像Tikhomirov和Gena一樣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不可避免地成為諸如普希金筆下的葉夫蓋尼·奧涅金或者萊蒙托夫筆下的畢巧林一樣心雖有志,但無所事事的“多餘人”。而社會地位的淪陷,無疑是為Tikhomirov的行兇埋了最深刻的根源。當他將放有女鄰居屍體的衣櫃拖到鍋爐房進而“真相大白”之後,他又感到無辜無奈,迫不得已。同樣,夢想成為詩人的Gena雖然有著知識份子的風範,但是同樣犯下罪行。因為Veniamin(男三號)欠了Gena的錢。Gena逼Veniamin為娼,四處為他尋找同性戀的嫖客。對於Gena來說,欠債還錢,那是天經地義,哪怕是把Veniamin進行“欲室禁培”也是覺得在正常不過。無論是Tikhomirov的割喉殺女,或是Gena的逼良為娼,按照正常的道德標準來說,這也是倫理上的暴行。而且施暴的人並非是冷血的黑手黨,反之為知識份子。這無疑是齊娜在電影中所編排的一大諷刺。
另外一種諷刺則是來自上文提及的“正常男人的缺席”。不管是Tikhomirov,Gena還是Veniamin,他們都是身心受到不同程度摧殘的人。當然啦,那些為Veniamin紛至遝來的男同性戀嫖客更是無以復加了。但是,有趣的是齊娜還在劇情上運用了“女人的缺席”的手法。短片中除了“女尸”和幾個諷刺男一號的臨時演員之外,就沒有女主角和女配角。儘管衣櫃里的女屍體是女性。但是當Tikhomirov要求Gena用鍋爐毀屍滅跡的時候,鏡頭一而再,再而三地對女屍體作出特寫,好不恐怖。而在兩個男人爭吵的時候,女屍體仍舊是冰冷地躺在衣櫃中,割喉位置的血已經凝結了下來。這也是一種最大的諷刺。根本用不著活生生的女人出席觀看男人們的醜態和窘態,一具女尸則可讓男人們變得瘋狂。那何況當初Tikhomirov衝動地殺死女鄰居呢?儘管,Tikhomirov覺得自己的行兇是一種解脫,一種替天行道,但是他的本意則是被現實的後果打了重重的一記耳光。
而到了短片最後,Tikhomirov和Gena依舊相持不下。在這個煉獄般的鍋爐房中,一具女尸和一個男妓則成為了兩位男知識份子的暴行展覽。而兩位男主角在解決無果之後的對哭,也是齊娜再一次把“男人的缺席”演繹得更為盡致。有趣的是,另外一位俄羅斯鬼才導演阿裡克謝·巴拉巴諾夫的《棺材200》和《鍋爐工》也有和《鍋爐房6號》的類似情節。對於一位把電影“演黑”的男導演,也許齊娜這樣的“無心插柳”反而來得更具殺傷力。儘管《三件事》上畫之後,齊娜不斷地說:“這只是電影,虛構的藝術。”但是正如當年西方電影界帶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去評價《衰弱癥》的情況一樣,齊娜的心聲,對於很多人來說不過置若罔聞。
《三件事》影评(四):《三件事》:齊娜·穆蘭托娃的“高尚小說”
◆文/熊仔俠©
之所以說齊娜·穆蘭托娃的《三件事》是一部“高尚小說”,也不全是針對昆汀·塔倫蒂諾的《低俗小說》而言。哪怕當初齊娜和自己的劇作朋友在構思《三件事》的時候,確實受到《低俗小說》的影響。但是“高尚”更多的是體現在電影之中本身的“犯罪的高尚”。前幾天,筆者就《三件事》的中文譯名和齊娜的電影風格作出了一個簡單的論述。當筆者讀完Jane Taubamn的《Kira Muratova》中關於《三件事》的詳細介紹和剖析的時候,更有茅塞頓開之感。確實,這部電影正如齊娜導演本身是說不完的。而筆者只能論盡冰山幾角,難免有所紕漏。而這篇影評依然是偏向“總括性”的,筆者也會在不久的時間里就本片中的三個故事再作剖析,僅供參考。
“探索”,“類型”和“艱難”:
在蘇聯解體前後,一大群本土導演肆無忌憚地將情色暴力一類的電影元素搬上屏幕,以挽回早被美國好萊塢驚悚動作片所吸引而去的觀眾的支持。只不過,這樣的“感官刺激”非但沒有挽回觀眾對蘇俄電影的支持,反而成為了蘇俄電影的“亂群之馬”,使蘇俄電影的質量遭遇滑鐵盧的慘況。而齊娜·穆蘭托娃在蘇聯解體前夕拍攝的電影《衰弱癥》一方面被稱為“宣判蘇聯映畫死亡的電影”之餘,又被稱為“黑片中的黑片”。儘管齊娜不斷向外界解釋這是一部探討“人性”而非“揭露”的電影時,眾多的國內外觀眾也置若罔聞。而西方電影界更是一直期待齊娜繼續創作《衰弱癥》式的電影。但是,蘇聯解體不久后齊娜所製作的《感傷警察》和《狂熱》卻讓西方電影界大失所望,甚至將齊娜打入了電影的冷宮之中去。而作為位於齊娜作品中間位置的《三件事》則是齊娜對電影類型的探索。一直以來,齊娜的電影一直偏向“無劇情”的風格。加之齊娜的骨子里就有一種不安分和不耐心的性格。於是她開始對“意識流”深感興趣,並要提出拍攝一部“有劇情”的電影。正如上文提及所提及的《低俗小說》的啓發,齊娜無意和美國的B級片作任何的較勁,反而關注到電影主題——“罪”的本質去。可以這麼說,《三件事》是齊娜的一部類型片。她憑藉自己獨特的電影語言和精通創造美化了暴力的本身之餘,又通過劇本和演員把人類“非人道”的一面表現得淋漓盡致。恰好,“被美化的暴力”和“角色的非人道”成為了電影由此始終的角力。正如電影一上畫所遭遇的各類批評一樣,《三件事》的拍攝過程也是充滿艱難。一方面是資金問題。儘管《三件事》是一部俄烏合拍的電影,但是當時經濟崩潰,國家資金也無暇顧及到每一部電影的製作上去。這無疑是當時橫亙在齊娜眼前的問題。結果,《三件事》在拍完第一部份《鍋爐房6號》的時候已經耗盡資金。幸虧得到烏克蘭奧德薩電影廠的資助,電影方可在1996年春天殺青,並在1997年2月中旬的柏林電影節上全球首映。另一方面是審查問題。當時齊娜把電影送到帕夫年諾克(前蘇聯國家電影局局長)手上。當帕夫年諾克觀看完《三件事》之後,他致傳真給齊娜,要求齊娜對電影作出修改和“必要的剪輯”。當然,齊娜一如在前蘇聯時期不可妥協的姿態一樣(齊娜在前蘇聯深受電影審查制度之苦),直接跟帕夫年諾克說到:“我總有一種來自蘇聯鄉愁,是閣下的傳真所致的。”就這樣,齊娜和帕夫年諾克鬧翻了,而電影差點也就流產了。這麼一說,齊娜當初將電影的名字從《憂傷故事》易名為《三件事》也就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來自資金和審查上的“艱難”還是映射出齊娜在后蘇聯時代拍攝電影時遭遇的困難不比蘇聯時代少。
電影中的歐俄藝術風骨:
哪怕《三件事》電影遭到不少“道德上的惡評”,哪怕在柏林電影節上與銀熊獎失之交臂(當年《三件事》和其他24部包括《英國病人》電影同時競逐銀熊),哪怕在俄羅斯索契電影節上毫無獎項的斬獲,但是依舊受到不少觀眾和影評人的好評,其中也不乏一大群文學評論人的推崇。其實也不足為怪。因為電影無處不透露著歐洲藝術的風骨。僅憑電影的三個短片的標題來說足以說明問題。《鍋爐房6號》是參照了契訶夫的《六號病房》進行創作。而《奧菲利亞》,顧名思義,則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的悲劇女角。而《小女孩與死亡》則是引申了音樂家舒伯特的第十四弦樂四重奏《死神與少女》的音樂名稱。當然,在每一個短片之中有著諸多這樣的“藝術細節”,筆者也會在分段影評中再加以剖析。在文學評論人對《三件事》的好評中不乏Oleg Aronson的評價——“電影運用了俄羅斯藝術中的前衛元素:謝爾蓋·愛森斯坦的電影蒙太奇和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形式主義文學手法”。愛森斯坦的蒙太奇享負盛名,在齊娜的拍攝手法中也就屢見不鮮。同樣,齊娜電影中美不勝收的鏡頭中也不乏“陌生化”的手法。齊娜一直運用象徵主義地手法將電影陌生化,同時也將理念訴諸于演員身上去,這也就塑造出“電影失實主義化的風格”(未來的分段影評會有詳細例子)。其實,齊娜將藝術,尤其是俄羅斯文學中的理念用電影手法演繹出來也不是一兩次的事情。在齊娜早期的作品《萍水相逢》和《漫長的告別》中,齊娜一度將巴赫金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提出的“複調”理論(Heteroglossia)用到自己的電影中去。因為電影本身具有語言演繹和觀眾受聽的特性,齊娜將“複調”運用到角色的對白,性格和思想上去。這也就創造了一種“開放的,多聲部的電影”,而電影劇情和角色的衝突也就信手拈來。所以觀看齊娜的電影和觀看塔可夫斯基,帕拉傑諾夫等蘇聯導演的感覺不同。齊娜從來就沒有為電影定下一個“終極的思想”,沒有通過電影對觀眾進行“絕對統治”。相反,一如她的“複調電影”本身一樣,觀眾也可以參與到電影中去,允許自己專屬的觀點融入到電影的角色和劇情中去。這同樣也把齊娜的“無劇情電影”解釋了出來。難怪,蘇俄電影界曾有人稱齊娜為“電影界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三件事》中,齊娜借鑒了果戈裡的小說精髓——笑中帶哭,為電影披上了一層黑色喜劇的外套。而齊娜的黑色喜劇也是從《三件事》中所開創的,以至後來的作品《二等公民》和《契訶夫的主題》也顯露得一清二楚。蘇聯電影有一個傳統。那就是“把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而齊娜將文學理念改裝成一種電影手法,無疑也是一種前衛而革新的做法。而這也是齊娜電影中其中一種魅力之所在。
在蘇聯六七十年代的電影界中有4位風頭盡露的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謝爾蓋·帕拉傑諾夫,米哈伊爾·卡拉托佐夫以及齊娜·穆拉托娃。比起塔可夫斯基和帕拉傑諾夫,穆拉托娃的創作生涯充滿痛苦的抗爭和無盡頭的打壓。這也就是她一直在國內備受忽視的其中原因。1986年,穆蘭托娃曾說到:“我知道自己的電影總有一天能重見天日,只是我沒能活到那一天。”在“蘇聯四幹將”之中的前三位導演先後離世之後,穆蘭托娃成為一位孤單的導演,繼承著蘇俄電影的遺風。只願在她有生之年,更多的中國影迷對其有更多的瞭解。而筆者也願為此奉獻綿薄之力。
《三件事》影评(五):《三件事·小女孩與死亡》:代際間的暴力暗湧
◆文/熊仔俠©
因為在《三件事》中的《小女孩與死亡》,齊娜在電影界遭遇了浪潮般的批評聲音。一方面,短片中飾演小女孩的莉莉婭正是其本人本名演出。不少成年人(尤其是家長)認為齊娜通過電影鼓吹兒童通過暴力解決問題。他們擔心電影中的“冷血兒童殺戮(Cold-blooded Child-murderess)”會為兒童提供心理暗示,不利於家庭和睦。另一方面的批評則是來自更為電影學術的層面上的。不少影評人認為齊娜的《三件事》是其內心“人性倒退(Retreat From Humanism)”的表現,也就趁勢對齊娜的其他作品大加評判,好不熱鬧。反而齊娜則是坐懷不亂,對外界宣稱道:“這只是藝術,不是現實。”當然,無論是《小女孩與死亡》,還是《三件事》整部電影來講,裏面確實摻和了齊娜更為之多的個人情緒和對過去和現在的電影審查制度的“報復心理”。筆者也只能說齊娜這個自尊心極強的老婆子確實不好惹。
而說到《小女孩與死亡》上去。正如上文所言,這是一部講述兒童謀殺老人的故事。其實這類題材在西方電影界也屢見不鮮,諸如西班牙的《誰能殺死孩子》以及美國的《玉米地裡的小孩》一樣。只不過與《小女孩與死亡》不同的是,上述兩部電影採取的是更為通俗和娛樂的手法去演繹。而齊娜和其本身“不合群”的電影模式無疑也是成為口誅筆伐者必須帶上的有色眼鏡。此外,就故事的劇情而言,小女孩莉莉婭拿老鼠藥毒死老人的情節和貝爾塔拉的《撒旦探戈》中的小女孩折磨小貓,最後將小貓毒死的情節類似。這不過不同的是,被殺害的對象不同。當然,齊娜對動物的極端喜愛也不會允許自己像貝拉塔爾一樣安排小貓被毒死的情節。反而短片一開頭,一隻大黑貓咬著剛宰殺不久拔了毛的雞的一幕則是齊娜自己喜愛的一大表現。這段“黑貓咬雞”持續了數分鐘才切換鏡頭。一方面是齊娜的個人癖好所致。另一方面則是一種符號化的標誌。齊娜借黑貓的兇殘的爪牙和低沉的呻吟表達出了人性内裏的獸性和兇殘。
而在這段結束之後,則是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男人驅趕黑貓。值得一提是扮演男保姆的男演員是Oleg Tabakov.他也是后蘇聯時代影壇裏面的大腕。當年,齊娜本來是在《小女孩與死亡》中安排一位女保姆。後來因為涉及到自己“男人的缺席”的電影元素,她便打了電話給Oleg,說要讓他扮演男保姆。而Oleg Tabakov本身的儒雅氣質也造就了自己在電影中的本色演出。作為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老知識份子,儘管身體殘疾,依舊對著到處搗亂的小女孩莉莉婭作出極為枯燥的說教和訓誡。特別是知道莉莉婭的母親專門在餐廳裡為自己的女兒偷來餡餅的時候,男保姆大為氣憤,認為這是盜竊行為,頻頻噴出“不能這樣!(Нельзя!)”的嘮叨話語。相反,身為小女孩的莉莉婭非但沒有尊重長輩,反而在長輩面前赤裸這身體,搞亂長輩的棋盤,搞砸長輩的私人物品。這無疑也使代際間的衝突不斷升級。正如男保姆所代表的老一輩知識份子階層一樣,小女孩的母親所代表的是工人階層。就蘇俄的歷史來看(尤其是蘇聯時期),這兩個階層的關係不但微妙,而内裏有著不可妥協的矛盾。不同於《鍋爐房6號》裏面的“被害女性”,也不同於《奧菲利亞》裏面的“施害女性”,《小女孩與死亡》中還存在著一個從未登場的“旁觀女性”。而這位“旁觀女性”則是通過男保姆和小女孩之間的對話表現出來,尤其是“媽媽偷餡餅”一事。另外“旁觀女性”(即莉莉婭的母親)則是影響著,甚至教唆自己的女兒(當然可以說她是教女不善,居然要一個老保姆看著自己的女兒)。當然,莉莉婭身上的刁蠻任性也是這位“旁觀女性”對其影響的集中體現。直到電影下半段,在和男保姆進行諸多語言上的暴力之後,莉莉婭最終“忍無可忍”,借著男保姆口渴的機會,炮製了一杯“老鼠藥茶”毒死了他(莉莉婭的獨角戲和《撒旦的探戈》裏面的小女孩有異曲同工之妙)。直到電影的結局,莉莉婭在取得勝利之後,得意洋洋地說道:“不能這樣!不能這樣!不能這樣!”。這也顯露出蘇俄知識份子的地位日漸式微,話語越發蒼白無力的階層現狀。這也是對《鍋爐房6號》中的兩位知識份子男主角作了一個前後呼應。而電影到了這裡也就落幕了……
:5篇影評終於寫完,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