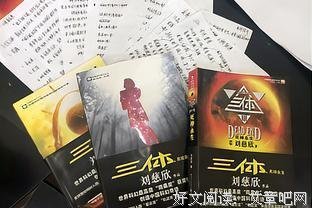《黑暗之城》读后感摘抄
《黑暗之城》是一本由Greg Girard / Ian Lambot著作,中華書局、圓桌精英出版的軟精裝图书,本书定价:港幣468元,页数:4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暗之城》精选点评:
●在一些人的眼中,它是前所未有的粗陋、绝望、邪恶;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它则有种前所未有的诡异美感。城寨是这个殖民地内的孤岛,人们为了摆脱贫穷躲进城寨,而城寨为了容纳他们,也不断成长。
●本来只是为了满足在美感上的猎奇心,结果发现九龙寨城不就是杨箕、共和、猎德、潭村……这些城中村嘛!有温度、接地气的故事,不再是传说中夸张的罪恶之城(另记录看完《20道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从业者碰上的不自由,和内地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呢。但特别是围绕14年事件的分析,十分清晰有理!哦,原来看新闻要关注这些点才能看出道道来
●我想读这本书 2016-01-25。0520。没有想象中好,但这应该是因为客观上的困难而非作者能力所限。对于纠正对于九龙城寨的过于浪漫化的形象(治安并不恶劣,警察巡逻、垃圾收集、电力等公共设施均存在),第一篇长文足矣。对住户的访谈照片部分较有价值,文字部分大同小异(自己什么时候来的,干的什么活,城寨还行啊),可挖掘性偏弱。《九龙城寨——本来面目》中关于城寨如有机体般自然生长的部分印象较深。个人较感兴趣的城寨内部社会如何组织、公共服务如何提供等有初步的解答,但碍于客观原因也只能止于表面。城寨已经解体,进一步的研究已然不太可能,就城寨的外在形象能在艺术创作中发挥的表现力来看,维持对城寨的浪漫化的想象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香港商务印书馆
●超棒的一本书,超酷的一座城,超有趣的一段历史。
●印刷极尽精美,照片多,文字集中写人物,寻常百姓的城寨生活可能比黑社会来得更超现实。寨内许多巷道终年接触不到太阳,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看窗外天色而是开灯。二战后不久西方记者的猎奇报道亦诉说着一种早在正常社会消失掉的难胞情怀。城寨建筑是鬼斧神工,同一个单位三楼可以比四楼大许多,证明楼宇是安全地倾斜着,一栋挨着一栋你不动我不动,直至最后都没有发生塌楼惨剧实属奇迹,另一奇迹是火灾的缺席,城寨内塑胶工厂林立,放满易燃物却经年没发生一次大火。现在城寨是一个弃置的公园,没有游人没有任何生趣的公园,大概这就是奇迹之后的代价。
●补记:今有重庆大厦,旧有九龙寨城,虽两者性格差异很多,但就香港城市研究的角度,都令人着迷。
●序言“回忆城寨并非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思考我们身处其中的空间."很棒的一本书。呈现了消失的九龙城寨。小家庭做糖果,铁笼露台和启德机场飞机飞过屋顶是最打动的照片。不管是理论陈述展开让人看到“九龙城寨”传奇化,以及背后真实的它,在历史九龙城寨的身份变化,还是赶在清城活动之前的拍摄与访谈所呈现的人情与温度,都实在让人喜欢。“浪漫的怀旧,也许是一种无法面对历史而生的感情”也斯这句也是说中了。
●“什么事情都可以在城寨内发生…它有可能将我们平日所接触到的香港社会的现实,完全颠倒过来,有另一套我们不太明白的社会秩序…”
●九龙城寨是一个贫民窑的极致,人口密度爆炸,建筑的朽败和密集已经到了科幻的底部,看了这些照片不难想象为何赛博朋克的城市雏形就是它。
《黑暗之城》读后感(一):消失于记忆中的飞地
自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了这块飞地,去过那个遗址公园后就迷上了这个黑暗之城。
很意外地找到了这本书,纠结了很久花了数百元买到了这本书,不得不说这本书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部分都相当负责任,语言除了编著者的动情描述外,还有大量曾经城寨居民的口述。
书对于寨城的介绍非常全面,从诞生到历史的错落,从鼎盛到被拆迁,都无一不体现于那些黑色的繁体字之中,那些收集而来的照片,让我想看到每一块像素点里都有怎么样的故事。
书本身很耐看,除了故事性和历史性兼顾的文字,还有一些难得的简易地图,可以一瞥大概,不过无论那座城怎么独立于纷扰复杂的香港之外,无论它怎样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无论它怎样让社会学家魂牵梦绕,它都随着历史而去,就像百年孤独里的那个村落,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仿佛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一样,美国漫画家博伊尔说,我宁愿他们拆掉的是埃及金字塔。
如果你爱香港,如果你爱历史,如果你爱建筑,如果你只爱你自己的生活,那就去看看这本书吧
《黑暗之城》读后感(二):有生之年系列
虽然是从摄影相关的分类下的链接意外发现了这本书(之前也并没有听过),但关于九龙城寨的传说,也是多多少少有所耳闻,但也正是这样的一知半解,甚至带有更多主观臆想的原因,才想要更进一步去了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局面糅合下诞生的独一无二的生态圈。
这里尽管独立于整个香港之外,中英港三方政治角力,但这里却和香港的发展紧密相随,换个不一定恰当的说法,城寨和香港都市的发展,都见证了香港经济的腾飞,这里也经历平房变高楼的巨变。
除了独特的历史、奇妙的建筑生态,这本书吸引我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书中有大量的生活在城寨里的老百姓的采访,真实而朴素,那些生活在里面几年、十几年,甚至两代人,虽然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但却让人很真切的感受到每个人那种面对生存的倔强劲儿,虽然环境不好,但是每个人做事也几乎不会昧着良心,这些普通人身上,亦有难能可贵的商人精神。
虽然香港如今也不必四小龙时期,但是香港始终是个让人着迷的地方。
《黑暗之城》读后感(三):既是黑暗,终会褪去
对生存的朴素需求和团结帮扶的传统文化,让黑暗之城野蛮生长!这里接纳了城市最肮脏的一面,也毫不吝惜地展现着现代社会最缺乏的人情味。
但是九龙城寨必然会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而消失,从社会的客观发展来看,法治社会和文明社会都不允许这样的法外之地存在;从居民的客观需求来讲,老一辈为了生存可以不在乎居住环境,街坊邻里的相熟和帮扶都让他们依赖这个地方,长时间的居住已经让他们与九龙城寨融为一体,这里不仅有生存的需要,更有精神的寄托。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开阔的眼界必然会让年轻人远离城寨,正如后来的年轻人说 “我也不愿只因为浪漫或猎奇而保存一个破落而无法安居的怀旧空间。”当城寨没有新鲜血液加入,必然失去了成长的动力甚至存在的理由!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当今的农村存在相似之处,当最后的留守老人离开,农村也将消失,大概这就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
但是,有的东西或许不能仅仅用来怀念,城寨消失了,农村城镇化了,曾经的团结、互助、诚信等精神却值得我们继承。
《黑暗之城》读后感(四):打死的野鸟歌声
看这本书让我对建筑的魅力产生了新的看法,或许非人类故意设计的建筑才更令人着迷,建筑是变动的、极富弹性的,人类在活动过程中的互动才是一个建筑存在真正价值。除此之外,书中对在城寨中不同职业群体的故事讲述勾勒出一张张下层人民的面孔,这些面孔在寨外人看来生活在水深火热、肮脏不堪的贫民窟,是可怜又令人难以接触的,但就生存所具备的基本要素(空间、水、空气)来看他们和寨外人并无区别,这个群体虽然有生存的挣扎,但同样也有生活的趣味和情怀。
学者作为他者的书写、城寨居民主体的故事讲述共同再现了九龙城寨的历史。每位学者所站的不同角度让我们了解城寨的不同面向。除了建筑方面的价值性,我更注重这本书的社会学色彩。
城寨的陌生化、恐怖性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他如何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元素?城寨作为微缩化的香港展现了这所城市怎样的颓废美感?书中不同职业的居民在讲述个人历史的过程中恰恰反映了城寨乃至整个香港政治、经济的变迁。
正如约瑟夫·拉康德在《海镜》里说的那样:“历史不断重演,但是一件毁灭了的艺术品的表现力永远不可复制,就像一只被打死了的野鸟的歌声一去不复返。”刨除建筑的宜居性,他本身所见证的历史是还原过去的最佳证据。当族群的标志性建筑被毁,那那段历史是否也成了任统治者随意揉捏的工具?
当建筑遭到毁灭化为废墟,那是该保存原貌,还是使其得到重塑?不同的是,城寨本身的恶劣环境足以让政府将其拆毁,但在如此环境下,仍有大量居民不愿迁出,对他们而言城寨是其生存的场所,也是身份、文化获取认同的重要空间。他们对空间的充分利用在某种程度上不恰恰是生机勃勃的表现吗?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做着不同的职业、体验着不同的生活,但每个人都值得活出自己的样子。
《黑暗之城》读后感(五):九龙寨城:安那其主义者的蛾摩拉城
九龙寨城,作为“赛博朋克”文化的象征,即使是在93年清拆结束之后数十年,全世界赛博朋克风格动漫、影视、游戏文化圈依然将其视为自己的圣地。Cyberpunk圈子之外,一般中国人却对九龙寨城少有了解。这本书便是在寨城清拆前夕的一次走访,制作组记录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影像,并且采访了即将离开寨城的各式居民:小店店主、医生、药剂师、小作坊主、经纪人、主妇、退休老人、理发师、机电技师、邮差、教士、救世军,甚至还有吸毒者。这些不同角度的描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九龙寨城。
九龙寨城的形成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在清朝时,寨城是九龙城的军事要塞和官府所在地。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租期99年,但九龙寨城除外。条约中规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这两句合约条文造就了九龙寨城特殊的政治地位:它名义上是殖民地之外的一块飞地,但各阶段的内地政府又不便事实上插手管理,这给寨城内部留出了权力的真空,使得九龙寨城成为港府和国府都无法插手的“三不管”地带。
然而根据大多数居民的描述来看,虽然寨城内部确实卫生状况堪忧,居住条件拥挤,但从社会治安上,民众的感受并未像人们普遍想象的“三不管”地带一样恶劣。只有在50年代,社会秩序被三合会所把持时,寨城的秩序才比较糟糕。后期,寨城的民众自发组织了巡逻队和仲裁委员会,维护寨城内部的治安、解决冲突和纠纷事件。虽然寨城是走投无路的罪犯所藏身之地,但据居民称,寨城内的犯罪率不高,遇到打劫的次数远低于他们曾经住过的其他寮屋区。
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安那其主义是实际可行的吗?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一个没有政府监管、仲裁、维持秩序和主导社会工作的社区,是无法良好的运转下去的。但是九龙寨城便是这种安那其主义顺利运行的典范。民众的自治组织代替了政府职能,而商业活动在人们自行维护的诚信体系下——而不是法律的监管下——运行着。我觉得社会学家绝对会想要仔细研究这一案例。
从更长一些的角度来观察,九龙寨城是香港,乃至中国城市内卷化的一个地理缩影。寨城就像一个有机生命实体,随着人口增加,它不断扩大着体积,向天空增长着,最终使得其成为97%部分都完全晒不到阳光的黑暗之城。总体占地面积仅0.027平方公里,3个足球场的大小,它容纳的人口规模从九龙被英国接收时的200人,增长到了清拆前夕高峰期的5万人。
在寨城最初被英军占领时,一直到日军占领结束的四十年代,寨城都有农田和畜栏的存在。随着日军侵华、内战的几波难民高潮,寨城的人口急速暴增,农田和畜栏从寨城中消失了。两三层的小楼房房取代了原本低矮的单层平房。随着人口进一步增加,五六层的楼房在六七十年代取代了原本的小楼房,寨城的外貌开始像广东在改革开放时出现的城中村;最后在七八十年代,密集扎堆的“大厦”最终取而代之,最终形成了九龙寨城那令人感到压迫的外观形象。
这种“成长”背后有其合理的经济解释。当人口涌入,新的更高住宅有利可图时,开发商会劝说居住在土地上的原住民卖出土地,或者换取新楼房中某几套房子的承诺,接手地皮兴建更高的楼房。而由于寨城是无政府主义的,几乎没有城市规划可言。所以单个地皮上的建筑会尝试着将地皮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值,而形成了寨城密密麻麻拥挤在一起的外观形象。
这恰好原生态的说明了内卷这一现象的本质——有限的资源,无限的发展。在恶性竞争下,个人的(居住)条件被推向极端。九龙寨城的生长高度是有上限的,若不是九龙启德机场所规定的高度限制,九龙寨城也许会进一步的向天空发展。
九龙寨城仅仅有三个体育场大小,当内卷化最终造成生活水平下降时,人们可以迁移出寨城。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内卷化竞争,人们又能向何处逃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