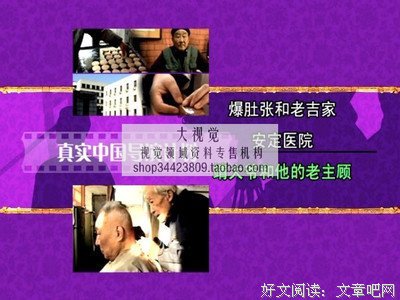《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经典观后感集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是一部由施润玖执导,靖奎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观后感(一):韩少功《青龙偃月刀》
何爹剃头几十年,是个远近有名的剃匠师傅。无奈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算一下,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他说起码要九百个脑袋,才够保证他基本的收入。这还没有算那些一头红发或一头绿发的脑袋。何爹不愿趋时,说年轻人要染头发,五颜六色地染下来,狗不像狗,猫不像猫,还算是个人?他不是不会染,是不愿意染。师傅没教给他的,他绝对不做。结果,好些年轻人来店里看一眼,发现这里不能油和染发,更不能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就打道去了镇上。
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这句老话都不记得了吗?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功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酥酥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吒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涌动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脏六腑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个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须眼角余光的照看。
一套古典绝活儿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仔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儿。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啊。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的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
我并不是抱着老北京情结看的这部纪录片,所以我并不能非常切身的感受到片子里所蕴含的老北京剃头的深厚传统文化,那是什么吸引我看的呢?或许就是那一幕场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颤巍巍的给同样颤巍巍的老人们理发的场景,我看到的,是靖大爷所坚持的剃头手艺的存在,他与其他老人之间那种联系的存在,他自己的一种生命存在,然而这些存在,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
“这老一套,根本就扯不掉”
片子的主角靖大爷是一位剃头艺人,从事剃头工作已经几十年,拍纪录片的时候靖大爷87岁。尽管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但靖大爷仍然骑着三轮车上门给老主顾们理发,一家一家的服务。冬天的什刹海,总是被定格在画面中,有时阳光洒满水面,有时水气缭绕雾霭阴霾,不变的是,靖大爷一下一下的蹬着车穿行,花白的头发整齐的梳成偏分,穿着十分朴素,一双球鞋,一个黑提包,这个黑提包就是靖大爷的“工具箱”,似乎也就成了靖大爷的标记符,而靖大爷无疑也成了老剃头师傅的标记符。
张耀新老人在理发的时候,说起了“绞鼻须”是老的传统,还有“刮脸、绞鼻须、掏耳朵”,靖大爷也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不行了,但是他们都坚持认为老人们还是喜欢这一套,毕竟这老传统。这是近百年的习惯养成,是一种抛不掉忘不掉的几乎与人合而为一的元素,就如靖大爷所说,“根本就扯不掉”。
靖大爷的剃头手艺的依旧存在,这是老人们生活的符号,来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可能即将消亡的一种生活状态。就如靖大爷所说,他的工具都能进博物馆了。因此,这执着的存在成为了一种对传统的仪式,来让传统尽量延续下去,让老人们珍惜的那种生活状态还能找到一点依存的痕迹。
在给老主顾们理发的过程中,靖大爷还和他们数次聊到了关于“拆迁”的问题,片子里出现的房子都是很老旧的样子,我们城市的变迁发展可能容不下这些陈旧……虽然片子里的老人们没有表现出对拆迁的不满,但从他们对剃头的坚持中,我似乎也看到了他们把过去、把传统、把生活投影到许多细小的事物上,一旦这些事物消失,应该会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吧。
于是想到去年外婆家装修房子,外公总是护着这个桌子护着那个柜子不肯丢弃,家里人则都是在半开玩笑半强硬的要外公妥协。当时我其实特别理解和心疼外公,虽然我被嘲笑怎么也有老年人的心态,只是想到了一句话:过去很长,回忆很多,承载的东西却很少。时光的河不可避免的一直在流走,人总是站在这河的浪尖,对于过去的光阴,只能回头看,而回头看,剩下的除了回忆,不就是承载回忆的那一张桌子,一组柜子……?
人出生时一无所有,死后什么也带不走,既然起点和终点都是零,那中间是什么?就是时光吧,多的或许有一百多年,少的可能只有几十,不到十,甚至更少,时光中都是回忆。光阴虽无刃,抽走留伤痕。当看不见的年华里,留下了那么些东西,那么些传统,他们就像长成了自己身体中无形的一部分,抽走后,或许人看上去还是那个人,没有少什么,但那空白感可能也只有自己体会吧。所以我愿意这么去认为,靖大爷是用坚持做剃头手艺这样一种仪式,让可能马上就要找不见的一切,起码现在都好好的在那儿,那一代人的过去,那一代人的回忆,那一代人的生活,那一代人的寄托……
“死完了完了,他们死完了我也就不干了”
一位穆老人,拍摄那年85岁,靖大爷在片子里给穆老人最后一次刮脸,出了屋子后靖大爷对着镜头说:“又完一个,死完了完了,他们死完了我也就不干了。二十来年死了四百多人了,都给剃跑了……”
这样的话语,顿时便给人一种从眼睛酸到鼻子的感觉。这就是靖大爷与老人们之间那种特别的关系的存在,同样是一种仪式,像是在互相陪伴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再用平凡的剃头刮脸,却也是老人们享受的方式,送他们走向另一个世界。因此,靖大爷与老人们之间不仅仅是剃头师傅和老主顾,更多的是老伙伴吧。
在片子里可以看到,每剃完一个头,老人们和靖大爷坐着一块儿聊聊天,抽抽烟。这种可能每月只一次的交流,却比日夜陪伴来得更有种不一样的温情。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没有意义,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意识到同样的话被反复说起,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和自己相似的老人,能听自己说重复的话,能懂自己说不明白的话。
靖大爷的老主顾们,看上去都并不富裕,甚至生活在底层。不过或许生活条件真的并不那么重要了,就像片子里的老人们说的,难道还比不上以前只能吃窝头的日子?但是比生活更贫瘠的,可能是老人们的精神,其中多少老人身边有人陪伴呢?就算有儿女,可能也不过是偶尔来看看,甚至还抱怨老人唠叨自己年岁不久。
有的孤独老人,只能因为靖大爷定期的光顾,而有那么一会儿的容光焕发。当老人向靖大爷说起自己的孩子,当老人说起自己与邻居相处的故事,当老人对着靖大爷用颤抖的嘴唇谈古论今,甚至当老人和靖大爷讨论又有哪家的老人不在了,他们内心一定知道这个老伙伴还陪伴在这儿,他们还在一块儿坚持。
那是赵明老人,得了脑血栓,一直被病痛折磨着。赵老人在片子中出现了两次,每次都带有一点恍惚的神态,第一次,靖大爷劝他喝点奶粉,吃点自己爱吃的东西。第二次,赵老人告诉靖大爷他还是不怎么吃东西,于是靖大爷继续劝他,等靖大爷走了,赵老人一个人却在屋里喃喃的说:“得了,又一天,又一天……”
又一天,又一天……赵老人的悲观让人难过,但同时也会为他庆幸,有靖大爷这样的老伙伴,还是能够被承认和鼓励,然后用这样的仪式,互相依靠着走过这剃落花白头发胡须的岁月。
在片子中,总是能够看到的是靖大爷和老人们在谈论生命,这里的“生命”并不是那么宏大的生命概念,而是老人们在几乎是生死边缘时对生命仍然抱有的一些想法。也许,到了那样的年纪,如那些老主顾一样,就像有种似乎看到死亡就在前方的预感。所以他们大多在静静的等待那一刻的到来,也不乏赵老人那样还带着悲观的心态。然而,我们也总能看到,靖大爷用他执着的方式,作为一种仪式在传递潇洒的状态。
靖大爷不断的劝老人们要多走动,不要总睡着,睡着起不来可不行;生活要有一定的制度,一日三餐要规律;心里头要抱有念想,想什么都行但一定要有想法,要自己对付自己,别等着别人来,要有心有茬的活着,要有信心活着。靖大爷认为“越老越没事儿”,他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想着好就行。
很早以前就读过,人到了一定年纪就可能会到达一种看透世事的境界,我不知道靖大爷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境界。但他的心的确已经很宁静,他每一次上门服务每一次剃头刮脸每一个周期的重复,被他坚持得就像修行一般。他不把事情往心里去,不争不介怀。靖大爷和几位老主顾都聊过,“现在吃喝不着急,旧社会那时候吃窝头吃白面都有时候,现在每天直白面,你还怎么着。”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心态的最好体现吧,人要知足常乐。
其中老主顾中最年长的是米老人,那时候96岁,精神矍铄,他跟靖大爷说:“思想没担负,不该人家不欠人家。一场大梦,一场大梦。过去做梦也没想活这么大岁数,现在活这么大岁数稀里糊涂了,什么都不想了,等着那一天了。”是啊,难道人生不过梦一场,世间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属于你的,财富、身体、爱的人……最后一切都会归于尘土,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借给我们的,我们都是时间里的过客。
在片子的结尾,剃头剃了一辈子的靖大爷却到街边理发,靖大爷表现得沉默低调,旁白响起:“也许靖大爷不想告诉别人他也是一位理发师。”对靖大爷来讲,多做点事情就多活几年,想不通就是受罪,想通了就是幸福。所以我想,靖大爷活着的状态也就是他对生命的一种仪式吧,一种我们同样要用生命去感知的仪式。
听说去年还有人去看望了靖大爷,依旧是潇洒的模样,如果现在老人家依旧如此,希望靖爷爷,长命百岁。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观后感(三):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
初一看,靖大爷无论是从外貌、穿着等当面都特别的像爷爷。满头白发,后背明显拱起了,棉袄的长度盖住了屁股,这点跟爷爷特别的相似,喜欢穿宽松肥大的衣服,身材瘦小,感觉整个身子躲在衣服里。10多年前的靖大爷骑的是三轮车穿梭在北京老胡同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公文包里全部是靖大爷的宝贝孩子,他细心照顾着它们,那是他的骄傲。又是他一生的伙伴,陪伴他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天,陪伴他看望一个又一个老伙伴。还是他的爱人,在相处间,靖大爷变得越来越有活力,心态越来越年轻,使他成为了那些老主顾们的心理导师。年轻时候的爷爷是骑个自行车,拿个公文包,穿行在山间小路中,在家和村委会途中奔波。在我心里,爷爷是劳碌命,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找些事情做,他的脑子一天24小时在运转的,像靖大爷那般,80多岁还坚持上门为他的老主顾们理发刮脸,我想他心里的踏实和有事忙的良好感觉远比5块钱的物质报酬让他满足了。每一趟回家,我都把自己当个小大人似的,在爷爷面前用大人的口气对他讲,少做一点,钱赚不完。多呆在家休息,少出去干活了,年纪那么大,身体最重要等等之类为他着想的话,看完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我发现我错了,老人度过眼下不多的余生,是一点也不想浪费在吃饭睡觉上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对老人老说太贴切了。孩童时期喜欢的无事忙,玩个昏天地暗。老人在还有劳动能力时,是闲不住的,或许是想证明还年轻,因为这个世上没有谁打心里愿意承认自己老人,有一个老主顾说到,谁都希望自己活着,有句话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老人希望有事做,有人陪伴,人越来越像个孩子,人的安全感是先上升,到底一个顶端之后又开始下降的,老人是跟孩子一样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当他有一份事情可以让他看到自己的存在时,安全感便会增加一点点。老人还需要个伴,不一定是伴侣,但一定是老伴,在年纪上相仿的人,聊聊天、唠唠嗑、斗斗嘴,面对死神来临时,心情是互相理解的。这让我想起其中一个老主顾,身体已经完全透支了,孤苦一人,与靖大爷的聊天中说到,就在等那么一天到来了。想想人这一辈子真的就这么一回事,年轻时,你可以千姿百态,可以肆意妄为,可以功成名就等等,在时间和死神面前,瞬间会灰飞烟灭。所以,人这一辈子,不管处于哪个阶段,都得有颗宽心,即装得下海水,也能让空气躲躲,还能让人类乱打乱撞。
靖大爷说:20多年400多个老人走了,说得我心都冻结了。有时候我觉得他像一个送葬老人,特别是有个场景,有个老主顾摔了一跤,差点去见了阎王大帝,靖大爷给他理发刮脸,导演是这样配词的,“靖大爷知道,这是他帮老人最后一次理发刮脸了,至少这样可以减轻一点老人的痛苦。”最后靖大爷说了一句,不洗了,留下次一起洗。眼泪已经模糊了我的视线了,因为谁都知道,再也没有下次了。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观后感(四):我认识他吧
暑假 一次和舅舅闲聊 说起我小时候的事 有一段就聊到了理发
我老家在西安 长安 儿时我们那里把男孩理发叫推头
小时候 经常呆在舅舅家 和外公外婆一起 从没上学开始到后来上学前班然后小学的暑假 那时和外公外婆在那座老屋有我记忆中幽深灿烂的童年 关于理发最早的记忆大概是在94年 那时候 小孩大是理小平头 稍大一点就是大平头 一把电推子和一柄小梳子足矣 完了给后脖子哪里铺一层痱子粉就搞定 男孩子理完的头型 从背后看活像馒头上扣一个黑色茶壶盖 理发一次都是五毛钱
而多年以后 我已完全不记得在外公老屋住时 具体在哪里是谁给我推头的
然后到今年暑假回家 舅舅说起小时候去推头的那个人还活着 他叫骡子 应该是个外号吧 店还在开 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吧 然后回忆一层一层铺开 我定定的
后来到开学前几天 我一个人摸到那个地方 去推头 看到那张条凳 十多年前坐在上面 十多年后又回来了
骡子问:“推什么样的”
“你怎么顺怎么来。。。”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观后感(五):所以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老人
21世纪初期的北京,刚开始大兴土木,1m多宽的胡同不是那么美好,道路两边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一层的待拆迁的破旧不堪的门面房。
敬大爷的老主顾们,少数年轻点的关心的是拆迁的事 ,老了的关心的是死亡,当然也有诸事都不关心,没有了想法的人。老人们的状态很多,患脑血栓,糖尿病 ,刚从医院出来弥留之际的一批,状态已经不好了,他们或许看到死亡在招手,那一双双颤颤巍巍不敢前行的扶着桌角的双手。另外一批不依靠人,自己还可以照顾自己,崇尚知足常乐,心情舒畅,与世无争。他们会记得旧社会里的苦,感叹新社会的好。有时候他们也会回忆过去梅尚程荀的艺术巅峰,他们怀念那些传统的文化,感叹一起的人越来越少。
看到这么多的老人 不知道作为儿女们该如何对待他们才能不那么心酸。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观后感(六):当何爹遇上靖大爷
老北京城里有这样一位老大爷,每天踩着三轮车穿街走巷地去给他的老主顾们理发。人们都亲切的称他为靖大爷。
靖大爷今年已经85岁了,但仍生得一副硬朗的身子骨,几十年如一日地踩着他的三轮为周边的大爷们理发。这些都是他的老主顾,他们享受着靖大爷的剃头手法。他们享受在靖大爷为他们提供的剃头、刮面、掏耳朵、绞鼻须这些传统的理发工序中。靖大爷的老主顾们说,这些老祖宗的传统现在那些年青人已经不会了,年青人不喜欢用这些老传统,但他们还是离不开这些老传统。
靖大爷依旧每天踩着他的三轮在老北京的胡同里转悠,但他的老主顾却越来越少。靖大爷每次只收5块钱,生活也越来越拮据。靖大爷说,人活着,想得开是幸福,想不开就是遭罪。他活着只是守着他的老传统,因为他的老主顾们都喜欢这套老传统。
这是纪录片《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讲述的故事。当看到韩少功的《青龙偃月刀》一文时,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这部纪录片。这是两个何其相似的故事,同是传统的剃头匠,同样固守着他们的老一套,同样面临着老主顾一个个离开人世,自己生意日渐萧条的景象。不同的是,靖大爷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何爹则被人认为是老顽固。
其实何爹何尝不是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不屑于现代的理发手法,他说现在剃头都不是人剃头,而是电剃头。他高傲,看不起那些只学两个月就自己开店理发的年轻人,更看不惯女人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他是个传统的老顽固,守着自己那老一套不愿革新。他又是一个可怜的孤胆英雄,固执地守护着他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
《青龙偃月刀》中韩少功用他独特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像靖大爷这样的老一辈剃头匠的故事。全文的语言独具特色,让人看后印象深刻,然后在这深刻的印象之中进行反思。文章开篇讲述何爹的生意越来越清淡是用了一串“脑袋”一词,让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而且韩少功从市井人物的视角描述这个故事,一串的“粗俗”语言让人看的会心一笑。这笑中,有嘲笑,有苦笑。嘲笑的是何爹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苦笑的是传统文化的缺失。
靖大爷这和他的老主顾们谈到这一套传统的剃头技术时很自豪地说,这些东西年青人都不会,他们做不来。大概何爹也会这样吧,不然他怎么不愿意给顾客染发烫发。这些他不是不会,只是师傅没有教过他,他只做师傅教过的活。
文章中最打动我的一段便是何爹为三明爹刨光头的那一幕。何爹见自己的老主顾许久没来,变亲自上门看看。而此时何爹见到的已是奄奄一息的三明爹了。何爹见着能听自己说说心事,能跟自己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聊到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老朋友的半条腿已迈入鬼门关,那种没落与伤感其实一两句话能说的清的。此刻的道别已没有任何意义,简单的“你放心”三个字中蕴含的是怎样的不舍与悲伤。于是何爹也不再多说,只是拿出他的剃刀,为三明爹最后刨一次光头,让他舒舒坦坦,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上路。
这一幕在《靖大爷与他的老主顾》中也出现过,靖大爷在为奄奄一息的老友剃头时,就像是在举行一场隆重的告别仪式。剃头、刮面、掏耳朵、绞鼻须••••••在完成了这一道道工序之后,我看到靖大爷眼角那抹不易察觉的泪迹。靖大爷说,老一辈的都走了之后,也该轮到我了。靖大爷的老主顾们一个个入土了,靖大爷也越来越孤单。
无论是何爹还是靖大爷,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想让自己的老主顾,老朋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受到人间最舒心的洗礼。
我想,韩少功应该是知道靖大爷这个人的,不然他怎么会塑造出与靖大爷如此相像的一个人物。《青龙偃月刀》中的何爹的故事处处散发着靖大爷的影子。但是,我们敬佩于靖大爷的手艺时并没有人会去批判他的守旧,我们只是尊敬他,褒赞他。可对于何爹,我们少了那样的敬佩,我们给予更多的是不解,是批判。我们会说他不思进取,说他是老古板。虽然那些习惯了老一套的老主顾们需要传统的剃头方法,但社会毕竟是发展的,发展新技术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旧的传统。虽然在看《青龙偃月刀》的时候我也会感慨于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传统文化的流失,但这份感慨远没有在看纪录片《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时来的强烈。也许影像的力量更强大一些,但是如此相像的两个故事,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
对于靖大爷,我怀着更多的崇敬的感情。敬佩他的坚守,敬佩他85岁地高龄还能那么精神抖擞穿梭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而对于何爹,我也敬佩他对于传统的坚守与传承,但同时我也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着这个人物。其实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对这两个人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其实这是两个人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就连个性也是那么相像。
当街边的理发大娘为靖大爷剪完头发后,靖大爷只是默默地离开,没有告诉大娘其实他也是个剃匠。在看《青龙偃月刀》是我就在想,何爹是在哪剪的头发。也许他也是找的一个街边小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那个剃匠拿着剪刀为何爹剪头发时何爹会一声不吭吗?我想不会。何爹受不了年青人剪头发不用剃刀,更受不了女人为他理发,摆弄他那颗脑袋。何爹是高傲的,他只觉得师傅教自己的那一套传统的剃头方法才是最好的,现在年青人那些吹拉烫染都是不入流的。他当然也不会沉默,他会与之争辩。也许这就是我对两个人物有不同看法的原因吧。靖大爷守着传统,不愿学习年青人那一套,但他并没有排斥年青人的理发方式,不会对女人拿着剪刀给人剪头发这件事嗤之以鼻。我想,这就是我会对这两个人物产生不同看法的原因吧。
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传统剪发工艺时代的现在大学生,我并不理解那些大爷们所说的最舒服的剃头方式带给他们的身体及精神上的舒适感。一直经历着现代吹拉烫染剪发方式的我也不觉得这种方式有什么不好。时代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飞速的发展也让老一辈们感到无所适从。
在“我”去找何爹理发时,何爹非常高兴且热情地招呼了“我”。“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但他却仍有他传统的想法。“我”又何尝不佩服他那套行云流水的传统刀法,但时代潮流并不会因为他那套炉火纯青的技艺而停滞不前。
我外公曾经也是个剃匠,我亲眼见过他拿着那把推刀为村里的人剃头。当时我的感觉是害怕,我总觉得外公那柄剃刀会刮伤了他手中的那颗脑袋。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的担心害怕一直是多余的,但是我依然担心着,直到村子里开了一家理发店,人们都跑去那家理发店理发,外公也就没什么机会使上他那套剃具。有时候外公会像个孩子一样哄着哥哥们让他为他们剃个头,但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脑袋交给外公。之后,我再也没见外公在人前拿出过他那套工具。
因为外公,我更理解何爹,理解靖大爷。他们都是被时代落下的一代。他们当然应该被尊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身上的那份守旧情怀。
传统文化自然该传承,但传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即时创新。何爹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靖大爷只能靠着自己一辈子结交的几个老主顾谋生,我外公干脆连剃头的工具都收起来压在了箱底。我们都知道他们对于自己这老一套的剃头方式的热爱与执着,但时代没有容下这些。试想几十年后,还有谁会记得推头、刮面、绞鼻须这一套。这不是我们不传承传统文化,只是我们需要更先进的新型文化。何爹说的对,现代理发离开了电什么都干不了,现代科技已然让人们对它产生了依赖,无法割舍,人们离开了这些现代科技寸步难行。但是这些科技却也令现代人的生活更方便舒适。
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何爹是个英雄,但站在时代发展的角度,何爹又是个固守传统的老顽固。文化需要适应历史潮流,只有能顺应潮流的文化才能长久的被传承,被保存。文化的传承不是自私的个人喜好与习惯,也不是简单的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它需要经过历史的选择与淘汰。显然何爹的老一套剃头方式并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愿革新的何爹自然也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那么伴随他的只能是孤单。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观后感(七):这年头可没几个人会剃头了
很平淡~
看着这一堆七老八十的爷们
本想着会不会有那些所谓温婉啊警示啊诸如此类的感动
最终,片子很还原的
把他和那些老头顾客们都纪录下来 放在那 塑起来 便似注入了时间的力量
每一次我们把它重温
津津有味~ ~
把这样的文化记录下来,很有必要
但是不是要继承下去
我不知道~
.影毕座谈会上,导演把主持人和提问观众噎得够呛,不知该说有性格还是2~
既然都来参加了这样的见面会,我觉得尽量要有个推广的姿态
直愣愣的 何必来呢
不过有位讲了5分钟都没讲清问题的哥们,换了我是导演,估计也晕
所以我赶紧撤了~~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观后感(八):15年前的生活
想起小时候,骑自行车半小时就能从城东头到西头,坐出租车超过起步费肯定就已经到了郊区。在乡下外婆家的时候冬天没自来水,还要去拉雪拉冰融了才有生活用水,洗澡自然是很不方便。所有的日子都是悠长琐碎无聊。
现在赚的钱超过了爸妈一辈子的积蓄,超过了我刚毕业时候的预想,但面对生活的无力感,那个焦虑……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爸妈还教育,生活平平安安就好,别总争啊抢啊,身体要注意,但看着现在上海的房价,他们也开始想当年那些积蓄如果早点给我买个房子多好。
靖大爷的生活离我们很近,其实也不过15年的时间,不知再过15年,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观后感(九):多少故事,終沒沒
很難想像自己也有一天會老到這個地步,老的對什麼都失去了興趣,只求簡單的三餐;老的逮了個人就歡天喜地的沒完沒了自己微薄的過去;老的連坐下都成了一種冒險。嘴顫,手抖,碎碎念,不自覺地發出囈語,都是老態。人是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動物,永遠不長記性,懈於居安思危推人及己。
但我知道,如果夠幸運,我終有一天會老到如斯境地,甚至更甚。
過去我很喜歡看人的一生的故事,一本書,或薄或厚,甚至幾頁,寥寥數語,跨過人一輩子的歲月,模糊了日月星輝裡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咬牙堅持,麻醉了讀書的人,人生本是苦寒。現在或者是我自己已不再年輕,看到這些,總有些於心不忍。到底婦人之仁,忍不忍的,平實的日子都是這樣過。年年歲歲積累的,緩慢重複的,到了最後就變成歲月的韻味,不可品,只有自己才知道。
02年的片子,早想看,一直找不到,今天抽空在YouTube上找到,已經15年過去了,片子裡的老人們,包括敬大爺,都不在了吧,想起來有些微涼。像是失約,再也沒有彌補的機會。像是我和我爸。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观后感(十):传递潇洒的人
终日生活在烦恼与无休止的社交中的年轻人们,完全不能感同深受地想象散沙状的个体如何在社会中正常地生存。简言之,孤身的高龄老人们的困苦,远超常人所能想象。最常见的表现是,老人们会在儿女们猛然倾巢出动来看自己时,总是提“我死了以后”、“我快死了”、“我啥时候死呢”这种听起来很“煞风景”的话题。子女们不爱听,甚至以愤怒对待老人,除了一部分是出于缺乏智慧的爱以外,占更大比重的原因,是不肯承认自己根本无法理解老人。的确,当人没有面临随时可能与死神握手的状态时,谁都不能感受到将死的预感,或说是生活濒临完结时应该保持何种心理状态。资深理发师靖大爷以87岁高龄,躬亲示范,告诉我们生活即将完结时更需要保持潇洒。对大部分自以为给老人带来重要东西的年轻人来说,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因为靖大爷本人是一个传递潇洒的人,他的性情和他的工作方式,像蜜蜂传递花粉一样,把潇洒的心理状态传递给一位又一位老主顾。
每剃完一个头,老主顾会邀请靖大爷坐下来一期抽颗烟聊聊天。在不同场景里,这样的对话总是显出多种一致性。与靖大爷年龄相仿的老主顾们都希望和这位老朋友聊上几句,一个月才见一次面,说来也未必能记住彼此的话,但有些话从靖大爷嘴里说出来,跟别人说的就是不一样。老人们需要老伙伴,只有老伙伴说的话,自己才能听得进去。他们需要的更多是这样的彼此承认的方式,并非其他各种名目的敬爱。在杨荔娜的《老头》中也能看到,老人们将同龄伙伴视为最能接受的倾诉对象。靖大爷总是跟老主顾们说,要经常起来走动,不要总躺着;心里要有念想,没有想法不行;吃饭要规律,生活要有制度。这样的话,每个老人的儿女都会在十几数十年中讲上千百遍,不过看起来效力可比靖大爷说的差了不只一点点。话从孩子口里说出来,就像幼儿园阿姨要求小朋友似的,老人都不爱服从;要是从老伙伴那儿听到,内容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好像吸收到一种力量一样。
靖大爷多少年里头能和这么多老主顾成为朋友,大家都离不开他,首先和他的为人有关。作为一位老理发师,他无论为谁服务,都保持优雅的礼貌,从动作到用语都反过来令顾客发自内心地尊敬他。搞服务业能做到这个地步,就是一种感情上的交换,而不只是“从抽屉里给我拿五块钱来”这么简单的买卖了。老主顾们也都记得回赠一句:“您受累了!”看这融洽的关系,怎能不让人羡慕?其次,当理发师多年,靖大爷深守行业规矩,说不到讲职业道德这么高的层次,但是他很明白做理发师就是应该和顾客成为朋友。等大家都老了,又添了一层老伙伴之间彼此依靠的感情关系。“二十多年,送走四百多位,都剃没了”,这话听起来真幽默,伙伴式的相对依靠超越了生死位置之间的张望。第三点,就要说到靖大爷的手艺了。片子里讲他手艺的老主顾有好几位,其中一位“爆肚张”全面概括过靖大爷的业务能力,说他的老手艺最全面,能“刮脸、铰鼻须”,这都是现在的发廊小伙不会的能耐。“刮脸对理发的人来说,最舒服了”,这估计是老主顾们选靖大爷这样的老理发师上门服务的最大理由。片子的末尾部分,我们看到一位病重的老人,已经无力坐起来了,躺着让靖大爷给刮刮脸,算在走之前再舒服一回,可见老手艺在老人心里的地位有多重要。
跟《老头》里的老人们比,靖大爷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和老主顾们之间都是老伙伴的同龄关系,服务员与顾客的关系更重要。靖大爷自己热爱理发这个工作,曾经也是为著名演员服务的“著名理发师”,有过自己的理发馆,这辈子在这行当里也算潇洒走过一回。除了练就了好手艺,交了好多朋友,他还非常清楚晚年继续上门服务对自己的生活有多重要。平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些老人,他们从忙碌的工作岗位上一退休,马上就很不适应悠闲的生活,孩子们总是说“您老栽花养鸟,跳舞下棋,看孙子,多开心呐”,孰不知这压根不是这些老人想要的生活。要老人作出改变何其难呐,年轻人都很难愿意改变自己,老人更没有这个必要了。靖大爷深知自己只有在毕生热爱的事业上才能找到最大的乐趣,也只有继续工作才能不断地和老主顾们见面,否则他和其他孤独又无事的老人一样,难免无聊。人心一空,身体就差,很快就剩数日子了。可见,“生命在于运动”,说的是真理。
最后还想感慨的是,如果什刹海不复存在,老主顾们必然不知所踪,靖大爷恐怕也乐趣全无。偌大的北京城,东西方建筑杂交混生,未必容得下这帮“需要走动,需要说话”的老人们。很多人跟靖大爷聊到拆迁,这是城市成长必然要见到的结局。即便后海胡同保留原样,居民们恐怕也早晚要搬走。世界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考虑到对这变化最敏感的人们,谁来考虑他们,怎样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可大多数人都情愿在青壮年时代装作自己是另一个人,老了再慨叹生死距离如此之短,想起从前悔不当初,这有何用呢?看看靖大爷就知道,我们很多人在很多方面,都实在太不潇洒了。千万不要再倦怠下去了。
关注纪录片,思考生活。请关注由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和UME新天地国际影城联袂推出的“真实中国·影院计划”。
http://dc.smg.cn/film-083.html
http://st1984pinglun.blogbus.com/logs/257573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