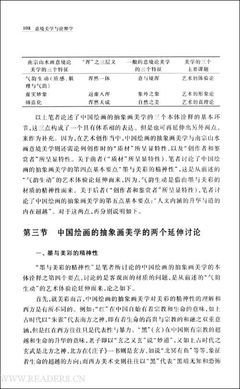现象学的观念读后感100字
《现象学的观念》是一本由[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元,页数:105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象学的观念》精选点评:
●105页啃了一个礼拜.........奶奶的!我看不懂!!!!
●跳过导读直接读这个实在是……回学校了还是要把导读找来看
●读前言后记书评,正文就翻翻,我不深究…
●胡塞尔是个矛盾重重的老头。最后成绩居然是A。泪流满面。
●读不懂…
●几近吐血,堪比纯批
●我偏打一颗星。
●拿着讲疏也看哭了,太虐了。
●读一遍,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
●很难,读的很慢
《现象学的观念》读后感(一):可亲的胡塞尔
胡塞尔的文字一直以来以晦涩难懂著称。这本作为其思想的导论性文章,论述层层细微,步步深化,无不凸显出胡塞尔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做人态度。而作为译者的倪梁康,不知道能否用“”化腐朽于神奇“一词来讲,将此作雕琢成了一幅散文式的图画,优美而可亲,敬仰。
《现象学的观念》读后感(二):现象学的入门
第二版序言中说,因为胡塞尔的学生无法从这5次讲座中理解他深邃的思想而感到非常的郁闷。其实老胡完全不用郁闷,看开点吧亲,没人能仅凭听1次就能懂的。
简单的说5讲中首先区分了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而后点明了认识批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引出了现象学还原。讲了本质直观和意识的构造。使得偶们可以进入现象学的大门。。
看完倒是给你了全新的视角,感受到了世界真奇妙。。不过,有些地方似乎吃不准,感觉是翻译的问题。。
《现象学的观念》读后感(三):发表一下我认为理解这本书的关键
凡曾涉足现象学领域,尤其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人,对现象学还原这个词都不会陌生。现象学还原在胡塞尔那里具有两个含义,其中一个含义等于现象学悬置(epoche),另一个含义是先验还原的含义,是要还原到先验主体性上去。现象学悬置的目的在于从自然观点向现象学观点的过渡。它意味着使那个规定着自然观点本身的普全存在信仰失效。然而只是如此并不足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哲学,它虽然提供了对抗相对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一种方法与途径,然而这种方法本身并未得到彻底的建基,就其基础的牢固性上来说,按照胡塞尔本人的话讲,这里还仅仅是“和心理主义在明见性的解释上发生了分歧”。由此现象学还原到先验主体性上去的任务,亦即先验还原的任务就是必然的,是由现象学悬置而来的深化、彻底化。而这本小册子就是论述了胡塞尔走上先验还原道路的心路历程。而从现象学悬置到先验还原过渡的部分,则在于本书的第二讲。我认为第二讲里两种内在和超越的区分是理解这本书的关键。两种内在和超越的区分对应于在后面数讲中频繁出现的实项的和意向的区分,这组区分在大观念里发展为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区分。我认为如果理解了这里实项的和意向的区分,那么对胡塞尔哲学中先验主体性的理解就不会错太多了。
《现象学的观念》读后感(四):认识何以可能(二):超越-内在问题的划分
“认识和认识对象的现象学”构成“现象学的第一的和基本的部分”,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划分和澄清内在与超越问题的模糊性和混杂性,建立一门严格科学( Wissenschaft)的哲学。
“哲学却处在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在开端还是在任何时候向超越的领域借贷,即把任何认识论建立在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做法都是一种悖谬”[2]25。胡塞尔对自然的态度和哲学的态度做了严格的区分:自然的态度是指由于科学自身的持续进步,它从来不考虑认识的可能性问题(the possible of knowledge ),胡塞尔称之为“自然态度的总设定(General thesis)”。近代以来的哲学却往往以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方法为楷模,而哲学要解决的就是自然科学无法解决、甚至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所以哲学不能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但可以汲取自然科学自身的那种严格性和一致性。除此之外,所有自然的认识、前科学的、特别是科学的认识,都是超越的、客观化的认识都必须被排除。因为它们“将客体设定为存在着的,它要求在认识上切中事态,而这种事态在认识之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被给予的,并不内在于认识。”
那么在自然态度的总设定下是哪些知识及其预设的方法论原则会带来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胡塞尔对此的回答可以重构如下:
1.自然主义不考虑认识的可能性问题。
1.1物理主义面对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通过修改观察或实验数据而保持理论形式的一致性或通过调整理论系统的自洽来融合数据。
胡塞尔的反驳认为:这样的知识论方法不考虑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而仅仅处理暂时的知识疑难。因此最严密的数学和数学自然科学在这里都不比日常经验的某种真实的或所谓的认识具有丝毫优越性[2]26。
1.2人本主义以认识对象来符合认识的主体,而此认识的主体却是经验的主体,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判断并无任何怀疑。
胡塞尔反驳认为;我们考虑的不是其有效性被局限在经验主体之上的纯主观有效的判断,而是排除经验的主体的客观有效的、即对任何主体有效的判断。先验统觉和一般意识对于我们来说将很快获得完全另一种意义,一种根本不神秘的意义。
1.3生物主义面对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认为知识只是一个进化和选择的过程,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表现了人种偶然的特性。
胡塞尔反驳认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可能性的这种真理难道不正是隐含地设定了矛盾律的绝对有效性吗?而根据这种矛盾律真理是不可能具有矛盾的。
所以,自然主义无法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
如果认识批判是一门始终想要澄清所有认识种类和认识形式的科学,那么它就不能运用任何一门自然的科学,它不能与自然的科学的成果和它们对存在的确定性发生联系,这些成果和确定对它来说是有疑问的。所有科学对于它来说仅仅是科学现象。把它同自然科学作任何联系都意味着错误的“越度”(μετάβασης;transition)。 我们从自然科学或者神经认知方面将认识解释为自然事实,以此来澄清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推移并牢记关于这种可能性问题的意义,就需要现象学的还原。
对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划分,追寻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胡塞尔在这里走的是康德的道路,而要回答认识、批判如何确立的问题,胡塞尔就转向了心理主义的解释和笛卡尔的道路,通过求助于我思的明见性而转而进入实项的内在和超越之中。
《现象学的观念》读后感(五):理性可确定性
观察,陈述?在科学那里是一种“正确的”方式,但哲学并不这么看。
科学是不关心“能不能被陈述”的问题的,在哲学这里这种思维被称之为“自然思维”,而哲学,研究的是自然思维“自然能不能被自然思维观察陈述”的问题,这就是“哲学思维”。它是对自然思维的一种反思。
翻阅各个历史上探索“本质”的著作,不难发现,所谓“理性”以各种形态,无所不在,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强调所认知的是“无须自证”之物。
在柏拉图那里,它被称之为“理型”,是一个简单的用于描述、认知宇宙的框架;在克里希那穆提那里,它被称之为“纯然状态”,一种不影响外物的自在状态;在戈雅的绘画那里,理性是各种邪恶的防护体。英语的理性一词为Reason,又意为“原因”,本身就不需要再进一步解释。在汉语里,这纯粹就是一个泊来词汇了,东方思维似乎一直就习惯于“模糊的”、“朦胧的”态度,以至于并没有一个相似的词汇可以描述“理性”这一状态。无论是其它的“理型”,还是“纯然”,都不是我们日常能用上的词。
所以东方思维在基于概念的上层出现的是“清谈”和“玄学”,而西方在基于概念上出现的是“形而上”和“现象学”。
接触胡塞尔的《现象学概念》是因为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中有太多的知识空白。阅读《现象学概念》又发现依然存在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空白。据胡塞尔在书中所言,现象学思想主要是基于康德而发展。此前阅读托马斯·泰勒的著作也是卡在康德思想介绍上。但我还是打算先记录目前的阅读理解轨迹。
现象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简单来说,它研究的对象是认知与认知对象之间的关系,它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认知究竟是否真的具备“可知性”,现象学认为,认知是一种“给予”,是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的一种“给予行为”。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颜色。汉语中说“蓝色”,英语中说Blue,西班牙语说Azul,见过蓝色并且知道“蓝色”的人会明白“蓝色”所代表的颜色,而不懂英语的人可能不知道Blue代表什么,但一旦说Blue并且指着一个蓝色物体时,他会明白Blue代表什么,但从来没见到过任何蓝色的人也许听说过蓝色这个词并且知道其存在性,但他并未真正认知到蓝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比如说瞎子,单凭借词汇是无法让他们真正“认知”。
这就足以说明,“认知”和“存在之物”其实是分离的。是认知主体“给予”了这些认知到“存在之物”。
所以疑问就出现了,即使是一些看似简单的道理,但真正要拿出一个有力的证明,即要表明这些认知是“理性”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更进一步抽象出来说,在表明“理性”之前,我们首先就要确证事物本身就是“可被理性认知的”,即理性认知可能性:我们的思维活动是如何正好和事物本身的规律发生一致?
胡塞尔提出了“先验、还原”的模式,将所有认知重新投射到存在之物去验证其真实性。这基本上是现在绝大部分科学研究的模式——从理论到实践。有趣吧?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现象学几个更有趣的例子:
1.时间构建的需要被验证的部分:回忆。我们如何验证回忆是否与当初事实偏离?
2.纯粹想象:我们可以想象出一种全新的颜色,但它是否真的能够存在?在古代东方思维中物质是“连续不断”的,在古代西方思维中物质是“有间隙的原子组成”的,谁才是和真实一致的?
3.存在与本质:蓝色物体是真实“存在”的,但蓝色光的频率是一种数字,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联系?我们该不该联系起来?
4.直觉:固定的思维模式,它的“断言”和最终发生的事实偏差度多大?
5.符号思维:在计算2 X 2 = 4的时候,为什么它与今天的天气无关?这是否说明思维活动在某些过程中具有“界限性”?为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理性是可确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