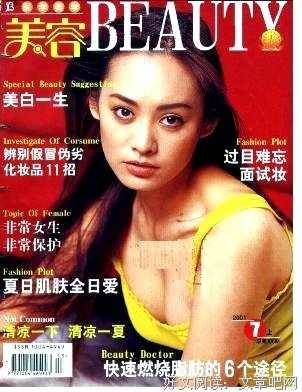剪紙读后感100字
《剪紙》是一本由也斯著作,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HK$ 60,页数:1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剪紙》精选点评:
●感觉大陆读者已经过了郭敬明时代的审美畸形,开始追求平实,而香港作家们文字里的诗意更多些。当然也许是我恰好只读了一派的作品:)
●梦呓般的文本,透过剪纸牵连的镂空与琐碎细屑窥见三十年前香港支离的幻象
●唉,这种读名作读不懂的感觉真是痛苦啊……
●也斯的语言和他的故事一样迷离,几乎破碎,读起来很不惯。所以看现代诗人的小说要小心,是么?
●居然可以这样写小说?句子不加标点符号来表现语言的失序和自我的错乱,也斯的句子写得也很漂亮,故事很有后劲
●真好。寡闻如我就没见过华语作家有谁这样组织语言的。山光水影花叶菩提,都见于字里行间了,且不止于此。
●看得有些乱 改日再睇过
●写得真好。
●是爱情吗 || 渐强的张力 || 生活的真实与幻觉 || 旧时香港怎么看起来像是今日 || 一时无法概括
●開首至中段甚具吸引力, 後半呈弱勢.
《剪紙》读后感(一):也斯《剪纸》
前1/2云里雾里后1/2爱不释手。故事没什么新奇,但语言的张力和魔力网罗生活场景,网罗人心各面向,网罗经不起解释和消磨的时代感和个人赖以生存的幻像,编织成不断生长蔓延的空间。不是文青不懂意识流不懂魔幻现实,不过很感动,很久没读到这么有魅力的文字了。作者刚刚去世,也希望他书写的香港历史,常给我们反省的机会,不要忘记,我们的根基,我们赖以生存和希望着的,是什么。虽然是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却很值得我们用现世的眼光去看。
《剪紙》读后感(二):剪紙
《剪紙》要說的東西並不容易說清楚,但文字所帶來的訊息會使人迷途卻真實得很。文字本來很真實,然而往往使人產生誤會,產生幻覺,於是溝通往往有剪紙般的美麗,但又使人費解,真而有假。
作者原意表現生活的幻覺,不過作品在最近的版本中明顯不只有這種表現。剪紙的象徵在生活描述中深化,涉及語言、文字所產生的隔膜,零碎的字句,容易被誤讀,因而遭誤解。也斯這部小說著力寫了一種當時香港人已有的生活面貌,對生活的幻想,對生活的誤解與扭曲,結果產生偏執。
小說的手法亦脫離現實主義,建立在意識流與魔幻寫實的框架上。小小的一部書,寫出人們生活中的迷惑,溝通的困難,意思的阻隔與偏離,成為人與人間的障礙。明顯地,這不是一部容易讀好的小說,我亦不敢說自己完成掌握每個細節,但幻想與誤解的表現則非常明顯。
《剪紙》读后感(三):诗人的通感之书
有的小说是这样的,随手翻开并未逐字阅读,不知内容为何,但一眼看到的都是漂亮句子。诗人写小说,随手一摘便是佳句,但也容易不擅于故事,情节简单。《剪纸》就是这样的小说,有他人不及的天才诗意,是需要等待知音的作品,不会走到人群中。
也许《剪纸》是思考香港文化的好样本。女子乔住在现代公寓,衣着入时,读不懂古诗;女子瑶耽溺于剪纸,时间对于她没有前进,而是一步步后退,心智已不在当下。小说中的许多元素确实可以加以解读,“我”和乔供职的娱乐刊物,杂志编辑们的故事,乔的寓所与瑶的家,乔收到古诗疑惑又费解,而“我”听瑶姐妹唱粤剧。即使也斯说这篇小说无意于对事件的看法,读者如果忍不住仅仅想要只往前踏一步地分析,仍会牵扯到文化上去。
我最喜欢《剪纸》的是它用灵动如诗的文字编织的沉迷。若是简单划分,那么乔是现代,瑶是传统。也斯写乔,并没有将她所在的环境描绘为冰冷单调的现代感,而是充满趣味与奇幻。到了乔的家,她递给“我”蓝色的红色的液体,“我”以为可以喝的并不能,“我”以为不能喝的又被洒掉。墙上画着红色的鸟儿,这些鸟儿可以飞翔又能够停留在墙上,乔拿方糖喂给小鸡。先入为主地会认为也斯对待传统的部分更深情,但他很多精妙的句子,都是出现在描述乔的部分。
而瑶从被书写的开始就已经耽溺于“过去”,她沉溺于剪纸这项古早的艺术中,不论眼前人事,只有在唱粤剧时才表现出正面的生机。除了艺术,“我”后来才知晓,瑶念着的见过的人,其实早已去世,那些事是瑶未曾经历过的历史。当“我”在情急中戳破瑶的幻梦时,瑶变得歇斯底里。直到最后,“我”还是无法让瑶回到当下,解开她的迷恋。
主角“我”身上也有迷惘。他读得懂乔收到的诗句,却无法全心去喜爱粤剧。他后来知道,同事黄单恋乔,从纸上剪下字来拼成诗寄给乔,黄以为乔能够懂得。这又是另一层迷恋的而无果的剪纸。“我”同情黄,看着他的生命日渐消失,看着他无望单恋,他人又无望地单恋着黄。小说以“我“的视角展开,”我“敏感多思,能够看到别人不能深入之处,却又做不到全然理解,也许就是这一点,”我“可以游走于乔与瑶之间。
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场景是主角供职的杂志社,“我“认为这本杂志尽是些意义不大的东西,同事形形色色,有人敷衍,有人认真。而那位认真的同事是偷渡客,其后失业去摆摊看相,他在看相时依旧是认真的。写到杂志社的琐事,过来人也斯信手拈来,同事间对话饶有趣味,他写黄”喜欢叶珊而不喜欢杨牧“。
也斯是最早把马尔克斯介绍到香港的一批文人之一,行文有受到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痕迹,尤其表现在初去乔的家,以及和同事在夜市吃饭描写充气的鱼、把水果和楼宇打成汁调成的鸡尾酒等等。但也斯没有故弄玄虚,《剪纸》优美而不艰涩,魔幻现实的描写是诗句的表述,与其说幻觉,不如说令人艳羡的通感。
《剪紙》读后感(四):《剪紙》的物體系
1. 語境
2003年4月1日,有關瘟疫的流言四溢,哥哥跳樓身亡,一切疑幻似真,香港剎時成了一個虛幻之城。懷著恍惚的心情,筆者依舊為「閱讀一本香港小說──《剪紙》舊夢新詮」座談會預備講稿,1 《剪紙》中的那份虛幻感,也就份外顯眼。這大概是本文的其中一個生產語境。
大約在座談會舉行的一個月前,筆者正在閱讀Elissa Marder的Dead Time: Temporal Disorder in the Wake of Modernity (Baudelaire and Flaubert),2 碰巧講者之一葉輝兄來電,邀約出席座談會,於是兩種異質的閱讀經驗,在偶爾間相遇了。
從前閱讀《剪紙》,筆者往往把注意點放在「溝通的困難」上,不管是小說中敍事者「我」與瑤、「我」與喬、「我」與黄,或是黄與喬之間,溝通都顯得困難重重。當然,正如作者也斯在《剪紙》後記中所言,《剪紙》「原來是想寫七O年代中葉香港生活的種種幻象」,3 但可能因為當時年紀小,當年《剪紙》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溝通的困難。
但溝通為甚麽會困難呢?也斯在後記中提到,《剪紙》不僅是一個愛情故事,也是一個有關觀看的故事,而兩者又是相通的;因為一個人對愛情的態度也好,對藝術的態度也好,都跟他的人生觀有關。4 「所以故事裹某個人看到或看猤到某件事,用這種或那種文字符號表達自己,自然跟他們各自是怎樣的人有關」。5 換言之,溝通之所以困難,在於不同觀看方式、人生觀,甚至人與人之間的差落。
此外也斯也提到,「文字/符號」本身便充滿了游離猤定性,故此「文字/符號」本身已為溝通帶來了無可避免的雜音。6
然而,對於Dead Time的閱讀經驗,卻為筆者提供了另一種析解以上問題的可能性;並猤是Dead Time釋放《剪紙》,也猤是《剪紙》引証了Dead Time中的某些論述;而是兩者的偶爾相遇釋放了筆者的視角。
Elissa Marder提到,在《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的第一章,作者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花了猤少篇幅描述一件似乎沒啥實際用途、也沒啥敘事功能的物件:「帽子」之細節。7 說也湊巧,重讀《剪紙》,筆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剪紙》也充滿了型型種種的物件。於是,筆者一邊在閱讀Elissa Marde對《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一邊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剪紙》對物件之處理上。當然,Elissa Marde的分析並不大適用於《剪紙》;但在重讀《剪紙》的過程中,它卻啟發了筆者以「詞與物的關係」以及「物件-符號」(Object-sign)的概念,整理《剪紙》中的「物體系」;而這些又與小說中的「溝通的困難」,密切相關。可以這麼說,本文希望從一個唯物的角度(Materialist Stance),提出另一種對《剪紙》的解讀。
當然,「物體系」(Le systeme des objets)也是一個借取自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字眼。8 然而,形迹相似,內函卻不必相同,還請各位留意。不過,跟布希亞相似,我所指的「物體系」並不是一個黑格爾式(Hegelian)、窮盡一切、且秩序森然的體系。與黑格爾式的體系相反,在《剪紙》中,不同的「物件-符號」是擴散地分佈的,之間不一定擁有有機的緊密關聯。但細讀之下,我們又不難發現,《剪紙》的確擁有某種特殊的「結構機制」或「結構化程序」,讓小說中的「物件-符號」得以連結起來,從而生產出一個獨特的「物體系」。
2. 詞與物之間的轉換
簡言之,《剪紙》的一個基本「結構機制」,正是「詞與物的關係」,或更準確地說,是「物件與符號」之間的某種特殊的關係。
當然,《剪紙》中有不少片段,都涉及符號與現實間的關係及差距的問題。然而,我希望討論的卻不是這種有關「符號與指涉物」之間關係的問題,而是當「詞變成物」或「物變成詞」時所產生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會發現這兩種「詞物間的轉換」同時存在於《剪紙》之中;而正是這種種的轉換,構成了小說中種種「物件-符號」的游離不定,讓小說中的人物之間的溝通,困難重重。
然而,我所謂的「詞變成物」與「物變成詞」,指的又是甚麼呢?且讓我先以《包法利夫人》的片段作些說明:
我們有個習慣,一進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好騰出手來;而且帽子非得一進門就扔,從凳子底下穿過,一直飛到牆腳跟,揚起一片灰塵;這叫派頭。9
透過建立「扔帽子」這個習慣,這班學童形成了一個社群;而對於他們,扔帽子這個動作有實際作用(騰出手),也有意指(mean) 作用:它意指此時此刻這個學童社群,也讓這個平日活在紀律規範的社群,能有片刻的解放及歡樂。在這裹,物件變成了符號,讓身體解放。但這些得到了片刻自由的手,很快便要回到常規的學校作業,抄寫拉丁詩句(一種以已死的語言寫作的詩句),將符號空洞化,轉化為物件(一種具有交換價值的資本/商本),以維護社會秩序。 10
回到《剪紙》的文本,我們發現小說的確充斥著類似的「物件與符號間的轉換」關係。比如說,小說中的瑤孜孜不倦地把紙張剪成種種剪紙,就是「物轉化為詞」的一個明顯例子;因為透過剪刀,瑤不單剪出在現實中有對應物的熊貓、小鹿等剪紙,也剪出了代表中國傳統價值的「物件-符號」,並形成了一個不為外人理解、自足的符號世界。
當紙張轉化為符號(剪紙),就有意義產生、傳遞及接收的活動;但透過這些符號,我們又不一定能夠真正理解到符號背後的意義;當符號變成了一堆不為外人所理解的東西,它不過是一堆無法產生意義的物件;小說中的敍事者「我」,一直希望透過瑤的剪紙符號世界了解近日變得反常的她,但這些符號卻一直對他閉上大門;在這裹,當「符號變成物件」,溝通也就變得困難。
這種「詞變物」的過程,也見於黄匿名地給喬奉上拼貼詩句的溝通過程上。在敍事者「我」看來,不懂如何表達情感的黄,不過是借別人的詩句,向喬表達自己的思慕;但對於完全沉緬於西方文化的喬來說,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原本是溝通媒介的這些符號,在喬的眼中,也就與物無異。
3. 傳媒這種魔幻文化工業
其實,這種「詞變物」的過程,也不單見於個人關係的層面。我們知道,《剪紙》的其中一個特點,正是對當時傳媒一類的文化工業,作出了貼身的描述與反省;而上述那種「詞變物」的情況,也見於傳媒的運作上。例如:
林問黃:「這兒植字稿比字位長了,怎麽辦?」黃看了看,說:「趕時間,不要移位,刪去這段算了。」林說:「可以嗎?」黃說:「這類星座的東西,誰會認真看?多一個少一個星座,沒人理會的。」馬接口說:「你們曉得嗎,有一回我拼好了版,才發覺在一段稿後面有幾百字空位。沒有圖片可以塞位,結果隨便找份婦女雜誌剪一段下來,塞在文後,結果誰也沒發覺有甚麼不妥!」他呵呵大笑起來。誰也沒發覺,球星生活和婦女美容的兩段文字之間,有甚麼猤連貫的地方。「所以,」他下一個結論,「你只要不留下空間就是了。反正老闆是外國人,他並不懂中文。中文版的雜誌,他只要圖片多,內容有沒有意思不要緊,只要不觸犯法例就可以了。」……11
在這個機械可複制性的時代,「物件變成符號」,「符號變成物件」,物件與符號猤斷生產與繁衍,好讓資本主義機器得以大量消耗,然後循環再造、再繁衍與再消耗;而符號也就變得游離猤定,溝通也就變得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在《剪紙》中,當符號被生產之後,它們很多都好像擁有了一種獨立的生命,它們的意義巳不在它們的生產者以及接收者掌握之內。符號被生產,彷彿擁有一種變幻莫測的自身生命。
依此,《剪紙》中的「魔幻寫實主義」就似乎不單是一種借自拉美文學、用來描述七十年代中葉香港生活的種種幻象的技巧,它也是這個機械可複制性的時代的一項隱寓(Allegory);12 而它隱寓的,正是在這個符號社會中,符號彷彿擁有了自己的生命,如脫韁野馬,變幻莫測,不為人所完全掌握之情況。
另外,我們又可以稱這個過程為「詞與物的辯証」:當物件變成符號,符號又可能會變成物件,而且還可能是擁有自己生命、永遠逃逸的「動」物。
2003年9月3日修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003年4月6日,筆者有幸參與「閱讀一本香港小說──《剪紙》舊夢新詮」座談會,而本文則根據當日講稿修訂而成。除了筆者,當日講者還包括王仁芸、洛楓以及葉輝。
2 Elissa Marder, Dead Time: Temporal Disorder in the Wake of Modernity (Baudelaire and Flaubert).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也斯著:《剪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頁138。按:本文以牛津大學版為引本,而《剪紙》的初版(1982)則由素葉出版社出版。
4 同註3,頁139。
5 同註3,頁139。
6 同註3,頁141。
7 同註2,p. 96。
8 布希亞著,林志明譯:《物體系》。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
9 福樓拜著,周希克譯:《包法利夫人》。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2000),頁35。
10 同註2,pp. 103-104。
11 同註3,頁22-23。
12 這裏所指的「隱寓」取自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的有關定義,用馬國明的話說,那就是﹕「象徵和隱寓的分別在於前者的意義是清晰自明的,象徵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完美和諧(的)……隱寓卻只是隱寓的作者自己替事物加上意義,中間的關係並不清晰,亦不穩定」;見馬國明著:《路邊政治經濟學》。香港:曙光圖書公司(1998),頁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