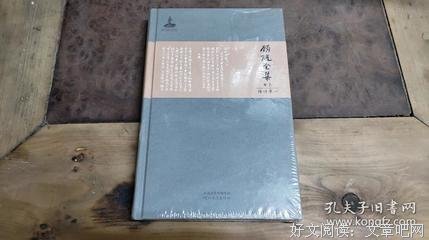顾随全集读后感精选
《顾随全集》是一本由顾随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45.00元,页数:20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顾随全集》精选点评:
●先生写文立身,乃吾辈典范也!
●叶嘉莹的老师,顾的词不错
●高中时代读了很多很多遍,非常动人,也恐怕是我成为直男的核心契机之一。顾随,直男中的直男,专与历史上的文学直男契合,所以讲老杜苏辛这种直男讲得奇好,带点儿女性气质的就次一点,只能用直男思维揣摩,但因为聪明之极,还是能讲出独到之处来,他人不可及。可以说是民国芥子(?
●讲稼轩尤其好,就冲这一点我就爱苦水先生(你也喜欢稼轩对吗!喜欢稼轩我们就是朋友!)。很棒很棒很棒的书。
●建国以后顾老先生也只好去赏析毛主席诗词了…然后退而训诂,再退而读起了《修行道地经》,再不能吐槽了…哎,明明原来是个只看得上陶渊明杜甫辛弃疾的高冷男神…
●读了第三卷
●大师们的老师
●苦水~
●把词集看了。积木词到解放前好,此前文字功力不足,此后不解释。
●国图四点的阳光
《顾随全集》读后感(一):我们是一伙的
回北京的飞机上读顾随,看他说陶渊明,然后回头看了看窗外白云,默默的流泪了。
我感他的诚恳,感他的纯净和野蛮,君子坦荡荡,感他对渊明穿越时空的心心相印。
读书读到穿过文字,和作者赤诚相见,有肝胆相照的念头,这是无与伦比的快乐,孤寂,私密,美好,似乎以前只有读薇依的时候有类似的感觉。当然,读薇依是有赞叹而有愧,又有自我清洁的愿望。读顾随则是寻找到先行者埋下的食粮,固然可口和窍要,也证实此行必不虚往。欣欣然走去罢,一句诗“到死誓相寻”,顾随说,做学问,求知的人,要有这样的心。
所以,我们是一伙的。
著述卷开篇讲稼轩,说起幼时学语伊始就颂唐五七句以替儿歌,六岁于中夜脱口吟哦诗篇,虽黄口小儿,雍容气势其可想见,我又是羡慕,又是欢喜。
《顾随全集》读后感(二):一个世界的风雨都在身外
顾公常说艺术要余裕。读古诗词,读顾随才真有这个体会。不知怎的看得特别慢,因为珍惜每一个字。读时好像一个世界的风雨都在身外。读完看窗外春雨不知今世何世。
O5年辞职的时候,在家看《顾随文集》,如珠如玉,循循善诱,幽默调皮,回味无穷。我以前说《蒲桥集》,也说“如玉”,但两者不同。汪是意象上的明丽,文字间的蕴藉。顾随是文学评论家,一个做理论的评论家可以“如珠如玉,回味无穷”恐怕很难想象是吧,顾先生居然就是这样的。那时好朋友怕我辞职心情寥落,打电慰问。我说我读到一本好本呢,废寝忘食,兴奋死了,哪里有时间来“寥落”。
顾先生是河北省清河县人,清秀,白衣瘦长,玳瑁边眼镜,和苏师兄很像。前两天看欧阳应霁《回家真好》,里面有一篇采访江哓原,留影一幅。江书桌上堆着《顾随全集》,我心里一动,同好。
周汝昌忆往,说当年恩师顾随提携他,鼓励他研究红楼。我心里只叹余生也晚,不能亲炙其学。更叹顾先生留给周汝昌的红楼评论在文革中遗失,如同后四十回的那种痛。
王璞曾说:“做艺术评论的人必须比一般读者高一层,不仅要明辨优劣,而且要知道它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为什么。最难的是,怎样把这种很微妙的感觉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让他人和你一样欣赏到它的好。”
我只举顾先生评论的三个小例子。一是评李义山的《雨夜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此诗如燕子迎风,蜻蜓点水,方起方落,真好。‘君问归期未有期’句后,若接‘情怀惆怅泪如丝’便完了,义山接‘巴山夜雨涨秋池’好,自己欣赏玩味自己。欣赏玩味外物容易,欣赏自己难。义山此诗有热烈感情而不任感情泛滥。所以诗人当能支配自己的感情,支配便是欣赏。‘涨’非肉眼见,是心眼见。后两句绕弯子欣赏,把感情全压下去了。太诗味,不好。感情热烈还有功夫绕弯子?冲动不够,花样多。”
二是比较杜甫和陶渊明,曹操父子:
“老杜也曾挣扎,矛盾,而始终没有得到调整,始终是个不安分的灵魂。所以其诗中挣扎奋斗比陶公鲜明,但他的力量比陶公并不充实,并不集中。老杜也有其痛苦,但是说了不能做。”
“诗人之伟大与否当看其能否沾溉后人子孙万世之业。老曹思想精神沾溉后人,子建是修辞华丽,是眼官视觉。曹子建无深刻思想,只是视觉敏锐。”
三是顾公论思想:
余之所谓思想乃从生活得来的智慧,以及对生活所取的态度。既不能禁止思想,就要使思想转出点东西,不使之成为胡思乱想。
《顾随全集》读后感(三):语录
顾随有些文字语近佛家语录,有人说他的讲录真好,自然也因他的著作所遭的厄运。还有他的不轻易发表自己文字。四卷本全集有一卷即为叶嘉莹所作课堂笔录。我向来不喜欢节录文章,这次来选些片段,不知道自己有没做得小心。
驼庵诗话
一、诗句不能似散文。而大诗人好句子多是散文句法,古今中外皆然。诗,太诗味了便不好。如李义山《禅》: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真是诗,好是真好,可是太诗味了。
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黄鹤楼》)
芳洲之树何青青。(李白《鹦鹉洲》)
似散文而是诗,是健全的诗。
二、创造新词并非使用没使过的字,只是使得新鲜。如鲁智深打戒刀,要打八十二斤的,铁匠说,“师父,肥了。”“肥”原是平常字眼,而用于此处便新鲜。
三、“三百篇”富弹性。至曹孟德四言则锤炼气力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步出夏门行》)
可以此八句代表曹诗。曹操四句将大海之雄壮阔大写出(写大海曰“中”曰“里”,看大家诗不能吹毛求疵),然仍不如“三百篇”之有弹性,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陶似较曹有情韵,然弹性仍不及“三百篇”。此非后人才力不及前人,恐系静安先生所谓“运会”(风气),及自然之演变。
四、平常说写诗写成散文,诗不高,其实还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诗为诗中散文最高境界。
《饮酒诗》“有客”一首的前两句: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似诗的散文。
五、俗说“他乡遇故知”。难道他乡人不是人吗,但总觉不亲近。
一个诗人有时候之特别可爱,并非他作品特别好特别高,便因他是我们一伙人。
六、中国诗最俊美的是诗的感觉,即使没有伟大高深的意义但美。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若连此美也感觉不出,那就不用学诗了。
七、辛稼轩的《满江红》(家住江南)不是大声吆喝着讲的。
“家住江南”,一起便好,尤其是“又过了,清明寒食”,什么都没说,而什么全有了,清明寒食对得起江南,江南也对得起清明寒食。好像只有在江南才配过清明寒食。说“家住北京”便不成,没道理,这是感觉。
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人相轻亦由自尊来;而以理智判断又不得不有所“怕”。欧阳修曰:东坡可畏,三十年后不复说我矣!东坡又怕山谷,盖山谷在诗的天才上不低于东坡,而功力过之,故东坡有效山谷体。而山谷又怕后山,后山作品少,而在小范围中超过山谷,故山谷又曰:陈三真不可及。
驼庵文话
九、蕴藉不是半吞半吐,不是含糊、适可而止,不是想不做,也不是做不了、干不了。蕴藉是自然。痛快与晦涩皆“力”,一用力放,一用力敛。
十、六朝时人性命不保、生活困难。文人敏感,于此时读书真是“苦行”,而于“苦行”中能得“法喜”(禅悦)。别人视为苦,而为者自得其乐。
太平时文章多叫嚣、夸大,六朝人文章静,一点叫嚣气没有。
十一、六朝人字面华丽、整齐,而要于其中看出他的伤心来。
《世说新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皆可看。《洛阳伽蓝记》漂亮中有沉痛,杨衒之写建筑与佛教实写亡国之痛,不可只以浮华视之。
无论弄文学还是艺术,皆须从六朝翻一个身,韵才长,格才高。
十二、读《史记》注意其冲动,不是叫嚣。注意其短篇。
《论语》六讲
十三、天下伟大的人没有一个是“自了汉”的。中国儒家末流把君子讲成自了汉,人不侵我,我不犯人,甚至人侵我,我亦不犯人,犯而不校。把自己藏在小角落里,这样也许天下太平,但现在世界不许人闭关作“自了汉”。
《文赋》十一讲
十四、小孩写什么都是“非常”,这是避难就易,因为他思想贫弱,字汇简单,人该避免用“非常”、“特别”、“十二万分”等等。
十五、“爱好”两个字真美,真是幸福。“爱好”是一件最美的“东西”(太具体),一件最美的“事情”(爱好非动作),爱好是最美的观念。每个人都该有其爱好。一个人活着必有所爱好始不致上吊、跳井、自杀。
论王静安
十六、现代青年人心中有苦不说。心中未尝没有,虽不见得欢迎,但不怕。精力饱满前途光明,有苦也不怕,有也能打破。觉得寂寞压迫最甚者,一个是小孩子,如失掉父母的孤儿。小孩子该是活泼泼的,无论其做事、淘气、讨厌,红脸上没寂寞痕迹。没父母的孩子做事安详、有分寸、斟酌,真寂寞。
《顾随全集》读后感(四):脉望馆书话 之 :听顾随先生谈诗论词
其实顾随先生的著作也算买齐了正安适地在书架上注视着我,河北教育的《顾随全集》虽然偶有失校错了些字词,但也称得上俊朗挺拔,其他几种零散著述也各有其芳华所在,最可宝的是一大本手自笔录的《驼庵诗话》伴我度过不少晨夕朝暮。讲诗词如果没有顾随先生,不管多么辽阔无边的天空将总会无端的缺失很大一块。
认识顾先生很偶然,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向身后满布的叉道开始不自觉的回望。
大学的那个旧楼图书馆很像个地下室。走下转角的楼梯,昏黄的灯光,伴着自己的足音,空空地响着。时常会有大门紧闭,空手而返的经历,这时大概算最为丧气的时候。我总觉得是我发现了这里的秘密:相对于新馆而言,这里文史类的老书特别多,当然不是什么善本,在卡片室的一格格小抽屉里常常会有填写着民国多少年,或者香港某某出版公司字样的小卡片像一条条红金鱼令人惊喜地游出来。顾随先生厚厚一册文集就是偶然在这里瞥见借出的,在此前只透过张中行老温煦雅驯的文字初识了这位身后寂寞的学人,却并不知道他的境界会有如此高妙,会令我一生景仰不尽。记得的是他写给张老的诗,是和东坡的黄州诗,(作于癸巳年,即一九五三年,《全集》本作误五二年)
“三年病垂死,今兹佳眠食。周命方维新,着意自爱惜。相看两白头,静好鼓琴瑟。细雨洒春城,山中乃飞雪。柳垂风有姿,桃开寒无力。朝来水边行,西山头更白。
二月已清明,余寒势渐已。高柳覆丛篁,一庵大城里。西州花已繁,明湖茁新苇。友朋与弟昆,妙词书茧纸。孰云隔形影,天涯若邻里。长吟动肺肝,既卧再三起。 ”
内敛,精严,有力,我甚至觉得好过东坡的原作。
直到手里拿着这部繁体直排的孤单的书,才发觉自己已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知的领域。世间竟然有这样的一种讲诗论词的东西。好像毫无系统,三言两语,却都能直指诗心,豁然开朗,直觉上很像禅宗的语录,像《五灯会元》,《指月录》一类,尽可能少的借用文字障,来捕捉言外之意,象外之形。其时的心几乎可以用狂喜来形容,海盗偶入宝山之欣喜或者与之相差无几吧。当下即开始动笔钞录,边读边钞,钞来再读。寒假甚至把他背回了家,辗转一千余里和陈寅恪的《寒柳堂集》挤在饱满的行李小包中,挨了母亲一顿埋怨。
钞到手软,仍只是冰山一角,眼涩指乏之际,不禁心生恶念,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据为己有算了。当然开学后书最终还是还了回去,却一直恨恨不已,陡然间竟觉得和唐人传奇里的“章台柳”有几分相似了。
接下去就到了二零零零年。那年的五一节,春雨如丝,远游未成,乃赴书肆闲游,不经意间竟见店内精品柜中四册《顾随全集》翩然望我,顿时心为之颤,目为之眩,只疑莫非梦境。乃疾驰携归,摩挲再三,方觉心定神凝,全集本较上古版增辑颇多,若书信日记,小说散文,尤以书信最见先生风神。
读先生诗词,取现代三数家词风相较,自家面目立时显现:沈祖棻《涉江词》清丽温婉,俞平伯《古槐词》繁缛缜密,郁达夫词哀感顽艳,换言之,沈作清而丽而婉,俞作清而缛而密,郁作清而凄而哀,沈似冯延巳李易安,俞似周清真吴梦窗,郁似成容若黄仲则,风神各异而气味仿佛,皆文人词之俊品;而苦水词风大异众人,朴质拙野之风大盛,似陶渊明,以平常语入诗,得自然醇真之趣,且多蕴哲思,又添几分宋诗骨力嶙峋,若啖橄榄,咀嚼不尽。拟之同时诸人,气味略同者恐惟知堂之杂诗,二人同在“野”与“拙”上使大力得大自在,然其间亦有分水处:知堂诸作几无门户可窥,走王梵志寒山拾得一路,苦水终不脱文人气韵也。其作敢面对肯担当,是以集中几无吟风弄月怨花伤柳情绪,倒是颇有四五分板桥老人道情味,此又非一般文士孱弱无力可比也。
诗词已是如此境界,论诗之语辄更见精彩,虽然只是转录,但就如同《论语》一般,高明的转录对原作而言也许并非是嚼饭喂人的尴尬与缘木求鱼的呆板,反而却会是水乳交融的和谐与酿花成蜜的清甜。叶嘉莹先生的听课笔记无疑就是现代学术史上的精要一章。顾先生述而不作,大半的精力都放于课室之内。但见得菩萨低眉,法相庄严,把三千缘法,向台下诸生细细道来,只恨不能早生数十年,哪怕做个旁听生,如此耳濡目染些许年月,还怕不成正果?
既然梦回不了那时的辅仁,只好辗转纸页间,借叶先生灵心妙笔,去含英嚼蕊一番,同时草此小文遥奠身后萧条寂寞的顾随先生。
漫题讲记卷端
大道叹多歧,世味从来苦;且以酒独斟,窗下常自足。远山暮色横,归鸦啼难住;昏溟灯火夜,填词供笑语。语既多酸辛,心安肯担负;如舟藏山壑,有力搬运出。生本为忧患,历历目皆睹;愁来仔细吟,夜尽天自曙。不信无繁花,春草成尘土。
《顾随全集》读后感(五):日记卷简述
全集中有日记三,《寻梦词》、《弄潮手记》(第二册)、《旅驼日记》。
《寻梦词》是顾随在河北某女师学院任教务主任时写的日记,从一九二七年新历八月廿九到十月七日。时顾随三十岁,已教书八年。日记中主要记录教书生活、自填词、与友人游这三个类事。记日记和写词可能有同样的感觉,都是因为无所事事才做的,“但又无事可做,于是便写日记。”(九月十二日),但写词顾随是真的喜欢,睡不着的时候(九月十九日、廿一日)、走着吃着枣儿的时候(十月二日)。
就教书来说,可能顾随还有别的抱负未实现的,有一则是这样说的,“鲁迅的《华盖集续编》二二六页有几句话:‘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这几句话,早已看到了。直到今日,才感到是千真万真。自己教了八个整年的书了。倘若这八年里面,拼命地去读书作文,虽然不敢说有多么大的成绩,然而无论如何,那结果是不会比现在还坏。”(九月五日)而实际上,顾随到了五十余岁也还在教书的,尽管那是也会对教书偶有怨言。
顾随比较喜欢鲁迅翻译的日人作品,但他自己日文不好,虽曾经学过,现在却忘记了,“当年曾学过三个月的日文,但,不要说是现在忘记,即在学时,也并未曾学到一个字母。”(九月九日)尽管如此,同月十三日又有记,“每日的傍晚,每周的土曜”这样的话。就日语来说,顾随大概多多少少还是记得一些的,只是日记说话夸张了。
再者,友人来信、回复友人信,似乎是那个年代或者那个年纪日记中常有的要记的内容?文中会写“味庄有信来”(八月卅一日)、“A君仍然没有信来”(九月四日)、“公纯书来,已复”(九月五日)、“A仍无信”(九月七日)、“得家书,即复”(九月八日)、“晚得伯屏信”(九月十七日)、“致伯屏、因百各一函”(九月廿日)等。
《弄潮手记》是顾随一九四八年记的,其时五十一岁,只两个月,十月到十二月。较二七年的日记,此本中多了天气记录,是人的年岁渐大对于天气的感受也渐增的缘故吧,毋宁说是岁数大起来了,耳鸣、臂酸等已纷纷来。此时之日记中更添搬家、联合罢课讨薪等日常事情,有两则记叶嘉莹寄来卢季野氏所印曲七册事(十月廿八、卅一)。又有一则“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烧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十二月四日)
就教书而言,“比来不读书不作文,只安分做教书匠,自觉精力尚可支持,然亦甚无意义矣。如何如何!”(十月十五日)但又似乎顾随是容易在教书时“兴奋”的,“然授课时亦时时留意不欲过兴奋”(十一月卅日),“上午辅大有三小时课,虽体乏而竭力不使自己兴奋。”(十二月二日)。也有时引以为傲的,“回思在中法上课,所讲汉诗之优点及劣点,亦颇感堪自信,惜不能自写语录。”(十二月三日)。“上午辅大有三小时课,偶尔忘其所以,遂至兴奋,归来觉疲。”(十二月十一日)那时候的学生对于顾随的看法,顾随自己亦有揣测“自家是旧时代人物,所教者为古典文学,现代青年即欲了解亦无从,则其心目中之物此翁亦宜也。”(十二月廿三日)
作为1948年年末几月的记录(盖集中于十二月),亦可以知道北平解放之前城中人的样貌以及对于解放一事之态度。如十二月十四日传闻辅仁大学将迁台、十五日的青年撕中共“安全注意”、廿一日师大上课只三数人、廿三日的街巷人家中皆住有兵士或军人眷属等。
这本手记与《寻梦词》有很大不同,很多记录天气之寒冷的,访客、事务之多之繁的,家庭买面买煤的。总之可以感到,生活之不容易与顾随之老。“废时失业莫过于闲谈,即谈道论文已属浪费时间与精力,况其他闲言语乎!此意难以告人,聊于此发之。”(十一月廿八)
又一,今日刚刚看完周一良译的《折焚柴记》,就看到“周一良、邓懿夫妇来…与之语颇兴奋,赠以年来所著词曲及杂文。”(十一月廿一)微妙的书航遇故交般的感觉。
《旅驼日记》是接续着《弄潮手记》的,记一九四九年一月到四月的事情,一月时也能看到北平解放之前之后样貌。但实际,市民可能更多关心的贴己的生活“报载近二、三日电灯可大放光明,企予望之”(一月廿三)。二月十九日始,顾随边便开始从《史太林列传》了解我党了,后又览看了《斯大林传》、《苏联哲学问题》等书。
匆匆读罢这三本日记,实际上那个平常模样的人会更加清晰而非他们说的“顾公”、“顾先生”之类。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在生活中产生诸多疑问,有时自己解决不来,有时突然又开心起来。也常在疑惑为何不能心如止水,也不能勇猛精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卅一日)。如果能不去上课,他会十分开心,如果多发一些钱来,他多包烟也好。我读出来了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一个在五十岁就已经身体状况糟糕的人,一个过分关注于天气与温度的老人。
这里似乎有很多我不能道出的智慧与哲理。(来自于顾随日记的记叙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