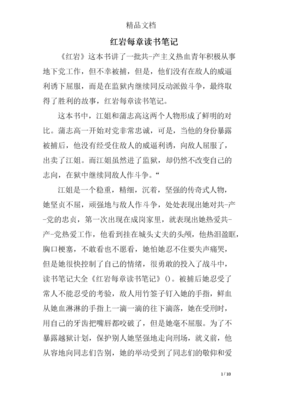电影书写札记读后感100字
《电影书写札记》是一本由[法] 罗贝尔·布烈松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00元,页数: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电影书写札记》精选点评:
●有必要把布列松、巴赞和周传基的电影理论结合起来学习。布列松的电影如行云流水,不经意间,有种内在的翻云覆雨涌上心头。有声片后,电影渐渐地被戏剧套牢,而在布列松的电影里却多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124:56|
●这本书是她的,现在是我的,可是她已经走了
●早年读的时候觉得写得挺有道理的,但现在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了。
●自成体系
●是“电影书写”,非电影“书写”;研究布列松必备。
●“为满足期待而创造期待。”“因要跟随果。”反舞台剧比较像新浪潮。模特儿达到布列松所要求的能够抗拒表达的冲动,运用机械性动作把情绪完全封闭于自身境界的难度绝不亚于方法派演员所谓锤炼演技。布列松出于自己的艺术标准而对于模特儿的剥削控制比一般演员受到的大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布列松也比那些平庸导演独断专行得多。当然,这也是出于追求艺术精益求精的必要。
●电影道德经
●不管到哪都一直伴随我的札记
●我的天,我想我终于明白picasso的呢句世界名言:“我不寻找,我发现。”是什么意思了。塔在《雕刻时光》里反复提到这句话,也提到布列松之凝练之简约。我也终于明白塔为什么说:“一个导演如果在拍摄中还在寻找或是探索,那他就完了”(大意是这个)实在是太享受这种阅读的过程中突然醍醐灌顶之前疑惑的时刻。感谢布列松。布在书里专门写下的一句柯罗的话:“不应寻找,应等待。” 布,塔,毕加索,柯罗以及蒙田他们共享着同一种语言。
《电影书写札记》读后感(一):一把小提琴足够时,绝对不要使用两把。
此书中。他主要强调几点:
1、模特。而不是演员。要清除演员脑子里的任何意图。保持导演的绝对控制权。演员不要去表演。要生活化。要“由外向内”。这一点就像“表现派”的理念一样。通过演员的数以千计的模仿重复、机械地动作单元练习。进入到角色精神层面。
2、绘画与音乐。将两者高度融入电影书写之中。房子、田野、树木,都可以成为“说话的方式”(张艺谋说过,一颗被拍进去的小草,也是有生命的)。
3、戏剧与电影。布烈松非常反感把戏剧元素融入电影。他以几乎决绝的词汇说,戏剧是相信与不相信。 电影是持续相信。可见,他觉得戏剧过于夸张、艺术化、集中化。电影是生活化的。是要更贴近社会与自然的。
《电影书写札记》读后感(二):布列松:先去感受才去理解
周末的睡前开始翻,第二天用了小半天看完。精巧的笔记。摘录4条:
1、电影书写的影片:感情的,非再现的。(P60)
2、诱发那出乎意料的。等待它。(P60)
3、你以清晰、准确的东西迫使那些涣散分心的眼睛耳朵专注起来。(P60)
4、观众正准备好先去感受才去理解,竟有许多影片向他们展示一切,解释一切。(P71)
最近学写作,google了很多辅导文章都讲一个原则“SHOW,NOT TELL(秀,不要讲)。不论是电影,文章还是写blog,都有同样指导意义。要不断学习练习提高SHOW故事的能力,提供能首先让人感受的文字,然后再帮助读者理解。
先摘录,周末做个完整书评。
《电影书写札记》读后感(三):摘录
控制准确性,让自己成为一件准确的工具。
不可有执行人员的心。每拍一个镜头,要在我已有的想象上觅放新盐。即时创新(或再
创新)。
自然:戏剧艺术将之泯除,为求一种学来的、并靠练习保持的自然感。
认为做一个动作、说一个句子,要这样子而非那样子才更有自然感,是荒谬的,在电影
书写里毫无意义。
一个影象接触其他影象时必须发生转化,如一种颜色接触其他颜色时那样。放在绿、黄
或红旁边的蓝不是相同的蓝。没有艺术不含转化。
压平我的影象(如熨过一般),而不减弱它。
一把小提琴足够,就不用两把。
拍摄。把自己置于无知和强烈好奇的状态,但仍要事先预见事情。
热中于恰当。
愈成功,愈容易失败(像一幅绘画杰作很容易变为七彩图片)。
不用音乐伴奏,承托或强化。完全不用音乐。
声响必须变成音乐。
原地深挖。不要溜到别处。事物有两三重底蕴。
由静止和静寂所传达的,要肯定俱已用尽。
你的影片要让人感受到灵魂和心,但要像手艺般制作。
让影象的亲密结合,使他们充满感情。
不要灵巧,要灵活
《电影书写札记》读后感(四):二死三生——影像话语的涅磐?
电影作为一种舞台剧的再现,重重地蒙扼了摄影机的独特性。在上世纪30年代正当罗贝尔·布烈松丢掉画笔,准备用镜头绘色世界之时,电影还是一张死灰色的脸。而对布烈松来说电影就似梦般新鲜神往,他说“我梦见我的影片在目光下自己逐渐形成,像画家永远新鲜的画布。”他不是要创造景致绝伦,而是暗扣着莫扎特的机宜:他们华丽出众,就是不够简朴。现在知道布烈松与古典主义毫不相干,他绝不赞同死一般凄丽的艳艳夺目,他要的是生灵活脱的“眼睛放射的力”。
“我的影片首先在我的脑海诞生,死于纸上。”这约莫是他离开绘画的理由,“我所用的活人和实物使它复活,但这些人和物在胶片上被杀掉。”这大概就是他所言的“舞台剧和电影书写结合只会共同死亡”的另一译本,“不过,当他们排列成某种次序,放映到银幕上,便重现生机。”合上这几抄断语,就是罗贝尔·布烈松的“二死三生”,不妨敷衍为电影话语的蘖磐。于是就有了此处陡立着的创造的另一面:由《乡村牧师日记》以至《武士兰西诺》。从《贞德的审判》以迄《金钱》,川流不息的影像以其充沛活力,到处留下的轻巧的痕迹、闪耀的灵光。
这样的道理,比爱森斯坦蒙太奇更要深刻些。所以我惊讶一个画家的直觉和敏性。直至今天再经典的,再时髦的都重返到往日的旧馆,心有嘁嘁地做些照本宣科的动作。卢氏兄弟创造此种魔术时,人们看到投影出来的树木也会惊讶,“因为叶子在抖动。”而《骇客帝国》你惊讶吗?《十面埋伏》会惊奇吗?先别摇头,先得想想为何。
《午夜之后狂恋》是去年意大利的时髦片,具备了该有的近似法国浪漫,仿似侯麦的笔法和意大利的情怀。票房如何,我素不过问。这是一部小成本制作,在可以重温电影旧梦的电影博物馆,男主人公义务守夜,他热爱影像世界,不爱说话,他的世界里就像每天晚上温习的黑白默片,没有话语,只有画面。好象布烈松的笔记,关于静止和沉默。整部影片将过去的影像和现实对接,偶有出彩之处,文字也铺盖得很多,有些地方未能尽领其意。然而这样的作品是确有温情,而与电影本身无关。于此种种都像在罗贝尔·布烈松的“二死三生”原则里迂回潜行。《午》片有来自戈达尔的形式感,确切些是戈达尔2001年自称最出彩的《爱的挽歌》,导演在片中对格言警句和历史文化资源的索引和挪用非常密集,主人公经常在玄思冥想中喃喃自语:“当我想着这么事的时候,真正想到的却是其他东西。比如我想到一片崭新的风景,它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我早已把它和之前见过的景色作了一番对比……”,或者“应该是感觉产生事件,而不是相反。”(罗贝尔·布烈松)。同样频繁的是打断叙述的小标题,它们像急促的呼吸一样不断的,反复的出现,提醒着观众眼前发现的一切是关于什么的。即便是《天堂电影院》与电影的关系也并非像有些影评所说的那么曲折缠绕,最末的几十个接吻镜头的拼接,也像在做着“二死三生“的游戏,只是前有伏笔,又有年华老去和隔世的情缘,来得恰到好处,陪着流泪的人也就多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众正日甚一日地依赖“中介”回溯过往,他们要求最小的信息量和最直接的满足感以对历史做最简单的解读。布烈松的“二死三生”就便得神奇而管用,影像话语的蘖磐在某种催生力下诞生了。我们感叹过去,感慨现在,感伤未来。
《电影书写札记》读后感(五):电影中的“逻辑哲学论”
布列松的《电影书写札记》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言辞凝重、意味深远。
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演员要尽力按照导演设定角色的要求来表演、展示演技,而由于演员不可能真正成为他欲表现的那个人,因此演员这个概念中必定含有矫饰、伪装、虚假的一面。出于这个理由,布列松弃用了导演/演员的二分,而改用电影书写者/模特儿两者的互动,电影书写就是把影片的创作看成写作——影像和声音就是这种写作中的文字,而非对表演的摄像复写(下文还会继续阐明)。
在电影书写者的视域中,模特儿代替了原来演员的位置,他不再受到导演意志和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表现自己的本性,或者利用自己的内在特性走出导演在外部虚设的角色,相反地,导演在创造、修改角色以及调度场面时却要服从于模特儿的言语和动作。模特儿内在个性、本性的差异性,恰恰是塑造角色的天然动力。甚至可以说,每个模特儿天生都是一个独有的角色。
当然,剧本、角色肯定是先于模特儿存在的,否则模特儿的行为就是任意化的。那么,模特儿怎样在一个先定的框架中展现其真实的存在方式呢?布列松采取了一种比较残酷的手段来实现模特儿言语、动作的自然化,就是让模特儿们在某一情节片断上重复排演,期间不断调整他们的姿态、话语声调,让他们变得更像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模特儿完成的是从外向内,或者说外在角色迎合内在本质的运动。
布列松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是影像。他认为应当把影像本身看作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体现在与其它影像的关系中,所以影片的本质在于影像重组。影片的意义就像一块磁石,把众多的影像吸引过来变成一件作品。这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一脉相承:只有在与其它事物/对象的联结中,某一事物/对象才能为我们所思考,而提供联结方式的是一些不能怀疑,或者称为解释终点的逻辑概念,它们与事物所在的形式、特性直接相关,比如该书中提到的明暗、颜色、空间位置、距离、运动状态。同样地,单独一个影像对于影片也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有和其它影像组织到一起,形成一种影像的流动状态时(也即在影片的放映时)才被赋予意义。既然如此,影像所指涉的人、实物、布景、道具也是缺乏意义的,它展示了一种物质性——事物和模特儿的本体。
当然,影像毕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的“事物/对象”,它还是有内容的,但是影像的内容过于丰富,反而会损害最终的影片,就像磁块和磁针相互吸引而失去了基点,作品也因此失去了形态、意义的确定性。
布列松既然把影像看作绘画的色调、钢琴的琴键、文本的字符那样的艺术原料、工具,那么他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影像本身,正如画家无法创造画笔、色调(但是他可以发明画笔,调制颜色)、作家不能擅自造出汉字,艺术家不能怀疑创作工具本身。这样看来,影像之前的剧本创作、模特儿的活动、拍摄只能看作一部电影的微观史。在一部电影的历史构成中,导演根据模特儿自身的特质修改纸上原始的构思,模特儿则按照导演新近的要求进一步回返自己的能力、个体状态,甚至表现他们隐藏的部分,用布列松的话来说,就是“相遇”并相互“照亮”,这是一种找寻共同话语,达到心灵默契的过程。
布列松还有一些极有启发性的论断,比如“剪接影片,就是把人与人、人与物用目光连结起来”,“影片不是拍来给眼睛浏览,而是为了让眼睛进入,让人完全投入其中”。由此我想到,摄像镜头应该代表片中人的目光,而不是导演的或观众原始的目光,这样才能让观众进入影片中。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