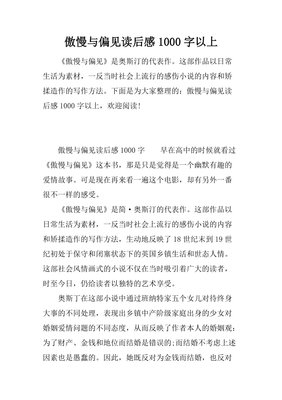未被摧毁的生活读后感1000字
《未被摧毁的生活》是一本由李伟长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未被摧毁的生活》读后感(一):关于后记、獾先生的小屋和走过的以及将要走的路
有一段时间,我的电脑桌面主题用的是“Warm Winter Nights”,这组主题一共有16张壁纸,16张壁纸清一色都是在积雪荒原里的温暖的独栋小屋。我幻想着自己就呆在这样的屋子里读书写作,心头会涌上一阵奇妙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李伟长老师的这篇后记中所提到的獾先生的小屋,和我幻想中的冬日小屋几乎一模一样;獾先生要躲在小屋里冬眠,而我就幻想自己是在房间里观赏着窗外雪景的宅男。我生活在南方城市,很少有雪天,更不曾见过积雪的荒原,而我对冬日小屋的幻想其实是一种在荒凉和寒冷之中寻觅一方安全感的想象。我并不是没有想过从这样的小屋中走出门,在我的想象中,我踩着积雪到小屋所在的小镇上去串门,或者去镇上唯一的餐厅下馆子,但无论我走多远,我都会回到这间温暖如春的小屋,而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隐喻:
毕竟,无论你走得再远,你都得回家,然后再出发。
我从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少年的我捏着双拳,说要一直写下去。十几年来也曾跑偏,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无谓的地方,或者说走到了距文学很远之处,所幸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归了初心,重新觅到了文学的道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迷路。李老师在后记中说:“有时感觉要迷了路,慌了神,硬着头皮往前走,幸有师长指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现在,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似乎又是对的。”对于这句话,我和李老师有着相似的体验:幸有李老师指路,我才不至于迷路。我觉得这很美好也很奇妙:李伟长的师长指引了李伟长,李伟长指引了我,如今我是教师,也许已经指引过一些孩子,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兴许也能指引他们遇到的更年轻的人。度过今年的冬天,我也到了而立之年,祝自己和所有人都能走得更远,也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未被摧毁的生活》读后感(二):被摧毁的作家
很多人沉湎于小说分不清书中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就快拿着小棍敲头了,别傻了,小说是编的,现实就是现实,而奈保尔认为福斯特鼓励人们撒谎,对印度人知之甚少,还想诱奸花园里的少年。于是李伟长说奈保尔是“一个自我的人,对这种不舒服有权利表达不满,哪怕此君死了几十年了,谁让他是奈保尔呢!”
后来李伟长又写到他和青年小说家聊天的事,这个小说家想学《米格尔大街》来写一下自己的事,他表面鼓励了这个人,内心的想法却是别写了,理由是《米格尔大街》太好了。
以上是他的《奈保尔的嘴》。看来李伟长和奈保尔一样,喜欢直言不讳。
如果一篇不能说明现象,那么在《你最寂寞,点亮灯火》里,他认为马卡姆《夜航西飞》是“在成功人士鼓励和催促下,她也有把自己的经历变成文字,会给男人们带来慰藉”的动机下诞生的,然后大谈特谈马卡姆的私事和她的恋父情结,还有马卡姆的漂亮,多次提到。在非洲,一个几乎没有人只有动物的地方会在意外貌吗?在《出生入死的桑塔格》里,这个风格就更加明显了,首先桑塔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铸就偶像》里桑塔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里面又夹杂一些李伟长自己的看法。在读完《特立独行的温特森》以后我彻底明白了为什么《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者只留下了名字,读者除了故事就只知道这是一个意大利名叫“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家了。
不怀好意的去解读作家就是在戏虐作家了,那读者读起来,就是在戏虐读者了。如果未被摧毁的生活是希望,是一本新书未读的心情,那在遇到现实也只能像扉页的墙壁一样轰然倒塌了。
《未被摧毁的生活》读后感(三):阅读本寂寞,却点亮思想之灯火
《未被摧毁的生活》是一部阅读随笔集。最先被吸引的是这本书的封面图片,一片废墟之中,三名头戴礼帽的男士驻足依然竖立的高大书架前,环境的破坏性与人物凝神的专注性形成鲜明对比。根据一位读者的查询,这幅图片名为废墟上的阅读者,背景是1940年10月22日,英国伦敦肯辛郡的一座图书馆被狂轰滥炸。时光定格,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一切都可能被随时粉碎,但人们对阅读的渴望,以及文化涵养所形成的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依然优雅的姿态,令精神世界之强韧跃然纸上。
想起之前读库出版的玛格南图片社以阅读为主题的一本书。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东方到西方,从贵族绅士到难民,跨越时空跨越种族跨越阶层,阅读如一粒种子在每个地方的每个心灵生根发芽,用寂寞的飞行点亮每一个渴望的灵魂。
注:图片来自《读》
《未被摧毁的生活》选取了李伟长的十八篇阅读随笔。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学理论,作者用自己的阅读体验呈现了这一命题:我们为什么要阅读?阅读体验如何输出?作为延伸阅读爱好者,面对一本书,作者不仅对书中内容进行联想、对照和拓展,还对同时代、同类型的作品或者作者进行对比与分析,极大的拓宽了一本书的内涵与外延,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
开篇《如何过好Nobody的一生》便可谓典型示范。从《小人物日记》这本小书到钱钟书对该书的评论,再从钱钟书先生的评论里发现同样推介这本书的三个大人物。费力寻找、求证与确认,收获的却是一次美妙的阅读体验。“相比于寻找的结果,寻找的过程更为美妙,不断查阅材料和请教方家,一点点扩大知识边际,渐渐确定自身局限,由此变得更为谨慎,于阅读者就是莫大的意义”。
本书提到的作者和作品多是耳熟能详的,因此更容易在探寻阅读的意义时激发读者的共鸣。比如对推理迷来说,劳伦斯•布洛克、松本清张、钱德勒的作品均属必读。在《布洛克的理想生活》中,作者点评的为雅贼系列作品中的《自以为是鲍嘉的贼》。不过,我个人更喜欢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系列。但奇妙之处在于,布洛克笔下的马修与钱德勒笔下的马洛这两个主角的塑造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爱喝波本加咖啡,一个爱喝螺丝起子,两个人在醉酒与清醒中挣扎,出色的完成工作却不追求物欲,有短暂的感情但几乎总是独来独往孤僻冷淡。阅读这两人的文字时画面感总是如影随形,故事情节倒成了次要,更令读者难以自拔的事面前展开的是一个人的生命镜像和身临其境的情绪氛围。
“阅读的迷人之处,就是在书中遭遇与自己有相同习性的人物,所谓辨认出他们,听其声,见其人,与之共呼吸,开怀大笑,潸然落泪,就是在这些人物身上看见了自己。有幸的话,通过他们还能将自己引往更远的去处”。
事实上,阅读是一件很个人的事,各有喜好,所读有异,理解有差。《未被摧毁的生活》以作者自身的输出经验给呈现阅读体验打了个样。当然,对更多的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开卷有益,不停追寻。
《未被摧毁的生活》读后感(四):俯仰之间——读李伟长《未被摧毁的生活》
写得很潦草,但大抵是真心话。一
序言里张新颖说:“这个朴素的叫法,并不像一眼掠过去那么’老实’。”
“叫法”指的是李伟长将自己出的几本书都统一称为“阅读随笔集”——不是文学评论,也不是书目介绍。“老实”张新颖没明说,而是大笔一挥,转头针对“阅读随笔”本身展开论述。
当然,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太老实——不仅是李伟长,同时也是张新颖——张新颖用这样的评论,遮蔽了读者对书本的第一感觉,也就为阅读本身提供了空间。而这种“遮蔽”的手法恰恰来自于李伟长:他用一种仰望的视角,以滞后的笔调对书本展开评述。大多数篇目里,他放弃了对文本的逐帧分析,而往往沿着一条人物的道路蜿蜒到林中深处。
可能这也就是“阅读随笔”的题中应有之义吧。不再试图站在高处统揽全局,一针见血抓住书本的核心激扬文字,取而代之的是围绕着作家笔下的人物,构建一个出入于现实与文本的新空间。
典型的例子是《布洛克的理想生活》。作者开宗明义直接讲明,自己要写的是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自以为是鲍嘉的贼》,核心是小说的主人公伯尼·罗登巴尔。但很快,书从文章中消失了,只剩下伯尼一个人物存在。李伟长以极度现实化的笔调将劳伦斯笔下的伯尼的生活重新改写,伯尼也随之变换于书本世界和现实世界。
“关于小偷和书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孔乙己。…………伯尼是谁?孔乙己的同行——专业的梁上君子。”
“伯尼不仅爱书,还在百老汇大道,开了一家二手书店,并且是独资老板。”
“偷窃,作为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业,从来就有大小之分,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这是李伟长最出彩的地方之一。不满足于常见的小说人物之间的横向比较,多出来的现实议论瓦解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去掉了多余的修饰词之后,因为叙述的肯定语气,伯尼直接登场于现实舞台。
做到这一步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照常人思路应该沿着从虚到实的路线抽离开文本,但李伟长却兜了回去,继续写伯尼喜欢那个书名中提到的、现实中存在的“鲍嘉”!在这一小节中,通过真实人物鲍嘉,李伟长串联起了虚构人物伯尼、真实作家奈保尔以及奈保尔笔下的虚构人物,外号“鲍嘉”的佩兴斯。也正因为奈保尔,原本的现实与虚构被颠倒了。在读者视角,他们进一步确认了伯尼的真实,以及作家奈保尔通过“鲍嘉”这一虚构人物重新创造的虚构人物佩兴斯。或者说,读者们需要怀疑的点在于鲍嘉是不是真的,而伯尼已经是一个无比真实的人物了。
这时候李伟长才不疾不徐抽身出来,略写了一段伯尼的爱情故事,重新回到题目里所提的生活——读者们的、劳伦斯·布洛克的、以及李伟长的。
二
并不是说这种写法完美无缺。
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这个神奇的伯尼,让我几乎忘了是在写一篇书评,而不是一篇小偷的传记…………你呢?如果你和我一样,不妨打开这本小说。”
当作者从记录者或改写者的身份中抽离,读者也会从欣赏者或围观者的身份中抽离。介乎于传记和书评之间的,既有劳伦斯·布洛克的《自以为是鲍嘉的贼》,也有重新出现的有关现实的种种纠葛。去追究是否为“奇文共欣赏”的拍案叫绝并不礼貌,但这一落笔一下子让文章的着眼变得模糊。
可能这是仰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仰视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取舍:放弃锋利,选择温和。
用几何的方式表达,常规的批评像是一个圆形的内接三角形:从一个点出发,用自洽的新理论解构第一文本的内里;李伟长的阅读随笔更像是一条经过圆的直线:二者从关系上说仅仅只是有接触,相切、相交、穿过圆心都只是一个概念下的细微分野。
这一点在写松本清张的《松本清张的乱世》里更加明显。李伟长看似用三个小章节将作为核心的《绚烂的流离》一书基本剧透了个干净,可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其实不然:集结成册的十二部短篇小说,出现名字的只有《夕阳下的城堡》和《车票》两篇。剩下的部分,李伟长选择围绕着松本清张展开,对犯罪动机的讨论、对推理文学的剖析、对死亡和乱世的慨叹交织在一起,故事情节与人物传记相融合。好像作者什么都说了,但对读者来说《绚烂的流离》依然是陌生却魅力十足的。
“这一切,作者全叫读者自己去感受。他不破口道出,却无微不入地写出。…………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和,或者,随便你,一种吸引作用。”
李伟长引用了这段李健吾评论沈从文《边城》的话来评论松本清张的《砂器》。若稍加延伸,读者对李伟长笔下的松本清张的《砂器》、或者就是对李伟长《松本清张的乱世》,不也一样可以吗?
所以如果退一步,站在评论的立场上去看李伟长,确实非常棘手:你想肯定这是非常优秀的评论,但文章明明没有太多的评论;你想批判这是非常不合格的评论,但面对他所做的文本之外的研究、文本之内偶然闪现的批评无法熟视无睹。
“这就是小说的魅力,相比难以置信的可能,令人信服的不可能才是小说家要关注的。”
“对一个文本进行解读,最有趣的方式就是照着他的方式,戏仿一篇”
“小说家不是讲故事的人,而是创作叙述者的人,由叙述者去讲故事。”、
…………
当这些精妙的话语在文章中闪现,你不能不击节于作者的敏锐。但这敏锐通常只是一闪而逝,除了专门一章写自己如何走上批评道路的《格拉斯的洋葱》,以及解读钱德勒的《钱德勒的自尊》,再难看到自成体系的讨论。
三
这就不得不回到知人论世的老路上——如果对伟长老师稍有了解,或者有心去翻一下《未被摧毁的生活》的封面,就会发现老师的上一本书叫做《珀金斯的帽子》,而那本书的同名文章在本书中依然被收录了。
显然,不同于本书前两篇文章,从《小人物日记》到普里切特,因为存在内在逻辑关联而出现的,如“普里切特的小说细节,通常使用明喻、暗喻和意象,这符合英国喜剧文学的传统,内敛又深沉,拒绝流于表面的肤浅笑话。”这样的重复。整篇文章的反复选取,除了版权更迭的现实因素,无疑还存在着作者主观选择的可能。
这就不得不提出疑问,对于作为出版社主编的李伟长,这本书里的哪个人更符合他心目中的自己?是张新颖专门提到的,也很明显带有自我传记意味的《格拉斯的洋葱》一文中清楚承认的“青年书评人”,还是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提及,但却无法忽视其突兀性的《珀金斯的帽子》里的那个美国出版编辑“珀金斯”?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伟长老师自述,书名“未被摧毁的生活”来自张新颖的诗歌,但这句话却在这些文章中反复出现:
“相对于身体的被摧残,意识对桑塔格而言最重要…………”(《出生入死的桑塔格》)
“松本清张对乱世中罪人的理解,表现为用悬置为他们营造现实生活未被摧毁的幻象。”(《松本清张的乱世》)
“未被摧毁的生活,之所以值得纪念就在于此……”(《我们村的凯鲁亚克》)
…………
自然可以理解为某种既定基调下的顺水推舟,但倘若理解为草蛇灰线后的画龙点睛,也未尝不可。而在某种矛盾与冲突里,我们却依然能清晰辨认一定属于李伟长的顽皮与诚挚,这来自文学,也来自非文学;所以有态度,也有温度:
“相对于桑塔格对自我形象的要求和有意识的塑造…………现在很多的中国作家…………要么是不修边幅的书房照,要么就是所谓漫步祖国大好河山的旅游照”
“八卦的传播也就全部在挤眉弄眼和会心一笑中实现。”
“讲台上的帕格尼尼。我瞬间记住了这句赞叹…………以后评价一个人,这语法结构可以借鉴…………编辑部里的温格教授。”
尤其最后这句,看着伟长老师豆瓣账号头像上的T9托雷斯,难以言明的幽默感充斥全身。
或许这就是文本与现实边界消解的另一种状况吧——在镜像与本体之间,在仰视和俯视之间。
《未被摧毁的生活》读后感(五):后记:未被摧毁的生活
想说和所能说的,都在书名和封面里。
给小朋友告告读《柳林风声》,读到鼹鼠和水鼠哥俩,出门遭遇暴风雪,在冰天雪地里迷了路,眼前一片白茫茫,不知道该往何处去,顿时心生戚戚。那么小的家伙,一阵风就可以将他们吹走,陷在漫天风雪中进退不是。幸好,他们遇到了獾先生。正是这位獾先生,打开了门,给我看到了一处迷人的地方。
为了躲避风雪,鼹鼠和水鼠寻找藏身之地,意外来到了獾先生的家里,那是一个幽深安静的洞。进门后,獾先生举着灯,领着他们俩,不紧不慢地穿过又长又暗的走廊地道,推开一扇厚重舒适的橡木门,进了一间温暖如春的大厨房。宽大的壁炉烧得正旺,炉前放着两把高背椅,用来招待朋友的到来。红色地砖泛着年久的光泽。一张长条大餐桌摆在中间,桌旁摆着两条长凳。美味火腿、几捆干草、几网兜洋葱和几篮子鸡蛋,挂在厨房的上方。想想洞外风雪交加,路人饥寒交迫,而此时此刻,在獾先生的家里,热气腾腾,有炉火,有食物,还有远道而来的朋友。书中有一段话描述这间大厨房的景致和氛围——
这段话让我入迷。一间谈不上豪奢的大厨房,可供凯旋的英雄欢聚;可供辛劳的农夫围坐一桌,欢歌笑语,庆祝丰收;抑或两三个脾性相投的朋友,坐下来吃吃饭,抽抽烟,惬意自在地谈谈天。如此的氛围让人放松。英雄打仗的凛冽,农夫劳作的艰辛,朋友日常的烦心,在这厨房里、炉火旁和餐桌上可一一卸去。我似乎都想象得出,写作者描述这间大厨房时的神情。
就会生活而言,獾先生真是一个榜样,不仅找到了这么好的地方,还打理得如此舒适,粮食储备够了,炉火时刻不息,真适合闭起门来安心过冬。冬天里的动物们都昏昏欲睡,有的已经冬眠了。冬天里休息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似乎过去半年多的辛劳和积蓄,为的就是过好这一个冬天。大雪的天,烤着火炉,饿了就吃点火腿和洋葱,不必受冻,不至挨饿,尔后浑然大睡,等待春天的到来,等待雪退冰融,等待水流再次潺潺。不用焦急,甚至连耐心都用不上,春天自然会像往年一样准时抵达。
我喜欢獾先生的厨房,以及厨房里的生活。据獾先生介绍,这间舒适的大厨房,以及家里其余的房间,并不是他亲手建造的,而是早先在此居住的人类建筑,他们在此生活,结交朋友,做生意,出门打仗。很多年以后人类迁走,用獾先生的话说,人类总是这样来来去去。风吹雨打,年久失修,这座城市一点点陷落,最终被泥沙覆盖,成了地下之城,动物们就搬了进来。需要房间,清理打扫一番就是现成的住所。把门一关,地下的世界让人安宁,用鼹鼠的话说,一进獾先生的家,回到地下,内心就踏实平静了,在这里用不着和任何人商议,时间和空间自己说了算,不会有什么事会莫名其妙地来打扰你,也不会有什么人会侵扰到你的生活,你完完全全成了自己的主人。
我喜欢大雪纷飞,听过雪落的簌簌声,推门见过大雪封门,也经受过下雪时的寒风呼啸,以及雪后的冰冻。年少时每逢落雪,一家人就围坐炭火,父亲有兴致就讲讲评书,因为出不去门,他打不了牌。母亲会撬开一个罐头,煮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感觉就像獾先生的家一样舒适安宁。第二天雪一停,大人们就会出门,就无暇顾及我们了。后来才知道,大雪的好全在将时间停在了那一天。动物会冬眠,人其实也差不多。在乡下,秋收之后,该忙的都忙好了,余下的就是过冬了。农闲的日子很长,大人们的生活就是烤火、串门、打牌、谈天说地,也有日子过得难的人家,多数是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得去借粮,借一百斤,来年还一百二十斤。日子过得艰难,倒不见借粮的人有多悲切,照样是乐呵呵的来去。
农人们的生活很单调,只要不遇天灾,一年的收成也就够吃够穿,余不下多少钱。遇上天灾就难说了,干旱或者受涝,才是最大的折磨。至于生活,顺着时节而过,到了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情,多少年以来的自然秩序指挥着乡村生活。于我而言,故乡早就回不去了。那些看似美好的童年记忆,只是一种记忆,也许根本就是一种错觉——童年记忆特有的错觉。记忆之物早已荡然无存,现实生活正在迅速地覆盖从前。农忙不那么忙了,农闲也不那么闲了。春夏秋冬的自然秩序还在,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有人会等着过冬。假如獾先生在,正巧大雪封门,他肯定依旧会在大厨房里烧起壁炉,储存好过冬的粮食,即便外头兵荒马乱,即便朋友遇上麻烦,也不会开门走进风雪。无论多大的事,冬眠过后再说。对他而言,好好过一个冬,就是头等大事。别以为獾先生冷酷无情,他相信很多事情都来得及,何况习惯冬眠的动物,在冬天出门就是强弩之末,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故事里就是这样,听到朋友可能会惹上麻烦,獾先生直言不讳,告诉鼹鼠他们,冬天里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得休息,也就是冬眠。忙活了半年,到了冬天动物们就会犯困,獾和别的动物没有区别,甚至他冬眠的时间更长。让獾先生放弃冬眠,强打精神,或者打着瞌睡,离开温暖的洞穴,是很危险的行为,他可能会冻死在冬天的路上。这是獾作为动物的弱点,换言之,就是他的有限性。獾很清楚这一点,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逞强没有意义,接受自己的局限并遵守它才是对自己负责。从十一月份进洞,到来年三月份冬眠结束,獾得沉睡五个多月。听上去是不是很漫长?的确如此,《柳林风声》美化了这个情境。我想说,和动物一样,人也有某些特殊的习性,有些习性就是弱点,同样可能致命。一个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要是还能接纳它,不想着强行纠正这些弱点,就已经很让人钦佩。事实上,总有很多人不甘心,以为凭着毅力和决心可以击败乃至克服自己身上的有限性,故而勉强行事,结局的不顺遂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我喜欢獾先生的“冷酷”,不冲动,不莽撞,不急不可耐,而是等着冬天过去。也许会错过帮助朋友的最佳时机,但只要生活还没有完全被摧毁,演出还没谢幕,就还来得及。事实上,生活也不可能被摧毁。何况,坏事还未发生,坏小子蛤蟆还没有锒铛入狱,为尚未发生的事情犯愁,不是獾先生的行事风格。几个月后,冬天过去了,冬眠结束,獾先生如约走出了洞穴,和一帮老友拯救了浮夸的蛤蟆老弟。冬天不出门,是獾先生的生存规律,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像曾国藩的几句话——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还没来的事情不必忧虑,专注当下更为重要。当你知道獾先生清理出这么一间温暖的大厨房时,就知道他的生活是怎样怡然自得,又顺守自然秩序。如果在厨房里补上几包腊肉、几条晒干的鱼、油浸的萝卜条和一些辣椒,就是我记忆里老家的伙食了。
我从乡下来到城市,有时感觉要迷了路,慌了神,硬着头皮往前走,幸有师长指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现在,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似乎又是对的。原来迷路也不容易,失掉生活方向的人才会迷路。莫泊桑在短篇小说《人生》中讲,“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这种感觉常在心头泛起又沉下,似乎说中了一些什么,又近乎矫情得不值一提。
2020年一过,我已不惑。原以为过了不惑会懂得更多的道理,实际上相反,是懂得了很多的无能为力,有许多事是做不到的,一些念想也熄灭了。我的精神生活大概就是想明白了“无能为力”并接受这些的过程,接受自己不完美的习性,接受自身的力不足,接受自己的不乐意,都是属于我个人的写作意义。倘能引发别人一些微小的共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喜悦。
未被摧毁的生活,这一书名,来自张新颖先生的一首诗《清单》,无比喜欢。我问,能否给我用作书名,他说,那你拿去吧。在这首诗里,他列出了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事物,有这样几句——不喜欢的:文学评论、头头是道、故作低沉的声音/喜欢的:李宗盛、阅读、写作、一个人无所事事、喝茶、晒太阳……不喜欢的:风景这个词、窗子打不开的酒店房间/喜欢的:风、水、大海、北方、夜晚的雪、天空、早晨……还有一句——喜欢的:未被摧毁的生活。词语并列安放,竟能生成如此美妙的意境。除了书名,新颖老师还为这本书写了序,没有他的鼓励,我几乎没有勇气出这本书。
谢谢责编魏玮,她的意见和耐心,让这本书的面目更为清晰。她嘱咐我写一篇后记,就我所理解的生活说说清楚,结果写成了这样,我自己也没想到。不可否认,我很想走进獾先生的大厨房,在壁炉旁烤火,看柴火烧得噼里啪啦,在餐桌上吃火腿,听鼹鼠说蛤蟆啼笑皆非的遭遇,听小刺猬讲下雪天被妈妈赶去上学结果迷路的故事,等温厚的獾先生睡醒,和他一道抽抽烟,喝喝茶,谈谈洞外的夜晚和纷飞的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