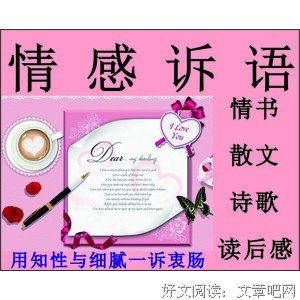《书情书》读后感1000字
《书情书》是一本由(德) 布克哈德·施皮南 (Burkhard Spinnen)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带函套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1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书情书》读后感(一):写给书的伤感情书
薄薄一本小册子。但是读到后面发现它的深度远远超过了它的厚度。
共鸣很多。对一个被数字化时代挟裹的纸质书拥戴者来说,也是一直处于半分裂状态。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与纸质印刷有关的部分在时代大潮里缓缓谢幕,比如纸媒,比如二手书店,比如纸书线下销售,作者说:“旧书店是时间退场的书店”,有伤感的味道。
虽然说文字做到传播文化即可,载体并不重要,但有时候我在想一个拿着电子产品阅读的人和一个捧着纸质书阅读的人专注于文字本身的力量孰轻孰重?
“每一本读过的书都是读者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讲,私人藏书是记录个人阅读生活的一份档案,或者说是一座纪念堂,其供人瞻仰之物比其他任何纪念堂都更具生命力。”
另:其中有一节作者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批判了纳粹焚书,是一个文化人该有的样子。
译者遇到好书是一种缘分——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关于与这本书的缘分,文景君已代我这个从不写译者感言的译者做了解释。如下:
转自文景小站:译者跟这本书的缘分太深了。家中书房的陈设和封面配图几乎一样。书里开篇,作者布克哈特·施皮南悼念了在近代生活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却很快被淘汰的马匹,来感叹纸质书是否会有同样的命运 ,而译者的朋友圈头像和封面一直都是马。图三才真的神奇,书中的插图都是各式各样的读书人,其中有摔断腿打着石膏无法自由活动之人的读书写照,而译者也因为滑雪摔伤过,而且也是用看书来打发康复时间的!看来,爱书之人总会和他们爱的书相遇,都能从所爱之书里找到共鸣——但是,大家还是千万保重,别为了赖在床上看书就去从事危险活动!
书跟人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乍看之下似乎很好回答,但当我打出这个问题的同时,突然觉得自己的总结苍白而无力。既然无法论言出书与人之关系,那我索性另辟蹊径,不如从到底‘何为书’这个问题重新发问。
书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数次——至今依旧——的改变与‘翻新’,但无论如何变换,书的本质与基本属性还是不会改变。那书的本质是什么?理清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理解何为本质。梅洛·庞蒂总结,无论外部环境的改变多么激烈,都不受影响的主体部分,就可以视为事物的本质。这一不变的恒量,可视为该主体的必需元素。那么一本书不会因为外部的改变而受到影响的部分是什么呢,即使不用通过用减法方式剥去它的形态与材质我们也能得出里面的‘内容’即是答案。因此,书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本质还是制作者和阅读者之间的一种媒介。
布克哈德·施皮南的这本《书情书》就是写的阅读者跟书之间的大小事。里面列举的大部分事情是每个爱书、好书之人都经历过的无奈之事。买到不喜欢的书,眼花缭乱的批注,残缺的书页,克制购书欲的爱之宣言,丢弃与被禁书状态等等,这都是每个爱书人之间的老生常谈,并无标新立异的地方,但每个爱书之人却从未把它当成垃圾而丢弃,甚至不厌其烦的拿来反复调侃。这里面充斥着各种无奈的琐言碎语让爱书之人倍显着可爱。人们如果拿以往失败的经历当做谈资,那里面必然会有他热忱的因素,施皮南把这些失败的因素总结成册。里面充满了他身为作者、读者和买家的各种失格的经验。它是作者跟读者坐下闲谈时发发牢骚的一本书,阅读时你会感觉作者与你相约而坐,为着之前不被理解的事情进行着书友之间的倾诉,而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简单而准确的答案和解决方法。你听得时候或许会随着问题而自省,但我们真的想要解决这些恼人的问题吗?如果答案是确定,那解决的方法就再简单不过,只要将家里的藏书当做废品垃圾般清除即可。但我们不会,之所以这样才会出现书中列举的各种问题,这也是爱书人对书表达的忠贞之处。你难道没有对已经读不完的书房继续施压的经历吗?难道没有看到当初买的那些失败之作而懊悔吗?当一本书被禁后你难道没有急着到处找寻吗?这本书里的事是好书之人‘失败’的事,只有好书之人能予以理解,我们喜欢听这些事,聊这些事。因为对于好书之人,它是件好事,也许它也是天下最好的事。
《书情书》读后感(四):我们为何依然恋着纸质书?读《书情书》
我最喜欢收到与赠送的礼物是纸质书,大部分情况下它们都是有用的,即便不是用来阅读,也可以用来作为阅读的一种召唤。偶尔瞥到书架上那些未曾翻阅的崭新的书,内心深处不免会略略升腾起愧疚之情,如若是他人赠予之书,则愧疚的对象除却书以外还添了赠书人。是负担,却是甜蜜的负担,纸质书于我来说是人与书,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书情书》,文景,2020年2月出版,(德) 布克哈德·施皮南 著 / (德) 琳娜·霍文 图爱读书的德国人非常喜欢赠人以书,故而作者布克哈德·施皮南在《书情书》中特意写了一篇“送礼的书”。“在大多数社交场合,送书都是一件体面事,容不得任何人说三道四。无论是高中毕业还是成人礼,或者是生日派对之类的庆典,当事人从校长、父辈和友人手中得到的礼物通常都是书,而不是毛毯,不是滑板,不是风干肠。”——这样的状况着实让地球另一端作为售书人的我感到万分羡慕,倘若书在本国也成为了流行又体面的礼物,书业的日子一定会好过很多。
《书情书》是一本令人爱不释手的小书,里面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却全面又扼要地说明了有关于纸质书的大部分话题,可以称得上是“纸质书通识”读本。读者会在其中读到许多“书”的影子,也会读到许多“自己”的影子。如在“被批注的书”一文中,作为旧书狂热收藏着的作者,讲述自己为了去掉书页上的“批注”而经历的惨败故事,令人忍俊不禁。我就是一个狂热的“批注”爱好者,第一遍阅读会用铅笔以横线和圈圈在书上做标记,再次阅读会用不同颜色的笔继续标记……不知作者要是看到被我“糟蹋”过的那些书,会作何感想。
《书情书》内页插画“书店”当然也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作者对于书店的定义相当精准:“书店的样子看上去很像是图书馆,可它并不是。对书籍来说,书店的角色更像是一处驿站或临时寓所,而旅行的最终目的地是读者或其他某个地方的书架。”我想借用某品牌矿泉水的广告词来描述一下书店的功能:“我们不生产纸质书,我们只是纸质书的搬运工。”书店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架上的那些书以最快的速度流转出去,从经济角度说,这是书店的生存之道;从社会功能角度说,这是书店的期望,联结人与书、传递思想。作者也提到即便在德国,独立书店也正变得越来越稀少,而对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彼此包容的这一理想可以通过阅读去实现的信念,正是提供内容更多元纸质书的独立书店一直试图坚持下去的原因。
《书情书》装帧设计我们为何依然恋着纸质书呢?为何内容一定要附着于有形的书和纸?我是一个电子书的阅读者,也是一个纸质书的爱好者,对我来说,后者提供了无法取代的触觉与视觉和混合体验,尤其是触觉那个部分。就拿这本《书情书》来说,去掉塑封后,黑白红三色明快的色调首先就十分赏心悦目,函套使用的纯白纸张摸起来有些涩涩的质感,印刷精细;将书从函套中抽出来,朱红色的封面慢慢增大比例,越来越鲜明温暖,与封面、书脊、封底通身红色配套的深绿色书签带亦是被精心挑选过的,让人感觉到书是很棒的“礼物”;内页排版简洁,字体和字号的选择舒服,窄长开本和轻巧身段可以支持毫不费力的单手阅读。以上这些感受,只有真真切切印刷装订出来的纸质书才能提供给读者。
懒惰的我,没有亲手栽种过一枝会在春天发芽的花,没有亲手编织过一件可以御寒的毛衣,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意我的手指可触碰的对象只能局限于键盘和屏幕,想要在书口处翻开一本书,想要去探究陌生的作者在一页一页薄薄的字里行间所隐藏的感悟,想要去触碰更有真实感的东西,想要去拥有更物理性的感受,所以我还恋着纸质书。
《书情书》封面插画除却作者理性又不乏深情的文字,琳娜·霍文创作的插画亦为本书的阅读增添了额外的情趣,尤其是函套上方形的书房图,背景是满坑满谷的书架,一张同样落着书的沙发位于画面的正中间。最吸引我的不是画面里的书或者是书房的舒适氛围,而是沙发上那个缺席的阅读者。是什么样的人有幸拥有这样一个被书包围又无人打扰的书房呢?又有多少个微寒的夜,此人裹着沙发上的那张毯子窝着翻书翻到睡意来袭?
《书情书》是一本关于“书情”的书,也是一本写给书的“情书”。每一个爱书人都可以写下自己的“书情书”,在那之前,这本来自德国作家的小书或可暂时替代专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本“未写之书”。
(原文载于 半层书店、文景 微信公众号)
《书情书》读后感(五):我想,我们可能正站在一个时代落幕的地方
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的最后,空寂无人的酒店大堂中,仿如奇幻的故事在作家笔下缓缓落幕,背后的箭头散乱地指向不同的方向,镜头转过,层叠的叙事一瓣一瓣合拢。年老的作家捧着旧日的作品,身后的房间里显现出新鲜装修的杂乱与未知;年轻的读者坐在荒旧废弃的墓园里,旧时代的歌者已经不见,雕像基座上挂满的酒店钥匙,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而非对“国宝”的缅怀。
事实上,这两天我也经历了一次颇奇幻的体验,一本穿着本白色书衣的绯红色的书,就这么贸贸然出现在我的桌上,不曾预先收到消息,寄件人姓名栏上的名字更显陌生。只知道书是文景出的,叫《书情书》。
上巳节,据最新近的说法,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在这一天收到写给书的情书,别添兴味。中国“古代的情人节”何其多也,单留这一天给书,倒也不错。毕竟,这一天留下了至圣先师一生中说出的最浪漫的四个字,“吾与点也”。这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对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最感性的喟叹。
书不厚,百四十页,版权页上的六万八千,如果是版面字数的话,实际字数可能也就五万出头,作为网文更新可能撑不过一个礼拜。阅读起来更快,从下午打开塑封开始算起,第二天中午已经读完,除开生活琐事,还有大量的富余时间让我在心底构思一篇书评。我依稀记得那是一篇非常动人的告白,然而正如作者所言,没有落到载体上的文字终究是篮子里的水,此刻记录下的只是些散乱的残叶断章。
伤感的情绪太重,张口而出,唯余毫无意义的呻吟。
目前这本书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3分,偏高了,实际可能在8.0分上下。毕竟浅,毕竟薄,作者描述的基本是一些私人化的读书、藏书经验,唯有书之爱,与人共通。好读书者,岂有不爱书?即使最坚定的电子书拥趸也无法避免,在某一地某一时刻,总有一本两本装帧精美、纸页间散着香气的书籍,突然间抓住你的心,想触摸,想拥有。
“地方太小”“书价太贵”,那是理性这个小人在你耳边喋喋不休,从中作梗。抽离开来会发现,你的感性早已把那本书牢牢攥紧。而此时此刻,试着抽离开来,同样会发现作者在薄薄的纸页间,早已用精巧的文字构筑了层叠的“陷阱”,一丝哀愁的情绪在迷宫的墙壁间回旋摆荡,勾起每一个展卷人情绪的共振。
阅读本书,哪怕是不读书的人,也会从此爱上书籍。
这一定是这个时代最令人哀伤的悖论。作者用十九世纪人们对于奔马的爱与依赖,在书的开头为其后的所有爱恋定下了基调。凡此以下,无论是对新书、旧书、珍书、毁书,还是对书封、书雕、书店、书架的叙述,尽皆回声的砖墙。穿行其间的金线是爱,迷宫深处的谜底是哀愁。
这本书的德文原名是Das Buch : Eine Hommage,直译过来好像是“向书致敬”,是互联网告诉我的,并没有认真地去翻字典。这话说的,好像我会有德汉词典一样。信息时代的集成性,剥去了书籍最后一层实用性的外衣。广告不用它,传播不用它,学习不用它,存储人类的记忆也用不上它。
新家装修时,曾异想天开地拒绝买电视机,觉得放在客厅里,使用率低不说,还占地方,更容易给孩子带去错误的爱好。相比之下,在客厅里放一架书,多好。但在家人的坚持下,最终,一台五十寸超高清的液晶怪物被供奉到了客厅最中心的位置,不仅可以看一般的电视信号,还可以下载APP,观看形色的网络视频。这个时代,新老两个巨人,在家庭地位上的最后交锋,烟尘遍地。而上个时代的尸骸,早已被送进了书房。它死了,没人看见。
《书情书》封面插画我想,我们可能正站在一个时代落幕的地方。这也许是我最灰暗的评论,往前不这么说,往后也不会再承认。
正如作者在跋中,勉力撑起的最后一丝乐观。“大概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一次历史课上,老师给我们念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年青一代的文化衰退问题。你肯定会以为这是一篇现代作品,可实际上,这篇文章出自古埃及。无论任何年代,老一辈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是文化的最后守护者。”古斯塔夫已死,而布达佩斯挺立。
读完全书,仔细端详封面,书与情,黑红交替的布局莫名让我想起了墓园里的碑。黑色已死,红色幸存,人情已死,唯书长存。也许因为人的移情别恋,书业确已黄昏,也许没有。但就像千百年来,一切走进人类生活中心又离开的其他东西一样,鞠躬,谢幕,光荣体面的退场,走向远离聚光灯的个性舞台。这从来不是一次伤感的告别。
伤感,是你我的伤感。
就好像马匹,摆脱了负重前行的命运,却意外成为某种贵种的标签。奔跑在附近商场的顶楼,体验课四百元,月卡三千六,年费四万。也许,我百年以后,所收藏书最终最好的命运,是在浙江某一村庄小楼的阁楼里无人问津地垒放着,静静忍受灰尘鼠蚁的啃食。直到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在老屋探险时偶然发现了这座“秘密花园”,随手撷取一朵“玫瑰花蕾”,却发现已是小众人群奢侈的文化享受,于是欣喜其丰厚,扼腕其残旧。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希望他能够先翻开这本书,试着了解曾经有人,为书,写过如此深情的长信。
作者: 田秋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