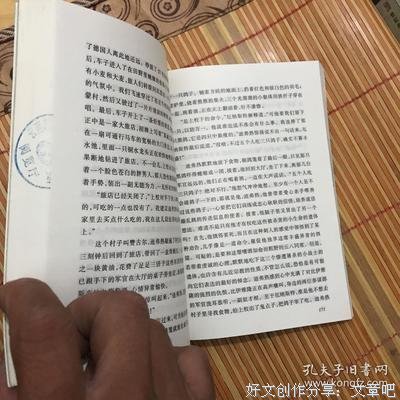桤木王读后感100字
《桤木王》是一本由米歇尔·图尼埃著作,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4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桤木王》读后感(一):意象、寓言与征兆
米歇尔·图尼埃,在惊人的意象的运用、寓言般令人着魔的句子、衔尾蛇一般的回环和象征、自我参照与无限循环中,创造出《桤木王》这样不朽的伟大作品。它充满人类记忆的痕迹,充满集体无意识的反馈,是由遥远的时间黑夜衔接现在与未来的神谕。
意象是一种仅能够感知、能够解释,无法真正触碰、无法倒推或刻意使用的东西。它就像是遥远的地平线,看似近在咫尺,一旦靠近就会远离;它是预言性的十四行诗,吉普赛人的的羊皮卷,岩壁中的野牛,教堂中的天使,灼烧龟甲时出现的征兆般的裂痕,是万事万物的联系,是人类命运的终极概括。意象永恒存在,却永远不可复制。
“你是个吃人魔鬼。”这一句话既是唤醒,也是错误的诱引。所谓魔鬼只是被指出的、不同寻常的、在荒谬中诞生的怪物。他们存在于这世界上,思考并且生活,可处处格格不入:要让魔鬼勉强披上人类外衣,扮演人类中的一员,于魔鬼而言无疑是一种自我献祭,而献祭魔鬼本身便是一种伟大的圣洁——然而是否,魔鬼就是存在就要被毁灭的事物呢?
“魔鬼”阿贝尔·迪弗热,除开那与生俱来的魔鬼习性,在一切约定俗成的习惯中,在暗流涌动的生活中,尽管有着天渊之别的认知,可依旧履行作为普通人的义务。他是无害的、人类世界的学习者。他无法理解人类普遍的情感,便只有从征兆和意象来辨别;他知道什么事物受他人钟爱,因此也令他渴求。
因为了解意图,所以,如果他想“成为”,他就能伪装。基于这种动机,他可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亦或是说,每一步都在往与本性截然相反的方向飞奔,在自我撕裂、自我毁灭,几乎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可是就在此刻,人类超越了魔鬼。
人类的恶意竟比魔鬼本身更为邪恶。迪弗热在浑浑噩噩的人生中,在推翻和重塑的过程中砌错了一块砖头,这个世界终于整个地垮掉了。他的灵魂在散乱的拼图里坐着,再也拼不起幻想中的世界。人类将魔鬼重新带回魔鬼的世界,山羊角从灵魂中钻出,恶魔的羽翼在身后展开,世界底色彻底变暗。
在虚无梦魇之中,他看见紫色眼睛的男孩,陷入谵妄的少年,无比沉重的救世主。那一刻,他想起桤木王的寓言,想起那夹在裹尸布般的泥炭层中的桤木王的那张平静和虚灵的脸。谁是魔鬼,谁是救世主,谁是征兆——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在六芒星的指引中,他展开羽翼迎接命运。
因为太喜欢这本书,所以不舍昼夜地读完啃了,大脑也几乎陷入疯狂。我的灵魂仿佛被剖开观望,露出最幽深的角落,因这惊鸿一瞥而狂喜狂悲、癫狂颤抖。我时常受幻觉支配,眼睛反映出见到事物之前,脑海中已经存在的样子;我无法不对表象进行发散,在恍惚得出结论之后,回过头看不到混沌的过程,于是狂热地喜爱比喻,喜爱虚无缥缈的东西,喜欢真实世界之外、以幻象堆叠出的世界。这本书就是疯狂者的乌托邦,魔鬼的救赎之地,人类难以抵达的神秘角落,几乎是文字所能承载的极限。
《桤木王》读后感(二):人生是一场错乱的盛宴……
人生是一场错乱的盛宴……
自己是第一次阅读米歇尔图尼埃的作品,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还以为就是一本普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得不说书籍的封面要背很大的锅),但开始阅读就发现这是一本你需要集中精神去阅读的作品,不然你会感觉其中的字句都拥有自己的“意志”,甚至你读完一句话不知道作者说了什么。
全书大约五个章节也是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人公从自己可以用左手写字而且还写得不错开始,主人公讲述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讲了自己的工作,自己如何成为汽车修理工的,自己对于认识的女性的看法,自己对于生活中的“征兆”的认识,其中关于哲学的命题和现实的讨论,对于宗教的拆解和认知世界的方法论交错并行……
第二部分故事回到了主人公的幼年和青年时期,讲述了在寄宿学校中的种种遭遇,可以说在其中毫无征兆的惩罚,各种形式多样的“强权压榨”是主人公后期性格形成的重要基础,对于权威对于强权的“逆来顺受”不再是不情不愿而是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如此,在这个学校中强权的代表在后期对于主人公的格外“照顾”更是让其觉得自己是某个伟大事业的一部分觉得十分庆幸十分幸运,哪怕最后这个强权的象征消弭于烈火中……
第三章节中,无辜的主人公却被人诬陷入狱之后参军,在军队中通过饲养信鸽他找到了自己生命中新的征兆,而这个时候故事已经进入二战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的时间线从这里开始就是战争时期但是正面战场和冲突在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有各种细节和线索但是读者又很容易知道这个是哪一些事情,很快的主人公被德军抓住,成为德军俘虏后在类似的“集中营”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战俘生活作者描写的并没有读者一般认知中的那种愁云密布凄凄惨惨,相反的主人公在这里收获了自己心灵的宁静,甚至其对于这样的生活还有一些享受,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他喂养视力不好的驯鹿,还是学习德语,他将身边的很多事情看做自己十分重要的征兆,而这些心理思考让其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十分珍贵的……
第四章节中主人公在自然保护区中工作,这其中的描写大量的动物意象,不单单是对于正面战场的隐喻也是对于纳粹的各种残忍残暴的暗喻,这其中主人公天马行空的想法让其面对强权的压榨依旧甘之如饴……
第五部分主人公在元首的预备少年团学校的工作,这里可以说是与恶魔为伍,但是主人公却又觉得自己生活的无比幸福,直到遇到一个犹太男孩,主人公原先羡慕的“加拿大”,那些遗传学研究,那些工程学研究,真实的面目出现,主人公发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层面上,而最后他沉入沼泽也许是最好的归宿吧。
总的来说,阅读这本书会想起自己十岁时候阅读的铁皮鼓而那是一本后来自己每年都想要再重新阅读的书籍,这本书中主人公到底是是善良还是邪恶,是因为适当的环境让内心的恶顺其自然的散发出来还是因为童年时候的遭遇认为真的“权威的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世界的运行规则”,支撑他能够在部队在战俘生活中一直“健康积极”的“征兆”是否就是他邪恶的本质,而真正的“吃人的恶魔”,单纯是纳粹是战争的发起者还是不少人不由自主成为了其帮凶呢,个人评分9.4分,推荐指数五星。
《桤木王》读后感(三):《桤木王》的寓言里,隐藏一个倒错的世界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纯洁与残恶之间隔着多远的距离?一个人的宿命与儿时的经历又有怎样的关联?
你想要的答案尽在《桤木王》这本寓言里。
当然,《桤木王》所讲述的内容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诞生的背景是二战时期,书中主人公写日记的时间也是二战时期,这也就意味着:作者米歇尔·图尼埃试图借寓言来写二战。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桤木王》一书中,并没有我们预想的战争场景,而是一个个故事碎片,这些碎片看似与二战并无直接关系,但从这些故事碎片中,我们却不难品出战争的残酷,它扭曲了人性,揉碎了善与恶的分界线,它就如同一个吃人的魔鬼,一步一步悄无声息的将人引入罪恶的深渊。
在《桤木王》里,隐藏着一个倒错的世界。
首先,来看看主人公阿贝尔·迪弗热的成长环境。十多岁的年纪,中学读书的阿贝尔·迪弗热因身体孱弱受人欺负,而他只能选择忍受,甚至被“示众”“隔离”“罚站”“关禁闭”,那么欺负他的人呢?他们非但没有收到惩罚,还在老师和学监那里享受豁免权。由此看来,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而这种黑白颠倒善恶倒错的种子,在成长的迪弗热心中已然埋下了。
《桤木王》用接近三分之一篇幅来描述迪弗热的成长,这也是为后续章节做铺垫。阿德勒认为,一个孩子长大遇到的问题,做出的判断与其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通过第一部分的铺垫,再进行后续的阅读,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迪弗热会从一个普通人,变成“吃人的人”,最终演化为“泥炭沼人”。
那么,纯洁与残恶之间又有多远的距离?其实它们二者并不遥远。迪弗热在读书时,学校学生的一些恶行往往在圣洁的殿堂发生,恶行与圣洁,这两者行成鲜明的对比,也为后文做了铺垫,正所谓作者米歇尔·图尼埃所言的“征兆”。
一切看似都是征兆。曾经倒错的世界,在迪弗热入伍、被俘后一样存在。被迪弗热认为安静的幸福之地“加拿大”,堆满了沾满罪恶的宝石、金块、首饰;象征纯洁的孩子们,看似在接受所谓的教育与训练,实则被强制灌输法西斯思想,心灵备受毒害。
这并非正常的世界,这是一个倒错的世界。人性在这样一个倒错的世界里,慢慢凸显,似乎善与恶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善良之人也可以变成恶魔,变成“吃人的魔鬼”。
菲利普·津巴多曾经在《路西法效应》一书中,研究过人性的问题,从路西法效应中,我们可以看出,善良正常的人类也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变成了个恶魔。也许人性就是如此,不是非黑即白,善良之人也可以变成恶魔。
当一个正常世界变成一个倒错的世界,一切不合理似乎都变得正常。这就是为何迪弗热会一步一步毫无征兆(但实际都是征兆)的变成“吃人的魔鬼”,这与他成长的经历有关,同样与二战有着莫大的关联。
虽然这是一部寓言,它影射的是二战的残暴,但这仅仅存在于二战时期吗?笔者认为未必,它可能发生在历史的任何阶段,而人性很难经受住考验,环境对人的影响不言而喻。
落笔至这里,似乎有点明白《桤木王》中上述内容的意思了。一个人究竟成长为怎样的人?与遗传必然有关,但环境也至关重要。而希特勒主义:遗传+时间,一个人虽然受遗传的作用,但是时间却能够改变很多……(至于这理解对不对,有待探讨)
翻译家许钧说:““桤木王”,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悲剧,它已经远远超出了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超出了人性与魔性之间的永恒冲突。”这是对本书最好的阐释,原本善恶之间并不是不可转化的,人性与魔性之间也只差一步之遥而已!
《桤木王》读后感(四):异变下的善恶倒置
《桤木王》世态异变下的善恶倒置
米歇尔·图尼埃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新寓言派”的杰出代表作家。其小说以颇具特色的叙事风格和对存在与身份等问题的深刻哲思而闻名于世。图尼埃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作品作品中对神话和经典文学作品的借用,他通过对经典主题的借用与改写,实现了古老神话的复活与重生。图尼埃借神话,将真实与想象融合一体,塑造了一个个具有鲜明图尼埃特征的人物形象。 《桤木王》来自于歌德一首神秘叙事诗《桤木王》。歌德在这篇短片叙事诗中,描述了一个恐怖的魔鬼的形象,他经常在深夜中潜伏于密林里,惊吓夺摄ertong的魂魄,甚至夺ertong的生命。作者以此为原型,将故事背景放在了纳粹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图尼埃借用这部经典的诗歌里的情节,进行了重述和构建。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和深刻的寓意内涵。本书中主要讲述的就是主人公阿贝尔 迪弗热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怎样一步步地产生的心态异变,怎样逐渐的演变成桤木王中那个恶魔。 图尼埃小说作品经常从大家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宗教故事,以及经典的名著人物里选取材料。进行重新的解读和演绎。将这些我们熟悉的故事和和他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及哲学上的思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有人把它称之为“重塑神话”或者“哲思小说”。
简单的说小说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全都是主人公迪弗热的成长日记以及作者对他的心理轨迹进行的记述。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基本上都是让主人公迪弗热自己讲述了他那有些凄惨不幸的少年生活经历。在圣克里斯多夫学校,他一直受到同学的欺凌,学校的惩罚,甚至他还感觉到跟他要好的一个同学的背叛,所以在他的少年时代已经见识到了绝望和崩塌。他也不指望会看到一束希望的火光,此时其实已经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会将善恶倒置的种子。或者说在他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一切,也是一种将使他发生转变的征兆。作者说道:“被纯洁这一魔鬼驾驭的人,往往在自己身边制造废墟和死亡。宗教的净礼,政治的清洗,对人种清洁性的保护等,有关这一残酷主题的变奏数不胜数,但最终都是那么千篇一律的与无数的罪恶联系在一起”。主人公的少年经历对社会的这种深刻寓意,在这句话中昭然若揭。
当主人公长大后又被人诬告。使他终于认识到,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身处的那个邪恶的时代与社会。当他被征召入伍。更是使他深刻的与那个时代的“恶”结合在了一起。预示小说中有了战俘营,有了德军元帅戈林,有了罗明滕的帝国猎犬队,有了卡尔滕堡纳粹政训学校。作者根据二战中法德苏的战场实际情况,安排了故事情节,将真实事件推到了读者面前。在现实中复活了有关e mo的原始神话。
阅读全书之后,可以看出作者通过对桤木王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的戏仿的同时,又赋予了它新的历史和社会的纬度。从对迪弗热命运的展示,以及他一步步走进罪恶的过程,揭示出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背负着痛苦一步步透过征兆认清罪恶之根源的过程。一篇作者所布置的整个的隐喻场,就是对战争对纳粹的指责和控诉。 本书中作者展示出细腻的感触和独特的想象力,此类描写使得小说具有意识流小说或内心独白小说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些细腻的精神分析式话语也展现了一个个宏大叙事,暗含了萦绕人类已久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等哲学主题。
可以看出图尼埃的文学观是受哲学,文学,神话学,甚至宗教等众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进而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和思想源泉。图尼埃对哲学思考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开拓,使他成为20世纪法国文学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桤木王》读后感(五):负载神圣的巨人与恶性倒错的世界
凡传递的都可荣称为表达,凡被传递的均可荣称为意义,一切都是象征或寓言。——保尔·克洛岱尔再读《桤木王》,依旧被它的精妙深邃所折服。这是一本思考密度、象征意义和信息量巨大的神殿级小说。大故事套着小故事,寓言镶嵌着寓言。小说看似离散,但每一句话都能在整个故事中找到意义,不仅能解释过去,也是对未来发生的事情的“征兆”。
Erlkönig by Georges Schwizgebel
主人公迪弗热有着令人着迷的世界观,而他面前所呈现的世界,是按照征兆、恶性倒错与负载之乐解释的。
迪弗热相信,每件事都是有寓意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未来命运的征兆。对征兆进行剖析,才是生命的重要所在。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征兆的答案。
征兆作用于万事万物,出现在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当中。在日记中,迪弗热说的话看似是一个个碎片,实际上彼此之间却有相同的内核牵引。那是这个时代滚滚洪流弥漫着的思想,作用在个人身上。一切都表现在征兆当中。
The Ogre by Volker Schloendorff
恶性倒错是一种混乱颠倒的价值观。比如中有一种扭曲但深入人心的社会观念:对杀人犯的变态崇拜,杰出军人的名字全都标在牌上供人敬仰。
战争就是这样一场恶性倒错现象,当今社会显示出恶性倒错的魔鬼本质。在书中,迪弗热的每一句话都在控诉同一种错误的社会价值观。他说左手写下的文字是魔性的,“大逆不道”的,他说自己是半肉体半冷酷的混合体,因为唯有魔鬼才敢挑战魔鬼。
在书中提到的宗教文学《金色传奇》中,有一个巨人圣克利斯托夫受命承载了耶稣,巨人最终光荣地完成了渡河的使命。
迪弗热的好友纳斯托尔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巨人,因此具有特殊使命。而他们所在的圣克利斯托夫学校也是一个巨人,学生们则是纯洁的孩童耶稣。学校供着孩子们,这是它的光荣之处。纳斯托尔死后,这个使命传递给了迪弗热。这之后,迪弗热开始吃生肉,喝生奶,长成一个粗犷的“巨人”,身体里附着纳斯托尔的灵魂。
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举着天空、顶着星球的巨人阿特拉斯。
迪弗热想成为负载天空的英雄。因为承载是一种使命,是迪弗热向往的命运。
此外,马也是一种典型的承载性动物。在德国,迪弗热为了满足帝国元帅戈林对野猪的喜爱,担任起了喂养野猪的屠夫角色。他骑上纳粹送的马,立刻感到了某种将要完成伟大事业的激动。野猪象征着纳粹/战争/罪恶,它们糟蹋纯净的东西——马,即迪弗热这样的人。非常讽刺的是,马替人找鹿,是人奴役着纯净的动物去猎杀另一种纯洁的动物。在最后,迪弗热也负担起了为纳粹政训学校挑选学员的任务:骑着夜色大马,带着一群嗷嗷狂吠的黑色猎犬出没在森林中,毫不留情地捕猎天真的儿童,从而被当地人称作“卡尔腾堡的吃人魔鬼”。
帝国元帅戈林将军
在德国黑森林中,迪弗热见到的,经历的一切皆是一种隐喻。动物园主任交配出了中世纪野牛,放在保护园里,可它们确是些暴躁的疯子,给森林带来恐怖的气氛。当人想改变自然,却往往给自然增添了恐怖。纳粹的人种学理论恐怕也是如此。
这本书的思想精髓就是承载与恶性倒错。承载在神话里是一种使命(责任),爱你的承载物(儿童),即爱你的使命。就是相信这一切都是神圣的。而在恶性倒错的世界里,多少人在这神圣的催眠下做出恐怖的事,变成一个“魔鬼”。
其实,迪弗热热爱自己承担负载的东西,但绝不是看着它们去死亡。他本质善良,内心极其柔软。可是恶性倒错把最善良的人变成魔鬼,把最纯洁的儿童送上死亡的绞刑架。在这一层面上,《桤木王》对任何一个人类时代而言都有很重要的象征寓意。
而我们可以解读出《桤木王》的深刻寓意,那就是说,假如没有意识到存在的恶性倒错,我们将会走向灭亡。唯有救赎,是唯一出路。
于是最后,迪弗热最后靠着肩上的儿童的指引,走入荒野,如那个泥炭沼人一样走在淤泥里。
这一切又是如此得富有象征性意义。
米歇尔·图尼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