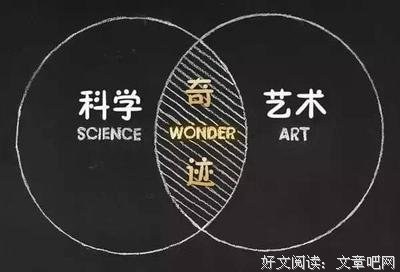《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读后感大全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是一本由[法]卢梭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页数: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精选点评:
●很薄的一篇文章,基于性善论,卢梭认为人应该追寻内心的道德,不要被科学与艺术搅乱内心的质朴。
●很薄的一本,简直浓缩了卢梭怼人的精华!已经盖棺的人可真惨,只能祈祷同样被骂的人帮忙说几句,在世的人估计气到全身颤抖地回信抨击(顺带一万个mmp)。卢梭这个小婊砸也阴险得很,被回击了就说“我骂的是那些不好好对待科学和艺术的人,你干啥自己对号入座”“我没说你的理论使得世风日下,只不过没让世道变好而已。”看到注释里卢梭对那些大佬说“我真服了“的时候差点没笑出猪叫。(虽然我知道这样看是在侮辱你,但真的想说你这出道也太成功了!)
●绝了,既无文学价值,更无哲学价值,不晓得是哪门子的黑屁。反启蒙有八百种方式,你丫偏偏挑了最弱智的那一种
●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忽视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即道德。
●作为一个死宅,我看哭了
●初读还以为是反智主义。。不过当把卢梭对问题的界定明确之后,他的论述确实给我展开了新的视角和提供了宝贵的反思精神。“《纳尔西斯》序言”对理解本书的观点十分重要。
●本来想给五星。卢梭文字的激情之力让我处处动容,确实真诚地想要脱离所谓精英主义的迂腐、自大和势利,而首先将自己审视为人——一个活生生的应具有自然美德的人。但初读之后我仍旧认为其中少些部分论述隐藏着自说自话的臆断危机,不多说,摘抄一句如下:“因为,在一个已无好人和好风俗的环境里,与暗中使坏的骗子生活在一起,总比与明火执仗的强盗生活在一起好一点嘛。” 当然,我也承认这其中不乏由于历史文化背景脱离,甚至个人理解偏差的原因导致对其表述思想的误解,只是暂时我仍以为保持对一切的怀疑态度是较为可靠的做法。 ps.我不否认卢梭的论述批判确实是一个相较其他哲学家来说更加独具特色的思路!
●1749年法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一名,卢梭。
●“它讽刺的不是我,而是我生活的这个世纪”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读后感(一):道德家做科学家,科学还能发展吗
卢梭认为科学艺术的发展使人心生骄奢淫逸,风俗只会变坏。这个论点其实并不引人反感。但是将风俗、道德作为最高评判标准,由于风俗会变坏就抹倒大部分的好处,实在尚可商榷。譬如对于科学,在科学与哲学尚未完全分家的卢梭时代,他认为许多知识毫无作用,是研究者装点门面,普通人浪费时间的东西,可以理解。但他又不拒绝科学的发展,那么怎么办呢?必须由艾萨克牛顿、弗朗西斯培根这样心灵伟大的天才,做出真正能够前进一步的东西,而非浪费时间的东西。说到底,无非是指责重复性工作太多,创造性工作太少。然而若没有社会对于科学事业的肯定、支持,以及充分的参与,仅凭个人天分就可以成为牛顿?恐未必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是渐进和积累的,牛顿亦有师,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是对人心有害的重复工作和无意义中蕴藏着变革。如果一起否定,毁灭所多玛,难免伤及义人罗得。上帝尚为十个义人宽免一城,科学与艺术真的坏到如同所多玛与蛾摩拉? 再譬如风俗淳朴又如何?卢梭动辄称赞马其顿人,动辄将贫穷民族征服富有民族作为风俗淳朴的优势。卢梭认为贫穷民族往往更加富于道德,尚可理解。但是将能征善战当做民族优势的体现,甚至有支持征服者焚烧图书馆的言论,恐怕难以说服从大战中恢复的无辜国家。那么为何能征善战是优势呢,他说体格强健顺应自然,书房研究毫无益处。其实这个论调,还是在说只应该少数有道德的人才应当研究科学,其他人应该顺应自然去劳作。这又回到了上一个问题。只让寥寥几个道德家做科学家,科学还能发展吗?他所设想的各司其职民风淳朴的社会固然不错,但是道德家做科学家与艺术家,可能只是与哲学家为王类似的,社会美好愿望的极端表达罢了。 卢梭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批评者无数。焉知不是过于强调道德,道学气太重,令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的缘故。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读后感(二):现已不可想象能够凭论证文一炮而红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微博上一个在美国读博士的小姐姐说,在她做助教讲课之前白人教授告诉她,学生可能会因为她1亚裔2女性3年轻4矮而不听她的话,但只要她站在讲台上,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鼓励。
这让我想起《光荣与梦想》中记到罗斯福视察夏威夷陆军医院的场景:他到夏威夷本来是要跟海陆空高级将领谈话,制定计划,发动巨大攻势,迫使日本屈膝投降。但在他离开夏威夷之前,他要人用轮车推着他穿过病房,去看看那些被截除上肢或下肢的伤员。他向他们微笑,挥手致意。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他的出现就代替了他要说的一切的话。坐在这轮车上的是一个两腿早已完全瘫痪的人。他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也有过这种心情。然而他克服了过来,当上了总统,他们没有理由感到灰心丧气,以为不再能实现战前所抱的理想。
因为买到的是李平沤译本,所以一旦有逻辑不顺畅或者意指不清之处,先不要怪卢梭,感兴趣可以找英文版或者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版本来读。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读后感(三):启蒙的反思
卢梭开启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在卢梭之前对人间罪恶批判的角色是基督教的牧师和教士,他们受命于天,是从宗教的,带有一种超越性视角来谴责人间的罪恶。而卢梭把这个责任置于知识的掌握者,是卢梭把对人间罪恶的审批拉回到人间之中,从此,人们不需要永恒语境来对现实进行批判,而是直接诉诸于历史和现实之中。
卢梭以真诚的立场为知识分子奠定了对社会批判的基调。卢梭的批评是自然的,他的理性是被情感驱使着,这让他看起来无比的真诚,他把自己的隐私抛之于众,这既满足了公众的偷窥癖又唤醒了读者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情感。
1.唤醒人性的尊严
在卢梭所生活的时代,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与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人们相信可以通过自身理性来认识外部世界,人们相信未来的生活将更加美好和幸福。而卢梭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理性发展的同时人们把外部世界当做研究对象,当人的思维越来越理性化后产生了另一种极端形式,把整个世界包括人都当做研究对象来理解,它们只是一种存在形式,没有生命波动,人变得非常的被动,失去人性的尊严。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拉美特利就认为,人也是一台机器,他有一本书就叫《人是机器》,他说:
“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人并不使用什么更贵重的料子捏出来的;自然只用了一种统一的面粉团子,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变化了这面粉团子的酵料而已。”“动物界的一切都取决于物质组织的不同。”人类并不比自然界其它动物高贵,他们是由相同的质料组成的。拉美特利认为人类的心灵也不过就是一个思维器官而已,他把心灵比作一座钢琴被弹起后发出的琴声,钢琴本身是人类的肉体,这样他就否定了精神实体存在的可能性,思维仅仅是肉体的附庸,世间被还原成一座大型机器。而人的道德与尊严受到前所未有的贬低。
同时,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助长了奢靡之风,而奢靡之风又让科学与艺术得以发展,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光挥霍在科学与艺术上。它们在不知不觉中腐蚀人心,削弱人的勇气,让身体荒废下去,就像哥特人在希腊到处劫掠的时候,却一座图书馆都没有损毁,因为他们认为:把图书馆继续留给希腊人,让他们在图书馆看书,无暇顾及军事操练。
“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日趋完美,我们的心灵便日益腐败”“无论军事上,还是其他类似的事情上,科学研究智慧削弱人的勇气而不会鼓舞人的勇气。”《一论》科学与艺术在更大意义上是人类自身理性发展的延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对理性是持批判立场,它的腐蚀人心方面是双重的,既是道德的沉沦,也是体魄的堕落。
2.回溯自然生活
而卢梭批判的立足点则是对自然状态的假想,他否认人类社会随着理性的发展会更加美好,卢梭赞美所赞美的自然状态,伏尔泰为此多加指责,当卢梭把《二论》寄给伏尔泰后,得到的回复是:
“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谨表感谢。”“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最后伏尔泰还毒舌的说让卢梭应该回到自己的故土瑞士,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享受自由,和故土奶年产的奶,徜徉的大自然中。伏尔泰对卢梭的抨击是否合适暂且不论,但是就卢梭作品内容对自然的赞美承担可见一斑。
卢梭不停地规劝人们去思考自然状态下淳朴的生活,面对的是被欲望驱使下的理性的泛滥,他要唤醒人性的道德尊严。
罗素曾说:我宁愿本体论证明也不喜欢发源于卢梭的烂弄感情的不逻辑。由此可见,感情是卢梭对理性批判的滥觞,他的感情是发乎于内心,带有道德的崇高性,而对欲望是以敌视态度。
卢梭对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在否定,而是以预见性的警惕着理性可能出现的膨胀。或者说卢梭批判的理性是欲望驱使下的理性。卢梭认为它践踏了人的尊严,理性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将被欲望所捕获,成为欲望的奴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被认识是人权的恢复者。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读后感(四):从洛克到卢梭: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兼并
按:史太是不善于写文案的。
约翰·洛克提出了现代国家的表述,其思想被吸纳进《独立宣言》,关于三权分立、私有财产、人民推翻政府等观念,我们对之再熟悉不过了。
在精神方面,野蛮人起初是纯粹动物性的,他们“因为没有任何知识,只具有来源于自然冲动的欲望,所以他的欲望不会超过他的身体的需要。”(p62)然而,大自然赋予了人们超过本能的能力,结果出现了过分满足欲望之人,“生活放荡的人之所以纵欲无度,结果招致疾病和死亡,其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精神一败坏了感官,尽管自然的需要已经满足,但欲念却有无穷的奢望。”(59)
卢梭搜索了各种证明,使得自然状态得以生成的“前理性”动力有两个:一是自我保存;二是同情心。在卢梭看来,野蛮的世界似乎更加文明,卢梭的倾向性难道是回归野蛮的状态?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我们别无选择。
据称,卢梭的核心观念寄寓在《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论卢梭的意图》p70)很显然,卢梭并没有简单的“赞扬野蛮状态”,他自己也声称这是对他荒谬的误解。列奥·施特劳斯以其惯用的显白—隐微二分法在《论卢梭的意图》一文中分析道,《论科学与艺术》面向两类不同的读者,当卢梭拒绝科学时,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面向普通人说实话,然而,作为伪装普通人的哲人,他要站在科学一边。科学与普通人的美德不相容,却能够与“伟大的天才”们相容,科学是坏的,却只是针对整体社会和普罗大众,而对于少数精英,却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公民社会要求一致性,或是把自然人变成公民;相对于人的自然独立,一切社会都是自重奴役的形式。但哲学要求哲人极为真诚地遵从他“自己的天才”,不考虑任何普遍意志或共同的思维方式。(《论卢梭的意图》p79)从这里,我们似乎也能够理解卢梭那些糟糕的行为了,并且他那洋洋得意的忏悔录式的自传,似乎是这样的哲学的最好确证。总之,卢梭的处理方式是试图尽可能保留现代社会,但同样需要古典时代的哲学,同时保留精英和大众两种形态,也就是允许一部分人成为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