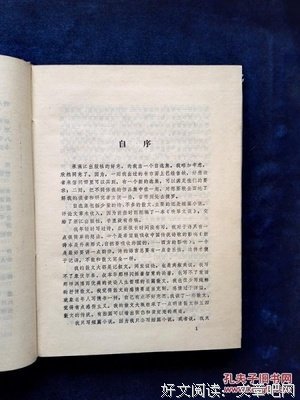汪曾祺自选集读后感精选
《汪曾祺自选集》是一本由汪曾祺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6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汪曾祺自选集》读后感(一):大师之作
汪老真是谦虚的作家,从自序中便可看出:“严格的说,这个集子很难说是自选集。自选集应该是从大量的作品里选出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我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的自选集不是选出了多少篇,而是从我的作品里剔除了一些篇。这不像老农民田间选种,倒有点像老太太择菜”。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大师的作品果然不同凡响,小说羊夕一夜真真的惊艳到我了,朴实无华的语言描述了一幅幅美好恬静的乡土和人文风景画。读来让人感觉清风拂面,异常舒服。
汪老的小说也透有他散文的风采,对果园的描写让我仿佛置身于果园之中,看到了一个个一串串果实挂在枝头等待被收获一样,真的是贴近生活而不俗。读到最后还有些依依不舍,希望能再有这些个好文章继续熏陶我。
好文章好书好作者。大家的作品是你读到最后都舍不得读完的,600页的一本书是我读过最厚的了,没有一丝不想读下去的想法。喜欢,10分都不够。
《汪曾祺自选集》读后感(二):他没有的那种天真去了哪儿
80年代的那一版也有,和家人有点缘分。这个是题外话。不提了。……
汪曾祺没有他老师沈从文的天真,但对人对世道更有余裕,为文内心有掂量,有分寸,朴素只是外现。
给无声知了的眼套上马齿苋的花瓣,也是绝了。写昆明的雨季,才可见柔软的内心,饱含的感情,是真爱,也不愿掩饰。对家乡,更远的距离与怀念,才能出好文。
他对于文章与审美的“和谐”,是自觉的主张。
所有的节点都拒绝铺排。点染之间节制很多,特别讲究收与放的比例。这一点从书画可知,画极简,线条笔墨有书法内功蕴含力量的底子,想起和大才女大画家凌淑华的画对比,有一点相似,又有更多的不同,后者文人画性格鲜明,风格一贯,汪老一画蔬果,就偏向了齐白石。
羡慕他的求学受教历程,其师承体系永远不可再复制。羡慕沈从文给他手批作品。 我私人的感情,是更爱沈。……也不提。只是,汪老也应该有天真的,他的天真去了哪儿?
对于后学,对于高邮现在的文人圈子,其实我有点看法,人人都赞汪老,却不知真正的好处。平淡与素朴,不是想学就能从笔下学的来的。现在出手连浓烈都做不到,连丰盛都没有,连文采文气都没有,是会淡出鸟来的,是开水加凉水,摆摆样子,连自己都不想喝。……写作,不是由奢入俭难,反过来了。
整天“汪味”,“汪味”,看的烦了,学得不像,很蹩脚。
……
本书想照顾多面,收了书画照片,文种分类齐全,但装帧潦草,字体令人不适,应该有上下册分或者其他办法。有点失败。
……
《汪曾祺自选集》读后感(三):书中自有真情在
在病中看这本书,亏得这本书,解救了我病中持续且越来越困顿、焦躁、烦闷的情绪。比起现在流行的心理医生、音乐疗法、舞蹈疗法、禅修……见效快、无副作用、更灵。
汪先生真诚,他说“有人建议我把小说抻一抻,就能成长篇小说了。我为什么要抻?抻了,就不是那个东西了”。
汪先生有趣,他说“人家叫我选自己的作品结成一集,我的作品本来就少,再严格选,就所剩无几了。我挑自己的作品,就像老太太择菜,择完菜,再从那扔掉的一堆里再捡出些能用的,扔回要用的这一堆,这就是我的自选集”。
汪先生有大爱,在这总是推崇成功的社会里,要是没有一股子从心底里涌出来的真挚热爱,他怎么能写出那365行里最普通最低微的劳动者,卖米卖水果卖猪头肉甚至卖蚯蚓、杀猪的、做鞭炮的、捣浆糊的、画画的、洗衣的、和尚、老师……他们的平实、快乐、鲜活、努力的平凡劳动者身上那一直被忽略的光芒。有段写栀子花的“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我就要这么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汪先生写书像宋画,有大家笔法。行文落笔既似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藻修饰的白描画,又似巧密精细的工笔画。由于并不是靠跌宕起伏的情节取胜,所以看书时和刚看完还不觉得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但看完闭卷后,越投入这浮躁的生活越久,越想念那一幅幅留在心里的逸然宋画。
汪先生让我更热爱生活的平凡细微之处,比如“我能听出那叫的鸟儿站在树上的位置”。让我重新看待自己的工作,我是否也能像那些个普通平凡却可爱的劳动者呢?让我第一次想去云南看看,之前看过无数云南画片、风光片、听说过什么丽江邂逅都从没想去过。
明明是书评,怎么写成了汪先生如何如何……也许是因为他既叫《汪曾祺自选集》,自然就看出他的影子了吧,只是这影子也太强烈了。
《汪曾祺自选集》读后感(四):生活的味道
两本汪曾祺先生的书,《自选集》和《生活,是很好玩的》,前前后后看了快三个月时间。说来真是机缘巧合,我这三个月的生活,正好搭上汪先生作品的节奏。
今年六月份,我接到组织通知,经过重重选拔,组织决定让我援藏一年。一个多月前,我来到高原,正式开始了援藏工作。说实话,到高原,我是怀着非常忐忑不安的心情来的。担心高原反应,担心长期缺氧会造成心肌肥大和脑损伤。更担心一年以后,安徽的人和事,将会面目全非。然而随着身体逐渐适应,我开始发现援藏生活的另一面,美的一面。
援藏工作是简单的,因为各种限制,我们做不了什么大活。援藏生活又是单调甚至乏味的,因为我们在的地方,虽然说是市,其实连内地县城都达不到。所以在这没有内地那么多的娱乐活动,也没有内地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正是因为简单和单调,让我能有许多空闲的时间,一眼一帧地、一草一木地欣赏高原的风景。我开始看寺庙房顶上的佛教经轮,看蓝天上缓慢飘动的白云,看纳木错湖边上矗立的雪山,看羊卓雍错湖边的油菜花田,看一朵一朵绽放在高原上的波斯菊,看拉姆拉错神湖边上飘荡的经幡。这是我在内地时候,从来都没有注意过的。因为在内地的生活节奏和情绪,让我绝对不会花费精力在欣赏这些事情上。
援藏生活,让我学会了观察身边一点一滴的事物。这和汪先生的下放生活不谋而合。汪先生说,他可能是中国吃过土豆品种最多的人。他下放的地方是一所农业研究所,研究所觉得他有绘画基础,所以就让他绘制土豆品种目录。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件相当枯燥无味的工作。然而汪先生天生的乐观,让他依然在这件事情中找到了乐趣。他画圆土豆、方土豆,画各种颜色的土豆花,每次画完的最后一道工序,当然是把那些土豆吃掉,烤着吃、生着吃。一样普普通通的土豆,竟能让汪先生作出许多文章来。
说生活啊,她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那酸甜苦辣、不遂人愿的味道。汪先生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经历过文革,一生充满了颠沛流离,也充满了五颜六色。老先生最宝贵的人生哲学,用那部书名《生活,是很好玩的》来概括,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当我们发现日常吃穿住行里面的每一样乐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现人生最大的意义了。我也很喜欢老先生在自选集里的两句话,一句是: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一句是:秋老虎再毒,他也有凉快的时候。再苦再难,一个人也不能被眼前的难击垮,也不能丢了精气神。这个精气神,不一定是与天斗与人斗的那股劲儿。这个精气神,更应该是敢于品尝生活味道的勇气。所以老舍先生跳了太平湖,汪老先生却能怡然自得走完一生。
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活永远只有苦、没有甜,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信的。说这种话的人,他只是缺少发现甜的能力和情绪而已。既然生活不愿意让我们心想事成,那我们就不应该被生活击垮,被生活玩弄于股掌之间。如果我们不能创造甜,那就让我们发现甜。就像高原,虽然低温缺氧,但高原,也有蔚蓝的天空,飘逸的白云。
《汪曾祺自选集》读后感(五):《复仇》多重意识的交织 ——一个和尚&两个和尚
一个和尚&两个和尚
旅行人长途跋涉,他走到一个庙里借宿。这是一座怎样的庙宇?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低头,又抬头。看看天,又看看路。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掠过他的视野。山把所有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他想: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及至走进那个村子,他向上一看,决定上山借宿一宿,明天该折回去了。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了。”
旅行人走过很多路,他几乎用一生寻找他的仇人,一个从没见过的仇人。他有些累了,有些疲倦了,但有些不想走了:“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于是,他走到山路尽头的庙宇。其实,也是他人生路的一个归宿。
在这里,旅行人见到住在庙里的和尚。“蜂蜜和尚”。
庙里只是一个和尚吗?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
旅行人突然喊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们也被吓了一跳。这一刻,我们才知道,庙宇不是一个和尚,这里有另一个和尚。
“这和尚好怪!和尚是一个,蒲团是两个。一个蒲团是和尚自己的,那一个呢?佛案上的经卷也有两份。而他现在住的禅房,分明也不是和尚住的。”
一切仿佛有着冥冥的注定。
然后,我们带着这一个声音向上或往下回溯。
“他在心里画不出和尚的样子。他想和尚如果不是把头剃光,他该有已投多好的白发。一头亮亮的白发在他的心里闪耀着。”
那一刻,旅行人以为那一头白发,是母亲的。但是,他不知道,那一头白发也是他的。另一个和尚,是他。这是神秘的预兆。文章结尾有一句话映照了这个预兆:
“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
为什么流泪?谁流泪?
旅行人。或许他为心中放下没有恨的仇恨流泪。或许他为仇恨放过他而流泪。
全文涌动着非常强烈的意识流。疲倦,仇恨,解脱,三者意识相互交织,非常完整地交代了一个故事。更巧妙地,汪老也用一个镜头的语言,交代了仇人的赎罪。
“好了,到了头:
一堆长发。长发盖着一个人。匍匐着,一手錾子,一手铁锤,低着头,正在开凿膝前的方寸。他一定是听见来人的脚步声了,他不回头,继续开凿。錾子从下向上移动着。一个又一个火花。他的手举起,举起。旅行人看见两只僧衣的袖子。他的披到腰下的长发摇动着。他举起,举起,旅行人看见他的手。这双手!奇瘦,瘦到露骨,都是筋。旅行人后退了一步。和尚回了一下头。一双炽热的眼睛,从披纷的长发后面闪了出来。旅行人木然。举起,举起,火花,火花。再来一个,火花!他差一点晕过去:和尚的手臂上赫然有三个字,针刺的,涂了蓝的,是他的父亲的名字!……”
过去与现在交织,复仇者与被仇恨者相遇,仇人与和尚形象重合,执迷者被渡,仇恨情绪终归于虚无,正应和了卷首的庄子之语:
“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
后记:文章同时通过多重意识交代复仇者破去执迷的过程。这一点也值得细细品味,篇幅所限,暂不在此小文中列举。
《汪曾祺自选集》读后感(六):读《徙》有感
到底意难平
读完汪曾祺的《徙》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大约是上周的时候,读起来很快,读完之后心里只有这一句话:到底意难平。小说不长,但是读起来很有味。在读完之后的一周或两周里(时间好像是一种幻觉,不知不觉往前推移,每一天都有一些模糊),生活中的无数的小细节都在一一照应小说。原来汪曾祺写的不是高先生,也不是高雪,是我们啊。
小说开头以庄子的《逍遥游》开头,也是很有意思,鲲化鹏,扶摇而上,将迁徙于南溟。北海的水不厚,不能够养鲲,所以必须要到达南溟,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是到达南溟却又必须有风。鲲要到达南溟必须乘世道交替兴衰之大运,才能够有所作为成就大业。所谓,时也,命也。
高先生名鹏,字北溟,少孤。少年丧父之后却遇到名师,有一定的天资又知道努力,果然十六岁中了秀才。如此年轻的秀才。但是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总是在猝不及防的地方拐一个弯。中了秀才第二年,停了科举,北溟之鹏徙不了南溟,只好留在小县城里,读了师范,当了先生。高先生认真有原则,出淤泥而不染,在一片浑浊之中坚持自我。在高先生的迁徙之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一生的轨迹与无奈。幼年求学时的苦读,结果废科举,十六岁的秀才给这个无奈的个人悲剧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知道如果不废科举高先生能不能考中功名,光宗耀祖。但是没有假设,时代不会为他妥协,到这个时候科举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你是十岁的秀才都没有用。高先生是一只将要徙往南溟的鹏鸟,但是却等不到他的风和他的运道。只能够在各种尸位素餐的教员中间坚持上好课,教好学生,写一首让所有学生印象深刻的校歌。人就像是沧海中的一粒粟,跟随着时代波浪的起伏在其中挣扎。又有多少人是向涛头而立的弄潮儿?寥寥无几。更多的是等不到风徙不了南溟的鹏鸟。要么自甘堕落混沌走完一生,要么挣扎挣得头破血流最后被命运无情拍息。成功的人除了自身的才华横溢,还有机缘巧合人生际遇,时代的成就。
然而让人耿耿于怀的是高先生的女儿,聪明美丽骄傲的高雪。初三毕业升学,她要读高中家里没钱,高先生叫她读师范。她挣扎不过向现实妥协。在师范学校里在城里,她是一颗明珠,样样出色。又时髦又新派,可惜只在县里教小学。考了两年大学没有考取。岁月蹉跎嫁给了高先生的学生,一个天资聪明却被家人要求学医的青年人。高雪想考大学奈何家中贫寒,无力承担,工作之后想考大学却又碰上战乱大学南迁。她也是想要扶摇而上的鹏鸟,无奈被现实折断了翅膀,又不甘于平淡,最后郁郁而终也是情理之中了。其实钻石和水晶的差别,多在柜台不同,和背后的射光。
两代人两代老师,活得如此苟且。 常常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想,其实人生来就是不自由的。从一出生起,就被无数的牵绊束缚,从基因到社会到时代。宝哥哥娶了宝姐姐,金玉良缘举案齐眉,心底却发出深深叹息:到底意难平。人生的很多抉择,并不是我们自己选的,而是被推过去的,推到它的面前,有且只有一个选项。你从未自由的顺从内心,这个世界也不曾温柔的待你。
心里的不甘是一把火,持续烧灼着,烧灼着,总有一天要燎尽。高先生和解了,自己消化了所有疼痛,高小姐却被熊熊之火燃尽生命。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莫过于清醒的忍受着这世道加诸其身的刀刀凌迟。突然想起朱淑真来,嫁作商人妇抑郁不得志,任才华横溢依然抵抗不了他者的意志,没有选项,元夕夜私会情人是她最激烈的反抗,但是无用。他人即地狱。
《汪曾祺自选集》读后感(七):汪曾祺:一生苦难,却道尽人世欢喜
最开始想要了解汪曾祺,是因为沈从文对他的那句评价“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看到的时候,我很好奇,大千世界文人众多,比汪老先生有名的不在少数,何以独独称他是“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想着想着,就决定拿两本书回来看看。 汪老先生是很受尊敬的文人,世人对他评价皆很高,所以他的著作也一直被大翻大卖,鱼龙混杂,我始终摸不准到底选哪个版本值得来看,直到发现了这本《汪曾祺自选集》,汪老先生在自序中解释说,之所以要出这样一部集子,一是因为当时市面上他的书大多已经缺售,需要一个新的选集满足读者的需求;二是因为这样的搭配组合,可以把他不同体裁的作品融合在一起,方便读者对他进行全面的了解,不用再去四处搜罗。瞬间觉得,正合我意。 《汪曾祺自选集》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据说是“老头儿生前最看重的集子”,包含了汪老先生少量的诗,不多的散文,以及大量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很“汪曾祺”。很汪曾祺的闲情逸致,很汪曾祺的随遇而安,他从不把感情表现得很满,相反,却总是很节制,带有一点音乐性,一点风轻云淡,一点欢喜,一点伤感。和他的人,他的人生,都很像。 苦难也值得享受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这是汪老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让人直觉得讶异,如此欣赏苦难的态度,想必也是汪老先生的作品之所以“纯粹”的原因。 汪老先生一生经历诸多坎坷,曾被打为右派,流落下放,又经历了大革命的批斗,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还隐隐记着当时发生过的事。 一天他照常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他的大字报,说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出现了“右派”的字样,他说,我顿时“傻了”,运动就是这样,突然袭击。像是一场暗算。但在回味之中,他也不忘调侃,说他血压高了,有数据可以证明,还说卫生局为了人民健康,应该制止这种突然性的政治运动。 在这场“暗算”中,他被下放到沙岭子,生活了四年,但这四年过得却不像是下放,反而像是“归隐田园”,听起来颇为享受。他起猪圈,刨冻粪,扛170斤重的粮食,下庄园干着农活,却也读书、写字、画画,享受他的人生。他说他画马铃薯,当然还画萝卜、葱、蘑菇,画各种蔬菜,但主要是马铃薯,画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画了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他画马铃薯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在一间屋子,画完一块,就把那块放在炉子上烤烤,然后吃掉。 在看《汪曾祺自选集》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到了《果园杂记》和《葡萄月令》这两篇散文,他在文里写道“我是个喷波尔多液的能手,我觉得这活有诗意。”他不止一次夸赞喷洒波尔多液的过程,称那蓝色的液体很美,我当时不了解他,从未敢想,这是他在下放时期的经历所写成的文字。那种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关注,不分地点,不分情境。 然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被当作右派批斗,和历经文化大革命时遭受的种种屈辱与痛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疤的,人的心,是脆的。他在说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的文人,自然,也在说他自己。他受了伤,倒却也像是对此从未认真过,他将批定义为是一出荒诞剧,所有上场的人都是角色,而他的角色,只是专心过好他的生活。 写文章是件纯粹的事 汪老先生喜欢静坐,静坐让人得以沉淀,让人思路清晰而饱满。他时常在每天清晨时,静坐一个小时,想想现在,想想过去的人和事,然后把它们串联起来,就成了故事。他的故事大多是这样写的,在静坐的回忆中激发出来的灵感,那灵感不仅自然,而且也纯粹得很。 汪老先生的作品一直有一种和谐之美,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所以在读他的作品时,往往不能过深地挖掘,挖得深了,就跑偏了,就不是汪老先生的本意了。 但也不是说他的作品是可以随随便便来读的,读他的作品,需要对“写文章”这件事,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才行,若全然不懂,只当做热闹,想必能读出个悲喜,却读不出他文字里的精巧,感受不到他文字里的纯粹。 拿《大淖记事》来说,这算是汪老先生作品里顶有名的一篇,他自身对于这篇也赞赏有加。喜欢的人叹它构思精巧,不喜欢的人则称它“头重脚轻”,忘了人物,而在景物环境上耽误了功夫。 翻开《大淖记事》就能明白这种争论的由来。一般的小说,人物都是重点,开门见山,总要在前几回就交待清楚主人公,但这一篇却反其道而行之,主人公硬生生拖到了小说的中间才出现,前面大量的笔墨所写的,都是大淖的环境和风土人情。让人读起来,往往不能“单刀直入”,直觉得没那么痛快。 但《大淖记事》仍然被奉为经典,为什么?其实与它这出人意料的构思方式脱不了干系。汪老先生觉得,这样写文无可厚非,在他看来,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多样的,如果都是一个模子,那也就不能称其为结构了。而如今,我们往往为了结构而结构,少了几分这种洒脱的韵味。 此外,在《大淖记事》中,汪老先生自称有一“神来之笔”,就是当他写到巧云给十一喂药的时候,忽然写到“不知道为了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他也不知为什么要那样写,只是觉得情感使然,觉得应该这样写。 “写作始终要贴着人物,用自己全部的情感去贴着人物,一旦贴不住了,人物就会“飘了”,就不具体了。” 所以在汪老先生的作品里,他一直贴着人物在走,那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创作的,却不是他,相反,他是他们。比如在《异秉》里,张汉说王二“大小解分清”是成功人士的异秉,陈相公和陶先生因此在厕所里相遇;在《受戒》里小英子一句“给你当媳妇”,惊起了一只小水鸟;落魄里,烟鬼的女儿从扬州人的媳妇变成了南京人的媳妇;《鸡鸭名家》里,陆长庚赶鸭子的钱赌输个光光,最后又惊叹一句“没光,还剩一块”…… 他的每一个人物走向都顺理成章,有着天然的悲喜,抑或嘲讽,抑或悲悯,抑或欢愉,这世间的情感,就在这几行字里,被一一道尽。而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一直把自己当做是他们,贴着他们,所以才会有如此纯粹的作品出现。 所以,沈从文那句“纯粹的文人”并不是胡诌的,更不是因为汪老先生是他的学生,为提自己的名声而大加吹捧,汪老先生确实是难得的写文章的人,不为成名,亦不为刻意表达什么,只是单纯的笔墨使然。 而他当作家也是,就如同他自己所说,“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他没有选择,却似乎做得更好。现在的文人想必不同了,刻意的成分太多,刻意追求的太多,刻意得多了,字里行间难免少了几分自在与自然,也就不那么纯粹了。所以想来,沈从文称他是“最后一个”也不无道理。 而今,当写作这件事变得日甚浮华,读一读汪曾祺,受一个感染和熏陶,回归文字的田园,想必是很有必要的罢。
《汪曾祺自选集》读后感(八):雨过碧云秋
纸上我按照惯例列出了“人物”、“内容”、“背景”、“结构”、“主题”五个模块,用于整理文本阅读过程中的可用材料以及确定阅读后的评论方向。在《云致秋行状》真正读过后,“结构”、“主题”“内容”被从纸上划掉了。如同小说的名字,汪曾琪用简单的时间顺序,叙述了“云致秋”这个普通人的生平,没有值得反复提及的情节,(汪曾祺自称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也没有精巧的叙述结构,即使小说主要背景是“文革”时期,也没有登楼望月叹水长东、凭栏吊往杜鹃啼血、去衣行仗龙场顿悟之类的情节。在文中反而更多的是浓厚的烟火气,汪曾琪“美食博主”的名号深入人心,以至于第一页看到致秋的肺病有关牛肉的描写“就每天给他留二斤嫩的,切的跟纸片儿似的,那荷叶包着”我就联想到了《切脍》中的“草鱼切薄片儿”和《手把肉》中的“一手把着一大块肉”。(我总是将牛肉羊肉联系起来,并加之以《水浒传》中的吃法幻想)烟火气还体现在文中浓透的老北京京剧味儿上,行话:“塌了中”、“搭班”、“跨刀”、“卯上”一串一串地冒,《玉堂春》、《四郎探母》、《得意缘》听过没听过的戏剧夺人眼球,透着一股新鲜劲儿(看我这北京腔)。这种烟火气很难让我不想到京派代表老舍,书中的人物似乎因为“今儿就是今儿了”、“我招了谁了”、“讪脸”这些词鲜活起来了。郜元宝《遗珠偶拾》说:“但50年代和老舍短暂的共事使他和这位风格迥异于乃师沈从文的文学前辈结下不解之缘。戏剧(京剧)和民间文学是汪曾祺小说艺术两大资源,这方面老舍的启发超过沈从文。”不仅如此,老舍作品中尤其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月牙儿》里的雏妓、《骆驼祥子》的车夫、《我这一辈子》里的巡警,在这一方面,云致秋虽然是个“有地位”的人,被人“云老板”“云老师”的叫着,在时代的浪潮下,无论是所处的位置和做出的选择,都是无数普通人的缩影。
是的,我认为《云致秋行状》中只有“人物”和“背景”,即小说写的就是(或者就是为了写)“云致秋这个人在文革中怎么样了?”这件事。在我们慢慢了解到云致秋这个“他”在文革前是什么人的时候,一个“我”突兀的出现了。笔者是在小说第六页“我曾经问过致秋:‘你为什么不自己挑班?’”这里才注意到的,实际上小说第一页、第四页、第五页都出现了“我”的参与(小说共26页),第一页“我认识致秋”时这句话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这句话下意识地被认为是一个引入,后文与“我”就从此无关了,而不是像小说中“我”是云致秋的同事,参与并了解云致秋的一些活动。那么,使用这种人称叙事的意义在哪里?谢倩的硕士学位论文《“变”与“不变”: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四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中提到其八十年代叙事人称的转变:由绝大部分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四十年代转向几乎全是第三人称的八十年代。谢倩认为这样转变的原因是“而对于汪曾祺来说第一人称的叙事非常投合40年代作家孤独苦闷心情,小说中主人公的观点、处境、思想都能在作家的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沉淀生活,已进入暮年的作者,本就温和的性格变得更加成熟和淡定,没有了401年代个性彰显的狂躁与坚硬,有的只是除净火气的淡泊和谐。这种情感的表达就不能通过“我”去直接抒发,要借用他人的口吻去完成。”仅仅如此吗?不使用第一人称是可以淡化作者的参与感,也相应地减少主人公的心理描写,这其实与云致秋的性格、作者描写文革的方式是相符合的。即使是描写文革这种风云激荡,红旗染血的年代,作者仍然没有着眼于其残酷性,对主人公文革中境遇的安排也比较缓和(当然这是符合汪曾祺本人和一部分人的经历的),这种相对缓和的残酷命运给“随遇而安”“从众随俗”“跟着谁,傍着谁,立志甘当二路角”的云致秋带来的痛苦是可以想象又无法估量的。让云致秋发挥超常记忆力喋喋不休地自白痛苦有多浓并不是汪曾祺想要描写的重点,我认为是他刻意采用“局外人”的视角使读者更易看清云致秋在命运前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要安排云致秋,这个曾经的戏子,现在的剧团干部,人际关系好到与领导,各大腕儿都‘忘形到尔汝’的“交际花”“宴席专家”、工作严谨细致但有时分不清轻重缓急的,甘当二把手又有些小权的人被迫去做“三件他在平时决定不会做的事”去揭发上级,泄露材料,又在别人受批斗时较早得到解放回到工作,四人帮被打倒后反而闲置,最后孤独死去呢?
这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理念和其个人经历有密切联系。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文学系读书时,受过梅贻琦、沈从文、冯友兰等大师教诲,在《汪曾祺两个年代与其他》中提到“汪曾祺是两种‘现代’的汇合”,继承了包括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传统、老舍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传统,赵树理、孙犁等为代表的延安/北方新民间文学传统,真正实现了新文学内部雅俗合流。《云致秋行状》其实也是他在八十年代一直呼吁的“散文化小说”或者“笔记体小说”的体现,其散文化写作受周作人和废名的影响也体现在此篇小说中“克制感情”、“超越理性直写感觉”“他后来的散文虽多写底层细民,却像专写贵族的《世说新语》那样竭力精准传达人物精神风貌。”但他传递人物精神风貌往往通过一些小事,一两句话,甚至一个小怪癖就使人历历在目(比如满嘴掉字歇后成语的马四喜、“吃饭”——赵旺等),这种风格在其《七十抒怀》中自述“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那么他是什么生活经历呢?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经历与他笔下的云致秋仿佛是一个人,先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1968年因江青“样板戏”的编写要求提前解放,四人帮垮台后反而接受“同志们”时长两年的政治审查,这种“个别性熬炼”的经历使他对命运、“新时期”与“旧时期”的看法再加深了一层。写“云致秋”这个经历身份与他类似的、时代面前随波逐流的“小人物”,像我前文说的,没有一定主题是不太准确的。汪曾祺自序是“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正如王小慧《汪曾祺的“内伤痕”》一文中概括的,汪曾祺的伤痕是内化的,无论是在文革开始,还是文革后期,汪曾祺都深深地体会到了“政治权威”面前“小人物”的“无可奈何”。他选择的是将这段时期所受的“内心伤害”展现给众人看,而非去呼吁去揭露。无论是内容还是方式,我觉得都是更加贴近我们“被迫害者”,大多数人的逆来顺受处境的。他像大多数人那样,“忠实于 、顺服于命运”并“关心在命运中辗转挣扎的平凡人物的内心,和这些平凡人物一起‘思想’一起体验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按别人哪怕是多数人的思想去思想”,这种对世事的看淡、看透,甚至对现实的疏离也体现在云致秋“死前”:我算是个什么人的疑问和“死后”:向来相送人, 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境遇里,我甚至感受到了加缪“反抗者”的精神,在察觉到世界的荒诞之后,这一点尤其在文革刚开始时“云致秋完全懵了”那一段能够得到体现,他习惯的世界分崩离析,以至于“他发现他是孤孤打打一个人活在这个乱乱糟糟的世界上,这可真是难哪!”,这与加缪说的“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里,人会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他的境遇就像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终身流放,因为他忘却了所有关于失去家乡的回忆,也没有即将到来的那种希望,这样一种与生活的分离,与环境的分离,真实地构成了荒诞的感觉。”这种人与生活的离异让云致秋感到痛苦,身体的病痛也没有给他重构价值的时间,他就已经死去。但死前“石校长”:“这个人很有用……”和死后常常有人念叨“这会要是有云致秋这样一个又懂业务,又能做保卫工作的党员,就好了!”,“一个人死后,还会有人想起他,就算不错。”表示了作者对他的肯定。而他在被闲置后得到工作,即使身体不允许,也想早点到戏校上班,用录音机接连录了五六天的音。这表示,云致秋虽然是个随波逐流的人,但在遭受命运的重击之后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仍然看重“眼前事”,我想,汪曾祺写这一个故事,在悼念亡友、记叙自己和普通人在特殊年代的内伤痕以外,还要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就应该像云致秋一样,有爬起来的勇气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