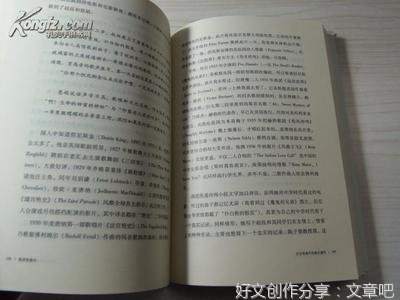李萌:重读张爱玲
再次翻开张爱玲的书,那凄婉优美的文采和撼人心灵的故事依旧会让我有很大触动。从《半生缘》到《倾城之恋》,从《金锁记》到《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她的字里行间,我读到的是一壶微苦的茉莉香片,吹开那缭绕的烟雾,一股清香透出,喝下口去,那丝微苦萦绕口际。看张爱玲的文章,就像在照镜子一样,爱过痛过之后才更加懂得。
很喜欢这个冷眼看世界的女人,喜欢她阴冷、空灵、典雅、精致的文字,喜欢她描述夏天时这样说:“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起来。”喜欢她在面对世人指责她和胡兰成的量年婚姻,被人认为是“汉奸文人”时的洒脱:“只要我喜欢,确实什么都不管。”她就像是一缕冷香,可以用来熏香制造情调,又如一株奇异的荆棘,在闹市凡尘中,的确少有,难以复制。她曾这样说自己:“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癖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欣赏张爱玲的同时却又心疼她,该是怎样经历的女子才能写出如此让人痛心的文字。
李昂这样说她:“这个女人好像替我以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任何一个作家,被人喜欢是由于他的作品,而被人迷恋则一般会有其他原因,面对为数众多的“张迷”,恐怕不是一句“张爱玲只是文章写得好”就能敷衍的。用木心的话评价她就是:“她称得上‘活过’、‘写过’、‘爱过’。”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看到触不到,亦近亦远,神秘而又真实,一句“爱情可以让人忘记时间,时间也可以让人忘记爱情”就足以让人动容。
重读张爱玲,读到的依旧是那一抹清香里的微苦,亦是苦也不愿松口。
丁伦义:去过陈家山
从小生长在渭北煤城铜川矿区的人们,或多或少的对煤城矿区各个矿井的印象耳濡目染。亲情之间的相互流动,朋友之间的相互走动,同事之间的相互调动,沟通了遍布矿区的山山卯卯,把整个铜川矿区原本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人们融合成了具有煤城特点的矿工群和家属群。
其中每个矿井的人们都有自己鲜活的特色,而作为铜川矿区后起之秀的陈家山矿,却集结了矿区众多矿井的特色,在经历的几十年发展历程中,基本上是作为铜川矿区的支柱矿井的姿态展现在铜川矿区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同事一起走进了陈家山。匆忙的行程使我们成了匆忙的过客,对陈家山的感觉只是相识过。后来,林林总总的消息、报道,把陈家山矿推到了公众视线的最前沿。再后来,直至我们矿的矿长调任陈家山矿矿长,又使我对陈家山产生了莫明的思念和回忆。
特别是近期出现的百年罕见的暴雨洪水,冲垮了陈家山矿的桥梁和路基,肆虐的洪水使陈家山矿几度成为“孤岛”。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每每直视垮塌的房屋,无不使我心情凝重。有一次,看到老矿长挽起裤脚,查看冲垮的道路,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默默的祈福。
在与家人的通话中,得知生我养我的矿区,同样遭受了特大暴雨的冲刷,好多危险地段的人们都被迫转移,但是,在矿区领导的通盘部署下,受灾乡亲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近两天,天气预报说是陕北和关中地区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我明白的知道,我的家乡和陈家山矿区一定做好了各项应急防范准备工作,但仍然把先前看到的图片看了多遍---
我不想表白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是怎样的忧国忧民,只想表达我对铜川矿区的家乡和陈家山矿的一缕牵挂,因为,我生长在铜川矿区,我去过陈家山,那里有我的老矿长和众多的矿区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