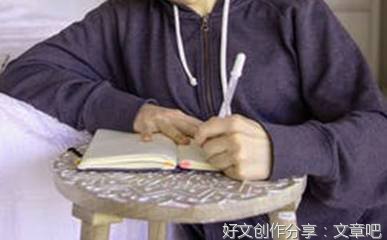最后的讲义读后感1000字
《最后的讲义》是一本由[日] 大林宣彦著作,海峡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2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讲义》读后感(一):最后的讲义——电影即哲学
《最后的讲义——电影即哲学》
恰逢周六值班,在单位事情不多,随手拿起来《最后的讲义——电影即哲学》一书读起来,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阅读完毕,没有任何压力,不像《枢纽》《穆斯林的葬礼》《文明之光》等书籍那么厚重,一本书拿起来需要读很久,所耗费的时间那么长。
这本书来源于作者讲述的《最后一课》的主要授课内容,有作者开始的讲课环节,还有最后的问答环节,都是摘取的精华内容,“取其精华”,至于有没有“弃其糟粕”以及弃了多少,尚不可知,毕竟没有完整的看过授课视频。
作者向死而生的这种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当做生活的结尾来度过,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多去考虑一下,能够产生多少价值和什么样的意义,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二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年的生日都会看一部电影叫做《遗愿清单》,以此来警醒自己,初心不能忘,要在有限的生的时光里,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少在生命的尽头留下遗憾,向世界证明,我曾经来过,努力奋斗过,也比较喜欢知识网红罗振宇的一句话,“做一件有价值的事,一直做,然后等待时间的回报”,做一个长期主义者。
通过此书了解到了更多的日本导演以及相关著名电影,一下子拓宽了观影视野,“一部电影一本书,一场游戏一场梦”,电影是浓缩的精华,短时间内将人物故事情节及电影哲学传递给了观众,是难得的艺术表现形式,之前很少接触无声电影,觉得黑白影像,没有声音,会是索然无味的,至此以后改变了想法,想必后期会观看类似的题材电影吧。
《最后的讲义》读后感(二):“电影不是看得很开心转头就能忘的娱乐。”
我平时很喜欢看各种电影,也会专门抽出时间来读书,却是第一次读和电影相关的书籍。
封面的配色很好看~
大林宣彦很真诚很用心地表达了对下一代电影人的心声和期望,作为早期独立电影的先驱者之一,拍电影之前先把想要传达给观众的哲思想清楚,已经成为大林导演的习惯和拍摄宗旨。
生长于战争年代的导演,对生与死之间的界限早已模糊,怀着“最后一次”的觉悟,把每件事都当成最后一次来做,这样就能更加慎重、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呈现出的结果也就更让人满意、不留遗憾。
还有对日本战败的反思与和平的期待,对过去的回忆与未来的祈盼,他的想法都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被传递出来。
这虽然是大林导演的最后一课,对新一代导演人却是崭新的一课。
日常看电影时,由于个人经历阅历有限,对电影中传达出的很多观点和隐藏信息都不太能理解到,读完这本书后,开始对电影背后的故事感兴趣了。了解电影背后的故事,这是深刻理解电影主题的方法之一。
“不能光把电影当做娱乐,而要去感受它背后的哲理。”不只是观众,更是那些电影相关的创作者,怀着表达哲理和思考的想法做出的电影,才有机会成为好电影。
现实世界并不和平,也不快乐,但它总有一天会变得快乐又和平。掌权的强者做不到的事情,弱者却能做到,这就是“美好结局“。电影就是在传达这种美好。
在书中读电影,在电影中看书,世界上的美好事物总会在各个角落以某种形式交汇、相融,最终构成一部部艺术作品。
《最后的讲义》读后感(三):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1
2019年,知乎推送一则提问:心动是庸俗的吗?
高赞回答说:心动就是庸俗的,好比一朵花开,一场雨后彩虹,你看到就心动了,仅仅出于本能。如此唾手可得,世间万物的心动不过落于俗套。
这则回答一度让我心灰意冷。
时隔三年,书里的大林宣彦道:我们一直以来都太过轻视依靠本能的生活方式了。人类对知性的过于依赖,让人逐渐失去了动物的本能。
本能就是所谓的心性。
当我读到这一句,恍惚间回想起好友曾斥责高赞回答:“怎么可能庸俗?心动是最可遇不可求的。”她说,“仅仅因为心动就想永远留下花开和彩虹,才是庸俗的。”
当时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袭击了我,只感到富含哲理,却道不清这令人无所遁形的哲理是什么,更无法找到情绪的出路,甚至梦见化身沟口,朝金阁寺举起暴烈的火把。在那个湿闷的夏日黄昏里醒来,仓惶慌张催生出偏激,我藏身牛角尖里对自己说:不要试图留下任何美好,因为我没有创造美好的资格。
但这结论如此单薄鲁莽,大林宣彦一戳即破,终于解开我发酵的疑惑。
这段讲述美极了。
人面对事物可以做出不同反应,可以用任何形式把这些反应记录下来。
原来这是我们私人的事情,对事物本身没有半点影响。
原来我们该留住的不是事物,而是面对事物能做出反应的心性。所以心动才可遇不可求,所以心动才至关重要。
原来矛盾点在于,“永远留下”并不包括“表达”。
心动是本能,看到事物就想表达,也是源于人的本能。
留不住的风,摘不下的花,永远会在午夜梦回勾起我们的记挂。世间八苦,求不得如小石硌磨心头血肉,一旦想起就心潮汹涌。所以我们趋利避害,一再抛弃情绪的触发物,后来连心动的本能也摒弃,和许多饱经疼痛的大人并肩站在岸边,看潮水奔涌,不用再被浪花沾湿衣角。决定是否做事前先衡量利弊,并谓之理性,宣扬理性战胜感性。
大林宣彦做了不同的选择。经历过战争噩梦的孩子,长大后坚决留在对岸,要当依靠本能心性去思考事件根源的人。不能改变过去,但可以塑造未来,是战后的人,同时要阻止孩子们成为战前的一代。
“我一定要通过作品体现想法,但我绝不喊口号。”大林宣彦如是说。
看了太多遍,不到一周就翻旧了
2
用电影传达哲理,听起来就很枯燥。
一说出口就想起无数鱼龙混杂的电影,强行煽情硬造升华,尴尬的特效里爹味十足,回头看见豆瓣上的低分还控诉观众不懂艺术,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电影是艺术,但对普罗大众来说,归根到底是种娱乐。
书中有听众提出类似问题,而大林导演的观点很有意思。
电影的本质并不是在娱乐作品中强插哲理,而是要基于哲理来创作娱乐作品。技术进步是好事,但先确定用最新的技术再强加哲理就是失败。
哲理一词对我来说很晦涩,百度说主要是探讨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形态。简而言之就是成为人的意义。
一辈子都在拍反战电影的老爷爷,眼花缭乱的鬼怪、少女和血河之上,汩汩流淌着对战争的思考。
想起被人称为“五毛特效”的《花筐》,画面过于绚丽浓艳,看完后眩晕感仍阵阵冲击,恍若浮生一梦。战争就是动荡,一切寻常无奇的美景和青春都会因此变得光怪陆离,一半现实一半梦境,少女莹润的侧脸替之以蘑菇云,血揉碎在海里。
专注于电影本身而没空研究哲理,但看完之后没人会想对战争鼓掌叫好。
“不知不觉地将一些很有冲击力的观点传达给大众”,看,五毛特效又如何,导演的目的就是达到了。
虽说是“终于”,但黑泽明曾说大林宣彦“从入行开始一直都是这么创作的,真好!”
3
有人说,比起反战,大林导演更想传达的是厌恶战争。深以为然。
反对是立场,是一种经过(或不经过)逻辑思考后得出的自认为正确的态度。而厌恶是发自内心的本能反应。书中屡次提到日本战败,并不是要因此忿忿不平,是对人类发动战争的行为深深厌倦。
只有本能上厌恶战争,才不会为了遗忘战争而去拥抱它,用一场争斗平息另一场胜负。在他们几位厌战导演眼中,恐惧和虚无感是战后一代的阴影。不太了解那段历史,回想仅看完的几部相关电影,竟才心有余悸。
从前看电影不会特意了解剧组人员,总觉得作品和作者是两回事,有时挖掘出作者生平反而会影响对作品本身的观感。《电影即哲学》算是第一回破例,读完感慨万分,对此类作品有了改观。原来创作者免不了要把自己投影到作品里。
《花筐》开拍前,大林导演确诊肺癌。原本剩下三个月的死亡倒计时并不准确,上映三年后,大林宣彦才宣告人生落幕。这场讲座是他去世前两年播放的,从开头就毫不避讳死亡。
不是探讨死亡本身,而是“拍完之前绝对不要死”。
之前读日本文学就喜欢“一生悬命”这个词,欣赏把人生活到极致的主人公。当现实里真的出现这种人,免不得要细看两眼,原来真有那么几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日本文学总有“物哀”,于是人之必死的悲往往与美相通。提及淀川长治、小津安二郎等故人,字里行间总透着悲壮,怀抱梦想死去,所以美极。
他真的爱电影,才会许下如此心愿,大概多少也想踩着悲壮的脚印走黄泉路。面对当代种种娱乐乱象,不可能不沮丧灰心,却仍坚持用“文艺复兴”的手法拍摄电影,仿若不肯倒下的最后旗帜,只能在炽烈热爱的事业里逝去。
不知最后大林导演在想什么,直到遗作《海边电影院》也没改变拍摄风格,像是穿越来的人仍执着地活在属于他的年代,始终坚持老电影的方式拍摄当代作品。
但比起《花筐》对浪费的大幅描述,《海》留下了一线生机。之前的电影都把人拉进梦中再一棒槌醒,《海》则像一场梦,结局温柔所以不必急于醒来。
一生只梦一场,一梦就是一生。
合上书,暴雨如瀑冲刷玻璃窗,虚无摇晃在半空。想起大学周末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一部接一部放长电影。外头是嘈杂的街道,里头是窗帘隔绝的异世界。暗房里堆满奥利奥和桶装酸奶,唯一的光源自屏幕里的爱恨情仇。当时并没发觉,无意间竟领悟了许多人生哲理。那些体验无比快活,只希望这样的光与影能持续十年,二十年,一百年。
“我的日常生活,仿佛就发生在虚构的空间当中。”
“好似我就生活在电影当中。”
“好似我就生活在电影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