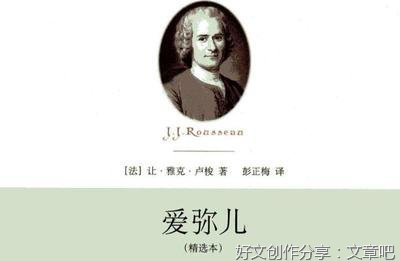刀子和刀子读后感1000字
《刀子和刀子》是一本由何大草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4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刀子和刀子》读后感(一):这把名为青春的刀
“何风”、“何锋”、“风子”、甚至“疯子”,却没人叫她本命“何凤”。她也认为自己仿若男人那样洒脱,不似所有的女子那般。她寸头、陆战靴,喜欢刀子。她视麦麦德为指引人生的导师,她有两把刀子。
简单、正义、讨厌懦弱,喜欢强者,在外人面前为父亲虚构了一个身份。父母在生活中的缺席,让她在喜欢的人面前会变得“女人”,那是她最瞧不起的样子。她认为自己的人生没什么经历,甚至不如麦麦德的流水账。人生总是会有相遇,有人会不经意间推动涟漪。转学生的入场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风子似乎成了青春期男孩彼此角力的工具。身边人也都因为各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被迫站队,来了去去了来。学校高层的肮脏更是将风子卷入其中,让她迷茫甚至恐惧。爱的人离开,新的人出现,情感的割裂让她更“堕落”了些。只有那个对她有着不一样感情的同性好友一直陪伴着她,与风子不同,她心思细腻,城府深沉。她不相信男人,看透风子身边男人的一切却不告诉风子,让她自己受伤看清,可惜最后她也离开了风子。
她的第一把刀是她父亲给的,而那又是父亲的战友也就是妈妈的情人给他的。她那喜爱的刀子的原主人,带走了她的妈妈。她的第二把刀是她恋人给的,而那恋人也是同所有故事一般离开,毕竟并非在一起就是有个好结果的。她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一把刀子。懵懂、痛苦、这些伤了人又自戕的刀子,构成了风子的青春。
书中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把刀子。正如我们的青春,也是一把刀子。
《刀子和刀子》读后感(二):那些欲望和怒火无穷燃烧的夏日青春
女孩子就应该只喜欢花裙子、留长发吗?女孩子就应该温温柔柔,哭起来惹人怜爱吗?并不是这样的,女孩子也可以留板寸,也可以暴力,也可以拥有守护自己的刀子。风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留着寸头,带着两把刀子在泡桐中学念书,这两把刀子都对她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第一把刀,是十二岁的时候一个叔叔带给她的,后来这个叔叔也带走了妈妈;第二把刀是十八岁生日礼物,来自一名叫陶陶的男孩,后来这个男孩和另外一个女孩走了。
风子迷恋着刀子,就像其他女孩迷恋香气扑鼻的花朵一样,虽然在风子的故事里也有花朵,但是花朵丛中始终安静地沉睡着闪亮的刀子。在泡桐中学,每个孩子都是正常的,只是当我们用不正常的眼光去看待这群孩子,我们就会觉得每个孩子都不正常。无论是转学过来的包京生和金贵,还是陶陶和阿利,还是朱朱和瘸腿的伊娃,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的秘密和情绪,那些在那个年岁是正常的事情,或许在成年人的眼中都是不正常的。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总是会回想起属于我的青春,在那些时光里也有着数不清的人和事,庆幸的是没有变成疼痛的青春,但还是拥有着无限的叛逆和怒火。我也感受过书中陶陶和阿利一种人的那种小团体生活,也曾经像伊娃一样写一些文字,也曾经像风子一样不懂自己为何和一个男孩在一起,也不懂自己为何会说“不”,也曾像朱朱一样对一个朋友无限度的好。
朱朱在书中说过一句话,“谁说的清呢,男孩的心思”,的确,就像看完小说的我并不明白陶陶的心思,为何会丢下风子和伊娃在一起,又在后来离开伊娃;我不明白包京生的心思,他为何对所有人都表现出嚣张跋扈的态度;我不明白阿利的心思,为什么愿意当别人的小弟,而谁又是他真正的朋友;我不明白金贵为什么执拗得像一把钝刀,他奇怪的思维方式是不是也在表达着些什么。
我的青春就像书中的青春一样,总是炽热地暴露在夏日烈阳下,所有情绪都被翻搅晒干,那些看起来不正常的怒火总是从心底滋生。我也希望我可以像风子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刀子,即便不是实质性的刀,但事可以保护自己不再受伤的刀。
《刀子和刀子》读后感(三):平行宇宙里的另一个青春
《刀子和刀子》初版于2003年,正值我的大学时期。手上拿着的是乐府的再版,在这近二十年来的四个版本中,这是装帧最棒的一版。封面上的书名,似用刀一笔笔刻在灰黑色的墙上而成,藏不住的情绪和张力。下面写着:“十八岁少女的刚烈与深情,欲望和怒火无穷燃烧的夏日青春”。
我生长于西南山区的小县城,没有太多入学选择,在当地的重点学校一路顺遂地读下来,考入外地开始大学生涯。大概是早熟的缘故,我的青春,有波澜却不惊,有伤心却不痛,有叛逆却也大多被消化在心底。
作为老师父母眼中的乖乖女,书中的青春,好似在平行宇宙里。学校里当然是有那样的小群体,那些被称为”混社会“的同学,耳边也会飘来一些”放学后风场坝见“的约架信息,但回想起来,这一类的故事都在在传说里,并未真正存在于我的生活。这本书,意外地让我触碰到了那个平行宇宙里的青春。
风子是刚烈的,陶陶是矛盾的,包京生是霸道的,朱朱是隐秘的,阿利是怯懦的,金贵是深藏不露的,伊娃是清醒的。在这个宇宙里,青春暴躁、冲动、不顾后果、残缺而真实。而大人们,蒋校长、宋小豆、任主任,小任,风子的父母,阿利的父母,他们或懦弱、或自私、或精于算计,作为老师、家长,他们或缺位、或无能、或冷漠、或暴力。他们,是青春背后的推手,是造成残缺的原因。
因此对故事本身,我谈不上有多少共鸣,也并不向往这样的青春。但只用了两天,就读完了整本书,主要归功于作者的文字风格。跟《春山》不太一样,《刀子和刀子》的文字就像刀子,锋利而闪光。作者用文字建造出了一种弥漫全书的特别气质,明知危险却忍不住被深深吸引。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我很久不说话了,我的嘴巴都要发臭了,看来的确是应该跟谁谈一谈了。就像把下水道的盖子揭开,敞一敞吧。跟谁谈呢,最好就是你这样的人吧,跟我素昧平生,不晓得我的过去和我的今后,只晓得我就是我说出的那一堆东西。那一堆东西里边有诚实也有谎言,当诚实多于谎言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肉馅很小的包子,虽然不上口,却经得住饿。可当谎言掩盖住诚实的时候,它就像一杯浇了冰激凌的非洲黑咖啡,在舔去了甜蜜之后,苦得你发慌。你别笑,我哪懂得什么哲学,哲学不是我这种人能谈的,也不是一个女孩子该谈的,对不对?我只是打了一个比方,用这种方式先谈谈自己,也许就说明我还是很正常的吧。”
刀刀见血对不?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这样的语言和开始,会不会也吸引到了你?
2007年,《刀子和刀子》被改编成了电影《十三棵泡桐》,读完书后,对电影充满了好奇。希望小说文字独特的气质,能被影像很好地呈现和还原。期待何大草老师的下一本书。
《刀子和刀子》读后感(四):痛楚的青春挽歌 犀利的生存寓言
今年夏天,乐府文化推出了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的最新修订版。
作家何大草在自己39岁那年,决定要写一部关于青春的小说。40岁那年,他完成了《刀子和刀子》。他这样概括小说的创作动机:“如果把它读作成长故事,它就是一部青春的挽歌;如果把它看成丛林法则,它就是关于生存的寓言。”
《刀子和刀子》不止是青春小说,而是一个度过了青春岁月的人回望青春,作者一面用少女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世界,一面用成年人的眼光来看待那个校园,这两种眼光交融在一起,使得小说兼具青春与沧桑、迷惘与透彻两种特质。
《刀子和刀子》首版于2003年,其后两次再版,并于2006年被改编成电影《十三棵泡桐》,该片入围了第1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评委会特别奖。
我们想和读者分享何大草老师的两篇创作谈(文章有删节),分别收录于2003年与2008年出版的《刀子和刀子》。
我的左脸
——《刀子和刀子》2003年版后记
我并不特别钟爱自己的左脸,却常常写到它,说到它,并以它为题,写下这篇后记。这是因为当我以左脸示人的时候,左脸恰好遮蔽住了我的右脸。如同一座喧闹的庭院,在它的背荫处,一定是藏着格外的安静,和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的确是一部关于秘密的书籍。它不全部是我本人的经历,但可以视为是某个人成长的自传。我熟悉这个人,就像我的左脸熟悉我的右脸,就像一个人熟悉自己逝去的青春。里尔克喟叹一声,“夏日曾经很盛大……”这不朽的诗句,一定写于秋风刮过了原野。青春的时候,我们何曾珍惜过青春?青春只有活在记忆里,才日甚一日,刻骨铭心。我熟悉这部书中的每个人,他们都活在我的身体中,活了好多年,就像何凤的刀慢慢割着我的肉。我感觉到他们在长大,他们在说话,他们说,割开一道口子吧,让我们钻出来!于是,他们真的出来了,他们从我切开的皮肤下边浸出来。我每在键盘上敲打一个字,都觉得有一点锥心的痛。
我是从秋天开始写作的。山里的秋天,草木正达到最后的丰茂。到处都是安静得很的,安静得可以听到光线在墙上移动的声音呢。当然,也可以听到小说中的人物,在憔悴、深情地述说着。述说一种最日常的生活,但却被我们可怕地忽略了。他们的故事并不另类,他们另类那就好了,另类成了时尚,成了做秀,谁都可以竞相模仿。他们不是另类,在一个迷漫着偶像和可乐的时代,他们的青春那么深色而又倔强。噢,其实他们从来如此,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们这种人,他们都以这种深色存在着,看起来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其实血管里喧哗又骚动。何凤也许是我的同桌,陶陶可能是我的哥们,而金贵大概正是我远在故乡的弟兄。我希望他们是超越年代活着的,他们是从我们身上撕裂出去的一部分,善或者是恶。就像我从戈尔丁的《蝇王》、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里,部分地看到了我自己。
最后完成这部小说,山里已经是第二年的秋天了。其间经过一个溽热的夏天,那真是一个少有的苦夏,新居刚刚落成,空调还没有安装,民工还在浴室里敲敲打打,做着修补工作。我埋头写着《刀子和刀子》,汗水啪搭啪搭地滴进键盘,把夏天的汗腻和郁闷,都浸染进了小说。小说发生的时间原来是在冬天,但我借着自己的汗水,把季节整个地改了过来。这应该是一个夏天的故事,夏天是欲望的季节,每一个毛孔都在秘密地张开。
全书二十万字,我一共修改了五稿。每次打开电脑阅读它,我都会伸长了鼻子,像猎狗一样在寻找让我不安的字句。我反复地修改它,我发现耐心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变得更加密实了,就像一棵北方的树,缓慢的生长,使它的织体紧凑又紧凑。我一向不信任高产的作家,一挥而就的作品,仿佛雨后迅速滋生的蘑菇,水汽淋漓、色彩鲜艳,然而,蘑菇也还是蘑菇。
曾经有人问过我,《刀子和刀子》是一部什么题材的小说?我难以回答,只能笑笑,不置可否。别人就哦一声,说,是高中生题材吧?我不能再装傻瓜了,要么点点头,要么摇摇头。但是,答案真就这么简单吗?如果《金阁寺》可以称作少年题材小说,《百年孤独》可以称作乡镇题材小说,那我也没意见。可是,题材可以覆盖它们的内涵吗?我以为小说只有两种分法,要么是好小说,要么是坏小说。坏小说其实什么都不是,它最多也只能写到一马平川,马是马、骡是骡。好小说不是一马平川,是起伏的山脉、丰饶的森林,藏着沟壑、陷阱、意外和惊讶。《刀子和刀子》我写的是十八九岁的男人和女人,为此我花去了全部人生的积累,因为那些人一直活在我的身体里,和我的经验、失败一起成长着。
又到了一年的夏天了,我楼下的树林里,布谷鸟还在日夜揪心地叫。布谷鸟是心事重重的鸟,是憔悴又倔强的鸟。布谷鸟叫了几千年了,它的叫声如同我们总以左脸示人,向别人掩饰着而又提醒着,它曾经有过的往事和秘密。
成都狮子山桂苑
2003年6月1日
时 间
——《刀子和刀子》2008年版后记
2002年6月,我的学生肖涛毕业前买了一本美国作家坎宁安的《丽影萍踪》送给我,作为我们师生之谊的纪念。谢谢肖涛,这是一本好书。那时我正窝在狮子山一座红砖楼的顶层写《刀子和刀子》。天气炎热,楼顶又没有隔热层,我写得汗水嘀嗒,心坎发痛,也很痛快。写得累了,就读几页《丽影萍踪》。这部长篇细腻、优雅,自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忧伤。我英语不好,但也能认出书的原名“The Hours”指示着时间,和丽影、萍踪并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遗憾。后来这部小说拍了电影,获了大奖,影碟流传时,名字已经翻译为《时时刻刻》。这个名字我是比较喜欢的,虽然它还未说尽我对时间的理解:无所不在的流逝,无所不在的重现。
我们常说,时间把人改变了。然而,我们可能忘了说,时间又把人带了回去了。我不止一次地发现,人活过了九十岁,他看待世道人心的方式,就和一个九岁的儿童差不多。我怎么会在已不年轻的时候,去写一部跟青春有关的《刀子和刀子》呢?我曾经想得很清楚,我应该写出这样一本书:
如果把它读作成长故事,它就是一部青春的挽歌;如果把它看成丛林法则,它就是关于生存的寓言。
2001年10月,我常一个人在山间铁路边的槐林中盘桓。槐叶茂密而细碎,已在微微地泛黄,有一阵风吹过,就窸窣作响,满山满谷地乱飞。秋风、黄叶,没让我怅然或伤感,相反,觉得是说不出的有力量、有生气,绚丽而庄严,宛如我喜欢的一类文字,不轻浮、不轻佻,既丰饶、饱满,又颗粒结实、肌理细致;即便有戏谑、有愤怒,也是蕴含着深情的。10月31日晚上,我在红砖楼里敲下了《刀子和刀子》的第一句话。随后,为了这本书,我把整整一遍的四季都给写穿了。2002年7月,我过生日那天,携着尚未杀青的《刀子和刀子》,搬到了桂苑一幢新的宿舍楼。《刀子和刀子》在2003年初版时,红砖楼已经被推倒、铲平,无影无踪了。旧楼故址,辟成了一条新大路,通向南校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踩过去、踩过来,脚步如潮。
《刀子和刀子》出版后,是一本引起争议的书。改编成电影《十三棵泡桐》,在国际上得了奖,也还是一部有争议的影片。我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然而又挺正常,没有锋刃的刀子,大概只能算是钝器吧。《十三棵泡桐》的导演吕乐,是极有才华的导演和摄影家,也是个低调、谦逊的人,和他的几次交流,都让我感觉很愉快。我对像他这样内敛而内心又充满力量的人,素来很敬佩。
是什么让我们远离了浮躁呢?应该是定力。我的定力并不十分够,但我愿意去努力。写出了《刀子和刀子》后,又过去了五六年,我一直还在认真地写,慢慢地写,写出了《盲春秋》《我的左脸》《所有的乡愁》,跟《刀子和刀子》不同,这三部长篇都指向了逝去的时光。写作是艰苦而孤独的劳作。它带来了什么呢?乐观地说,它改变了我自己,我面对我的文字就像面对镜子,看到一个能在时间中保持成长的人,有力量踩着小路走。
那么悲观地说呢?我以为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悲观”,只有一种比乐观更为复杂的心情。坎宁安在《时时刻刻》结尾处借克拉丽莎的内心独白说出的一段话,正是我深以为然的感喟:“我们呕心沥血创作小说,尽管我们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亦充满最崇高的愿望,然而,我们的书却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便酣然入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珍爱这座城市,这个早晨,并对未来充满极大的希冀。惟有上苍知晓我们如何热爱它。”
成都摸底河
2008年1月,大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