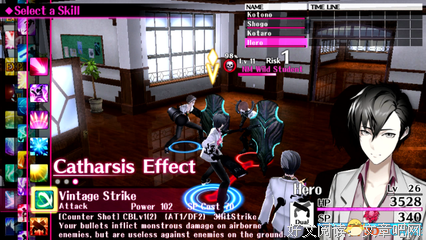卡利古拉的读后感10篇
《卡利古拉》是一本由(法)阿尔贝·加缪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136图书,本书定价:22,页数:201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卡利古拉》读后感(一):卡利古拉与局外人
加缪自己在《西西弗神话》谈过哲学与创作关系问题,他的结论和古往今来的那些作家一致,创作最好的部分就是话留三分的部分。一旦作家自以为掌握并宣称某种真理时,创作就走向低级了。
但他的荒诞哲学在《卡利古拉》里呈现出一种主动、积极扩张的态势,就像他的反抗哲学在《鼠疫》里一样。因为人不能永生,因为得不到月亮,因为无法得到永恒,身为皇帝的卡利古拉感觉人生了然无趣,既然没有那么一种充满激情的绝对,那么人世的一切慰藉与幸福都是妥协,彼岸的希望也是欺骗,卡里古拉不仅本人无法容忍,也不能容忍他的王国中存在这种自欺欺人。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推到极致处,就是自杀和杀人的合法性,而这种逻辑是大多数暴行的来源。听起来挺熟悉,一股尼采的味道。在《卡利古拉》加缪的这种荒诞逻辑也像轰隆隆的拖拉机碾压过字句,文本,截然把自身立在读者面前。
局外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加缪的哲学在其中体现为被动的,荒诞人默尔索抗拒他人意义的渗透,而在这本书里,荒诞人卡里古拉要把他的荒诞推论推及到他人。默尔索的沉默远比卡利古拉的宏篇大论、装神弄鬼要有力。这说明所谓荒诞哲学可能只能是个人的,被动的。或者在其受到损害时,才能透射出力量。或者说,荒诞只是人生途中的一个中点,在这个针尖般的点上,我们只有翘起一只脚,战战兢兢地单腿站立着,而无空间邀请别人相与。加缪当然知道这不是终点。
加缪的小说都是理念小说。局外人比别本成功是因为这种理念被包裹得更好,种种矛盾的司法细节如同理念在自身周遭吐出的丝,于是理念的面目被包裹,退回深处,而外部一层层环绕的丝是小说最优美而复杂的部分。预审法官、陪审团,国家指定辩护律师,这些完全符合小说创造时的当时法。和卡夫卡这个法学博士相比,记者出身的加缪在触及司法程序时反倒显得更加有依有据。
由于默尔索在和别人的较量中始终处于守势,始终被动,他几乎没有机会也不想让别人明白他的看法,他疲于应对各种压力的进攻,于是荒诞在文本的压力中缓慢渗出了,就像石油因岩石的压力而渗出。回到《卡里古拉》,当文本和人物都呈现一种进攻的态势,只是向读者暴露了一种逻辑推向极端的哲学的幼稚,毕竟,加缪在写下这部剧时也只有二十五岁。
《卡利古拉》读后感(二):生于荒诞,死于虚无
“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一生创作和思考的两大主题可以归结为四个字:“荒诞”和“反抗”。如果说《反抗者》是全面阐释他反抗思想的理论力作,那么他的哲理随笔《西西弗神话》则是对于荒诞哲理最集中的阐释。这两本书都是理论著作,换成中文语境很难完全读懂,所以我今天要谈的是一部剧本——《卡利古拉》,加缪将其与《局外人》、《西西弗神话》一同视为“荒诞三部曲”。尽管加缪曾明确表示对该剧的“价值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但却又是他耗费其心血最多的作品,是他第一次独立创作的戏剧作品,从首次公演以来数次修改。通过舞台上的卡利古拉形象,我们也更能直观的感受到加缪的荒诞哲学。
剧本主要讲的是作为国王的卡利古拉认识到世界的荒诞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疯狂反抗的举动。在打乱国家机构的政治经济学、动摇社会道德基础后,他甚至要在亵渎神灵之后试图对其进行取代。加缪称卡利古拉的行为是一场高级的自杀行动,在剧本最后,疯狂的卡利古拉认识到自己同样有罪后在沉重的夜晚中享受这孤独和痛苦的同时,作为高歌杀戮者的幸福的卡利古拉在谋反者的致命一击中烟消云散。我们只能在历史的阴云中对卡利古拉形象进行回溯,尽管在死亡的最后一刻,这位反叛者还高喊“我还活着”。
通过在不同层面上(演员,教师,自由人,艺术家)去比对卡利古拉的多重身份,我们无疑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卡利古拉的拯救世人的欲望不能满足,因情绪错乱而进入疯狂状态,进入扮演角色而后想用实际行动教会臣民反抗,意图使所有人自由,却面临着自由与损害的悖论。而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无不渗透这他的艺术家/诗人的气质。
如果放在与哲理随笔《西西弗神话》相同的坐标上,我们似乎更能理解卡利古拉的行为与动机,这部剧本用一种特殊的情境向我们展示了关于自杀,荒诞,自由,存在等哲学问题实践。卡利古拉不仅是个宣教者,也是一个践行者,是荒诞处境中的荒诞的人。在这中间,卡利古拉多重身份的背反和哲学与实践中的矛盾激发出的更多的能量使得人们对其展开思考,同时由个人感性经验推导出世界存在的存在主义者们面临这与社会实践的幼稚的尴尬处境在今天看来仍旧具有反思意义。如果存在主义者们的个人存在,总是悲观颓废的色彩,然后随着孤寂烦恼畏惧和绝望,最后迎来死亡的话。那么充满激情的满口谵语的疯狂的卡利古拉的最后下场,实在是命中注定。
如果深入比对,西西弗一个人的修行只能是关于幸福的神话,而掌握巨大权力的进入社会卡利古拉也许因杀戮和清醒享受这幸福,却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西西弗作为神的无产者因知晓自己的悲惨状态的深厚而无能为力于是默默反抗从而完成自己的胜利(西西弗,这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却又在反抗,他知道他的悲惨的状况多么深广)。那卡利古拉正是作为有产者的精神世界的痛苦和奋起反抗,用尽所有心力一事无成同时又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强有力的破坏。二者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又具有一定的辩证和互补的色彩。
如此看来,那么在异化变形以及荒诞感严重侵袭人类精神和物质世界的今天,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又变得异常重要。
卡利古拉想在这荒诞的世界上通过欲望的完全实现来对抗这荒诞吗?他是因为握有这无限的权柄而完全自由了吗?剧中卡利古拉反复说出的这个词:自由,其实正是整出戏的荒诞所在。自由,是在欲望之外的事物,是欲望不可企及的实在界。而我们的行动与言语,是在象征界围绕无法化解的内核而展开的症状。
真正的误解在于,卡利古拉的自由行动从不自由,他的欲望从不是他本人的欲望。欲望的本质是他人的。卡利古拉的欲望其实只是他人欲望的折射。在舞台上作为背景的一面面镜子正揭示出了这一点。卡利古拉对大臣妻子的凌辱,不正是大臣本身的欲望吗?而大臣的欲望,又是欲望他人的欲望。在这欲望之三劫连环中,无穷的能指导向不在场的所指。
卡利古拉反复寻找的那一个事物:月亮。却无法寻找到。月亮,正是自身无法发光,折射他人的光。而卡利古拉则是折射他人的欲望。但是我们却一直以为他是太阳。
《卡利古拉》读后感(三):卡里古拉神话:关于荒诞的实践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援引索瓦热关于头脑错乱与感情变化的关系:我们头脑中的错乱是我们盲目屈从于我们的欲望,我们不能控制和平息感情的结果,由此导致了迷狂,厌恶和不良嗜好,伤感引发的忧郁,遭拒绝后的暴怒,狂饮暴食,意志消沉以及引起最糟糕的疾病—疯癫的各种恶习。 从这个科学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卡里古拉》中主人公一系列的疯狂表征中得出头脑错乱的原因:得到不可能得到之物的欲望。这个悖论式的原因使得卡里古拉做出一系列荒诞的实践。
如果把《卡里古拉》作为加缪荒诞哲学的图解并不为过,加缪把其视为“荒诞三部曲”,与小说《局外人》和哲学散文集《西绪福斯神话》来整体构思。尽管加缪曾明确表示对该剧的“价值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但却又是加缪耗费其心血最多的作品,是他第一次独立创作的戏剧作品,从首次公演以来数次修改。通过舞台上的卡里古拉形象,我们也更能直观的感受到加缪的关于荒诞的哲学。
剧本主要讲的是作为国王的卡里古拉认识到世界的荒诞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疯狂反抗的举动。在打乱国家机构的政治经济学动摇社会道德基础后甚至要在亵渎神灵之后试图对其进行取代。加缪称卡里古拉的行为是一场高级自杀的行动,在剧本最后,疯狂的卡里古拉认识到自己同样有罪后在沉重的夜晚中享受这孤独和痛苦的同时,作为高歌杀戮者的幸福的卡里古拉在谋反者的致命一击中烟消云散。我们只能在历史的阴云中对卡里古拉形象进行回溯,尽管在死亡的最后一刻,这位反叛者还高喊“我还活着”。
在这里通过卡里古拉多重身份的形象的分析,试图对加缪笔下的荒诞世界中荒诞的人的形象进行一次深度的探寻。
作为演员的卡里古拉
加缪是这样写卡里古拉的登上舞台的:“悄悄从左侧上,神态异常,衣衫肮脏不堪,头发湿漉漉的,双腿沾满了泥水,几次抬手捂住自己的嘴,咕噜着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
神态异常是其疯癫的表征,就和之后充满激情的自毁倾向和强有力的恐怖主义式的破坏一样,卡里古拉已经为接下来的演出画好了浓妆。
卡里古拉做出了改变,由一个完美的得体的做事一丝不苟的皇帝变成了一个残酷的暴君。作为演员的卡里古拉在白日天光之下面对臣子们的演出,滑稽又荒诞。
加缪写道:“这就是荒诞的矛盾本身,就是那个想达到和体验一切的人,就是那个徒劳的企图,就是那种没有意义的固执,永远自相矛盾的东西却在演员身上统一起来了。”
剧本中多次出现镜子的意象,作为演员上台前的必要工具,卡里古拉也必须在面向观众时重整衣容。卡里古拉第一次登场时变走向镜子。同时,镜子作为卡里古拉的真实形象的扩张,在全剧中如同卡里古拉的权力的重影统治着整个舞台:第一幕结束时,卡里古拉用指头戳着镜子高喊:记忆不存在了,所有面孔都逃开了,留下的只有卡里古拉。而在最后一幕的结束,卡里古拉同样在镜子中观察自己,之后用板凳掷向镜子,镜子破碎的那一刻,谋反者涌入。
似乎卡里古拉只有面对镜子的那一刻才是真实的,只有面对镜子的时候才能对自己强有力的逻辑的再次肯定和对孤独和虚空状态的逃离。
同时剧本中还出现了两次关于卡里古拉的扮演和表演。一个是卡里古拉滑稽的装扮成一身维纳斯女神,痛苦和舞蹈的女神。一个是身穿舞女的短裙,头插鲜花,像演中国皮影戏一样出现又消失在屏幕上,同样滑稽。
很明显,卡里古拉的渎神的目的是为了销毁神迹然后成为神,装扮成命运销售自己的哲学。而装扮舞女的意图则更加隐蔽,加缪在《荒诞与自杀》中互文式的写道:这个舞蹈既是基本的,又是细腻的,精神可以分析其形象,然后阐明之,并且再次亲身体验。于是,剧本中的如同鸡肋的不露头面渐渐消失的舞蹈显得格外重要:对贵族和臣民的最后的宣教。
作为教师的卡里古拉
究竟是什么导致卡里古拉选择登上戏剧舞台呢?是爱情的丧失?贵族们觉得这个理由更加感人;是乱伦暴露,贵族们觉得这是可以但是要谨慎。而作为一个拥有洞察力的旁观者埃利孔说出了真相:一切都是因为不自由。
因为失去妹妹(爱情)后的情感错乱。是加缪附加给卡里古拉大彻大悟前的一个标志。
其实乱伦并不重要,爱情也并不重要,对卡里古拉进行任何的心理/精神分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卡里古拉做出了改变。
贵族们纷纷强调以国家利益为重时,强调皇帝要识大体,终于职守时,卡里古拉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如今的状态无法让人容忍,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卡里古拉的欲望无法满足,他拒绝作为皇帝的责任。他想要获得自由,想要获得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同时作为一国之君,还要让所有人活在真实之中。卡里古拉,要做一个言之有物的教师。
卡里古拉说道:“人必有一死,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卡里古拉似乎认识到当下的荒诞的处境,于是用他强有力的激情充当救世主的形象。于是作为国王的他动用自己的权力对自己的王国进行改造。他的最终任务是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这是一个悖论。但卡里古拉坚信,只要坚持到底,遵循逻辑,有始有终就够了。
当然,面对镜子的卡里古拉也曾对其行为进行过反思,面对杀人如麻的自己,卡里古拉想就算不可能得到的东西马上得到,也不能走回头路,必须走向终结。这是卡里古拉走向毁灭的道路:毁灭世界和毁灭自己同样重要。
卡里古拉口中的真实是存在主义者们的世界观:这个世界是荒诞的。而卡里古拉并不像西绪福斯一样是个被压迫者,卡里古拉拥有绝对的权力和一定的自由,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激情(癫狂)和行动力必将把世界改造,因此竟然放弃休息。这时的卡里古拉,是力比多严重过剩的狂人形象。
作为君主的卡里古拉先从经济问题入手:通过打乱国家的政治经济来实现他的极权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取消子女财产继承权,捐给国家,处死财阀);之后动摇社会基础,道德感丧失(藐视贵族夺走他们的妻子儿女和金钱);然后亵渎宗教,扮作维纳斯;最后掐死自己的情人,杀死最后的爱,在杀戮和毁灭中得到幸福。
卡里古拉通过改造国家机器,道德伦理,宗教神圣和最后的爱来改造世界和解放自己。在其中仍旧能看出某种变化。前两幕的改造国家机器和道德伦理是在做一个积极的社会层面的变革,虽然手段十分之不人道,但这种恶德所积蓄的力量强大的具有毁灭性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加缪曾说过,卡里古拉的失败在因为否定人。是的,卡里古拉似乎在刻意的否定人道主义,他说,他的明火执仗的掠夺并不比往民用必需品的价格里偷偷塞税道德,统治就是掠夺。他简明扼要的阐释了自己的统治术。他用战争和瘟疫为自己辩解,人道主义在他看来是一种无以为继的遮羞布,似乎野蛮和罪恶的手段的实行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的话一切都可以被谅解。
而正是因为一个崇高的理想,他并不害怕死亡,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圣徒的献身。他之所以草菅人命是因为自己本身就视死如归。以至于后两幕的卡里古拉装神弄鬼,恢复宗教和内心的自省,他似乎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尽管加缪试图从卡里古拉身上用极端的方式阐述资本主义的丑恶,但于此同时还能从他身上反思某种扭曲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时的卡里古拉的大教师形象是积极的在用变态的形式激起臣民做出改变,进行反抗。
而后卡里古拉似乎认识到社会改造的不可能性,所以在最后的杀戮中同样为自己辩解,我生活,我杀戮,我行使毁灭者的无限的权力。我是唯一一个自由的人,杀戮的幸福的人,最后才能领悟,于是一个社会革新者认识到其实还存在另一种幸福,贫瘠的美好的幸福,庸庸碌碌。当一个从自己真实情感体验的存在主义者认识到世界的荒诞,并试图进行社会改造的时候,他就已经失败了。
中途面对镜子他也产生过迟疑,但他明确是要遵照逻辑继续到底,进行最后的反抗。而直到对诗人的彻底失望,对空虚感的悲痛,对命运降临的等待,是卡里古拉最后的抉择。这反抗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加缪说我的方法只有一个,问题在于坚持。
当然,作为“大教师者”的卡里古拉在具有清晰洞察力的埃利孔看来,是一个什么都要管的理想主义者,他早就预言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其实,无论幸福与否,生活在如何糟糕的环境中,人们总要吃饭。自由并不是多么重要。所以,即使卡里古拉的逻辑具有重要性,但这套逻辑是有害的,妨碍大家的,是危险的,所以卡里古拉必须消失。
作为自由人的卡里古拉
卡里古拉也声称自己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自由人,唯一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的一名局外人,他看到自己的国民如此不幸福,他选择了撕裂他们身处的幻觉和伪饰的布景。这是不人道的一种手段。
卡里古拉说道:这个世界并不重要,谁承认这一点,谁就获得自由。]整个罗马城唯独他自由,而他要将自由赏赐给他的臣民,考验随着而来。
卡里古拉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权力是在疯癫之后所争取来的。他选择逃离了贤良皇帝的身份,走向暴君的深渊。但是卡里古拉站在启蒙主义者的高度姿态对荒诞的世界进行反抗,用不自由和虚假的方式教给臣民们自由和真实,这又是一个悖论。直到后来的卡里古拉才明白:似乎普世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后来的卡里古拉心里明白一个人要自由,就必须要损害别人。
后来拥有绝对权力的卡里古拉在自由的情境里(把最后的爱卡索尼娅都给掐死)沦为了虚空。这时的卡里古拉就连病态的拯救者形象也不再是了,他是一个毁灭者。所有人的幸福并不可能达到,但他选择为自己辩护:他认为自己得到了幸福,毁灭者的杀戮者的幸福。但他又承认,自己的自由并不是好的,人类永远有罪。
加缪说:“荒诞的人应该明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赖以生存的幻想之上的那个关于自由的假设一直在束缚着他,他成了自由的奴隶。”[ 《西绪福斯神话》 新星出版社 2012 57页]自由作为个人最根本的特性。卡里古拉认识到个人的存在之后,寻找到了自己的个性,拒绝帝王的标签。尽管他一直声称自己是罗马第一个获得自由的人,实质上卡里古拉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得到了自由。同时,相伴而来的,是生命坠入了虚空。于是,卡里古拉在狂想般的谵语和消灭一切的强大行动力之后,在友谊和爱情的消失和战友的死去后陷入虚空。
荒诞的人得晓自己处在一个荒诞的环境之中时所面临的三种选择:肉体的自杀,精神的消亡,和反抗。荒诞者以一种孤独的努力在日复一日的反抗中获得唯一的真理。卡里古拉的死不是和这个世界和解,而是想方设法的穷尽一切,并且穷尽自己。似乎只有死亡才能到达自由,但这又是与加缪的荒诞哲学相悖的。
卡里古拉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但他还是高喊:“历史上见,历史上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努力证明自己还活着。尽管他知道,存在主义者不相信未来,他只能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一颗流星。
作为艺术家的卡里古拉
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卡里古拉是在是一位在思想和行为一致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他的纯粹的恶的品质会让人感到尊敬。尼采称这种人是“不合时宜的人”。他想让所有人的思考,把他最荒唐的思想像一把匕首一样插入现实,就像是强奸。
这是作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卡里古拉的纯粹。所以卡里古拉的毁灭性的作为只是为了一个诗意的表达:寻找月亮。这悬而未决的月亮到底指代什么呢?卡里古拉说,月亮就是幸福或者永生,需要的东西也许是荒唐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所以我们又不能说卡里古拉是疯癫的,因为他十分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我们只能说卡里古拉是疯狂的,属于诗人的狂想。
卡里古拉说:“恰恰是因为不可能,问题就在于不可能。再确切点儿说,就是要使不可能变为可能。”是呀,诗人的狂想。贵族们称卡里古拉喜欢文学喜欢的过分,而在大臣们的聚会中,舍雷亚询问诗歌到底能不能造成死亡。卡索尼娅说卡里古拉正在写一篇阐述诗歌的屠杀能力的雄文《利剑》。而同诗人西皮翁的对谈中,泯恩仇,称知己。而对诗人的失望是他的改造计划化为泡影的最后一击,他心甘情愿的迈向死亡,并以真正的行动践行生活的最伟大艺术。思想和行为上的统一,是作为艺术家的卡里古拉最伟大的地方。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恐怖才被他的艺术家的疯狂给消解掉了。
只有把卡里古拉放在艺术家的精神层面上来看,才更能理解当舍雷亚说,“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应该为这个世界辩护;眼睁睁看着人生的意义化为乌有,生存的理由消失,这才是残忍的;人生在世,不能毫无缘由;卡里古拉的思想一旦胜利,就意味着世界末日;这种哲学无懈可击,只能依靠武力”时卡里古拉的不屑一顾,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卡里古拉承认世界是荒诞的,撕破美好现实的虚假布景,作为艺术家的卡里古拉从内心的情感体验出发,藐视国家机器的机械运作,指向真实。所以正因为是行不可能之事,所以又极其显得可爱,正像堂吉诃德手持利剑与风车决斗一般。
通过在不同层面上(演员,教师,自由人,艺术家)去比对卡里古拉的多重身份,我们无疑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卡里古拉的拯救世人的欲望不能满足,因情绪错乱而进入疯狂状态,进入扮演角色而后想用实际行动教会臣民反抗,意图使所有人自由,却面临这自由与损害的悖论。而卡里古拉的所作所为无不渗透这他的艺术家/诗人的气质。
如果放在与加缪的哲学散文《西绪福斯神话》的坐标上,我们似乎更能理解卡里古拉的行为与动作,《卡里古拉》用一种特殊的情境向我们展示了关于自杀,荒诞,自由,存在等哲学问题实践。卡里古拉不仅是个宣教者,也是一个践行者,是荒诞处境中的荒诞的人。在此其中,卡里古拉多重身份的背反和哲学与实践中的矛盾激发出的更多的能量使得人们对其展开思考,同时由个人感性经验推导出世界存在的存在主义者们面临这与社会实践的幼稚的尴尬处境在今天看来仍旧具有反思意义。如果存在主义者们的个人存在,总是悲观颓废的色彩,然后随着孤寂烦恼畏惧和绝望,最后迎来死亡的话。那么充满激情的满口谵语的疯狂的卡里古拉的最后下场,实在是命中注定。
如果深入比对,西绪福斯一个人的修行只能是关于幸福的神话,而掌握巨大权力的进入社会卡里古拉也许因杀戮和清醒享受这幸福,却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西绪福斯作为神的无产者因知晓自己的悲惨状态的深厚而无能为力于是默默反抗从而完成自己的胜利,[ 西绪福斯,这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却又在反抗,他知道他的悲惨的状况多么深广。]那卡里古拉正是作为有产者的精神世界的痛苦和奋起反抗,用尽所有心力一事无成同时又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强有力的破坏。二者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又具有一定的辩证和互补的色彩。
如此看来,那么在异化变形以及荒诞感严重侵袭人类精神和物质世界的今天,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又变得异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