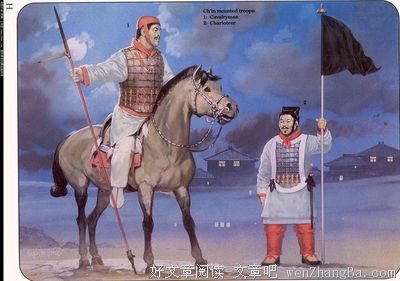战争年代如何看待“逃”
读过一篇文章,名叫《潘先生在难中》,所谓的难即在军阀混战前夕。难中即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落荒而逃。以潘先生为代表,去论述一些自私,胆小怕是,内心矛盾的一群人。战争年代如何逃成了一大问题。怎样粗鲁的逃却又不失风度,或妻离子散,或全家齐跑。跑的时候也不忘记眼前的利益,究竟如何做到在别人的眼里高尚又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矛盾,于是出现了“潘先生”。
归根于底,逃分为三种,一种有权有势,心理和行动齐行动。一种是没有思想,处于社会最低阶级,社会生活全靠别人的推动,过着混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最后一种则是处于社会中层阶级,既想满足自己的利益又不想失去自己的身份。这是最聪明的人更是活着最累的人。
中国于1840年拉开鸦片战争的序幕,这时候中国人思想过于迟顿,并未感觉到战争到来会怎样。于是出现一大批站在岸上看海边的人,看一个个炮弹如何进入中国,更对外来事物侃侃而谈。谈坐在轮船上的洋鬼子,看各种各样抽着大烟的国人。直到后来慈禧太后也看上了鸦片。我不知道多久以后的她是怎样拉着光绪帝东逃西窜的,历史给予怎样的评价不得而知,但是我想说的是心理上害怕行动上早已规划,等到一定时候觉得可以了再出来压压惊。是啊,一个老人,一个小孩,怎能够不怕外来者呢?论谁都怕,可怕的结果还不是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令,你是正真的逃掉了吗?论一个国家,所有人都不逃,像那些看热脑的人,等待灾难的到来,知道有人觉醒大喊一声,战争来了,国家亦会灭亡。怎样逃,是像大狗一样看还是像老鼠一样逃?这是问题。 (很有哲理的日志 www.wenzhangba.com)
如果行动不能满足一个人的私欲,那么思想可以摆布一切。
不论是慈禧思想中的如何去应对敌人还是鲁迅笔下阿Q精神,思想总是很容易满足。潘先生想着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去安全的地方,这对思想无非是一种解放。行动让自己知道,他们已经去了安全的地方,思想让自己明白,私欲可以这样埋在心底,让表面上自己奉献于事业,不论国家如何自己也坚守岗位,多伟大呢?这条贱命怎有国家的事业重大呢?这就不逃吧,我的行动思想早已决定。于是,战争尚未来,人心早可猜。我说阿Q他只是虚拟的代表,他并未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活成了一类人,一类活在自己的世界无法自拔。不论生活如何欺侮他,他绝不反抗,我如何逃,逃与不逃总会有人指点,我总知道我是正确的。所以阿Q让我们知道他并不会去逃跑。所以这是一群不敢面对现实的人,一群自欺欺人的人,他们自称一派,成了无思想,无行动与慈禧相比,他们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还有一类人叫做潘先生。有了思想却无法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是一类中层阶级。他们思想强烈,却不敢像邓世昌谭嗣同那些人直接反抗起来。这些人拿起自己的武器去猛烈的抨击别人,无论有多不满意绝不直击死亡。我说他们怎可局限于眼前的不满而一命呜呼了?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怎可让好汉吃了眼前亏呢?你们行动上可以制止我,思想上怎可以禁锢我。而我可以在人前叫你一声大人,心里却想着你这卑鄙小人。这类表里不一的人最容易适应社会,更容易生存。技术刚好,嘴上功夫了的,可是当今社会却缺了这类人才,我不该大笑我该狂笑。而我是真心实意的厌恶这类人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就是自私的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踩着别人的肩往上爬,爬的时候还不忘记抱怨几句话。这值的思考。
如今年代少了战争却多了战事,而战事的受害人还是这群“潘先生”,如何看待逃跑,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