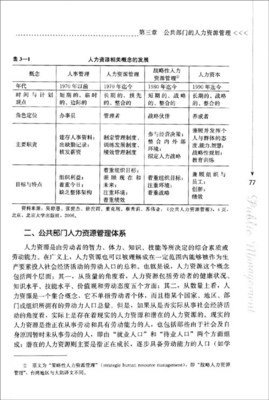公共法哲学读后感精选10篇
《公共法哲学》是一本由孙国东著作,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9.00元,页数:201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公共法哲学》读后感(一):《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孙国东)
《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作者:孙国东;版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年11月)法哲学,即法律哲学(Philosophy of Law)。一般而言,凡是涉及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都可归属于法哲学。作为非法学领域的读者,我们也可将之简单理解成关于法的、最基本的哲学思维。与社会科学绝大多数学科一样,法哲学首先是一门专业知识,追求学科化、技术化,并以此在学科体系获得正当性。
而青年法学家孙国东则“为了超越各种专科化的视野,恢复中国法律秩序之建构的公共属性”,长期致力于提出并发展一种“转型法哲学”,他在新著《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中又称之为“公共法哲学”。所谓“公共”者,需直面中国现实议题,需敏锐而兼具胆识的问题意识,而不只是教室黑板或学术期刊上的理论知识。他的“公共法哲学”围绕“现代转型”展开学理研究,介入真实世界的分析,有问题反思,有展望图景。全书包括“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转型中国的法治与转型中国的正义等篇章。中国需要努力进展为一个更全面更深度的现代国家,通览该书或许更能体会“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和意义。
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9/03/02/552035.html
《公共法哲学》读后感(二):“罗尔斯之问”的中国回声 ——孙国东《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读后
刘 杰*
当代政治哲学巨擘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如何从正义的角度来探寻一个 “良序社会”。贯穿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本人提出的这一问题:“如果说,一种使权力服从其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义社会不可能出现,而人民普遍无道德――如果还不是无可救药的犬儒主义者和自我中心论者――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以康德的口吻发问: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是否还有价值?”[1]事实上,这一“罗尔斯之问”堪称政治哲学研究的出发点。环顾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迅疾发展,社会财富攒聚,社会变迁剧烈,但我们也看到一个因为城市化和现代化所导致的愈发不平等的社会,继而导致人们对于改革的共同预期发生变化,共识破裂,公共商谈的机会空间愈发逼仄,社会正义落入到一个泥淖之中。面对如此形势,任何有现实关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无法熟视无睹,而当用自己的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做出学术上的回应。
孙国东的新著《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2]正是这种值得赞赏的学术努力。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他所界定的“邓正来问题”出发,提出迈向“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第二部分则对适合于中国情境的“功能主义法治观”进行了实体性理论建构,并从法治社会层面对“法治中国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回应;第三部分则分别以“底线正义”诸原则、“关联性正义”和“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等原创性的理论建构,对中国情境中正义问题的共时性、正义问题的整体性和文化正义问题进行了回应。作为一个跨越法哲学、政治哲学乃至社会学、历史学等的跨学科研究,《公共法哲学》一书为我们勾勒了直面中国情境的“正义议程”。可以说,该书堪称对前述“罗尔斯之问”的中国回声(事实上,该书第六章关于“底线正义”诸原则的建构,恰恰沿着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逻辑,并以中国特有的结构化情境为参照而形成的)。
众所周知,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建构源自“原初状态”这样一个思想试验。“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处于“无知之幕”之下:他们既对自己和其他各方的身份和地位一无所知,也对他们将处于何种社会和历史条件一无所知。正是从“原初状态”出发,罗尔斯推演出了著名的“正义二原则”(差异原则和平等原则),因为它们是处于原初状态的各方当事人最合乎理性的选择。之所以使用“无知之幕”作为立约的起点,意图是将那些任意的属于运气部分的个人禀赋及结构化的不平等归结为“上天的自然博彩”,遵循一个起点意义上的平等。
通过分析“反正义的公平”观念的思想渊源(中国文化中的机会公平传统)、意识结构(20世纪人民共和革命所形成的“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话语基础(当代中国实践哲学中的权利话语),特别是更具有结构性和塑造性的“背景制度”(当下中国缺失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孙国东引导我们洞察到三种可从社会基本结构层面超越“反正义的公平”观念的正义议程:(1)保障经济正义/分配正义(落实“实质性的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2)建构公共商谈(公共自主)的政治机制;(3)厉行法治。沿着罗尔斯的学理逻辑,同时参照中国作为“非丰裕社会”的文明发展阶段、转型中国不存在罗尔斯式“差别原则”的适用前提等结构化情境,孙国东最终确立以上三个正义议程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并明确提出我们应秉持经济正义(分配正义)优先的正义原则。这一关于“底线正义”诸原则的建构,恰恰是当代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正义观念出发的——他称为“反正义的公平观”,即一味诉求形式的公平,丝毫不管在道德甚至法律上是否“应得”的观念。
显然,政治哲学层面的“思想实验”并不能遮蔽政治世界的复杂性,就像逻辑不能代替历史一样,我们终将回到“社会实在”而思虑正义实现的社会基础。质言之,正义理论真的可以超越被罗尔斯“无知之幕”所屏蔽掉的社会历史条件吗?或者说,正义理论不应该面对真实的社会情境吗?事实上,正如孙国东在该书中指出的,罗尔斯本人关于“正义优先性”原则的论证,也是以文明发展的特定阶段(也就是西方社会基本满足要求的“丰裕社会”)为前提的。因此,孙国东尤为重视对在中国语境中探讨正义理论的实践约束条件,他将这种实践约束条件的称为“结构化情境”,即“经由历史的积淀、社会的演化和政治的博弈而形成的某些相对固化的情境”。
在《公共法哲学》一书中,孙国东直面了“差序格局”这一制约法治中国实现的文化—社会结构——他将其称为“法治的中国结”。不过,他对“差序格局”的研究,不是走向他所批判的“文化不可变迁论”,而是借用社会学家莫顿“以功能替代促进文化变迁”的思想。在他看来,社会结构层面的人格不平等与社会关系层面的自我主义,固然是中国式差序格局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所发挥的“反功能”,但只要通过某些“社会基础秩序”的建构所实现的社会正义和社会建设之实质性推进,我们完全有可能纠偏、甚至消除这种局面,进而形成与法治中国相适应的人格平等和公民精神。
通过分析差序格局的再生产机制及其与法治的冲突,整合法哲学、法律文化、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孙国东得出了如下结论:社会正义的推进(普惠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社会成员人格平等的实现,亦助益于公民精神的化育;社会建设(包括社会组织建设和现代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则可以更直接地规约差序格局的自我主义取向,从而有助于公民精神的化育。因此,社会正义的推进、社会组织建设和现代信用体系建设,是城市化背景下法治中国建设的三大“社会基础工程”。
当然,《公共法哲学》一书由于关涉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这一具有宏大关怀的议题,内容颇为广博,而本文只是简要勾画了《公共法哲学》一书中与“罗尔斯之问”有关的研究部分,鉴于它是基于中国情境对理想法律和政治秩序的理论建构,我们可以在总体上将其视为“罗尔斯之问”的中国回声。这一“回声”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我们肯认,一者,该书重新将我们制度与社会中的核心命题——“何为好的生活”——放置于政治哲学视野中来,并立足中国语境,探究正义实现的可能路径;二者,该书也是作者在深耕转型中国正义议题多年之后的一个小结,我们从中可以体察到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坚持和道德热忱。
[1]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2] 孙国东:《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公共法哲学》读后感(三):慈继伟、赵汀阳、许章润等关于《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的推荐评语
全文链接:http://sunguodong.fyfz.cn/b/962521
孙国东的《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是一部很有学术与思想价值、值得出版的书稿。作者有抱负,有思想者和公民的担当,有学术素养,有想象力,有创见,有原则,有政治成熟,有自己的声音,甚至有自己的体系至少是系统。
这部著作主要致力于“清理地基”(作者语)的工作,而中国法哲学现在最需要就是这种工作。这种工作包含对作者所说的“公共法哲学”之性质、任务及意义的澄清,包含对中国社会的相关现状和历史的理解和判断,也包括对潜在的思想资源的梳理和取舍。在这些方面,作者都做出了系统、清晰、审慎和有相当深度的思考。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决定了作者必须超越狭义的法哲学,广为涉猎政治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作者在这方面的尝试表现出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学术判断力、尤其是在思想层面的整合力和解释力。
这种“清理地基”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提出、梳理、澄清并确定相关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以“转型法哲学”的面目出现的“公共法哲学”所要应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清理地基”工作的起点必须是清醒的、审慎的“问题化”。这就是为什么作者用了很大篇幅(即整个“上篇”)确立问题的由来、性质和意义。值得商榷之处是,尽管邓正来教授在这方面的角色毋庸置疑,作者的处理方式有时显得太过个人化,最好做适度调整。
在清理地基的基础上,作者也做了不少相当有意义、有成效的建构。可以说,作者主要的学术范式来自于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他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解纯熟而不浮浅,因此远非简单的照搬而是基于中国问题和中国实际的参考和使用。在方法论和问题意识方面,作者更接近哈贝马斯,对中国已经进入但尚未完全进入后习俗道德意识(以及更广义的后形而上学知性意识)这一根本转型有准确和稳妥的把握,同时在总体上显然倾向于用哈贝马斯所说的商谈方式处理公共法哲学的根本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作者以罗尔斯(而非哈贝马斯)的方式提出实质性的规范原则,包括在修正罗尔斯基础上提出的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正义原则。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方面的尝试有很大难度。哈贝马斯和罗尔斯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已有的(现当代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及文化的有选择的、规范性的提炼、发挥及延伸,这就是为什么当罗尔斯谈到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和liberal socialism等尚不存在的制度安排时显得苍白无力和缺乏想象力。相比之下,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今中国的情境中做系统的法哲学理论建构更像是做霍布斯式的开创性努力,其挑战性可想而知。鉴于此,作者的建构性尝试实为不易,其成果(不论有何争议)弥足可贵。加之,作者对中国国情表现出了系统的敏感(如作者使用的“法治社会层面的差序格局”和“法治国家层面的政党—国家”等概念),更使得这种建构具有成熟的建设性和潜在的实践意义。
如果要我指出一个遗憾,那就是作者在思考公共法哲学时基本上没有考虑经济制度安排。这种作法难免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永续国家”的概念,如果放到西方情境中,难免会预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续”。迄今为止,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永续性”在经验层面上是与资本主义的“永续性”密切相连的。然而,资本主义的“永续性”是一个很有可能并不成立的预设(见Wolfgang Streeck, Paul Mason等),相应地,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永续性”也就成了一个问题而不是定论,除非后者具有独立性,而这又是尚待证明的。这一置疑仅供作者参考。
孙国东教授的《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一书不仅分析了法哲学的理论问题,同时还分析了中国情境,他试图调和诸种正义观之争,给出一种近乎第三条道路的正义观。其中最有新意的是提出了“关联性正义”的概念,强调了理论和实践、原则和情境之间所需的协调关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任剑涛(著名政治哲学家,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本书以转型法哲学的理论模式承载公共法哲学的思想立场,着力展示建构中的中国现代法哲学的基本轮廓,将法哲学及政治哲学的现代论题凸现出来,问题意识突出,论述进路自成一格,有力推动读者针对中国情境进入规范思考,是一本富有学术锐气、值得认真对待的著作。
刘 擎(著名政治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孙国东博士的著作《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是一部兼具学术创见与思想探索的力作。著作针对转型时期中国法治与正义的关键问题,力图通过“公共法哲学”的建构提出系统而深入的理论回应。作者体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开阔的学术视野、批判性建构的理论综合与跨学科论证的水平、以及用理论有效回应实践问题的能力,在青年学者中实属罕见。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秉持公共理性的精神,充分介入了与当代中国思想界不同立场和流派的对话争论,使其论述反映出当代中国学界的前沿水平。这部著作因为涵盖了相当广泛的议题,在理论建构的体系化程度上或许尚未完全达到作者预期的抱负,但其深度与创见在中青年学者的作品无疑属于第一流的水准。我由衷地、毫无保留地强烈推荐这部优秀著作的出版。
许章润(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书概分上、中、下三篇,起于社会—历史维度,聚焦于中国法哲学的“元问题”,而以正面回应中国转型正义的“三大结构化情境”收束。经此作业,作者旨在建构“公共法哲学”的知识形态,并阐发一种“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的理论模式,而以“转型法哲学”的理论模式承载“公共法哲学”的思想立场,可谓心思周密,别开新面。
为此,作者采取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进路,力争超越当下中国的左右之争,倡行中道理性的稳健立场,既避免封闭的“中国特殊论”,亦警惕“去情境化的普遍主义”。基此,标榜“反思性情境主义”的审慎品格和“内在批判”的建设性方式,并贯通运用于致思行文。
作者循沿此径,次第提出了四大核心理论主张。此即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以法律秩序为基础,故而,法哲学堪称“第一哲学”;重点考察“前司法”甚或“前法律”的立国、立宪、立教、立法和立人等议程;“公意政治”与程序主义的人民主权观;区辨现代性价值形态与其制度和实践形态,分清现代性价值与其具体的规范性要求。——凡此种种,逐一梳理,清晰论证,时见辟论。
揣其心志,度其旨趣,凡此作业,不外旨在抉发中国转型的理论思想资源,从而建构中国现代法律秩序。作者多年沉潜于此,凝神敛智,多有心得,独树一帜。其理论视野宏大,家国忧思情见乎词,却又不失理性的冷峻。而全书结构自洽,论证有序,行文流畅,实为难得之佳作。
季卫东(著名法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凯原讲席教授)
在一个转型社会,失范现象频现,需要通过公共哲学来重建社会的基本共识。当然,“以法为公”也是一种历史选项。还有舆论以及公约,对于公共性的界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人际关系网络非常发达的条件设定下,复杂的互动过程有可能不断解构那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体系,使得公共哲学的命题越来越碎片化、相对化。为此,我曾经提倡一种新程序主义作为在中国语境里建构公共哲学以及法治秩序的础石。国东的新书《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为基本框架,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把程序民主的原理嵌入法律秩序的建构,试图演绎出中国式的公共法哲学。这样的尝试颇有雄心,也值得给予适当的关注和评价。
郑 戈(著名法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如今面临着公共话语撕裂、有正当性赋予能力的理论缺失的困境。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儒家凭借直觉式的对转型中国一些关键问题的把握,各执一端,无从对话,虽然间或有策略性的结盟。一种能够超越派系斗争、立基于对中国转型实践的深度体认、而又体现着某种能够凝聚共识的价值追求的公共哲学可谓是时代之亟需。孙国东博士的这本书不仅回应了这种需求,而且回应得恰如其分。
全书从一些最为基础的共识出发,包括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性以及法治在现代“永续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等等,推导出法哲学作为中国现代转型之“第一哲学”的命题。进而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地以法哲学为枢机建构出一套统摄法律之国家前提、宪政基础、文化依托和社会基础的反思性理论体系。全书既是一种公共哲学的表达,也是一种公共哲学的实践。它主动介入了与当代有代表性的且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流派的对话,并试图在思想层面构建它们彼此之间的对话,以期贡献于“公意”之形成。由于全书格局宏大,内容复杂,在某些环节上还有论证不周之处,但这些都无法遮蔽本书作为一部有深度、有担当、有知识贡献的学术力作的光芒。
孙笑侠(著名法学家,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国东博士的《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既是对作者自己十余年法哲学研究的总结,也是对他的老师邓正来教授法哲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理想图景论”)的阐发和推进。
该书试图在“专业法哲学”、“政策法哲学”和“批判法哲学”之外,阐发并呈现“公共法哲学”的思想立场,并以“转型法哲学”的理论模式承载这种思想立场。该书采用了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情境的法治与中国情境的正义等三个关涉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根本问题,进行了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无论是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法哲学原理,还是对于提升和拓展法哲学在中国公共思想界的言说能力和话语空间,都具有探索性和示范性的重大学术意义。
在该书中,作者既充分展现了对法哲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历史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和知识的驾驭和整合能力,也以“内在批判”和“反思性情境主义”的建设性立场,展现了其公共担当、学术审慎、思辨理性和学理逻辑的有机统一,是结合中国情境进行自主的法哲学理论建构的可贵探索和尝试。
鉴于此,我毫无保留地推荐该书出版,并期待它能对提升中国法哲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谢 晖(著名法学家,广州大学特聘教授、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国东著的《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是一部尝试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法律转型中哲学问题予以整全性阐述和把握的著作。作者在其先前对哈贝马斯商谈合法性理论“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中国问题,以及其中独具的哲学话题,提出了“公共法哲学”这一崭新命题,并在历史视野中阐明该命题的问题意识;在“结构化情境”中,把握转型中国法律的特质;通过“反思现代性”,在流布百年、深入人心的各种政治理想和现实的“结构化情境”中寻求某种“反思性平衡”;在法律秩序建构的非自主性这一理念下,提出“认知开放但运行闭合”的法律定位……最终把其法哲学搭建在法律之外部合法性和内部自主性这样两个命题之上。在此基础上,作者揭橥“公共法哲学”与法哲学的其他理路,如知识、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人文等统领的法哲学之间的区别,形成其独具一格、自圆其说地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法律转型的法哲学解释。
全书由作者已发表的几个系列的学术论文整理而来,但各篇章之间问题意识集中,逻辑关联紧密,论述由浅及深,层层递进,共同拱卫其“公共法哲学”这一主题。
什么是法哲学?这在法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坚持内部(规范)立场的学者和外部(社会)立场的学者对该问题有并不相同的意见。在本书中,从作者“认知开放但运行闭合”的法律定位及命题中可见,他企图寻求内部立场和外部立场的某种通约、甚至结合。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或许对内部立场的观察不是其所长,或许其使命在于对社会转型这一外部立场的解释,因此,该书寻求“通约”的使命,只在某些概念和篇章中有所呈现,并未在全书中自觉地贯彻到底,甚至在“公共法哲学不是什么”的阐述中也未予重视。鄙以为,这是作者在后续研究中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当下中国,不仅“公共”在制约法律,而且法律在越来越明显地结构“公共”,故法律与社会的间距与互融,内部立场与外部立场的分歧与合作,乃是公共制约法律和法律结构公共对法哲学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共法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该书的创造性、前沿性、现实性以及对将来后续研究的启发性,本人愿意推荐该书出版。
魏敦友(著名法学家,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国东博士的公共法哲学建构是现代中国思想中的重大创获,它立基于邓正来教授所开掘的中国自主性立场,对法治中国问题进行了全方位透视与深度开掘,在批判普世论与特殊论的基础上,在形式主义法治观与工具主义法治观之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功能主义法治观,倡导立国、立宪、立教、立人、立法五位一体,为现代中国人重新思考转型中国的国家建制、社会重构与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晚清以来是中国现代思想出场的历史性时刻,但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现代思想一直表现为反应性的特质,今天我们从孙国东博士所建构的公共法哲学这里,看到了中国现代思想从反应性走向建构性的“重大突破”,可以预期,中国现代学人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建构现代法律秩序的法哲学原理应为期不远了。
《公共法哲学》读后感(四):迈向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代序(下)
全文链接:http://sunguodong.fyfz.cn/b/963393
迈向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代序(下)*
孙 国 东
“夫道公而我独私之,不仁也。风尚所趋,循环往复,不可力胜,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环往复之中,而思以力胜,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学也。不足言学,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 ——章学诚三、在“溺爱”与“棒喝”之外
本书不但提倡一种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抑且力图以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把它呈现出来。介入性的学理分析,是公共法哲学区别于其他法哲学知识形态的重要特征。“介入性”(Engagement)本身,既体现了公共法哲学的实践导向,亦试图恢复法律秩序作为公共治理秩序的特质。介入性学理分析,使公共法哲学首先与学院派的各种专业法哲学研究区分开来,并进入公共讨论和思想对话的空间。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则意味着:本书不只是进行“批判法哲学”式的批判工作,更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建构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法哲学理论形态——质言之,不但指出错的,抑且还试图指出对的。[19]而且,这种实体性理论建构,是在特定的问题意识、理论关怀、思想立场和研究取径下形成的。简言之,它力图兼顾公共担当、学术审慎、思辨理性和学理逻辑。
对学术研究来说,“指出错的”是容易的,但要“说出对的”却殊为不易。任何具有一定学术研究经验的人,大抵都会同意我的这个判断:只要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甚或仅仅是简要了解或排他性地信奉某种宗教教义或哲学、道德整全性学说,我们便很容易指出既有理论模式的所谓“缺陷”;但要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理论模式,却十分考验研究者的学术洞察力和思想创造力。推进实体性理论建构,其实蕴含着我对某类批判性研究的拒斥,即用他人提出的理论模式(多为学科内获得较广泛认可的某种理论)去批判另一种理论模式。这种做法也许可以增进研究者个人的智识愉悦,甚且可以澄清某些实践问题或理论问题,但却无益于产生真正的“学术增量”[20]。不客气地说,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啻为表演性的“理论秀”或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游戏”。余英时曾转借金岳霖的话说:以一种“义理”去评判另一种“义理”,只能变成“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21]翻检学术史,任何能在学术史上留名的学者,几乎都有自己的一套概念体系、认知框架、研究视角、理论模式乃至研究范式。即使那些以“批判”见长的思想家,譬如马克思和福柯,亦都提供了替代性的理论模式或研究范式,至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认知模式或研究视角。他们的批判,不在于批判本身,而毋宁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概念体系、认知框架、研究视角、理论模式或研究范式的优越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增量。
然则,面对中国这样后发的文明型国家、超大规模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党治国家,任何从事实践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学者,若想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工作,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只要对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稍有感知,任何学人便不难发现:几乎所有西方实践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未经反思或不经转化地径直适用于现时中国的道德、政治、法律和社会等问题时,都不免有方枘圆凿之感。不惟如此,中国现代转型的“进行时”,亦为我们进行自主的实践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建构提出了特殊挑战。这种挑战大致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遵循现代化(现代转型)基本逻辑进行学理分析和理论建构时,我们会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如果把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法治诸现代性价值,与这些价值在当下西方的特定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形式剥离开来,并将它们视为中国现代转型之“理想图景”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须厘清在转型中国实现这些价值的实践约束条件(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并基于此建构这些现代性价值在转型中国的独特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换言之,如果可以确定中国现代转型的大致目标,我们即需从实践哲学和社会科学层面探究实现这个目标的“路线图”,即从转型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找到“接榫、吸纳和转化”现代性价值的方向和路径。
其二,基于对现代化(现代转型)本身的反思立场进行理论建构时,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如果我们对现代化本身采取反思立场,并认定中国独特的文明遗产有可能为超越西方现代性理念(当然也包括其制度和实践形态)提供想象空间,那么我们即需从中国的文明遗产中寻找思想资源,探寻可“超越”西方现代性价值的理论模式。我个人愿意为这种“超越”保留想象空间,因此,一直认为“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愿景之所系。然而,本书尽管把“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并提,但实际做的工作主要是第一个层面的工作,即在遵循现代化基本逻辑的前提下,从转型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进行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这么做,当然受限于我目前的认知能力,但亦包含了我个人对目前某种研究取向的疑虑——我指的是目前很流行的那种中国研究取向,即罔顾实践困境和外界接受力而盲目进行所谓的“理论创新”。依我个人拙见,如果对某种文化或政治认同的理论建构,不能回应现时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正当化压力”,那么尽管它们对于特定个体是可欲的,但它终究不可能成为对所有国人而言具有本真性的文化认同。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共同体层面,其在根本上指向的是个体对“何为善生活”的本真性想象。把上述取向的研究工作做到极致的,便是前述许章润式的“道德—历史主义”。它们多从各种古典思想典籍中寻找资源,因而建构了一种“典籍性的中国认同”,但它们与现时中国现代转型面临的各种“正当化压力”乃至现时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传统中国的历史现实等均无涉。[22]而如果不能建立起“典籍性的中国认同”与转型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历史情境的可靠关联,我们毋宁更应建设性地厘清我们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依我个人鄙见,这才是探究中国作为“旧邦”之“新命”的前提所在。维特根斯坦说:凡无法言说者,应保持沉默。对一切未知保持敬畏,是学术审慎的基本要求。
本书采取的正是这种建设性的研究立场。一方面,它尊重中国在20世纪的实践历史中已然形成的那种“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自主现代化道路,即官方话语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学术话语表达,这条道路,即是以社会主义党治国家的政治架构、文明型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结构,建构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另类现代性”道路。但另一方面,它还旨在恢复这条道路的现代转型特质,捍卫其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想,并试图为此提供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层面的规范性范导。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内在批判”(immanentcritique)的研究取径。它同情“新儒家”旨在捍卫中华文化的不可替代性之文化立场,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新左派”旨在捍卫中国道路独特性之政治立场。但它并不直接把这种文化或政治立场作为论说对象,而是主张在隐含或预设这种文化和政治立场的前提下,把它们及相关的研究论题,共同放在现代转型的历史视野与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中,予以深度把握。正如我在阐述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曾指出的,“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确立绝不仅仅是‘学术为本’的自省自律或自得其乐就可以实现的,亦不仅仅是对‘主体性中国’的自尊自觉或自我宣称即告完成的”;毋宁说,我们更应该站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教制度、乃至中国现代转型的高度,看待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并以自己实体性的理论建构为这种自主性的确立创造智识条件。[23]
本书的这种建设性立场,与思想界占主导的两种思想立场区分了开来。我们不妨把正处于现代转型中的中国,类比为正处于成长期的叛逆少年。两者的共同特质是,它们都偏离了所谓的主流成长道路或发展模式,但由于仍处于未定型的成长状态,未来发展空间其实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样,我们便可以把家长面对孩子的教育模式,与学者面对转型中国的思想立场进行对照。鲁迅曾揭示了“溺爱型”和“棒喝型”教育模式导致的后果: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24]
事实上,面对正处于现代转型的中国,论者亦极易形成“溺爱型”和“棒喝型”的思想立场。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对峙,大致即为这种立场的分野:如果说,前者的“溺爱”在根本上放弃了理论对实践的规范性范导,那么后者的“棒喝”则以特定的理论视野限定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探索空间。换言之,如果说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遗忘了自我转圜的反思性,那么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丧失了自我创造的想象力——而兼具现代性与中国性的“另类现代性”道路,最关键的恰恰是要兼具反思性和想象力。显然,它们要么因秉持一种封闭的“中国特殊论”(Chinese exceptionalism)而放弃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想,要么因采取一种去情境化的普遍主义(decontextualizeduniversalism)立场而遮蔽了中国现代转型的结构化情境(实践约束条件)及赖此为基的想象空间,都不是面对转型中国的稳健立场。就像“溺爱型”和“棒喝型”的教育模式,不能成就一个健全的个体人格一样,“溺爱型”和“棒喝型”的思想立场,亦不会成就一个独立且受人尊重的国家人格,从而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以自己的“理想图景”贡献世界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就像在“溺爱”和“棒喝”的教育模式之外,还有更为稳健和谦卑的“劝导”模式一样,面对正处于现代转型的中国,我们同样可采取一种中道而不失建设性的思想立场。这种立场,就是“公共法哲学”采取的“劝导性的中道理性立场”:充分意识到中国现代转型的实践约束条件(结构化情境),同时又坚定地捍卫其现代转型的未竟理想,即贯穿于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为建国者所承诺并为《宪法》《党章》及政治纲领(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认的那些“仍待兑现的承诺”。[25]我们既不必为既存的实践困境做无谓的理论辩护,甚至也不必预先设定任何达致目标的特定发展模式,但通过实践约束条件与政治理想/价值理想之间交互比勘所达致的“反思性平衡”,却可以大致廓清我们实现理想的独特路径。如果说,听任实践病态肆虐的“溺爱”,是一种放弃德性追求的“德性的自宫”,那么以有限的经验面对无限成长(发展)可能性的“棒喝”,则是一种僭越理性界限的“理性的自负”(借用哈耶克的一个书名)——它们在实质上都是一种智性的懒惰。“德性即知识”(苏格拉底语),因此,无论是面对个体的成长还是国家的发展,要想培育其向善的潜能,必须秉承道德立场,运用智性发掘并据有导向“良序社会”(well-orderedsociety)甚或“良善社会”(goodsociety)的各种知识。智性意味着有节制而能动地运用人的理性,既需对哈耶克意义上“理性不及的”(non-rational)知识保持必要的敬畏,亦要对理性范围的知识具备能动的创造性。显然,惟有秉持“劝导性的中道理性”立场,我们始能在保持德性追求、持守理性界限的前提下,积极而又能动地运用人的智性。换言之,它可以把我们对德性的信念感、对理性的界限感与智性的能动性恰当结合起来,因而是一种中道而不失建设性的学术立场。这种学术立场所预设的,既不是自由主义论者惯于采用的“向假定处思考”的思路,亦不是新左派实际上采用的“向给定处妥协”的思路,而是一种“在给定处着力”[26]的建设性思路。它主张把中国现代转型承诺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想作为范导实践的规范性空间,从转型中国政治与社会—历史的给定条件入手,探索其实现现代转型的发展路径。因此,它既可以避免“向假定处思考”势必带来的“理性的自负”,亦可以避免“向给定处妥协”必然导致的“德性的自宫”。如果说,李泽厚所倡导的“不泥国粹,不做洋奴,努力原创”[27],彰显了一种于“中西古今”之间砥砺前行的学术品格,那么公共法哲学不但力图践习这种品格,抑且追求一种于左右对峙中独立探索的思想立场——我们姑且称之为“不师新左,不法老右,自主求索”。[28]
四、超越犬儒主义与直觉主义
如果我的观察不错,继1990年代的“思想退隐,学问凸显”之后,我们已进入“学问退隐,策论凸显”之颓势愈加显明的时代[29]。早在本世纪初,王元化先生即曾说道:“我敢断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研究也不会成为可以和其他文化活动抗衡的力量。我们长期以来,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学术为政治服务,在这种理论下,真正的学术渐渐消失,代之以为时政服务的学术。”[30]未曾想,他的断言在今天已基本应验。显然,这种颓势是犬儒主义(cynicism)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表征。很多论者对政治的关心是将政治问题“治理化”,进而再将“治理”问题技术化。然则,我们不仅要关心政治治理术意义的政治,更要关切大写的政治,即作为政治共同体集体目标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想。余英时先生曾说,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如果此处的“政治”是指“权力—政治”逻辑下的政治治理术,我亦复仅有“遥远的兴趣”;但如果它是指“伦理—政治”特别是“道德—政治”意义上的政治理想,我则抱有深切的兴趣。依我个人鄙见,我们尤应将所有针对社会世界的言说,视为康德意义上“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典型方式。不同于“理性之私人运用”,“理性之公共运用”既需守护政治共同体的价值理想,亦需遵循公共性和可证成性——即公共证成——的运行法则。借用康德的话说,其言说其实是学者“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面向无限时空的读者言说,其理性之运用是“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出的那种运用”。[31]
如果说,犬儒主义是笼罩在学术场域(学术界)的一片乌云,那么直觉主义则是飘荡在公共领域(思想界)的一个幽灵。直觉主义原本是道德或伦理规范的证成方式,并最终体现为一种道德哲学理论模式;它认为,道德直觉对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把握,较之人的理性更可靠,亦更基础。但此处所谓的直觉主义,具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它是指排他性地诉诸某种类型的直觉言说公共事务的取向。因此,它既包括基于道德直觉的直觉主义,亦包括基于伦理直觉和政治(或实用性)直觉的直觉主义。如果借用哈贝马斯的“实践理性多态论”,它们大致与现代社会实践理性的三种表现形式——道德理性(实践理性的道德运用)、伦理理性(实践理性的伦理运用)和实用理性(实践理性的实用运用)[32]——一一对应起来。换言之,它们分别把实践理性排他性地还原为道德理性、伦理理性和实用理性。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规范性政治哲学(特别是将康德式的道德哲学径直转化为政治哲学论说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包括罗尔斯、德沃金、诺奇克等的自由主义学说),以古典政治哲学为依托的施特劳斯主义、以黑格尔法权学说为理论渊源的共同体主义/社群主义,与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为底色的政治现实主义(包括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的政治哲学、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法学、合理选择理论[theoryof rational choice]等),即大致分别将实践理性排他性地还原为道德理性、伦理理性和实用理性——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任何形式(语义学或语用学上的)道德普遍主义的追求,伦理理性和实用理性常常会相安无事地形成相互倚重、互为支援的关系,这在施米特主义本身及其与施特劳斯主义的暧昧关系中,特别是现时中国新左派、新儒家、施特劳斯学派互相支援、相互转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正如哈贝马斯明确指出的,政治社会不能被排他性地还原为道德世界、伦理世界或实用世界。毋宁说,三者的结合加上受实践理性制约的必要妥协,才符合与现代复杂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世界的运行机理。[33]
前文已指出,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儒家,即分别立基于社会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具有正当性的道德直觉、具有目的合理性的政治直觉和具有可欲性的伦理直觉之上。事实上,它们之所以成为当下思想界最主要的三种思潮,与当下中国存在的民粹主义之风有着内在关联——我把当下盛行的民粹主义称为“基于直觉主义的民粹主义”(populismbased on intuitionalism)。已有论者注意到,毛泽东时代的道德取向,其实是民粹主义、直觉主义、非理性主义、道家的无政府主义与理想主义、威权主义等取向的杂合。[34]作为历史遗留,由“基于直觉主义的民粹主义”所形成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似乎已成为当下中国的顽疾。那些将西方浪漫化的社会成员,将当下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从道德直觉上归结为对世界主流文明秩序的背离,从而为自由主义提供了思想市场;那些把“前三十年”浪漫化的社会成员,将当下严重的社会正义等问题从政治直觉上归谬为对社会主义传统的偏离,从而为新左派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那些将古典传统浪漫化的社会成员,将当下严重的道德和信仰危机从伦理直觉上归咎为对古典传统的背弃,从而为新儒家提供了社会舆论环境。这种“基于直觉主义的民粹主义”,与思想界盛行的文化思潮交相辉映、互为支援,不但使直觉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蔚为公共言说中的主流取向,抑且因斗争哲学的根深蒂固而使不同的立场彼此攻讦、寸步不让,从而显现出把中国社会(包括思想界)完全撕裂的危险。从学理上看,当下“基于直觉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形成,与意识结构的现代转型带来的“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有着根本的关联。由于个体获得了生活世界的自主地位,加之自由、平等、民主等各种普遍主义道德原则已进入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中,人们事实上获得了在以生活世界为背景的公共领域中的“自我立法”地位,因此不但对自己的道德直觉,抑且对自己的政治直觉和伦理直觉,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乃至基于这种自信的偏执。而这种民粹主义之所以能演化为席卷全社会的非理性风气,则与我们仍未能建构起“后革命时代”的常态化政治秩序有着内在关联:斗争观念的积重难返,及相应的公共理性的历史性缺失和制度化缺位,使得人们仍习惯于依靠简单粗暴的强力支配而非温良恭让的理性对话,来解决彼此间的认识分歧。哈贝马斯的“康德式共和主义”及其他诸多共和主义论者的研究已表明:不经由公共自主实践形成的“学习过程”,社会成员不可能以公民角色习得主体间性的“共享”视角,也就不可能不断调整和限制自己自我中心的视角。换言之,公共自主的实践,可以使公民不断践习康德—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性之公共运用”,从而培育与良序社会甚或良善社会相适应的理性品质、换位思考、对话精神、寻求共识、规则意识等公民美德。“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35]在现代条件下,惟有公共自主之实践,始能确保人们“忍私”“忍情性”,从而培养与良序社会乃至良善社会相适应的公民美德。
可见,无论是超越犬儒主义,还是克服直觉主义,其实都需要诉诸“理性之公共运用”。不过,前者指向了学者的自律;后者对学者而言是一种自律,但对普通社会成员而言,则指向了社会的建制化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实践哲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视为某种个人修为过程,其核心在于要使之成为“言公之学”。要达到这一点,借用朱熹乐于采用的术语,我们既要以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的“道心”超克源于个体自然欲望的“人心”,又要在现代条件下“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获取对实践秩序所蕴含之“法理”的理性认识。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古训,我们更应在现代条件下重新体会朱子的诠释和教诲:“人心则危而易陷,道心则微而难著。”“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如此,“从道心而不从人心”,始能“允执厥中”。[36]
公共法哲学之为公共法哲学,正因为它不但在学术研究中以“理性之公共运用”自我期许和自我要求,抑且把“理性之公共运用”视为顺应“公意政治”合法化机理、回应实践困境的建制化要求。换言之,公共法哲学同意朱子“以理制欲”(或康德以“意志”克服“任意”)所体现的道德认知主义取向,但主张借鉴哈贝马斯等关于现代意识结构之特质、现代政治和法律合法化之原理的认识,认为据以“制欲”之“理”应由公共证成——而非独白式的“道德唯我论”——确立起来:在现代条件下,“以公证理”应成为“以理制欲”的前提。
* * *
关于“公共法哲学”的研究,无疑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但却包含着我个人近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在向一些学友讲述我的研究构想时,他们几乎无一不投来怀疑的目光,并善意地规劝我放弃这种“宏大”“空玄”的理论抱负,而转向那些更易获得体制内各种知识规划项目支持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我相信,这也会是部分读者的感觉。且不论这种“知识规划”的是与非,是谁规定只能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言说社会世界的问题?若有人认为诸如定量、定性之类的社会科学方法,可以充分把握现代社会世界的复杂性,甚且认为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来把握,恕敝人愚执,期期以为不可。哈贝马斯曾指出:
“对政治理论采取的显明规范主义(及隐蔽的观念论)立场,认为应当优先进行概念分析;而从社会学视角对这种立场提出的有节制之保留意见,则提供了有益的矫正。但若是在淑世主义的(melioristic)意义上理解这种矫正,就不必定会将这种保留意见扩展为如下的原则性拒斥意见:由于社会的复杂性,规范性理论归于失败。只要同意复杂社会自身仍然能够通过法律和政治的途径反思性地运行,纯粹的规范性考量仍大有可为。”[37]
虽然现代社会已变得愈发复杂,但它仍需本着“淑世主义”的精神使自己不断趋近于良序社会甚或良善社会,其关键便是要通过法律和政治变革举措使社会始终保有反思性,而各种规范性理论正是践行和扩展这种反思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而且,公共法哲学的研究,并不追求那种“去情境化的”规范性。相反,它寄望通过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的深度结合,使规范性理论更具有中国情境的切己性、相关性和介入性。可以说,正是这种基于中国情境的规范性理论之建构,为我们拓展兼具正当性和可欲性的反思性发展空间[38]提供了学理依据。
或许,有人不同意我的上述观点。但学术研究,作为耗费自然生命的智性活动,其实与研究者的价值观或自我认同密不可分,与学者自我建构的那个“意义世界”不可分割。既如此,缘何不能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往精神?熊十力先生曾语曰:“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39]钱锺书先生亦云:“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40]也许,在这个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主导的世俗化时代,在这个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大众文化时代,标榜“素心”“孤往”未免太过于古典和自矜了。但如果它们是特定情境下安守学人本分的必要前提,那么就是值得追求的。事实上,就拙著来说,无论是提倡公共法哲学也好,倡导转型法哲学也罢,抑或对中国语境中法治和正义的结构化情境、规范性基础及反思性空间等进行学理探究,都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追求,也不具有多么高尚的学术品格。它们本应是任何关心中国现代性问题且具有思想能力的学人,都极易触及的主张。但认同知识规划逻辑的学人会认为从事“规划外”的学术是一种病,正如“在笼子里出生的鸟认为飞翔是一种病”(佐杜洛夫斯基语)。就像飞翔是鸟的天性一样,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亦是学人的本分。因对湮灭本性、泯灭本分的结构化情境已无抵御和反思能力,便把他人的安守本分视为病态;因不事本分成为常态,安本守分始成美德——转型中国关乎道德的诸种乱象,似均可作如是观。
两个多世纪以前,清儒章实斋先生曾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学界的“言私”之风:“呜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41]比照时下的知识界,不但“道不足而争于文”“实不充而争于名”之风已然兴起,“言可得而私”之“私”似乎亦已为“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语)之“私”全面渗透:“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杜甫语),乃至“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语),似可谓当下学界“言私”之风的生动写照。由是观之,无论是“学问淡出,策论凸显”之颓势的显现,抑或更严重的学术惨遭政治、市场和传媒之三重裹挟,均可视为“言私”之风沉渣泛起的表征。本书所提倡的公共法哲学,不但意在抗衡各种“言私”之风,抑且旨在倡导真正的“言公”之学——其之为“公”,既呈现为研究对象上对公共论题的关切,亦体现为价值取向上对公共价值目标的坚定守护、对理性之公共运用的自觉践履。学问本为精神流浪者之志业,是文化具有生命力之表征。作为对实践秩序的哲学思考,实践哲学是社会具有反思性、政治具有想象力的学理基础。在“言私”之风盛行的当下,要坚守学术本分,倡导“言公”之学,素心孤往尤应成为学人自持的首要品格。
我不敢说,拙著一定能发人所未发之高见,但它至少见证了我在学问道路上砥砺前行之轨迹。现在,我把它呈献给读者诸君,如果她能对您理解转型中国的法律/政治问题有些许助益,我便心满意足了。如果她还能进一步引发您的学思共鸣,那我就更加愉悦了——
苟如此,吾道不孤矣!
2015年12月30日初稿于美国圣路易斯大学
2016年5月26日二稿于沪北寓所
2017年4月1日三稿于复旦光华楼
2017年6月7日四稿于复旦光华楼
2018年3月5日改定于沪北寓所
《公共法哲学》读后感(五):迈向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 ——《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代序【上】
全文链接:http://sunguodong.fyfz.cn/b/963392
迈向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代序(上)*
孙 国 东
“夫道公而我独私之,不仁也。风尚所趋,循环往复,不可力胜,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环往复之中,而思以力胜,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学也。不足言学,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 ——章学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继《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之后,出版的第二本学术专著。借用冯友兰和张立文的说法,如果说第一本是“照着讲”的著作,那么眼前的这本则是力图“接着讲”乃至“自己讲”的著作。激励我坚定这种研究旨趣转向的,其实是我在第一本专著“后记”中曾援引过的康德的一段名言。这段话记录了康德何以依循卢梭的教诲和示范,从自己曾念兹在兹的纯粹形而上学迷梦中惊醒的缘由。请允许我再次摘引如下:
“我的本性是研究者。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醉心于推动知识的进展,并对它的每个进步感到满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知识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而且如若我不能相信这种见解助益于确立人类之权利,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1]
诚哉斯言!作为实践哲学的从业者,身处也许是人类现代史上社会最遒变、文化最激荡、政治最复杂的现时中国,若不能为社会的自我反思、文化的自我超越和政治的自我转圜,做出自己的思想贡献,我们确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
初看起来,“照着讲”的评判标准是准确性,即对研究对象之思想的把握是否准确;“接着讲”和“自己讲”的评判标准则是解释力,即所建构之概念框架、理论模式甚或研究范式,是否对研究对象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然而,无论是“照着讲”之准确性,还是“接着讲”和“自己讲”之解释力,其实均凭赖于研究者独一无二的洞察力——无论是对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洞察力,还是对于问题意识(研究对象之选择)的洞察力。正如章实斋先生所言,“学问文章,聪明才辩,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2]我不敢妄言自己有多么别具一格的洞察力和识见,但为了便于读者的了解,把我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略作介绍却是必要的。
简言之,我要追问的根本问题是:在全球化和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如何结合中国情境推进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换言之,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应遵循怎样切己的法哲学原理?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个问题固然重要,但却是空悬到几乎无法把握的问题。或者说,它是任何关心中国法律实践的论者均会直接或间接触及的问题,只不过他们采用了更为既有学科体系乃至学术评价体系接纳的方式。我个人充分尊重各种专科化和技术化的学术努力,但我却不愿采取这种学术视角和研究取径(approach)。事实上,正是为了超越各种专科化的视野,恢复中国现代法律秩序之建构的公共属性,同时又具备相对厚实的学理基础,我在本书中试图阐发并呈现一种有别于“专业法哲学”及“政策法哲学”“批判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并以“转型法哲学”的理论模式承载“公共法哲学”的思想立场——我称其为“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publicphilosophy of law as a legal philosophy on transitional China)。
一、 “公共法哲学”是什么?[3]
所谓“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即一种以“公共哲学”的思想立场看待法律问题的视角。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以公共法哲学为思想立场、以转型法哲学为理论模式的法哲学主张,也即是一种以中国的“现代转型”为基本问题意识和理论担当、旨在恢复现代法律秩序作为公共治理秩序之面目的法哲学主张。它认为,现代法律秩序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秩序,应是依循康德特别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意义上的“理性之公共运用”(public useof reason)原则而获得“公共证成”(public justification)的秩序;同时,它主张法哲学研究者应当为这种“公共证成”的规范性依据提供认知前提和学理基础。
从总体上看,本书对“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的阐发,建立在如下四个核心理论主张基础之上:
第一,由于现代社会的社会政治秩序以法律秩序为基础,法哲学堪称中国现代转型的“第一哲学”——这意味着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理论知识应以“法哲学”为核心呈现出来(至少法哲学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鉴于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中国的现代转型)仍是“进行时”,我们更应关注“前司法”(pre-judicatory)甚或“前法律”(pre-legal)的立国,特别是立宪、立教、立法和立人等发展议程——这意味着“转型法哲学”必然导向综合运用法哲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法律社会学和法律文化等理论知识的“跨学科”视野;
第三,考虑到中国的现代转型历程对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Chineseness)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y)道路之历史嵌含和前景承诺,同时顺应现代政治作为“公意政治”(遵循“同意”模式)的合法化逻辑,我们应当把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纳入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中——这意味着:我们应优先秉持一种程序主义的人民主权观,以回应中国现代转型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第四,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我们必须把“政治/法律价值”(政治/法治文明)与“政治/法律价值观”(政治/法律文化)区分开来,即要把属于普适性政治文明范畴的现代性之价值形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现代性价值)与特定政治文化关于现代性价值的观点(即关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现代性价值之规范性要求的观点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区分开来——这意味着:我们须否弃各种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并代之以在促进现代政治文明所承诺的政治理想(价值理想)与中国政治文化所凝结而成的实践约束条件之间“反思性平衡”(reflectiveequilibrium)的基础上,围绕“中国的现代价值观”(特别是关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现代性价值之规范性要求的观点),推进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4]
为深入探究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本书主张把它置于晚清(乃至宋明)以来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视野中进行把握。
(一)历史视野与问题意识
从实践哲学与历史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把中国自晚清(乃至宋明)以来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解读为一种世界观的转型,即从“天理世界观”转向“法理世界观”。其要义有二:其一,指向了法治的观念,即实在法具有“不可随意支配性”(unverfügbaren,indisponibility;借自于哈贝马斯的一个术语)的观念,也即是要确认“规则之治”(the ruleof rules)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正当性(rightness);其二,指向了民主的观念,即形成一种“后习俗的道德意识”(post-conventionalmoral consciousness),即基于原则的、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并以最低限的公共参与、公共证成确保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正当性与社会政治秩序及法律秩序的合法性(legitimacy)。这种世界观的根本转向,实乃哲学界或史学界所谓“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之命题的实践哲学性质之所在。借用魏敦友的话来说,这种现代转型指向了中国文化继“子学”“经学”“理学”之后有待实现的新的“哲学突破”。[5]事实上,它亦确立了法哲学作为中国现代转型之“第一哲学”的核心地位。可为此提供的理据,是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历史转型的逻辑:基于“公意”的法律已取代超越人世的“上帝”或“天”,成为人间秩序(社会政治秩序)的主宰和枢机。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的现代转型蕴含着一大根本的历史使命,即形成现代条件下的“永续国家”(eternalstate)。换言之,建构永续国家,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政治理想。所谓“永续国家”,是指不存在政体危机(政权统治危机)、只存在政府危机(政府治理危机)的国家,即通过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政体架构)将政府更迭限制在和平的框架内,从而有效避免通过暴力革命、政变等实现“王朝更替”之命运的“后传统国家”。无论是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谓的“历史三峡”(即从帝制到民治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还是毛泽东以民主超越“兴亡周期率”的政治构想,抑或邓小平“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政治理想,均在实质上指涉永续国家之建构。如果说,确保“人民的出场”是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现代法律秩序)合法性的根本,那么“永续国家”就是通过以选举民主确保人民的“周期性出场”、以商谈民主(discursivedemocracy)或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确保人民的“常态性出场”,从而制度化地避免传统的“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因欠缺“人民出场”的制度化机制而陷入由人民的“历史性出场”所导致的——治乱循环的国家形态。从根本上看,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实就是建构中国式的永续国家。
从运行机理上看,永续国家包括四大实质性要素:国家能力、法治、民主问责制政府和社会正义。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只要全面厉行法治,并在法治框架内实现政府更迭的民主化及社会正义,即可建成远离政治统治危机的永续国家。中国式永续国家所蕴含的政治统一(对应于国家能力)、法治、民主、正义及自由、平等等政治/法律价值,即构成了中国现代转型所承诺的价值理想。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谓“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即是基于现代中国文化认同,对这些价值理想进行学理上的“格义”而形成的相互兼容、互为倚重的价值结构。如何结合中国现代转型的价值理想与转型中国的实践约束条件,对这些价值在转型中国的具体规范性要求进行学理阐释,并形成学理融贯的规范性体系,即是中国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者的使命之所在。
相应地,中国现代转型包括“立国”“立宪”“立教”“立人”“立法”五位一体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议程。所谓“立国”,即建立主权独立、政治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此一任务已于1949年完成);所谓“立宪”,即形成遵循现代政治文明运行逻辑的民主立宪政体和民主问责制政府;所谓“立教”,即形成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及相应的核心价值体系);所谓“立人”,即培育具有公共精神和规则意识的公职人员(政治家、公务员、法官和检察官等)、培育具有公民美德且积极参与社会合作的公民;所谓“立法”,即建构功能完善、结构合理、运行良好的现代法律系统。在这五位一体的发展议程中,“立法”是一个全局性的基础工作:它集建构性(变革性)与保障性(保守性)于一身,既可以以自身的建构性、生成性作用(主动)推进“立国”“立宪”“立教”“立人”事业的进行,亦可以为已经取得的“立国”“立宪”“立教”“立人”成果提供(被动的)法律保障。就其保障性角色而言,“立国”“立宪”“立教”“立人”分别构成了“立法”的国家前提、宪政基础、文化依托和社会基础。在成文法国家,立国所确立的国家性质、立宪所确立的政体架构和国家形式、立教所确立的文化认同,乃至立人所形成的政治风气和国民素质,常常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亦会直接影响着法律秩序的运行,譬如,立宪所确立的司法制度便会直接影响司法的运行、立人的成效会直接影响法律的现实有效性等等。
基于上述历史视野,我们很容易判定:中国的现代转型仍是“进行时”,远未臻至“完成时”。所谓“公共法哲学”,即是要关注“前司法”甚或“前法律”的公共要素,并把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置于立国特别是立宪、立教、立人、立法之视野中,探究其法哲学原理。正是源于现代转型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担当,本书主张的公共法哲学以“转型法哲学”的理论模式呈现出来。
(二)“结构化情境”与转型中国(法律)问题的性质
本书主张的“公共法哲学”,以“转型法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它旨在恢复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并主张把它置于现时中国由历史凝结而成的实践约束条件(政治与社会—历史情境)中进行把握。关于这些实践约束条件,本书尤为关切其中的“结构化情境”(structural-contexts),即经由历史的积淀、社会的演化和政治的博弈而形成的某些相对固化的情境。
这种“结构化情境”,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元结构化情境”(meta-structural-contexts),即对中国现代转型构成整全性制约的“结构化情境”。“元结构化情境”,又可区分出两种不同类型:⑴历时性的“元结构化情境”,即依循历时性脉络形成的“元结构化情境”。此类“元结构化情境”,概有三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文化/历史遗产、超大规模型国家(super-large-scalestate/extra-large-scale state)的社会结构及社会主义党治国家(party-state)的政治架构。它们在性质上均属具有不同时间性和属性的“传统”,可以比较具象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并直接制约着所有(特别是西方)既有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模式之于中国问题的可适用性和解释力。⑵共时性的“元结构化情境”,即依循共时性逻辑形成的“元结构化情境”。此种类型的“元结构化情境”,大致体现为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与整体性。其“共时性”,一方面是指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和回应的现代性问题,在当下中国是共时性地存在的;另一方面是指前述不同时间性和性质的“传统”,在现时中国也是共存互嵌而产生影响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现代性问题亦具有整体性:一方面,由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存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性;另一方面,由不同时间性和性质的“传统”之共存互嵌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不同渊源的整体性又是相互交缠在一起的,由此为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性问题这种相互交缠的整体性,既是其真正的特质和复杂性之所在,亦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相比而言,这种共时性的“元结构化情境”更为抽象,亦更难以把握。惟有保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情境自觉,并兼具历史感和比较视野,始能洞察到这种“元结构化情境”。
上述“元结构化情境”的存在,其实决定着中国的现代转型只能走一条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Chineseness)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道路;而20世纪中国以社会主义党治国家推进中国现代转型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另类现代性”道路:它既顺应了上述“元结构化情境”(特别是超大规模型国家、文明型国家及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和整体性),而且党治国家的历史遗产本身已成为现时中国新的结构化情境。
第二,具体的结构化情境,即受上述两个层次的“元结构化情境”制约,对具体法律(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构化情境。譬如,本书第五章中探讨的“差序格局”,就与前述三个历时性的结构化情境有关,但却是法治中国必须回应的实践困境;第六章中探讨的“反正义的公平观”,则是我识别和建构的一种结构化情境,它严重制约着转型中国社会正义的实现。如何把握具体的结构化情境,常常直接影响着中国情境中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建构的解释力。
由于前述结构化情境特别是“元结构化情境”的制约,转型中国(法律)问题常常具有如下性质:“合理但不正当或善”(rational but not rightor good),即既有制度安排具有(相对于政治统一、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等的)目的合理性,但却既不符合我们对法律秩序(社会政治秩序)正当性的道德期许,亦不符合我们对(共享)伦理生活的本真性想象。这种性质,使得论者极易形成直觉主义(intuitionistic)的论说模式或研究取向,形成立场先行、“主义表态”式的政治理想主义、政治现实主义或政治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基于“正当性”道德直觉的政治理想主义,新左派基于“目的合理性”政治直觉的政治现实主义,新儒家基于“可欲性(desirablity)/本真性(authenticity)”伦理直觉的政治温情主义。然而,这种直觉主义的论说模式或研究取向,要么放弃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政治现实主义),要么遮蔽了中国现代转型的结构化情境(政治理想主义),要么忽视了中国现代转型所赖以为基的社会政治秩序机理(政治温情主义)。
(三)反思性的情境主义:政治理想与结构化情境的“反思性平衡”
本书对待这些结构化情境的基本态度,是借鉴于艾森斯塔特、吉登斯等阐发的“反思性现代性”(reflective modernity)立场,即从“反思性”这一现代性的内在精神出发,把现代性视为一种能动且反思性地创造未来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谋划。基于此,本书形成了一种“反思性的情境主义”(reflective contextualism)立场:那些具有不同时间性和属性的“传统”,既是我们反思特定现代性模式(特别是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凭借,其本身亦是反思的对象。
为此,本书主张通过结构化情境(实践约束条件)与现代转型所承诺的政治理想或价值理想(中国式永续国家及其承诺的价值理想)之间的交互比勘,推进转型法哲学的“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从而为廓清实现这种政治理想或价值理想的制度依托和发展路径提供学理依据。这种交互比勘的方法,可借鉴罗尔斯所谓的“反思性平衡”法,力图在政治理想或价值理想与结构化情境之间达致某种“反思性平衡”,即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现代性价值的核心内涵作为“暂时的定点”,然后再以相应的结构化情境与之交互比勘达到“学理格义”的效果,从而拓清这些现代性价值在转型中国情境中的独特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乃至发展路径。
(四)理论依据、研究对象与研究取径
转型法哲学的基本理论依据,是法律秩序建构的非自主性(heteronomy)——更准确地说,对中国这样现代法律秩序正在建构的国家来说,我们更应在立法阶段强调法律的非自主性,即要积极回应法律秩序的政治哲学承诺及其所依托的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我主张把立国、立宪、立教、立人连同立法一起纳入转型法哲学的视野,正源于此)。对法律非自主性的认识,本书综合借鉴了马克思关于法律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科勒—庞德法律与特定时空之文明条件相适应等思想,并主张把这种非自主性限定为法律的政治哲学承诺、政治制约性和社会—历史制约性。换言之,通过凸显法律的政治与社会—历史之维,我试图基于转型中国的政治哲学承诺及其依托的政治与社会—历史情境,推进关于“邓正来问题”(基于中国文化认同的[法律]理想图景问题)的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从而探究转型中国的法哲学原理。
转型法哲学主张,我们要在现代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中把握其建构原理。在现代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中,合法化(legitimation)原理是最为根本和基础的机理。借鉴韦伯、哈贝马斯、列奥·施特劳斯等的相关论述,可以把合法化原理的现代转型概括为从超越于人世的“自然/天理”转向本原于个人的“理性意志”。借鉴卢梭、康德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相关思想,我们可以把法律承受者(addresses)作为法律创制者(authors)的公共商谈和公共证成(即“受到影响者”与“商谈参与者”的同一及“受到影响者”作为“商谈参与者”的“同意”),视为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合法化的根本途径。把公共商谈和公共证成纳入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中,是转型法哲学之为公共法哲学的根本表征。此种意义上的公共法哲学,预设了一种程序主义的人民主权观。这种民主观,既符合现代政治作为“公意政治”的合法化原理,亦积极回应了现代社会所依托的现代意识结构(“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更契合于当下中国党治国家的政治架构,从而有助于立宪、立教、立人、立法等中国现代法律秩序之实体性内容,在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上不断填实。
在现代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中,法律系统本身的运行逻辑是其基本机理所在。对此,我们须区分立法和司法。在现代法律秩序有待建构的成文法国家,立法不但在时序上优先于司法,抑且在功能上优位于司法。为深入把握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卢曼—托依布纳法的自创生理论(autopoietictheory of law),把法律视为“认知开放但运行闭合”(cognitivelyopen but operationally closed的系统,同时结合中国情境将其明确阐发为:在立法过程中,我们应强调法律的“认知开放”;在司法过程中,则应强调法律的“运行闭合”。惟其如此,我们始能在遵循法律系统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化解法律的合法性与法律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换言之,在法律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我们应优先强调法律的“认知开放”(法律的非自主性),以确保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在法律适用的环节,我们应优先确保法律的“运行闭合”,以实现法律运行的自主性。
遵循现代法律秩序的合法化原理与法律系统的运行机理,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主张:现代司法固然具有职业性,但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却是政治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不经过政治共同体内部具有最大限度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立宪、立教和立法过程,法律不可能体现最大限度地体现政治共同体的“公意”,也就不可能将其专门委诸职业化的法律人共同体看护。
基于上述定位,转型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关涉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那些问题。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包括两方面的历史课题:其一,确保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看,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包括两大要素:⑴“语义学的合法性(semantic legitimacy)”,即法律规范之内容的合法性,也即是要确保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合道德性)与可欲性(合伦理性);⑵“语用学的合法性(pragmatic legitimacy)”,即立法的程序普遍性,也即是要确保法律“承受者”与法律“创制者”的同一性。其中,前者涉及立教问题,后者关涉立宪问题;由于“后习俗”的现代意识结构下(法律)规范之语义合法性(正当性和可欲性)是主体间“非强制性共识”的产物,立法的程序普遍性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其二,确保法律运行的自主性,即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合法律性”(legality)。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涉及现代条件下的立人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法律秩序建构的上述两大课题分别具有不同的政治功能:确保法律秩序的合法性,有助于法治发挥建构基于“共识政治”的“公意政治”之功能;确保法律运行的自主性,助益于法治发挥形成基于“规则政治”的“常态政治”之功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书第四章建构了一种新的法治观:“功能主义法治观”)。
因此,转型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其实是关涉中国现代治理秩序基本构成的那些方面,即法律秩序中与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相互交叠且深度关联的部分。这种交叠和关联,大致分为三种情况:⑴大致对应于罗尔斯意义上的“社会基本结构”(the basicstructure of society),即整个社会中具有政治意义并具有法律形式的根本秩序结构及其价值理想(理想图景、宪政秩序、国家和社会组织原则等);⑵直接影响法律秩序运行成效的社会“基础秩序”(infrastructuralorder)(如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组织机制、现代信用体系等);⑶直接影响法律秩序运行成效的政治“基础秩序”(如合宪性审查制度、财政法定制度等)。由于现代社会秩序特别是政治秩序是在法律秩序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谓的转型法哲学,其实亦是一种“转型政治哲学”。
正是源于对研究对象的这种定位,转型法哲学顺其自然地达致了一种“问题导向的”(issue-oriented)跨学科视野。但这种“跨学科”不是“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而是根源于研究对象的内在要求。具体来说,本书的跨学科视野,主要是通过对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之“一进一退”的理解而获致的。所谓“一进”,是指要进一步看到“法律的政治之维”。由于现代社会政治秩序是以法律秩序为基础的(法律系统是现代社会“全社会整合”[societal integration]的媒介,是作为现代社会政治秩序运行的功能系统而存在的),因此,要深入把握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必须进一步把握法律秩序中具有政治意义的那一部分——特别是立宪和立教[6]——是如何建构和运行的。换言之,“法律的政治之维”包括两个维度:法律的政治制约性(立宪)与法律的政治理想/政治哲学承诺(立教)。这样,那些与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有关的社会理论、政治哲学、政治学等思想资源,自然就进入到了本书的视野。所谓“一退”,是指要退一步看到“法律的社会—历史之维”。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仍需要社会文化方面的积极配合(立人)。因此,我们须为制约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各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之正向调适性变迁,创造良好的结构化情境。这样,那些与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有关的法社会学、法史学(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等思想资源,亦进入了本书的视野。
为了实现其研究旨趣,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采取了“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取径。它主张通过“问题化的理论处理”与“理论化的问题处理”的结合,特别是通过价值理想与结构化情境的“反思性平衡”,实现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的深度结合,从而把转型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政治哲学承诺与各种实践约束条件紧密结合起来,建构转型中国的法哲学原理。
二、“公共法哲学”不是什么?
以上简要勾画了公共法哲学的基本轮廓。下面,我拟与既有的理论模式相比勘,以进一步呈现公共法哲学的面目。大致说来,它与如下言说转型中国法律问题的研究取径或研究取向[7]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曰“知识—法学”取径。此处特指邓正来的法学研究取径。正如本书“上篇”揭示的,这种研究取径试图以知识具有“正当性赋予”力量这一知识社会学洞见为依据,对1978年以来以“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法律文化论”等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系统共同遵奉的“现代化范式”进行反思,从而提出了我所谓的“邓正来问题”,即“基于中国文化认同的(法律)理想图景问题”。然而,由于忽视了法律本身的文本双重性(法学知识生产文本vs.立法文本)及相应的法律实践之两重性(立法实践vs.法律实施实践),“知识—法学”取径无力对现实的法律实践是否遵奉“现代化范式”进行评判,从而未能充分地论证“邓正来问题”的出场——这使得其知识社会学取径沦为一种“跛足”的知识社会学,即“有知识但无社会”的知识社会学,同时亦使其基于“知识—法学”取径的学术批判,具有王小波所说的“批判人而不是批判社会”之倾向。
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不同于“知识—法学”取径:第一,如前所述,公共法哲学不是把法学仅仅视为用于呼吁“基于中国文化认同的(法律)理想图景问题”之历史性出场的可替代个案,而是把法律秩序视为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把法哲学视为中国现代转型的“第一哲学”。第二,公共法哲学放弃了“知识—法学”取径明确主张的精英主义(法律职业主义)取向[8],主张把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视为政治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从而将中国现代法律秩序视为需依循“理性之公共运用”而获得公共证成的公共治理秩序。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法哲学旨在推进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其中,前者旨在推进法哲学研究之于中国情境的相关性、之于中国问题的介入性;后者旨在综合运用法哲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法社会学、法律文化等思想资源,切实推进“以中国为思想根据”(邓正来语)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的实体性建构。本书对“现代转型”之历史视野的引入,对“邓正来问题”出场之社会—历史背景的阐述,对作为“邓正来问题”要素的法治、正义及文化认同所依托之结构化情境的识别和定位,乃至以公共法哲学的思想立场更主动地介入到当下中国主流思想争论的尝试等等,都是自觉推进介入性学理分析的体现。本书对法律之政治性的学理阐发,对正当与善之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现代法律秩序建构之相关性的阐述,对现代转型之政治理想和价值理想的论述,对“永续国家”之性质和要素、功能主义法治观、转型中国“底线正义”诸原则、“关联性正义”、“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原则”等等的理论建构,则是我力图推进实体性理论建构的学术努力。正是依凭这种学术努力,我力图以更具学理性的公共关怀,填实并扩充邓正来所开辟的法哲学思想空间。
二曰“政治—法学”取径、“社会—法学”取径及“历史/文化—法学”取径。我把三者并置,主要是考虑到了它们分别排他性地强调了法律的政治制约性、社会制约性及历史制约性。换言之,它们在表面上歧异的背后,其实共享了一种决定论的研究取向。体制内各种知识规划项目资助的研究课题,多有意无意地采用了“政治—法学”取径;所谓“社科法学”或各种法社会学研究,则自觉地采用了“社会—法学”取径;各种法律文化研究,特别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采用了“历史/文化—法学”取径,试图从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出发捍卫法律秩序的中国性[9]。以上三种研究路向(特别社科法学和“历史/文化—法学”取径),对于把握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实践约束条件(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其缺陷同样明显。正如邓正来指出的,“政治—法学”取径预设了法律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甚至预设了这种依附的可欲性。[10]这种依附,不但把法律视为政治的附庸,抑且无力对中国法律问题进行自主性的思考。关于社科法学所预设的经验主义取向的缺陷,正如吉登斯告诫的:
“如果社会学家仅仅将他们学科的范围局限在易于用经验事实进行验证的那些领域,那一定是错误的。这是一条通往毫无结果的形式主义之路,使社会学与真实的生命和生活疏离化,使它与那些原本最能有所贡献的课题变得毫不相关。”[11]
只要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对德国“历史法学派”刻薄而不乏深刻的嘲讽,我们便可以洞察到“历史/文化—法学”取径的缺陷: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历史对这一学派,正像以色列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只是表明了自己的过去,因此,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国的历史。这个夏洛克,奴仆式的夏洛克,发誓要凭他的期票、历史的期票、基督教德意志的期票来索取从人民心上剜下来的每一磅肉。”[12]
马克思的嘲讽尽管尖刻,但对那些将中国历史(包括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浪漫化的论者而言,尤其值得警醒。
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不但同时凸显法律的政治制约性、社会制约性和历史制约性,抑且主张捍卫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想,特别是“永续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政治哲学承诺。换言之,与它们多隐含地预设了“政治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不同,我主张以一种基于“反思性现代性”的“反思性情境主义”立场,对待所有这些实践约束条件:它们本身既是反思的凭借,亦是反思的对象。为此,我建议通过政治理想或价值理想与实践约束条件的交互比勘所达致的“反思性平衡”,对于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我对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关注,力图超越任何单一的学科化视角,从而把现实的政治架构、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与现代转型的共通演化逻辑深度结合起来。为此,我尤为强调社会理论视角、法哲学/政治哲学视角与历史/文化视角的结合,从而在充分把握现代化所蕴含之普适性社会演化逻辑的基础上,在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中,深入(而不是直觉主义地)把握文化传承的运作空间与促进文化变迁的社会机制,特别是对某种文化传统具有“功能替代”作用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秩序”——本书第五章对“差序格局”的探究、第六章对“反正义的公平观”的分析等,便充分展现了我经由“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所形成的这种学术立场。
三曰“法学历史主义”(道德—历史主义)。在此,我特指许章润的“汉语法学论”。汉语法学论,尽管采用了法学历史主义的研究取径,但不同于排他性地捍卫法律文化传统之延续性的“历史—法学”取径,其对“历史”的理解更具有开放性和反思性。在许章润的视野中,“历史”不等于“死的传统”,即黄宗智所说的“博物馆化”的传统,而是把传统本身在历史中的“转进新生”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所谓的法学历史主义,包含着“思考过去并有选择地遗忘的可能性”。这里的关键是,他赋予了“历史”本身以理性品格和道德内涵。这种理性品格和道德内涵,主要通过他关于历史之三个不同向度的独特观念凸现出来:⑴以“法度高于法律”的法律观,阐释(hermeneute)关于历史的过往向度;⑵以“生活世界、规范世界与意义世界相统一”的社会观,解读(interpret)关于历史的当下向度;⑶以“期待人性趋善”的人性观,展望(expect)关于历史的未来向度。经由对关于历史的三个不同向度的这种理论把握,许章润既赋予了历史以理性品格,又以道德蕴含来填实这种理性品格,从而具有显见的“道德—历史主义”取向。从许章润的内在理路来看,对历史之过往向度的阐释、对历史之当下向度的解读,是其对未来的“社会想象”(socialimaginary)是否可欲且可行的认知性前提。然而,他对历史的阐释采取的却是“信念性”态度,而不是追求可分享性(shareability)的“认知性”态度。其历史阐释主要是一种思想史的把握,部分与制度史有关,但基本与社会史无涉。因此,其所建构的中国文化认同——基于儒家义理形成的“汉语法学”文明品格——便只能是我所谓的“典籍性的中国认同”(Chinese identityin classics)。它只能保有与历史典籍的一致性,但却无法确保与传统中国的历史现实的一致性、与当下中国人的文化记忆的相关性。进而言之,由于未能积极回应现时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正当化压力”,他所建构的中国文化认同无法通过“情境化正义”的正当化检验,从而无法通过公共证成确保文化认同的“本真性”。就他所主张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来说,如果不能妥善措置社会正义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它便不可能处理好“自由”“共和”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具有学理融贯性的“法理”。由于未能妥善处理社会正义与文化认同的关系,许章润势必会在其学理论说中陷入文化情怀凌驾于政治担当之上的困局之中。而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韦伯所说的“群众性政治家”)的公共论说,又以针砭时弊的政治担当著称。因此,如何将其深浓的文化情怀与果敢的政治担当整合为学理融贯的思想体系,仍是许章润的未竟之业。[13]
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主张建构“基于中国文化认同的(法律)理想图景问题”,但是它把这种有待建构的文化认同视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未赋值的占位符”(unsaturatedplaceholders)。我不认为学者或知识分子可以无视现代社会“公意政治”的合法化原理,因而可以替代公共选择和公共证成而对文化认同的实体性内容进行“独白式的”(monological)理论建构。毋宁说,我们应根据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结构化情境,并结合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对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化认同形成的理念(政治哲学法则)和程序性机制进行理论建构。本书第八章(《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正当法则》)既是对中国情境中的文化正义的论述,亦是根据“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及社会主义在当下作为“共同政治文化”等结构化情境,并结合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化认同形成之政治哲学原理所进行的理论建构。本书在多处阐述了公共商谈和公共证成机制在转型中国建制化的必要性,这便指向了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化认同形成的程序性机制。可以说,我为许章润深陷其中的“自由”“共和”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找到的出路是走向一种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程序主义民主观,即程序主义的人民主权论。此种民主观,既顺应了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合法化机理,亦为中国宪法(如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等)所确认、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所承诺,还符合现时中国党治国家的政治架构,甚至还可以制度化地消解因公共自主实践之历史性缺位所导致的民粹主义顽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建设性举措。更一般地看,把法律和政治问题置于由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与实践约束条件(转型中国的结构化情境)之交互比勘所形成的反思性空间中予以深度把握,既可以增强理论建构的情境相关性与学理自洽性,亦可避免儒家人文主义式的政治理想主义常犯的毛病,即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由于儒家的部分观念(特别是仁爱/仁义观念、王道政治等)具有“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规范性空间,而现实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则与之多有扞格不入之处,因此以回归儒家道统为名,使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朝着更为正当和可欲的方向发展,便成为儒家人文主义者念兹在兹的政治哲学或法哲学立场。然而,如果我们的学理言说或公共论说,只是从自己信奉的某种理念、价值甚或偏好出发,而把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与转型中国的结构化情境均置之不顾,那么我们不但会因对后者的忽视而导向政治激进主义,抑且会因对前者的无视而具有直觉主义、情感主义(emotionalism)甚或独断主义(dogmaticism)倾向。
四曰“法教义学”。“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legal doctrinalanalysis/legal dogmatics;或称教义法学)原本是德国法学界盛行的法哲学理论,但近年来随着有德国学习和研究背景之学人的大力推介,已在当下中国蔚为与社科法学分庭抗礼的理论模式。法教义学,其实是更为彻底和精致的法律实证主义。正如诺依曼(UlfridNeumann)所言,“法教义学要以对一国现行实在法秩序保持确定的信奉为基本前提,这也是所谓的‘教义’的核心要义所在。”[14]阿列克西(RobertAlexy)进一步指出,法教义学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的研究:⑴描述—经验的维度,即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⑵逻辑—分析的维度,即对法律之概念—体系的研究;⑶规范—实践的维度,即提出解决疑难的法律案件的建议。[15]可以说,法教义学是以法律规范、法律体系及其运行过程为中心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因此,它具有实证主义法学的所有缺陷。我并不一般性地否认法教义学研究(特别是对法教义学理论本身的学究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但我尤为怀疑以法教义学取径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思想价值。必须看到,以法律规范、法律体系及其运行过程为中心的法教义学研究,惟有在法律规范相对完善且基本得到遵循、法律体系健全、现代司法体制已经确立起来的国家——质言之,现代法律秩序已然确立即现代条件下的立宪、立教、立人和立法事业已告完成的国家——方始具有更大的学术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现代法律秩序仍亟待历史性的突破,我们何以对其法律规范、法律体系及其运行过程进行法教义学研究?梁任公先生逝世后,常燕生曾做出了如下评价:
“在整理国学方面,梁先生的功力、成绩未必胜于王国维、陈垣诸人,然而在社会所得的效益和影响方面讲,梁先生的成绩却远非诸学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轨道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一千个王国维的出现,抵不住一个梁启超的死亡的损失。”[16]
在现代转型仍待收束、现代法律秩序仍待建构和定型的转型中国,社会更需要的其实是法理思想家,而非擅长“螺蛳壳里做道场”“在针尖儿上跳舞”的法理专家。固然,我们没有多少人有机会成为思想家;但保有思想者直面现实、引领时代、范导实践的情怀和品格,却是每个有担当的学人应当、而且可以做到的。
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其实秉承了马克思的一个教诲:“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17]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相应的社会文化,仍处于现代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相较于对实在法体系的教义学研究,构建与现代转型相适应的法权体系,当成为更为优先的历史课题。因此,公共法哲学主张把我们的视角,转向“前司法”甚或“前法律”的立国、立宪、立教、立人和立法诸课题,把转型中国的法律现象视为“前法律”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现象,从而为转型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做出自己的思想贡献。
五曰“人文—法学”取径。我这里特指魏敦友所谓的“新道统论法哲学”采取的研究取径。在《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魏敦友教授法哲学讲演录》《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新道统论及其语境》“法哲学三部曲”中,魏敦友集中阐述了其法哲学立场。依我个人鄙见,将其法哲学立场贯穿起来的,可谓之“人文—法学”取径,即利用历史学、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等人文思想资源,把握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魏敦友的法哲学论说,是在邓正来“理想图景论”的激励下形成的。他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阐发,主要借用余英时、钱穆等的论说,把它置于中国道统之重建、中国文化之演进的大历史视野中进行把握——他把法哲学视为中国文化继子学、经学、理学之后有待实现的新“哲学突破”。这种阐发既在中国文化的演进逻辑中,颇具匠心地定位了中国现代法律秩序所倚赖的文化母体,亦赋予中国现代法律秩序以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底蕴,是对我所谓的“邓正来问题”的建设性推进。但其学理缺陷同样明显。从现代法律秩序运行的角度来看,魏敦友视野中的“人文—法律”知识,仅仅是作为生活世界之伦理共识(而非道德共识)的备选(或罗尔斯意义上的“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而存在的,尽管其内容对于部分社会成员而言是可欲的,但它们能否真正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道统”),有待于以立法机关为核心的“合法化系统”的反思性过滤——质言之,有待于社会成员作为公民的公共证成。再者,作为集“知识/符号系统”与“行动系统”于一身的社会功能系统,现代法律既与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成就相联系,亦是“全社会整合”的核心媒介。换言之,作为知识/符号系统,法律与社会成员在生活世界中的道德共识和伦理共识相关联;但作为行动系统,法律亦是现代社会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系统、以权力为媒介的行政系统之组织手段。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不像后习俗道德,法律不但代表着一种文化知识,抑且构成了制度化秩序的一个重要核心。”[18]显然,魏敦友式的“人文—法学”取径,只关注了法律作为“知识/符号系统”之维度,但却遗忘了法律作为“行动系统”之维度,而后者则是现代法律具有“不可随意支配性”之关键所在。由于未能把法律作为行动系统对待,并视之为全社会整合的核心,它不可能基于现代社会政治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对转型中国“道统重建”之实体性内容或程序化机制,进行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与此相适应,其所采用的核心概念,诸如政统、道统和学统云云,本身是含义指向十分模糊的概念,且无法指涉具体甚或宏观的法律现象,若非经过概念转换,无法真正进入法哲学的论域之中。
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在诸多方面借鉴、吸纳了魏敦友秉持“人文—法学”取径所获得的认识成果,诸如“中国思想的四次突破”“邓正来—邓晓芒律令”等概念框架,已成为本书把握相关论题的学理参照。但不同于“人文—法学”取径,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采取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取径。因此,它既可以避免其将法学“人文学科化”的缺陷,亦可以把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置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哲学承诺与转型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情境中,推进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
《公共法哲学》读后感(六):言公之为责任——关于“公共法哲学”的答问
全文链接:http://sunguodong.fyfz.cn/b/966898
言公之为责任——关于“公共法哲学”的答问
孙 国 东
按:这篇答问录系围绕孙国东新著《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进行的学术对话。冷志武、杨勇和程威等学友阅读完该书后提出了若干问题,然后由孙国东将这些问题归并,并予以回答。其中,冷志武系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杨勇系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程威系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孙国东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一、源与流
程 威:作为邓正来先生的学生,您在书中多次提到自己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是对邓正来思想的推进与深化,可否简要谈谈邓正来对这本书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理解您对邓正来思想之推进与深化?
孙国东:邓正来先生对我这本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我目前关于“公共法哲学”研究的影响,至少包括以下两个不同层面。
首先是论题方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拙著《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就是以我个人过去十余年的学术探索,回应邓正来先生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提出的“基于中国文化认同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我把它叫做“邓正来问题”。在拙著的“代序”“上篇”和“跋”中,我曾分析了邓先生“理想图景论”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力图进行的学术推进工作。毋庸置疑,邓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过去20年来中国法学界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但正如邓先生本人一直强调的,“知识一定是有其限度的,而知识的限度主要是由我们人的理性所具有的构成性限度所决定的。”毋庸讳言,他本人的既有论说也有其自身的学术缺陷,这至少表现在:标明其法学研究特色的“知识—法学”路径,其实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有知识、无社会”的跛足的知识社会学,缺乏对中国社会(法律)实践层面的指涉性和介入性;他严重忽视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合法性最终依赖于公共商谈(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这一现代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他把法学仅仅视为其“理想图景论”得以出场的个案,严重低估了法律秩序作为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之核心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法哲学作为中国现代转型之“第一哲学”的地位;等。
我在拙著中写道,我“力图以更具学理性的公共关怀、更具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更具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回应他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开掘出的思想空间。”这里的三个“更”,其实就表明了我对“邓正来问题”的阐发和推进方向:其一,我力图以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历史社会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增强法哲学研究对于中国情境的相关性、指涉性和介入性;其二,我想挑战自己的天赋极限,力图在中国情境中做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那样的实体性理论建构工作,而不只是做宣言性、论纲性乃至口号性的研究(拙著关于功能主义法律观、底线正义原则、关联性正义、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等的建构,就是我在中国情境推进实体性理论建构的努力);其三,我力图把“思想性的学术”和“学术性的思想”深度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关于公共事务的思想关怀与学理性分析深度结合起来。
以上研究取向,既是我区别于邓正来先生的地方,也是我区别于国内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同行的地方。我个人不太喜欢学术界盛行的那种匠气十足、但与中国法律和政治实践无涉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也不满足于像邓先生那种只是发出“主体性中国”“以中国为思想根据”等口号,但却不能以自己的学术努力进行自主理论建构的取向。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是:邓先生作为学界领袖,固然可以担当那种引领学术议题、指明研究方向的工作,但作为年轻一代的学者,我们这么做恐怕是要挨骂的。毋宁说,我们须以更加合乎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的方式,以自己具有创造性的学理分析和理论建构,承载我们的公共关怀。
其次是在学术取向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更加潜移默化、不太容易察觉的影响。对我个人来说,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问题导向的跨学科视野。以所研究的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归属自我设限,这是邓正来先生和我共同遵循的学术研究取向。如众所见,以哲学的分析哲学化、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占主导为标志,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在朝着学科主义、技术主义的路向发展。这种“内倾型”的发展导向,在强化各学科身份认同(identity)的同时,其实极大地削弱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创造能力,以及对于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回应能力——所谓“精致的平庸”,莫此为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诸多重大实践问题,比如跨国公司对于民族国家的威胁、金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精细化发展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正义的威胁、信息化时代大型网络公司对于个体自由的威胁、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威胁、伊斯兰世界对于现代性的挑战,乃至正在进行的中美对峙等等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回应能力甚至还不如电影、小说和新闻作品来得犀利和透彻。就中国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来说,很多研究者急于与国际接轨,沉浸在学科主义、技术主义的迷梦之中,并以此捍卫各自学科的正统和边界。他们挥舞着“学科”的大棒,实际上奉行着“山头主义”(parochialism),醉心于规训信徒、清理异己的纪律整肃工作——“discipline”(学科)的另一个含义就是“纪律”。在他们看来,政治哲学如果脱离了分析路向,如果脱离了罗尔斯或施特劳斯,就是低劣的政治哲学——我个人就曾听一位连“政协”都不知道为何物的青年政治哲学研究者大放厥词说,不懂分析哲学的政治哲学都是不入流的政治哲学;由于现代法哲学更具有专业性,它如果偏离了实证主义和教义学传统,甚至就不能称为法哲学——套用一位青年法哲学研究者的话来说,就不会被视为法哲学研究的同行。他们沉浸在学科主义、技术主义这种看似先进且时髦的学术导向中,却没有看到这种以学科设限的“内倾性”取向,是以牺牲包括法哲学、政治哲学在内的实践哲学之实践性为代价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科主义、技术主义取向是以其法律和政治秩序已然定型、现代学术传统根深叶茂且学术分工精细化为背景的,那么,对仍处于现代转型进程的当下中国来说,对于现代法律/政治秩序仍待建构、现代学术传统仍待塑造的转型中国来说,盲从学科主义、技术主义取向则不啻为一种思想和学术上的“双重自戕”:它既无力推进可范导法律和政治实践的思想创造,也无益于创造和积攒“本于中国、但属于世界”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学术传统。显然,要推进基于中国情境的思想创造,积攒中国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学术传统,我们必须超越学科主义、技术主义的取向,而代之以回应转型中国的法律和政治问题为旨趣,推进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其二是将西学思想史研究与关于中国的研究适度分开。邓正来先生在中国学术界一直被人误解。由于是中国最权威的哈耶克研究者之一,他常常被误认为是“哈耶克主义者”,进而被纳入自由主义的阵营之中;由于他晚年对“主体性中国”和“重新发现中国”等的呼吁,他又是新左派阵营乐于亲近的学者。据我个人理解,这在根本上是因为评论者没有看到他关于哈耶克的研究与关于中国的论说是相对分离的两个研究。事实上,将西学思想史研究与关于中国的研究分开,是我个人从邓先生那里获得的几个最大教益之一。两者一个是“照着讲”的研究,一个是“接着讲”乃至“自己讲”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研究性质,自然也具有不同的学术旨趣和评价标准(一般来说,“照着讲”的评判标准是准确性,即对研究对象的思想的把握是否准确;“接着讲”和“自己讲”的评判标准则是解释力,即所建构的概念框架、理论模式甚或研究范式,是否对研究对象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之所以要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区分开来,根源于我在拙著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基本判断:几乎所有的西学理论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情境错位”的。这意味着:我们应在深入把握转型中国的结构化情境的基础上,对既有的思想资源进行转换、嫁接或整合,而不是直接舶取任何既有的理论资源。事实上,在学术上一味盲从西方,既是像中国这样的“尾随着国度”(韦伯语)学术自主性缺失的一大表征,也是其亟待超克的学术顽疾。日本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学家之一丸山真男,就曾尖锐地批评了二战后日本政治学者“不从本国的现实提出问题,而是一味地追随欧洲学界的潮流和方法”的取向。然而,“欧洲政治学概念看起来描述得很抽象,实则背后蕴含有欧洲数百年来的政治历史脉络,哪怕是其中的某个命题,也是在其现实的变化波动中孕育而成的。”借用丸山真男的话来说,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像“过去亚里士多德直面古代城邦国家一般;马基雅维利研究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般;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研究17世纪的英国一般;马克思研究二月革命和法国巴黎公社一般;”要通过研究本国政治发展的趋向,“来洞察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的规律,并要把这种确切获得的命题与范畴不断地在现实政治中加以验证,使之发展下去”。我在拙著中曾写道:
“就中国法哲学(甚或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来说,既有的理论资源都有用, 因为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文化传统共同影响的当下中国,所有的中西理论资源都蕴含着我们可以汲取的思想养料;但既有的理论资源又都无用——如果我们不去建构它与本身就有待予以深入把握和理性认识的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在当下中国学术界,那些从事西学研究的学者,常常不自觉地把他们所研究的某一种思想或理论原封不动地拿来作为言说中国(法律、政治、社会、道德等)问题的依据。请恕我直言,这其实是一种“智性的懒惰”。
其三是把尊重学术传统与挑战既有思想格局结合起来。邓正来先生曾有关于“知识的两大铁律”的论说,其中的一个铁律是关于学术传统与知识增量之间关系的铁律。“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我们的学术传统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学术传统就无所谓知识增量和不增量的问题。”因此,他一直强调我们须在充分了解和尊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推进自己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研究工作。他本人其实一直在做挑战既有思想格局的工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就是这种工作的代表。李零先生曾说:“只有挑战格局的人才能成为大师,只有挑战格局的人多了,才能成为大师辈出的时代。”我自然不敢以“大师”自居,但像邓正来先生那样挑战既有的思想格局,为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做一些前提性、铺垫性的学术工作,却一直是我个人在学术上的自我期许——我把这种工作叫做“清理地基”的工作。
冷志武:您的回答似乎是一个总体性的回答。能否结合您的这本书,谈谈相对邓正来先生的既有论说,您做了哪些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工作?
孙国东:在拙著《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中,我至少力图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学术突破工作:
第一,以对“政治/法律价值”(political/legal values)与“政治/法律价值观” (political/legal conceptions of values)的区分为突破口,通过借鉴“反思性现代性”等思想资源,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探讨,特别是主张围绕“中国现代政治/法律价值观”(基于中国情境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现代性价值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推进中国法哲学、政治哲学的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显然,这种努力对于推进中国情境中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自主理论创新,具有探索性的学术意义。
第二,从学术立场(“内在批判”/在给定处着力)、研究取向(“反思性的情境主义”)到研究思路(政治理想与实践约束条件/结构化情境之间的“反思性平衡”)、研究路径(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力图形成一整套基于中国情境推进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试图藉此超越当下中国知识界盛行的左右之争:封闭的“中国特殊论”(向给定处妥协)与“去情境化的普遍主义”(向假定处思考)。
第三,通过以“从天理世界观到法理世界观”把握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把法哲学视为中国现代转型的“第一哲学”、法哲学知识形态的四分法(“专业法哲学”“政策法哲学”“批判法哲学”和“公共法哲学”)等理论主张,对提升中国法哲学的实践介入性(情境自觉性)、拓展中国法哲学在公共思想界的言说能力和话语空间,进行了探索性的努力。
第四,通过“功能主义法治观”“以功能替代促进法律文化变迁”“反正义的公平”“关联性正义”“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等独创性的理论概念或理论观念,对关涉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两大基础价值——法治和正义——的规范性要求进行了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从而对适合于当下中国情境的“转型法哲学”原理进行了探究。
以上就是我力图进行的学术创新工作。当然,它们都只是我个人的探索,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学术创新意义,仍有待学术共同体的检验。
冷志武:您的博士论文选择哈贝马斯作为研究对象,我注意到您在本书也多次援引哈贝马斯的观点,可否谈谈您的“公共法哲学”思想,主要吸收了哈贝马斯哪些基本理论?
孙国东:我关于哈贝马斯的研究与关于公共法哲学的研究,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照着讲”的研究vs.“接着讲”乃至“自己讲”的研究。熟悉哈贝马斯思想的人,大概都能明显看到我关于公共法哲学的研究与哈贝马斯思想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之所以把自己的法哲学主张命名为“公共法哲学”,尽管直接受到了麦克·布洛维关于“公共社会学”论说的影响,但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商谈(公共参与、公共证成)论说的借鉴,却起着更为基础的作用。不过,我对哈贝马斯的借鉴始终是以中国情境为出发点,而不是邓正来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前反思性接受”。具体来说,我主要借鉴了哈贝马斯两方面的论说:
一是哈贝马斯关于现代社会“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的论说。在我的论说逻辑中,这种意识结构为现代条件下的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提供了基本的文化条件。但我在借鉴哈贝马斯的这一论说的同时,还结合中国情境做了社会—历史分析工作。在拙著第六章,我把哈贝马斯关于“后习俗道德意识”的论说与罗尔斯关于“原则化道德”结合起来,对20世纪中国的人民共和革命如何为中国带来“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进行了社会—历史分析。这种社会—历史分析,旨在呈现哈贝马斯关于“后习俗道德意识结构”的论说与中国情境的相关性和契合性——正是这种契合性和相关性,证成了我在情境中借鉴哈贝马斯这一论说的必要性。
二是哈贝马斯程序主义的人民主权观。哈贝马斯式的程序主义人民主权观,是我关于公共法哲学论说的四个核心理论主张之一。但我同样不是“前反思性的接受”,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它与中国情境的相关性和契合性。关于这种相关性和契合性,我事实上有较为系统的论说,不过拙著的相关论述较为分散。在此,不妨总结一下我的论说依据。首先,我把程序主义人民主权观所依托的“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视为与选举民主相并立的民主形式,认为它们分别确保了人民的“常态性出场”和“周期性出场”,是与“永续国家”(eternal state)——即有政府治理危机、但没有政治统治危机的国家形态——相适应的民主的两种制度化形式;相应地,以传统社会中被统治者起义或造反为表征的人民的“历史性出场”,则是民主的非制度化形式,是与“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即没有政府治理危机、但存在政治统治危机的国家形态——相适应的民主形式。其次,相比选举民主,“审议民主”是更为激进的民主形式,它可以回应阿伦特所说的“持续同意”(ever-renewed consent)问题,即在两次选举周期之间国家权力常规运行时的合法化问题,特别是不能解决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化延搁”(defermentof legitimation)问题,即由现代行政系统及时、自主、高效运行所导致的“合法化赤字”。最后,审议民主还是可以与“多元现代性”相适应的民主形式。考虑到中国现代转型所面临的独特结构化情境(如文明型国家的文化遗产、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义党治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转型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应当优先秉持一种程序主义的人民主权观,从而在充分确保中国现代法律/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的同时,为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Chineseness)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道路保留充分的想象和探索空间。
二、词与物
冷志武:您在书中多次提到现代社会的“后习俗道德意识结构”,请问“后习俗社会”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除魅的世界”有何关系?后习俗意识结构的确立又是如何影响法律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来源的?
孙国东:前文提到,我关于“后习俗道德意识结构”的论述借鉴了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说。哈贝马斯的这一论说,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韦伯关于“世界除魅”的论说与科尔伯格关于“后习俗道德”的论说。对此,我在(由博士论文修改的)第一本专著《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研究》的第一章中有较为细致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简言之,哈贝马斯把科尔伯格关于个体道德意识发展的论说进行了“社会进化论改造”,从而以“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定位现代意识结构的特质,并将其同韦伯关于文化合理化(世界除魅)的论说对接起来。
所谓“后习俗的道德意识”,表现为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基于原则的道德意识和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这就是说,把普遍主义的原则作为道德推理的依据成为现代人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的存在,使得依靠习俗性伦理证成其合法性的统治类型——即韦伯意义上的“传统型统治”和“卡里斯马型统治”——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相反,我们只能把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建立具有普遍主义证成基础的“法制性统治”之上。质言之,“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的存在,使得公共参与和公共证成具有了文化上的必要性。它意味着: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产生,还是政治统治所依托的政治举措和法律条文,都具有了基于民意而变更的必要性。“后习俗道德意识”的存在,与政治和法律合法化“古今之变”的逻辑是一致的。经由“古今之变”,政治和法律的合法化,不再能溯源于(恒常的)“自然”或“天理”,而只能求诸(流变的)人的(理性)“意志”。借用韦伯的说法,政治和法律的合法性不再能溯源于“基于传统共识的有效性”,而只能乞援“基于合理共识的有效性”,也即是说它开始成为非强制性共识的产物。
杨 勇:您在书中有这样一个判断: 把法哲学视为中国现代转型的“第一哲学”并且认为法律秩序是现代社会秩序的核心,因而一切的思想和研究都须以法律秩序的思考为重点。请问您做出这一判断的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是什么?还是说,您只是单纯援引哈贝马斯的观点?
孙国东:这里可能存在误解。我的确说过要把法哲学视为中国现代转型的“第一哲学”,并且认为法律秩序是现代社会秩序的核心,但我并没有说过“一切的思想和研究都须以法律秩序的思考为重点。”我只是说,“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理论知识应以‘法哲学’为核心呈现出来(至少法哲学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请注意,我强调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理论知识”——我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性”这个短语上加上引号,既预设了一种兼具现代性与中国性的“另类现代性”模式的可能性,也旨在强调它是以一个“古今中西问题”为题旨、以中国现代转型为关怀的题域。
概略地说,我的这一判断主要有两个依据:其一是社会理论依据。在现代条件下,法律秩序是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核心。如果说前现代社会要么把“神”(西方)、要么把“天”(中国)视为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那么在现代社会,表征着“公意”的世俗化法律则取代了“神”或“天”的至上地位。在这方面,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和关于合法统治的类型学,已经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社会理论论证;当然,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其他学者的论说亦充分证明了这一结论。其二是历史社会学依据。考虑到法律秩序是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同时考虑到处于“古今之变”进程的中国主要受前现代的“天理世界观”之支配,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为从“天理世界观”向“法理世界观”的一种世界观转型——或者借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来说,从“天理世界观”转向“法理世界观”,既是中国文化合理化(文化的现代更化)的历史逻辑之所在,也是中国社会合理化(社会政治秩序的现代转型)的文化前提之所系。正是基于上述依据,我主张把法哲学视为中国现代转型的“第一哲学”,认为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理论言说应以法哲学为核心呈现出来(至少法哲学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此处所谓的“第一哲学”之“第一”,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而是功能意义上的:考虑到法律在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同时考虑到中国现代转型有赖于“法理世界观”的确立和维系,因此,与其他所有知识形态相比,法哲学这种知识形态在认知功能上更能充分把握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
杨 勇:您多次提及您的研究是要基于中国情境,进而寻找到一个具有实体性的理论建构。请问这个表述的实质意涵是什么?什么是“实体性的理论建构”?是指理论所建构的规范体系能够作用于现实社会吗?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您的理论又如何下落到现实,成为一种具有实体的言说呢?
孙国东:我个人所追求的“实体性理论建构”,主要是为了超越学界流行的如下两种学术论说倾向:
一是赵汀阳先生曾经批评过的一种倾向:“指出错的,却说不出对的”。对学术研究来说,“指出错的”是容易的,但要“说出对的”却殊为不易。任何具有一定学术研究经验的人,大概都会同意我的这个判断:只要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甚至仅仅是简要了解或排他性地信奉某种宗教教义或哲学、道德整全性学说,我们便很容易指出既有理论模式的所谓“缺陷”;但要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理论模式,却十分考验研究者的学术洞察力和思想创造力。推进实体性理论建构,其实蕴含着我对某类批判性研究的拒斥,也就是用他人提出的理论模式(多为学科内获得较广泛认可的某种理论)去批判另一种理论模式。这种做法也许可以增进研究者个人的智识愉悦,甚至可能会澄清某些实践问题或理论问题,但却无益于产生真正的“学术增量”。不客气地说,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啻为表演性的“理论秀”或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游戏”。余英时先生曾转借金岳霖的话说:以一种“义理”去评判另一种“义理”,只能变成“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
二是那种论纲性、宣言性乃至口号性研究的倾向。有很多具有学术敏感性的学者,常常可以敏锐地洞察到某些学术问题,但却只能进行论纲性、宣言性乃至口号性的研究,无力推进具有实体内容和学理逻辑、包含特定理论构件(theoretical building blocks)的理论建构。无论是邓正来先生的“理想图景论”,还是魏敦友教授的“新三统论法哲学”,乃至许章润教授的“汉语法学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倾向。由于无力推进实体性的理论建构,他们的论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思想但轻学问、情怀先行但学理不足”的倾向。所谓“实体性理论建构”之所以注重“实体性”,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学术取向。它力图在遵循既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推进真正具有学术增量的研究。
翻检学术史,任何能在学术史上留名的学者,几乎都有自己的一套概念体系、认知框架、研究视角、理论模式乃至研究范式。即使那些以“批判”见长的思想家,比如马克思和福柯,也都提供了替代性的理论模式或研究范式,至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认知模式或研究视角。他们的批判,不在于批判本身,而毋宁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概念体系、认知框架、研究视角、理论模式或研究范式的优越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增量。
程 威:您在本书当中使用了很多的概念,哲学的、法学的或法哲学的,请问您这些概念中的元概念或者说核心概念是什么?是什么概念构成了您所关注的公共法哲学/转型法哲学的基础?
孙国东:在拙著中,我的确采用了很多概念。这些概念有些是法哲学和政治学中通行的概念,有些是我个人自创的概念,有些概念尽管是通行的概念,但我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进行的是规范性研究,而规范性研究的一个关键就是进行概念分析——这是规范性研究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科学研究(如描述性研究或解释性研究)的重要方面。不过,我所有具有个人特色的自创概念(如“功能主义法治观”“反正义的公平”“关联性正义”“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等等),都是服务于我对中国情境中某些结构化情境(经验参照点)的理论把握的。之所以要创造新的概念,是因为既有的概念都不足以充分把握我所要研究的对象或我所洞察到的问题。
在我的研究中,并不存在一个“元概念”。但有一对概念构成了我关于公共法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此外还有一个概念则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
这一对概念是我在前面反复提到的“政治/法律价值”与“政治/法律价值观”的区分。所谓“政治/法律价值”,是指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性价值本身;所谓“政治/法律价值观”,是指特定时空的政治社会关于这些政治/法律价值的某种观点,即关于政治价值的具体规范性要求的某种观点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政治/法律价值”与“政治/法律价值观”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政治文明(法治文明)”与“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的区分:政治/法律价值属于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政治文明(法治)范畴,政治/法律价值观则属于具有情境依赖性的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范畴。
对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区分“政治/法律价值”与“政治/法律价值观”至关重要:这样的区分可以使我们在有效抵御西方“政治/法律价值观”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法律价值”的制度化方式。进而言之,可以有效避免“现代化=西化”的文化本质主义取向,从而在抵御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同时,避免落入文化民族主义的窠臼之中,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的“另类现代性”保留想象和探索空间。
近年来,知识界所谓的“普世价值论”与“反普世价值论”之争、“宪政论”与“反宪政论”之争,论战的双方恰恰都未能把政治/法律价值与政治/法律价值观区分开来:一方(“普世价值论”“宪政论”)用(西方的)政治/法律价值观绑架了(现代)政治/法律价值;但另一方(“反普世价值论”“反宪政论”)一味地拒斥这种政治/法律价值观,却忘了解救被对方绑架的(现代)政治/法律价值。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后者的反应,就像警察把绑匪和人质一块击毙一样,过于仓促和草率而失之审慎和理性了。显然,只有区分了政治/法律价值与政治/法律价值观,我们始能在有效抵御西方“(政治/法律)价值观”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法律价值观(政治价值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拙著关于中国情境中法治和正义的具体规范性要求的探讨,其实就是对中国现代法律/政治价值观的规范性建构。这种学术努力,也体现了我所谓的“学理格义”。因此,关于“政治/法律价值”与“政治/法律价值观”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关于公共法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公共或公共性”则是贯穿于全书的另一个基础概念——它甚至是贯穿于拙著的一条红线。我至少在如下不同意义上谈到了“公共或公共性”:学术研究是康德意义上“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典型方式;学术应当成为章实斋先生意义上的“言公”治学;现代法律秩序是一种公共治理秩序;现代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依赖于公共商谈和公共证成;现代条件下的法哲学正在呈现“公共转向”;适合于转型中国的法哲学知识形态,应是区别于专业法哲学、政策法哲学、批判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即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可以说,在我关于“公共法哲学”的论说中,捍卫“公共或公共性”是一以贯之的立场:“公共或公共性”不仅关涉一种学术姿态,还关涉我个人对现代法律秩序的性质、现代法律秩序的合法化机理、适合于中国情境的法哲学知识形态等诸多学理问题的把握。
我所主张的公共法哲学,不是一种仅仅基于个人偏好的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而是建立在我对学术言说的公共性、法律秩序的公共性、在中国情境中不断积攒公共理性(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必要性等的深刻体认基础之上。因此,我不仅像哈贝马斯那样秉持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观,为公共商谈和公共证成保留了充分的程序化空间,还像罗尔斯那样为“良序社会建构细节性的设计方案”——这是哈贝马斯式的程序主义取向明确反对的。只不过,我所做的,是力图基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与结构化情境(实践约束条件)的之间“反思性平衡”,对那种在中国情境具有充分的公共证成前景的“政治/法律价值观”进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慈继伟先生在评价拙著时曾说:
“在方法论和问题意识方面,作者更接近哈贝马斯,对中国已经进入但尚未完全进入后习俗道德意识(以及更广义的后形而上学知性意识)这一根本转型有准确和稳妥的把握,同时在总体上显然倾向于用哈贝马斯所说的商谈方式处理公共法哲学的根本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作者以罗尔斯(而非哈贝马斯)的方式提出实质性的规范原则,包括在修正罗尔斯基础上提出的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正义原则。”
应当说,慈先生对我学术努力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
冷志武:您强调公共法哲学的“公共性”,提倡用公共商谈的方式取代独白式的理论推演来解决现代社会的合法性问题。请问,公共商谈的对象是什么?或者说公共商谈的边界在哪里?当公共法哲学的批判性体现出来时,如何平衡批判性与现实权力结构之间的张力?
孙国东:关于“公共商谈”(public discourse),社会理论家卢曼曾将其追溯至罗马法在处理监护关系的一个原则追溯:“Quod Omnes Tangit, omnibus tractari etapprobari debet”(直译为“影响到每个人的事务应当得到所有受影响者的倾听和同意”)。从根本上看,“公共商谈”的合法性原理仍依赖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同意”原则:从“承受者”(addressee)的角度来看,具有充分合法性的政治决策和法律条文只能是经他/她同意或授权同意的。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只有当政治决策和法律的“承受者”同时也是其“创制者”(authors)时,它们的合法性始能获得证成。因此,公共商谈的对象包括所有具有公共性的政治和立法举措。
从规范性的角度看,公共商谈不应当具有边界。但在实践中,它常常是受限的:既受限于政治当局主观上是否具有广开言路的意愿,也受限于政治共同体内部是否具备进行公共商谈的合适场域和充分时间、其成员是否具有践习“理性之公共运用”(公共商谈)的意愿和能力等这些对政治当局来说相对客观的条件。不过,从根本上看,公共商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充分性,直接决定着政治决策和立法举措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法性——一言以蔽之,公共商谈的赤字,会导致合法性的赤字。有必要指出的是,公共商谈体现了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观,它并不预设任何实体性的政治和法律内容。它允许将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根植于其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之上,但强调其合法性有赖于政治和法律承受者的同意,其同意的方式就是经由公共商谈而认可。
你所谓的“公共法哲学的批判性”,大致体现为公共商谈的批判性维度。公共商谈作为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形式,的确可能会对现有的权力结构构成挑战。当这种挑战的对象是宪制结构时,它体现为政治学或宪法学上所谓的“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对这一问题,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无论是美国立国时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的争辩,还是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间关于公共理性(理性之公共运用)的争论,恰恰表明我们很难从理论上给出一个适合于所有“时势”的正确答案。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像基本自由权项(liberties)这样的“宪法根本”(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问题,尽管是在原初状态——可理解为“立宪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商定的,但一旦确立下来,它们就是超越民主程序的存在,不能依民主程序修改。但对哈贝马斯来说,人权与人民主权是互为前提的,因此,“立宪时刻”(人民主权)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它可以依据政治意志的动员情况(人权特别是政治权利的践履)因时随势而启动。上一个世代的“立宪时刻”并不能完全替代当前世代的“立宪时刻”,因此,“既存的宪法原则在充分的政治意志被动员起来的情况下,可以受到挑战并得到修改”。据我个人理解,宪政对于民主的制约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制约的正当性,在根本上取决于既有宪制架构是否具有充分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既依赖于其在“立宪时刻”的合法性,也要受到当下世代和未来世代之政治意志(“公意”)的进一步检验,公共商谈的民主程序则提供了政治意志(“公意”)聚合和检验的政治机制。
冷志武:您对中国现代法律秩序有何期盼?或者说,哪些标准可以评判这种法律秩序已经实现?仅仅是“立法过程中,法律的认知开放”以及“司法过程中,法律的运行闭合”吗?
孙国东:我个人对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期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和实践约束条件,它应当是什么样的。我个人的研究,力图在中国情境中践习“理性之公共运用”。它力图从超越于权力逻辑(政治场域)、市场逻辑(经济场域)、传媒逻辑(社会场域)和个人价值偏好的自主立场出发,秉持“反思性情境主义”立场,对适合于中国情境的政治/法律“价值观”进行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阐释。
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可理解为卡尔·施米特所谓的“制序”(ordering)。“制序”的历史境况,决定了转型中国的法律现象必然是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必然包含着诸多“前司法”(pre-judicial)乃至“前法律”(pre-legal)的发展议程——具体包括立国、立宪、立法、立教和立人等五位一体的发展议程。这五大议程中,除“立国”已于1949年完成以外,其他四项议程仍有待突破或完善。
我的确主张:在立法过程中,我们更应强调法律的“认知开放”;在司法过程中,则更应强调法律的“运行闭合”。这种主张,一则是为了从学理上化解法律的合法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张力,二则旨在强调立法阶段我们须把法律视为政治共同体的公共事务(而不仅仅是法律人共同体的专业事务),从而使法律最大限度地成为政治共同体“公意”的体现。当然,这种主张也与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有关: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仍是“进行时”,远未臻至“完成时”。因此,我们更应在立法阶段大力发扬沟通理性,从而充分确保法律秩序的合法性。
三、群与己
杨 勇:您的理论似乎具有非常强的理性主义意味,许多的概念和观点的形成,都必须要首先借助对话和辩驳才能形成。这种思考的方式也许适合您所说的“理性的公共运用”。但是您同时也说到,对于思考和学问的追寻,除了社会政治的公共关怀外,还有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国问题和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另一个关切的方向是每一个人的内在生命体验,是活生生的生活变迁和情感伦理纠葛,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情感和伦理纬度。请问您是怎么看待和处理这部分问题的?
孙国东:我不太确定我完全把握住了你的问题的要点。我想,您是不是想质疑我的论说过于理性和冷峻,从而对于每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体的情感体验缺乏必要的观照和呵护?如果是这样,我承认这一点。我个人从事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我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应如何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法律和政治秩序)。因此,我关心的是国家层面的立国、立宪、立教、立法和立人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只有立教和立人涉及个体的情感体验和伦理维度。但就“立教”来说,我关心的是“伦理—政治”意义上的集体文化认同,而不是“伦理—存在”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就“立人”来说,我关心的是与现代法律和政治秩序相适应的公民应当具有何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个体在现代条件下的存在主义焦虑。
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吉登斯关于“解束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 与“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区分来阐明这一问题。相比关涉生活方式之可欲性的“生活政治”,我更关心涉及生活机会之正当性的“解束政治”——即使偶尔涉及“生活政治”,我也力图把它放在“解束政治”的框架内予以把握。这种取向的选择,固然是学术兴趣使然,但在根本上与我对当下中国问题判断有关: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经由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已然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落实了“解束政治”的基本成就,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与自我认同有关的“生活政治”问题,那么“解束政治”和“生活政治”是我们需要同时回应的历史课题,并且前者比后者更为基础。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确保社会成员生活机会的正义,单纯追求生活方式的不可替代性是不牢靠的,是没有保障的。在这方面,想想像LGBT这样的生活政治问题在中国情境中面临的困境,就不难明白了。
冷志武:您认为中国法律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对现实情境的关照,而且能在新左派和自由派之间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径。如果您的判断成立,那么在此过程中,法哲学家与普通公民应当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孙国东:我个人的学术立场,是一种中道理性的建设性立场,它具体体现为“在给定处着力”的内在批判立场。因此,它与“向给定处妥协”的新左派与“向假定处思考”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在拙著中,我曾用面对叛逆期少年的两类家长(“溺爱型”和“棒喝型”)来比喻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而我个人主张的则是一种“劝导性的中道理性立场”。这种立场力图在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与中国特有的结构化情境(实践约束条件)之间保持“反思性平衡”,从而对适合于中国情境的政治/法律“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现代性价值在中国情境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进行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建构。在这一过程中,法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一大使命,就是推进我所谓的“学理格义”工作。
如果说,西学东渐之初我们对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术语的翻译(如把“liberty”翻译为“群己权界”,进而译为“自由”),是类似于传统中国迻译佛经的文字或概念上的“格义”,那么在当下中国,为了切实推进具有中国情境自觉性的研究,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学理上的“格义”。这种“学理格义”之必要,根源于现代性本身内在地具有文化依赖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现代性价值,尽管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但这种普适性仅限于价值目标的普适性,而不是制度化形式和实现路径的普适性——换言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现代性价值的制度化形式和实现路径,具有高度的文化/情境依赖性。现代性价值的这种文化/情境依赖性,既是规范性的,也是现实性(实践性)的。就前者来说,只有把现代性价值与其在特定时空下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区分开来,我们始能充分保留文化情境对于现代性的范导空间,进而为现代性之中国特色(中国性)保留充分的阐释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对现代性价值在特定时空下的规范性要求进行学理阐释,既是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进行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的主要方面,也是其推进有学术增量的理论创新的主要方面。就后者来说,只有基于特定时空的文化/情境探求现代性价值的制度化形式和实现路径(制度和实践模式),我们始能把对现代性价值的追求推进至制度层面,进而落实于实践层面。因此,所谓对现代性价值进行“学理格义”,其实质就是要凸显现代性价值的文化/情境依赖性,进而结合特定时空现代转型的价值理想与结构化情境,对其具体规范性要求进行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阐释,并对与这种规范性要求相适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进行政治学和法理学阐释。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需要不断践习和积攒“理性之公共运用”(公共商谈)的能力。关于现代条件下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在道德上的期待(“立人”),我与两类论说取向区别了开来:
其一,它不同于儒家“成人”意义上的“立人”,即如孔子所言,“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第十四》),成为具备智慧、廉洁、勇敢、才艺、礼仪等完备人格的“大人”。与“公共法哲学”的思想立场相一致,我所理解的“立人”,凸显了“立人”的公共性。因此,它不是——至少首先不是——具有各种美德的“道德人”(moral man)(践行儒家“成人之道”的君子),而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共人”(public man),即充分尊重各社会功能系统的自主运行逻辑且具有公共自主性、积极投身于公共参与的公民——正是遵循这样的思路,拙著把转型中国“立人”的课题定位为“培育具有公共精神和规则意识的公职人员(政治家、公务员、法官和检察官等)、培育具有公民美德且积极参与社会合作的公民”。
其二,它也不同于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而采取了更具建设性的立场。现代条件下的公民美德,不应仅仅体现为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要求,更应体现为社会成员与罗尔斯意义上的“背景制度”(background institutions)之间的良性互动。正如卢梭指出的,
“我意识到,所有的事物都在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并且无论创立什么样的原则,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塑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就还原为这样的一个问题:何种政府性质最适于造就出最具德性、最开明、最聪慧且最好(这里的‘最好’取其最广义)的人民?”
因此,我们不应把某些国民素质问题视为不可更易的“国民性”,进而对其进行文化模式上的反思和批判,而是主张将其置于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中进行把握。关于现代条件下的公民美德问题,我们不能如传统社会般仅仅依靠道德教化,而毋宁需要把它放在与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互动格局中予以把握。现代条件下的“立人”在根本上是哈贝马斯意义上“学习过程”(learning process)的产物,即社会成员在由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秩序)塑造的社会互动情境和行动平台中,习得某些公共品格和公民美德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化,我们更应当建构有助于公民美德化育的“背景制度”。
冷志武:您在本书的“致谢”部分提到了您在美国参观耶稣教会社区的经历,说它让您对守护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加强烈的自觉和更加坚定的信心。我也注意到,您尤其在书的“代序”部分对学界当前的一些风气提出了批评与质疑,作为一位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您对自己有何期许与要求?
孙国东: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我此前对耶稣会士(Jesuits)的了解主要限于书本。如众所见,在涉及西方宗教改革的观念纷争和晚明以降的中西文化交流时,耶稣会和耶稣会士都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主体。但在我去圣路易斯大学哲学系访学之前,我难以想象耶稣会士在现实的西方社会中还有如此大的影响。圣路易斯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与我因同样研究哈贝马斯而结缘的William Rehg在该校任教。自2007年以来,Bill Rehg因应国内的各种留学项目要求,先后为我提供了近10份邀请函,但我一直到2015年3月才找到合适时机到他那里访学一年。不过,我怎么也没想到,Rehg就是一名地道的耶稣会士。他在耶稣会的层级是Brother Coadjutor(相当于世俗修士),还不是可以正式传教的神父(Father),因此在正式的场合,除了可以称他为“Prof. Rehg”外,还可以称他“Br. Rehg”。2016年1月,Rehg邀请我和太太到他们居住的社区参观,并在那里同另外6名与他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耶稣会士共进晚餐。在与他们的聊天中,我对人的纯粹有了前所未有的直观体认。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仍遵循着耶稣会成立之初所设定的戒律,不能结婚,没有私有财产,他们的工资收入统一归耶稣会所有,吃穿住行一应有耶稣会方面以普通标准供应。普通人孜孜以求的世俗幸福指标,对他们来说几乎都是戒律。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很难想象把我们追求的那些世俗化指标都抹去以后,我们还能不能生活?能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正是这样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让我对守护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强烈的自觉和更加坚定的信心。我只是一名学者,并不具有多么高尚的精神追求。或许,可以借用邓晓芒先生的一个说法,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我信仰“真善美”。我常常告诫自己:在那么多的职业门类中,我选择了学者这一职业,每天为此劳心劳力,既耗费着自己的自然生命,也消耗了那么多的稀缺资源,总得让自己无愧于学者的身份吧?在我们终将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回首自己作为学者的人生,即使不能让自己感动和骄傲,至少得让自己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平静和无悔吧?
古往今来,从张载的“横渠四句”到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到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关于学者的定位有很多让人高山仰止的说法。但我个人最感心有戚戚者,是康德把学术视为“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典型方式。在康德看来,“学者”身份具有内在的公共性;它并不专属于特定职业,任何公民只要是在践习“理性的公共运用”,他/她就是在以“学者”身份言说。因此,“学者”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即“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的态度。
清代大儒章实斋先生曾针对时弊提倡“言公”之学,并把“问道”与“言公”内在地关联起来:“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文史通义·言公[中]》)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庄子的话补充说,惟有“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庄子·天下》),始能“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贯”(《文史通义·言公[下]》)。因此,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我常以“问道且务学,言公而不党”自勉,并视之为自己努力接近的学术境界和学问品格。《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一书,正是我秉持这种自我期许所积攒的成果。我不敢妄言自己已然臻至这种境界和品格,但沿着这一方向自我修为、砥砺前行,至少是我正在做、将来亦会坚持做的事情。
《公共法哲学》读后感(七):【跋】:关于“公共法哲学”的虚拟对话(下)
全文链接:http://sunguodong.fyfz.cn/b/962532
跋:关于“公共法哲学”的虚拟对话【下】
孙国东
本文收入孙国东著:《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477-531页。
不泥学究,不做公知,努力创新
薛玖:我想先听听你对“不泥学究”的解释。
孙国东:我所讲的“不泥学究”,是说不拘泥于学究,绝对没有任何看轻学究的意思。事实上,我个人也做了很多学究性的工作,比如我关于哈贝马斯思想的系列研究成果,就完全是学究性的。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我借用了麦克·布洛维对社会学知识形态的分类,把法哲学分做四种知识形态:专业法哲学、政策法哲学、批判法哲学与公共法哲学。我特别指出,这四种知识形态都有各自的学术价值,当然也各有其“病理学”;四者之间并没有历历可辨的界限,而且常常相互支援对方。所谓的“学究”,在法哲学领域,大致就是从事与“专业法哲学”相关的各种研究。
与“针尖上跳舞”“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学究化工作相比,但我个人更欣赏思想性的工作,也就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创造,一方面促进学术增量的生产,另一方面对社会实践进行范导的智性活动。这既有我个人的学术旨趣等方面的原因,也与我前面反复提到的对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基本判断有关。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曾经引用了常燕生对梁启超的一个评价。他说,“在一切未上轨道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一千个王国维的出现,抵不住一个梁启超的死亡的损失。”只要我们正视并承认现实,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也许不能说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在当下中国仍处于“未上轨道”的状态,但至少可以说它们仍处于远未定型的状态。有鉴于此,我们其实更需要的是法理思想家。
薛玖:你这么说,我基本理解了,但问题是:即使你把自己定位一个“法理思想家”,你有信心创造新的法理思想吗?
孙国东:我绝不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法理思想家”,我只是一个有点思想关怀的学者。汉语中的“思想家”,要比英语中的“thinker”具有更深的内涵。并不是所有从事智识创造的人,都能称为“思想家”;相反,它多指称那些在思想创造方面天赋异禀且成就卓著的人。因此,“thinker”的准确翻译,应该是含义更广泛的“思想者”——我注意到新近有人主张将其译为“醒客”;这尽管是一个新创的词,但堪称音义兼顾的绝佳翻译。因此,像我等资质平庸的学人,最多只能称为“思想者”或者努力做一名“醒客”的学者。换句话说,最多只能追求把我所说的“思想性的学术”和“学术性的思想”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个人以“问道且务学,言公而不党”自我期许的一个缘由所在。
我绝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创造新的法理思想或法律理论。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介入性的学理分析”与“实体性的理论建构”放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这也是我把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努力原创”改为“努力创新”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性”工作的要求太高,切不可轻言“原创”。人类有多少思想是“原创”的?就连孔子也只敢说自己是“述而不作”,更遑论我辈?思想的创造是非常困难的。我个人觉得,如果能在前贤的基础上做点滴的思想推进,就已经无愧自己作为学者的一生了。
薛玖:你的言语中似乎包含着对“学究”,尤其是对“法理学究”的不满。而且,既有的法理思想或法律理论难道不足以解决当下中国的法律问题吗?为什么要另起炉灶自己去建构呢?
孙国东:我们也许应该区分两种“法理学究”:第一种是像你这样的学究,专注于“专业法哲学”的工作,不关心自己的研究与中国法律实践的关系。对这类研究工作,我个人表示尊重。因为他们的确对中国法哲学学术传统的建构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还存在一类比较隐蔽的“法理学究”: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法律专家,一方面从事“专业法哲学”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自己研究的“专业法哲学”思想,去言说中国的法律问题。对这类“法理学究”,请容我坦率地说,这是一种智性的懒惰。
辛佐:“智性的懒惰”——我很喜欢这个评价。中国学界总有那么一批“食洋不化”的人,总是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对这种“食洋不化”的人,一定要狠狠地加以批判。
孙国东:我没有你这种排他性的情绪。我更关心的是问题本身,也就是薛玖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既有的法理思想或法律理论,可以回应当下中国的法律问题吗?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法学界所采用的法理思想,几乎都是西方现代法理思想家创造的。它们都根植于西方的特定情境,是为了回应西方国家的特定问题而出现的。大体来说,自然法学派顺应了西方国家建构现代法律秩序的历史需要;实证法学派顺应了西方国家维持现代法律秩序的历史需要;“历史法学”适应了德国在崛起过程中保持文化不可替代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文化需要;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学法学”则顺应了西方建构福利国家的社会需要;当代西方的各种整全性的法律理论或者专门性的法哲学思想,包括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批判法学、女权主义法学、法律论证理论等等,适应的是西方国家进一步完善现代法律秩序的历史需要。特别是当代西方的那些法理思想,经常被当作法哲学的前沿思想,成为了中国法律学者言说中国法律问题的理论依据。然而,我们却没看到,它们其实预设了一个根本的前提,也就是与现代法律秩序相适应的基本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已然形成。比如说,罗尔斯就明确指出,他的正义理论只适用于文明的特定发展阶段,即大体对应于“丰裕社会”的文明发展阶段;他对“差别原则”的表述,也明确预设了一些基本的制度安排——仅从经济方面来说,就包括市场经济体系、惠及全民的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我在本书第七章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尝试建构了适合转型中国情境的“底线正义”原则。还比如,西方所有与司法改良、法律论证和法律方法有关的理论,都预设了“三权分立”下司法权独立的体制已然建成。显然,这些理论的所有预设条件,在当下中国都付之阙如。
从根本上看,当下中国法律问题的“元问题”,仍是法治问题——这正是本书中篇为什么聚焦于“法治”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元问题”没有基本解决之前,探讨与司法技艺等有关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至少意义会大打折扣。这是中国法律实践与西方法律理论之间根本的“情境错位”。正是这种“南橘北枳”式的情境错位,会使我们在直接舶取西方理论时会出现秦晖所说的“问题误置”。只要对这种情境错位有深刻的自觉,我们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既有的法理思想和法律理论,可以完整地回应转型中国的法律问题。其实,转型中国的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亦可作如是观。
龚梓:我想沿着您思路往下追问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在中国还没有最终形成,难道我们不应该借鉴西方法理思想去建构与现代法律秩序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吗?
孙国东:我想说的是,如果一项关于法治改良的议程走向了某种政治行动,它就不属于严格的学术讨论的范畴。换句话说,它不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沉思”(mediation)领域,而属于“行动”(action)。正如哈耶克关所说,“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人民采取行动。”关心政治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用政治的方式关心政治”,最终成为“键盘革命家”或政治行动者;有的人“用闲谈的方式关心政治”,最终成为“饭桌革命家”;政治哲学家则应当“用学术的方式关心政治”。
龚梓:你似乎把自己定位一个学院派的学者,但问题是你关心的却是一些相当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问题。我很难想象你遵循怎样的学理逻辑。你能说说你的学理依据吗?
孙国东:简单地说,我的理论依据就是“多元现代性”或“反思性现代性”。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元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思潮,是建立在否定“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的,也适应了“后冷战”时代大量非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历史需要。
龚梓:“多元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这种论调,已经成了陈词滥调。问题是,它有现实依据吗?有实现的可能吗?
孙国东:“多元现代性”或者“反思性现代性”不仅是一种理论,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种已被制度化的实践。20世纪中国的实践历史,事实上已经为中国建立了“多元现代性”或者“反思性现代性”的实践道路。我曾经写过一篇思想札记,名为《20世纪中国的三次“西化契机”及其历史反转》。在这篇札记中,我已对这条实践道路进行了勾画。大体来说,辛亥革命、重庆谈判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着三次“西化”契机,也就是全面追寻“西方现代性”的契机。但是,相应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创造和政治智慧,都使这些“西化”契机最终走向了历史反转,也就是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实践。
按照艾森斯塔特的理解,现代性根源于人的反思性和能动性,也就是以人的反思性能动地创造理想未来的可能性。在20世纪中国“多元现代性”的实践探索中,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俄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党建国模式与西方现代性价值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主要的反思性资源。如果说,孙中山试图以俄国社会主义建党建国模式与部分社会主义理想(新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部分社会主义要素),来探索落实西方现代性价值(民主、自由、平等等)的中国道路,那么毛泽东在借鉴苏联建党建国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特点等,试图开掘出一条试图超越“卡夫丁峡谷”的“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相应地,邓小平则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与现代化的经济体制之间,奠定中国现代性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议程)和政治框架(“四项基本原则”)。经过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三大历史巨人的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经走上了“多元现代性”和“反思性现代性”的实践道路,形成一种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我把它叫做“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辛佐:我觉得这个基于中国历史的把握,是准确的。既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又有历史和实践依据,可以弥补汪晖从思想史视野建构“中国现代性”的不足。
龚梓:问题是,即便这个把握是准确的,但是如果听任实践的逻辑,不等于就承认“存在即合理”吗?
孙国东:我这里只是一个非常粗浅的论述。而且,我对历史的阐释,并不想导向对实践的无谓辩护。如果那样的话,就真的具有“存在即合理”的倾向了。我个人认为,我们固然要避免“存在即合理”的倾向,但也应该避免“可欲不可行”的倾向。如果说,“存在即合理”是实践主义取向的社会科学和保守主义取向的实践哲学论者常犯的毛病,那么“可欲不可行”则是盲从西方道德政治哲学(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论者易出的问题。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也可以放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审视。
但是,在“存在即合理”和“可欲不可行”之外,我们有没有第三种出路?我认为是有的。其实,哈贝马斯所说的“内在批判”和罗尔斯所说的“现实的乌托邦”,就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道路,即采用哈贝马斯式“内在批判”的路径,基于中国情境推进罗尔斯式“现实的乌托邦”的理论建构,从而超越“存在即合理”的实践主义—保守主义取向,获得“可欲且可行”的规范性空间。这种“内在批判”的规范性依据(乌托邦),蕴含在中国现代转型所承诺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想中,因此它是“可欲”的、“批判”的;这种“内在批判”的实践依据(现实基础),则体现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及其所凝结的基本政治结构中,因此它又是“可行”的、“内在”的。
龚梓:我想追问的是,这条道路不是还没有成功吗?我们仍没有建成现代国家,这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孙国东:的确,中国在历史实践中展现的“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还没有成功,而且仍需要依靠理论家的想象力和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去突破困局。我在那篇札记的最后,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话: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方面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清算,但袭自苏联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却仍未根本松动。在未形成超越苏联模式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前,‘西化’思潮仍是威胁现有发展道路的一股潜流。因此,如何建立‘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仍是亟待突破的历史课题。”
我想,这段话可能是辛佐不愿意读到的,但是这也体现了我和你之间的区别。
龚梓:既然如此,我们难道不应该借鉴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成果,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吗?
孙国东:我没说过我们不可以借鉴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成果。毋庸讳言,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成果本身,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反思性资源。但问题在于,如何把西方现代性作为我们的反思性资源?
我觉得,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内涵和要求,而不只是停留在理念或口号层面,这样很容易把这个理念本身意识形态化,从而丧失它对实践应有的范导作用。
钟励:作家、收藏家马未都曾说过“文明求同,文化存异”的话,你也曾引用刘小枫在《刺猬的温驯》中的一个观点,认为要把现代性的价值形态与现代性的制度和实践形态分开,也就是要把现代性与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特定制度和实践模式分开。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法治这些现代性价值具有普适性,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范畴;但与它们相适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却具有高度的文化依赖性,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深刻把握“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内涵和要求的一大秘诀。
孙国东:但是,仅仅有这个“秘诀”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真正把现代性的价值形态与现代性的制度和实践形态分开,我们必须还要进一步把现代性价值在当下西方的规范性要求,与它在转型中国的规范性要求分开,也就是要建构适合转型中国情境的独特规范性要求。在本书“上篇”第四章和“下篇”的三篇文章中,我已经分别以“法治”和“正义”为突破口,建构了它在转型中国的独特规范性要求。这个层面的细微区别,尤其应当引起思想者的重视——在我看来,看到这个层面的问题,是在中国推进政治哲学或法哲学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
钟励:这么看来,所谓“普世价值论”之所以遭到当局的排斥和抵制,“普世价值论”的主张者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甚至是主要责任——就像“宪政论”遭到误解甚或抵制,“宪政”的阐释者也要承担责任一样。这在根本上是因为,“普世价值论”的主张者多把当下西方对这些价值的主流阐释原封不动、不经转换地移植到了中国,从而使这些价值连同它的制度和实践模式一道“捆绑式地移植”了进来。
龚梓:我们为什么要把“把现代性价值在当下西方的规范性要求与它在转型中国的规范性要求分开”?有这个必要吗?难道这些价值的规范性要求还有中西之别?
孙国东:这个问题问得好,请容我慢慢道来。
第一,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法治这些现代性价值,其内涵不仅不是自明的,而且是相互交缠在一起的,甚至相互之间存在着莫大的紧张关系。如何把握它们的内涵及其与其他价值的关系,本身就需要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讲,政治哲学家或法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对这些现代性价值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阐释。现代以来,无数政治哲学家或法哲学家的学理歧异,在很多时候就体现在对这些价值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分歧上。关于这一点,只要稍稍了解现代政治或法律思想史,就不难明白,无需多言。
第二,对这些价值的阐释,必须从转型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做出“切己”的阐释,也就是做出与中国情境高度相关的阐释。对此,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它们在西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规范性含义,就可以理解了。比如说,在20世纪以前的西方,对平等的主流阐释是形式平等(人格平等、道德平等、法律平等),直到二战以后才普遍开始具有实质平等的内涵。还如,就“法治”来说,也有英国“法的统治”模式与德国“法治国”模式的著名区别。这其实表明:现代性价值的内涵,具有相当程度的情境依赖性。
辛佐:我补充一句。如果从形式平等的制度化的历史来看,西方走得比我们想象得要慢得多。以美国为例,女性和黑人获得平等的选举权分别是1920年和1965年,非婚生子获得平等的继承权是1973年,同性恋者获得平等的结婚权则是2015年(并且是在巨大的争议声中通过的)。
龚梓:慢着,我必须打断你们的话:难道在全球化的21世纪,我们可以拿西方19世纪的价值观说事?
孙国东:这就涉及到我马上要说的第三点:对转型中国来说,要真正做出“切己”的阐释,不仅要考虑以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表现出来的“碎片化”的情境,还要充分考虑一个更为根本、更具有整全性的“元情境”,即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所谓“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其基本含义是:西方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现代性诉求在当下中国是“共时性”地存在的。
认识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就基本触及到了转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固然不宜直接拿西方19世纪的做法,为当下中国的某些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但我们必须把握真正属于中国的独特情境,以及这种情境对可行的规范性空间的制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可以追溯至晚清(乃至宋明甚或秦代),但在政治统一条件下的全面现代化,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如何在韦伯所说的“尾随者”(epigone)国度——即“追赶型”现代化国家——几十年的历史时段中,同时容纳并协调西方国家在几百年历程中逐步实现的现代性诉求?如果再考虑到这些现代性诉求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呢?如果还考虑到中国十亿以上体量的国家规模、“文明型国家”的“轴心”文明遗产以及现代大一统政治架构(党治国家的国家组织模式)呢?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国作为非宗教国家的特性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构成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本情境限制。一旦对这些基本情境有了自觉的认识和深刻的体认,我们就不会再专断而又信心满满地舶取当下西方对某些现代性价值的规范性阐释了。显然,如何协调现代性的共时性诉求与转型中国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建构现代性价值在转型中国的独特规范性要求的关键所在。
钟励:结合转型中国的独特情境对现代性价值的阐释,既考验着阐释者的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中国思想者捍卫自身工作的不可替代性的关键。如果原样照搬当下西方的阐释,就可以回应转型中国的问题,那么这种工作就是可以替代的——因为任何具有政治哲学、法哲学兴趣和英文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因此,如果要落实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法治这些现代性价值,我们必须通过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与转型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反思性平衡”,去建构这些价值在中国的独特规范性要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
孙国东:是的。事实上,我在本书正文中提到的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区分,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观”。前者指涉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法治等现代性价值本身,属于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政治文明范畴;后者指涉关于这些政治价值的某种观点,也就是关于政治价值的具体规范性要求的某种观点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它们则属于具有情境依赖性的政治文化范畴。所谓的“普世价值论”与“反普世价值论”之争、“宪政论”与“反宪政论”之争,论战的双方恰恰都未能把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观(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区分开来:一方(“普世价值论”“宪政论”)用(西方的)政治价值观绑架了(现代)政治价值;但另一方(“反普世价值论”“反宪政论”)一味地拒斥这种政治价值观,却忘了解救被对方绑架的(现代)政治价值。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后者的反应,就像警察把绑匪和人质一块击毙一样,过于仓促和草率而失之审慎和理性了。显然,只有区分了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观,我们才能在有效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在我看来,通过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与结构化情境之间的“反思性平衡”,建构适合中国情境的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是中国法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进行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的关键所在。
未竟课题及其他
钟励:皮埃尔·布迪厄曾说:“我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人们不再对社会世界说各式各样毫无意义的胡话——我之所以著书立说,就是要让人们,首先是那些被授予发言权的发言人,不再能针对社会世界制造那些表面上听起来酷似音乐的噪音。”你的研究是不是也包含着这样的自我期许?
孙国东:如果抛开语境单看布迪厄的这句话,的确包含了学者独立求索、努力创造的自我期许。但我们知道,布迪厄本人所提供的是一套有激进左翼取向的理论。我个人很喜欢阅读布迪厄、福柯包括马克思这样的激进左翼所撰写的文字。他们的文字,常常会给人以“偏执的深刻”的感觉。事实上,布迪厄的这句话,曾经长期写在我个人博客的显眼位置。这当然是我年少轻狂时才会做的事。现在的我对所有针对社会世界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论调,都持怀疑态度。谁又能保证你说的这一套,不是另一种“表面上听起来酷似音乐的噪音”呢?一般来说,这种“舍我其谁”的论调,不是具有激进左翼的色彩,就是具有极端右翼的倾向。如果这种论调只出现在思想领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一旦诉诸政治行动,常常会是社会的巨大灾难。晚年恩格斯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时,曾经提出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原理: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我个人秉持的“中道理性”立场,更愿意对形成社会进步的“总的合力”的可能方向——也就是平行四边形对角线指向的方位——进行建构和阐述。
龚梓:我知道你想做思想性的工作。但思想性的工作,只有面向大众,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社会影响。你这样一本只印刷几千册的书,能对整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孙国东:学术或思想的价值,绝不是依据他的阅读量来评价的。必须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观看艺术电影的人,肯定会比观看商业电影的人要少得多;阅读孔子和康德的人,肯定会比阅读韩寒和郭敬明的人要少得多。但我们显然不能说,韩寒比孔子更伟大。一般来说,“公知”是以大众化的方式关心一些大众话题;学者要么关心“小众”的问题,要么以“小众”的方式关心大众话题。两者之间,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应该互相尊重、相互支援。
钟励:“公知”进行公共言说所依据的就是别人创造的思想,特别是某些西方思想家所创造的思想。只不过,那些原本深奥的思想经过无数人的咀嚼和诠释,变成了可以向大众宣扬的观念或知识。在这个从思想创造到思想传扬的过程中,思想创造者处于始端,“公知”则处于末端——尽管“公知”很多时候只从二三手资料中获得了对某些思想的歪曲解读。按理说,“公知”应该对所有从事思想创造工作的人抱有敬意才对。如果没有思想创造者的工作,“公知”的公共言说岂不就成了“无源之水”?为什么不能相互尊重反而要去敌视思想者的工作呢?
龚梓:我刚才这个问题完全是善意的,是从最大限度地扩大你的思想的影响力出发的。在我看来,你采用了那么多的学术“黑话”(jargon)组织你的思想,这本身就极大地提高了你的著作的阅读门槛,会让很多读者望而生畏,甚至望而生厌。
孙国东:之所以出现所谓的学术“黑话”,与我这本书的读者定位有关,也与思想或学术创造的规律有关。一方面,就像哈耶克会为自己的《通往奴役之路》成为畅销书感到不解甚至不耻一样,我绝不期待自己的著作成为畅销书。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写给社会大众的书,而是写给同行看的书。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完全撇开既有的思想和学术传统,“闭门造车”地去创造一套全新的思想——那是所谓“民科”或“民哲”的路子,不是属于严肃的学术讨论的范畴。就像我一直努力的那样,我尝试着把“思想性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结合起来,以思想创造引领学术研究,同时以学理逻辑贯通思想创造。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沟通学术与思想,这不可避免地要把思想建立在厚实的学理基础上。正是为了衔接各种思想或学术传统,我才不得不采用大量所谓的学术“黑话”。其实,我个人已经做了一些主动降低阅读门槛的工作。我之所以在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收录了这篇对话体的“跋”,正是为了便于我有限的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我的思路或想法。
龚梓:那你预期的读者是谁?对他们又能产生什么影响?
孙国东:我预期的读者,是那些有基本的法哲学、政治哲学知识储备,同时又愿意随我一道去深切而又理性地思考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人。这样的人在当下世代也许不会很多,但是只要中国想要平顺地完成现代转型的预期目标,就必须主要依赖他们。因为他们是中国“公共理性”(“理性之公共运用”)的主要依托力量,而“公共理性”(“理性之公共运用”)对于中国现代法律或政治秩序的建构来说是必备的核心要素。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特别是网络公共领域)已被我所谓的“基于直觉主义的民粹主义”裹挟,甚至已经成了部分民众激情狂欢的舞台,在公共领域受欢迎的言论常常那些比较极端、出格和具有鼓动性的言论。这当然是十分不理性的。
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中曾经探讨过“非理性的移情作用”。举个例子,一个遭遇感情挫折的女人声泪俱下地说:“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她这么说当然是不理性的,因为更理性的说法应该是:“一部分男人不是好东西”;或者“一个叫张三的男人不是好东西”。然而,当一个女人做出这样一个非理性的全称判断时,她却可以很快捕获听者的同情。“非理性的移情作用”,可以解释很多社会和政治现象,比如说,为什么真性情的人(特别是在酒桌上表现真性情的人)更容易交到多朋友?为什么文学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对人物性格的塑造都是性格比较极端、个性比较鲜明的类型?为什么2016年的美国竞选中激进的Trump可以一路高歌猛进,稳健的希拉里反而败下阵来?……等等。在我看来,非理性不仅有“移情作用”,事实上还有“叠加效应”——我们姑且称之为“非理性的叠加效应”。为什么当一个人突然提高嗓门要和我们辩论或者吵架时,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提高嗓门?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时期获得历史舞台的政治力量越来越激进?为什么当下中国思想界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左右对峙越来越不可调和?……等等。在我看来,它们都与“非理性的叠加效应”有关,当然最终还是以“非理性的移情作用”为基础的。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公知”、“意见领袖”、在公共论说中取得较大话语权的思想者,乃至在政治普选中获胜的政治家,多秉持某种较为极端、激进的立场?显然,非理性的言论更容易激发和捕获受众的某些情感、情绪乃至情结,如民族主义情感或情结、与自身遭遇相联系的某些道德直觉等等。然而,道德直觉可靠吗?这种集体不理性的局面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怎样的历史逻辑、社会背景和政治结构中产生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本身就应该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一个严肃的学者或理性的思想者,不但不去对它进行分析和批判,反而去迎合它,是不可思议的。
钟励:在学术史上,凡是那些可以产生巨大学术影响或者社会影响的学者,都会有明确的“主义”标签。这种“主义”标签,既方便了受众的把握,也会极大地便利其思想的传播。在中国,“新左派”“新儒家”“自由主义”这样的标签,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你所谓的“转型法哲学”,似乎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你本人也明确同意赵汀阳所说的“无立场”方法。你为什么没有加入一个“主义”阵营或者为自己打造一个新的“主义”标签?
孙国东:“主义”标签的产生,也与我前面提到的“非理性的移情作用”密不可分。一种理论学说,如果成为某种标签化——实质上是极端化——的“主义”,就可以借助“非理性的移情作用”迅速产生良好的传播效应,但它也同时具有了意识形态化的潜质或特质——当下中国思想界(如果我们假定存在所谓的“思想界”的话)左右两派的水火不容般的互相攻歼,就表明了这一点。我大体同意盛思吾的一个说法,思想不是
“科书上苍白的痕迹或固化意识形态的同义词,思想是流质,是活火,是生命的自我拷问,是不可能超脱活体的人而存在的,从来只有个人的思想,所谓集体的思想(意识形态)者,不过是大人物们摆弄的一些图谱,而由感受力匮乏又贪图省事的学究以各种概念和逻辑语言去填充而已。”
因此,思想不是“站队”,不是“打群架”,不是“一群人的狂欢”,而是思想者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社会政治关怀进行的言说。
“转型法哲学”的确不是一个“主义”标签,我前面提到的“中道的现代主义”算是一个标签,但它并不符合学术传统的常规用法。之所以没有加入一个“主义”阵营,或者另行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主义”标签,一方面是想在纷繁复杂的中国问题面前保持一种审慎和谦卑,另一方面想保持一种我所秉持的理性品格。
如果非要找到一个可以表明我思想立场的标签,“公共法哲学”可能更合适,也更具有学术色彩。“公共法哲学”,不仅是章学诚意义上的“言公”之学,还可以恢复法律秩序作为公共治理秩序的面目,从而增强法哲学对转型中国公共事务的介入性的学理言说能力。而且,经过我的界定和转化,它还可以与“专业法哲学”“政策法哲学”及“批判法哲学”形成既互相区别又相互支援的关系。我之所以相对偏爱“公共法哲学”这个标签,因为它只是表明了一种学术旨趣意义上的思想立场,而不是像各种政治意识形态那样,指向的是一种封闭性、排他性的政治立场。
在我看来,要研究中国问题,保持对真实世界的好奇心,远比预先皈依某种政治立场重要。中国历史中的实践进程和当下中国实践中所呈现的历史逻辑,既超过了目前已知的几乎所有思想或理论模式的认识范围,也蕴含着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的契机。
辛佐:我记得苏力曾经把转型中国的法律实践,当作在中国推进法学学术创新的“富矿”。他主要是从相对于西方法治模式的中国法律实践的丰富性这个角度来讲的。你在本书上篇提到的非西方世界整体崛起的“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学者的学术创新来说,也堪称一个“富矿”。我觉得中国学者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争取创造属于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并使这种话语体系走向世界,在国际上争夺关于中国问题的话语权。
孙国东:我完全同意,当下中国是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的“富矿”。但我个人觉得,它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你刚才提到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为基础的方面。
我个人认为,当下中国体现了多种历史契机的“起承转合”,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范围内现代性本身的“起承转合”,也就是辛佐刚才提到的非西方世界整体崛起的“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下给中华文明提供的历史契机,即对现代性历史的“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全球性未来的“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贡献世界”的契机。第二和第三个方面,涉及的是中华文明自身不同思想传统的“起承转合”。
第二,中国自晚清以来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轴心”时代文明遗产的自我超越带来的历史契机,即对中国“轴心”文明遗产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其实现自我超越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实现“自我转圜”的契机。
第三,20世纪以来为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选择的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下为我们带来的新的历史契机,即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其实现自我超越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自我整合”的契机。
显然,这三个方面的历史契机又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人类现代史上有两种与资本主义相竞争的意识形态在一些国家被制度化: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已成为历史遗迹,但仍具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当下世界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性,那就是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主动吸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又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这种社会主义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经济要素共存一体的独特框架,使中国为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想象空间。同时,“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激发的对中国“轴心”文明遗产的传承期待,又把中国“轴心”文明遗产的自我升华以及这种遗产与社会主义新传统之间的思想整合推向了历史前台。可以说,当前对中国“轴心”文明遗产的重视,其实是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倒逼”出来的,是中华文明“贡献世界”的历史契机“倒逼”出来的。显然,建立在中华文明“自我整合”基础上的“自我转圜”,为中华文明以何种形态“贡献世界”提供了文化前提。
对中国来说,如何“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是远未完成的历史课题。总体来看,在晚清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主要是依靠实践主义的“试错”展现出来的。尽管在特定时期我们曾把某种“主义”写在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议程中,但是一直在根据实践中的“试错”效果不断调整“主义”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承诺的实践主义取向密不可分,也同它所容纳的相对宽松、允许“试错”的意识形态话语空间有着紧密联系。但是,从晚清以来的历史进程和当下的历史契机来看,没有任何现成的思想或理论足以全面把握其中的复杂性。因此,如何把握“历史中的实践进程和当下实践中所呈现的历史逻辑”,是远远要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的事情。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逻辑和实践进程,为我们自主的思想创造或理论创新提供了学术“富矿”。同时,它也警示我们:要对实践的复杂性保持更多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是预先宣誓对某种“主义”的效忠。
钟励:我在想,有没有现成的“主义”比较充分地把握住了这种复杂性?
辛佐: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充分把握住了这种复杂性的理论体系。因为它可以同时容纳“轴心”文明遗产、社会主义和现代性要素,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国家指导思想。
钟励:但是,我觉得它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由于过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很难适应国东博士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非西方世界整体崛起的“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给中华文明的“贡献世界”的契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凝聚国内的改革与发展共识,厥功甚伟。但如果把它当作是“贡献世界”的文化软实力的话语依托,未免显得格局太小。近年来,柯华庆提出的“现代社会主义”,就是试图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达。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这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似乎不太适合作为学术讨论的范畴。
孙国东: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不说资本主义而是祭出了“自由主义”这面旗帜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必要拿出更具有学术争辩空间的话语符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时考虑到中国的“路径依赖”,“现代马克思主义”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钟励:如果沿着“转型法哲学”的思路写一本终极性著作,它应该怎样定位?
孙国东:“转型法哲学”,试图围绕转型中国“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法律秩序,进行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它其实预设了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任务:一是遵循现代化(现代转型)基本逻辑的学理分析和理论建构;二是基于对现代化(现代转型)本身的反思立场的理论建构。显然,本书所做的主要是第一个层面的研究工作,也就是对中国“接榫、吸纳、转化”现代文明秩序(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进行了部分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并没有涉及如何“超越”现代文明秩序(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理论建构。在我看来,关于“转型法哲学”的终极性著作,恰恰应当主要着力于后者,这样才可能在米德意义上“不断扩大的共同体”赢得更大范围的普适性和影响力。
钟励: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自身的演化逻辑来看这个问题?
孙国东:是的。我在本书中曾把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现在面临的挑战,与佛教曾经带给我们的文明挑战进行类比。两者的性质都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如何“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异质的文明体系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佛教和以西方文明为源头的现代文明是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面临的最大两个外部文明挑战,而后者带给我们的挑战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胜于佛教带给我们的挑战,因为它不仅涉及生活世界的个性(自我认同和信仰)和文化(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和内容)领域的根本变化,还涉及社会领域,以及以社会为背景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型。
不仅如此,为了回应中华文明的“自我转圜”问题,在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又给我们带来了我前面提到的中华文明的“自我整合”问题,即如何整合社会主义新传统、华夏文明、主流的现代性价值及中华文明内部的其他非华夏文明要素(如藏传佛教、中国伊斯兰文化等)。
这里需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主流的文明模式(自由主义),整体上都属于现代文明秩序中的不同文化模式:前者大体上是非主流的模式,即以落实现代性价值中的平等(以及民主)为根本旨归的现代文化模式;后者以落实自由的优先性为旨趣的主流现代文化模式。从思想谱系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属于现代社会政治思潮中的左翼,而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化的自由主义总体上其实属于中间派,既有发展为左翼的空间(如罗尔斯式的左翼自由主义或“新政”自由主义),也有发展为右翼的可能(如诺奇克式的自由至上主义和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属于右翼)。但是,它们总体上都是从属于现代性的社会政治思潮。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自我整合”,其实要比我们想象得要困难得多,不但要完成现代性不同思潮间的整合,而且还要完成中国自身的不同古典性传统之间的整合,更要把两者整合成一个相互兼容的思想体系、文化体系乃至文明体系。继续拿佛教来类比的话,我们知道,中华文明花了超过1100年时间才完成“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佛教的历史任务;而从利玛窦来华(1582年进入澳门)算起,我们与西方文明的遭遇迄今刚刚400余年。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非常类似于唐朝时期。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以及邓正来先生、刘小枫先生、刘东先生等所做的移译西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玄奘当年所做的迻译佛经工作。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角度或者采取更具学术性的方式(如前些年盛行的“中国模式论”)对西方主流文化模式的批判,还是从儒家或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模式、马克思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都类似于韩愈当年所做的“辟佛”工作——只不过,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现代性的“双头身”,而且这“双头”本身还是相互拉扯的。显然,这种类型的批判和反思,都只具有局部性和阶段性的历史意义。要想真正“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能够提供替代性的文明秩序机理——就像朱熹的理学所做的思想创造工作一样。或许,要完成这样的工作,我们只能像《中庸》所说的,“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或者如孟子所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我当然不是期待所谓的“圣王”,而是寄希望于可挑战思想格局的“思想巨人”。
钟励:很多论者(特别是古典自由主义或“儒家自由主义”论者)无视马克思主义这个传统,甚至把与之相适应的政体结构视为一种过渡性的政体形态;但他们其实对中国作为“跨体系社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共同体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组织机理,缺乏深刻的体认。
孙国东:的确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制度化,固然有政治博弈和军事决战等历史偶然性因素,但其背后也有着充分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依据——杜赞奇关于国民政府时期政权“内卷化”的分析,已经部分揭示了这一点。单一的儒家或者自由主义模式,如果可以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建构,一百年前它们就有着比现在大得多的施展空间和舞台,但它们为什么最终都失败了呢?就儒家来说,想想康有为为什么在张勋复辟前后会放弃衍圣公,转而支持以皇帝为政治认同的核心建构现代中国,就不难明白;就自由主义来说,想想孙中山为什么在1914年创建中华革命党乃至后来“以俄为师”、开展“国民大革命”,也不难知晓。
单一的儒家方案和自由主义方案的失败,绝不能简单归结为在政治博弈和军事较量上的偶然失败,它们有着更深的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逻辑。如果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思考起点,其根源在于它们都无法填补“后帝制”时代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组织化真空”,即在国家与社会的再组织化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和主权独立。如果说,儒家的问题在于它在“后帝制”的民主共和时代缺乏兼具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内在组织资源,同时完成国家与社会的再组织化,那么自由主义的问题则在于其个人本位的国家和社会组织方式,在当时无法确保“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现代条件下的政治统一。从另一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制度化,则根源于20世纪出现的列宁主义建党模式,有效地填补了“后帝制—后儒家”时代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组织化真空”,也就是以共产党以兼具政治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全涉型”组织结构,实现了国家与社会跨民族、跨阶层、跨地区和跨行业的再组织化,从而及时且有效地填补了传统中国由皇权专断(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士大夫理政或辅政、科举取士、宗族制度、士绅制度、“耕读传家”制度等行政整合和文化整合机制消失后留下的“组织化真空”。当然,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由此给我们带来了党治国家政治架构,也面临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课题,也就是如何使其转型为受民主、法治监控并促进社会正义的永续国家模式。
我讲这些背景,当然不是说我所谓的“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就可以完成朱熹那样的大思想家可以完成的工作。毫无疑问,这种级别的大思想家,既是中华文明的福音,也是人类的福音,不是我等庸常之辈可以望其项背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以此为历史视野、问题意识和学术担当,做一些前提性、奠基性的工作,也就是为这种思想家最终建构“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的思想体系,做一些思想和学术的铺垫工作。
薛玖:但是,这么宏大的思想创造工作与法学或法哲学有什么关系呢?它难道不是中国哲学、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更应该考虑的问题吗?
孙国东:这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现代文明秩序及其对中国的挑战。我在前面提到过,现代社会政治秩序是以法律秩序为基础形成的;相应地,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它在根本上其实是一种世界观的转型,也就是我所谓的从“天理世界观”转向“法理世界观”。如果同意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及相应的“法理世界观”的形成,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核心课题,那么可以“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的思想体系,应当主要是一种法哲学的思想体系——至少,法哲学应是其核心内容。
薛玖:如果这么看,你设想的“转型法哲学”的终极著作应当是什么样的?你能举出类似的著作为例吗?
孙国东:我觉得我们似乎可以拿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作为类比。在我看来,这两本书建构了当代西方捍卫和改良现代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的主要想象空间。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而不是《正义论》),以“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有效地回应了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理性的多元论事实”)对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挑战,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则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拓展了西方的民主合法化空间。如果说,罗尔斯为捍卫和改良西方现代宪政模式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那么哈贝马斯为捍卫和改良西方现代民主模式做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两人合在一起,为捍卫和改良西方宪政民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本为中国现代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建构服务的著作,也应该具有这样的担当和抱负。与具体制度层面的设计相比,它应该更关心的是关涉罗尔斯意义上的“宪法根本”(constitutionalessentials)和“基本正义事项”(matters of basicjustice)的制度原理。与学者相比,政治家显然更擅长设计制度。而且,在我看来,很多制度之所以难以建立或建立起来后难以施行,主要与这种制度背后所承诺的政治理想或价值理想,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认同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因此,从规范性层面上建构适合转型中国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的规范性体系,是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的职责所在。
薛玖:你刚才只是说到了它的基本定位,我想知道的是,如果真像你说得那样,为什么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呢?它的难度究竟在哪里?
孙国东:除了个人的天赋和资质方面的限制以外,主要与诸多前提性工作有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诸多需要开展介入性分析的前提性工作面临着论说空间十分有限的局面;这些前提性的工作,由于远未形成集体共识,很多时候需要做一些澄清乃至宣扬工作;同时,很少有人在与“转型法哲学”相同或类似的思想方向思考一些前提性的问题,因此,必须首先完成对一些前提性工作的研究;等等。借用我的同事陈润华兄的一个说法,要完成这样的一本书,必须首先完成一系列“清理地基”的工作,而且这种工作的展开还面临着诸多客观限制。
薛玖:天赋的问题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吧。自然天赋决定了一个学者可以达到的学术高度,但后天的努力方向及努力程度则决定着一个学者可以达到的最低水平。只要你沿着自我期许的方向努力,应该是可以无限接近地完成这样的任务的。
孙国东:其实,更难的其实还不是这些,而是与“普适性”有关的问题:如何把这样一种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建构提升为一种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的学理言说?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是更核心的难题,是因为只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内在批判”路径或者罗尔斯意义上“现实的乌托邦”式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建构,才会是兼具“可欲性”和“可行性”的学理建构。如果我们建构的只是从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寻找灵感,但与现实不涉的“乌托邦”,比如近年来关于“天下观”“天下体系”的论说,正如葛兆光批评的,它只能纯然是一种“乌托邦想象”,将极大地弱化对现实的范导作用。在本书中,我曾把这种方式建构的中国文化认同叫做“典籍性的文化认同”。这种理论建构方式,显然是要予以否定的。我们固然不必臣服于实践,但应当大致同实践的走向——至少是它的可能走向——保持一致,从而确保规范性空间的可行性。如何把握转型中国的实践走向,并建构基于中国情境的“现实的乌托邦”,同时还要确保它具备跨文化的普适性?这的确是非常大的难题。
钟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要比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完成那样的著作要困难得多。他们所依托的是过去五百年内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一套价值体系。在他们之前,从霍布斯到洛克,从孟德斯鸠到密尔,从卢梭到康德,从联邦党人到托克维尔,无数先贤尽管各有歧异,但都为这套价值体系的确立贡献了智慧。
孙国东:尽管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建构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但在我看来,只要中国不能产生一大批可以代表现代中国价值观的政治哲学或法哲学著作,中华文明“贡献世界”就只能停留在我们的“天朝迷梦”中。显然,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所有其他中国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从业者,目前所做的工作都是远远不够的。
钟励: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无法完成这样的著作了,但至少可以做一些你所说的“清理地基”的工作。在你看来,有哪些前提性的学术工作可以做?
孙国东:本书其实已经做了一些“清理地基”的工作,比如我对“邓正来问题”的进一步阐发、对转型中国法治观的建构、对法治中国所面临的两大“结构化情境”(法治社会层面的“差序格局”、法治国家层面的党治国家)的积极回应、对“底线正义”的探究、对“关联性正义”的建构、对文化正义(文化认同建构法则)的探讨等等,都属于这种性质的工作。接下来,至少还有三个方面“清理地基”的专题工作要做。
一是对民主、宪政的“学理格义”,特别是对中国情境的“人民共和”进行介入性的学理分析乃至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尽管这一论题目前的论说空间十分有限,但它既是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所在,也具有很大的理论创新空间。在这方面,把我在前面反复提到的“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观”区分开来,尤显必要。这就需要我们把民主立宪政体所承诺的现代政治文明精神,同它在西方国家的制度化形式(制度和实践模式)剥离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构和完善既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也符合转型中国实践约束条件的现代民主立宪政体。“人民共和”作为中国国名的核心内容,既表征着中国以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独特政治模式,其所包含的“共和”精神也是可同时与政治现代性的要求、中国古典传统相接榫的政治理念。换句话说,它可能成为在中国情境中“打通中西马”的一个政治哲学突破口。如何结合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与其实践约束条件,对“人民共和”进行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是中国情境中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是关于中国文化之现代转型的研究,特别是我前面提到的以“从天理世界观到法理世界观”这个分析框架,来把握晚清(乃至宋明)以来中国人在世界观上的历史转型。此前,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史领域进行的。但是,这种局限于学科视野的研究,一般都是对思想观点的罗列或堆积,既缺乏社会史维度的考察,也没能真正清理出其中的历史逻辑,并不足以把握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性质。在本书中,我已经提出了“从天理世界观到法理世界观”这个分析框架,并做了初步的分析。但仍需做更为系统的论证,其难题在于如何把握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与中国现代法律/政治秩序的建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果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和论证“从天理世界观到法理世界观”在晚清(乃至宋明)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的逻辑展开等等。这个专题涉及前面提到的中华文明的“自我转圜”问题,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中国现代转型的“思想母体”有直接的学术意义。
三是关于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清理和理论建构。对此,我们需要把20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潮,放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各个历史节点中进行把握和阐释,同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哲学、中国哲学等思想资源,对它的未来形态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在这方面研究的难度比较大。其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社会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而这一难题的关键又在根本上指向了对列宁主义要素、马克思主义要素与传统文明遗产等在现代条件下的重构。除了理论上的这一难题,我们还面临着实践中的难题:一方面是如何在历史阐释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建构为一种首先对当下中国人具有价值吸引力的规范体系,本身面临着挑战;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圭臬的国家,但中国学者主要是把它当作封闭的意识形态进行把握和阐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开放性。这个专题的研究,直接涉及前面提到的中华文明内部的“自我整合”问题,其实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化认同的关键环节。
前两个专题,大体属于“接榫、吸纳和转化”现代文明秩序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则为我们“超越”现代文明秩序提供了想象空间。对这些问题,我个人接下来应该都会展开探索和研究,也期待其他有兴趣的学人一道来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
我把“转型法哲学”的终极目标及“清理地基”的工作说出来,是想提请有着类似关怀或兴趣的读者与我一同努力。我始终相信:无论是学理探究,还是思想创造,都需要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充分发扬“沟通理性”。这种“沟通理性”不仅会极大扩展学术研究的视野,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评判学术研究“真理性”的前提——如果我们认同皮尔斯—哈贝马斯的意义上的“共识真理论”。因此,我个人特别期待和欢迎有类似关怀或兴趣的读者,对拙著及未来研究计划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如果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