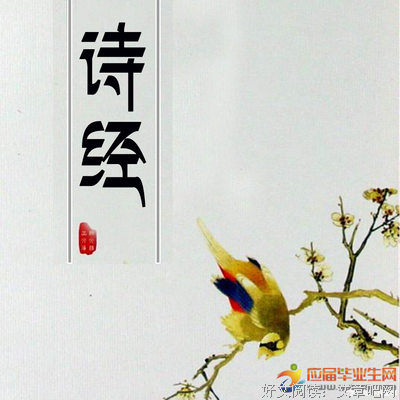诗经讲评之风人深致读后感精选
《诗经讲评之风人深致》是一本由苏缨著作,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元,页数:1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经讲评之风人深致》精选点评:
●采采卷耳,不盈顷框。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能把诗经讲得这么深,又这么好看,不容易~已经反复看了好几遍了,每一遍都能读出新内容来,力荐!
●难道熊逸就不准备继续写下去了?
●不枯燥的考据派 可以一读已解决多年误区
●从诗经诠释看历史和文化。
●目前读过最好的一本《诗》评析 基于训诂 评析各家的解读 有破有立 所立也比较合我的味 《诗》成的年代已远 难说后世解析几分是合原意几分是合今人心
●人类学真是渗透到了方方面面……
●今天早上起来读完最后一小节的。本来是打算读读诗经名篇的,可是太古远读不懂便想找一本有一定讲解的。这本也很不错,不过于我而言太过于追究考据,也能了解一下各家之言。
●苏缨的解读建立在熟谙《诗经》成书年代的社会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等知识基础上,所以,这本书里对汉儒的道德教化联想和现代人的浪漫式解释的批判,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诗经》年代久远,汉字的歧义性又较大,两千年来《诗经》的学术研究,都绕不开基本的字义和语义的探究,也是一种悲剧。
●《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苏缨以其全面的考据和易理解的语言解释了诗经的深奥。读诗经如涉水,是否能修得船渡要看修为。它是值得研读的一本书。
《诗经讲评之风人深致》读后感(一):诗经-古代的政治书
终于啊,终于看见一本有参考文献的中文书,太不容易了。
学到不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发现了诗经不是虾米情情爱爱不是民间质朴生活,而根本就是本政治书!经嘛,就是政治学范畴的。305篇是孔子亲手修订的,那时候考试解《诗经》都是有标准答案的!
当然啦,不同时代看问题不一样啦,小猫得出的结论:和谐是自古就有的,不关gcd什么事啊……
《诗经讲评之风人深致》读后感(二):原来我不曾懂过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样的诗句我们再熟稔不过,自然我们也自以为深知其意。
书的开篇说,胡适《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中“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颇有故弄玄虚、断章取义之嫌。但看过关雎、葛覃,我失了继续读下去的勇气,这样的诗经为何在我自幼至今的读书生涯未曾见过?曾经熟读在口的诗句变得面目全非,俨然没有丝毫的浪漫情怀,原来篇篇在言道。
诗经,原来我不曾懂过。
《诗经讲评之风人深致》读后感(三):不变的是诗经,变的是我们
苏缨的这本《诗经》讲评,在天涯上读过一些,原先以为会由出版《纳兰词典评》的广西师范出版,不过后来貌似黄了。不过这次改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装帧质量倒也保持了应有水准,应该是值得庆幸的。
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诗词解读汗牛充栋,良莠不齐。不过在其中,苏缨的作品我一向比较喜欢。其解说有情感又不似小女生般滥情,有功底又不似老先生般酸腐,其中的“度”把握比较到位。苏缨曾自承解说风格比起那些“读起来觉得美就好”的朦胧派,更偏向于要把诗词的写作背景与人物关系弄清楚再来探究其中的意味。这一点在其解读纳兰词和唐诗的几本作品中就已经显露无疑,此书中更是如此。
需知《诗经》可不是普通的诗词歌赋,它可是《六经》这一,相传孔子亲自编撰,在历朝历代都被奉为经典。针对其的解读也是古往今来,不绝于道。然而,《诗经》也是争议颇大的一部诗歌集,看似浅显的诗句下有着无数的阐释和注解,却又彼此争论不休,暧昧不清。胡适甚至说“诗经有一半至今读不懂”。对此,作者试图在本书中给出自己的一些解读。
苏缨的解读,一大特点就是旁征博引。解读诗经,不仅从诗经本身入手,更是引用了古今中外一堆注释。从《毛诗》、训诂学到胡适、闻一多,再到庞德,加上涂尔干、奥卡姆等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解读,可谓丰富。而作者并没有犯为注解而注解的错误,而是辩证地看待这些注解。她指出解读诗经的几个主要错误就是过度阐释、以今度古,以及为了自己的目的去阐释。这样的解读方法,不但会把本来简单的事情越弄越复杂,还是对诗中原有意义的扭曲。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古代把所有诗经内容都往“后妃之德”上凑,还是解放后将其全部理解为“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都是有失偏颇的。要真正理解一首诗,就要首先还原其时代背景和写作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合理的揣测和推断。这一观点,倒是颇似新文化史及心灵史的看法,让我想起之前看的《屠猫记》。
只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今人真的能够揣摩清楚吗?虽然中国有着不间断的文字和文化传承,是为一大优势,但文字的意义在传承之中却无时无刻不发生着流变。这一点,作者其实比谁都清楚吧。更何况,人们从来都是更多按照自己意愿来解读作品,正如《诗经》的官学地位催生了“后妃之德”的正统解释,而阶级解读的盛行也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一样,如今安意如们对诗经的解读回归情感系,不也是由于“市场导向”?人们想要的,是否真的是诗的原意?还是自己所希望的意思?《诗经》没有变,那么到底是什么变了呢?看完全书,其实反而有了更多的迷思……
不过,能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仍旧能够静下心来仔细解读诗经,努力还其本来面目。这本身何尝不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钦佩的举动呢?
《诗经讲评之风人深致》读后感(四):男女相思之外的政治情怀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 国风▪周南 关雎》
这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句子。这就是《诗经》的开篇。
如果中国的文学史是条长河,那么站在我们现在的位置,也许《诗经》是我们能够眺望到的最久远的一颗明珠。具体的创作成文时间已不可考,但大体的说法是自西周至春秋横跨了600余年,也就是说,距今已2500至3000年有余。
谢谢苏缨,让我与《诗经》再次相遇。早前我曾读过她与毛晓雯合著的几本书,像是《诗的时光书》(赏西洋诗歌)、《卿须怜我我怜卿》(赏红楼梦诗词)、《唐诗的唯美主义》,对于像我这样爱诗却不懂诗的读者,苏缨无疑是个极好的向导,她深厚的文史造诣、别致的美学观感,让“读诗”这件小小的美事,成为一次次饶有滋味的按图索骥。
朱光潜有句话,我深深的喜欢:“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我想,“读诗”之所以有趣味,也正是这个道理。诗之言有尽,遣词用韵需要独具匠心;诗之言有尽,抒情言志需要配上想象与画面;诗之意无穷,微言大义,而解诗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那句“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诗之意无穷,诗能起赋修性,亦能安民振邦,不然何来孔老夫子的一句慨叹 “温柔敦厚,诗教也”。
文学是美的,那么作为中国文学之始的《诗经》,所饱含的美当是最质朴纯稚。少时初读诗三百,记得“式微式微,胡不归”那般劳役的怨苦,记得“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那般被压迫者的呐喊,也记得“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那般恋歌的悠远。我至今仍然相信,那些歌谣的初创,只是源于抒发的必须,就像我们卸下一天的疲倦,就着灵感在淋浴头下会哼出的小曲。
然而解读《诗经》,就绝非如此轻松了。翻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诗经与楚辞》该章结尾的“参考书目”,出现了《毛诗正义》(汉毛亨)、《诗集传》(宋朱熹)、《诗经通论》(清姚际恒)等九部解《诗》之作,其中还包含郑老先生自己的《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书目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有兴趣的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346424/)。古往今来的百家之言,在《诗经》音韵、训诂、名物、校勘等诸多方面的孜孜探寻,却留下了更大的歧义空间。精心抄选这诗三百的孔老夫子,一定没料到,后人可以将此书解读得如此千差万别,也一定没料到,自己最初寄托其间的“思无邪”的理想,竟被后朝的儒家后人发扬做了统治阶级的教化文本。
仍旧要谢谢苏缨。若不是通过这本书,接触了各类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诗》解,和文人雅士在疑古考据上的歧见,我不会理解这本书古典政治哲学教材的地位,亦不会感慨前人在诗教上的煞费苦心,更不会得空静下心来反观思索诗的本意、诗的本质。
初看《关雎》一首,似是借“关关雎鸠”、“参差荇菜”的意像,婉转表达“君子”对“窈窕淑女”的思慕之情,毕竟借采绿来吟咏相思,已是一种习用套语。然“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似出自庙堂,抑或是婚礼才有的场面,因而《关雎》为贺婚诗的说法也颇为流行,只是这难免有些以今度古了,婚礼鸣钟奏乐的习俗在周代还是不曾有的,细想来似乎只是男求女的手段罢了。汉初,齐、鲁、韩三家官学曾解释《关雎》是暗讽周康王的荒淫无道,而因着董仲舒的影响和重建纲常的需要,至汉后期,《毛诗》又在之中释出个“后妃之德”。自“雎鸠”这种动物“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的特性,《毛诗》解为“挚而有别”,这个“别”正是儒家礼制思想“克己复礼”的精髓。由此想来,作为《诗》之首,《关雎》的训诂和义理可谓深远,无怪乎《韩诗外传》引孔子与子夏之言,感慨“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当质朴纯稚的原初之美,遭遇到如此沉重的政治包袱,实在令人感叹“焚琴煮鹤”。然而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苏缨写道“解诗有时候很像圆谎,既然发现了一个纰漏,就尽可能找些理由把它圆上”,《诗经》毕竟做了千余年的政治哲学教材,它能始终不因改朝换代而为人所厌弃,要归功于历代文人墨客在“自圆其说”这件事上的不遗余力。试问,这何尝不需要一种过人的才华,又何尝不是一份良苦用心呢。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 “风”可解为《国风》,王国维也许是用“深致”二字道出了《蒹葭》的深情含蓄、婉曲流长。苏缨择“风人深致”作书名,精选了《关雎》、《卷耳》、《桃夭》等十一首“国风”小诗,引经据典地慢慢讲说,继续延续对古典文学之美和历史底蕴的探寻。
“于嗟”,《蒹葭》之外的“国风”里,“深致”仍是俯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