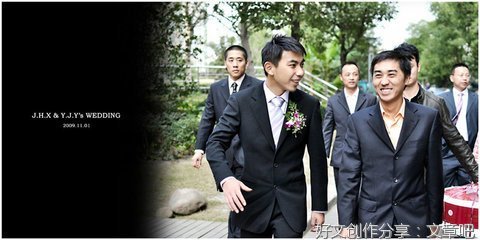早春读后感1000字
《早春》是一本由[英国]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页数:26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早春》读后感(一):早春:生活中是一种循环
佩内洛普. 菲茨杰拉德年近六十才开始文学创作,《无辜》、《早春》、《天使之门》、《蓝花》属于她晚期的作品。
《早春》被誉为佩内洛普. 菲茨杰拉德写给俄罗斯的一封情书。在这部以革命前的俄国为背景的小说中,你会惊异于她对于1913年莫斯科这座城市的了解,笔下满是生动且惊人的细节。
“亲爱的、邋遢的莫斯科母亲,一百六十座教堂的钟声让她迷茫,她不偏不倚地庇护着工厂、妓院和金色穹顶….不断向外延伸,带着一股霉味….”
小说从这里展开,以一位妻子突然的出走为开端。印刷厂老板弗兰克的妻子内莉突然离开了家,留下丈夫茫然不知所措。有点讽刺的是,她本是带着三个孩子走的,结果又把他们集体留在了火车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这像是一个谜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贯穿小说的始终。内莉像一个影子,或者幽灵,她究竟经历了什么,是有什么精神变化促使她做出这一举动?
有关内莉的出走,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弗兰克。相比即将到来的大变革,弗兰克的生活提前陷入混乱。接下来,以弗兰克.里德的视角展开,他身边有托尔斯泰的虔诚信徒塞尔温、豢养熊崽的俄国商人库尔金、携带枪支私自潜入印厂的学生沃洛佳,让他产生了冲动的家庭教师丽莎,还有三个看起来比他要淡定的多的孩子…..
佩内洛普对于人物的描写细致而微妙,冷静沉着的文风中又不失幽默与风趣。就像看似平静的湖水,以为波澜不惊,实际上荡漾着各种活泼的小水花。
第一个引人入胜的小高潮是熊崽。孩子们期待一只会跳舞的熊,这样可以显摆一下。而来到的这只小熊崽却“糊里糊涂,涉世未深,明显还需要一段时日的呵护。它必须动动脑筋,才能在地上笔直地行走,而且没法次次成功。”
“它不会跳舞,什么都不会,它就是个笨蛋。”他们往它身上泼着冷水。
“看门人谢尔盖冲了进来,他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毫不犹豫地抄起一把铁铲,揭开白色的陶瓷火炉的盖子,铲出一堆热得发红的木炭,撒到了熊崽身上。桌布早已被烈酒浸湿,火焰顿时腾空而起。熊崽尖叫起来,叫声像小孩一样。
这显然演变成为集体虐待熊的恐怖故事。在这里,每个描写都精确且细节化,足见作者敏锐的观察力。每个人的语言动作都设计的非常精彩,在短短的场景中让人物跃然纸上。熊崽惟妙惟肖,憨憨的却试图反抗,让人从心底涌现出对它的遭遇的同情与怜爱。
而多莉,弗兰克的其中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像个冷眼旁观者冷冷地说:“它渴了。”看了一会熊之后,她和本没有跟其他人站在一起,而是一起站到了窗帘后面。
其实早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弗兰克就发现他的孩子们对于母亲的出走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感缺失,至少没有像他一样焦虑。
文中,弗兰克有三个孩子。佩内洛普本人也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任性的丈夫。不乏有人疑惑佩内洛普为何快到六十岁才写作?
她出身名门、毕业于牛津大学,曾经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然而命途多舛,结婚之后开始陷入困境。在连生了三个孩子之后,她在戏剧和文法学校教过书,在书店工作过,也曾住在泰晤士河的老旧驳船上。她的丈夫从北非战场回来后,开始酗酒,身上的重担压在了佩内洛普身上。所以这就不难理解她为何这么晚开始写作,因为首先是要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而正是如此,经历过漫长的艰辛岁月,生活的洗礼,沉寂的岁月,她才能够以更加深厚的沉淀去写出她所想要的故事。这么一想,不难理解她那句:写作可以在生命的任何时刻开始。
她笔下的孩子有种超年龄感的成熟,常常用漫不经心的感觉说出一些挺有深意的话。在后面无论是多莉、本还是安努什卡与弗兰克或者查理舅舅相处形式,他们都像一个小大人一样。
查理临走前要选一些礼物,他和多莉来到了一个巨大集市的顶层。多莉兴高采烈,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拿走他的清单,拽着他快速往前走。“这边是食品杂货区。不是进口货,都是些俄国本土货。红酒焖鲟鱼,罐头,罐装麋鹿肉….现在,我们快走到金银珠宝和宗教物品区了。”而查理心虚地表示,我可买不起这些东西。多莉思路清晰明确,表现出优越感,感觉她对这一切都熟悉极了。
“他们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他喜欢在晚上自由地走在那些不幸的人中间。”这不像的孩子说的话。但作者却就如此写道。你会由此琢磨,或许孩子的眼睛才是人间清醒。
弗兰克在妻子离开后的这段时间,塞尔温“好心地”给孩子找了一位家庭教师,丽莎。而弗兰克随后对她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而最终塞尔温却自己说出他才是弗兰克妻子内莉相约一起离开的人,只不过他爽约了。这个循环可真是有趣。
最后,内莉回来了。
这是一个有点可笑的,暧昧的结尾。但正是佩内洛普迷人之处。没有什么特别圆满的结尾,意想不到随时可见,有时候有点愤懑却又能够忍受。这些却正是生活的瞬间。
小说名叫《早春》,文中散落着许多美妙的风景描写。嫩芽细枝,温润的春雨,明亮的绿色,橄榄绿,亮银色。让人仿佛能够闻到春的气息。春寒料峭,而又很快将春意盎然。
《早春》读后感(二):那个不怎么关心我们做些什么的世界,将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其壮丽的一面
文/安德鲁·米勒 译/黄建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书桌上方都钉着一张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照片,照片是我从某份报纸的书评栏目里剪下来的,看起来总有些发皱、易碎。这张照片很常见,是张半身像,照片里,菲茨杰拉德望向镜头外,浅浅地笑着,略显疲惫。想必(或许只是我自己设想)摄影师曾鼓励她用手托住脑袋一侧,且认为这一姿势会让这类照片更活泼。我猜,照片里的她已近古稀之年,但我也拿不准。她穿着一件条纹衬衫,衬衫一直扣到脖颈处,套一件黑色羊毛开衫,开衫的袖子很蓬松;能瞥见衬衫里面穿着什么很暖和的衣服,仿佛照片是某个大冷天在某栋冰冷的房子里拍摄的。她喜欢别人拍她吗?也许不喜欢;我认识的大多数作家都不喜欢。可人们能感受到张力带来的某种东西,创造这种张力的,是冷静审视的目光、似笑非笑的表情、似闭非闭的嘴唇。那张嘴准备说话,或许还想放声大笑。
当然,从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的照片里读出些什么来实乃愚行,不过我的确与她有一面之缘,那是一九九五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当时她来到巴斯的水石书店[1],朗读了她新出版的(结果也是她最后一部)小说《蓝花》。我那时三十出头,第一部小说写了一大半。除了那位对葡萄酒严加看管的大胡子书商以外,我是活动现场唯一的男性。我坐在靠后一排的最外边。起初,我误以为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是某位听众。接下来,她突然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面向我们;她微笑着,说话声虽小,但很清晰,似乎对我们很感兴趣。她问道,在座的听众有没有人在写书。我不知道她是否当真期待有人会举起手来,可是,有那么几秒钟,我意识到她的目光正快速扫过我们;向我走来时,她顿了片刻——几乎可以肯定,顿住是因为我是男性,且相对年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原因——可我觉得受到了关注,并且立即将那一瞬间视为我具备某种秘密的作家气质的证据,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有这种气质,可她知道。
虽然我很感谢她,也很高兴自己参加了活动,但当天晚上,我并没有抱着一大堆她的书回家——还都是签过名的——然后埋头看书。一年多后,我才开始认真读她的作品,并且感到一阵激动,读书一辈子,这种时刻实在难得。我一开始读的是晚期的小说——《无辜》《早春》《天使之门》《蓝花》——实际上,这些作品依然是我的最爱。我想不通自己之前为何没能好好了解她,又为何会有眼不识泰山。为何并非人人都在谈论她?为何在巴斯的那场朗读会未能出现人挤人的盛况?
我手里这版《早春》——如今,这个版本看起来就像我所珍爱的其他书籍一样,仿佛在洗衣机的滚筒里走了一遭——的封底上有一行字,来自简·莫里斯的一篇评论,开门见山道:“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啊,是怎么回事呢?这部小说与“晚期四部曲”的其他小说一样,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品质,一种难以捉摸的秉性,一种事情在光天化日下另有隐情的感觉。情节不足为奇,用一两句话便可概括;情节并不重要(我喜欢的书里,情节基本上都不重要)。事情发生,人们来了又去,枪响(实际上,只响了一次);生活悄然逝去,充满谜团,恍若人们在河堤上看到的景致,可除此以外,到底还发生了些什么,书里还讲了些什么,我真说不上来。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的俄国;任何读者心中可能都会有个疑问,那就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的人,居然对一九一三年的莫斯科的日常琐碎了解得如此透彻,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知其然还不够,还得知其所以然——她是什么时候了解到的,又是从哪里了解到的。这当然要归功于研究——还能归功于什么呢?巫术吗?——可是,研究得如此透彻,如此深入,以至于故事跃然纸上,行云流水,天衣无缝。我们从未听见在舞台上拖动布景的噪音,也不曾对她有丝毫怀疑。
本书开头几页很是热闹,小说的主人公弗兰克·里德刚刚得知妻子离开了自己,彼时正心不在焉地凝视着自家的院子,“院里堆着冬天用的柴火,如今还剩最后一捆。邻居家的油灯亮着,可以透过后院的篱笆看见零星的灯光。弗兰克先前同莫斯科电力公司达成协议,在家中安装了二十五瓦的照明设备”。
只是瞥了一眼,相当于一连串动作中停顿了片刻,却让读者能想象与感知到一个完整的世界,使得薄薄一册书———不到两百五十页———读起来像一本大部头,类似那些菲茨杰拉德一定非常熟悉的俄国经典小说。打出这几行字时,我想到,她的那些句子实在是太实事求是了。克制,简洁,毫不含糊。菲茨杰拉德并不标新立异,文风也不浮夸。进来,说出口,出去。别站在那里要求别人爱自己。这种写作方式非常适合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本以为是普通玻璃杯里装着的白开水(看似如此),然后你就开始头晕目眩了。
此时此刻,有必要说一句也许本该早点儿说的话:多数时候,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多数时候,《早春》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这场莫斯科狂欢围绕着弗兰克·里德这个人展开。他不是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虽然他成长于莫斯科,说当地的语言,对当地人深表同情,非常热爱他们,可他举手投足间又显出一种爱德华时代的正派绅士派头来,他聪明却略显狭隘,一心想做正确的事,却又经常拿不准该做些什么。你若乐意,可以把本书看作一部与马克思兄弟[2]出演的电影(是演《鸭羹》的马克思,而不是写《资本论》的马克思)截然相反的喜剧。在电影中,三个疯子在一个看似有序的世界中制造了一出喜气洋洋的闹剧;在书中,我们却看到一个看似有序的人身陷闹剧之中,最终无力控制局面。可是,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一旦出现喜剧,几乎总有迹象表明,会有反转发生。小说里有一个片段写得妙不可言:弗兰克想找人帮他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孩子们总有能力让成年人感到不安,而且一直没有明显的情感诉求),他便求助于自己的朋友兼生意伙伴阿尔卡季·库里亚金。“阿尔卡季有孩子,至于有几个,弗兰克说不上来,似乎总有些之前他没见过的孩子———或许是侄子侄女,又或许是流浪儿,甚至是人质———来了又走。”
弗兰克不太走运,孩子们头一次去库里亚金家的时候,某个与库里亚金有生意往来的人刚好把一只熊崽当作礼物送到了他们家。熊崽到来后,库里亚金的孩子们要么是想讨好客人,要么纯粹出于淘气,企图让那只动物跳起舞来,可它就是不跳。受了挫的他们决定玩个新游戏。熊被喂了好几茶托的伏特加,很快便烂醉如泥:
这个场景值得注意的地方有很多——它编排得很巧妙(至少得操控五个孩子),还悄悄地将一场闹剧变成了一个恐怖故事——可我们渴望看一看菲茨杰拉德接下来会带我们去哪里,便读得飞快;只有等我们回过头来,读第二遍的时候,我们才会把玩起细节来,比方说,熊崽的耳朵露出了“内侧的苍白皮肤”。先前,她在同一场景中写道,那只熊的毛“长得到处都是,却没长在整根脊椎上——于是,秃掉的部分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见的线……”这其实已经无关“研究”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密切关注世间万物的人,一个不错过任何细节的人。
《早春》是本很有条理的书,我猜菲茨杰拉德也是个很有条理的作家,或者说,是个通过不停地改写,给人留下这种印象的作家。她曾说——我们应该始终非常谨慎地对待作家们的创作谈——开始写小说之前,她必须知道第一段的内容,最后一段的内容,书名叫什么,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就这本书来说,我忍不住想要相信她说的话。第一段颇具戏剧性,又很直白,让情节变得灵动起来;而到了最后一段,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却并非如此——那一刻,人们似乎看到了生活重回正轨的曙光,可事实上,结果很可能与此截然相反。至于书名,它别有一番诗意,而本书的结尾也迎来了春天,这充满讽刺意味——讽刺的,当然远不止居住在利普卡街二十二号的那些人的生活。
“生活,”那位马车夫在小说开头对弗兰克·里德说道,“是会修正自己的。”这句话既美丽,又神秘(但愿车夫们真能说出这种话来),或可作为本书的卷首引语。对于弗兰克、他那些脑瓜灵活的孩子们、讨人喜欢却并非不会伤害别人的塞尔温·克兰、莫斯科、母亲般的俄国来说,生活的确会修正自己。新的困惑将取代旧的,男男女女们将继续误解自己;在此过程中,那个不怎么关心我们做些什么的世界,将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其壮丽的一面。
安德鲁·米勒[3]
2013年
[1]一家英国连锁书店,其第一家书店于1982年开业。在英国,该书店随处可见,除了各大学校和伦敦重要的街区,在其他城市也均设有分店。
[2] 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也译“马克斯兄弟”),知名美国喜剧演员。他们五人是亲生兄弟,常出演歌舞杂耍、舞台剧、电视、电影。后文提到的《鸭羹》(Duck Soup),是一部由马克思兄弟主演的黑白喜剧电影,上映于1933年。
[3] 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1960— ),英国小说家。1995年于兰开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1997年出版处女作《无极之痛》(Ingenious Pain, 又译《从月亮来的男孩》),为他赢得多项大奖,其中包括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2001年出版的《氧气》(Oxygen)曾入围布克奖短名单。
《早春》读后感(三):早春中的帝国、诗歌与……印刷机
文/李公明 转自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当代英国著名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 ,1916-2000)出生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就读于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曾就职于BBC、学校、书店,要担负家庭的重任。当她终于在年近六十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生活阅历、信念和对历史以及异国政治的探索兴趣都不断融汇到她的小说中。 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早春》(原书名The Beginning of Spring,1988;黄建树 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4月)讲述的是英国侨民、莫斯科的一家印刷厂老板弗兰克的故事:1913年3月弗兰克的妻子内莉突然抛家弃子出走,原因不明;弗兰克心情烦乱但仍然要保持生活的秩序,为了照顾孩子而聘请的家庭女教师丽莎走进他的生活,他的会计塞尔温是虔诚的托尔斯泰主义信徒,携枪潜入印刷厂的大学生沃洛佳引来秘密警察的查问……。小说以人物为中心,有悬疑的情节,更有俄国在一战和十月革命前夕的历史氛围,深深地吸引读者的是看似紊乱但又符合生活真实的情节逻辑、对人物心理及性格的深刻体察以及随处可见的生动且精准的细节描写。细腻而深刻,平静和舒缓中隐藏着时代变迁的激流,有评论说作者像变魔术一般,将这座正在经历巨变的城市创造了出来,描摹出了十月革命前夕充斥着问题和裂缝的俄国社会。“早春”于是具有了某种象征性意义,意味着变化和除旧迎新。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众多评论中似乎都认为该小说中与政治相关的情节和描写都只是背景性的或隐约的情绪,而且也很少从“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评述它。我也不想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本政治或历史小说,但是我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及精神世界乃至整个城市生活的内在网络,都渗透了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对此一时期俄国政治与历史的深刻认识,政治与历史并非仅仅是人物的舞台背景。由此想到她被誉为“简·奥斯汀的继承人”的说法,布鲁姆曾认为“时下那些对奥斯丁作品进行‘政治化’阅读的人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她的作品”(见《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前言”,译林出版社,2011年),我倒认为“政治化”视角的阅读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是何种“政治化”。即便拿简·奥斯丁来说,虽然她的小说回避了对时代的政治风云、社会时政的直接描写,但是在她描写上层社会中人对财富与爱情看法的时候,或者是“让她笔下那些低贱小人很容易获得成功”的时候,所揭示的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就不是所谓“政治化”阅读的读者所强加的。《早春》故事中的政治视角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早春季节中的帝国、诗歌与印刷机,都与革命前的风暴紧密相连。 小说以在莫斯科生活的英国侨民为主要人物形象,首先就让我想起埃娃·汤普逊在她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提出的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为何在俄国文学中难以发现这个多民族实体中非俄族裔的存在与思想意识?为什么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到索尔仁尼琴,都具有大俄罗斯民族观念和殖民主义思想?似乎是作为一种另类的回应,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弗兰克既有对俄罗斯的真诚归属感,同时又不断在现实中感到缘于族裔身份的挫败感。当他在被秘密警察的盘问中感到自己仍然是一个异国分子的时候,以及他发现在莫斯科所有接受过他帮助的人“都会时不时地提醒他,他只是个外国人,哪怕情况不妙,他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148页)的时候,他深感委屈和挫败。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这种情绪无疑具有敏感的身份政治意识。 作者通过描述兰克的父亲艾伯特·里德如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俄国办厂创业的过程,很精准地揭示了俄国社会中的身份政治与政商关系:在俄国经商,不能有太长远的目光,否则会让人丧失信心;应该看到虽然英国投资者以及各种专业人员不再受欢迎的日子会即将到来,但是好日子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当他开始创业办厂的时候,除了要准备符合英国法律和俄罗斯帝国利益的相关证明文件之外,还要擅长交际和具备一种本能,“知道在贿赂穿着制服的人、政治警察、直接进口和工商业部门的办事员、技术和卫生检查员的时候该给多少才算合适,才不至于一无所获。这种贿赂必须叫作‘礼品’,弄明白这个词以后,俄语学习才算入了门”。(24页)另外,俄国与英国的双重视角总是不断出现。关于1905年冬天在莫斯科爆发的罢工和暴力事件,菲茨杰拉德马上写到“在德国和英国的报纸上都刊登了许多照片,照片里,人们把损毁的有轨电车放在街道上做成路障。电力早已被切断;煤油熊熊燃烧,点燃了积了厚厚一层雪、像坟墓一般的路障”。(42页)弗兰克的内弟查理在英国给弗兰克写信,也专门谈到英国的煤矿、铁路和印刷工人的罢工运动,印刷工人不仅罢工而且还自行印制质量不比《每日邮报》差的报纸;《泰晤士报》呼吁公众应该做好准备,以应对规模前所未有的劳资冲突。(60页) 弗兰克对于政治有相当敏锐的感觉。当他看到印刷排字员特维奥尔多夫拿出一本托尔斯泰的未遭审查人员删减的俄文全本《复活》的时候,他说“这个版本没有通过合法渠道发行。如果我是你,我想我会把它处理掉。”特维奥尔多夫问他“你觉得我能顺利拿国际护照吗?”他回答说“他们不希望熟练技工离开。”“可另一方面,他们很乐意摆脱捣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由于特维奥尔多夫是工会秘书,他认为政府会放他走,但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249页)这当然都是有历史依据的。 在这部小说中,印刷与革命、印刷与地下政治和秘密警察这样的主题在情节与人物的对话间起伏穿行。比起读罗伯特·达恩顿关于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的印刷过程的论述(《启蒙运动的生意经》第五章“造书”)和他关于法国革命前的图书市场与政治风险等关系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引言”等),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的描述更显得生动、感性、有现场感。小说中弗兰克的工厂承印很多东西:包裹的标签、拍卖商的目录、悬赏捉拿盗贼和杀人犯的传单、商人的名片、俱乐部的会员卡、空白单据、瓶子的包装纸、医生的执照、优质信纸、音乐会节目单、票券、考勤表、某些杂志以及教材的订单,但是不印报纸,更奇怪的是也不印诗集,唯一的例外就是要印自己的同事塞尔温的诗集《桦树之思》。“《桦树之思》目前正处在审查阶段,既然所有的诗歌都脱不了嫌疑,那么相关人员也许会对这本诗集进行比以往更为严格的审读。可弗兰克从没想过那些革命者或是政客会找他印东西。这些人似乎有能力炮制出使这座城市动荡不安的非法宣言和恐吓内容,他们做起这件事来几乎随心所欲。弗兰克很好奇,有时甚至会推测,到底有多少印刷机藏匿在住着学生的阁楼和地下室、牛棚、澡堂、后院的小便池、鸡笼、圆白菜地和土豆堆里;都是些小型手摇印刷机,也许是阿尔比恩式的,只能印单面,一旦嗅到危险的气息,可迅速转移至别处。他想象看那些异议分子不顾莫斯科一年一百四十天的霜冻,将油墨加热,以便多印一份警告书。印刷机的油墨很容易结冰。”(56-57页)后来弗兰克新聘请的成本会计也说过,“如今,手工印刷和托尔斯泰派、学生革命者以及藏在阁楼和地下室里的激进分子联系在了一起”。(161页) 读政治史专业的大学生沃洛佳·瓦西里奇偷偷闯进印刷厂的事件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开始他对弗兰克解释说想在这里找到一台手摇印刷机印些东西,弗兰克问他为什么不按正常方式来下单,但又马上补充说“我必须警告你,我们不碰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东西。” 沃洛佳回答说他写的东西跟政治无关,“写的是普遍的同情”,思考了一番又说确实有可能会让人觉得与政治有关。弗兰克说“我猜那得取决于谁被普遍同情”,说明弗兰克这位英国侨民对于俄国话语的政治性还是很明白的。更有意思和有点意料不到的是,沃洛佳马上从与政治有关的敏感性转到了身份问题:“你是个外国人,要是情况不妙,你顶多会被驱逐出莫斯科,回到自己的国家……一个俄国人没办法生活在俄国以外的地方,但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问题。”(147页) 沃洛佳闯入印刷厂并开了枪,工厂守夜人古利阿宁把这事告诉了警方,拿到赏钱。弗兰克后悔没有坚持先见到阿宁,给他一百卢布就可以让他不报警。于是警察到工厂来了。“只来了一位探长以及一位勤务员,他们穿了制服,这让弗兰克松了口气。”为什么他会“松了口气”?“那意味着守夜人没看见沃洛佳离开这栋楼,否则,他就会通过沃洛佳的帽子辨认出他是个学生,若是学生犯了事,那就会惊动便衣警察,也就是秘密警察。”(155页)弗兰克当然很明白治安警察与秘密警察的区别,而且他的办公室就存放有专为上门的警察准备的用葛缕子籽调过味的伏特加酒。警察只是例行公事地询问是否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塞尔温却插了一句说首批印刷的《桦树之思》少了一本,其实那是弗兰克在分手的时候送给大学生的。因此“弗兰克做了一番解释”。“通常情况下,诗歌是可疑的,并且很有可能再次受到秘密警察的特别关注。但这些诗都是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塞尔温·奥西佩奇写的,所以探长只是说道:‘呃,先生,桦树在思些什么呢?’”塞尔温回答说“长官,桦树会随着春风而动,就像女人会身随心动。”弗兰克此时已经看出警察感兴趣的是什么,于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他很清楚这么做不会冒太大风险——要知道,整个俄国的行政机构实在过于臃肿,得依靠无数的这类信封的传递,才能维持正常运行,不过也只是刚好能维持正常运行——便将信沿着桌面滑向探长。探长毫不害臊地打开信封,数了数里面装的三百卢布,就把钱装进一个介于皮夹与钱包之间的皮具里,那是他用来存放好处费的。”(158页)在这里的“信封”真是一个很形象和传神的概念,毫无疑问,弗兰克这点交际能力是继承了他父亲对“礼品”的理解和恰当的把握。 但是这个大学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有一天弗兰克被国防部政治处(“更准确地说,是秘密警察”)一个电话叫去位于尼基茨卡亚大街的秘密警察总部,要他指认被扣押的沃洛佳。负责问话的警察首先让弗兰克明白他们对他的所有情况了如指掌,然后要求他做沃洛佳的担保人,“保证他品行良好。他自然会受到我们的监视,但你也有责任确保他不会参与任何颠覆性或是政治上反动的活动。” ;“简单来说,如果他再次行为不检,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撤销你的出境许可;总之,只要格里戈里耶夫还在大学里,你就不能离开莫斯科。(222页) 离开警察局后,沃洛佳对弗兰克坦白说他闯入印刷厂不是为了什么印刷政治宣传品,而是因为他在心里爱上的丽莎·伊万诺娃到了弗兰克家当教师,他无法忍受像弗兰克这样的人接近她、跟她说话、对着她呼吸,甚至还有可能触碰她。因此他拿着手枪到工厂想吓唬弗兰克。(226-227页)沃洛佳后来再次被“预防性拘留”,国防部寄给弗兰克的一封公函说他已被免除沃洛佳所负的担保责任,因此“现在已无人反对他和家人在方便时尽早离开俄罗斯帝国。”(247页)对此弗兰克感到很受打击。“巨大的痛苦不由自主地涌上了弗兰克的心头,这是他头一回被这个壮丽非凡却摇摇欲坠的国家拒之门外;自从他出生以来,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成了他的历史,而他几乎无法猜测它会有怎样的未来。秘密警察也许会再次改变主意。”(247页) 为弗兰克的印刷厂管理会计工作的塞尔温·兰克也是英国侨民,他独身一人,是托尔斯泰的忠实追随者,在托尔斯泰去世后更加坚定不移。他会用俄语写诗,诗中经常提到桦树和雪。关于写诗的年龄,作者说“中年诗人与中年父母一样,都异常脆弱。”(130页)他对弗兰克说:“每个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写诗。也许你只是还没到写诗的时候。”(141页)这话说得很对。可以补充的是,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某个时刻”决定了写出不同的诗,如愤怒的或献媚的。 他没有请仆人,因为在他看来那种主仆关系是不对的。面对生活中的恶,他的哲学是“从来不相信可以直接对抗恶。唯一的办法是借助好的榜样,让恶者感到问心有愧,继而让它落荒而逃”。(49-50页)因此他不会意气用事,仅凭一己之力对抗混乱的局面,而是老老实实地躲开,让“历史的潮流推着他慢慢向前走”。(48页)但是在全书的最后,塞尔温终于把内莉弃家出走的原因告诉弗兰克,这才是他最惊人的一面:他和内莉在思想和情感上产生共鸣,“她想和我一起去某个更自由、更天然的地方。……在那里,一对男女可以全身心地结合在一起,弄明白他们在这世界上到底该做些什么。”(254页)因此约定在车站见面,带着三个孩子去伦敦。但是塞尔温在最后关头退缩了,躲在远处看着丽莎把孩子托付给车站站长之后就上车离去。他的解释是两个原因,一是想到弗兰克的感受,二是想到自己任何确定的收入来源,很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养活这一大家子。他告诉弗兰克,内莉最后去了某个托尔斯泰主义信徒的聚居地,那是他曾经向她讲述过的地方,那里有手工艺品、种植蔬菜的菜园子和音乐。(255页)这或许是作为女性作家的菲茨杰拉德对这个被道德说教笼罩的男子的逃避、懦弱性格的一种不失温柔的讽刺。 帝国的国情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例如“法律规定,星期六以及宗教节日的前一晚不许发工资,以免那些人第二天一早还是醉醺醺的”。(207页)更重要的是,帝国的政治现实也会随便在某个地方冒出来,例如塞尔温对弗兰克说看到丽莎的生活没什么乐趣,于是想到应该在晚上带她出去走走,“当然,所有的大型聚会都被禁掉了,特别是那些年轻人的活动,可我们也许可以去戒酒小组,或者某个叫‘谦卑之道’的俄国朝圣组织的聚会,抑或某个文学圈子碰碰运气。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要不然就花费很少;只要控制好人数,让人数少一些,所有活动都能得到政治警察的批准”。(216页)又比如英国圣公会牧师埃德温·格雷厄姆的太太在剑桥长大,在俄国生活的经历使她看问题也很有政治嗅觉,当她与弗兰克谈到家庭教师丽莎·伊万诺娃的时候,会突然问弗兰克:“也许我不该觉得她身上有什么神秘之处。可您觉得她有没有可能和某种革命团体联系在一起呢?”弗兰克回答说她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他认为搞政治活动需要闲暇时间,而丽沙整天要照顾他的三个孩子是不会有太多闲暇时间的,而且她没有搞政治所需要的那种气质。(191页) 后来弗兰克与丽莎谈起沃洛佳的事情,并向她表示了爱意。但是丽莎被孩子们从乡下别墅带回莫斯科的时候,也像内莉一样把孩子们交给车站,自己乘另一班车离开俄国去柏林。作者对这个故事的小结也渗透了政治色彩:“弗兰克本以为沃洛佳是个谋反分子,结果他只不过是丽莎的爱慕者。弗兰克原本非常肯定丽莎可以做他的情人,结果天知道她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如今,已经很清楚秘密警察为什么会支持他离开俄国。他有一批危险的员工,或者说,至少有一个危险的员工,一个假装帮他照顾孩子的危险的年轻女人。他让她逃跑了,更有可能是他安排了这次逃跑。比方说,他肯定没向当局汇报,就把证件还给了她。”(260-261页) 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的历史与政治叙事完全可以得到历史学家研究的印证。十九世纪末期的俄国社会建立在核心家庭、流动的社会阶层、经济功能化的模式之上,涌入城市的新移民无法找到认同感和可以表达利益诉求的机构。而出版业的发展则是此期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1905年以后检查制度有所放松,但当局对那些“发布假信息”“制造社会混乱”“煽动公众反对官员、士兵或政府机构”等的出版社仍然保持处罚和查封的权力。在1910至1914年间,城市工人的罢工事件十分频繁。面对社会的变对和与日俱增的政治压力,政府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设立了安全局,晋升了一批经过特别训练的安全官员,秘密警察组织日趋专业化。(参阅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二卷,李国庆等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351-374页) 另外,小说中有多处描写弗兰克与他的会计讨论工人报酬与成本核算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可以在专门研究十九、二十世纪俄国社会经济史的俄国学者Т.Я.瓦列托夫的论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城市劳动者的收入来源》(载《北方论丛》2019年第3期)中找到踪影。至于诗与政治警察的关系,的确是此期俄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颇有意味的景观。1912年底,未来主义者的第一本合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刊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两首实验诗《夜》与《晨》,他们还到各地巡回演讲,宣传自己的诗歌与美学主张。有些地方的警察因马雅可夫斯基在政治上有前科而禁止他讲演,有些地方则派了很多警察出现的会场上,马雅可夫斯基对此感到非常激动:“除了我们,还有哪个诗人能配得上这番大场面……一行诗能抵十个警察。这才叫诗!”(本特·扬费尔德《生命是赌注: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糜绪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20页) “早春”是这样来临的:“最先昭示春天到来的是某个抗议的声音,那声音由水发出,出现在从家里通往厂房的木头小径下的冻冰融化之际。……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挣脱束缚,可一旦流淌起来,它便化作潺潺的溪流,一整年的天平也由此开始倾斜。”(152页)“到那时,雪几乎都化了,可城里那些封得严严实实的窗户还得等上一段时间才会打开,以迎接春天的到来。”(171页)实际上,打开窗户才是春天到来的真正标志,但是要打开窗户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小说最后对这过程的描述真的有声有色:封窗的油灰要除尽,外窗和内窗间的死苍蝇也得清理掉,窗台得用软皂冲洗。等到窗户完全打开,“莫斯科的钟声、人声、出租马车声、出租汽车声在此时闯了进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春风,比在街上时感受到的更加清新,风不断吹进屋里,它们来自依然银装素裹的北部地区。” 这时,仆人托马打开门,弗兰克的妻子、出走的内莉突然回来了。(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