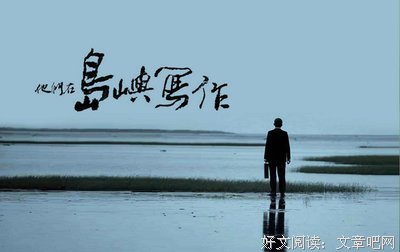《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城》经典影评集
《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城》是一部由陈果执导,西西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有好多文學的,香港的,現代主義的意象與西西有關,今天我只想說,最感動我的是她的自由。陳果把她畫过縫製过的想像朋友們全扮裝入鏡,與她同在。在那個段落我感覺陳果亦是深愛西西的。然而剛看了何福仁对陳果的批評,實在遺憾,片子拍攝過程沒有給西西應有尊重。但西西自從遠離文字創作后就遠離社會。透過此片是唯一機會看見他的生活和精神力量。片子还是很有看頭。讓我在觀後數日仍心緒激盪不已。
我們年輕時著迷西西的同夥們,曾經大段的誦念她(烘麵包,烘麵包,味道真好)而從青春本賦的輕快不息繼續跨越--像蜜蜂一樣本能的認知花和巢的方向--跨越,而非桎梏,生命才能打開空間給我們每一個人其它許多許多。這是西西給我的啟示。
60年代西西学习法文.榮膺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在斯德哥爾摩頒典獎禮上的致辭裡说:“一個作家,至少說一個小說家,經常是拙於言辭的。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語言學習中書寫與口語的分別,可以說小說家在書寫方面比口語表達更具天份。他習慣於緘默無語,如果他想浸潤於某種氣氛中,他必須融入人群,若無其事地傾聽各種對話.”在电影中西西也这样说。
Modiano也说:消失、身份、似水流年的主題常和一個城市的地形息息相關。這便是為甚麼十九世紀以來,城市便成了小說家創作的題材,他們其中的佼佼者都和一座城市連在一起:巴爾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倫敦、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聖彼得堡、東京和永井荷風、斯德哥爾摩和 Hjalmar Söderberg
西西也是这样的
《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城》影评(三):跳格子
我在大概一年之前看过西西的《我城》这本书,我忘了我是在哪里看到关于香港文学的推荐然后找来看的,我觉得她的文字是奇幻美妙的,有时候说的又像个小孩子在呀呀呓语,站在大人的角度,如果没有认真听,认真想想是不懂他们的语言的。读西西的文字参与程度很高,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如果心浮气躁,总是不能把一个故事完整读下来,但是如果选一个闲暇的时间,闲暇的心情,慢慢阅读,慢慢想,慢慢在脑海里画画,这样倒是会读的很流畅,也挺好玩。
马世芳说,西西的文字经过打散、重组、拼贴,之后会出现新的语境,新的阅读方式。我非常同意,我也同意说西西是艺术家不只是作家。西西把协作当做一种跳格子,西西的字形好像也是由跳格子而来的,很有联想通感的感觉。
《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城》影评(四):就讓“城寶”自己發光發熱吧
對西西是熱愛的,對陳果也是欣賞的,兩者不能說沒有火花,但是何福仁的怒氣好像令這美事成為一樁尷尬。在這麼一個本土人不及外地人重視“城寶”的現實中,憤怒指正創作者不深入不尊重,好像并沒有很大的必要。2小時下來其實倒嫌結構過於簡單(就不想想西西喜愛的高達電影?)而說陳果沒有花心思也是失去公允的,當然你可以嫌他的東西草根,不夠精緻。那就像作家老友的居高臨下,似乎作為殿堂級的西西作品,就不該以草根導演的草根趣味來做指引。那樣其實置西西于一個刻板而尷尬的位置。若果沒有一針一眼對於市井的關注和記錄,肥土鎮又怎能建成?這裡倒不是非要排除大陸,或者台灣,有更具文學素養的電影作者,可以勝任此次任務,當然更希望有本土人士,不論名氣,但是真粉,從某處殺出,送上一出既具啟蒙意義,又令老友們心悅誠服的作品。但是現實卻是,可能陳果已經是可以有的最貼近的選擇。
當作品脫離了母體,就會接受每一個人的檢驗和解讀,這時作者就好比失去了作品的控制權。陳果,或者更大範圍地歸罪,他的team,都是半吊子的西西讀者,但是卻不能以權威之見去壓倒任何一個普通讀者,輕忽他們的“誤讀”。好比你說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西西片中話語,創作團隊一樣可以以這番說辭回應。而且這麼一搞,令到好不容易留下的作者現身說法,也像掛上逢場作戲,不可信的面具,這又是所有人希望見到的否?
《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城》影评(五):我中意城市多d
#他们在岛屿写作 我城# 陈果导演的纪录片,主要讲的是西西的作品。
西西真的是迷人、可爱、有趣、天真(童心)的老太太
我第一次知道她大概是在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抑或是严飞《我要的香港》里面知道她的。不重要,只知道第一部知道的作品便是《我城》,书评家都说这是属于香港的城市文学,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便怦然心动。
“我城”那样简单、纯粹、利落地表达了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纪录片里的西西很有趣,仿佛不是一个著名作家,就像他哥哥说人群中她很普通。但却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作家”与“生活”之间存在的关联性。西西的生活就是她的作品,她的文字有点儿跳脱,但像是诗。每每描写城市、人、情感,都是克制冷静却充满兴味。西西说中意卡尔维诺,我也觉得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非常诗意。但西西的文字更加轻盈,一瞬间又让我想起了麦兜......想起了旧时的香港。有时我感觉到王家卫的感觉:碎片与断裂,但冥冥中又觉得有根线将这一切串起来。如果说王家卫是中环,那么纪录片里的西西更像是新界(或者说城市里的村——城中村)。其实香港也可以很诗意,也可以很乌托邦——任何城市都可以,在于你如何去看待她以及你与这座城市间的联系。
说到文学:人有信仰真好,文字也是极好的治愈。在心情烦闷压抑,作家总将自己的苦闷融于文字,字里行间记录的是属于个人的历史。西西是个艺术家。她写、她画、她创作、她爱、她生活…如她所说,制造玩具熊也是一种创作,艺术本身就有很多表现形式。而我觉得艺术本身便是“移情”———喜欢这个在人群里不出众的老太太,是怎样热爱她的生活:快乐、悲伤、疾病、痛苦、简单的快乐、个体的城和作为集体的城。
看到最后,b站的弹幕写道“2017年8月3日,我觉得自己抑郁,看完医生的第二天,谢谢这部片子”或许可以作为结尾吧。
#失眠的夜晚#
《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城》影评(六):劇透
(并非影評, 實是劇透.)
有影迷說不明白陳果導演嘅手法, 好散亂.
恕細佬不能認同, 細佬在下覺得有兩種順序, 平行剪接, 兩線行車.
一係順去, 由頭交代她創作經歷, 從她讀書時學法文與好友陸離小姐(香江第一杜魯福粉絲)相約寫信給法蘭西新浪潮兩大高峰卻學法文失敗寫唔到俾大大師高達先生反而好友成為杜生筆友此一瘀爆古仔講起, 跟住俾羅卡先生拉去寫過影評, 再推薦去做編劇, 實淪為抄襲荷里玉鬼佬經典劇本文章一大抄之抄斷手, 以致使出雷死你唔使本嘅文藝至死對白絕世功夫, 天是藍色的…樹是綠色的…直接將此對白之電影畫面無縫接上(仲要由當時得令金童玉女蕭芳方小姐謝老四先生講出--而影迷笑到斷氣為止-西西小姐若在場必吐血三升再揾窿鑚), 落嚟黯然回歸強項兼主場-寫小說仲係後現代存在主義加鄉愁加法式旋轉天馬行空又篇篇攞膽轉風格, 換嚟呢個上大銀幕做第一女主角機會, 中間不停加插名家名士訪談國粵語朗讀一干流金文字......
二是倒敘她的個人私生活, 從她現時最貼身的狀態, 慢慢倒流逆行到她的身邊環境, 到出身來處父母家史.
西西小姐之前得病導致右手無力, 一鏡直落她用左手加根筷子如何慢慢地擰干一條毛巾, 只為了洗個臉;
慢慢地下米煮飯, 跟餐廳訂兩小菜便當, 只用左手吃菜吃飯;
日常活動是去逛街, 拍她戴著小紅帽, 慢慢地走著;
走到母校和工作地, 協恩中學教了20年 (寫小說換不來太多面包);
她還躲起來, 和陳導玩捉迷藏;
帶攝影隊到舊居樓下, 說起當年周圍是一片田野;
看海心公園, 到舊照相館拍照-是的不是用數碼相機;
和縫熊師傅縫熊, 原意是為了治病;
知道得了乳癌的感受; 治病時的難受;
回家了-樓下擠滿了遊客;
父親去世, 認識了象我這樣的一個女化妝師;
老照片, 青蔥歲月(年青的西西好美);
一家人原住上海, 大時代變遷時來到香江;
哥哥說她小時候平凡得很, 事事都聽他的......
陳導攞嗮強項耍家嘢出來, 利用埋西小姐添, 專登整只人咁大熊人係西西坐渡輪行過去, 老作家驚喜到呢, 好返老還童, 夢回六十年.
一堆路人甲乙丙搶戲, 臨尾陳導自己玩埋一份, 扮只小蜜蜂……
再劇透實有人唔肯放過我……
《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城》影评(七):真实不存在
纪录片,最基本的属性就是真实,用相对客观的方式还原人和事。当然,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不用说纪录片,就是新闻也会因为剪辑或者选择性展示而营造出一个虚假的客观视角。作为艺术片导演的陈果,从一开始就不准备用传统的纪录片拍摄手法去记录和展现作家西西而是不停的在影片中 “刷存在感”,以展现“他”眼中真实的西西。
一部电影如何开头,以什么形式开始,无疑决定着整部影片的调性或者风格。导演陈果用在片场的花絮——一部部摄像机准备就绪,主人公西西可以进来了——作为开头,刻意地提醒观众,之后所呈现的内容是有意识地安排好的。在后边的内容中,还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工作人员和摄像机的“穿帮”镜头。
尽管影片是围绕西西及其作品展开叙事,但对于没有读过西西作品的观众来讲,观影过程中会有些难度。内容零零散散,西西的人生轨迹,写作风格的转变,穿插着作品片段、史料影像、模拟布景和不同人的采访,却没有让我印象深刻的点。
影片中,导演采访了一些西西的朋友、以前的同事、同行、文化批评者,两岸三地都有涉及,从不同人的视角去“看”西西和她的作品,分析其写作风格。对于采访部分的呈现上,陈果并非采用中规中矩的中景来拍摄受访者,而是全景甚至远景。试图与被访者拉开距离,但背后的原因为何我们只能猜测。
童心是影片中描述西西的一个关键词,从她写作《我城》时采用的儿童视角,到最后她罹患癌症后制作的毛绒玩具。我想,这是陈果所想表现西西性格中的一面。似乎作为西西内心的投射,卡通人偶毛熊、猿猴出现在街头,并配合拍摄内容做出一些相应表演。影片中,为数不多令我动容的一个场景是,西西坐在船上,与她曾创造的卡通人偶猿猴相遇,相拥。西西眼中闪烁着光,用不那么灵活的手抱了抱它。那是一个小姑娘看到自己喜欢的毛绒玩具时的眼神,最简单、最原始的幸福和快乐。
导演陈果也预感到了西西看到这些玩偶、玩具的激动。不仅将毛绒玩具进行放大,还按照《浮城志异》中所描述的场景做了微缩景观。纪录片最后,西西在回答者读者问题“为什么小说中比较少有爱情”,工作人员都身穿卡通人偶的服装,似乎创造出一个狭隘的童话王国。
有一个人评价西西是一个艺术家。没错,西西的创作已经不局限于用文字表达,尤其是在她的右手不灵便后,缝制毛绒文具已经成为了她另一种表达途径。可惜的是,西西本人并不是一个高调、夸张的人。如果像日本的草间弥生之流,她所拥有的影响力必然会比现在更大,但就可能有悖于这个普通老太太的童心了。
《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城》影评(八):[轉貼]他拍了一齣自己不懂得的電影 ——對陳果拍《我城》的回應
【明報專訊】陳果替目宿《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拍了西西的紀錄片,名曰《我城》,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率先推出,之前之後在訪問及映後座談陳果說了些極不恰當,也不符事實的話。朋友之間有強烈的反應,對影片也有意見,我如今稍作回應,因為善人可欺,結果愈欺愈甚,再啞忍即是失責。
拍攝之前西西和我並不認識陳果,拍完了再無聯絡,拍攝期間西西盡量配合。由陳果執導,是目宿的主意,拍攝前,西西囑我四處找來他的電影,《香港三部曲》、兩齣《妓女三部曲》、《細路祥》,等等,還有《人民公廁》。因此,是西西認識他多於他認識西西。
事前我有點憂慮,因為他的電影很市井、草根,這不單是口味,以至品味的問題,還有結構之類的毛病。他往往拿到好的材料、意象,到頭來糟蹋了。但西西對我表示,這也許可以撞擊出一些新東西,獨立製片,他未嘗不可以改進。我把資料給他,包括香港書展裏西西成為年度作家所有展出的材料、我拍下的短片、訪問對象的建議,等等,還提供小書房供他拍攝訪問。此外也提供一些西西朋友的聯絡電話,例如莫言。接受訪問的一些人,難道是因為他的原故嗎?台灣方面,目宿、洪範一定給他很大的幫忙。
我的角色是什麼呢?我是其中一個游說西西同意拍攝的人。西西年紀不輕,加上治療癌症的後遺症,近十年右手逐漸失靈,加上已不用電腦,要不是為了推廣毛熊、為正對瀕臨動物的視聽,她幾乎已息交絕遊,朋友都知道,基本上她對外聯絡都通過我這個老朋友。但她仍然讀書、寫作,也看電影;偶然也和談得來的朋友聚會。所以所有拍攝時間的安排,陳果都和我聯繫。後來,到了最後目宿寄給我們看第四剪,我才知道目宿「封」我一個「文學顧問」的銜頭。
他看了多少西西作品?
無論如何,既樂見其成,拍攝前我表示過歡迎陳果任何問題,儘管他從沒有問過。整個拍攝,沒有劇本,更從未與西西商量。材料他用了一些,不過,書必須他自己讀。西西的書差不多30本,當然很難要求都讀過,但拍攝人物紀錄片,尤其這人物是文學家,不認真看一些,怎說得過去?更重要的是態度問題。他在說話裏,一再主動帶出自己看了多少這人物的作品。多少?一本,另一次則說兩本,座談則說一本也沒有看過,理由是書太厚,很後現代,自己沒有時間(映後座談紀錄及其他各種訪問上網可見),前言不對後語,可知是順口開河。初聽是坦白,再說兩三遍就是自炫,是不尊重人,也不尊重這工作。難道以為拍一兩齣賣座的商業片的時間比其他寫作人的時間更寶貴?此片的投資者聽了又有什麼感想?就是看了兩本,也不過十五分一。電影人倘仍認為這種態度合情合理,並為之推波助瀾,我們的電影還有希望嗎?看他幾次解釋「我城」,就知道他甚至連《我城》的含意也不清楚。據吳世寧的採訪﹕
陳果在訪問說了好幾遍,「為什麼一定是『我城』,不可以是『我們的城』?」(西西《我城》也是我們的城──陳果拍西西,明報2015年3月27日)
不懂我城 不懂西西
近似的說話,還可見於其他的訪問,這可見是他頗為自得的想法。這好像要感謝他把我城的涵義延伸、拓闊。實則相反,這是收窄,更且誤導。通讀這書一遍,即知「我城」已包括「我們的城」,並不止於是「西西的城」,這個「我」,是小說裏的所有人,之所以用「我」,一如《我的喬治亞》,是對每個個體的肯定,對獨立人格的尊重,這是互為主體,並且,這又是在「我們」之前的謙遜。「我城」這詞已成典語,兩岸三地都有人用,不會變成我們的城。好作品總有超乎時間與空間的普通性。他其實拍了一齣他完全不明白卻又沒有虛心學習的電影。
陳果拍了一齣他不懂的電影,我再從片中及談話中各舉一例。其一,西西言談每喜自嘲,不認識她又不加深究當然不會了解。例如片中她談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她為電影公司編劇,電影公司只要她改編外國名劇,並不讓她創作,她於是說自己不適合寫劇本,因為不會寫對白,陳果於是自作聰明,據此論定她不會編劇才從此轉寫小說。他聽不懂那是指在「抄劇」的情况下她不會寫。她自己創作的後設小說《東城故事》不是寫成電影拍攝的分場?她同時寫的《寂寞之男》不是劇作?她不是參與早期實驗電影的浪潮,自己從新聞片拼貼出充滿創意的《銀河系》?她眾多的小說中不是有許多對白嗎?
說西西發脾氣 是中傷
其二,在映後座談中,導演輕佻地答觀眾的問題;紀錄片不必拍得深,土瓜灣又有多深?(香港電影節網頁﹕紀錄片可以有多深?2015年4月2日)西西固然大半生都在土瓜灣度過;長於斯,成於斯。她在土瓜灣寫作,還寫過許多與土瓜灣有關的作品。這裏並且是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創校授業的地方。余英時在這裏大學畢業。牟宗三曾長居於此,他的一家之言,大部分就是在這地方思考的成果。這些名字如果聽不懂,至少不應該忘記這裏還有一所從中央宰牛的屠房改成藝術家和藝術團體駐場的牛棚藝術村。地區雖舊,卻充滿一種我城深厚的人文精神。
我可以多舉例子,但也夠了。最近朋友給我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30號(2015年4月)的陳果訪問,談拍攝《我城》的過程,訪者問他拍攝時有什麼趣事。他答﹕「有呀,西西在拍攝過程試過大發脾氣,說以後都不拍,不講了。」在訪問裏還一再強調西西生氣。不尊重人,只暴露了自己的無知;但說西西曾經大發脾氣,說以後都不拍,卻是中傷。拍攝從2012年6月至10月,西西工作的部分14次,另外兩次到東莞和廣州方所展覽毛熊、猿猴,東莞由目宿拍攝。還有一次,助手和我約定,素葉的朋友為拍攝搞了一次聚餐,這是西西三十多年來的社交生活,我還得游說素友出席,因為並非人人都喜歡出鏡,在某大酒店包了一個房間,結果他只派一個助理和攝影師來。所有拍攝,只除了其中一次因事,由適然代勞照料,其他我都在場。我可以證明西西從沒發脾氣,適然的一次也說並無不愉快。
突如其來的南生圍
而且,陳果沒有說明西西何以生氣,在什麼的情况下發大脾氣。這很重要,不然這是一面之詞的中傷。說不定,她真應該大發脾氣;她絕對有大發脾氣,拒絕再拍的權利。他不說明,我唯有加以註解這背後的真相。事情是這樣的,拍攝的第三天(我保留了所有拍攝的日誌),下午一時,陳果接了西西,一路乘車,途中才知要去南生圍。路途遙遠,我已知不妙;西西從沒到過這地方。在南生圍的渡頭坐定,讀書,並且由助理發問,受訪者都知道,那是大學剛畢業的助理替代導演讀書之故。而問題,對不起,都是惡補回來,而且忽然而來,鏡頭之下也不容怎樣思考。最大問題是,拍攝至傍晚六時,這是西西每天固定吃藥的時間,藥不在身上,她本來也要吃一點什麼控制血糖,但零食早吃光,血糖降低,這事可大可小。我四處張羅,幸好渡頭已打烊的一家小店願意替她弄一個杯麵。她回到土瓜灣已八時多。第二天,我就約來導演,在座還有西西,以及許迪鏘。我聲明以後拍攝不能多於四個小時、西西不是演員,並不演。迪鏘補充﹕也不要連續兩天拍攝。這些必須說清楚,這不是「講數」,因為並非討價還價,這是事前和目宿說過的,後悔沒有白紙黑字存照。生氣的反而是陳果,他說我「詐型」(「耍無賴」、「耍賴皮」),這句話我是相當介意的,因為西西不是他的僱員,我們並不欠他什麼。在場的西西沒置一言。陳果在訪問中仍認為去南生圍值得,因為南生圍被地產商買去,快失去了。但這與西西沒有關係,更不能罔顧老作家的健康。陳果有個人的政治社會議題,大可另行發揮,不必利用西西的紀錄片。
一齣要「演」的紀錄片
事後拍攝,果爾沒有超時,一直和洽。但仍不乏要西西演的場面,例如在照相店,例如在布幕前作狀周遊列國(刪去了,當時目宿監製也在場),西西照演如儀。西西一直充分合作。還有要她演的一場,只有這一場,她拒絕了。
陳果要求西西穿上長頸女子的毛熊衣服,我心想這可不得了,當場問西西﹕如果你不願意,就說出來。西西於是說不穿。幸好拒絕,試想想,三十三、四度的八月炎夏,要一個七十四歲的病患長者穿上只餘小孔呼吸的毛衣毛頭在街上行走,簡直是謀殺。我替那位年輕演員苦。或者,這些就是他的所謂「大發脾氣」吧。大毛熊在這裏那裏行走,這是他在訪問中說的「魔幻」?但途人只覺錯愕,大多不看一眼。再提點一句﹕這和他開場時貌作實錄的指示﹕「按平常那樣,不用管我」,就不調協。這片子病在太多的這個「我」。如今想想,西西要接受十多次各種初級文學水平的提問,其實表現了過人的耐性與寬容;她久已拒絕眾多有關她的文學寫作的訪問。你以為她還需要借陳果出風頭?不過答應了朋友,就盡力完成它,單是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好好學習。
回應至此,且留有餘地。這片子還是看得的,因為西西,她長期深居簡出,家居生活從未公開;她的創作多元化,有豐富的內容,只取其中兩三點已有可觀。下面是我對西西的發問﹕
何﹕陳果接受一本刊物訪問,訪者問他拍攝時有什麼趣事,他答你在拍攝時試過大發脾氣,說以後不拍了。我想問你,在拍攝的過程你曾否大發脾氣,說以後不拍了?
西﹕答案是沒有,不單沒有發脾氣,更沒有大發,也沒有說過以後不拍的話。如果說以後不拍,我就真的不會再拍。他以為這是有趣的事麼?我如今是否應該發一下脾氣,以便證明他說的是實情?
文__何福仁
編輯/屈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