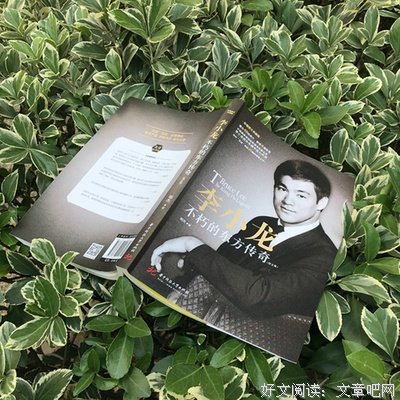《不朽的女人》影评摘抄
《不朽的女人》是一部由阿兰·罗布-格里耶执导,Françoise Brion / 雅克·多尼奥-瓦克罗兹 / Guido Celano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朽的女人》精选点评:
●对说谎的人和欧洲快车多喜爱,就对这部多厌恶
●相遇-相识-寻找-重遇-死亡,导演彻底摒弃正常叙事、使用形式主义风格的镜头将关于现实与虚构、真实与谎言的内容呈现出异常美丽的结果。在他人最痴迷、最深爱的时候,神秘的消失或死亡,便成了他人生命里不朽的存在。
●不存在的电影。
●是虚无吗?凝视与被凝视、寻找与被寻找构成了一场异域情事;记忆碎片的重复呈现拼凑一场非典型艳遇。真相兀自矛盾,越神秘就越想探测,越靠近就越接近死亡。伊斯坦布尔天空下的废墟中谜一样的群像佐证了这部梦一般的电影。
●摄影真的是太美了。但是总体还是觉得有点形式过于内容。
●trompe l'oeil/假象/赝品/梦(一切纯视听情景:装饰物特写 古建筑 停滞的人 镜前自省) ;禁脔/女性的怨恨; 结构的对位;叙事的语焉不详与自相矛盾昭示叙事的虚构属性;双向窥视; 单镜头摇移中位置突变与时间变形;不同速度的时间/心理时间; 视线衔接对象:作为预言者的角色 一种赤裸叙事; 跨时空的声音蒙太奇
●作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编剧,格里耶的这部《不朽的女人》处处都是《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影子。雕塑般矗立面无表情的人物,尤其是在女人失踪后,男人不断的寻找,曾经和女人在街头巷尾游荡时遇见的商贩或熟人等等表示都没见过女人,而后在某一个时刻男人在苦苦寻找中终于在街边遇见了失踪已久的女人,这时街道上所有路人都保持姿势矗立不动,如同定格一般,这完完全全就是《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上流酒会场景的再现。在影片开始不久时,格里耶运用了别致的转场方式,通过突然出现的人物身体与移动或推拉的镜头相交待整个画面被遮挡时转场到下一个画面,下一个场景与空间,这样的转场方式出现了三到四次左右。
●他的第一部不如以后的作品那么嚣张。
●看的是无字幕的,实在看不懂,只觉得很诡异,与导演的其他作品风格差不多。
●平移的运动镜头,物化的精确测量,面无表情的静态状物,不确定的人物、似真似幻的情节都是为了印证“一切都是假话”。以静止人群站立为背景,镜像的巧妙运用很好地平衡了空间,而人物对峙的紧张感凸显了空间结构,相对于其小说,文本被释放到环境,更有独特风貌。节奏适合大提琴的无变奏。
《不朽的女人》影评(一):格里耶,沃霍尔,斯诺,弗兰普顿,梅卡斯
那天看了格里耶的处女作《不朽的女人》后(以及之前看的《欧洲快车》),我即把格里耶奉为我的同路人。在《罗伯-格里耶谈艺术》中,小汉斯与格里耶的访谈,格里耶说到:也就是说我很喜欢梅卡斯这个人,但不喜欢他的作品,一点儿也不。而我欣赏的那几个美国地下电影艺术家正是那些仍旧在进行叙述的人,例如我想到了迈克尔 斯诺,甚至霍里斯 弗兰普顿。......(去美国的时候)沃霍尔是兄弟般迎接我的人之一。
而我说过,我最为尊崇的三位电影人正是 Michael Snow,Hollis Franpton,Andy Warhol,我同样也非常敬重Jonas Mekas。
《不朽的女人》中,女主角对男主角说:至于所有这些都是你的想象。我们可以把这句台词看作是格里耶借电影中人之口对观众说的话:至于所有这些都是你(看到)的想象只存在于电影中。
而在《欧洲快车》中,男主角在旅馆和妓女完事后,他掏出皮夹时一张照片从口袋中掉落地板,彼女即说:是你太太的照片吧,通常这时候都会这样。这句台词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看作是电影中的人物直接跳出来对电影自身发表评论,同时指涉所有类似的电影桥段。
格里耶的电影的核心观念,可以用他说的话来概括:银幕不是世界的窗口,银幕自身既是世界。而沃霍尔电影的核心,即如他所说的:我只是把摄影机打开。
《不朽的女人》影评(二):不朽的游戏
作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编剧,格里耶的这部《不朽的女人》处处都是《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影子。雕塑般矗立面无表情的人物,尤其是在女人失踪后,男人不断的寻找,曾经和女人在街头巷尾游荡时遇见的商贩或熟人等等表示都没见过女人,而后在某一个时刻男人在苦苦寻找中终于在街边遇见了失踪已久的女人,这时街道上所有路人都保持姿势矗立不动,如同定格一般,这完完全全就是《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上流酒会场景的再现。在影片开始不久时,格里耶运用了别致的转场方式,通过突然出现的人物身体与移动或推拉的镜头相交待整个画面被遮挡时转场到下一个画面,下一个场景与空间,这样的转场方式出现了三到四次左右。影片中有大量的横移镜头,每一个出现在横移画面中的人物都如雕像般严肃静止。同时影片也反复出现相同的空间和人物,但时间却无法重复。前半段是男人与女人在伊斯坦布尔的邂逅与游荡,中段是女人的失踪和男人的寻找,后半段是女人的重新现身以及女人驾车男人坐副驾驶时发生的车祸。女人死了,男人如雕塑般站在车外看向车内,但女人又不断出现,不断在重复的场景里出现,就像男人的幻想,又像男人的记忆,甚至最后出车祸死掉的变成了独自驾车的男人。这就像是记忆修改又或者是真实的回溯,格里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那个行驶在夜路上的车头画面不断出现,就像一辆时空机器,带领着男人去到一个个新鲜又熟悉的场景里重塑或虚构记忆与真实,就像一场游戏,循环往复,乐此不疲,而女人也在这场不断出现的游戏里变得不朽。
《不朽的女人》影评(三):变成一只眼睛
开场几分钟之后,以为是阿伦.雷乃拍的,因为很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后来才想起这是前几天下载好的《不朽的女人》,那就一致了,因为阿兰·罗布·格里耶正是《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编剧。
格里耶说过这件事,当时他还只是午夜文丛出版社里一个没冒头的作家:“我写出的不是一个场景,而是一部完整的剧本,包括每一个镜头,每一帧,每一次机位移动,一拿到便开拍。很少会有导演接下这种剧本,但阿伦.雷乃接受了,电影在两个月内便杀青。”
其实,在写这部电影的剧本之前,他就已经写好了《不朽的女人》,但是直到《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在威尼斯电影节大放异彩之后,他才得到了拍摄的机会。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又不自然地想起戈达尔,这种联想的发生在于它们形式上的接近,即不遵循所谓的电影文法,它讲一个男人在伊斯坦布尔碰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在她消失的时候,他尝试寻找她,然而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这个女人真实存在。那些和她同时出现的配角们,纷纷对这个男人摇头,本身看似存在什么阴谋的这样一个电影上惯常出现的定式,并没有出现。由此激起了我更大的兴趣。
但是这种兴趣也仅仅是形式激发而来的,是他的拍法使然,开头并不觉得这里还有什么更值得往下深潜的地方。又逐渐意识到,这种形式和戈达尔实则很不像,虽然格里耶本人很推崇戈达尔,但是在电影的处理方式上,他和戈达尔有根本上的区别。
这种区别在于他如何看待电影的文本。
从他选择的剪辑,转场方式上就能看得出来。就是那扇百叶窗,从那里躲藏着的男人的身影,他的眼睛从百叶窗看出去,然后镜头就开始跟随着这个女人的足迹,一小段,一小段地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叙事会不断地回到百叶窗后,再不断出发,这时候,文本是有一个根据地的,但戈达尔不会回归,他不停在剪碎文本,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他需要的不是电影(他需要的当然不是电影),而是“剪碎”这一行为。又当然,这只是一个极为偏颇的说法,本身并不正确。
格里耶在《巴黎评论》里谈及自己的作品《重现的镜子》时说过这么一番话:“每一点对我来说都不同寻常,但同时又没有哪一点让我产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元素在运动中糅合的方式,不断移动,不断变化,就好像在我身上散落下来的那些碎片一样。这些人物“运动”的方式,是拒绝被定型的方式。”我想,这番自我评价同样也适用于《不朽的女人》。
离开形式,再回归到文本,其实这个女人是有原型的,她的名字叫做卡特琳娜,格里耶在游览伊斯坦布尔时遇见了她。于是就有了这部电影,是的,这部电影是一个回忆。但正如他本人说过的那样,回忆属于想象的一部分。回忆其实是想象。它们看起来会像某些存在于我眼前的事物,但它们永远不是那些事物。
科学的眼睛正在看想象的事物。
用的就是那个藏在百叶窗后的眼睛。文本也正正藏于百叶窗后的那个眼睛里。在这个眼睛里,我好像可以找到方才提到的那个更值得往下深潜的地方。但继续想下去,又觉得这是条死路,或许我能找到文本对应现实的那一点点痕迹,但其实它丝毫不代表格里耶,作用为零。
不过并不用因此气馁,我是会问这样的问题,通过这个文本,他试图在叩问什么?但我觉得他不准备提供一个答案。阿兰·罗布-格里耶,他不准备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就像他对福楼拜的评价一样:“福楼拜没有任何话想说,没有任何讯息想传达。他的所有人物都活在文本当中,存在于生命过程里的是文本本身。他的文本就是一个世界,而不是对世界的描述。”
对,无论格里耶在女人身上投放了什么意义,是以她带出伊斯坦布尔的绝唱,还是其他什么别的,这个文本终归都不会是一个再现世界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洞悉”世界的问题。在失败的革命正中心之处,有一种永久的渴望,也是永久的失望,它是一张尚不存在的脸,但你却见过,每个人都应该见过。这个文本的重要性就在于让你通过那个百叶窗后的眼睛去看这个文本本身,看那个“世界”本身。
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不是在说废话吗?可能是,但我有时又会觉得,这不就是电影吗?或者说,电影不就是可以这样没有意义吗?存在这样的电影,来让我在某个现实的下午当中抽身去想一些无边无际,逻辑混乱的问题不是很好吗?
我对自己讲,电影的评论四通八达,随处可见,但站在原地自言自语这样一些不见得有准确形态的问题,也挺好玩的,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我根本不懂任何东西,没有评价,我也不依赖导演去为我创造什么,这是我自己看电影时的一种心态。
这种心态和我记录下来的这些文字在方向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它不存在方向,拍一部电影要讲一点事情,写一点文字,从开头已经给自己预备了一条路要通向某个即将被自己证明的东西...这我来说,好像并不太有意思,至少在这个下午如此。
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是不是都知道自己即将要写出什么呢?写作是为了让阅读者来到我规划好的花园而作出的努力吗?可不可以怀疑这样一件事,拍电影也如此。我写这个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下一秒我会来到哪里,这应该也不算得奇怪吧。奇怪吗?爆炸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你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你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文本当中?来到这个位置之后,又应该如何呢?
我又想起前晚看的《狮子星座》,看完之后,S和我说起《狮子星座》里宿命论的问题,来到哪儿,成为什么,将会如何,这些问题是否早就被决定好?我们是哪个我们是否不由分说?又可以问,候麦的这个《狮子星座》究竟代表的是宿命论还是海德格尔的决定论?--我们的决定早就被决定,决定的我们的那个决定也早就被决定了。我不太清楚。
但是,在今天看完《不朽的女人》之后,我又觉得,在命运的推波助澜当中,内在的那种细微冲动或许是可以超越决定本身的。正如现在的我正在被这个文本底下的我所超越一样,我依赖着他,来到了与“决定”无关的地方。
因此,我突然意识到,写下一个文本,不是为了处理这个文本,而是要被这个文本处理。正如格里耶在他的电影里所做的一样,但打破这种决定,绝不是意味着他要成为那个掌握决定的人。我们要做的,只是任由它发展而已。
我相信这一点,没有不朽的女人,也没有不朽的文本,只有问题是不朽的,而决定也不对问题起任何作用,或然率成就的不是结果,而是那个可以不停回返的百叶窗,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到那个场景,看待一座真实存在却又不是真正存在的伊斯坦布尔,或者巴黎,或者我们自己。
“这都是你想象的产物,看,你梦里的清真寺,坍塌了,还有你梦里的船只,一只禁不起风浪的船,一切都要重头再来。拜占庭的城墙,它们肯定要被再次重建,目所能及,从马尔马拉海到金角海港,你可以经过一个废塔遗迹,到达七狱城堡,你可以随心所欲去哪,在这里你是个外国人,你到达了梦中的土耳其,伪造的监狱,伪造的城墙,伪造的故事,你回不去,逃不掉,如你所见,连船也不是真的。”
而现在我更记得,只要再经过一次那个百叶窗,一切又都可以重来。那我不就成为了那个科学的眼睛么?好像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