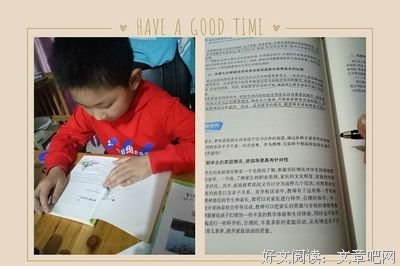《血缘与归属》读后感100字
《血缘与归属》是一本由[加拿大] 叶礼庭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一):默克尔已经走得太远了
2018年12月底,默克尔说:“民族国家今天必须做好放弃部分主权的准备,尤其在移民、边境甚至是主权问题上,民族国家不应听从本国公民的意愿”。
但是从叶礼庭这本啰啰嗦嗦的书里,他得出的结论是:“即便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世界主义情怀和权利,依然需要一个能落实功民权利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段我觉得我组织的比译者清楚)。基于他的结论,默克尔就走的太远了,你不能要求功民让渡这样的权力,这样不仅建立不了她理想的“世界新秩序”,反而会撕裂民族国家的共识基础。更何况是欧盟这种建立在发展很不平衡的民族国家之上的联盟的基础。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二):血缘与归属
叶礼庭教授深入若干民族冲突与暴力的现场,观察、感受、探访,通过纪实化写作,追寻现代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本书选取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五个国家与地区的案例,展现民族主义不同样貌与不同根源,每个国家的民族问题背后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与逻辑,各国共同采取了民族主义解决方案即独立建国,来解决这些复杂的涉及历史的、种族的、信仰的、经济的问题,难免出现了民族主义地域不耐受的症状即民族直接的暴力冲突。“当民族主义者说暴力因自我防卫和寻求自决而成为正当,理性主义者断定,这是暴力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民族主义者通常是年轻人,他们热爱废墟,热爱毁灭,热爱来自他们枪杆子的权势,“民族主义叛乱背后的隐形原理之一是它们发掘出深植于男性之中的对现代国家自身斯文和秩序的憎恨”,“国家秩序是父亲的秩序,而民族主义是儿子的叛乱”。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三):虽然有不满,但还是本好书
读叶礼庭的《火与烬》是惊艳的感觉,所以来读他的其他书。虽然我也打了五星,但是实际上这本于我是不如《火与烬》的。也许是因为人对于自己真正深入参与的事情,才能说的更加透彻。《火与烬》是作者竞选总理失败之路的记录,而这本书本身是作者与bbc纪录片团队,采访南斯拉夫地区、德国、魁北克、乌克兰、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等,顶多算深度报道,所以对我有种民族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分析不够的感觉。
收获还是很多,以前不关心政治,即使看到电视报道一些其他国家的问题,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地区问题背后的渊源。这两年跟外国人接触多一些,世界变得跟我关系多起来,脑子里自然出现了很多疑问,开始看看这些书。
还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可能作者和bbc预设的对象是欧美人士,有一些部分我读起来费劲,比如说北爱尔兰,很多前因后果和名词并没有特别明白。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四):笔记
叶礼庭,也是看来这本书才了解他的背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曾经还做过加拿大自由党的党魁,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行动派学者。只不过中文版出版的晚了一点,93年考察了南斯拉夫、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以及北爱,叶礼庭认为如果将种族民族主义转变为公民民族主义,用公民身份取代血统,让愿意融入的外来者加入民族国家,让国家保护公民而不是让人民从血缘中找到归属,也许能更好的实现世界主义。这本书让我更深入的来思考民族主义这个问,为什么血缘和共同的信仰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为什么不同的血缘不同的信仰就一定要互相残杀,特别是在相同宗教不同分支之间?是长久以来历史的积怨,是被民族主义政客相互利用,还是出于人类嘴本能的对安全感的依赖?并没有人能给出最终的答案,新民族主义也想过去一样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只不过换上了现代化的外衣而愈加蛊惑人心。作者所说的公民民族主义要实现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五):漫漫民族主义之路
“如果一个人的父亲生于俄罗斯,母亲生于英格兰,在美国接受教育,职业生涯在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度过,我们很难过多寄望他成为一个种族民族主义者。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那必定就是我。”在此书中,作者写了他的六次关于新民族主义的旅程,理性又有温度的给我们提供了新民族主义的各种范例。它们的本质都很相似,只不过是换了时代和环境,上演的剧本没有本质的差异。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开始,经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再到北爱尔兰,他们各有各的问题,对生存的渴望,对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焦虑,归属感的缺失,让他们成为民族主义者。通过这些旅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当今“后冷战”之后的新民族主义的灰色甚至是血腥的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世界各地的新民族主义倾向是如何导致冲突,甚至残酷战争。
谁能够保护我?面对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局势,人们想知道谁可以信赖,谁是自己人。种族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直观明白的答案:只相信那些与你血缘相同的人然后排除异己。双方的民族主义政客接受了微小差异的自恋,将其转化成一个魔鬼寓言:自己的一方显然是不应谴责的受害者,另一方则是大屠杀的刽子手。
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出在民族主义本身。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有一个家,每一个这样的饥饿民族都必须得到抚慰。错的是某一种类的民族,那种民族主义者想要创建的家园,那种他们用于追寻其目标的手段。这种主义像是一种演讲,叫喊声不仅是让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也是由此相信自己。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古语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人们生活在熟人中间。此后,随着现代性的展开,当身边充斥着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时,当技术使得天涯若比邻时,思想家们一度认为,民族主义即将成为过去式。
然而,他们错了。历史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变本加厉。
新民族主义的破坏力有多大?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叶礼庭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民族冲突的前线,实地考察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创伤。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他看到炮火下破碎的村庄和心灵;在德国,他看到同胞经过长期隔离后的挣扎和彷徨;在乌克兰,他看到两个民族间的相爱相杀;在魁北克,他看到民族自决的吊诡;在库尔德斯坦,他看到一个民族为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园所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北爱尔兰,他看到重压之下扭曲的民族身份。
作为流亡沙俄贵族的后裔,作为哈佛毕业的学者,叶礼庭亲身体验着新民族主义的这种表现形式,以细腻的笔触大力批判这种基于血缘的身份认同。在他看来,公民民族主义才是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唯一出路。
时至今日,距离叶礼庭写作本书又过去了20多年,放眼世界,从国内的各种抵制到大洋彼岸白人至上主义抬头,无一不向我们昭示着本书的意义。或许,就新民族主义的破坏力而言,种族冲突的各方在地缘政治上所造成的裂痕,却是殊途同归。
叶礼庭:《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成起宏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8月,48元
子扉我 2017年秋 季风地下空间
原载季风书园微信2017年9月6日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七):生存在夹缝之中的库尔德民族
据《经济学人》报道,2019年10月6日,特朗普(Trump)宣布美国军队将撤出叙利亚东北部。此为叙利亚和土耳其的交界地带,大量库尔德人在此居住。几乎与美国撤军同一时间,土耳其军队开始进攻由此导致的“军事真空区”。截止至10月17日,数以百计的库尔德人因此丧生,预计至少十六万人被迫离开居住地。面对国际上和美国国内的无数质疑和谴责,特朗普的一种解释是,他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战争,而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可以应对叙利亚的烂摊子(the mess) 。在特朗普发布撤军决议不久后,美国副总统彭斯(Pence)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以经济制裁为筹码,要求土耳其停止军事进攻。17日晚间,彭斯公开宣称土耳其方将暂停在叙军事行动120小时,给予库尔德人时间以撤出受灾区。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事和尚未明朗的局面显示了库尔德民族对自己命运的无力。他们仿佛是散落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线上的棋子,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各国利益之战下的牺牲品。而为何库尔德民族的问题会成为世界问题?这个民族有着怎样的历史,以至于他们现在需要西方大国的庇护?加拿大作家、学者、前政治家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亲自探访了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地区—— 一片名义上为伊拉克所有的库尔德聚居区。他发现,库尔德民族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家园位于现代世界最具攻击性和扩张性的四种民族主义国家的交汇之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四种民族主义困扰着库尔德人自身创造共同民族身份的努力。而库尔德斯坦这片土地是在为联合国所认可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干预下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西方的空运援助和持续的国际关注,就不可能有家园。
真正的归属,究竟来源于血缘,语言,法律,还是(常常隐藏于外交辞令下的)赤裸裸的利益?当我们对一个民族,或是一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时,能够做出的评价,其实是非常之少的。叶礼庭对库尔德斯坦的记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发生于库尔德民族身上的事件。
(本文原载于三辉图书官方公众号,ID:sanhuibooks)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八):也就过了20年
这2天读了叶礼庭的《血缘与归属》,写得非常好的一本书。居然成书于90年代。里面提到了很多潜在的冲突,比如克里米亚,库尔德斯坦等,现在仍在动荡中。而反倒德国,加拿大的魁北克运动,以及英国与北爱,目前看起来还比较太平。但是在成书时期德国对土耳其移民的看法就非常矛盾,看上去已经是无解了,没想到这几年不仅没有解决,反倒是引入了更多的阿拉伯和北非难民。
这几年俄罗斯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不奇怪。早90年代作者就指出了这块地区三个民族的纠结。现在已经觉得这地方一堆乱麻,但是在90年代苏联解体的时候更是一团糟。比如庞大的黑海舰队的归属,或者尚未毕业的海军士官生未来的效忠对象,等等都是问题。书中鞑靼人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大意是没有自己的土地,在大巴上也会被人欺侮。鞑靼人放弃一切,从中亚回到自己的土地。
库尔德工人党当时面对的是萨达姆,没想到十几年后萨达姆灰飞烟灭,但现在情况更加复杂,库尔德人面对的是ISIS和土耳其人的打击。看书上的描述,对照这几年的新闻,我的直观感受是,现在的战斗比当时更加残酷。
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运动是让作者无法理解的。因为这是发生在以宽容、成熟著称的加拿大,并且加拿大政府已经给了魁北克很多方面的特权。同时在过去的30年魁北克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几乎要和英裔加拿大区的经济并驾齐驱。但是作者碰到的各个阶层的魁北克人还是坚持要独立。所以这证明了几点,即期望经济提升并融合就能抑制民族主义的想法不现实,即使在加拿大也被证明不可行;民族和国家还是会被人区别开来。英裔加拿大人对国家认同大于民族,而魁北克人相反。这也是作者不可理解(即使他自己就是加拿大人!)在作者看来魁北克人的所作所为只是要一个一个名分。但魁北克人可不这么认为。不仅是工人,还是跨国公司的总裁,或者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这是最让作者感到悲伤的。
关于有时候真心觉得时间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武器。很多问题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解决,或者说,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的问题变成了另一个问题。也许这是东方哲学的一种态度。以前觉得非常僵化,或者稀里糊涂,现在看来,也许是真正的智慧的体现。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九):“公民民族主义”道阻且长
战地记者出身的加拿大作家叶礼庭于20世纪90年代初,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和重新统一的德国六个国家和地区。他通过大量的采访和细致的观察向读者展现当时全世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阐述其对“民族主义”这个大问题的理解。细节和对话使整本书细腻易读,充满人情味。下面是印象较深的一处:
在一个展示柜中,有一张铁托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照片,他坐在一个写有‘南斯拉夫’的小牌子后面。不知道是谁粗暴地用圆珠笔把国家的名字涂抹掉了。”通过描写一个展示柜中的一张照片,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便如在眼前。
在我看来,“民族”是一种用来界定自我身份、塑造自我认同的“话语”,人们试图通过这种界定和认同来找到归属、获取安全感。和其他话语一样,“民族主义”话语并非天生、自然的,它体现权力,并服务于权力。
作者引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段话:
只是你的姓氏成为我的仇敌;你就是不姓蒙特鸠,你还是你自己。蒙特鸠是什么?不是手,不是脚,不是臂,不是脸,也不是人身上任何其他一部分。啊!换另外一个姓吧:姓算得什么?”叶礼庭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幻想和逃避”的语言,是一个充满“高尚事业、悲剧性献身和残酷必要性的幻觉王国”,充满了虚假和伪善。它提供了一种持续狂热、永恒亢奋的光荣政治,取代了实际政治的平庸,取代了直面现实的政治世界。人们试图通过民族主义从现实中逃离出来,赋予自身行为以光荣和使命。这样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只能是暴力、恐怖、死亡。作者指出了民族主义中存在的“微小差异的自恋效应”,两个民族之间的实际差异越小,它们就越要寻找彼此间的差异以进行区别和对抗。
基于此,作者认为,“公民民族主义”应取代“种族民族主义”。一个民族国家应当是所有人的家园,种族、肤色、宗教和信仰不应成为是归属的障碍。人们可以通过共享同一套政治理念、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而聚集在一起。
然而,“公民民族主义”道阻且长。作者在书中描绘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经历、思想与情感让我们不忍心站在道德的高地,对其民族主义行为加以指责与批判。
只有没有母亲的人才知道母亲是什么,只有没有土地的人才知道土地意味着什么。”魁北克一个年轻的人类学女学生说:“我们只是想要像成年人那样被对待,而不是像孩子那样。”在贫穷、落后、战乱中,人们有这样普遍的诉求:只有拥有自己的土地,一个民族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类、完整的自己。
我们不是他们,我们不在那样的地方、拥有那样的经历,因此可以高谈“公民民族主义”。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前,“公民民族主义”该如何发展与实现?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十):种族民族主义的狂热与残酷
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德国,在文字与图片的指引下,我跟随作者叶礼庭,深入这六个于我而言分外陌生的国家和地区,探讨种族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公民民族主义的威胁与挑战。 作者出生在多伦多一户国际家庭,祖先多为加拿大、俄罗斯两国著名政治人物。其父作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外交官,曾任驻南斯拉夫、北约及驻联合国大使。作者本人从牛津毕业后在多所欧洲、北美洲高校任教,丰富的海外求学与职业生涯消解了他的民族主义信仰。作为一名世界主义者,他追求移居不同国家的生活方式,倡导混血优于同族,杂交胜过地方化的文化伦理。但他的民族融合理论并不超越民族,因为“世界主义精神最终仍依赖于民族国家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因此,他自称公民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维系国家的是公民身份,而非种族界定的归属;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根源,而是法律。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国家并不由单一民族构成,尽管同族也无法自行消解分歧,种族之间仍然以血缘与归属作为划分标准。同一条街原本相安无事的街坊邻居,因为一句煽动人心的民族主义口号,便愚蠢地将匕首刺入对方的胸膛。 当然,在作者考察的国家和地区,种族民族主义冲突要狂热与残酷得多:战死沙场的贝尔法斯特16岁少年,为了阿尔斯特忠诚主义,心甘情愿伪造服役年龄;澳大利亚的郊区女孩,因为“贴近生命”的归属感,成为穿行在库尔德斯坦山区的游击队员;塞尔维亚族民兵在克罗地亚族村落大肆进行种族清洗,而这些被炮轰的小镇极有可能也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年轻的男性民族主义者热爱废墟与毁灭,沉醉于屁股上枪支的力量和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深度快感…… 学界与政界似乎一直无法清晰界定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异同。在许多学者眼中,“对祖国的热爱”等同于“对民族的忠诚”,民族主义似乎只是极端爱国主义的延伸。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似乎狭隘得多,它苛求于民族与宗教信仰的纯粹性,为了血缘或思想上的纯正,可以置家国于不顾,可以对山河破碎视而不见。这份对民族家园的渴望明显超出理性范围,露出骇人的疯狂。 由于对作者所举六地的政经文史背景知之甚少,加上对民族主义概念不甚明了,在阅读过程中,我不得不一次次查找资料,翻看地图,冗繁的查阅过程大大降低了精神愉悦感。也因为一知半解,我终究无法精确地阐述作者的思想,只能通过只字片语的摘抄来体现其视角的独特与深刻。书评的最后,写下于我而言最具启发意义的一段文字,它不仅是对民族主义的疑惑,更是对人性的反思,当然,还有对世界主义的温和期盼: “自由派的文明——法治而非人治、以辩论代替武力、以妥协代替暴力——是与人类本性深深对抗的,只有通过与人类本性进行最为坚忍的斗争才能达致和延续。自由派的美德——宽容、妥协、理性——仍像以前一样有价值,但它们难以灌输给那些因恐惧而疯狂、因复仇而疯狂的人们”。 推荐指数:四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