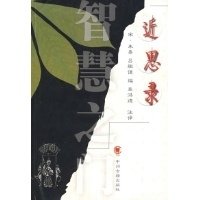近思录读后感锦集
《近思录》是一本由(宋)朱熹//吕祖谦著作,中州古籍出版的468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00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思录》精选点评:
●真实性有两种,一是科学世界之真实。一是意义世界之真实。事实与价值的鸿沟可以存在,也可以从来都没有。比起事实世界里的整饬有序,纯粹的意义世界则显得十足可爱而动人。(前段时间翻了一番,暂时就这样过了)
●只前5章尚好,其余就不合时宜,不合现代了……!
●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
●必有事焉
●理学入门必读
●性理根基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不好在于误解佛法。
●于儒学爱之深责之切,读这本近思录感慨更深。那么多的糟粕,近天理远人欲的宏愿与存天理灭人欲的恐怖只就一线之隔。告诫自己,万物取一片足矣,儒家亦然。
●给自己在思想上多点素养,读这个不错呢!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近思录》读后感(一):学以为己——自我检讨读书方式
看的是kindle的公版书,整个看完之后收获并不大,可能和看的是原文并没有注释有关系。 感悟最深的应该是2.10:
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知于人也。伊川先生谓方道辅曰: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到也。求入其门不由经乎?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之蔽,人人皆是。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觊足下由经以求道,勉之又勉,异日见卓尔有立于前,然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也。
这里面所讲的今之学者的做法,我也有犯:不管什么书,都喜欢看那么两三行就不看了,转而去寻找相关的书评,相关的介绍。并总以看过这些东西作为读过一本书的标准。
仔细想想,我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耐心真的去读完一本书了。经常都是看一眼,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作为常规动作。却忽略了自己找书评,找介绍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并不比认真读一本书所花费的少的事实。
文以载道,的确是该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
《近思录》读后感(二):《近思录》札记(卷一 道体)
一、元亨利贞对应于仁义礼智信
元代表本体与起始,有了元就有了后三者,同样的关系类比到仁与其他四者,仁是主体,其余是四肢,用仁这个概念来总领儒家的概念。
天道在阴阳,地道在柔刚,人道在仁义。具备了仁义就是可以磅万物为一,大通与万物(类似道家的同于大通,与造物游)
二、规矩是重要的。
这一点与性善论结合在一起。人性本善,只有自暴自弃(自我戕害与自我抛弃)之人才没有希望。
即使是至愚之人在外界风尚的熏陶之下也会变好。而那些不会进步的人往往不是没有力量的小人。小人生活在社会当中,受到“王法”社会规范的制约,所以很少犯过错(小人革面),与常人表现一样。规矩在这里起到了避免普通人以及小人堕落的作用。换句话来说,真正做坏事的是那些强有力但是思想不正确的人。
三、极其强烈的把社会的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神圣化的特点,人伦的秩序比为天道的运转。
四、爱智慧,爱自然与和谐。程颢 曾经因为发现自然界的关系都是两两对立的,而这种和谐不是人安排,是本征的,高兴的手舞足蹈。
五、性善论的补充与修正。引人了“才”的概念,“才”是人的禀赋,是“气”的体现。人是由气聚而成形的,而气可以分为清浊,所以,人性是善的但是每个人的才具不同,恶是这样产生的。
六、世界是由“气”构成的
《近思录》读后感(三):省 察
省察
佛家神秀有偈日:
身似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冬瓜孥钝,常觉此偈,比之六祖“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偈,胜在可操作性强。禅学理学,痕迹相近。神秀此意在理学道来,就是省察。
阳明讲,有些人,是“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不知昼夜”。七年前,初读此话,只觉堪百般玩味。七年后,再念及此十四字,揽镜观心,心犹蒙尘;揽镜照人,性相近,习相远,照仁者见仁,照智者见智,照了王八蛋,只见王八蛋。
其实论及省察,冬瓜十分敬畏,不因那满天星斗,亦不为鸟道德法则,只为五千年人心皆近似,而先哲在前,目光如炬,轻轻拈出这两个字来,给不知昼夜之人以光的指引。而多少脸孔,犹自不知,茫然随波逐流;又有多少人,如冬瓜般,知而不行,不能吸收转化为人生意义的一部分,犹是不知。
冬瓜一直以为,省察是理学修身工夫第一要诀。但今日只论省察,不谈克制,冬瓜亦不认同阳明所讲“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搜寻追究出来,定要拨去病跟,用不复起,方始为快”。仁者省仁,智者省智,不必“一日三省吾身”,一日一省,人即知了昼夜。王八蛋知了省察,亦能修成千年乌龟王八蛋。
《近思录》读后感(四):【转】汤元宋:《近思录》编纂时间考
摘要: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和吕祖谦于寒泉之会时合辑《近思录》,乃是理学史上一大事件,但关于《近思录》编纂的具体时间,至今仍有所争议。争议之来源,乃是关于编纂时间的记录,有不同的文献来源。过往学者虽有留意到文献之间的冲突,但大多在文献之间小心折中,而未有能大胆假设文献本身记录有误者。本文通过细致分析各则文献之间的矛盾,指出导致这一争论的根源皆因《吕祖谦年谱》中一条文献所致,并对此条文献正误提出来合理的推断。 关键词:吕祖谦;近思录;寒泉之会 作者简介:汤元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一、文献 关于《近思录》编纂年月最重要的文献来自三方面,分别来自朱熹《书近思录后》、吕祖谦《入闽录》和吕乔年为吕祖谦所作之《年谱》。 朱熹的《书近思录后》记载了《近思录》编纂的时间终点为当年五月五日: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 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 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谨识。 严格而言,《近思录》正文的编纂与朱熹作《书近思录后》一文,或有数日之隔,但若以此文完成视为《近思录》编辑事件的完成标志,也无不可。关键在于,无论《近思录》完成于五月五日,或者五月之初,都与现存其他文献并不冲突,考订古人年份异同,若无文献冲突,且于大事无碍者,自可不必深究。 吕祖谦的《入闽录》体例近似日记,专记吕祖谦此次入闽武夷之行,可惜今无全本,但因其逐日记录行程,环环相扣,所以残本可信度极高。此录记载了吕祖谦武夷之行的几大关键时间点: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早发婺州。 二十八日……入建宁府浦城县界。 四月初一,入五夫路……访朱元晦,馆于书室。 此节所论五夫路即朱熹常年所居之五夫里,而书室或为紫阳书室,即刘子羽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为朱熹母子所建。五夫里距寒泉精舍,脚程约在一两日间。 《入闽录》可以确定如下几点:吕祖谦出发之日乃是三月二十一,入闽之日乃是三月二十八,而与朱熹首会之日,乃是四月一日。此录随后记载四月初一至初五,吕祖谦五夫附近游玩访友,其中初三、初四两日朱熹同游。自初六日后,《入闽录》缺。 因为现存《入闽录》所记吕祖谦入闽与朱熹相会的首个落脚点在五夫,因此为后人提供的一个线索在于将二人的相见视为两段或两处,首处相会点在五夫路的书室,在此地应有一段时间跨度,第二处相会点在建阳的寒泉精舍。此一问题也将关系到《近思录》究竟是作于五夫路书室,还是建阳寒泉精舍,以及对一些文献的解读。 最可疑的文献来自吕乔年所作之《年谱》,现录此年谱于淳熙二年乙未前两条: 春,在明招。 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访朱编修元晦,潘叔昌从。留月余,同观关、洛 书,辑《近思录》。朱编修送公于信州鹅湖,陆子寿、子静、刘子澄,及江 浙诸友皆会。留止旬日,归。至三衢,又留旬日乃归。有《入闽录》。 吕乔年所记年谱最重要的一条,乃是加入了四月二十一日这一时间点,且是孤证。此条孤证虽在后人的解读中,使之与其他文献调和,但仍然有所疑点。 《近思录》的编纂在吕祖谦武夷之行整个行程之中,因此还需要明确吕祖谦离开福建的时间点。《年谱》简单作“朱编修送公于信州鹅湖”,束景南认为当是五月十六日从建阳寒泉出发。 此说的证据主要也来自吕祖谦本人: 某以五月半后,同朱丈出闽,下旬至鹅湖。 束景南认为“五月半后”当指的五月十六日,如此实指或可商榷,但若将之作为五月十六至十九日之间,当无疑问。 束景南的另外一个观点,乃是认为抵达寒泉精舍的时间应为四月二十四日,其理由是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中有“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之说,束认为“旬日”当确指十日,因此由《书近思录后》中五月五日倒推十日,即当为四月二十四日。 刘玉民也持此说,认为“四月二十四日,在寒泉精舍,朱熹、吕祖谦二人开始编订《近思录》”。 以上乃是时间节点,关于朱熹、吕祖谦相聚时间跨度的文献出处另有数段,除了上述“留止旬日”、“留月余”。吕祖谦另有两段文字可供参考: 某自春来为建宁之行【“来”,四库本作“末”。】,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出至鹅湖。 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 甚觉有益。 吕祖谦此两段文字,揭示了两点,其一是其在建宁两月余,与朱熹相聚四十余日,其余十余日二人并未同游或同处,其二是二人相聚四十余日,亦非一段或一处。前引《书近思录后》所记“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则上文吕祖谦此行与朱熹相遇分别在五夫书室和寒泉精舍,不为无据。而《年谱》所记“留月余,同观关、洛书,辑《近思录》”,所对应的当是两处,“留月余”对应“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同观关、洛书,辑《近思录》”对应“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朱熹所谓“过予”之“过”字,也正说明此行吕祖谦非仅拜访朱熹,更非仅停留于寒泉精舍,而《入闽录》所记的笔法,更似吕祖谦本人的寻访日记,非止于朱熹一人或《近思录》一事。 在整个寒泉之会中,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即朱熹与吕祖谦共同考订《蓝田吕氏乡约》和《蓝田吕氏乡仪》。此事朱熹曾专为两书作跋,文末皆有“淳熙乙未四月甲子,朱熹识”之语。四月甲子,即四月十三日,束景南在《朱熹年谱长编》中,在此一日条下记“考订《乡约》、《乡仪》作者,为作跋”。 但作跋之日虽仅标示一天,但考订却可能连续数日。刘玉民便认为:“初六日至十三日,二人共同考订《吕氏乡约》、《蓝田吕氏乡仪》。” 很显然,刘说乃是将吕祖谦《入闽录》所缺的初六日,视为考订起点,这与束景南之一日说,皆为文献不足征之下的猜测。 二、诸说 本节将对前辈的结论稍作梳理评议,并指出各陈己说的关键,乃是因《年谱》所记四月二十一日之事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带来。 对上述文献之冲突,最早提出质疑的乃是陈荣捷。陈氏在《吕东莱访朱熹于寒泉精舍》一文中曾指出“《年谱》谓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而《入闽录》则谓三月二十一早发,显是冲突。”而其理由乃是“浙江东阳郡金华县离福建建阳约二百五十公里。至少需时八九日。必无四月二十一日动程,而能于五月五日完成《近思录》之理”。因此陈氏认为“编辑《近思录》之工作,必起于五夫里。随后到建阳县之寒泉精舍,‘留止旬日’”。 其实陈氏认为《近思录》编辑的时间不止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中所言的“留止旬日”,而应起于五夫,此说亦可见清人朱栻之《史传三编》:“祖谦欲编《近思录》,因与朱子同止寒泉精舍,分类抉微,一月而成。” 朱栻与陈荣捷皆认为《近思录》之编纂,不止旬日。 陈氏虽未详细辨析其他材料,亦未提出《年谱》错误的原因所在,但依照最核心的《入闽录》和《书近思录后》两条材料,判断《年谱》有误的结论,本可作为定论,直到虞万里直接针对陈氏之说,提出新解。 虞万里最主要的证据是改变了年谱“四月二十一,如武夷访朱编修元晦”条中“如”的字面解释。虞氏认为:“‘如’应是‘到’之义,亦即正式到寒泉精舍与朱熹共同编纂之日,不能如陈氏理解为‘动程’。”虞氏指出,较为合理之解释,应是朱、吕自四月一日在五夫相会游胜之初,就已萌发编纂《近思录》之设想。及至四月二十一日,吕氏至精舍才进行具体编辑工作,“留止旬日”(《书近思录后》),相与读四子书,遂遴选汇编,至“五月五日”(《书近思录后》)草成,费时一旬有余,若统算前期酝酿筹划阶段,则前后有一个月左右。 很显然,虞氏虽然不同意陈氏视《年谱》此条有误的论断,却继承了将《近思录》的编纂分为五夫路与寒泉精舍两段的观点。杜海军在《吕祖谦年谱》中,继承了虞万里训“如”为“到”的观点,认为“《年谱》所云(四月二十一日)盖至寒泉精舍时间”。 此处先辨析虞训“如”为抵达、而非陈荣捷所谓之出发是否合理。吕祖谦《年谱》中所用“如”字有数十处,其意义当前后一致。但《年谱》中多数例子为“某月,如某地”,而两地之间距离多不过数日,则“如”字究竟表示出发或者抵达,皆难以找到明确的旁证。《年谱》中“归自”、“自某地归”等术语亦同此理,皆不易判断是指的出发还是抵达。 较为理想的证据在淳熙元年甲午八月二十八日条下:“如越。潘叔度偕行。”此次出行,吕祖谦恰有《入越录》为记。《入越录》起首之句便是:“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华与潘叔度为会稽之游。” 二十八日,吕祖谦尚未抵达会稽,可见年谱之“如”当作“出发”,而非“抵达”解。 稍有疑问者,在于《入越录》二十日有“五里,至关头,南折入会稽路”语,或可解释为此日虽未到会稽城,但已入会稽行政区(路)境内。但此处路当为道路,而非行政区之路,如同段另有“十里,自驿路北折入香山路”、《入闽记》所记“五夫路”等。若以行政区而言,南宋会稽属绍兴府、金华属婺州,皆属两浙东路,即《宋史·地理志》所言:“绍兴、庆元、瑞安三府,婺、台、衢、处四州为东路。”《 入越录》在三十日亦写到:“过义乌、东阳、浦江、永康四县巡检寨,婺、越界焉。五里,邵家湾。”越即绍兴府之别称,“绍兴府,本越州”。可见出发三日后,吕祖谦方到婺州与绍兴府边界,检谭其骧著《中国历史地图集》图,邵家湾亦在绍兴府与婺州边界之上。 稍可补充的是,杜海军认为《年谱》所记乾道五年已丑“(八月)二十七日,如三衢见汪公圣锡”有误,当改为九月,因为“吕祖谦所讲三衢之行及之官日期恰与九月相符”。但若将年谱八月二十七日视为出发,则抵达三衢在九月,则年谱所记未必有误。 但除训诂外,更强有力的证据仍然应来自核心文献中时间的彼此冲突。很显然,若将《年谱》四月二十一日的“如”解释为“出发”,则逻辑如陈荣捷所言,此条自然有误。若按虞万里将之解释为“抵达”,实际上仍然有误。《年谱》所记“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访朱编修元晦,潘叔昌从。留月余,同观关、洛书,辑《近思录》。”而从四月二十一日其计算,“留月余”,则吕祖谦在寒泉精舍最少需待至五月二十一日后,而实际上如上节所言,最晚于五月十六日至十九日间,吕祖谦便已经和朱熹离开寒泉精舍,出发前往信州鹅湖。 此外如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的叙述,亦属有误。束景南在列举《入闽录》所记四月前五日诸条后,直言“在以后的十来天中,两人在寒泉精舍共读周、程、张的著作,从四子的十四种书中辑出六百二十二条,分为十四类,在五月五日编成了《近思录》一书。”此说中“十来天”应是来自《书近思录后》文中“留止旬日”,但束景南将此简单地嫁接在《入闽录》所存四月五日最后一条之后,所谓“在以后的十来天中”之说,则显然疏忽了四月六日至五月五日,远不止“旬日”或“十来天”。而在后出版的《朱熹年谱长编》中,束氏所论要较《朱子大传》更为准确。 三、推断 对于引起争议的《年谱》四月二十一日之说,一个大胆但合理的推断是此条即可能原作三月二十一日,至于其原因是吕乔年记忆有误、下笔有误、还是刊刻之误,则不得而知。 此种推断理由有三。其一在于《年谱》的体例,吕乔年此条以《入闽录》结尾,说明他编纂年谱时即使手头无《入闽录》参考,也必定是知晓吕祖谦此番入闽全程大略。《入闽录》所记之事,起于离开婺州,也很可能包括最终返回婺州,而非仅止于福建境内,因此《年谱》此条所记之事,如鹅湖之会、访三衢等,也皆有可能在《入闽录》记载范围内,即便《入闽录》不记离开福建后续之事,此番吕祖谦出行也当为视为一整体——始于离开婺州,终于归自三衢。既然《入闽录》起于三月二十一日,《年谱》不记始,却代之以中段的时间点四月二十一,则不能不令人起疑。 第二条理由在于前述吕祖谦《与邢邦用》书信中有“某自春来为建宁之行”一句,“春来”二字在宋人语录、文集中并不常用,更重要的证据是从逻辑上看,南宋淳熙年间以正月为春,以四月为夏,若“春来”不误,则《年谱》所记“四月二十一,如武夷访朱编修元晦”必误,因为四月已属“夏来”。但“春”字古籍刊刻不易误,从此条也可知吕祖谦在《与邢邦用》书信中所言建宁之行当在春季,而“来”字与“末”字又形似易混,此段四库本即作“末”,合理的推断在于此处“春来”或为“春末”,如此则“春末”之说与所推断《入闽录》起于三月二十一日相合。 第三条理由在于吕祖谦文献中,同样有将此年入闽之事“三月”误作“四月”的例子。在《东莱吕太史文集》卷第一有《夜宿浦城鱼梁徐删定之子出示林谦之挽其父二诗时谦之方按刑广东有怀次韵》一诗,目录下小字作“淳熙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而《入闽录》宋版补录部分二十八日条下云:“入建宁府浦城县界内。……十里,鱼梁岭。……进士徐良肱来谒”,则此诗必作于《入闽录》所记是二十八日,进士徐良肱或即是徐删定之子。《入闽录》宋版补录部分极为零星,且皆不标月份。此条虽未标此二十八日是几月,但依行程路线,必在三月二十八日无疑,此条所记“入建宁府浦城县界内”、“鱼梁岭”(当在鱼梁驿附近)、下一条二十九日所记“浦城县”,皆为循序渐进入闽线路。因此,可以断定《文集》目录乃是误将三月二十八日误作四月二十八日。《吕祖谦年谱》中留意到《入闽录》此条的情况下,或因《入闽录》此条未标月份,依旧采纳文集目录所标时间,将此诗定为四月二十八日所作,当误。 寒泉之会的全部细节,或许只有等待全本《入闽录》等文献的出现才能最终定论。本文的目的,不仅在于辨析现有文献的真伪,也希望以此为例,展示不同来源的文献,记误、笔误、刻误的古人记述,是如何在层层累加中,造成后人各式解读。这种前人无意之失,所能带来的有意误读尚且如此之多,那有意的扭曲、编造、篡改,所带来的误读更不知凡几。读史之难、著述之慎,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