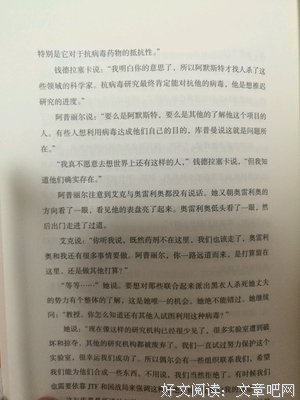《旺达》观后感精选
《旺达》是一部由芭芭拉·洛登执导,芭芭拉·洛登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旺达》观后感(一):震惊
看完被震惊了,这么好的片子竟然在美国默默无闻!巧的是,之前刚看了她老公的 The Visitors, Wanda 很明显的细腻了很多,可以看作是女性现实主义的邦尼和克莱德。
很多细节余味无穷。一直以为索菲亚科波拉让人惊艳,原来早有珠玉在前。可惜 Barbara Loden 一生竟然只导了这一部片子,才48岁就死于乳腺癌,让人唏嘘。
《旺达》观后感(二):无与伦比
偏爱战争、暴力题材的凯瑟琳·毕格罗非常强悍,凭借拆弹部队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史上第一位女导演)。从未觉得她是才女,也不喜欢她的电影。才女是创作天才,含蓄、细腻展现人性的深度,不是左右逢源的机器、流水线。 表现亡命鸳鸯的公路片,人们首先会想到《雌雄大盗》《天生杀人狂》,以艺术品质而言,《旺达》无与伦比。 寄人篱下、找工作的苦楚、艰难,被玩弄抛弃、掉钱包的凄惶,逆来顺受、拼命搭上亡命徒的战车;想多吃一些,男友要走,立刻停下。笨拙地试图讨好男友,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诸如此类的细节让人想起《大路》(1954)。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甜蜜、悲怆。 从被冷眼到被重视、关爱,旺达刀尖上的幸福比太阳雨还要短暂。鬼使神差躲过一劫,男友已命丧当场。 才女的字典里没有自恋,那简直是侮辱。对人物饱含同情,但绝不沉溺,很有分寸。几十年过去,同类影片星光璀璨,但人们依旧无法忘怀《旺达》。
《旺达》观后感(三):雌雄大盗的雌性版
开头有点儿像贾樟柯的片子,旺达住在噪音严重的煤矿上一所带门廊的小房子里,婴儿哭,机器吵,跟丈夫离婚了,找不着工作,闹得跟不专业的小妓女似的,结果等她再回到那家酒吧,却被个杀人犯拐走了。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没处安置是什么感觉,就是旺达着感觉,她就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糊里糊涂地跟着茶色眼镜走了。
一路之上,她与酷酷的茶色眼镜倒也有那么点生情,特别是如果没有一个男人关心过她的头发、穿着,没有一个男人赞扬过她,你做的不错——她就需要那么一丁点儿肯定,跟救命稻草似的。
结果,茶色眼镜去抢劫第三帝国银行的路上,旺达开车却跟丢了。这一来却救了她,茶色眼镜被当场击毙。
她在人群中、电视上,看到那个世界上最相关的人死相难看。
这好像是《邦妮与克莱德》的70版,或者说是东欧版本,主演Babara Loden也是剧本写作和导演,里面有些镜头语言和人的旺达的那种无助感令人沉重。当一个人被世界抛弃并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世界的边缘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旺达的结局是什么呢?也很抒情气质。虽然是美国出品,但不很美国。自己看吧。
《旺达》观后感(四):她的生存迷惘,是对我们内心不安的投射!
故事其实挺简单,影像技术层面放在当代来看也并不复杂,它的运用却非常准确、到位,但电影的灵魂人物“旺达”却让这部作品显得极其复杂,作为女性的旺达,她生存的迷惘贯穿在整部作品。她是特别的,从与丈夫的淡定分手可以窥见她生存的迷惘之下对思考男性存在于自我意义后的一种冷静,她既非将自己置于一个柔弱的女性面,(当面临缺钱的生存困境)又非坚强的将自己伪装起来,她是真实的,她也是活在自我世界的。从遭遇抢劫犯并被卷入,她与抢劫犯之间的这一段故事,我们看见她的生存带着蒲公英似的无自主意识,抢劫犯正是那一缕吹走蒲公英的风,而吹着的风与被风吹着的蒲公英成为两个陷入同样生存迷惘生命的一场命运交汇。而二者的相处中,男女差异,及微妙的生存现实与彼此依赖产生的一种关系,成为旺达在抢劫犯抢劫银行被击毙后,一种失落迷茫悲伤无声而出包裹着她此刻又回归独身一人的生存现实中。旺达爱那个男人吗?显然并不爱,她只是在短暂的生存依赖中,与这个陌生人有了一段牵袢,这个男人在她短暂的生命过程中排解了她的孤独,尽管这个男人如此可恶又如此与她不同(或许是男女差异,或许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结果便是,男人的逝去,让旺达陷入更深层次的生存迷惘! 电影不能单纯归类于女性电影,我其实觉得旺达这样的人物又或者抢劫犯这个人物,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她/他性别无关年龄无关,生存的现实中迷惘与孤独扼住了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索,他们只是在迷失,既迷失在外在世界,又迷失在内心世界,然而他们是否有何不同?并没有。人与人的相似在于灵魂...
《旺达》观后感(五):旺达出走之后
影片开头旺达的“出走”,让我想起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出走”,我下意识的会将她们进行比照,但时代背景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的不同,也让我认为,相较于娜拉在戏剧最后有着“作为人的觉醒”、“女性作为个体的意识”,旺达这个角色在影片一开始便是一个有着强烈个体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女性。导演并没有将旺达只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女性”而已,她呈现出复杂的人:与所处的阶层有关、与性别意识有关的复杂个体。
她或许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底层女性的代表:一方面,她被制度所捆绑,她在缺乏合理制度保障的工厂体系中选择妥协,她在进入城市时也会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她作为个体,又强烈地意识到结构性的不公给她的“出走”所带来的制约。所以,她更像是一个彷徨在“妥协”与“自主选择”中的双重困境者。
旺达极具个体意识地出走并不能使她摆脱社会所附加在个体之上的影响,这似乎是对在新自由主义裹挟下的个人主义的一次反思但也并不是一场批驳与否定,或者说这部电影是对时代的一次提问:如何更好地缓解个体自由与社会结构间的冲突与矛盾。
再回到影片开头,她出走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在观影的时候一直想要替自己回答的问题:
借用卡夫卡《启程》中的话来形容——“你去哪里?” “不知道,只有不停地离开这里,才能到达目的地。” “那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我说过了,离开这里就是我的目的地。”
《旺达》观后感(六):旺达
这是今晚在深圳空体放映的一部电影,看完之后听了几个观众发表的看法,其实都不是很同意,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到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在回家的路上才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和大对数这类电影一样,看完一定会有一部分男性认为旺达不自尊自爱,自己明明有选择为何偏偏选择依附于男性。而一部分女性会认为旺达处于一个男权社会,她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这样的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她其实没有选择。
但是我觉得旺达其实根本不想选择什么,她只是自然而然就走到了这一步,她对男人其实也不存在什么依恋或者依附的感情,她并非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她自己其实也不断地在男性身上得到好处,她能非常自然地问别人讨钱,讨酒喝,不觉得有什么羞耻的地方,她身上其实是有一种生命力在的,我甚至在她身上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女权,她其实是最不依附男性的,她这些行为只是为了在男性身上不断吸取生存的养分,是没有感情根基的。
关于结局,有人说旺达最终选择了堕落,也有人说她在觉醒。但我只是觉得这个结局其实没有什么特定意义,就只是旺达人生中最普通不过的一个节点。她先是感到局促跟不自在,慢慢地,她就开始接过男人递过来的烟,开始拿起面包吃了起来。对旺达来说,没有什么比填饱自己的肚子和抽烟喝酒来得更重要了。和这个男人离婚毫不留情,被那个男人在路中间抛下继续去买冰淇淋吃去逛街看电影,抢银行失败同伴死亡之后身边又迅速出现另外一个男人,这样的事情,可能在电影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并且在电影之后也会继续发生,结局只是电影的结局,不是旺达的结局,对旺达来说,她今后的一生还会出现无数个男人,她会继续不知羞耻地向别人讨酒喝,用自己身体和男人做交易。
《旺达》观后感(七):不朽情缘什么时间点容易爆分,怎么触发滴血解铃还须系铃人
日常玩不朽情缘中我们总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游戏分数快消耗光了,突然变的很好打,很快不到10分钟又打回来了,甚至可能还能翻一番,但到一定程度如果我们仍然继续玩我们会输掉所有的分数。这就是游戏的周期规律。所以如果你问我不朽情缘什么时间点容易爆分及怎么触发滴血,那么找到不朽情缘爆分时间其实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里也是涉及到了很多细节问题的,今天就来谈谈不朽情缘一些实用的技巧攻略,权当抛砖引玉。
首先是瓶台的爆率与吐芬比例要达标,现在可选的台子有很多,但不是什么地方都值得尝试。就比如人烟稀少的地方因为游戏池积累的速度慢,爆率变化慢,有时候可能好几天都处于吃芬阶段。另外就是瓶台得吐芬比例,有些地方吃的多吐的少,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想要拿高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想要更准确掌握不朽情缘什么时间点容易爆分一个好的瓶台必不可少。诸如天博(aa3398典夕欧木)。
当你拥有了一个达标的台子后,可见图成功就有类基本的保障,那么接下来就是讨论不朽情缘技巧攻略问题了。很多人会问不朽情缘什么时间点容易爆分,其实就是问什么时候爆率最高,我认为要判断是比较难的,只能说要长期摸索就慢慢有判断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要熬时间,所以建议入场先低分试探5分钟左右,这里举个例子来描述:比如分三个档3、6、12,每个档旋转200次,如果没有出高分就提高一个档,当然中途任何环节出高分,就一定要调回3或者离场,另外每次玩的时候确保足够的旋转次数,比如至少保证1000转。
高爆吉利入口aa3398 典☪❂♏关于不朽情缘什么时间点容易爆分及怎么触发滴血技巧攻略相信看完本文后你可能也会有所领悟,希望分享的能为您排忧解惑。茫茫人海,如果你能看到本帖并且一直不如意,那么不妨按照本帖子的思路坚持下,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最后记住分享的,相信只要努力必有奇迹。 不奋斗就是每天都很容易,可一年一年越来越难。能干的人,不在情绪上计较,只在做事上认真;无能的人!不在做事上认真,只在情绪上计较。拼一个春夏秋冬!赢一个无悔人生!早安!—————献给所有努力的人。
《旺达》观后感(八):自由之痒
61年前路易马勒的「情人们」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作品,导演策划了一场出逃,已为人妻的让娜对于沉闷压抑的生活让她喘不过气,在丈夫和友人面前她不顾道德的与情人逃离。导演将观众置于诱惑之中,甚至将偷情出逃这一主题刻意的营造出一种浪漫主义
Thelma & Louise (1991)52年前的「雌雄大盗」则充满自由主义,影片另一个名字「我们没有明天」,以极端的方式对抗社会旧习,注定悲剧的宿命欢唱起命运的赞歌.「陌路狂花」的女权成长、「天生杀人狂」的暴力爱情也都以一种极端的姿态诠释自由的理想主义。
49年前的「旺达」既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有自由主义的浪漫,结果却则显得真实而绝望.
Wanda (1970)Wanda从梦中醒来,屋内的抱怨声,小孩的哭啼声,丈夫的漠不关心,房子在一片嘈杂而喧闹的矿区。汽车挖掘机24小时的运转着,Wanda从远处一大片矿区走进镜头,又走出镜头。她从一位捡煤的矿工那讨到一些钱,开始她重复而又虚无的生活.
她从毫无生命力的矿厂坐车来到都市,仍旧是颓废、绝望、无所适从。摄影机纪录片式的跟随,噪点中模糊的光影、跳动的红色、孤零零的冰淇凌...旺达面无表情的脸,哀愁的眼神下是一条挣扎的生命,在现实的世界里寻找光亮.
《旺达》观后感(九):黑色、红色与冰激凌
制作成本仅10万美元的《旺达》,拍摄剧组只有3个人(导演兼主演洛登、摄影师兼剪辑师Nicholas T. Proferes、以及灯光师兼录音师Lars Hedman),如果说一般电影的剧组是个“交响乐团”,那《旺达》俨然出自一支摇滚乐队,而洛登就是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
《旺达》讲述了一位和丈夫住在一片煤矿地中的女子在脱离了家庭和婚姻以后,独自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苟活着,最终无意中勾结上了一个银行劫匪并展开了一段“雌雄大盗”式的故事。在开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中,穿着一身白色的旺达独自行走在一大片黑漆漆的矿地里,在远处看着的摄影机里只是一个小点,它缓缓地在远处跟着她的步伐。纵观全片,旺达都是一个极为被动的角色,她对自己遭到的伤害或者不公都表现出了异常的漠然,也导致了其最终的宿命。
电影的这一特点让很多观众非常费解,甚至成为了讨厌角色或者影片的理由。在罗伯特·麦基式的剧作体系中,一个主动寻找目标(goal)的角色才能被称为电影的主角(protagonist),而被动的人则无法驱动电影。这是一个有道理但并不完全通用的方针,但似乎已经成了电影学院老师授课时的一个共知。我曾在上课时和老师反复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可惜最终谁都没有说服对方。被动的角色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她/他是否能够成为电影的主角?在《旺达》中,你很难说女主角有任何的所谓目标或者一个确定的前进方向。甚至在第三幕和劫匪丹尼斯先生(Michael Higgins 饰)进城执行一场银行抢劫时,单独驾车跟在丹尼斯后面的旺达也因为跟丢了车子而迷失了方向,最终只能在警方的警戒线外默默看着行动失败。
回答上面的问题,如果说《旺达》有什么主旨宣言的话,那便是为所有的被动者所作:被动的人也可以是电影的主角,只要我们足够敏感,被动者的生活依旧可以拍出动人的电影。旺达的生活或许看上去是了无生气的,无所事事的,虽然这点毋庸置疑,但这不代表她的生活就不是美丽的,最起码不代表这种生活不值得被拍摄。电影的镜头始终认真地观察着,感受着,而丝毫不多愁善感或带有抱有批判。
或许一个场景能说明这点:旺达被一个男人扔在冰淇淋店前,变焦镜头从远处的坡上推向车子,它停在店铺门前扔下旺达,迅速开走了;旺达看着四周的矿地,一会儿之后,一双手递上一支白色的甜筒;她看了看甜筒,上面的冰淇淋有着优美的螺旋形,多么单纯的一件事物,就如旺达本人。然而很快电影就切到了下一个场景,我们看不到旺达吃掉这个甜筒,因为这会让电影变得太过怜悯:“哦,我是个可怜的姑娘,被扔在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吃着冰淇淋!” 旺达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怜悯,她继续以她的方式游荡着。当然,旺达也爱美食(这就是她为什么会被扔下车),遇上丹尼斯先生后,她津津有味地在小餐厅吃着意面和面包,还颇有幽默感地告诉他她最爱吃的面包部位,即便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个男人是个在逃罪犯。
作为独立电影的《旺达》被称为有着 “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般的影像,技术层面上看确实如此,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其风格化的色彩展现,显然洛登在影像上有着更绝对的控制权。之前已经提到的黑色煤矿地,它粗旷的表面和电影本身的胶片颗粒感一脉相承。电影的主色调则是青色:旺达的衬衫、房间的墙;而另外一个抓人的颜色则是夺目的大红,或许是作为一种标记危险的颜色,它时不时出现在旺达旅途中遇到的男人身边:开场的矿地里出现了一辆红色卡车;第一个扔下她的男人把一个大红色的套西服的袋子挂在车里;旺达被偷走钱的电影院门口有着大红色的门,她走了进去;意大利面酱和汉堡包里的番茄是大红的...... 这些颜色的反复出现,预示着某种思维定式的存在。
包括与丹尼斯先生如黑色电影般的情节在内,旺达在电影中的轨迹似乎都遵循着一个定式:遇上男人,并没有结果地最终分离,如此循环...... 即便洛登以引入丹尼斯,另一个游走在道德边缘的悲情人物,将电影带向了另一个岔路口,我们最终依旧回归到原点。旺达遇上一个试图诱奸她的军人,他开着辆大红色的敞篷车,而此时在一个全景镜头中,汽车(与它刺眼的红色)驾驶在一片白色的荒地上,和开场时的黑与白刚好反了过来。在此,旺达会在全片第一次试图掌控自己的生命,她拼命挣脱着军人,逃离了红色的车,接下来镜头切到她跑进一片绿色的树林,鲜活的绿色终于包围着她。但直到最后,洛登依旧没给出关于未来的答复,或许谁都不能?或许谁都心知肚明。我们只见在一家酒吧,舞台上唱着欢快的歌谣,旺达围在一群陌生人间默默喝酒,电影便如《四百击》的结尾一样定格在她的脸上,结束了。
《旺达》已发行The Criterion Collection蓝光碟
《旺达》观后感(十):唐·德里罗谈《旺达》:远处的女人
当现实上升到奇观的层面,人们会说:「这事儿跟电影一样。」《旺达》抓住了这种电影感并让它彻底变质——唐·德里罗
【译者按】本文为唐·德里罗所作,题为《Woman in the Distance》,刊登在文学杂志《Black Clock》第四期(已停刊),可以在这里看到原文。唐·德里罗非常敏锐地探察到了《旺达》的气质,他在标题里就提到「距离」这词,一如杜拉斯所言「这里,间距消失了」(这是巧合吗?)。包括他还说「这是一部有颜色的黑白片」,以及「她是被设计出来的一片空无」。在我看来,旺达的「空」,一如李斯佩克朵「对空的痴迷」(科尔姆·托宾语);旺达的「贫穷」,一如「《星辰时刻》和玛卡贝娅的贫穷」(埃莲娜·西苏语)。这或多或少说明了,何以德里罗还称其为「the movie on paper」。
——芭芭拉·洛登生命最后的纪录影像可以点这里,由「CC标准收藏」发行的修复版影碟收录在《旺达》的花絮中。
——杜拉斯及卡赞关于《旺达》的对谈可以点击这里,该文刊载于1980年12月号的《电影手册》。
远处的女人
电影开始时,一个女人的白色影子,在长镜头里穿过一片充满矿堆和采矿设备的惨灰色景象。这场景有种幽灵般的美,就像是宏大时刻被错放进一部倾其力量却只对准细微处的电影。不过这个场景只是尚在运算的等式的第一部分。远处的那个灰白身影,在结尾处会出现在有力的特写中,此时她的面容和心灵都显现出来。
这女人叫作旺达,也是这部电影的名字,是1971年的美国片,由芭芭拉·洛登编剧和导演,也由她出演标题中的这名女子。
《旺达》这部影片有着「16毫米」的气质,还有着漂白了一般的霓虹炫光。电影赤裸且不假中介,直接看向一个女人,而不是把她当作无依无靠的边缘人研究样本。
旺达有小学二年级水平的阅读能力。她不做决定也不下结论。她任由一切发生,然后随波逐流,有时候这一切就发生在她的卷发筒里。她和给她买啤酒的人上床,被这人抛在路边摊后,她走进了一家酒吧——此处正遭抢劫——叫正在作案的歹徒给她满上一杯酒。她和这个劫匪上床,这男的派她出去买汉堡,还扇她耳光,最后又让她入伙、做他抢银行的帮凶。
这是写在纸上的电影。一个暴力的男人,一个易受影响的女人。影片本身是复杂而强烈的,它不停变换对角色的洞察,还会有深深嵌入画面却几乎从你眼皮底下溜走的喜感瞬间。
当欧洲电影和日本电影的伟大时代在这个国家走向尾声时,《旺达》出现了。它属于70年代美国电影汹涌浪潮中头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我以前常在工作日的下午去看电影:在死寂的午后来一场电影,影院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还总有人在熄灯之前的昏暗中翻《村声》杂志。很多时候我都能回忆起之前是在什么地方看的什么电影——从这一天的纽约戏院游荡到那一天的布利克街,我警惕又无比期盼:想被带离这周周日日的琐碎和作家「孑然一室」的枯燥生活,准备好投入到断断续续的时空折线中。
但我不记得是在哪儿看的《旺达》了。过了这么多年,它在我记忆里渐渐褪色成一部黑白片。当最近有幸再次得见,其独创的彩色摄影技法令我惊讶,它有很多地方是粗粝的,偶尔有盲色片的笔触。这东西是一种有颜色的黑白电影。
可怕的想法冒出来了。我根本不是在电影院里看的《旺达》。可能它是电视上放的深夜电影,我是在自己的黑白电视上看到的,那台电视戴着兔耳朵天线,换台旋钮也掉了。
当现实上升到奇观的层面,人们会说:「这事儿跟电影一样。」《旺达》抓住了这种电影感并让它彻底变质:让它变成沉闷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个步态可笑若丧家犬的女人。
这部电影不从属于新现实主义传统。里面不带有什么社会性的评述,只有一个眼界皱缩的女人。这并非黑色电影。里面没有混合什么悬疑气氛和命运性的决定。银行劫案的调子也没有和影片其他部分脱节。就是很庸常的,用手枪。这是《邦尼和克莱德》的月之暗面,单调、潦草、歪斜,它没有被编排好的情绪,但绝非没有感觉。
有一个法国作家给我写过信,说他在巴黎曾住过的街道就是《精疲力尽》里贝尔蒙多被杀死的那条。据说,芭芭拉·洛登提到过《精疲力尽》是她的参考来源。但她的电影里拒绝了像时髦、迷人、可爱这样的元素。你看《旺达》的时候很容易忘记:洛登同时也是它的编剧和导演。不存在演员,角色和电影的并置。他们是没有接缝的实体。
在电影里,人们的死是现在时的。贝尔蒙多是一遍又一遍(现在时)地死掉,这不同于在贝尔蒙多死掉的那条街上住过的那个人的死亡。
在她走进被劫的酒吧前,旺达去看电影还睡着了。人们是不会在看舞台剧的时候睡着的。看舞台剧的时候,他们会死。总是会有个男的——而不是女人——在靠近后排贵宾座的什么地方窒息了、倒下了、有时候是当场毙命了。
「他在马丁·贝克剧院里死了,」此后人们会谈上数年,「就在《刁蛮公主》第二幕的时候。」[1]
这不像是会在电影院里发生的事情。电影院里人们又吃又喝,他们手淫,他们睡去,他们会像旺达那样——醒来想找出是谁偷了她的包。但他们不会死。人们会在游客热门餐馆里匆匆吃一顿四道菜的全套晚餐,或花上一整天时间从西北、西南或者草原州这样的地方旅行而来,然后他们在剧院里死掉、在百老汇死掉。[2]
电影不承载物理现实,对于在三维空间和现实时间中在彼此对话的演员来说,电影也不承载他们在空间和情感上所带有的东西。电影是纯粹的光。它凝结不出血肉。
旺达的罪犯情人饱受剧烈头痛之苦。他永远在焦虑。他不像其他美国电影里上演的暴力雌雄大盗那样,把自己和他的犯罪行为分割开来。
在旺达那里没有任何暴力。她仅是一处空无之所,被设计出来以容纳一个男人的自我怀疑和旺盛怒火。她称呼这个男人为「丹尼斯先生」。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只是因为她好像并不晓得他名字叫什么,当然也可能是带着尊重才这么叫的。他痛骂她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所求。她简直不是美国公民——他如此说道。接着,为了准备抢银行的活计,他列了一个单子让她背下来。
和作家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是不讨论书的。我们聊电影。不是因为我们在(从基耶洛夫斯基到泰伦·马利克的)某一部电影里看到了运行其中的小说技法。而是因为电影是我们的第二自我,也是当前文化的主流叙事力量,某种程度上电影是意识联通到睡眠与梦境的一种面相,正如小说是清醒人生漫长而艰难的跋涉。
我有一个作家朋友,他有过濒死体验,但没体验到什么灵魂出窍的事。这人总是想不起印象不深的电影里偏门演员的名字。我曾打电话给他说我正在回想《旺达》里演劫匪的人叫什么名字。他立马答了上来:「迈克尔·希金斯。」便挂掉了电话。
迈克尔·希金斯牢牢地进入了这个角色,以至于看过他在《旺达》里表演的人很难在其他电影里认出他来。我都不知道自己认没认出他来过。有一天早晨,我正想着这件事,就打电话给那位朋友,他正半睡半醒满嘴支吾抱怨。我问他知不知道除了《旺达》之外希金斯演过什么其他电影。
他立刻答道:「《窃听大阴谋》。」
他开始昏昏沉沉地给我细数希金斯在那部电影里的表演,包括他在哪些场景出现过。结果发现这位演员在不止50年时间里,已经出演了超过50部电影。
数年前《旺达》在法国广受赞誉。在美国迟早也会一样——我是这么和自己说的,只是时间问题。
这部电影里的声音往往是在你意识到听见对话之前,就突然从角色嘴里冒出来的。对话就这么在房间深处的什么地方出现,然后作为强效中和剂,让场景摆脱固定的镜头语法变成了更粗粝、更自由的样子,就像在拖车营地里某个陌生人的厨房之中。
这部电影悖逆于它所处的时代。其核心角色既非对抗体制的反叛者,亦非体制的受害者。男人是一个老派的强盗,比起这类角色本该有的样子,他无非是让自己被更彻底地撕裂、被更自暴自弃地玩弄。女人是一个迷失的灵魂,但绝非已故亡魂,编导也不企图通过为她按上什么世界观来拓宽这一角色,世界远远超出她漂泊其中的狭小空间。
在结尾处,旺达发现自己身处一家酒馆中,提琴和吉他手正演奏着欢快的乡村调子。她被夹着坐在一窝大吃大喝、聊天说地、吞云吐雾的人中间。她的脸,从此定格住,随着音乐淡出,浮现出顿悟真我的恐怖。这是一个强烈、悲伤且有美感的特写。
灰色矿堆中那个远处的身影,现在是一个完全成型的人——独自坐在人群中,陷入沉默和苦痛,正若有所思。
影片不可避免地带有芭芭拉·洛登的个人经验。让我们略过那部分吧,只记下她逝于1980年,才40多岁。这是她执导的唯一一部电影。
【译注】
[1] 马丁·贝克剧院(Martin Beck)是百老汇的一家老牌剧院,2003年改名为艾尔·赫什菲尔德剧院(Al Hirschfeld Theatre)。《刁蛮公主》(Kiss Me, Kate)是40年代末的百老汇音乐剧,90年代末曾于上述剧院搬演。
[2] 草原州(Prairie States):伊利诺斯州的别称。
本文由 路米内 翻译 / 小南玩小南 校对
首发于公众号「小把戏去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