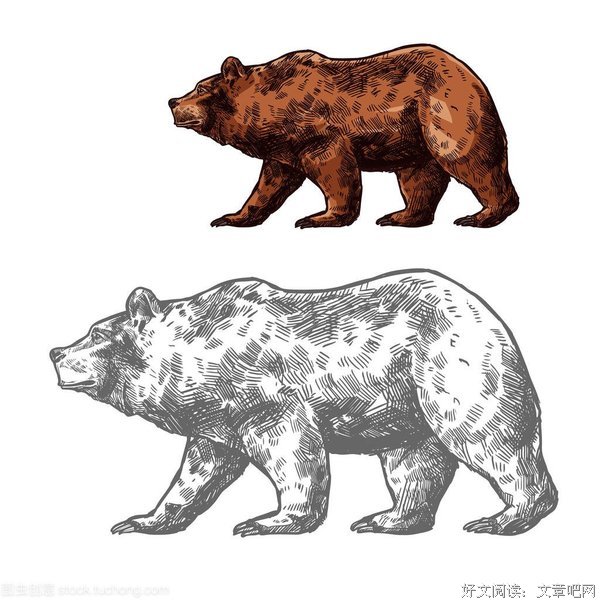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1000字
《重访灰色地带》是一本由刘海龙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2.00,页数:2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一):喜欢~
对传播学历史中许多刻板印象都重新进行了分析,从所谓的灰色地带入手,来考察传播史中的所谓断裂处是如何延续,发展的,这个视角确实需要大量的阅读和知识储备。
以及回溯了中国的传播史,从民国开始讲述,复盘了社会学视角的传播学,和78年后以为是新闻学的延伸的传播学各自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的。
总之对于反思当下传播学的一些困境与问题,可以说提供了一些视角,对于新传的学生更好的梳理传播学的发展也很有帮助。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二):回顾重访
【二刷(一)】 灰色地带,并不是模糊不清,即褒非贬的确定话语,而是被主流话语所抛弃,所掩盖,被我们熟视无睹的链接部分。 教材中多以一种编年史式,里程碑式或者焦点人物式的话语呈现,而很少关注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二刷《重访灰色地带》,希望再次发现新的视角。
在传播思想史上,有关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的矛盾现象如何形成的?是否存在不属于两极分化的哥伦比亚学派成员和成果?如何分界有限效果论和新强效果论?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三):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前四章对经典传播学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真的感慨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概论类的传播学专著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太刻板化了,像高中的历史教材,一切都是盖棺定论的结果。然而理论自有其生命力。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远比拉斯韦尔的5W模式全面和广泛得多,以“管理学派”著称的哥伦比亚学派也并不仅仅是有限效果论的拥护者,李杜之争和芝加哥学派其实都是被詹姆斯·凯瑞构建的,被忽视的帕克原有超越芝加哥学派其他成员的思想光辉。
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回溯中国的传播研究史,这部分非常有意思,一个学科的建立不仅仅是施拉姆访华那么简单。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的传播学研究,却因为思想禁锢导致中国传播研究者对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集体失忆、批判学派的“被消失”,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的概念被偷换......这些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灰色地带,也揭示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渗入学术场域。
当延安时期总结的新闻理论逐渐成为教条之际,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刘海龙老师说:“在那个过度政治化的语境里,追求学术自由便通过追求科学折中地得以实现”。在那个一切都强调“政治正确”的时代,如果能少一点批判和警惕,传播学的发展恐怕不必如此曲折,也不会存在如此多的误读了。直到读了这本书我才明白原来“学术自由和独立”并不容易。
打破主流叙事,引发对司空见惯的事实的思考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而反思和重新解释历史往往就是突破学科发展瓶颈和避免内卷化的必经之路。在这本书里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是一种思考方式。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四):建构中的学科历史
在导言中,作者提出了全书重要的几个概念,包括“灰色地带”、主流叙事结构和反讽的叙事等。简而言之,作者力图在本书呈现的即是,通过运用反讽的叙事,借以审视所谓传播思想史中间的“灰色地带”,从而证明有关传播思想史的主流叙事结构的“虚伪性”。
作者指出,由于传播研究的实践与应用特性,使其与权力的场域、与知识的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因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传播学,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学科自治”的威胁,于是,身处其中的学者们便更有动力去“建构”一套有关传播研究历史的话语体系。
在阐明了这一有关理论历史建构的冲动后,作者进而指明并评价了当前在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的5种主流叙事结构:编年式结构、里程碑演进式结构、大师主导式结构、学派冲突式结构和观念统领式结构。作者认为,这五种主流叙事结构所致力营造的是一种思想“连续体”的“幻象”,而真实的理论演进则是充满着断裂的,也就是充满着“灰色地带”的。
作者指出,主流叙事背后是对秩序感的强调,“秩序感的获得常常建立在武断的分类体系和线性的过程描述之上”。在这种思想的左右下,主流叙事或者说宏大叙事,通过“有意省略或遮蔽”思想史上那些模糊之处,将“灰色地带”拒斥于外。
本书所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发掘连续之中的断裂和断裂之中的连续,从而更为“真实”地还原理论的谱系。
【导言基本上规定了(或阐明了)全书的某种价值取向,即对历史采取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整个传播思想史是基于在该学术场域中的人们所采取某种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五):坦诚的人坦诚地写了一本坦诚主题的书
读了一些专著,最喜欢写这本书的评论了。
其一,逻辑极其清晰而连续,导言篇作者已经把他的立意、思考视角和研究缘由都说得非常明白,读了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其二,言简意赅,正如他在后记中说,“表达和做人一样,一定要保持简单”。
其三,独创性是这本书区别于其他传播学著作的最大特点,正如其名——灰色地带。作者解构历来在中国传播学界的偏见和神话,试图为我们构建更全面而客观的传播学世界。在论述中还不乏幽默风趣,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看到导言部分:“第八章以culture industry一词的翻译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的变迁,描述了传播研究与中国现实之间如何发生错位:为什么中国内地还未有真正的文化工业时中国学者会大肆批判中国的文化工业,待到中国的文化工业真正做大做强时,学者们反而熙熙攘攘的为文化产业出谋划策?”
读到这,我笑了半天,甚至还有点想发朋友圈的冲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是反讽味道十足。
最后,你能从中学到做学术做研究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价值观,我觉得这点尤其重要,也让我不断想起琅琊榜的主题,梅长苏再怎么手段诡谲多变,算计人心,但他始终都在坚守本心、坚守“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坚守真相绝不会被堙灭的信念。做学术同样如此,在没有现实需求时何必要引进和现实不搭的理论,到了该批判时又为何万马齐谙或一味地随众流?学术场域终究不同于其他,对事实和客观本身是比其他场域有更多的追求和坚持的。中西方的研究路径姑且粗略分为应用和理论,这两个面向就好比唯物与唯心的争论,要么经世致用,要么固守象牙塔,但事实上很多事都是相互影响的,没有什么一概而论或一锤定音,也没有哪种理论或话语能够一直保持正当化。你需要的,是发掘它的全部,关注被遗忘的灰色地带,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素养,更是一种对历史丰富性和人文关怀的负责。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六):寻找断裂处的联系,理解思想的复杂性
重读了一遍,还是感触很深,于是写下我第一篇书评。
刘海龙老师所言的“灰色地带”并非黑与白、是与非的中间地带,而是在传播研究史中往往被忽略的人和事。
以往的传播学研究总是一种宏大的、单一的叙事逻辑,似乎有些理论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去重访这些灰色地带,可以让我们从过往的断裂中找到连续,并为传播学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
我们总是希望给学派进行归类,将其抽象为固定的形象以便进行研究,詹姆斯凯利在为芝加哥学派正名时同样是这样的逻辑,于是帕克的思想被简单化、边缘化。
刘海龙老师认为,芝加哥学派并没有真正衰败过,或者说是逐渐过渡到了哥伦比亚学派,而帕克曾有过传媒的工作经历,这使得他与杜威、库利等人不同,更加重视经验式的研究方法。因此刘海龙老师将帕克视为两个学派之间断裂处的连接点。
此外,我们对于这两个学派的理解也过于表层,实际上他们不少的学者并非完全排斥其他的研究方式与思维。我们都知道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合作失败,认为这是管理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思想对立的体现,但实际上拉扎斯菲尔德也对阿多诺的才华赞不绝口。
当一个个学者、学派变成教科书上的知识点,我们容易忽略其自身复杂性、矛盾性,将鲜活的思想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因此,刘海龙老师这本书对我而言,并非简单告知我了这些历史,而是告诉我在今后学习中如何去思考。
最后想用一个八卦来结尾,赫佐格原来是拉扎斯菲尔德的妻子!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七):论国内新闻学院名称之争:兼论新闻学传播学与社会学之学术关系
读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厘清了新闻学、传播学与社会学的相互之间几个问题。
传播研究起源于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尤其以社会学在传播研究上的耕耘贡献最大。最先进行传播学研究的是芝加哥大学的杜威、库利、帕克等人,后来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式微,社会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哥伦比亚学派,但是哥伦比亚学派的社会学家对传播功能失去了研究的兴趣,转向了工具性的题目、以民意调查、市场调查为代表的注重短期效果的应用性研究取代了纯学术研究,新闻学科接管传播研究后将其学科化与体制化,排除了其他学科的介入。也就是说,传播学研究的范式进行了革命,范式的转向使得传播研究与新闻传媒界紧密结合,不再关注社会学领域。新闻学进入传播学研究,取代了社会学对传播学研究的地位。
80年代,施拉姆来华推销传播学,也是用新闻进行了包装,他主要在新闻系活动,不再关注社会学领域,于是传播学在中国和新闻学进行了结合。其实,本来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在民国时代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学学术传统,只是在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下,社会学被认为是孔德的改良主义,被无情取缔,社会学领域的传播研究被边缘化。文革后,从美而来的传播学已经是脱离社会学、将新闻院系当作垦殖目标的传播学,这时候传播学已是改头换面的传播学。另外,中国的传播产业不发达,中国社会学学者关注的领域转向其他问题,如城市底层、农村问题等。于是,传播问题被划入新闻学的势力范围,这样就加重了传播学和社会学的断裂。
所以,正是第一,美国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断裂,新闻学介入传播学后对其他学科的排斥性;第二,文革后传播学进入中国后,已经不是社会学领域的传播学,第三,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社会学被当成“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到猛烈批判,社会学关注下的传播研究只是处于暗流涌动的状态,并不入流。
有个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当下国内大学新闻学院的有“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院“等名称之争,看似是”新闻“与”传播“之争,其实是新闻和传播之间断裂的学术传统所造成的。因为一直以来,传播在社会学和新闻学之间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而且中国传播研究的传统断裂,而民国历史记忆尚未完全挖掘,使得新闻、传播之间纷扰不断。灰色地带过于狭长。这也算是”社会唆使下的遗忘症“的一种表现吧。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八):如何避免被“灰色”
在我们学院的午餐会上有幸目睹男神风采,非常专心地听完了他的每一页PPT(以至于连我导的到来都没注意到),还当了第一个提问的人,奖励就是这本签名版的《灰色地带》,哈哈哈哈当时心里那个暗爽。
借用国庆假期仔细翻看了一遍。拉斯韦尔作为被误读的传播学“奠基人”,其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被传播研究的“无形学院”逐渐抛弃;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的经验分析法长期以来成为“众矢之的”;芝加哥学派尽管创造了传播研究神话,却忽视了帕克从知识社会学与现实社会建构的角度去理解的传播与新闻现象;伯内斯前瞻性的《宣传》却一再被冠以“精英主义”的头衔……一直以为传播学术史短短几十年的进展历程不过是简单的“魔弹论——有限效果论——新强效果论”,而这本《重返灰色地带》让我脱离了平面观点,重新站在了三维的立体角度上去审视传播学上这一段曲折的发展史。
这门年轻的学科在百年不到的发展历程中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与误会,书里已经详尽描述,我个人受到的启发则在于为何会出现这些“灰色地带”,又该如何在将来的学术领域和实际生活中避免被“灰色”。
首先,作为一名创新者,即书中所说“卡里斯玛”式的开创人,拥有前瞻性的想法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如何能让自己的想法得到流传与继承,经历后人的阐发与衍化,最终在不断修正和重新建构中葆有生命力,这就需要来自外部与内部的竞争与挑战。这也是拉斯韦尔被“灰色”的主要原因。他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传播观念,想尽力使其变得完美和逻辑缜密,却也剥夺了其他人参与的兴趣,最终人们不得不将他的观念简化为“漏洞百出”的“拉斯韦尔5W模式”,才能得以进一步的“修正”。因此开拓者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亲力亲为地查漏补缺,而是如何提出一个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谜题,从而诱惑更多人的参与。
其次,大众都喜欢追逐“新鲜”的事物,从而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被学术主流拥抱的是施拉姆新颖的“范式革命”而非席勒用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和阶级分析对于政治经济批判的“老生常谈”。这也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学派为了凸显自己的“突破性”以及迅速获得大众的注意力而简单粗暴地树立起了一个“魔弹论”的靶子(尽管随后他们也成为了“有限效果论”的稻草人,并被人忽视了其他更为丰富的理论贡献)。
最后,成功的宣传营销并不是直接暴露出自己的目的,而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实现其目的的环境。这一点可以从伯内斯的《宣传》一书中习得:传统的宣传不过是就事论事,简单粗暴地把劝说性信息硬塞给受众——我国目前大多数硬广告和新闻发布会仍在采用这种做法;而新的宣传则是创造促进某种行为的环境,让接受宣传者自愿地产生某种行为(比如口香糖有助于口腔卫生,钢琴厂商鼓吹起居室应该留出“钢琴角”等)。这种近一百年前的宣传理念在当前的互联网扁平化宣传语境下看竟仍有超前之处。
总有人错误地把传播学与新闻学画等号,甚至担心新闻客观主义是否会受到宣传的影响。而在这一点,我引用海龙老师的观点:对传播学的研究其实更多地应该落在对人的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上。
(本文系原创,如需转载请联系本人 微信号:shidaostorm)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九):灰色地带,以往传播学习中忽略的部分
刘海龙老师对于传播史的观察是福柯式的,反宏大叙事,反对已经被建制的内容。在传播学史流行的叙事中,比较经典的包括编年史叙事、里程碑演进式叙事、大师主导型叙事、学派冲突式叙事、观念统领式叙事。
前四章主要是针对已有的经典的传播学传统中的叙事,做了简单的笔记如下。
最经典的研究就是5W,但他除了5W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研究,如对于注意结构研究和对驻防国家的思考: Lasewell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所读、所见和所听了解一个人的生活。”但他并不关注信息的微观环境,而是强调信息系统的整体影响。他认为国家制造的信息环境具有垄断性,所以大众媒体的信息具有不可抵抗的影响力,这也是他用内容分析替代效果研究,并被认为是魔弹论支持者的原因。
“他的理由是社会结构演变会导致社会信息环境被中央政府所统一控制,单一的信息环境最终会导致强大的效果。”——不管多元化社会中各种意见如何交锋与协商。特别可以从他对于宣传的研究中看到。
而对于哥伦比亚学派等于有限效果论的叙事,一个是依莱休卡茨对自己学派的建构、另一个是施拉姆等人的确认。而在哥伦比亚学派内部也有像赫佐格这样的异数,还有默顿提炼出的焦点小组访谈的研究。不仅仅是在视角上,也有批判,而且在方法上,也不仅仅是研究实证的。
而所谓芝加哥学派的神话,其中也有帕克这样的灰色地带,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本质上也是控制研究,他也用社会生态学一词来解释城市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把社会比喻成有机体。
而Bernays作为公关的代表人物,则时常因为要保持传播学术的庙堂性而被忽略,而Bernays的宣传概念,则推动了整个公关行业。
而在中国部分,他借五六章梳理了所谓史前史,也就是1978之前的事情,很早就有新闻学的传统和社会学传统下的传播学,不然不会翻译成“群众思想交通”,但这种学术传统都在1978后失踪了。另一方面,在引进后,很长时间里批判学派是失踪的,而批判学派的失踪直接导致的就是在话语符号方面的争夺中,文化工业被文化产业而替代;另一方面,批判学派的失踪,则使得当前批判学派的发展稍微有些畸形,有些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语境,另一方面,批判学派自己的很多问题可能已经不再适应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有些问题不要太拉入到公共领域。
而去年刚刚了解到的传播学本土化这一名词,刘海龙认为这首先是很暧昧的一个话语,中国有没有本土化,当然有……那么多实证研究都是本土化。但是有没有确然的理论化的本土化?有没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意义上达成统一的本土化,答案是没有的。刘海龙的视角是知识社会学的,关注行动者。
此外,刘海龙一再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治经济利益让开的问题,这也是我这几年在新闻学院最担忧的一个问题——我们传播学到底在学什么?为什么总是和新闻学挂钩在一起?为什么大量的实证研究?为什么总是要和xxx70周年、xxx40周年绑定在一起做一些题目?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刘海龙老师的书中得到了一些解答,我也明白学术者的无奈。作为一门与意识形态牢牢挂钩的学问,传播天然不能和政治利益分开,甚至作为一门难以带来生产力的学科,它必须接受政治经济利益的供养。但我仍然怀抱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梦想,和衷心的愿望。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十):值得重读N边的好书:视角比内容更重要
传播学相逢恨早系列!菜鸡迷妹决定坑底躺平,刘海龙老师太迷人了。这本书是刘海龙老师常年累月所积淀的对传播学思考的论文合集,但由一条明晰的“专注于游走于传播学史中灰色地带”的主线统筹,所探讨的“并不是自我存在的美国传播研究,而是中国传播研究者眼中的美国传播研究。”洞见独特、轶事丰富。可要命的是,作为刚刚入门传播学的小白,前半部分收获颇丰,后半部分略显吃力,尤其是后面两章所讨论的传播学在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如果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学界对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争执不熟悉,会对具体的问题细分感到懵逼。
本书大概可以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是关于西方经典传播学叙事的反思,解构这些被神话包裹的主流宏大叙事与代表人物,拨开种种被误读的迷雾。在错误的思维与语境下,导致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与研究被简化;被长期批判的管理学派代表——哥伦比亚学派与其他学派的真正矛盾应该是:研究的操作方式与服务目标,还有误读其研究成果如《人际传播》对有限效果论的支持;本就非统一体的芝加哥学派其实异见纷呈,被边缘化的帕克所被遮蔽的亮点: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开创,细究其原因——成也神话构建、败也神话构建;接着就是我一直喜欢不起来的公关之父伯内斯,代表了进步主义与唯科学主义,宣扬宣传正当性的神话里其实漏洞满满:将秩序与混乱对立(这个点极有启发:意见分布是否必然秩序优先?)、将宣传=教育,缺乏反思现代性与精英主义立场的思维。只要对西方经典传播学研究稍有涉猎,这部分读起来超级爽,只管感受刘海龙老师强大的理性细致的观察、反思和分析能力。
后半部分主要是关于中国的传播学起源的主流叙事的反思与传播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这一过程的观察批判。反思1978年为中国传播学史开始这一历史叙事的正当性,并补充了1978年以前的传播学研究,专门将“传播or交通”的翻译问题拎出来追溯和重构中国传播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呈现这一神话神话里面被掩埋的“连续中的断裂,断裂中的连续”及历史政治原因。还有一个很有启发的点是,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这一词义变迁来透视学术场域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政治对学术独立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尴尬处境,这与我之前在赵勇《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中提到的“真正的批判精神内核丢失”相应衬——反应了中国传播学术研究一直以来的重实用理性缺乏反思的思维定势。由于我积淀浅薄,后面两章探讨中国传播学本土化有些没有看太懂,比较吃力,以至于在宏观批判层面刘海龙老师说什么我都觉得:卧槽,说得太对了……
刘海龙老师的书从来不是只教予知识,更教予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与能力。一定要多读重读经典务实基础,要对主流叙事保持困惑和反思,才能提出切实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再次表白刘海龙老师,值得重读N遍的好书。
“第一,要理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不宜把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简单照搬到社会科学之中,尤其需要警惕西方研究中那些带有特殊文化烙印的前提假设。第二,我们要摆脱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理性地看待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只有一种,而是多种,除了实证的范式,我们还可以使用诠释的或批判的范式,不同的研究范式令我们有能力反思单一的、标准的垄断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第三,要区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应该关注的是在今天仍然影响着社会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简单地用现代的术语去剪裁传统文化,或简单地用传统文化的概念去剪裁当下的现实,甚至单独搞一套话语体系和理论。第四,警惕“特殊性”或“多样性”背后的狭隘民族主义或思维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