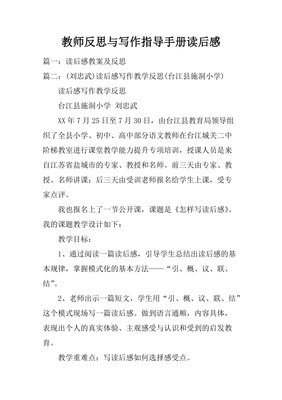反思现代读后感精选
《反思现代》是一本由黄克武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元,页数:3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反思现代》读后感(一):筆記
- 去年因為讀了中文大學出版的《顧孟餘的清高》,第一次接觸到作者黃克武教授。黃教授曾為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明、清、民國史乃他的專攻領域。
- 也忘了是在哪裡知道黃教授出了這本書,估計較大可能是豆瓣吧。當時特意在網上查了一查,發現這書沒有繁體版,四川大學的這個版本是第一次出版。
- 翻開書本,了解到作者根據幾個主題收入了不同的文章,不少過去已發表過。當中的文章最早發表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最晚的卻是2017年,也有一兩篇沒有出處、假設就是為了這書而寫的。
- 作者著作等身,發表過的書與文章估計相當豐富,是故我在閱讀這書時比較好奇、或有些疑問的是,作者選擇把這些文輯編輯成書、並選擇在中國大陸出版,背後的考慮不知為何。他在序言中最尾處有提到,兩岸的史學因著歷史的原因,有著不少分歧及矛盾,也希望有多點交流互動,是故我估計他的其中一個初心是希望促進交流。
- 從文章的內容來看,作者選入的文章有涉及的內容各有不同,比如有探討較為理論化的東西(像現代這概念的生成、演變)、關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不同理論模型,也有相對具體一點像考據學的源流,立憲派與革命派於辛亥革命中的合作與角力等。因為文章多為期刊文章、書評等,文章也相對易讀。當然對於我這種門外看來說,有些內容有點專門(如考據學等的討論)。
- 也許對於熟悉大陸史學研究的學者和讀者來說,這書的選文能對應到學界的一些特點、現象。但對於不在學術圈子混的我來說,這書的文章雖然是有啟發及知識點,但卻有點不清楚作者編這書的核心問題意識。
- 以我所見,這書所說到的重構,主要是談到對現代化作為線性歷史的書寫的反思,以及和應柯文提到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打破西方中心視角的歷史研究進路。這些討論和美洲歷史學者們的努力與討論也很相關,惟近年從貿易、海洋研究、內亞視角等討論在書中卻沒有提及。而作者也沒有處理馬列史觀的特點與問題。
- 作者專長於明清、民國史,是故書中收的文章也多以清末、民國時的內容為多(除了談胡適的一篇有涉及六七十年代的台灣)。不過這樣的選稿,便無法讓讀者了解到關於四九年後的歷史研究圖景了。
- 作者在書中提到,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華文世界以大陸及台灣為主,國外的話則有歐陸、美國及日本的傳統。有點可惜的是書中並沒有進一步介紹幾地不同傳統的異同、互動,不然應該是個相當有趣的題目。
《反思现代》读后感(二):读《反思现代》
现在假设某一天,我的小孩问我一个近代史的问题,比如:论述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吓到了吧,这可是一道试卷中的大题,却是每个中学生都能顺手拈来回答正确的得分题。套路是这样的:(1)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和相互制约,然后自由发挥200字。(2)最根本原因: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侵略斗争,此处同样自由发挥200字,如果写上“三元里抗英和义和团运动严重打击了侵略者”更能够意外获得幸运值和魔法值的加持。最后,一句“综上所述”再重抄一次题目,写个四、五百字就可以完美得分了。这个套路从初中到大学的近代史考试都可以往里面装东西。所以我的小孩从来不用来问,也不用跟我讨论这个会显得为父弱智的问题,因为他比我更清楚这是一个万能的框框,敲上去哐哐作响,摔在地上啪啪有声。
难道答案真的那么简单吗。放在上面的情境里,只要低头看看手表和后面还有的几道大题,你还能强求什么,赶紧这样答吧。然而大概总有人不用考试或者考完试竟然还要“反思”标准答案的,总想探讨于近现代史这个锅里究竟熬了什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答案是先给出结果,然后进行循环论证。这个时候他们会用广东人的口吻告诉你,每一煲老火汤各家各户都有不同的配方一样。近现代史这煲汤也一样难以三言两语盖棺定论,因其资料丰富,材料之间有矛盾和张力,还有意识形态等等问题,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家近现代史里人丁旺来客多,众声喧哗之下这汤已不是“不变的配方”了。
《反思现代》这本书正如其的副标题“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这本书简而言之,它主要透过综述和书评的方法呈现作者对近代史演进的理解和理想的历史书写。可以说是作者心目中冶史方法表达,也提供了近现代史研究的门径。本书的编排,颇下了一番功夫,把不同文章连缀起来俨然有君臣佐使。第一篇“典范转移”从“中国近代史”形成过程是怎么把“鸦片战争”作为开端和转折点,怎么把近代史变为“国难史”,其目的和意图为何,指出随着中国近代化史学书写的演进。可以说这本书在第一篇文章里开了个好头,以点带面,一上来就从思想和史学的角度去回顾“现代”观念的起源其后的变化。其后由内观外,从“文明”和“文化”一词的消长看20世纪中国思想的曲折变化。各种各样外来的新鲜玩意儿如何翻译包装重新构建“近现代”。然后又由外观内,既有西方汉学的精英阶层研究总结并对应探讨外来的世俗化概念。
最后捧出喷喷香“建立史学典范的一个努力:论余英时《史学评论》‘代发刊辞’”一文。堪为第一部分《典范转移》的压箱之作也锚定了整本书,黄克武先生本人透过余英时文章的评论,既对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批评,又借文章表明了态度并称其具有”典范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历史是多样与发展的,并在发展的脉络里了解未来的动向;在方法层面上应用比较研究和社会科学的解释法则;在价值层面上史家关怀时代,但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以世界的眼光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 某种程度上能够回应“所谓真实的历史,就是政治正确”
“晚清史的反省”和“民国史之检讨”两部分可以说是对第一部分的补充,一个侧重点历史资料的应用方法和分析,比如对“经世文编”和“胡适档案”的应用,对个人史、口述史的反省。另一个是透过书评来展示专业方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研究不陷入历史只是言说的虚无主义——正如不是所有水鬼尿和刷锅水都能叫汤的。
本书的不足也不是没有,首先作者尽量回避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意识形态却是近代史研究最难绕开的,在章开沅和张玉法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辩论,作者虽然没有表明立场但更倾向于张玉法的“全民革命”的看法。并不是说必然要作者综合各家看法,做到面面俱到,而是在读该书时读者更应该反思他的“反思”。
还有一个小问题,译名不能统一,比如Edward W.Said,有译为“萨依德”、“ 扎伊尔德”及“萨义德”,文集不同文章发表的杂志不一样,为了适应不同地区的习惯,难免会出现译名不统一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同一篇文章里前后两页(P238,P240)出现两个不同译名,那还是要紧扣主题“反思”一下。
《反思现代》读后感(三):读《反思现代》有感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杨万里《桂源铺》
人生如溪。万山拦阻下,浅溪仍能排除万难,流向前方的村庄。这既似个人的悄然成长,又像时代的无息变化。《反思现代》是一本收录黄克武老师在过去30多年间撰写的论文合集,涵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典范转移、中外学界研究状况的反省,以及几本中英文史学著作的书评等广泛内容,反映其个人成长与时代变化。这些论文大多已经发表,最远是1984年的《建立史学典范的一个努力:论余英时<史学评论>“代发刊辞”》,最新近的,则是2017年的《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可见时间跨度之大。当然,其中也有两篇并未发表的,或更倾向于私作,或是新近的书写,这便是我不得而知的了。
正因这是黄克武老师对自己三十多年学术道路的回首,我并无资格在此评头论足,只想谈谈其中一二收获即可。本书的序言题为《回首来时路》,回顾了黄老师自1975年进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以来的治学道路,带领读者走入那个时代下的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欧洲和日本五个迥然不同的史学传统。他曾提到在其成长过程中,一直有两股文化力量在心中激荡。一是钱穆、唐君毅和牟宗三等新儒家的学说,二是北大和“五四”的传统。正是因为成长于这样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具有强烈关怀的环境中,黄老师的那一代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均怀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如今年轻的求学者身上似乎已不复存在。在台师大毕业,转赴美国的过程中,黄克武老师感受到了美国汉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也助他打破跨越东西方学界交流的障碍,早已成为史学界的翘楚。
《反思现代》一共有十六篇文章,分为“典范转移”“晚清史的反省”“民国史之检讨”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黄克武老师对于“现代”观念、“文明”与“文化”的论述、近代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领导阶层的研究、世俗化理论、史学典范等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黄老师对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一文的解读。他分别从承旧和创新的角度反省,承旧的方面厘清章学诚、钱穆的史学渊源,创新的方面则尝试以近年来国内的学术经验回观余文。他指出,余氏的发刊辞和与此相呼应的史学作品,对现代史学具有建立典范的意义。这种意义,既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也在价值层面。也即是,历史的多样性与发展性须受到重视,进而从发展脉络中了解未来的动向。比较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解释法则也要适当应用,从而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从事疏通知远的工作。史家应关怀时代,但要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重要的是,应以世界的眼光超越民族主义的偏狭态度。黄氏指出,这一系列的看法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继而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在不久前才得知余英时先生去世消息的我,此时读起这些文字,尤觉振聋发聩。
第二部分,“晚清史的反省”。主要包括黄克武老师对经世文编、清代考证学的研究,以及四篇评论性的文章。这几篇书评之中,评论海外汉学家柯文的《历史三调》篇幅最长,且最为精深。他对柯文有高度的评价,“对于历史学科还怀抱温情、敬意与希望的从业者而言,柯文著作所显示出来的娴熟技艺、流畅文字、清晰概念以及深刻反省,无疑地为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做出了一个优秀的示范。”实际上,黄克武先生的文字与研究,也值得同样的称赞。
第三部分,“民国史之检讨”,涉及辛亥革命、胡适档案、口述史及一篇有关翻译史的书评。翻阅《从晚清看辛亥革命》一文时,猛然想起有老师说过,辛亥革命曾是一个时代的热点,学界的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对孙中山、辛亥革命有过研究。随着史学领域的不断拓宽、深耕,辛亥革命逐渐被遗忘,甚或因“研究门槛高”而令年轻学者避之不及。但通过黄老师这篇2012年的文章,我们仍能在时代的见解中得出新的启发。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辛亥革命更是如此。革命成功乃是各种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亦多秉持类似的共和理想,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社会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的妥协之中获得成功。而这种妥协的气息,也逐渐在民初的诸多困难与挫折中逐一彰显。
最后,还想谈谈胡适档案与胡适研究的问题。似乎有一个学者说过,读懂了胡适日记,也就读懂了民国时期的大半个中国。究竟是谁我已忘记,只是有一个懵懂的记忆。重要的是,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黄老师写道,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中至少有思想文化、学术、政治实践与学术行政三方面的意义。思想文化上,胡适宣扬文学革命与文化革命,并在行文用字时一丝不苟、明白晓畅,今天他所留下的文字,一定是清清楚楚。这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的理念,也即任何文字表达都要准确、清晰、清楚易懂。这个准则对于目前正在求学道路的我们,何尝不是一个警示。继而,学术上的意义,胡适除了用科学方法研究传统学问外,还用英文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将中国文化的精深内涵带到世界。第三则不用多谈,1938-1942年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他间接帮助中国取得了许多国际援助。随后,黄老师细致介绍了胡适纪念馆的藏档,更是不惜笔力地协助从事胡适研究的学者们“穿透迷雾”、寻找胡适的真实面目。
好的著作,总能启人深思。好的文字,总能走入人的心灵。如同黄克武老师反思“现代性”,讨论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发展理路、中西历史交融互释的问题一样,我们也应始终以“反思”的态度探寻流动易变的近代中国。
《反思现代》读后感(四):黄克武:回首来时路
我在1985年进入“中研院”近史所工作,1993年第一次去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以后几乎每年都去大陆从事学术交流,偶尔也去欧美等国家开会。在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以及两岸关系、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连带影响到近代史研究的走向。
这一本论文集所收的文章是过去30多年间所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典范转移、中外学界研究状况的反省,以及几本中英文史学著作的书评等集结而成。我将这些文章分为典范转移、晚清史的检讨、民国史的反省等三个部分,可以反映我个人的成长,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
我在1975年进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台师大历史系与“中研院”近史所都和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郭廷以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在台师大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跟随郭廷以先生读书。我的老师辈有两类:
第一类是从大陆来台湾教书的学者,如朱云影、李树桐、朱际镒、曾祥和、高亚伟等教授,他们多半是北大、北师大,还有中央大学毕业的老师,整体的学术氛围是倾向肯定传统的“南高”学派(出版《学衡》杂志),而非批判传统的“北大”学派(当时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学风倾向此派);
另一类就是郭廷以先生(也属于南高学派)在台湾培养出来的“中央研究院”的子弟兵。这些子弟兵包括王聿均、张朋园、李国祁、张玉法、陈三井、陆宝千等先生。
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研究同人大多数都是郭廷以的学生,也是我在台师大的老师。所以,我继承了此一治学传统。
目前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外,大概主要有另外三个地域的学者也在研究中国,包括美国的史学传统、欧洲的史学传统和日本的史学传统。这五大史学传统都对中国研究很感兴趣。所以,目前有关中国的学问已不仅是中国人的学问,而是世界的学问。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我自己亲身接触的是台湾地区、美国和欧洲的部分,最近也接触到一些日本的学术传统,并与大陆史学界密切联系。当然我的根还是属于台湾地区的史学传承。怎么说呢?这要从我成长的过程谈起。我所生长的时代是两蒋父子威权统治的时代,那个时代政治上比较单纯,思想文化上要稍微复杂一点。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两股文化力量在我心中冲击。
第一股力量是钱穆、唐君毅和牟宗三等新儒家的学说。一如钱穆先生所说,我们应对中国历史文化保持一种“温情与敬意”。我们从小要读儒家经典,要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记得中小学时我父亲在我放假期间,就叫我背诵《唐诗》《古文观止》等。
一直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论语》中的一些句子在我心里还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在面临困难时想到的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君子不忧不惧”。这些话给了我精神的安抚与无比的激励。《唐诗》《古文观止》则让我感受到中文文字之美。
这种感受当然跟钱穆、牟宗三等学者对中国传统的提倡与诠释有关,也跟蒋介石的教育立场是一致的。蒋介石十分欣赏阳明学,对他来说,牟宗三和钱穆都是国师级的人物。那时我们的教育里洋溢着一种对中国传统的温情与敬意。
第二个部分是北大和“五四”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代表人物是胡适。所以,一直以来,在我心中有两个人格典范:一个是钱穆,一个是胡适。问题是:这两个人物典范怎么结合在一起?胡适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毕生提倡“科学”“民主”与白话文运动。1949年之后胡适是台湾文化界的领袖。
从胡适引领出一系列的政治与文化运动,继承了“五四”传统对于中国文化的反省、对专制政权的批判。当时有不少人受他影响,最典型的代表是李敖。李敖可以说是“五四”的产物。他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礼赞、对于自由主义的提倡,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对于“老年人与棒子”的反省,在台湾都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李敖的作品非常有吸引力,他是我们的鲁迅。当然,除了李敖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学者,像我的老师张朋园先生即深受“五四”思想影响,毕生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改革与革命、民主与宪政的历史。
这两个传统在我们那个年代长大的学生心中是两股相互拉扯的力量。这个拉扯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传统的优点,另一方面也感到这个传统的确有一些问题。那要怎么去修改这个传统呢?这一个议题是“五四”跟新儒家的共同议题。我们要怎么样面对中国传统?又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接引到西方的民主、科学?这也是台湾学界一直在努力思索与追求的方向。
1949年时台湾只有六百多万人,现在有二千三百多万人。台湾大学的社会学家陈绍馨教授(1905—1966)讲过一句话:台湾是中国文化的实验室。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到位。的确,台湾让大家看到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里的另外一种可能;当然目前这个实验还在继续进行之中,未来如何颇难断言,可是我觉得陈绍馨所谈的“台湾是中国文化的实验室”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我在这样的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具有强烈关怀的环境中长大。我还记得1983年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先生刚到台湾来教书,他很喜欢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将来希望当王永庆还是要当余英时?”那个时候王永庆是台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而余英时则是学者的典范。余先生跟台湾有非常深的学术根源,他的书如《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在台湾流传很广,几乎是我们那一代读历史的学生的经典书刊。
所以当墨先生问我们“要当王永庆那样赚大钱的企业家,还是当余英时那样对中国文化有非常深入的认识的学者?”我们每个人都举手说:“想当余英时。”后来我碰到余英时先生,告诉他这段往事。他说:“其实我自己很想当王永庆。”
我们那一代人基本上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是在所谓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之下成长的。对我们来说,李白、杜甫、苏轼是我们的先人,最感动我们的文字一定是先秦文字与唐宋古文,是唐诗、宋词、晚明小品等。我想这就是文化的根,也是我感觉到两岸在将来可以合在一起的最重要基础。说到底其实就是文化的基础。
我在台师大毕业后先到英国读书,后来又到美国留学,开始接触到欧美的汉学传统。这个传统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洋人读中文非常困难,光是把中文学好、读好,看得懂文言文,至少就要花上十年的功夫。所以中文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难的语言。我到英国读书时碰到几个汉学家,如我的指导老师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伊懋可(Mark Elvin),以及麦穆伦(Ian McMorran)、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2017)教授等。
欧洲汉学研究基本上是非常朴实的。他们的目的是想了解中国。开始之时这些汉学家多做翻译的工作,就是把中国的各种经典翻译成英文或其他的文字,作为主要的学术成绩,进一步再做文献解题等。所以欧洲的汉学研究不太花哨,多半不讲理论,而讲究踏踏实实地研究文献,对文本进行精确的翻译与深入的探讨。
这个研究取向和美国汉学传统不太一样。美国学界讲究科际整合、谈理论,强调怎么样把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同时历史研究也努力要和理论对话。美国的史学研究求新求变,而且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个理论过后又换一个新的理论,让大家有一点应接不暇。
我在史丹福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主要是墨子刻、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康无为(Harold Kahn, 1930-2018)等先生,大约有两个传承,一个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 K. Fairbank)的弟子,一个是加州大学的李文孙(Joseph Levenson, 1920-1969,或译作列文森)的学生。这两者刚好是东西两岸的学术传承。
东岸的学术重镇是哈佛大学,中国近代史方面主要是费正清的弟子,墨先生与康先生都是出自哈佛,范先生则是柏克莱毕业(1964)。费正清1960年代起在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一整代美国的中国通。他有雄才大略,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有一种全盘性的规划和笼罩,我们可以说整个美国的学术版图几乎都被他控制住了,另一位中国研究的奇才则是费正清的学生李文孙,他被誉为“莫扎特式的史学家”,很可惜英年早逝。
中外学界对他毁誉不一,西方学者较欣赏他,而中国学者则批评他文献解读的能力,萧公权说他诠释的梁启超有时会“捕风捉影”,不尽可信。后来在柏克莱教书的学者是李文孙的学生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1937—2006),成绩斐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说他是“近三十年最好的中国史家”,魏斐德的学生叶文心目前在柏克莱教中国近代史。简单地说,费正清开创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费正清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基本上是美国目前中国研究学界的核心人物。我在1990年到美国之后,开始透过英文著作学习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大家用中文读中国历史比较习以为常,但是用英文读中国历史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
我在求学时不断遇到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到英国或美国去读中国历史?这不是很可笑吗?”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洋人有他们治学的长处。这个长处跟欧美整体的文化实力和文化霸权是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整个近代学术的形成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汉学是其中的一环,而且是比较薄弱的一环。欧美学者是在做全世界的学问,中东、南美、印度研究都做,此外还有日本研究、韩国研究等。
我在史丹福大学时读得比较多的是东亚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史学传统(我的日本史老师包括Jeffery Mass、 James Ketelaar、Peter Duus,还有亚语系的William A. Lyell、Peter J. Ivanhoe分别教我中国文学与哲学)。这些学者都有非常好的训练。他们都曾在中国、日本学习过,都有非常深厚的语言训练。所以他们都能够读中、日文书。
当然,刚开始那一代还只读不说,后来的一代学者则说、读、听、写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近年来,美国的汉学传统有长足的进步。我自己也是深浸于这个传统。我到史丹福大学之后就从本科的课程开始学习,和本科生一起考试,一直读到研究生的讨论课,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读,然后考学位资格考试、写博士论文,2008年我出版了由博士论文改写的英文书。这是一整套的培育体制。
美国的汉学界的确给我相当多的启示,我觉得他们有几个长处。
第一,他们对学科本身有很强的反省能力。特别对于研究典范,基本上是不断地深挖、不断地反省。我想可能很多人看过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和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等书,可以看到他们在一个时代就有一个时代的研究典范。
从早期费正清的“冲击-反应” 说,到“现代化理论”,再到“中国中心论”。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研究中国的典范,而这个典范过一阵子就又会受到批判与反省。每一次批判与反省都是一个提升的过程。这种自我批判与反省的能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本书中有关典范转移的几篇文章与此一思路有关。
第二,美国的学术根基很深厚,治中国史的学者多有很强的其他学科的背景。例如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会告诉你,如要读中国历史,除了要通中文,还要读社会科学的著作。例如要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马克思(Karl Marx)等,也要从西方近代哲学变迁开始读起。也就是说,这些社会科学、哲学、文学以及语言学理论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
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的中文不如中国人那么好(很多汉学家可能不承认),怎么样在中文不如中国学者的情况之下,做出一个别有新意的成果?他们有些人就开始采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治中国史。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人这样阅读大量的史料。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采用新的问题意识,例如韦伯与马克思的理论就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这样一来依靠少数关键性的数据就可以大做文章。这是他们的一个长处。
这个长处也跟他们深厚的学术传承有关。我到美国之后,感到非常惊异之处就是美国学界中“学术社群”十分重要。我觉得在台湾地区的发展都还不很成熟。学术社群就是由学者组成的民间社会。美国最重要的学报,不是官方机构编的机关报,而是各种各样的学会所发行的刊物。
例如明史研究学会、清史研究学会、近代中国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研究等,最大的当然是亚洲研究学会。这些学会是从会员身上汇集到一笔钱,然后开始办刊物,稿件由学者彼此互相审查。民间刊物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现在我们想要深入了解美国学界,那就得看这些专业性的刊物。
这些刊物的一个很重要作用是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发表专业性的研究成果,另外几乎三分之二的部分则发表书评。书评有两类:
一类是“单篇书评”(book review),单篇的书评不长,最多一页到两页,清楚地介绍书中的论点,并做评论。
第二类较长,称为“书评论文”(review article),中文也有这样的写法,主要是综合评论几本书,或者说针对一个特定主题,对整个研究领域加以回顾与展望。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评估机制,就是由学者参与的互相评估。通过这个相互批评的机制,建立起一个学术的体系,从而让他们的学术工作能更上一层楼。
第三,美国的学者基本上像柯文所说的,是“外在的观察者”,跟我们的“内部观察者”不一样。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对美国人来说,为什么要了解中国?当然有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历史、文化的背景认识,也提供美国舆论界、一般人民能以一个适当的表述来了解中国。他们对于我们最关心的“中国往何处去”并不特别重视。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不易达成共识。他们的研究主要在于描写与分析的层面,而尽量不做应然的判断(当然很难完全避免应然的立场)。这一个特色,跟中国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学者用中文写的作品,无论分析还是评估,往往都跟对未来的建议交织在一起。
我们对历史的回顾,背后每每藏有经世的意图,最后是希望能够指点江山,能对现实与未来有所影响。这是中文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很大特色。这种特色不一定是一个缺点,但最极端发展有可能成为所谓的“影射史学”。在这方面,我觉得美国学者比我们容易避免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不在局中,反倒能多方关照,而且能够比较置身事外地来看待其中的问题。这些特点都很值得我们参考、学习。
从1990年代初期,我也开始接触到大陆的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参加的学术研讨会是1993年11月23日—27日在广东新会与南海召开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我受到一个很强烈的文化冲击。那是我第一次去大陆开会,也是第一次跟大陆的学者有学术上的交流与交往。
我发现大陆学界跟我所想象的很不相同。那时我就问道,这边学者写文章为什么不先做学术史的回顾?在台湾地区以及欧美学界博、硕士学生训练的第一步就是做文献的回顾。90年代时,大陆学者的著作却不很注意这样的学术规范。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略微了解到,其实这是因为当时信息不发达所致。大家看不到国内外的很多研究。
同时,学界也不强调“站在巨人肩上”的重要性。最近已经改变了很多,学术史回顾的规范性要求已被明确提了出来。现在大陆的一流学术刊物如《历史研究》就非常重视这一点,这是很有意义的发展。我也感觉到,大陆学界挣脱了诸多束缚之后,整个学术的进展非常可喜,跟国外与港台等地学者对话的机会也增加很多。本书中许多评论与反省的文章是在这样的脉络之下所撰写的。
两岸中国近代史学界无疑地均追求客观的历史研究,然而因主观立场之差别而双方仍有歧义。近年来两岸共识增加了许多,不再是黑白对立而没有交集。我认为两岸的研究可以产生互补的效果。双方同意以史料为基础从事解释,而非以既定立场来讨论问题。台湾学者也希望能从历史问题的和解走向现实的和解,而共同思索两岸的未来。
为达成此一目标,最近海峡两岸有不少的共同研究计划,在这方面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由王建朗教授与我所编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一套书(2017)。此套书是两岸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合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本书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规划,并邀约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学者撰稿,历经约五年多的时间完成。
全书分为晚清篇与民国篇,每一篇又有上卷与下卷(共四册),分章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一些历史课题。全书共57章,其中大陆学者撰写34章、香港学者撰写2章、台湾学者21章,为中文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内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现。
内容上本书以时间和事件为经,政治、社会、经济等面向为纬,从鸦片战争开始,描述了洋务与变法运动、立宪运动、清朝的覆灭、民国的肇建,乃至其后内忧外患之纷扰、国际关系之演变、内政外交之调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国共两党之发展,下至20世纪中叶而止。
大致上包括了晚清史与1949年之前的民国史,也同时讨论了清朝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至光复初期的台湾史。读者阅读此书,可以最有效地掌握学界最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变迁的重要观点。另一方面两岸学者在共同编写此书的过程之中发现双方仍有不少的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海峡两岸的交流与互补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海峡两岸的政治情况还存在很强的张力。在此过程中双方不免会有竞争,但可以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透过海峡两岸的互访、透过双方阅读彼此的作品来达成此一目标。这一本论文集即着眼于此,笔者衷心地希望这些介绍与检讨研究典范、中外史著的文章能增加读者对海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而共同创造更为光明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