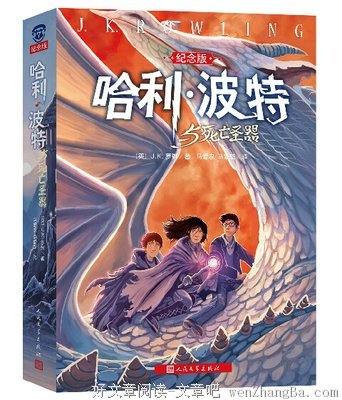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读后感10篇
2017-11-29 22:55:4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是一本由柴春芽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一):从宗教的角度批判汉文明?
当我把这本书从上海书展买回家的时候,老婆明显表示了她的诧异——这种有着文艺小青年标题的书,怎么会入我的法眼?而我不得不承认,是被他的名字所吸引,同时也因为它是本签名本。我是倒过来看这本书的,先把剧本看完,然后再看作者的自述。这样的好处就是在看作者的自述的时候,清楚地知道哪些是说电影,哪些是说真实的世界。
作者在自述的时候,把电影拍摄的过程,以一种奇特的形式展现给我们,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的自传(因为其交代了他的父母,交代了自己的经历)。
不知为什么,在读该书的时候,一直隐隐觉得作者有站在宗教角度批判汉文明的味道:从选择《奥义书》中的 地、水、火、风来作为其电影的四个章节;从认为拼音是思维的产物而汉字是感官的产物;最后的结论是——一个不信天谴和末日审判的种族,怎能凭借不受节制的欲望找到打开现世困境的钥匙!作者在接受采访时候说的如下文字,可能是最好的注脚:“我们汉民族是个经验主义的世俗民族,对于超验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思考,我们一直欠缺热情和智力。恰恰是那些超验的事物——正义、善、美、上帝的律法、自由意志等等——才是人之为人的属性。世俗事物诸如吃与住等,并不是人之为人的属性,而是动物之为动物的属性。”
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作者号称其电影是关于土地的电影,那么这本书就是作者思想的另一种表达(绝对不是电影的简单重复!)。有机会,我会去看看这部号称中国诗电影的开山之作。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NzcwNjgw.html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二):对故乡的哀悼
故乡已死。这是大多数从农村逃离出来,游离于城市的知识青年共同的哀叹。面对日益荒凉的“过去”,很多人不知如何哀悼。当悲情得不到祭奠时,一种感同身受的文字,无疑是慰藉心灵的良方。正如柴春芽新书《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中的文字:“年轻人全都挤入城市,只留下空旷而寂寞的村庄,给世代坚守的孤独的神灵。只有行将就木的老人,还在残破的节气里,不忘祭祀的艺术,为那孤独的神灵唱一台皮影戏。皮影戏台下,除了另外几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之外,还有一群骨头锋立的流浪狗。这就是我那故乡如今的现实一种。”
近十几年来,城镇化以及经济开放的浪潮,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却也让一些人产生了迷惘。作为中国社会根基的乡村,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伦理道德和居所一起被剥离后,许多漂泊在路的人在异乡找不到心灵的归依,又与故乡有陌生的疏离。
作为一个信仰灵魂轮回和天堂地狱之说的人,当物理层面上能够安身立命的居所不复存在之后,柴春芽开始寻找一个超物理世界的栖息之地。恰好,脱胎于古印度关于物质世界的传统说法并且后来在佛教中延续下来的关于世界四大元素——地水火风——的哲学观,为他这种形而上的求索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
于是,他就试着以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来结构一部电影,并以此为主题,探讨死亡的现象与本质。在这部电影中,柴春芽用哲学的语言让现实与幻象交叠,以一种意识流的形式,表现乡土的幻灭与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其实是一部哲学电影。另外,由于电影的叙事一直保持在一种意识流的层面上,现实与幻象频繁交叠,这就使得电影又像一部诗电影。
对于柴春芽来说,电影不是要给出答案,而是要引出疑问。他并不试图通过作品教导什么或者解释什么,他只是用多维的尺度去衡量世界,表达生活和感受。于是他打破线性叙述,用四大元素讨论灵魂和故乡的消亡。
电影里的人物具有一种忧伤的尊贵,因为他们的死亡并不是死亡,而是向死而生。作为故乡的4个符号化人物的死亡,暗示了一种悲观的希望。
而与电影同名的《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本书,包含了电影小说和电影剧本两个部分,记录了柴春芽的拍摄过程和拍摄心得,是一场艰难的追寻。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发现,作者在电影中其实是在讲一个充满诗意和宗教意味的故事。有关“湖”的传说、神灵附体的人、七面镜子、走向深海,种种意象的设置背后都沉淀着作者对死亡的理解,对故乡的哀悼。
很显然,这本书对物理意义上的故乡涉及很少,讲的都是非常现实的东西。最为关键的是,这本书的文字充满了诗意、哲学和宗教气息。并且,在书中,柴春芽以他那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宗教徒般的救赎情怀,向大家展现了一个诗意而荒凉的世界。
原载于/《法治周末》
原作者/西木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三):故乡死亡的方程式
最近浏览回到故乡所拍的照片,跟记忆中的故乡已有很大的差异,频频回顾这是我曾经生活的地方吗?可不是,那依稀有着故乡的身影。
炎夏里,读柴春芽《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话题虽然沉重,却逼近我们的生活。这不只是一种感叹,而是在面临着过往岁月,努力找回曾经的记忆吧。
本书为柴春芽的“故乡三部曲”之第一部,并由其亲自编剧和导演同名独立剧情长片,该片已入选2013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及台湾金马电影节等。
这种对故乡的爱,也许多少有些“病态”,看上去曾经美好的地方,现在完全改变了模样,自然有一种哀伤在。这种哀伤的情调是时下回顾故乡的基本基调。但这种对比能说明什么呢?
柴春芽所描述的故乡,实在是每个人的故乡都有这样一种衰落的面貌出现。所以,才有每个人的故乡在沦陷的说法。
说到底,我们对故乡的热爱更像是一个意象,虽然知道它在沦陷,却站着旁边感叹,不去采取拯救行动,也因此,这就像是一种伪抒情。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包含了电影小说和电影剧本两个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影故事发展的线条中也融入了作者坎坷的拍摄经历,文字上充满了诗意,哲学和宗教气息,并且在书中作者以他那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宗教徒般的救赎情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诗意而荒凉的世界。
柴春芽在对故乡的书写过程中,从地、水、火、风四个视觉观察故乡,因由贴近的方式介入到故乡生活,其所呈现出来的原生态也就令人震撼。
这类似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或西奥•安哲罗普洛斯那样的“诗电影”,崔卫平说,再看下去发现他其实更接近“魔幻现实主义”,是从荒芜破败的现实中,重新走出曾经有过的理想、光荣和辉煌,再现这片贫瘠的土壤曾经有过的恩典与呵护。
不过,因为贴得太近,情感太浓,以至于无法闲闲地渲染一下,使整个乡村的基调变得更为荒芜。
故乡为何会陨落成这种面貌?这也许是这几十年工业文明、物质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成为一种向往,财富、资源不断地层级向上发展,而乡村的变化却得不得更多的眷顾,以至于远离故乡之后的人们,很少再去光顾,故乡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精神的祭坛。这如果说是这个时代的宿命,不如说是我们已放弃了故乡的那种人文关怀。
在电影剧本里,柴春芽将故乡诗化,与现实当中的故乡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人类学上的变迁,或许更有深意一些。
是的,当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日渐被现代文明所取代,曾经的故事消失在记忆当中,这种可怕的现象所蚕食的是每个人的心灵。
柴春芽对故乡的依恋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是在于我们的故乡跟此相类似,在逐渐消亡的过程当中。
当乡村充满老弱病残、留守儿童时,乡村建设的主力为了生活得更美好一些,远走他乡,去往工厂、城市,成为经济的推手。当偶尔走回故乡时,那一种情感也是有着微妙的变化。故乡的生命在于自我更新,这一种能力现在已是贫弱不堪。
固然,随着打工者的财富累积,乡村的建筑、道路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可看着那道路上生满了野草、沟渠不见河水,真是有些伤心、失望。这或许是对故乡的预示:死亡终究不可避免。
可既是这样,故乡还是否有美好的明天呢?这一种疑问,或许我们得去别处美看看他们乡村的经验,并依此为参照,让故乡逐渐恢复生机,才是使故乡有复活的可能。柴春芽式的浓情挽歌,但愿不是最后的愿景。
原载于/《信息时报》
原作者/朱晓剑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四):梦里的天堂
本书为柴春芽的“故乡三部曲”之第一部,文字上充满了诗意,哲学和宗教气息,并且在书中作者以他那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宗教徒般的救赎情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诗意而荒凉的世界。人生经历了几许离乡,似乎也渐渐懂得了昔日熟读的那些思乡曲,慢慢体味出“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那种远离故乡还尚可解的落寞;也试着品尝了“近乡情更怯”那种回乡途中的忐忑与不安;更从父辈的身上看到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那种无可逆转的淡然的感慨……
诚然,每个离乡的人对于故乡都有一种别样的情感。柴春芽亦不会例外。
坦诚地讲,柴春芽的《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电影版并非我所喜爱之类型,但文字版的《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着实让贪恋文字的我不禁细细追读之。逢这样一行文字映入我的眼帘:“当我有一天发现,自己在城市里其实是个异乡人的时候,我想返回故乡,结果却是,故乡已死。”我没法抑制内心的震惊,我想那种怅惘是不可解的,那种无奈与绝望又必定是不可轻易言说的。
柴春芽以一种独特的意识流语言虚构了四个人物的死亡故事,并借来源于藏传佛教的宇宙四元素——水、火、风、地——的哲学观来对应四个故事;并以此为主题结构这部同名的电影。可能你会说以这样一种方式去探讨人的生存与死亡,或者说人的诗意栖息之所在——“故乡”的死亡,不啻于肤浅和消极。而我反倒觉得这是救赎灵魂栖息之所——“故乡”的一种极好反思和坦然至极的乐观,就如老子所云:“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应该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乡愁的质朴展示,也不仅仅是一种寻找乡土而不得的绝望悲凉与沉痛无奈。它应该是德国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追问——“存在何在?”的另一种生命书写,只不过被电影人柴春芽换成了一种可感可思的具象话语。或许,在现代化的盲目进程中,比比皆是雷同与无特色的建设,故乡的死亡无可逃避,也无处逃遁,但我们若从不去追问则是浑沌于世。柴春芽很勇敢,他让“故乡”死去,还以四种形式死去。柴春芽说他的表现方式是“裸裎”:“这种裸裎,仿如利刃,毫不留情地切开被政治宣传伪饰的假面,从而暴露出脓血与肿块之下潜隐多年的质朴与真诚,就像地层掘开,露出蓝色的矿脉。”恐怕我们真的只有把死亡拉近眼前,才能进行严肃的思考与痛快的抉择。我想这也正是“向死而生”的智慧所在:由于面对死亡才能加倍珍惜生命,进而活出存在的价值,甚至让死后获得另一种重生的可能。
所以,你会看到柴春芽援引《奥义书•第二梵书》的诗句:“一个人死后,身体回归地,汗毛回归草,头发回归树,血液和精液回归水,言语回归火,眼睛回归太阳,思想回归月亮,耳朵回归方位,气息回归风。”这是对于死亡的多么诗意化的解释。是的,故乡死了的话,故乡又将会在哪里?在梦里?在心底?还是在未知的未来?
做过这样的追问,我想在故乡未死之前,恐怕还可以亡羊补牢;哪怕故乡真的在某一天死去,仍然能为在他乡的某处寻找到故乡的影子,或者让它获得另一种形式的重生,以安抚荒芜了的灵魂。
原载于/《黑龙江日报》
原作者/洪艳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五):清醒的死亡
在这部充满着土地滋味和神秘气息的作品中,带给人们的是一场精神之旅,穿过物质丰盛的窗牖,审眺人们的精神荒原。人被现实物质需求的满足蒙蔽住双眼,六识感官的快感将精神的触角死死包裹起来,使精神在外在感官享受中“乐不思蜀”,当人终于想到精神需求时,精神已经处于死亡的绝地,贫瘠的精神荒原使人感到绝望,无助,死亡。
尕桂是从死亡中走过来的人,她寻着“湖”的传说回到了村庄—这块精神荒原。在这里,尕桂的依靠是那品患有梦游症的骆驼,这是人最忠实的伙伴,是人的行走在精神荒原中的无声引路使者,是人不离不弃不叛的伙伴。在人们的集体精神荒原上,能够救赎人的就是那传说中的湖,尕桂在最后的绝望中,听到了水涛声,似真似幻中,尕桂走向了自我的救赎……
尕桂的父亲意识到了人们精神的死亡,因为他闻到了村庄里飘荡的死人味道,但是他有心救世,无力回天,只是躲进棺材生活来躲避人们堕落的现实。尕桂父亲的形象是中国人“鸵鸟式”心态和行为的典型代表,是看透生活的“多余人”。
神灵附体的人寻到了启示,被七面巨大的镜子围裹着沉入了大地,是“神”在人间的死亡,神代表了宗教,宗教可以给人的心灵以净化,而现在,宗教已经失却了其净化人心,保持人的本真,追求救赎的作用。但是“镜子”的出现,就是在等待黎明的那一束光,一束可以通过镜子的发射照亮人心的光。
炼狱之火将世间的一切善与恶焚烧殆尽,于涅盘中等待人的寻找到生命之源—水,通过火的焚炼和水的滋润,人将会在黎明得到光,在光的照耀下得到新生。
……
尘归尘
土归土
一个人死后
就回到土地里去了
身体回归地
汗毛回归草
头发回归树
血液和精液回归水
眼睛回归太阳
思想回归月亮
耳朵回归方位
语言回归火
气息回归风
自我回归空
……
透响的诵经声,指引着人走向救赎。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六):已被目录所吸引
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观看第一遍时对于导演的讲述故事的方式还略感吃力,加上陇西当地方言,但看过第二遍之后,惊喜不断。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能激起人们思考的电影。如今电影同名书籍出版,对于作者在多领域的知识深感佩服。读罢书籍目录,便知这本书囊括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内容,并且很有可能电影中还没有明白的一些导演意图能在他的书中有所揭示。
柴春芽的每一部作品都让人眼前一亮,希望能继续保持独立深入的思考,创作出更多惊喜的作品给我们。
给作者致敬!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七):悲悯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为什么我们在有时满含热泪,因为听到了来自遥远故乡的消息,可是现在我们再也听不到了,并非源于我们源于生计或何种原因的逃遁,而是故乡已成为“故去的乡村”,消失的无影无踪,再也看不到了。《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作者柴春芽凭着新闻过来人的敏锐感,察觉到了时代的变迁和事态的扭转,在城市化快速进展的过程中,试图竭力挽留住家乡质朴的乡愁和久远的通灵传说,呈现粗粝乡村中悲凉的生活,以及无家可归的普世现状。带着对导演阿兰·罗伯-格里耶电影小说概念的信仰,柴春芽打破传统的时间线性逻辑和导演全知视角,还原人物本真的状态,通过神媒四舅姥爷、尕桂、皮影艺人杨家巴巴、四眼子婆娘等人的出场寻求不同的叙述空间,跨文体意识流实验作品,融合了诗与魔幻现实双重元素,以非虚构的笔法讲述一个独立电影导演回故乡拍电影的经历,同时以虚构的笔法讲述了四个人的死亡故事,从而探讨小说和电影的关系。
“对于没能去观看电影放映的人来说,电影小说还能够像一本乐谱那样被人阅读。”《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将小说文本和电影脚本放置在同一个文本之中,纪实与虚构、传说与寓言、自传与梦境、现实与超现实在视听中相融合,技法的革新是柴春芽作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意识到电影不是要给出答案,而是要引出疑问。于是,从对故乡的追寻延伸到对人生存的审视。
《奥义书》中说:“人死后,身体回归地,汗毛回归草,头发回归树,血液和精液回归水,言语回归火,眼睛回归太阳,思想回归月亮,耳朵回归方位,气息回归风。此时这个人在哪里?”这个哲学问题开启了小说的主题,在柴春芽看来,汉文化主张“未知生,焉知死”,在泯灭鬼神与死亡的世界的同时,还将神灵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其中不乏一种功利的态度。文化批评家特里林曾说:“在对待原始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既尊重,又警惕的态度留意其中可能存在的真理,但同时也要怀疑其中的神话和非理性成分。”的确,在半开化的农村,强大的巫术信仰支撑着仪式化的行为,萨满舞蹈、社火游行外显为精神的狂欢和对超自然的力量的膜拜,民间艺人为了动物式维持生计,毕生依靠残损的艺术过道德的生活,那些被城市人视为行将就木的祭祀艺术并未完全衰退。
“小说是一种用来探索超验世界的工具,也是我用来赎罪的忏悔词。作为一个有着原罪意识的人,我很幸运自己能够运用这种工具。”宇宙四大元素“水火风地”的理论来源于藏传佛教,骨头是“地”,血液是“水”,体温是“火”,呼吸是“风”,它们分解之后,灵魂才得以摆脱肉体。柴春芽因此设置了与四个符号相对应的人物死亡暗示了农业文明家园的消亡:神用泥土造人,人死后重归于泥土——神媒四舅姥爷盘腿坐在七面大立镜中间,闭眼睛讲述着他被神灵召唤的梦,身下的大地开裂,镜中互相映现的面孔逐渐消失,被大地吞没,大地复合如初;在封闭的空间里向往更加宽广的自由——患梦游症骆驼热卡亚的死亡和在棺材里关了七年之久尕桂愤世嫉俗、疯言疯语的父亲,他们分有着飘忽不定的基因;带着皮影的光辉一去不复返的忧伤和无家可归的恐慌——杨家巴巴扛着一棵插满皮影的榆树睡觉,梦见他扛着皮影树在冰冷的大地上漫游,三位皮影戏老人在大火燃起中高歌并逐渐消失,皮影以符号化的隐喻和家园最后的守望者一并吞没。
尕桂是柴春芽的代言人,在目击了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死亡事件——四舅姥爷沉入大地死亡、父亲的死亡、骆驼的死亡、三个皮影戏艺人隐匿于大火,以及女巫消逝于风中,苏干尔湖召唤着她虚无灵魂的复归,水的象征洗刷着对过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迷茫,成为灵魂的栖息地。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存形式的开启。
台湾联合文学称柴春芽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在他看来,悲悯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记忆如火焰召唤文字的神祗,为了活着回到故乡,以独立的态度和自由的气质,在沉疴缠身的民族得到心灵的解放。
2013.09.06 北京青年报
http://bjyouth.ynet.com/html/2013-09/06/content_8389.htm?div=-1
转载请发豆邮告知,谢谢。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八):故乡何在?故乡已死。
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北京,偌大的一座城市,却无我一个小小家,我在想,不行就回家吧,可是家在哪儿呢?父辈居住的地方?可是父辈们个个都在说,哎,现在村子里都很少见到个人影,静得让人难受。他们希望我能将他们带离那个地方,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出去了,带着小孩进城打工。只留下一些老人。可是我也在漂泊,在这座大城市我没有丝毫安全感,怕生病,怕有任何事儿。如果带上他们来这里,又能有什么幸福的日子呢?故乡已经今非昔比,那些记忆中美好的邻里玩伴,都已经变了,经济发展中,人们眼里多的是钱,而不是什么邻里。
故乡何在?故乡已死。
之前看过柴春芽导演的电影《我故乡的四中死亡方式》,如今再看他的这部小说,感慨更深。电影里面没有体现的很多东西,在小说里都完美地呈现。
已经看了一半儿了……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九):为逝去的故乡招魂
这是一部跨文体的实验性作品,用虚构的笔法讲述一部独立电影的故事,并用非虚构的笔法讲述这部独立电影的拍摄经过;这又是一部具有哀歌或者挽歌性质的作品,它以甘肃陇西一隅的某个偏僻乡村为个例,深刻揭示了在方兴未艾的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传统的家庭观念、伦理道德、世俗民情、宗教信仰等如何遭到彻底颠覆,中国乡村逐渐沦落,乃至最终走向瓦解、死亡的全部过程。作者柴春芽是一位作家,一位独立电影人,向以文学和艺术作为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唯一尺度,曾经做过媒体记者和报刊编辑,后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高山牧场义务支教。他在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中,有意识地打破一般电影所常见的线性叙述,以“地、水、火、风”的印度哲学中有关宇宙始基的四大元素为逻辑结构,让人物和故事为这四个抽象的元素服务,探讨“我故乡”的沦陷,以及故乡人灵魂的消亡,“为那段惨烈的历史作证”,“为那段丧失人性的历史保存证据”。他在文字版的《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中,既是讲述一部独立电影诞生的艰难过程,进一步展示故乡人当下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失落,同时也是诠释如何借助某一种结构,去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因果关系的链条,从而创造出一种能够真正与现实的真相相契合的艺术,并借以更多地体现出作者人道主义者的悲悯和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即是人的肉体“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消亡的过程。其中,骨头是为地元素,血液是为水元素,体温是为火元素,呼吸是为风元素,四大元素的分解,即意味着生命走向终结。柴春芽把言说的自由转让给电影中的人物,让他们依次说出自己的经历,并以电影中的四次死亡,来对应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他们分别是四舅老爷沉入大地的死亡,父亲沉溺于水的死亡,三个皮影艺人归隐于火的死亡,一个女巫消逝于风的死亡。他们是一种符号化的隐喻,各自象征着“我故乡”的家庭观念与伦理道德,世俗民情和宗教信仰,代表了“我故乡”所有的人文传统,以及寂寞乡村世代坚守的神灵。而他们的逝去,则意味着故乡的沦陷和人文的凋零物理意义上的故乡已不复存在,精神层面的故乡是否能够就此诞生?柴春芽其实正是以自己的电影和文字,为消失的家园号泣,为逝去的故乡招魂。
那么,故乡的消亡是否意味着一种文明的终结?抑或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开始?面对着渐行渐远的故乡,那丑陋的老房子,那倾圮的矮墙,那脏乱的街道,那在衰败中垂死挣扎的村庄,柴春芽一反众多作家和导演对以农民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的描述,力图在这片被遗弃的土地上,寻找到被忽视已久的尊贵。他说:“我的抱负是用艺术来塑造一种尊贵的人生,从而确立一种尊贵的人性的典范。”柴春芽一方面“裸裎”乡村土地的粗砺,仿如利刃一般毫不留情地切开被现实所伪饰的假面,从而暴露出乡村表层之下潜藏的质朴与真诚;另一方面,则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故乡人在贫困、苦难的重压之下,所从来未曾丧失的人性尊严。
柴春芽将自己的电影称作“哲学电影”,在他的文字间,也同样充满了哲学思辩的意味;他说他的电影不是给出答案,而是要引出疑问,他的文字也同样充满了上下求索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柴春芽认为,中国当下绝大多数的学者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和爱思爱智慧的天真,他们是权力的附庸。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污浊的传统,而他本人则逆风而行,只是为了获得精神自由而写作,把电影当作探索世界之谜的工具,不唯上,不媚俗,不趋时,茕茕独立,踽踽而行,在追寻理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对于独立创作和艺术,柴春芽这样说道,恰恰正是它们,“才是一个公民社会最有原创精神和自由气质的东西,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在心灵深处彻底消解奴役的酵素。”他以独立创作自度,也以独立艺术度人。
原载于/《深圳商报》
原作者/慧远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读后感(十):关于故乡的生死书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不论是书作,还是同名电影,注定是无法被广泛接纳欣赏的作品。粗犷的土地,错乱的时空,交替呈现的现实、记忆、梦境,连同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中阴世界,带着些许蛮荒的味道,遥远又赤裸地呈现在作品当中,它是关于故乡的生死书。“故乡”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记忆中是一个热切的、有着家长里短、婆姨叔婶,带着世俗、肮脏,又兼具几分圣洁温暖的家园。如今,村庄渐渐被城市包围、吞没,我们失去的并不仅仅是故乡,更少了一份与大地、自然的血脉联系。我们再也感受不到来自大地的呼唤,听不到自然的声音,人成了游移在土地上的浮萍。
在柴春芽的作品中,你无法直接找到故乡的死亡方式,只能一点点去感知,去体悟。书中,作者反复运用地、水、火、风的意象,不断地昭示,又不断地布下一个个世俗者看不清的迷局。狂放诗人的歌吟,睡在棺材里的濒死之人,不断梦游的人和骆驼,能够通灵的史天生,民间萨满性质的四眼子婆娘,一切的一切让人看不清,摸不透。恍恍惚惚的现实、梦境、预感、中阴世界轮翻交替出现,皮影艺人扛起的树旗,看上去像招魂的灵幡。
尕桂和腊梅是传承乡村体征的孩子。尕桂的绝望、眼泪,对已经消逝湖泊的找寻,令人感知她终将归于水。而腊梅,失去了姐姐尕桂和相依相伴的骆驼,在梦中不知所踪。三位老艺人在为老友、为这个颠倒的世界唱了最后一首挽歌后,消逝在熊熊燃起的火焰中。书中没有关于这些人物的结局,他们全都飘散了,在地、水、火、风中消散,最终印证了本书的标题——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
柴春芽的作品里有幽深的历史感、苍茫感和神秘感。我更喜欢在半梦半醒之间,去品读这样一部作品,太清醒反而看不透作者的真意,更无法理解那些绝望不甘的灵魂。该书是作者本人对其同名电影的深入解读,也是对电影录制过程的再呈现。在书中,电影本身所要讲的故事与作者拍电影的故事,作者自身的经历与长辈的经历水乳交融在一起,共同构造建起一本超越电影、超越故事、超越画面的纸上书。灵魂在书页间歌吟,文字拥有了比画片、声音更有质感的立体多维生命,这种全新的创作歌吟方式,尽管难以被大众接受,但相信它一定能在时光中历久弥新,供时光和岁月品味、把玩。
书中颇引人争议的地方便是对一些村民“超自然”能力的描写。民间萨满、通灵者,她们不断述说自己看到的不寻常世界,作者认为已经被世俗蒙蔽了双眼的人们无法理解这样的世界。我们身在此岸,就连对彼岸的猜想也世俗化了。我只愿将这一切当作一种灵魂的低吟,民间萨满是在安抚在世的灵魂。她们今天仍以半地下的形式存在。而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所有的人都将渐渐失去与大地、与灵魂的联系,同时对世界也不再敬畏。届时,民间萨满自然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或者躲入自己的心灵世界,再不与俗世交流。
柴春芽在书中说,他不喜欢中国式的线性叙事法,那不是真正的小说,他追求的是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艺术,与智力、想象力和道德判断力有关。无疑,真正有深度的作品必是经过千锤百炼,经“反叛之反叛”、“否定之否定”后的作品。这个反叛和否定的过程并非是针对一部作品的反复打磨,而是作家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用入世的眼睛,出世的思维,反复酝酿沉淀的情感,最后喷涌出来的人生体验,思想和文字唯有在浴火后方能成金。在作者的这部作品中,作者的体验是流淌于全书中的唯一线索,关于乡村、文化、文明、死亡、记忆,一切都是那么入魂入骨。作者刻画呈现的这些东西,同时也是我们自己遥远的记忆,陌生又熟悉,恍若隔世。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它死于城市的包围,死于自身的失血,死于人们失去与大地的联系,失去对自然的解读能力,我们再感受不到来自地、水、火、风的启示,真正死亡的并不是故乡,而是我们的灵性,城市里住着的是真正的游魂,没有来路,没有归途。
原载于/《佛山日报》
原作者/胡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