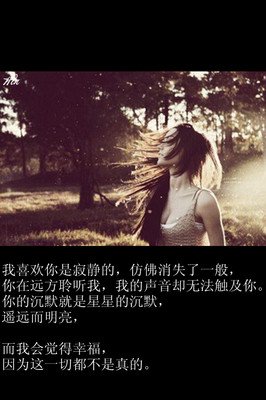神在远方喊我经典读后感10篇
《神在远方喊我》是一本由嘎玛丹增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2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神在远方喊我》读后感(一):神境与魂镜之旅
嘎玛丹增并非那种走马观花、喜好猎奇的旅行者,文集中的大多数散文既非通常所谓的游记,也非那种哲理散文。我以为,它更像是一次次回旋曲式的精神漫游,带给读者的感受如同一次精神洗礼和心灵历险。读这样的散文,扑面而来的是青藏高原的酥油气味和雪融般的灵魂气息。可以这样说,抵达心灵的神性光束,在他的字符里转化成一种天启般的悟性和忧思——他用那根在神境点燃的灵炬从内部照亮文字,为当下提供一面灵魂之镜,然后传递给他的读者。
——苍耳《神境与魂镜之旅》
《神在远方喊我》读后感(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人说故乡,不一定是出生的地方,而且你选择灵魂栖居的所在。第一次去西藏时,我不小心将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那里,从此魂牵梦绕。
读嘎玛丹增的文字,听他讲诉他所经过的那个神的故土上所发生的故事,自己曾走过的路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不同于市面上铺天盖地而来的旅行书籍或杂志用大篇幅的图片,再配以少量的或资料介绍式的文字或吃喝玩灯红酒绿的攻略,嘎玛丹增在每一次行走中都注入了自己关于生命、关于人生的体验和思考。对待现代文明和现代人正在走向何处,作者在文中发问,也让读者沉思。
他的文字,犹如一个出口,让读者能够从这趟浮躁纷扰又高速前进着的红尘列车上逃离分秒,让灵魂喘息片刻。又如一座灯塔,让漂泊已久的灵魂找到归家的路,一解乡愁。
见到林落先生对嘎玛丹增文本的简评,摘录于此,说出了我们这些读者体会到了,但无法准确表述的真实感受:
”嘎玛丹增的非故意行走、非故意寻找追问,漫漶在生活和文本里,对老读者已不止是一个标签,而是确定无疑的一种活法、一种存在方式。
所以总是一次次被作家耳提面命一般,甚至是逼迫你,看看杂芜和炫目的表面后有什么、是什么。
回答是个体的,追问尤其一生的那些追问,一定是人类全体的。然后结论不是重要的,问没问,生命却是一定不同的。
文字直至自己,成为灵魂的镜子,没有对神性的相信不行。正像作家苍耳先生在《神境与魂境之旅》的评论中,敏锐看见并简要列举的那些文章和段落和细节,其中和背后,无一不是有信人的洞察。
文辞是天赋,可以不羡慕;认知却是个人对小宇宙的挖掘,难不钦敬。
一直跟读嘎玛先生文章,超过对更知名更火爆的作家,即为此。一个个体,一以贯之,从无懈怠地向自己纵深走,其步型、背影,都是所抵。叶隐说过“任何事物的极致都不在它本身”,因为极致必是一种高度和深度不分的境地。
尤其必真实。所谓“世界还保存在天真的人那里”,打动人的是所有朴素看见所具之力量,是真实。“
《神在远方喊我》读后感(四):神的孩子都在旅行
神的孩子都在旅行
评《神在远方喊我》
神的孩子都爱旅行,他单纯地惊奇并相信:神在远方喊我。于是,他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旅途,探索每一个神可能存在的地方,去寻找神,去寻找那个未知的自己。
听从神的召唤,也许是因为对于纯真、质朴的向往,也许是出于对世俗的逃避或功利的厌恶,或许只是简简单单地向往心灵的安宁。所谓的安宁,只不过是灵魂的井然有序罢了。神的孩子把神当做信仰,是相信他所有思想的世俗和功利,在神的庄严和肃穆面前都会变得单纯和彻底。
旅行开始了,暂时搁下的生活算计和职业伪装,活脱脱一个生动的自己。用一种孩童时的最简单眼光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世界,为神性的光辉赞叹,为信仰的生活感动,不去索取,不去破坏,不去惊扰,你会发现,大自然依然是安静地接纳孩子。神的孩子看到了神,钱的奴隶看到了钱。不一样的是,神的孩子的心情会无比的平静,灵魂会无比的安宁;钱的奴隶心情会无比的激动,灵魂会无比的躁动。
现代文明对地球物理是一种照亮,还是遮蔽?不一样的立场有不一样的答案。我们知道的是,汽车开到的地方,神已经离开,贫富差距来到了这里,人类奴役自然用资源的获取计算进步的成就,人人用金钱的取得标榜自己的地位,他们在钢筋水泥的囚笼中,靠相互伤害来谋取生存和发展。我们确信的是,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伤害和损毁,将反过来毒害文明本身。神的孩子都在旅行,他们想寻找远方的圣地;钱的奴隶紧随其后,他们奸诈的笑声让神敬而远之。
历史一直是在曲线中发展,因果也在轮回中印证。发展中存在的悖论,一直存在于文明的旅程之中。玩累了的孩子,听到了村口妈妈喊着回家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回家了?伤痕累累的现代文明,在舔舐着自己伤口前行,当听到远方大地传来的“停下来,想一想”的神谕时,是不是应该调整方向了?
当习惯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时,人活在记忆里;记忆储藏在纯真中,到哪里去寻找纯真?神的孩子相信纯真,自然是回归那里的唯一途径;神的呼喊也许是在远方,也许那个远方是在更远方等你。
神的孩子都爱旅行,神的孩子都在旅行。曲直向前,福慧双全。
2015-4-28
文/乡村土狼
非常棒的一本书!语言太精美了, 简直处处珠玉。看作家本身也非常传奇。不要说三四十年前就用三百块钱走遍中国边疆大泽荒漠,想想谁真能把一个流浪的念头贯彻半生?不为猎奇、更不要说现在遍天下的有闲旅游! 作家真在用流浪的方式活着,令人敬仰。总在行走,皈依了流浪。走一路就想一路也记一路。不是肤浅的心灵鸡汤,但也不故意深刻,尽管足够深刻,那是心灵自有的质地。读这本书,感觉作家心底像有个万年失乐园,以至于一生都在不由自主地执拗寻找。流浪在外面世界,更流浪于内心灵魂。自觉的深度自我挖掘,尤以其中的《神启猎人》一文为最,绝对比《忏悔录》更真,超越了文学文字本身! 读这本书,作家本人的一生行迹,心灵世界的颠沛流离,都清晰可触。作家真实不虚地过着传奇似的人生,让人钦服。尤其感兴趣的,是有这么深刻认知后,还能对人对生命对世事对人心,有纯粹坚定的大信任,由此相信了世界真比看上去宽阔,生命比以为的尊贵,而天真是金子。 序言作者格桑梅朵,用一句话就说尽了这样看世界的功德: “世界还保存在天真的人那里”。(这位老师经典句子非常多) 作家上一本书《分开修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扉页词,标示格桑梅朵名字;书中很多警句箴言也这么标示,还猜想是否是作家自设的交谈对象。这本书一看序言,原来真有格桑梅朵其人。 细读下来,原来是“青梅之诺”!奇哉。 序言和后记,都精美深邃纯粹,过目难忘。 总之是一本经得起岁月的心灵游记,适合安静向内活着的读者。 诚恳推荐!(——谁在远方评)
《神在远方喊我》读后感(六):敞开身心行走,处处箴言警句
评论人:冀群
不能归类的书!不是游记,虽然以行走为线索;不是书斋作家,虽然哲思禅意漫漶在整个文本始终。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流浪的梦,可是,完整地实现了的人,是这个物质化功利化的时代,最稀缺的人!算计,生命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算计,这就使得真正的流浪,从实体到心灵的流浪,成了真正的梦幻,而最少的人能去实现它。 这个作家在我看来就是这少数人之一!最少的物质考量,最坚定的内心追寻者。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行走,从外向内,用脚步丈量山川大地,用勇敢和纯真打开内心。真实真诚,对待一生就是面对一个转瞬就失的礼物那么急迫,那么郑重,以至于看上去有一点不可思议。这应该就是一个以雪岳山川为阅读蓝本的人所具有的必然品质。 这本书里作家所行走的地方,并不陌生。但看它们的视角,绝对与众不同。有人说世界是心灵目光的样子,在这里就是非常好的验证。在作家笔下眼里,任何熟悉都有了新的面目,不只是思考,更是身心全部相溶于其中的看见和懂! 一滴水,一款石头,一个寺庙,在作家心里都是镜子,照到了灵魂的本相。 尤其作家对自己的真诚不欺,正像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格桑梅朵评价的:天真得像一个相信童话的孩子。 读过这本书,了解作家本人,就首肯格桑梅朵的序言题目,是对作家最好的评断,最深的懂: “世界还保存在天真的人那里”。 是一句箴言。也是对这本书的精髓的精准概括。 诚恳推荐这本书,给那些想在身外的虚无后、动议想关照内在的读者。 随作家一行,定不会空手而归。 尤其被其中的一些篇目震动:《世界还保存在天真的人那里》、《神启猎人》、《泽戈兄弟》、《神迹开口》,和后记《垂直的光线》。 这本书的最好阅读者,是相信生命相信爱、相信人比看上去尊贵的人。 非常棒的文笔,文辞纯然精美,甚至可以由此抄录出一本子箴言警句。而这只是作家文本的副产品,作家的行思才是稀少的盛馔。 诚挚推荐。
《神在远方喊我》读后感(七):世界保留在天真的人那里
西藏,人世间最后一块净土,无数人心目中的圣地。嘎玛丹增,本名唐旭,四川人,但对西藏的热爱,他给自己起了一个藏族的名字。藏语中嘎玛是星星的意思;丹增中丹指教法,增指固守、继承弘扬,合在一起意思就是持法的意思。事实上,嘎玛丹增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从《神在远方喊我》可以看到他的行文如同苦行僧式的行走,常涉足无人之地,行他人未行之路。
藏地旅行书很多,写旅行游记的,写所见所闻的,或者前行采风者,徒步朝圣者皆有,嘎玛丹增的文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文字深刻而带着灵魂的印记,他的这次藏地行走,也被称作“一个孤独的行者心灵朝圣的笔记”。藏地于他,就像“一束垂直的光线,从正午的天空落下”,那是被这束神光唤醒的梦想和希望,那是沐浴神光的今生今世,或者永生永世。藏地于他,是醍醐灌顶的人生彻悟,也是他在般若路上的踏刀山,蹈火汤的人生信路。
作者嘎玛丹增,被誉为当代行走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文字也常散见于各大报刊,曾获“冰心散文奖”、台湾“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林语堂散文奖”等。我读嘎玛丹增的记行,读出的不仅仅是藏地行的妙景人伦,更是虔诚与庄重的心性,是饱含人生热量的自由和神性的探索。《银雪贡嘎》《毛垭大草原》等篇都非常优美壮阔。而这些,对于有钱有闲的旅行,太难得,让人钦羡,也更有质感和人文深度。以前有去过藏地的朋友向我说起他的遇到的“神迹”,无意中走入某处圣地,但回首想再次重游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刻意却无所得,或许这就是这份神迹想传达的自然和顺其自然。
嘎玛丹增的文字又是散文化的是冷静的,是丰富和优美的,甚至单篇来看可作一篇篇赏心悦目的美文。他是修道者,于是总是以感恩之心悦览所见,他边行边修行,在山川之间与天地同在,与万物同在。感恩之心,感念大地,山泽的赋予,也同样感恩存在本身。
喜欢他这样的漫游,也喜欢他这样充满哲思的表达,融入个人独特心性感悟的文字超越了浮华的本相,回归心灵的自由盛境。在毛垭大草原开篇,嘎玛丹增说,“翻过去,就是天堂”,如今想说,翻开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天堂。
《神在远方喊我》读后感(八):雪山、河流、足迹
雪山、河流、足迹
读《神在远方喊我》/by烟波浩渺1980
最近读过不少游记,风格各不相同,有的注重旅游攻略,有的是萌系绘本,有的是个人心情记录。作为读者跟着作者的脚步、心情和文字一路前行,实现身体和心同在路上的愿望。即使没有身体的施行,我们的心还是向往之。
藏地风物,几乎是很多人都想去看一看,游览一番,哪怕是走马观花也好。由于很多原因:时间、身体、金钱和机遇都可能与之错过,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再的错过,就像是语文书中蜀僧至南海的故事,如果不下定决心,也只能是永远看别人的身体在路上行走。
当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的雪山、河流,当我们面对心中的旅行圣地时,心中是无限的感慨,渴望借着那遥远的风景洗涤心灵,而“久居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面对高山大川时,心胸变得更加开阔起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游记,更多是有很多人文思考在其中,例如藏民家中豪华的经堂与简陋的生活居室给人的震撼;现代化对风景的开放和破坏;金钱与生活的碰撞,像书中所写采挖虫草的事情;带着草木灰的炖土鸡。
看到本书的“副标题: 川藏、吴哥人文旅行纪事”,一下子就吸引到我。尽管我短期内不能成行此线路,但是内心的渴望从来不会因为岁月的消磨而变淡。作者嘎玛丹增,一位孤独的行者,带着侠者气,带着现代人的思考,结交着原住民,写出心灵与雪山河流的对话,用孤独做注解,看他所去的地方很多都是一般旅行者很难到达的地方。
本书图片很大气磅礴,我喜欢那些于雪山、河流相关联的图片,面对这些不言不语的物体,在高原,在很难接近的地方,他放佛是神的代言人,虽然我非宗教信仰者,也愿意相信自然中某些神秘之处,正是这些不能为人所知的庞大山峰,连带着那片土地、天空中飘着的云彩都充满了神性,遥远不可捉摸,而我们也只能匍匐在地,高山仰止内心充满敬意。还有生活那种艰苦环境的住民,他们的生活和信仰一切都是那么与自然切合,毫无违和感,既不抱怨连天,也充满了自然没敢,他们不困于生活,乐意把更多金钱和经历放在神的面前,对自己严格,对神佛宽容信仰。这一点是我不能理解的状态也是我充满好奇的地方。
通过看作者嘎玛丹增的游记,会发现他到一个地方不是简单的去一趟就完结,而是更多体验和观察那里的环境和人文,也会写一些接地气的生活故事。例如他结交的好友豁达的泽戈兄弟,泽戈愿意带他去旅行,带他体验生活,愿意替他出资出书,送他虫草,嘎玛丹增则为泽戈兄弟的孩子在成都求学费尽心思。这是感情融合的生活状态,就因为所以的来来往往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结下的深厚友谊,不能言说,就如武侠小说中意气相投结为异性兄弟一般,豪气冲云天,这就是现实版的武侠情结,让人看的非常感动。
那些面膛黝黑的康巴男子,在草原和城镇中穿梭。那些盛装的藏地女子,她们将万贯家财穿着身上,他们将黑发结成密密麻麻的小辫子寄托着情思,放飞着梦想。
书中的游记分为川藏和吴哥两部分,我比较喜欢川藏篇,所以写的这部分比较多。
川藏、吴哥这些旅游必去之地,什么时候能不看书,自己去一趟啊。
2015年5月6日星期三
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者或2933702061@qq.com。
《神在远方喊我》读后感(九):万物皆有神性
嘎玛丹增的字是走心的。
他的散文,是可以让读者从嘈杂琐屑的境地到安静详和的境地,是瞬间的事。
在嘎玛丹增诗意精炼语言直白的文字里,他构建了自己的文字宗教。恍若暗夜里的一簇光亮,行者趋步。而读者沉溺。
“用我的脚走你的眼”,这里,万物皆有神性。无论是山川河流,古刹旧物,还是石头鸽子和羽毛。我们跟随感受的不但有自然景观訷迹般的存在,还有神性和人性相斥相融的过程展示,更有对人类自身灵魂的拷问及人性的透彻剖析。
这是一次将信仰植入人间烟火的行走。从青藏高原到贡嘎雪山,从甘南草原到澜沧江,从湄公河到吴哥窟。人类信仰缺失的诘问,生存条件贫瘠的痛。对话,自省,修行。
“庄严认真的简单有信”,我以为这就是嘎玛丹增的生活态度。我以为这就是他的文字欲呈现我们当下精神家园生存更为内在的核。
祝福嘎玛丹增!
《神在远方喊我》读后感(十):在行走中思考
在行走中思考
文/ 孙牧青 来源:《中国三峡工程报》2015年5月9日8版
试图把当下的散文贴一个不同的标签是荒谬的。但嘎玛丹增的写作却始终奔向一个强烈的主题——青藏高原那片神秘的远方。作家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梦一样的精神情结,他渴望山永远是青的,水永远是蓝的,我们的心灵永远像云朵一样洁白无瑕。
最早读到嘎玛的作品是在几年前。那篇《乡医刘汝北》,让他的名字与实力散文家划了等号。说句实话,在当下的散文写作中,真正打动我的作品不多。嘎玛最初的写作与他后来的写作好像有些不同,在题材与文本上有了一些差异。他早期的散文比较着力于文章的氛围与内在的节奏,是属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美文。在后来的写作中,作家好像有意在确立一种属于自己的文体,我姑且将其命名为“地理散文”。
他的散文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博大恢弘的气度,篇幅一般都很长,在诗性的叙述中向你展开一方水域,一方风情,让你顺着他的导航去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但他所创立的这种崭新的散文文本又绝不同于一般的报告文学,在嘎玛的散文中会出现许多具体的数据,这是在传统美文中应该竭力规避的东西,如果这些成分太多,将会削弱其作品的整体格调。但就其本身来讲,地理散文可能在兼顾文学性与地理咨讯的完美统一。如果仅此而已,它是无论如何也称不上美文的。嘎玛将散文的地理性与文学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正是其不断探索不断臻于完美的过程——他成功了。
我在想,嘎玛为什么这么做,这样做的意义在哪儿?或许,他可能想在散文的文学价值以外找到另一种文本的实际价值。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我曾经说过,散文要怎么写,真的是八仙过海,异彩纷呈。关键是,第一要真实,事实与情感的真实;第二要有文学性,散文的言语必须要比小说的语言更精粹,更唯美,更诗意;要给让人行云流水般的阅读快感,要像音乐一样起伏跌宕。
但凡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写景与写场面最难。你要写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其实是非常难的。在行文的过程中又不能有停顿,一停,气就断了;你勉强衔接上了,文章的瑕疵就出来了。嘎玛是一位武功高深的作家,举重如轻。写大散文,对一个人的文学修养与生活积淀,以及精力,都是一种较量。它与写长篇小说是一样的道理。
嘎玛不是纯粹以文字为生的作家,他去过许多方,一直在行走中沉思,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能始终保持一定的新鲜度,就像刚出炉的烧饼,外黄里酥。
散文写作重在发现,你的写作必须呈现出一定的精神高度。在嘎玛所有的作品中都透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那就是对日益消失的诗意山水、诗意乡村、诗意民风的惋惜之情。这种精神深处的忧患意识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的道德与良知,同时也构成了一位作家宿命般的文化自觉。
譬如鲁迅,在他一生的写作中都贯穿着一个主题,他毫不留情地用他投枪匕首般的如椽巨笔剖析着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他试图在精神上拯救当时麻木的国民。散文家筱敏一直在为民主与法制而呼喊,陈丹青先生一直在为中国的教育体制而忧心忡忡,等等。
我以为,一位作家一旦选择彻底放下自己的是非立场与公民意识,那么他的文字就必将浅薄苍白。
嘎玛丹增的地理散文呈现出敞亮澄明精神气象,有引导读者走回大地根部的深度意愿,不同于普通的游记,耐读,知识容量大,给人以诗性和神性的身心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