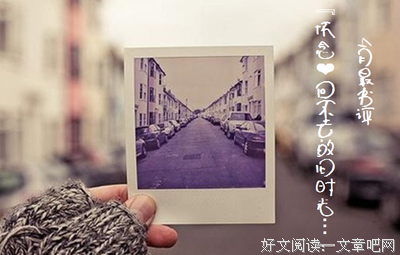《騎士団長殺し》的读后感10篇
《騎士団長殺し》是一本由村上 春樹著作,新潮社出版的単行本图书,本书定价:JPY 1944,页数:5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一):集体记忆与个人——《刺杀骑士团长》中的“历史”
2017年村上春树又一力作《騎士団長殺し》问世,书中所提到的南京大屠杀问题也成为了中日议论的焦点。《騎士団長殺し》小说本身并非直接涉及具体的战争与历史,但小说的结构试图在讨论“历史”这一概念本身。“历史”永远没有绝对客观的记录,“历史”也是建立在无数个人叙事与记忆之上的集体的叙事。而生活在当下时间点的我们与“历史”又如何产生联系?“历史”对于个人而言是否是无关紧要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是怎样的?对我而言,《騎士団長殺し》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故事。
“我”是一个画家,与妻子婚姻破裂,我住到了一位老画家雨田具彦的房子中,而在脱离“我”的日常的空间下,“我”的奇遇开始。“我”发现了雨田具彦藏在阁楼上的一幅《刺杀骑士团长》的画,也遇见了那个在祠堂附近的洞穴中摇铃铛的“骑士团长”(idea)。“我”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奇遇开始相互发生联系,但又无法明白“真相”究竟是什么。“我”试图从雨田具彦出发去寻找《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真谛和隐藏在这幅画下的历史。
与“我”辈而言,活生生的“历史”仍旧还存在,它掩埋在不可知的沉默之中,“历史”还同上一辈人的记忆相关联,“历史”在战争时期层层审查的书信之中(雨田具彦的弟弟),在那些审查人涂黑了的字句之中,在自杀了当事人的记忆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的烧毁的书信中,“历史”还在那些年迈失忆的老年人的回忆之中。就这样,雨田具彦曾经在奥地利经历的暗杀事件,和雨田的弟弟在二战被派往中国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逐渐拨云见日。“我”是同“历史”相关的,“我”不再是“历史”之外的事物。“我”需要去寻找“历史”。
今の父はもう、(略)混沌とした、ほとんど泥沼みたいなことになっている。(笔者译:如今我父亲的记忆,已经是混沌的,如同沼泽一般了。)(『騎士団長殺し 第2部』・182页,引自新潮社2017年出版的日文原版,下同)即便如同沼泽一般的记忆,也要抛开已有的虚假的观念,从不想触碰的记忆中撕开伤口。于是“我”第一次来到雨田具彦的面前:
そのようにして雨田具彦は歴史の激しい渦の中で、かけがえのない人々を続けざまに失ってしまった。また自らも心の傷を負った。そこで彼が抱え込んだ怒りや哀しみは、ずいぶん根深いものであっただろう。何をしたところで、世界の大きな流水に逆う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無力感、絶望感。そしてまたそこには、自分だけが生き残った精神的な負い目もあった。だからこそ彼は、もう口を塞ぐものがいな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ウィーンでの出来事についてはひとことも語ろうとはしなかったのだ。いや、語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だ。(笔者译:就这样,雨田具彦逐渐失去了历史漩涡中不可或缺的那些人们,而他的心自己也伤痕累累。他所隐忍的愤怒和悲哀如此之深,无论如何都无法逆转世界的洪流,他陷入了无力和绝望,同时又承受了自己苟活的精神负担。正因为如此他缄口不言,他对于维也纳发生的一切只字不提。不,是无法诉说。)(『騎士団長殺し 第2部』・314页)“我”让记忆苏醒,让腐烂的伤口再次曝露在阳光之下。我在雨田具彦面前杀死了骑士团长。
しかしながら、肉体的な苦痛も戻ってくる。彼の身体は肉体的苦痛を消すための特殊な物質を分泌している。(然而,他的肉体的苦痛逐渐苏醒。他的身体为了消除痛苦而分泌着特殊的物质)見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を見ているのだ。(他正看着一定要看的东西。)そこにあるのは、おそらく、彼自身の精神の深い苦悶なのだ。(那里,恐怕是他自己精神中深深的苦闷。)我拿着雨田具彦的儿子政彦亲手研磨的刀刺向了骑士团长:諸君は今ここで邪悪なる父を殺すのだ。邪悪なる父を殺し、その血を大地に吸わせるのだ。(诸君现在是在杀死邪恶的父亲,杀死邪恶的父亲,让大地吸满这血液。)记忆的再叙述与苏醒是痛苦的,但即便如此我们需要去面对那些历史,这似乎暗指日本对于二战的问责。而对于罪的审判既是父辈的痛苦又是对我辈的试炼,也同时意味着拯救秋川所象征的下一代(小说中没有把我刺杀骑士团长同秋川的失踪设定为绝对的因果关系,二者在冥冥之中互相联系)。我”杀死了象征着“邪恶的父亲”的idea,但其实“骑士团长”作为一种idea是中立的,既非恶又非善,杀死的“邪恶之父”或许意味着捏造“历史”的恶,或许也意味着审判父辈在“历史”中留下的罪恶。而这一罪恶的审判也是由idea(骑士团长)提出的,是经由“我”辈之手去审判的。正如骑士团长称我为“诸君”,“诸君”一词并非单数,而是复数,它所象征的绝非小说中个体的“我”,是包含你我的,包含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个体是在集体之中的,每一个个体才是集体。
小说的最后,作为弑父的结尾,我和柚子又再一起重新生活,我之于柚子的孩子,色免之于秋川まりえ,血浓于水的父亲不再重要,正如小说中所说,“人間と人間との関係というのは、そんなDNAだけのことじゃないんだ”, 人和人的关系,不仅仅靠DNA的维系,属于集体记忆的“历史”或许并非你我个人的直系的父亲的记忆,但个人之于“历史”是责无旁贷的。“父亲”不再存在,但存在的是我们每个个体之间的、无法切断的关系。
最后,需要承认的是,这部小说结构上的确再次陷入了村上春树式的叙事,两层世界,“我”寻找某一个冥冥之中注定的东西,现实和非现实的交叉等等。特别是第二部中小说叙事语言略显冗长,情节叠加反复的略显啰嗦,想必是有目共睹的。在2017年10月东京立教大学举办的日本近代文学中,对于这部村上的新作,许多学者也一致认为小说“最後は、ちょっと残念でした”(结尾有些遗憾),主人公在唤醒雨田具彦之后故事似乎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对于讨论的主题有些半途而废。但即便如此,小说中在描写雨田具彦的记忆苏醒的苦痛的叙事张力是非常好的,同时在亚洲对于历史问题争论之下,村上这部小说的反思是非常有意义的。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二):《刺杀骑士团长》读后
“从那年五月到第二年初,我住在狭窄山谷入口附近的山上。山谷内侧的夏天,雨水一刻不停地落下,山谷外侧却大体放晴……那本是孤独静谧的日子,直到骑士团长的出现。”(『騎士団長殺し(新潮社)』书封介绍 笔者译) 我不是在横滨,就是在去横滨的路上。二月已近尾声,雨后初晴的下午,我从横滨站下车,沿高岛水际线公园的海滨石子路,用大约三十分钟,穿过低压下来的高速路桥,绕过铁道模型博物馆前的雕塑,贪婪地吞噬空气里的养分。行人除我之外,只遇到一个穿着深色旧大衣的初老男人,和系着厚厚围巾的母女(也许是母女)。天与地在远处连成一线,巨大景色在视野里展开,原来已经是周三了。
读书是一项危险的作业,与未知的相遇,可能突然改变预定路径,无情而强烈。小说尤其如此。从“无”中构筑出的故事,拥有了具体的生命,制造了原理的模型,内藏了一切可能的真实。没错,我正是在阅读小说的间隙来到横滨的。在读完《刺杀骑士团长》第一册的节点,暂时从故事的现实回归现实的现实,感受书里书外的风,空气,色彩与律动。
从万里桥到浅山桥,我穿过稀疏的水道,空地与线路,来到港未来的高岛中央公园,为了去附近一家专门放映短片电影的影院看奥斯卡特集。公园里多了小孩子(有一半是头发金色的外国人)的笑声与色彩,只有他们的衣服是彩色的,好像停在码头客轮的喷绘。公园左侧是闲置地,裸露的黄土偶尔长出顽强的植物,简单而矍铄。土地的最里面,用铁丝网围住的,好像是进行到一半的工事。唯有一件怪异的膜结构扁平建筑,好像隈研吾的自立生命型设计,或者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动态雕塑。
原来是一家叫木下的马戏团,今天晚上的公演又是满场。父母弯下腰,牵着小小孩子的手,队伍已经排开了。他们的身高对比,让我想象到人站在长颈鹿前的样子。马路对面的人,以另外的队形站了两层,有人手扶靠在地面的大型标牌,有人把稍小的举高。仔细看时,原来是反对马戏团的抗议示威。小标牌写着“动物虐待”“禁止一些形式的动物表演”“提倡没有动物的马戏”…。地上大标牌的标题写着“不能让孩子看马戏的十个理由”,下面密密麻麻挤满了小字(大概是解说的内容)。
马路两旁构成了一幅静止的对峙。每一边都是无声,每一边都遵循着自己世界的规则与信仰。好像冷战隔开的透明高墙。不,他们的互相无视还无法构成一场战争,不过那宁静里有一种杨德昌电影式的张力。
我只是从人群中间穿过的一介路人,好像飘过那条分隔“有”” “无”河流的小船。从此岸也许无法眺望彼岸,但故事的搭桥,可以从技术上延伸视线。表面平静的水下,没有丧失原始的急流。我想起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the river》,想起免色的话“你知道真实带来的孤独有多大么?”这天上映的短篇电影之一,是《bear story》。
《美国之音》报道说,玲玲马戏团(Ringling Brothers-Barnum & Bailey Circus)将在5月21号关门。从1871到2017,走过一个半世纪的玲玲终将在告别公演后解体。永恒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半世纪很短。19世纪,泰国连体人“昌“和”恩“加入玲玲马戏,成为世人的谈资。这对无法分离的兄弟购置了黑奴,娶了双胞胎姐妹,分别生了12和10个小孩。他们睡在一张特制的四人床上,直到双胞胎姐妹失合而分居,连体人只好轮流住到对方老婆的家里。如今,连体人死了,马戏黄了,真实带来的孤独有多大?纸月亮的世界,也会流出真的血。
从横滨回来后,因为要处理几件其它事情,真正读完小说的第二册,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我用三月末整整三天时间,除去进食与睡眠,把它快速读完了。视线从书页离开的那一刻,冬天的风已被迎接春天的风代替,青叶台公园那株新移来的河津樱已经结束花期,长出了柔布般的绿叶。书里的时间度过了九个月,书外的时间是它的九分之一。
我不是好的小说读者,上次阅读超过1000页的长书(小说),已经是7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读的是台湾版的《1Q84》,全部读完三册实际上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发明了一种对话的阅读方式(人与书对话),时而会穿插进其它内容,读书在书外。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宗教的研究便是从那时候起步的。我的另外一个收获是训练了快速阅读繁体字的能力。其实慢读繁体字也有它的好处,阅读简体因为太熟练了,反而容易错过很多细节。换读繁体,好像从新干线换乘各站停车的当地线路,进入视野的风景自然增多起来。有时候,我们无法了解太熟悉的东西,这样说不是矛盾修辞法(oxymoron)的文字游戏。临摹字帖总是学不像的时候,把字倒过来看,其中的真意马上浮现了。我盯着《镜子国的爱丽丝》中逆转的文字看了很久,陌生感的营造让我们回到一件事物的初始。
七年后,当我阅读完《刺杀骑士团长》,像当年熟悉繁体字一样熟悉了日语,它们从各站停车变成准急,特急。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变成比新干线还快的磁悬浮。生活在外语的环境里,重新拾起久不阅读的简体字,反而生出一种纯粹简单的美感,因为看风景的位置变化了。
《刺杀骑士团长》的结尾处,有几条没有回收的伏线,绘画这条主线却一以贯之。画家和小说家的工作是相通的,只是技术不同。索亚(Edward W. Soja)早就批判人为的学科划界,他们死守在自己的井底,不知道天空是相连的。实际上,我常在数学中找到语文的灵感。我不仅是严谨的宗教研究者,还是很好的绘画鉴赏家。阅读两册小说的间隙,忙里偷闲,去横滨看了日本画和洋画的回顾展。我不是在横滨,就是在去横滨的路上。
日本画和洋画构成了小说的重要轴线,《刺杀骑士团长》这个很西洋的名字其实是一幅日本画。日文语境中的日本画和洋画都指日本人的绘画,只是风格,绘材不同而已。日本画填进动物胶质,金银薄粉,表现的可能性绝不输给洋画。竹内栖凤的《斑猫》是日本画,岸田刘生的《丽子像》是洋画。日本画的概念是通过与洋画的对比才出现的,没有南极以前,北极的概念是多余的。
小说也是一种绘画,它的画面让我最先想到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神秘邻居盖茨比的豪邸。不知道为什么有钱,反正就是非常有钱。《刺杀骑士团长》中的重要人物免色,让人想起盖茨比,也想起村上春树上一部长篇《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中的多崎作。事实上,戏仿(parody)是村上春树的常规技术。《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什么》仿卡佛的《当我谈爱情时我谈什么》,《东京奇谭集》仿保罗·奥斯特的《红色笔记本》,《1Q84》仿奥威尔的《1984》,老大哥成了小小人。但是他的戏仿,往往生出独自的光辉和魅力。好像鲁迅从俄国无名作家中吸收灵感,贯穿到自己世界里去的时候,反而比原作取得更大成功。
村上春树这一次不仅戏仿别人,还戏仿起自己。秋川麻理绘让人想起《1Q84》的深绘理,雨田具彦让人想起天吾的爸爸,骑士团长让人想起little people。戏仿的艺术实践盛行在1970年代的日本,由后来成立“路上观察学会”的赤瀬川原平等人发起,最后甚至上升到法律问题的讨论。东京站画廊最近举办的《二重之声 戏仿的世界》对这次艺术潮流做了完整的回顾。
村上春树在《作为职业小说家》一书中谈到,日本文坛一直把他的作品视为对欧美文学的拙劣模仿,直到他的“模仿作品”在欧美自身获得巨大成功与认可。好像他2016年获得安徒生奖的发言,有光的地方便有阴影,不制造阴影的光不是真正的光。没错,他只是把事物的另一面补全而已。《刺杀骑士团长》的主人公再一次下到“深井”,他和免色的身份调换了,他不是乞求涅槃的禅定老僧,而是决心与自己内面的阴影对决。勇敢与坚强的人,经过牺牲与试炼,才能看到火星的美丽运河。还有一刻,直到死亡把两人分开。
地下世界最危险的是“二重隐喻”,没有名字的主人公与免色形成了完美的镜像。他们像所有人一样,把生活中的秘密伤口藏在衣服的深处,期待用象征的暴力达成隐喻的和解。显露的意志和移行的隐喻,读书是最危险的行为。书中的所见其实都是自己。张爱玲在《论写作》中说,“作者给他所能给你,读者拿他所能拿的”。她说得太简单了,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理想的原型让人思之落泪。小说毕竟永远是读者责任(caveat emptor)。我们不像海豚,可以把左右脑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读者才是永远的西西弗斯。
草间弥生用绘画与自己对决,村上春树靠写作。如果没有这些技术与媒介,他们一定是被核心世界抛弃的outsiders。《你看起来很好吃》(『おまえ うまそうだな』)中暴龙没有吃掉小甲龙,远远目送了它。但是暴龙转过身,会继续吃掉其他大部分甲龙。生命的自然现象,我们很难去违背。但是只要你意识到它,通过一次目送,其实就已经达成了和解。“只救文姬一人归”有它的无奈与温柔。
阅读两册小说中间的一个月,日本发生了两件新闻。一件是筑地鱼市的豊洲转移问题。东京都议会设立百条委员会,对前知事石原慎太郎进行了“证人喚問”。84岁的石原两年前罹患脑疾,损毁了埋藏记忆的海马,连平假名都不认识了。第二件是森友学园的国有地买卖问题。议会行使国政调查权,对笼池泰典进行了证人喚問。问题涉及到安倍和昭恵夫人。本来,在收集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先经过众议院的参考人招致,再进行证人喚問,最后进入参院才是正常步骤。这次的喚問过于仓促了。美国新闻周刊日本版评价其为“拙速”。当一切都可能成为被利用的道具时,善恶的分界已经蒙上迷雾。本体迷失,大众主义抬头,不正是今天世界的倒影吗?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早在1920年代就指出,渴望合法食料的议员,持续着野蛮狂热的杀戮,甚至不惜相残,这些都是被合法化的残忍行为。
从历史上看,今天的德国继承的可能正是条顿骑士团。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忘记日本曾经的恶行。小说中,雨田具彦的钢琴家弟弟被迫参加南京大屠杀,弹惯钢琴的纤细手指还不适应笨拙的屠刀,退伍后他只有靠自杀重新唤回生命的尊严。雨田具彦从被纳粹吞并的奥地利秘密遣返,战后复出从洋画改画日本画,却一直把《刺杀骑士团长》封锁在屋顶的阁楼上,老后罹患阿兹海默症却还是心有所念,幻化的生灵从伊豆高原回归小田原的画室。对比完成度很高的《刺杀骑士团长》,历史上很多画是没有画完的。圆环还没有闭合。作为意念(idea)的骑士团长死后,隐喻(metaphor)连接了一切,主人公在不断变窄的地下洞穴听见了自己死去的妹妹的声音。听见了唐娜安娜的声音。他杀死了骑士团长,但他不是唐・乔望尼。当一切成为隐喻,现实的本质也许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英国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现代再归性的概念。《刺杀骑士团长》却留了一个缺口,无面人终究会送回企鹅,索要自己的画像。
在为无面人绘制肖像以前,我需要再去一次横滨。
3月30日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三):让我来驳一驳你的自信
本想着上来查一查,看看赖小姐这边有没有把这本书先翻译出来,毕竟新作都是台版要出来的快一些。没想到随意点开评论区,却发现大部分的书评跟书几乎都毫无关联,还能上热评,实在是让人无比惊喜,比如这篇
“村上的“自信”哪里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415438/。对于骑士团这本书,我还没读过,对书的内容暂时不发表评论,但由于豆瓣限制必须评分,就先打3分,回头读完我会再写一篇书评并重新打分。不过你所谓的书评也基本上好无营养可言,通篇充满着酸臭的妒忌感和宣泄私愤的愉♂悦感,跟书的内容没什么关系。作为村上一枚小读者,我想来看一看,你写这篇“村上的“自信”哪里来?”的自信,又是从哪里来?
1本来1Q84就已经乱凑了3本书,差的要命,没想到这一本还要差。这样的作品不过是圈钱和讨好中国的下沉之作,村上春树最好的作品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一部文学作品是好是坏,每个人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你觉得差的要命,而且这本骑士团更是还要差。这一点,我不驳你。
但,你说这样的作品不过是圈钱和讨好中国的下沉之作。
圈钱?excuse me?你以为日本的作家的版税收入跟天朝一样?你以为是咱可怜的莫言爸爸?版税那么点准备开开心心拿诺奖奖金在北京买套房却被网友打趣说根本搞不清楚状况?村上需要圈钱吗?光是13本长篇小说就出了多少国语言再版了多少次?60岁的人要圈钱用得着每天早上四五点就醒开始写长篇小说?干嘛不出村上朝日堂五六七八九十?新书出版的时候怎么不开全世界签售会?干嘛不出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续集之大蘑菇和难挑的凤梨?大芒果和难挑的荔枝?大牛油果和难挑的哈密瓜?开辟网站专门回答读者问题都出了几本书了要不咱也搞个收费回答跟知乎live一样?日本出版社出钱让村上去世界各地随便玩只为要一篇游记村上怎么那么傻送上门的钱都不要?每年跑那么多马拉松也没见要去当运动健身的代言人?要圈钱怎么不再回去国分寺重开peter cat一杯矿泉水定他妈的1万日币我就不信没人去?药店碧莲吧动不动说人圈钱,btw,你懂圈钱吗?
讨好中国的下沉之作?excuse me?你以为是你妈那不争气的儿子要讨好你跟你说您今儿真漂亮但是你看我把人家女孩肚子弄大了要不您给我点钱我让她自个儿去打个胎?你以为村上是狗?还讨好?你以为是库克看中中国市场发布会专门提中国还特地跑到中国见领导人?村上除了写奇鸟行状录的时候坐火车路过东北因为眼睛有疾临时下车买药,还有正式的出访过中国吗?照你这么说村上写地下去访问被沙林毒气伤害的日本民众是为了给新书做宣传?村上不顾国内军国主义分子威胁去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当着人以色列总体的面抨击以色列,呼吁减少战争,他是脑子进水了还是什么?骑士团长里面写的南京大屠杀难道不是事实?村上一个日本人顶着国内多大的压力敢于说真话说事实,你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认可就算了,怎么就他妈的讨好了?中学老师怎么教的你?照你这么说那小平爷爷搞改革开放是不是为了讨好英美资本主义?你用的苹果手机吃的肯德基麦当穿的阿迪耐克劳是不是就是卖国贼?我侯亮平搞反腐是不是为了讨好沙瑞金田富国再进一步颠覆汉东政权?药店碧莲吧动不动说人讨好,btw,你懂什么叫讨好吗?
就算是他写得最好的“冷酷仙境”(个人认为)也不觉得是能获得诺贝尔的程度关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不是村上写的最好的书,这一点我不同你争论,因为没意义,我粗粗略略看了看你的阅读历史,村上的长篇也就读过三本:挪威的森林,1q84,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剩下的也就一些乌龙茶类的中篇和随笔而已。我跟你聊诺门坎战役有用吗?跟你聊海豚宾馆有用吗?跟你聊山德士上校有用吗?药店碧莲吧,你以为是玩狼人杀我他妈就聊你ppd盲跳预言家我就是盲毒jy怎么了?
还有你读的其他书,基本上都是畅销书,大概就是这段时间市场推什么我就读什么,东野圭吾,村上春树,郭敬明,莫言,大概就这些吧,真是让人惊喜又惊喜。
东野圭吾,不奇怪,我也读,畅销书嘛,读起来虽没什么营养,但是爽快。虽然书的水平参差不齐,上限和下限都比较高,但瑕不掩瑜,不否认东野是位优秀作家。另外作品水平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但我奇怪的是,你一边在冷嘲热讽,“呵呵,以后不会买东野圭吾新书了”,一边又马不停蹄的读东野的书,excuse me?这跟一边饥渴难耐看斗鱼女主播撸管,撸完之后就骂“草泥马这女的怎么这么贱”有什么区别?你看东野也是一样随着一阵抽搐然后整本书索然无味?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四):不是村上太浅显,而是你的理解。
这里必将成为村上主义者和反村上主义者的德比战场。
那些开场都没读懂的人就在那里喷村上写空话,这可能会让一向害羞,喜欢用复杂隐喻和细节化的抽象的村上先生显得更为疏离。
“画一个没有五官的人有多难?而且,时间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这句话本身就是村上的自描——文学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五官的人”,特别是在越来越分裂的21世纪的“全球共同体”这个语境下。
而作为一个不断老去的,并没有悲惨命运的作家,他是在不断尝试打破自己给自己筑起的墙,这同时也像二战后的人类的命运一般,既没有炼狱般卓绝的环境来完成史诗的叙事,然而又暗含着一个幽灵,一个来自中世纪黑暗的幽灵,在全球制造着骑士和非骑士的那些矛盾,制造着高墙和鸡蛋。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是不会在威士忌和咖啡之中让自己袖手旁观太久的。
可以说,村上无疑是在进化,从人们说的“小格局”到了很高的高度——不论是在历史上,他都还是好的进化成了更关心世界的作家,和加缪一样,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述说自己的哲学,用隐喻来讲述真正宏大的东西——而也只有隐喻能够真正体现出那些宏大的东西。
然而有人连副标题都读不懂。。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五):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的剧透与节选
【全书剧透】(正在等待中文版问世、憎恨剧透党的请勿浏览本文)
故事的主人公“我”是一名36岁,以画肖像为业的画家,在某天妻子提出离婚后深受打击,数月漫无目的、孤独伤心地流浪在日本东北地区和北海道。后来受到美术大学时期的好友雨田政彦之邀请,因而住进其父雨田具彦的工作室旧宅中。友人父亲雨田具彦是日本十分出名的画家,老画家讨厌尘世喧嚣,过着隐居的创作生活。“我”在工作室旧宅的阁楼中,发现了一幅具彦未曾载录在任何地方的作品《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题目,取自莫札特歌剧《唐·乔凡尼》(Don giovanni)的开头,歌剧中,主角唐璜本欲非礼未婚女性安娜,故身为骑士团长的安娜父亲便出现与唐璜决斗,最终却被唐璜杀死。雨田具彦将这个场景“翻案”为日本飞鸟时代(约 6世纪末-8世纪初)的日本画,有别之处更在于画面左方,竟有歌剧中不存在的长脸男从地底探头而出,作为观看这一幕惨剧的见证人。这幅血腥又深含无言意蕴的杰作令“我”的灵魂为之震撼。
“我”对这幅画十分在意,想追寻画作背后的迷团。而后,“我”又在现实中遇见一位谜样的白发富豪免色涉,进而又遇到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例如画中那位被刺杀的骑士团长竟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并自称为“伊狄亚”(即idea)。
进入第二册,谜团一一揭晓,村上重现了雨田具彦、继彦两兄弟的痛苦战争记忆。时钟拨到上世纪30年代,兄长具彦留学维也纳学画期间正值德奥合并,与奥地利恋人共同参加了反法西斯组织,因涉嫌密谋刺杀纳粹高官,不幸被捕,恋人被处以死刑,具彦亦受到残酷拷问。其弟继彦性格老实,本应继续在大学深造、成为前途无量的钢琴家,不料因征兵卷入了南京大屠杀。他接到上级指令用军刀残杀俘虏,这在战时是无法抵抗的命令。战场上砍杀俘虏的一幕使其精神遭受重创,退伍后留下描述当时惨景的遗书决然选择自杀。然而这一切在当时军国主义泛滥的社会背景下,被视为懦弱无能、羞于启齿的事情,遗书被悄悄地烧毁。信仰自由和平、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精神苦痛的具彦则将历史的沉重神韵于画。“伊狄亚”要求“我”将之杀死,重现画中场景;(为什么要重现画中场景啊?!楼主也不知道。)而“我”照做后,随之是画面左方那位神秘长脸男的出现,他开启了一条隐喻通道,使“我”进入其中接受试炼。最终,时间来到三一一大地震前后,“我”不仅穿越时空,而且回归现实,与妻重修旧好,并生下一女。
村上一反过往结尾失落的常态,在故事最后给予正面希望,更让小说终止在这一句上:“‘骑士团长真的存在。’我对着在身旁熟睡的女儿说道,‘你最好要相信。’”村上在结尾强调“相信”的力量,传递出呼吁日本年轻人正视历史的信号。
----参考林敏洁《重温战争记忆,呼唤和平友好——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评析》 与 孙志超《三分钟看完<刺杀骑士团长>》
【节选】(这是村上新书出版后引起最大话题与关注的一节)
「……由于这两起事变,希特勒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接着奥地利全国也因为希特勒的意志卷入了漩涡。反法西斯组织的那些学生们开展了地下运动,雨田具彦也因此遭到逮捕。这下你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了吧。」
「大概理解了。」我答道。
「喜欢历史吗?」
「虽然了解不多,历史书还是喜欢看一看的。」我说。
「日本也发生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一连串致命的,颠覆性的,再也没有回头路的事件。这你清楚吗?」
我试着整理了一下脑子里堆积已久的历史知识。1938年,也就是昭和十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欧洲方面,西班牙内战正在激化当中,德军的秃鹰军团就是在当时对格尔尼卡进行了无差别轰炸。日本方面呢......「卢沟桥事件是那一年发生的吗?」我问道。
「那是前一年的事。」免色说道,「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为发端,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当年十二月,发生了由这起事件派生而来的重要事件。」
那一年的十二月发生了什么呢?「南京入城。」我说道。
「对。也就是南京大屠杀。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最终占领了南京市区,并在那里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既有在正规交战过程中发生的杀戮,也有在战斗结束之后发生的杀戮。因为日军并没有管理俘虏的余裕,所以对投降的军队和平民大肆残杀。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杀害,历史学家们在细节上有着种种争论。中国人死亡的数量,有四十万人的说法,也有十万人的说法。但四十万人跟十万人有什么区别呢?大量的市民卷入战斗,遭到屠杀,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抹销的事实。」
当然,我也不知道那有什么区别。
----译者:漆松(知乎答主,加州理工学院认知神经科学在读博士)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六):小小人
不管外界好评或是差评,村上的书我总是会看的,怕是成了习惯。
这部久违的长篇还未引进大陆,亏得豆瓣网友C劳心劳力地翻译,我们才得以一睹为快,感恩。
村上有村上的风格,人物塑造也好,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好,这本新作依然很“村上”。从前几部作品,村上就把触角伸到了悬疑方向,或者说带有一丝“奇幻”的世界,追求现实性与非现实的冲突,这也是很吸引人的其中一处。在非现实中找到现实的对应,也就是所谓“隐喻”。
隐喻在他的小说中十分常见,这次的隐喻就出现《杀死骑士团长》这幅画中。至于画中的“骑士团长”隐喻着什么,还不得而知,似乎是与屋主雨田具彦在维也纳留学期间有关。他在那段时期经历了何种事件,要在下一部才知晓。
主角依旧是热爱古典音乐,读书,游泳,低调,习惯对他人不做判断,工作上认真踏实总是能得到别人赏识,总是能吸引不少女性的男性,而且他的周围总是发生超乎常识范围的事件。
对于这样的设定,我怀疑村上君对自己的处世之道颇为满意,以至于主人公的设定几乎鲜有改变。
村上在《作为职业小说家》中曾提到一件事:他坐电车上大学,车厢基本空空如也,然而一个长相颇好的女子偏偏选择在他旁边坐下,与他攀谈。类似的经历也在《杀》中出现了:主人公在乡下餐厅就餐,一个似乎在躲避谁的女子也是偏偏选择坐在他对面,让他假装和她认识以掩耳目。同样的,世界有那么多肖像画家,免色先生偏偏选中了主人公。不过,主人公若是连这点奇遇都没有,故事也难以展开吧。
几十万字但情节并不复杂,诸君一看便知,用以堆砌的“材料”是村上君拿手的“日常描写”。以前的我乐于观看主人公的各种生活琐事,听着瓦格纳煮意面啦,嚼着柠檬糖踏着网球鞋找猫啦,可以说是啰嗦,也可以说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但对于看惯村上的prototype的忠实读者来说,日常已经看饱,想看些新东西啦。我又在想,作者有作者的步调,若是轻易改变,很容易失去节奏,被所写的文字带跑,最终失去主动权。创新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从第一部还看不出太大的端倪,留下好几个线等着填上:
1、《杀死骑士团长》这幅画中的隐喻关系以及雨田具彦在维也纳时期经历的事情。
2、免色先生的背景
3、驾驶白色巴鲁斯森林人的男人为何者
4、疑似免色先生的女儿秋的铺垫作用
5、意识体“骑士团长”对主人公的影响
6、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的作品吗?主人公在寻求什么?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七):如果说第一部是提出问题,那么,第二部就是解决问题
断断续续花了一个月读完日文原版。如果说第一部是提出问题的话,那么第二部就是解决问题。(因为忙着准备考研¬_¬)
人物设定、情节安排、故事背景等,延续一如既往的风格。分离、独处、莫名其妙的人物陆续登场(值得一提的是,此作关键人物并不多)、性、酒、美少女、隐喻(第二部标题就很明显了)、失踪、寻找失落的什么、进入隐喻。
第一部读完后,给人感觉是作者给你扔出了一堆问题等待解决。第一部标题是《意念的显现》,指的是一切故事的开端。
第二部后半部分进入全书高潮部分。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转折(小小剧透:13岁少女突然失踪),怕是很难坚持读下去。村上的作品总是在寻找失落的什么,比如失踪的妻子(《奇鸟》)。与此同时不得不说的是,有令人诟病的地方,大多数地方描写过于冗长,明明一两句就可以交代清楚的情节,用了几页纸。有些景物描写过于琐碎,很多句子重复用不同句式表达相同含义。有时候你看了几页发现还在讲同一件事。说实话看第二部时我几度想弃,后来在我对村上的嫉妒喜爱之下坚持读完.....
第二部完全是对第一部的总体揭示。同样出现了主人公与黑暗势力搏斗的场面。这里不多说了。故事背景有关战争我也不说了,因为其他人已经说过很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结局我有些意外。居然出现了貌似皆大欢喜的场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改变。
情节安排上酷似《奇鸟》,可以说是延续一如既往的风格了。
打四星,我对村上的爱就占两星,其余两星给作品。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八):现实与非现实共构的世界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
<有些微情节剧透>
断断续续花了两个星期左右终于看完了村上春树的《騎士団長殺し》的第1,2部。
说起来我实在不是一个村上粉,之所以看这本书是因为孕期里闲来无事,此书在日本又红得很,所以兴起借来一看。想起我第一次看村上的作品还是在十年前看的《挪威的森林》,当时实在不太懂村上的风格,只觉得其笔下的女人莫名其妙,男人磨磨唧唧。我那时年纪不大,对日本文化和日本人也不甚了解,总之就是欣赏不来此种风格。
时隔十年,再看村上的作品,谈不上到懂得欣赏的地步。但至少能理解人物性格,也确实佩服村上在对事物的描写上,高超的明喻暗喻手法。
此篇小说是以第一人称书写,作者用一种近乎繁琐的方式将所有主人公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一切都用文字描写出来。比如主人公听到的优雅的古典音乐;看到的摄人心魄的画作;略带神秘色彩的人物与其长相装扮;乃至山上的风,雨水,空气和树木都被作者用各种恰到好处的形容与比喻描绘出来,让人有如身临其境。
另外,除了这些具象化的能见的事物,他对人物内心的孤独,被抛弃感,漂泊感,甚至是时间流逝的空虚感和异世界的虚无感,等等这些抽象化的情感描写都很玄妙的恰如其分,让人产生一种共鸣。
但相对的,村上似乎也特别喜欢这类描写,有的时候难免觉得细节太多太拖沓。
回到小说的故事本身,我对村上不算了解,但觉得他似乎很喜欢那种“现实与非现实”相结合的情境。当年翻了几页《海边的卡夫卡》,也是如此这般的感觉。他喜欢用玄幻与现实交织结合以构建一个村上春树的世界。
本书中被隐藏的神秘画作;后山树林中的奇异洞穴和从其中被释放出来的观念性存在(イデア、idea:超越时空的非物体的,绝对永恒的存在);主人公被拉进的偏离逻辑与理性存在的异空间……
这些非现实的存在和现实的地名,现实的音乐剧,现实的时间相结合,形成了本书的村上世界。
我虽然也看得一知半解,但若刻意解读,总有种作者将这非现实世界作为一种“隐喻”(メタファー、metaphor:暗喻。映射自己倒影的异世界)来表现的感觉。即将现实中人物内心的挣扎,纠缠,恐惧投映于另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中。
书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36岁的给人画肖像画维持生计的画家。在妻子毫无征兆的提出离婚后,离开旧家,其后9个月内发生了一系列内心的,现实生活的巨大变革。其中,包括其独自驱车毫无目的的漂泊时遇到的人和事,在朋友父亲的旧居安定下来后遇到的有些神秘的依赖人免色,在屋顶阁楼发现的刻意被隐藏的画作《騎士団長殺し》,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非现实经历。
也许这一系列经历正是映射了“我”对自我内心的挖掘,发现,挣扎乃至最终的克服与超越的过程吧。
在我看来此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主人公“我”的最初状态就是和妻子住在广尾的公寓里靠着给人画肖像画维生,而到第2部结尾处,“我”的状态依然是“和妻子住在广尾的公寓靠着画肖像画维生”。
似乎辗转经历了如此多的现实与非现实的变革,“我”的生活状态却完全没有变化。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最后一章节“我”和妻子的一段对话说:
「あなたは少し変わったのかしら?顔つき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が?」(你是不是有点变了,脸型之类的?)
「顔つきのこと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けど、ぼくはいくつかのことを学んだんだと思う」(脸型有没有变我不清楚,但我觉得我学会了一些事情)
「私もいくつかのことを学んだかもしれない」(也许我也学会了一些事情吧)
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事实上“我”的内心早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如其所说“学会了一些事情”。
对于妻子,主人公从最初的潜意识里将妻子和逝去的妹妹同化,到如今也许他已放弃了在妻子身上寻觅妹妹的影子。而对于肖像画,从最初因生活家计而被动画画,到如今他主动的想要画肖像画,并试图着手“自己真正想画的画”。
虽然表面上,最后的生活状态和最初相差无几,但其内心的状态却是完全不一样了。
书中,有多处直接或间接的提到“目に見えないもの(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和“目に見えるもの(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一样重要。就像“现实与非现实”,“存在与非存在”,“事实与观念的世界”,都同样重要,两者相结合,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所以看得见的表面生活状态虽没有变化,却不可忽略其内在的看不见的内心状态的改变。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主人公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然而却已不是那同样的最初。
一切都已经变了,但一切都像没有变化一样。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九):难道是第一篇村上春树《騎士団長殺し》/《杀死骑士团长》/《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书评
从2月24日发售日到现在已经五天。终于读完了村上的新作『騎士団長殺し』(《杀死骑士团长》/《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上下两册,新潮社出版,英题Killing Commendatore)。不能算读的快的。因为听闻有的日本读者24日凌晨买到书后当天就读完了。这估计不是传言,因为日本亚马逊24日当天下午就有人读完上册随手转卖了(这自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騎士団長殺し》读后感(十):只是单纯庆祝一下上译拿到了中文版权
(不懂日文,只不过是给村上近年来几本书的综合评价)
几年前我也跟风(几乎是特意的,有选择性的)读过赖明珠与施小炜(倒不如说,读遍了所有中文译本)。恕我直言,即使是误译与平添辞藻,也比平铺直叙死板干瘪的译文读起来欣快。虽然现在想想或许我迷恋的只是林少华,但无所谓。在我看来,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二次创作。我在想幸亏村上还没有被大众认同到发展出一门“村学”(然这迹象已经隐隐抬头于各译本的支持者间的党争),不然diss来,diss去,好好的阅读愉悦都变成了他人评头论足,写译本书评互殴的牺牲品。 阅读林少华的译文让我感到一种脚下浮风,四周景色快进成线(如同使用ps里浸水模糊并飞快拖动鼠标)的美,这是我在其他译本里感受不到的。上海译文向来是我最喜欢的出版社。感谢上译的积极争取,使翻译权不旁落他社(我承认我对南海出版公司有某种程度上的偏见)。即使如今已到村上的创作生涯后半,几本书下来,他的写作能力已经明显显示出退化迹象,但我还是不由得说句:能交给林少华真是太好了。(一本正经的acg翻译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