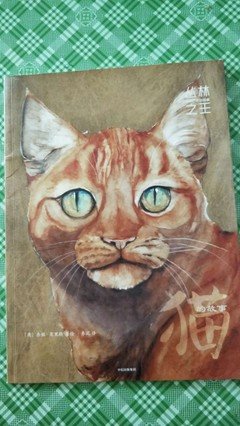众病之王经典读后感10篇
《众病之王》是一本由[美] 悉达多·穆克吉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5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众病之王》读后感(一):经典
这本书值得我去写点书评!
虽然还没读完,但我就是喜欢这种把历史铺垫开来(当然,这包括了作者的文笔成分)。
但是,我觉得更令我看重的是,这简直可以算是我理想中的教科书了。作者把每一个阶段遇到的困难,及应对手段都写出来。并且,期间穿插非常多的医学知识,一下子就提升了我这种医学小白的一些医学常识。另外,也增加了我对一些现代医疗手段的原理和成数的了解。
:新增一些读后感
看到此章,联系到我的亲身经历和别的书看到的,真的觉得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特别是在没有提前知会患者或者是即使知会了也没如实相告,如详相告的情况。
我去年在手术后住院期间,医生竟然偷偷给我开了一个新药,当时因为第一次手术,也没啥经验,也没有一些“就医智慧”(后来看书并且自己也总结了一点,这方面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然后打了针后,很快便发生了过敏反应,然后我问护士,她才含糊其辞的说是试药。过后当然幸好也消退了。
另外,在凌志军的《重生手记》里,他也记述了他被尝试新药,也是含糊其辞及副作用明显的经历(第二章,“前三个月里最容易犯的错误”,最后几段)
我觉得,为了医学的前进,应该有这样的临床试验。但是,必须得在知会了病人的情况下,并且真实、详细的解释清楚,并在病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要不然,不等于偷偷就帮别人捐了器官?!当下是最实在的,人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众病之王》读后感(二):癌症的隐喻
本文与其说是书评,倒不如说是笔记。
作者在Author’s Note的第一段即点明本书主旨,也是本书最重要的特点:将癌症隐喻为人,并为其立传。
This book is a history of cancer. It is a chronicle of an ancient disease—once a clandestine, “whispered-about” illness—that has metamorphosed into a lethal shape-shifting entity imbued with such penetrating metaphorical, medical,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potency that cancer is often described as the defining plague of our generation. This book is a “biography” in the truest sense of the word—an attempt to enter the mind of this immortal illness, to understand its personality, to demystify its behavior. But my ultimate aim is to raise a question beyond biography: Is cancer’s end conceivable in the future? Is it possible to eradicate this disease from our bodies and societies forever?
在Prologue中描述癌症为“more perfect versions of ourselves”。并比较人类与癌症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恶性增长并追求永生。And cancer is imprinted in our society: as we extend our life span as a species, we inevitably unleash malignant growth (mutations in cancer genes accumulate with aging; cancer is thus intrinsically related to age).If we seek immortality, then so, too, in a rather perverse sense, does the cancer cell.
在PART ONE的A Private Plague部分更是用了一大段的描述更系统地论述这一相似性。Cancer is an expansionist disease; it invades through tissues, sets up colonies in hostile landscapes, seeking “sanctuary” in one organ and then immigrating to another. It lives desperately, inventively, fiercely, territorially, cannily, and defensively—at times, as if teaching us how to survive. To confront cancer is to encounter a parallel species, one perhaps more adapted to survival than even we are. 并进一步点明癌症,与人类一样,也是经过进化所产生的终极产物。The genetic instability, like a perfect madness, only provides more impetus to generate mutant clones. Cancer thus exploits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evolution unlike any other illness. If we, as a species, are the ultimate product of Darwinian selection, then so, too, is this incredible disease that lurks inside us. 因为这种类似性,癌症不仅仅作为某种疾病、某种物,更像是某种人的存在。My subject daily morphed into something that resembled an individual—an enigmatic, if somewhat deranged, image in a mirror. 最后说明这确实是一本关于癌症的传记,才开始回顾两千年前人类文明史有记载的癌症现象。This was not so much a medical history of an illness, but something more personal, more visceral: its biography.
对癌症这一拟人化的隐喻一直伴随我读完整本书,说是细思极恐真是不过分。与癌症互相映照,人类与癌症的存在方式犹如镜中影像:癌症之于人类就如同人类之于自然。当我们感叹癌症凭借进化的完美,无情贪婪地侵害我们的身体、夺走我们的生机时,人类不也凭借进化出的智慧,肆无忌惮的掠夺着自然的资源,追求自身的舒适享乐,也如同癌症一般从小聚居地转移到更广阔的大陆,给迁入地带来大范围的物种灭绝,而且这种状况只会愈演愈烈。人类的每一次技术革命,就宛如癌症发生过程中的somatic driver mutation,为其development赋能,从而加深对自然的更大程度上的掠夺。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会驱动下一轮的driver mutation,如此循环往复,只能陷入不断恶心循环的怪圈。虽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人类作为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地球是其仅有的生存环境,对自然的破坏必然带来自身所能获取资源的枯竭及生存环境的恶化。我们在诅咒癌症带走我们的亲人时,是否也有看透人类被诅咒的命运。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对这一相似性过度地隐喻总有些不合时宜,只会徒增对生命存在的厌恶,而这绝不会是生命存在的意义。人类纵使享有地球最高智慧,依然不能明白自身的存在,还是说生命本身就没有意义或是就是意义。
以下是单独摘录的笔记部分:
ART THREE
At the NIH, Alsop wrote pointedly, “ Saving the individual patient is not the essential mission. Enormous efforts are made to do so, or at least to prolong the patient’s life to the last possible moment. But the basic purpose is not to save that patient’s particular life but to find means of saving the lives of others.”
ART FOUR
The idea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s faintly un-American. It means, first, recognizing that the enemy is us.
tatistics are human beings with the tears wiped off.
tatistical methods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for cancer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descriptive rather than mechanistic: they describe correlations, not causes. And they rely on a certain degree of foreknowledge.
ART FIVE
cience is often described as an iterative and cumulative process, a puzzle solved piece by piece, with each piece contributing a few hazy pixels of a much larger picture. But the arrival of a truly powerful new theory in science often feels far from iterative. Rather than explain one observation or phenomenon in a single, pixelated step, an entire field of observations suddenly seems to crystallize into a perfect whole. The effect is almost like watching a puzzle solve itself.
Cancer, in short, was not merely genetic in its origin; it was genetic in its entirety.
Cancer’s life is a recapitulation of the body’s life, its existence a pathological mirror of our own. Susan Sontag warned against overburdening an illness with metaphors. But this is not a metaphor. Down to their innate molecular core, cancer cells are hyperactive, survival-endowed, scrappy, fecund, inventive copies of ourselves.
ART SIX
In Lewis Carroll’s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the Red Queen tells Alice that the world keeps shifting so quickly under her feet that she has to keep running just to keep her position. This is our predicament with cancer: we are forced to keep running merely to keep still.
《众病之王》读后感(三):感冒带来的惊喜
上周的无挑,他们通过节目组的设置让他们近距离接触了历史,对他们韩国的独立史有了深刻直观的认知。大神一直感叹果然要了解背后的故事才会觉得有趣啊!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鲜活的故事。这周和家人出行也是如此,我想细细了解,可是他们看完就走,似乎那些东西没有意义,这是旅途的遗憾。看《众病之王》,了解到白血病的命名史,也让我这一想法更加确凿,了解能产生共情与理解,了解了癌症向现代走来的道路,使得我更加能理解那些新闻中的故事、他人口中的传说。一切不再是一些数字,冷漠的报道,而是有血肉有情绪的生命。
看到他们在探索对付癌症的方法,切除、化疗、以毒攻毒...不禁觉得浑身不自在,看书都不想坐着看,觉得身上每一处都很脆弱、容易损伤,于是躺着,侧倚着,怎样都不舒服。
科学家,医生,解剖学家等不断的寻求更好的,能根治癌症的办法,穷尽一切,每一次细小的发现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惊喜,都是引导他们最终解决病症不可或缺且可遇不可求的一环,从开始到结束这一过程,有起有伏,惊心动魄。我想起去年看的《模仿游戏》,图灵他们为了研究出破译密码的机器经历各种阻难,内外的困境最终取得成就。而这本书里的多位解剖学家、医生们,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令人惊叹,对癌症的研究一环扣一环,研究进程有起有伏,精彩跌宕,若是拍成电影一定相当精彩,而且极具意义。(啊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hiv科普书,有时间找来读读
看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感叹翻译的良心,言语顺畅自然,情绪煽动性很强。本身书就很精彩,翻译也好。很值得一读,尤其我这种对医学没有概念之人。Orz
噢顺带提一下我看这本书的初衷,哈哈。原本自己这几天感冒,非常不舒服,而且来势汹汹头晕脑胀无法制止。主要还不是不舒服,而是非常烦躁,很烦感冒的状态,以往一感冒就的一周以上才能好,无法正常学习活动,所以一气之下想弄清楚感冒到底是什么玩意,于是搜医学科普书。搜到一本和感冒有关的但是找不到电子版,kindle都没有,又急着想看,于是随便找了本与感冒无关的写疾病的高分书来看。感觉非常出乎意料!作为一本医学科普书,即使有些许专业名词也通俗易懂,直击人心,不能更棒!!开心:)
《众病之王》读后感(四):众病之王——癌症,21世纪的你依然惹不起
从微博上得知这本书,看了差不多两个月(请忽略我的效率)才看完。特别好的一本书,作者是悉达多·穆克吉。从书的扉页介绍可以看到,是一名印度裔的美国医生、科学家和作家。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医师和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在牛津大学获得致癌病毒研究的博士学位......本书2011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我,讲了这么一堆就是想说明,这本书是一本值得读的,由当今世界上极高学历与学术成就的科班出身的一名科学家写就的一本科普著作。这里面,没有谣言,没有夸张,以最真实的手笔如实的反映了癌症的前世今生,以及我们现在对抗它的奋斗进程。
我不准备洋洋洒洒写太多专业的东西,我就讲一些,我在里面学到的以前不了解或不太了解的关于癌症的情况:
1.癌症是现代病吗?
癌症不是现代病,对癌症最早的医学描述,见于最初撰写于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文本中“乳房的隆起性肿瘤......触摸他们就像在触摸一只球状包裹。”
2.为什么以前得癌症的人少,现在罹患此病的人却越来越多?
因为癌症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其发生概率有时是呈指数性地随年龄增加。如患乳腺癌的概率在30岁左右的妇女中是1/400;而70岁左右的妇女,每9人中就会有1人患乳腺癌。在古代社会,人们长期受到肺结核、霍乱、天花、麻风病、鼠疫或肺炎等疾病的威胁,往往还没有得癌症,就死掉了。即使癌症存起是由“双重否定”造成的结果:只有当所有其他的“人类杀手”被消灭了,癌症才成为普遍现象。文明并没有导致癌症,而是通过延长人类的寿命,暴露了癌症。
3.癌症是一种疾病吗?
癌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整组的疾病。有前列腺癌、乳腺癌、淋巴癌、胃癌、血癌(白血病)等等。而且,很多情况下同一发病部位的癌症还有很多亚型,如乳腺癌有Er阳性乳腺癌、Er阴性乳腺癌、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严格的说,每一位癌症病人所得的癌症,在其活体组织细胞切片下,其癌细胞DNA都是不同的。而他们的共性是恶性细胞的病理性异常增长。
4.化疗?放疗?靶向药?
化疗:化学疗法(就是打针吃药啦)
放疗:放射治疗(用X射线杀灭癌细胞的疗法)
靶向药:近50年出来的,专门杀灭癌细胞的药物,不损伤人的正常细胞。
5.得了癌症会不会死?我怕死~o(>_<)o ~
这个要看是什么癌症,并且要看是什么阶段,早期晚期?有无扩散?有没有药吃?以及,你是否买得起药吃。
6.什么癌可以治,神马癌没得治?
不一一列举,能治的是少数。不能治的是多数。并且,还有一些情况是本来能治的,后来癌细胞变异、抗药了。你变得不能治疗了。OK,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7.得了这种病是不是会破产?
是的,你穷,你会破产。抗癌药物非常贵,而且种类多。有时候你幸运能延你几年狗命。但,你要是命不好,你的癌症是有可能复发的,基本上复发了,就无解了。这绝对会是能改变你一生轨迹的疾病。
8.有没有一种防癌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还可以拯救一下?
暂时没有找到一种已在大型人群研究中临床验证过的“防癌的生活方式”。但是我想说,你们可以远离致癌物。从不接触致癌物开始。对了,很重要的一点是,请大家去科学可信的地方查致癌物列表好吗?求求你们了,别看两条微信公众号就致癌了,就养生了。大众可查的机构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什么,你登不上WHO的官网?不知道科学上网吗亲亲?什么,科学上网要钱买vip?那你可以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看。这个还是比微信稳得多
9.癌由什么引起?
我也不知道。主流的当下的被广泛接受的,现阶段看起来很完美的解释是,癌由正常细胞的基因变异引起。所谓的致癌物致癌,是因为致癌物诱发了基因突变。
10.不想得癌症,想多活几年该怎么办?
年轻的话不用太担心,毕竟癌症发病率与年龄正相关。但是请从年轻的时候就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远离致癌物、多护肤(紫外线会致癌,用些防晒用品好不baby)、可以多读癌症相关的书籍、少公众号养生。还有,多赚钱,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你的钱或许可以让你飞美国用上某种新药品/疗法,来延你几年狗命。
11.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措辞还严谨,后面写得越来越浮夸。
因为我皮 (*・ω< )
《众病之王》读后感(五):与众病之王斗智斗勇
与众病之王斗智斗勇zz
因监测出家族性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缺陷,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切除双侧乳腺,“患乳腺癌的概率从87%下降到5%以下”。在发现了叫做Her-2的基因后,一种针对乳腺癌细胞进行精准打击的药物赫赛汀被研制出来。
虽然已有超过70亿人加入战斗,但面对癌症,人类至今仍没有胜算。
在疾病的王国中,它不是一个新被搬来的救兵。当人们在来自公元前2500年的一张埃及草纸上,发现 “乳房上鼓起的肿块,摸上去又硬又凉,且密实如河曼果”的记录时,就已经窥见敌人最初的面目。
只是,在几次意外的露面后,它狡猾地隐匿起来。直到19世纪末,在人们逐渐征服诸多疾病之后,才发现这个更凶残的敌人隐藏在后面,冷冷发笑。
当印裔美国医生悉达多·穆克吉决定为这个恐怖的敌人写一本传记的时候,他恰如其分地把书名定为《众病之王:癌症传》。虽然青霉素等众多药品的发明让人们对征服疾病王国充满信心,但王者的出场,轻易就为溃不成军的疾病大军扭转了战局。
这种表现为细胞病态分裂的疾病,就隐藏在人体深处,一不留神,就会偷偷掳走我们的一个战友。2012年,中国每分钟有6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7到8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而且,依靠人类的身体作为挡箭牌,它阻挡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1898年,在纽约的一家医院里,一名叫做霍尔斯特德的医生准备发起一场猛烈进攻。针对乳腺癌患者,他试图彻底捣毁敌人藏身之所。为此,他不仅切除乳房,而且切除了患者的锁骨,直达其下方的一小簇淋巴结。而他的学生,很快青出于蓝,甚至探索从脖颈处开刀,切除一串位于锁骨上的腺体。
用这种叫做“激进式手术”的方法,人类确实揪出了一些破坏分子,但还是有一些类型的癌症,看似被柳叶刀击中,但其实早已悄悄转移至人体其他器官。
当时并不了解真相的人们为揪出这些坏分子而欢欣鼓舞。“越是根除,效果越好。”在这种旗号下,手术朝着越来越无畏、激进的极端路线发展。
“最后,患者没有死在手术台上,医生已经认为自己很走运了。”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医师的穆克吉如此评价这次冲锋。
但是,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结果,并没有阻止医生们继续冲锋的决心,利用X射线的放射疗法,以及利用各种化学毒素搭配治疗的化学疗法相继出现。人们悲壮地把这些毒性强烈的子弹投向自己,试图阻止隐藏在身体里的癌细胞继续生长。
1901年,一位芝加哥的医生自信地评论化学疗法:“我完全看不出这个治疗方法有什么局限性,我相信它绝对可以治愈所有类型的癌症。”仅仅60年后,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一名研究员的说法,相信癌症能够被治愈就需要相当的勇气了。
占了上风的癌症不可一世,落败的人类垂头丧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人们避免谈论癌症,将其隐晦地称为Big C。出租车司机宁愿绕远,也不愿经过纽约著名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骄傲的人们很快从狂热中清醒,开始认真地观察自己,这才发现最有用的弹药原来藏在自己身上。手握这种叫做“基因”的弹药,一些癌症开始无所遁形。
因监测出家族性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缺陷,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切除双侧乳腺,“患乳腺癌的概率从87%下降到5%以下”。
而且,更让人欣喜的是,通过分辨基因,人们不必再像以前一样,无分别地向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一起投出子弹,而可以开发最具特异性的癌症靶向药物,对癌细胞进行精准打击。
在发现了叫做Her-2的基因后,一种针对乳腺癌细胞进行精准打击的药物赫赛汀被研制出来。而另一种叫做格列卫的药物的出现,则毫不夸张地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存在于血液中的癌症,划分为“前格列卫时代”和“后格列卫时代”。截止2009年,用格列卫治疗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预期存活时间为诊断后30年,这种药物“改变了全美癌症的面貌”。
但作为众病之王的癌症并不容易屈服。格列卫制服白血病,靠的是滑入一个叫做Bcr-abl致病基因中央的楔形裂隙中,“像箭头刺穿蛋白质的心脏中央”。但在这种弹药出现不久,狡猾的癌细胞就把致病基因进行改造,使其“心脏”不能被格列卫刺穿,因此产生了完全的抗药性。科学家不得不继续研制药物,来对付这次突变。
虽然不知道会在何时,但针对新药物的基因突变最终还会发生,人们不得不研制出更新的药物对付这种突变。如今,人类与癌症的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如果我们稍稍放松警惕,哪怕只有片刻,战争的天平就会倾斜”。
这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让穆克吉想起了一则流传已久的童话故事。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红桃皇后告诉爱丽丝,脚下的世界永远在飞快变化,唯有不断奔跑,才能保持在原位。
“这也是我们对癌斗争的困境:我们被迫不停地奔跑,只是为了保持留在原地。”穆克吉如此评说。
《众病之王:癌症传》
悉达多·穆克吉 著;
李虎 译;
中信出版社
《众病之王》读后感(六):作为癌症患者家属,阅读之时非常激动,颤抖得经常想哭
对于癌症患者家属而言,菠萝的癌症科普指明了“我们怎么做?”,《众病之王》则梳理了“我们做了什么?”
这本书只看了一半,却已是非常激动,看的时候经常想哭。
难得不出于负面情绪而流泪,而是充盈着发自肺腑的感谢。
想对千百年来为医治癌症而做出了伟大贡献的陌生人表白:‘Thank you, cancer fighte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granting every living moment my mother is enjoying right now.’
妈妈现在的每一天,其他癌症患者能够畅快呼吸的每一刻,都是你们赐予的。
这本获得了普利策奖的作品,便仿佛为“癌症”赋予了人格一般,为之著了这样一部传记。
那些发明完成的瞬间,那些试验成功的瞬间,那些欣喜若狂的瞬间,那些开天辟地的瞬间,尽管在当时反响平平,有些甚至不被自知,却都值得逐一被后人了解与铭记。
书中闪过一位位科学家或医者,便叠嶂起救助者一个个穷尽智慧和努力的身影,更让人想象起那如汪洋般病患的一具具尸体。
原来,我们的历史就这样构成了,我们自古埃及时代就与癌症并肩前行的历史。
书还有一半。我们的未来也还没有来。
知道英国癌症研究院的墙上有这样一句目标:Together we will beat cancer.
只是但愿这个梦会成真。
但愿一项项新突破能够迈向‘Yes, WE WILL.’的每一步路。
但愿等我们都不在的时候,等我们的下一辈都不在的时候,等我们的下下一辈都不在的时候,等我们的下下下一辈都不在的时候,有一天,人类可以非常轻松自如地回答‘That‘s for sure cuz we’ve already made it.’
《众病之王》读后感(七):读这本书的几点感想
一年以前,我不会读这类书。因为在我心里,我认为生活应该是阳光的,不应想生活中黑暗恐惧的东西。至今我还记得小学时,爸爸给我讲解死亡,我憋闷了一下午的感觉。同样的原因,我一般也不会看恐怖片。
这本书讲述人类癌症的抗争史。对于一个乳腺癌病人家属来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背景恢弘壮阔,人物个性鲜明,娓娓读来不亚于名著。
以下是阅读时的胡思乱想,并非针对书中的观点。
1,迷信。正如人类的其他历史一样,历史充满了偶然。对于癌症的治疗来说,各种药物的发现,基因缺陷的发现,都有其偶然性。并非什么科学系统的尼克松计划就能攻克难关。中医究竟有没有用?转基因大米能不能吃?在这方面,我觉得人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很渺小,敬畏自然,承认自己懂的很有限,知道很多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不要轻易的否定或肯定不符合自己语言体系的东西。既然西医都误打误撞,何不给中医一点空间,几千年流传下来也许有其理由。而要改变人类几十万年的食谱,也是否不要急着下判断。只是一味相信现代的学术不知道怀疑,迷信科学也是一种迷信。
对于癌症来说,假如只是基因突变,那么它的发病应该是直线关系,而不是五十岁以上的指数关系。这说明应该还和人体衰老有关。所以这和中医的培元固本理念是相通的。另外在书中提到的中国王教授治疗白血病的贡献。能在书中提一笔都是抗癌史上不得了的人物。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没仔细查证。发表过关于中医用砒霜治疗白血病的药方,经过现代的仪器检测,砒霜中的几价砷可使白血病癌细胞分化失活,这恐怕远远早于书中开篇法伯治疗白血病的年代。虽然这样的中医治癌症的事例并不很多。但我至少看到三个医学院士讲到了中医的辅助作用的观点。另外,气功,冬泳,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呢?
2,永生。癌细胞可怕之处,在于不停地繁殖。例如在书中提到,在营养液中培养癌细胞三十年。如果破解了这个密码机制,那么人的生命能否得到永生呢?至少在营养液中,脑组织以及人的意识长期存在。
3,实验。现代医学的临床医学几期实验,确实保障了患者利益。但对于癌症来说,一个大型试验,生存期,无肿瘤生存期往往耗时几年来自十几年。医生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例如即使他突发奇想想到了砒霜治疗白血病,但他绝对不敢用于临床自找麻烦。这种冒险试错的困境在书中大剂量治疗白血病时曾经讲过,两位医生后来也铩羽而归。而书中提到的两个中国人另一个被辞退,虽然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且载入史册。这是否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4,兵法。假如把肿瘤治疗看做一场抗战。我觉得医生应该学一学兵法,有时穷寇莫迫,据说经过化疗后癌细胞会变做梭型,更具侵袭性。有时十则攻之,例如强化疗法。这个度在于个体化治疗,知己知彼,兵法之妙存乎一心。另外这又涉及到医生的激励机制。
5,站在上个世纪之初,清王朝风雨飘摇,很多有识之士面对当时的时局,思索中国的命运,很多人也彷徨挣扎疑问。就像面对癌症的困局。胡适曾经说,成功不必在我,努力必不唐捐。
《众病之王》读后感(八):第一遍读书感悟
众病之王
20151010深夜网购
20160201第一遍读完。
读得断断续续,只读些大概,索性涂抹几句:
作者用四五百页不仅一步步顺着历史的轨迹解开癌症它古老而又神秘的面纱,亦结合自身所读,所感,所闻深刻讨论了桑塔格所言“疾病的隐喻”即癌症之于整个社会,文化,人的价值观的意义。
作者的科普较为形象,让我稍稍温习了高考后忘得几乎殆尽的生物知识。作者对于文学名著的深刻理解并且对于其中文字的运用更是让我耳目一新。六个部分中的每一个小篇目都是以文学/演讲/社科等中摘出恰当的文字作为引子。
我记忆最深的一句是出现在整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引自《爱丽丝漫游奇镜记》的中王后所言“在我们这儿,得拼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要是想到别的地方,得再快一倍才行。”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我们对癌斗争的困境:我们被迫不停地奔跑,只是为了保持留在原地。
而我相信,我们人类可以做出更大更快的努力,便能追上疾病变化的步伐,占得先机,取得最后的胜利~
to be continued…
《众病之王》读后感(九):读这本书其实是因为怕死
癌症在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种罕见疾病,就我而言,身边的亲人,朋友,得癌症走的,得了癌症还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不在少数。
癌症真正进入现代社会视线的是在21世纪,随着医疗技术以及工业化带来的作物产量的提高,人类的寿命得到了有效延长,正是因为人类生命的延长,癌症这个人类疾病的终极问题才暴露了出来,如同退潮后才看见河底的乱石。
除了人类寿命的提高外,如果硬要把癌症病发律与现代科学联系起来的话,我想有两个词可以概括:辐射和化工。
信息技术在21世纪突飞猛进,如今的我们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面对电脑和手机,并长时间甚至全部时间置身于无线信号里,谁说只有细胞不会对外界的信号产生刺激?
化工行业同样在21世纪得到了腾飞。食物领域。饲料,农药,添加剂,现在人吃到肚子里的比两百年前的人丰富却也复杂得多;烟草,汽油都是人用化工创造出的美好产物。
书中提到:“我们认为癌症是一种‘现代病’,因为它的隐喻很现代,这是一种‘过度生产’,一种爆发式增长的疾病。”
说信息辐射和食物添加剂致癌,这简直是玄学。书中提到,原癌基因需要进行二次突变,抑癌基因亦需要通过突变灭活,癌细胞才真正狂妄起来。谁知道哪一次人的行为或者环境导致了一次突变?又是什么环境导致了二次突变?没人知道。
不如做出这样的假设吧: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表面上没有病症,不代表身体里的癌细胞没有生长,它们只是还不够强大,或者正被抑癌基因压制着,当不利因素逐年累月地积累,直到原癌基因突变,人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意识到自己对自己以前都做了什么。
比较讽刺的是,得癌症和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很类似: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而当你做出某种行为的时候,事情就已经在悄悄发生了。类似于佛家的因果,却也揭示了一个永恒的道理:大的变化永远来源于积累,看不见不代表着没有变化......比如对某件事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比如对身体进行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摧残......
另外说几个阅读时的感受:
每个生命都可贵,可在医院里的绝症病房里,生死最终不过是化为数据。听起来残忍却是真实,死亡来临时,无可抵挡,死亡来临后,对于活着的所有人,日子依然照常进行。
医学界的先驱们确实伟大,他们为了人类的医疗技术的发展付出了时间,精力,甚至是生命。在美国x射线医学实验室工作的先驱们,几乎都死于由射线灼伤引发的癌症。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打响的“抗癌战争”惊心动魄。调用舆论,社会关注后,采用工业化的实验方法研究.....一个抗癌的“曼哈顿计划”。
《众病之王》读后感(十):摘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96-9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7:33:28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军事史——但敌人无影无踪,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这里同样有胜利与失败、有连绵的战役、有英雄人物也有傲慢之徒、有劫后余生也有旧病复发;并且不可避免地,有人受伤、有人被诅咒、有人被遗忘、有人死亡。最终,癌症真实地浮现出来,正像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曾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的——众病之王,恐怖之君。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04-10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7:34:14
但是,有一项鸣谢却不能放在最后。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癌症过往的探访之旅,也是我作为癌症研究者的个人“成年之旅”。而如果没有那些病人,这第二段旅程也是不可能成行的。他们,超越了所有的贡献者;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教导我、启发我。我永远都欠他们一份情、一笔债。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80-18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7:45:59
索尔仁尼琴可能打算用荒谬的、极权主义的肿瘤医院,来比拟医院外荒谬的极权主义国家,但是,我曾向一位患浸润性宫颈癌的女人询问这种“相提并论”,她讽刺地说,“不幸的是,我并不需要任何隐喻来阅读这本书。癌症病房就是我受拘的国度、我的监狱”。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04-20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7:48:34
2500年前,36岁的阿托莎(Atossa)身患Ⅲ期乳腺癌,她的绝望与悲愤久久地回荡在耳边。这位波斯王后用布裹住自己癌变的乳房,藏匿起患病的躯体,然后以一种毅然决然与先见之明的态度,极其愤怒地要求手下的奴隶用刀把她的乳房割下来。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13-21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7:50:54
这种看似简单的机制(细胞毫无障碍的生长)能够位于这个怪诞多形的疾病的核心,证明了细胞生长具有深不可测的力量。细胞分裂使生物体能够成长、适应、恢复和修复——让生物体能够生存。而这种机制一旦被歪曲和解缚,它就可以让癌细胞生长、繁荣、去适应、去恢复、去修复——以我们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癌的生存。癌细胞(比正常细胞)生长得更快、适应得更好。癌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更完美的“版本”。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20-22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7:51:45
癌症是生在我们的基因组里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解放了正常细胞分裂的那些基因,并不是“外来者”,而恰恰是“曾执行关键细胞功能的基因突变、自我扭曲的版本”。而且,癌症根植于我们的社会中:随着我们这个物种寿命的不断延长,也不可避免地会释放恶性增长(癌基因突变随着衰老而逐渐积累,因此,癌症在本质上与年龄相关)。如果说我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话,那么,从一种执拗的意义上说,癌细胞也在寻求长生不死。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25-22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7:56:16
正如20世纪生物学家霍尔丹喜欢说的,“宇宙”不仅比我们设想得更奇特,而且比我们所能设想得更奇特。科学的轨迹也正是如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未来的故事无论怎样展开,都会打上过往人类曾经尝试各种努力的烙印。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08-31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8:02:31
一百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另一种疾病的名称改变——从“同性恋相关免疫疾病”(gayrelated immunedisease, GRID)变成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艾滋病AIDS),标志着人类对该病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10-31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下午8:03:09
魏尔啸像贝内特一样不了解白血病。但是,他没有像贝内特那样不懂装懂,他的见解完全出自于“负面效应”(negative)的视角。他抹掉黑板上所有的先入之见,清理出了一片可供思考的天地。 这个谦逊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95-39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7:56:11
白血病,尽管有许多特质,却也有一项独特的诱人之处——它是可以计量的。 科学始于计数。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528-53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08:20
法伯在1947年进入“癌症世界”时,十年前的舆论浪潮已完全消退。癌症已再次成为一个政治上无声的疾病。在儿童医院通风良好的病房内,医生与患者正在进行着一场仅属于他们自己的癌症战争。而在楼底下的通道里,法伯则以他的化学品和实验,开启了一场一个人的战斗。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531-53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25:13
这种孤立反而是法伯取得早期成功的关键。法伯与公众监督的聚光灯绝缘,促使他可以针对令人困惑的“癌症版图”中的一小片进行研究。白血病是疾病中的一个“孤儿”——内科医生抛弃了他,因为无药可救;外科医生抛弃了他,因为谁也不能对血液开刀。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从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二战’以前,白血病甚至算不上是癌症”。这种疾病寄生于疾病王国的“边陲”,是一个潜伏在学科之间和科室之间的“贱民”——恰与法伯本人同病相怜。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669-67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35:33
法伯第一次临床试验的失败,曾激怒了儿童医院院方。现在的第二次临床试验把院方的忍耐逼到了墙角。医院通过表决,认为白血病病房的气氛过于激进、太过冒险,不利于医学教育,因此决定从白血病化疗病房撤出所有儿科实习医生。这一决定实际上让法伯小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法伯和他的助手们只能亲自承担所有照顾病人的工作。正如一名外科医生指出的那样,患有癌症的儿童,通常都被“塞到医院偏远角落里的病房中”。儿科医生认为,既然他们已经离死不远了,何不更仁慈温和一些,“让他们平静地死去”。一位临床医生建议,将法伯新的“化学品”只留作挽救孩子生命的最后一招。这令法伯不禁回想起自己以前作为病理学家的生活。他忍不住反唇相讥:“真到那个时候,你需要的唯一药品就是防腐液了。”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677-68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35:54
法伯的助手们要自己削尖骨髓针,这种古老过时的做法犹如让外科手术师自己在磨刀石上磨刀。他的工作人员注重细节,一丝不苟地跟踪记录患者的病情:每一次血球计数,每一次输血,每一次发热,都要详细记录。如果能战胜白血病,那么法伯希望能为后人记录下这场战役中的每一分钟,即使没人愿意亲眼见证。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704-70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37:17
1948年夏天,法伯的一位助手为一名接受了氨基喋呤治疗的白血病患儿进行骨髓活检,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他写道:“骨髓看起来那么正常,让人恍惚以为可以‘治愈’白血病了”。 法伯的梦想的确如此。他梦见某种特异性的抗癌药物杀死恶性细胞,让正常细胞再生,重新回到它们的生理空间;他梦见一整套能消灭肿瘤细胞的抗癌药物;他梦见用化学药品治愈了白血病,然后再将这种施治经验应用于更一般性的癌症治疗中。法伯在抗癌医学领域掷下了挑战书,令整整一代医生和科学家投身于这场战争中。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724-73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42:22
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者把肺结核(或曰“痨病”)提升到了病理学上的一种极端表现——发热、不停不休、难以呼吸、极富强迫性。这是诗人的疾病:约翰·济慈(JohnKeats)在一个小房间里,俯瞰着罗马城的西班牙阶梯,渐渐地走向死亡;或者迷恋浪漫的拜伦(Byron),幻想着死于这种疾病,让他的情人心疼。1852年,梭罗(Thoreau)写道:“死亡和疾病往往是美丽的,就像……痨病引起的脸泛红光。”在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中,这种“脸泛红光”在其受害者身上释放了热烈的创造力——一种清醒、启发、宣泄的力量,似乎满载着时代的精华。 癌症,相比而言,则充满了更多的当代形象。正像外科医生兼作家许尔文·努兰(Sherwin Nuland)所写的:癌细胞是一种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者”,“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位不守规矩者”。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734-73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44:34
如果说痨病曾经通过病理性地掏空内脏来杀死患者(结核杆菌逐渐地蚀空肺部),那么癌症则是通过让体内充斥太多的细胞,而令患者窒闷而死;其意义恰与痨病的消耗互补,是一种“过度”的变态。癌症是扩张主义者的疾病;它侵入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充满创意;它手段残酷、精明狡诈;它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有时候,它似乎是在教我们要怎样才能生存下来。面对癌症就是面对一个同类物种,这一物种甚至比我们更适于生存。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739-74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45:21
癌症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恶毒的现代恐怖幽灵。这种形象令人如此难忘,是因为它至少部分是真实的。癌细胞是正常细胞的惊人变态。癌症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入侵者和殖民者,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所凭借得逞的特性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赖以取得成功的特性,是一样的。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752-75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50:53
如果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达尔文式选择的终极产物,那么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我们体内潜伏的疾病,也同样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终极产物。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779-78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56:38
乳房上鼓起的肿块,又硬又凉,且密实如河曼果,潜伏在皮肤下蔓延——很难再找到对乳腺癌这么生动的描述了。莎草纸上每一个病例中,都有简洁的治疗讨论,即使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如通过耳朵向做了神经外科手术的病人灌以牛奶、为伤口敷药膏、为烧伤涂油膏。但对于第45个病例,印和阗陷入了不寻常的沉默。在“治疗”项下,他只写了短短的一句:“没有治疗方法。” 在承认了医疗上的无能之后,癌症就几乎从古代医学史中消失了。其他疾病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循环,在传说和史册中留下了它们神秘的足迹。公元前1715年,狂暴的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Typhus),肆虐了港口城市阿瓦里(Avaris),杀死了大量人口。公元前12世纪,天花在一些地区爆发,天花令拉美西斯五世(RamsesV)的脸上落下了麻子。在印度河流域,结核病如同季节性洪水一般起起落落。然而,如果说癌症在这些大规模流行病的空隙中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只存在于沉默中,在医学文献或其他文献中未留下可循的踪迹。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788-80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8:58:26
印和阗描述肿瘤两千年后,我们才再一次听到癌症的消息。这次它同样也是遁形于沉默中,成为一种隐秘的耻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440年左右撰写了《历史》(Histories)的一书,其中记载,波斯皇后阿托莎突然患上了一种不寻常的疾病。阿托莎是赛勒斯(Cyrus)的女儿,也是大流士(Darius)的妻子。大流士不仅继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帝位,也继承了以残暴著称的统治手段,国土从地中海的吕底亚跨越到波斯湾的巴比伦。阿托莎皇后在位期间,发现自己的乳房上有一块流血的肿块,可能是由一种特别恶性的炎性乳腺癌造成的(在炎性乳腺癌中,恶性肿瘤细胞侵入乳房的淋巴结,造成红肿)。 只要阿托莎愿意,从巴比伦到希腊的医生便会蜂拥而来,侍候于病榻之侧。但与此相反,她却自我封闭,脾气暴躁又令人费解。她将自己裹在床单里,强加隔离。大流士的医生很可能曾试图治疗她,但无济于事。最终,一名叫德摩西迪斯(Democedes)的希腊奴隶说服了她——让他来帮助她切除肿瘤。 手术后不久,阿托莎就从希罗多德的文本中神秘地消失了。对于希罗多德来说,她仅仅是一段小小的剧情曲折。我们不知道她的肿瘤是否复发了,或她是怎样死的、何时死的,但德摩西迪斯的这次切除至少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他让阿托莎摆脱了这一病痛的折磨,活了下来。阿托莎内心充满了狂热的感激之情和领土野心。原来大流士一直计划东征邻国东斯基泰(Scythia)。而一心重返故乡的德摩西迪斯怂恿阿托莎向夫君游说,向西征讨希腊。波斯帝国从东到西的转身,以及随后一系列的希波战争,成为西方早期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因此也可以说,是阿托莎的肿瘤悄悄扬起了千艘战帆。癌症,即使是作为一种秘密的疾病,也在古代世界留下了它的指纹。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832-83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08:44
如果这一发现的确代表一个古老的恶性肿瘤留下的瘢疤,那么癌症就远远不是一种“现代病”,而是有史以来,在人体标本上见过的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很可能还是最古老的疾病。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844-84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10:24
癌症在世界上的崛起是由“双重否定”造成的结果:只有当所有其他的“人类杀手”被消灭了,癌症才成为普遍现象。19世纪的医生往往把癌症与文明联系在一起,认为现代生活的匆忙无序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体内的病理变化,导致了癌症。这种推论是正确的,但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文明并没有导致癌症,而是通过延长人类的寿命,暴露了癌症。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873-87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14:26
疾病,从某些角度来讲,只有我们感知到了它、命名了它,并对它做出了反应,它才存在。 —— C.E.卢森堡(C.E. Rosenberg)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879-88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15:38
古代疾病的名字本身就是浓缩的故事。斑疹伤寒是一种凶猛的疾病,伴有不稳定发烧、蒸汗的症状。这种疾病的称谓来自于希腊词语“tuphon”(众风之父)。现代词语台风(typhoon)亦来源于此。“流感”(influenza)来自于拉丁词语“influentia”,因为在中世纪医生们的想象中,流感的循环爆发是受到了恒星与行星靠近或远离地球的影响。肺结核(tuberculosis)是由拉丁语“tuber”转化而来。“tuber”指的是膨胀的腺体,像小蔬菜一样的团块。淋巴结核被称为“scrofula”,来自于拉丁语中表示“小猪崽”的词语,其病征为一系列肿大的腺体,排列成行,让人想到一群哺乳的小猪崽。 在公元前约400年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时代,一个描述癌症的词语“karkinos”首先出现在了医学文献中,它来自于希腊语“螃蟹”一词。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879-88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16:02
古代疾病的名字本身就是浓缩的故事。斑疹伤寒是一种凶猛的疾病,伴有不稳定发烧、蒸汗的症状。这种疾病的称谓来自于希腊词语“tuphon”(众风之父)。现代词语台风(typhoon)亦来源于此。“流感”(influenza)来自于拉丁词语“influentia”,因为在中世纪医生们的想象中,流感的循环爆发是受到了恒星与行星靠近或远离地球的影响。肺结核(tuberculosis)是由拉丁语“tuber”转化而来。“tuber”指的是膨胀的腺体,像小蔬菜一样的团块。淋巴结核被称为“scrofula”,来自于拉丁语中表示“小猪崽”的词语,其病征为一系列肿大的腺体,排列成行,让人想到一群哺乳的小猪崽。 在公元前约400年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时代,一个描述癌症的词语“karkinos”首先出现在了医学文献中,它来自于希腊语“螃蟹”一词。肿瘤,以及它周身蔓生的肿胀血管,让希波克拉底想到了挥脚掘沙的螃蟹。这种画面很奇怪(很少有癌真长得像螃蟹),但也很生动。后来的作家,包括医生和患者,都为其加入了修饰。在有些人眼中,肿瘤硬化黯淡的表面让人不禁联想到螃蟹那硬邦邦的躯壳。有些人觉得肿瘤在体内悄悄扩散,仿如螃蟹在皮肉之下行走。对另一些人来讲,癌症带来的突然刺痛就像是被螃蟹的大螯夹到了一样。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889-89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17:13
还有一个希腊语也和癌症的历史发生了交汇,那就是“onkos”——人们有时用这个词来描述肿瘤;现代肿瘤学的用语“oncology”正是脱胎于此字。“Onkos”在希腊语中表示一种分量或负载,或者更通常地表示为一种负担——癌症被设想为身体上承载的一种负担。在希腊的舞台上,“onkos”这个词还被用来描述一种悲剧角色的面具,这种角色的头上往往戴着一个笨重的锥状物,象征着其所承载的心理负担。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894-89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17:32
希波克拉底的“karkinos”大多是肉眼即可看到的大型表皮肿瘤,如乳腺癌、皮肤癌、颌癌、颈部癌和舌癌。他甚至连恶性肿瘤和非恶性肿瘤都没有区分出来。希波克拉底的“karkinos”包括任何一种可以想到的隆肿:像是结节、痈、息肉、突出、结核、脓疱和腺体。他将各种隆起不加区别地堆入了同一个病理学范畴。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910-91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22:13
在中世纪抑郁症被称为“melancholia”,它得名于希腊词语“melas”(黑)和khole(胆汁)。因此,抑郁症和癌症这两种因黑胆汁而患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因其内在特质而纠缠在了一起。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980-98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31:32
不管维萨里多么努力地检视人体,他仍然无法找到盖伦所说的“黑胆汁”。“autopsy”(尸检)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亲眼看见”;随着维萨里学着自己亲眼所见,他已不能再满足于盖伦的虚幻定论。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056-105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11:12:48
消毒和麻醉这两项技术的突破,让手术化蛹成蝶,从中世纪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有了乙醚和石炭酸皂做武器,新一代的外科医生冲破了曾令他们望而止步的瓶颈,在人体上实现了亨特及其同事当年只能对尸体进行的复杂解剖程序。一个癌症手术的辉煌世纪展现在人们面前。从1850至1950年,外科医生向癌症发起了大无畏的进攻——剖开身体,切除肿瘤。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096-109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11:15:53
结束了:她穿上衣服,优雅而轻柔地走下桌台,寻找詹姆斯;然后她转向那位外科医生和他的学生们,屈膝行礼——并低声而清晰地请求,如果她有不当的举止,请他们原谅。我们这些学生,全都像孩子一样哭泣着;外科医生把她搀扶起来。 ——约翰·布朗(John Brown)描述19世纪的一次乳房切除手术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113-111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11:17:12
他用英勇的奥利匹克式精神,拼命努力达到生理极限,随之而来又是几近崩溃的状态。这种模式,几乎成为了霍尔斯特德面对任何挑战的解决方式。他在进行外科手术、外科教育以及癌症研究时,也留下了相同的独特印记。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190-119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11:22:50
霍尔斯特德承认自己的手术是一种“肉刑”,乳房切除术牵连甚广,永久地损毁了病人的形体。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193-119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11:23:06
然而霍尔斯特德认为这些后果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是在一场全面的战争中,伤残是无法避免的。但霍尔斯特德也流露出对病人真挚的关怀,在描述90年代所做的创口深至脖颈的手术时,他写道:“患者是一位年轻小姐,我真不愿毁坏她的外形。”在他的手术笔记中,除了潦草地记录手术结果,还有一些个人备忘录,用语温柔,宛如一位慈父。在某一病例结案后他写道,“手臂运用自如,都可以伐木了……无肿大”,在另一个案例的页边记下:“已婚,有四个孩子。”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312-131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11:39:00
希波克拉底宣誓:我愿以自身判断力所及,遵守这一誓约。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让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519-152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8:23:03
当时,与埃尔利希同一车厢的学者已经打起盹来。但是,他在这节车厢中的激昂陈辞却以其纯粹、根本的形式道出了医学界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化学疗法”——使用特定化学物质治疗疾病的这一观念,在这个午夜时分诞生了。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529-153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8:25:54
试验了几百种化学品后,埃尔利希与其合作者找到了他们的第一种抗生素:一种鲜艳的红宝石色染料衍生物,埃尔利希称之为“锥虫红”(Trypan Red)。这个以疾病和染料颜色并列命名的名字,主宰了医学史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585-158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8:35:11
战时的化学家回到他们的实验室,去设计新的化学物质以用于其他战场,而埃尔利希学术遗产的继承人,则继续四处去搜寻特异性化学物质。他们寻找可以除去人体内癌症的“神奇子弹”,而非让受害者半死不活、失明、起水疱和终身贫血的毒气弹。他们的梦幻子弹最终竟出现在剧毒的化学武器中,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对特异亲和性的曲解,残酷地扭曲了埃尔利希的梦想。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718-172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8:51:05
科斯特来到法伯的办公室,看到的却是一位激昂、表达清晰、心怀远大愿景的科学家,犹如隐于斗室的弥赛亚。法伯并不想要一台显微镜,他提出了一项富有远见的计划,令科斯特着迷。法伯请求综艺俱乐部帮助他创立一项新的基金,用于建设大规模研究型医院,致力于儿童癌症的研究。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794-179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8:54:23
法伯认识到,这场针对癌症的运动很像一场政治运动:它需要偶像、吉祥物、形象和口号;它既需要广告策略,又需要科研方法。任何疾病,想要提升到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就得进行推销,正像政治运动需要推销一样。一种疾病,要想实现在科学层面的转变,首先需要政治层面的转变。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802-180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8:54:49
从语源学上来说,“患者”就意味着“受罪的人”。最令人深深恐惧的,不是受罪本身,而是受屈辱的折磨。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812-181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04:33
许多儿科医生认为法伯是“入侵者”,所以在医院内部增加他的病房空间是不可能的。一位医院的义工回忆说:“大多数医生认为他为人自负,又不知变通。”在儿童医院,即使有空间能容纳病人的几具尸体,也没有空间来容纳他的“自我”。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831-183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05:46
人们可以从细微处看到法伯那双执著的手的影子。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法伯,生性节俭。[列昂纳多·劳德(Leonard Lauder)喜欢这样评价他这一代人:“你能把孩子从大萧条中带出来,但是你却不能把大萧条从孩子体内带出来”。]尽管如此,对吉米诊所,法伯还是舍得放手去做——在通向门厅宽大的水泥阶梯上,每个台阶只有1英寸高(约2.54厘米),孩子们可以轻易地攀上去。阶梯由蒸汽供暖,以对抗波士顿严酷的暴风雪。就在五年前的那个冬季,这样的暴风雪几乎终断了法伯的工作。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838-184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06:13
周边医院的走廊中通常悬挂的是已故教授的画像,鬼影幢幢;而这里的走廊却大不一样,法伯委托一位艺术家画上真人大小的童话人物——白雪公主、匹诺曹、小蟋蟀,在“癌症世界”里融入了“童话世界”。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846-184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07:49
一位50年代初曾在法伯诊所接受过治疗的孩子的母亲写道:“我对这所医院中所弥漫的欢乐气氛不断感到惊异,因为我发现所有我看到的孩子,几乎在几个月之内都会注定死掉。的确,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父母们满腹狐疑的眼神特别明亮,那是流出的或未流出的泪水。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853-185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08:10
他陷在了自己的候诊室中,仍然在苦苦寻找下一种药品,能够让他的孩子们再勉强多维持几个月的生命。他的病人们,曾走过奇妙的汽暖阶梯,来到他的办公室;曾在音乐木马上腾跃旋转;曾沉浸在童话世界的欢乐中……但到头来,他们都会无情地走向死亡,而夺去他们生命的仍然是与1947年同样的癌症。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939-194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13:21
在经过了一段无效的治疗后,拉斯克的母亲于1940年在威斯康星去世。对于拉斯克来说,母亲的病逝点燃了她埋藏几十年的愤慨与怒火。由此,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之后,她告诉一位记者:“我要对抗心脏病和癌症。就像我们对抗罪恶一样。”玛丽·拉斯克要消除疾病,就像牧师通过传播福音来消除罪孽一样。如果人们不相信对抗疾病的国家战略之重要性,她会用尽一切方法,改变他们的观念。 第一个被她改变的人,就是她的丈夫——亚尔伯特·拉斯克,他理解了玛丽的决心,成为她的合作伙伴、顾问、战略家和同志。他告诉妻子:“资金到处都有,我告诉你怎么去争取。”通过政治游说和史无前例的规模募资来改变美国医学研究现状这一主张,让玛丽感到振奋。和专业的科学家、职业运动员一样,拉斯克夫妇都是专业社交家,有丰富的人脉、出色的游说术,善于跟人打交道,说话让人舒服,且言之凿凿,令人信服;通过写信、办鸡尾酒会、与人谈判、巧妙地搬出社会名流彰显自己的身价,最后与人敲定合作,各种手段,运用自如。筹募资金特别是广交朋友,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他们的社交网络四通八达,能够轻易直达私人捐赠者以及政府的心灵和钱袋。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987-199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15:16
随着里多的辞职以及董事会的更迭,福特和拉斯克更加势不可挡。为了适应这次接管,社团的章程体制都被重写,这一进程快得几乎像报复(里多)一样,再一次强调了它游说和筹款的行动。标准公司(Standard Corporation)的总裁(同时也是“外行团队”中的一位首要交涉者)吉姆·亚当斯(Jim Adams)为协会草拟了新的规则,对于一个科学团体来说,这一新规则恐怕非同寻常——“委员会不应该容纳四名以上专业人士和科学家,首席执行官应该是非科学人士。” 在这两句话中,亚当斯简述了美国癌症协会发生的非凡改变。这个社团当时是一颗高风险的重磅炸弹,由一帮“外行”积极分子带头筹款,为医学运动展开宣传。拉斯克是这个集团的中心,它的核心动力、它的“女王蜂”。这些积极分子被媒体称为“拉斯克派”。这是一个令他们骄傲并欣然接受的名字。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1999-200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15:58
但是拉斯克灵敏地抓住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这场战役在被推送到国会之前,必须首先在实验室打响。不过,她还需要一位来自科学界的盟友,发起一场募集科研经费的战斗。在众多广告商和游说者之外,“抗癌战争”还需要一名来自科学界的人鼎力相助,一名真正的医生。这个人,既要理解拉斯克派优先考虑政治的本能,又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还要拥有无懈可击的科学权威。最理想的是,他/她能专注于癌症研究,但又愿意从这种专注中站出来,在一个更大的、全国性的舞台上奋斗。这个角色的人选,恐怕也是唯一的人选,非西德尼·法伯莫属。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需求珠联璧合:法伯急切地需要一名政治游说者,正如拉斯克派急需一名科学战略家一样。就像是两队旅者的相逢,每一队都带着另一方需要的半张地图。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026-203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20:02
法伯在给拉斯克的信中亲切地写道:“我给你写了很多次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我日益喜欢的技巧——心灵感应。但是这些信从来没有寄出去过。”从相识发展为熟知,再从熟知发展为友谊,法伯与拉斯克建立起一种协作伙伴关系,一直延续了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法伯开始把他们的抗癌战役描述为“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对于西德尼·法伯,还有玛丽·拉斯克来说,这场抗癌战役的的确确变成了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张扬狂热与科学的战斗,唯有这个宗教上的比喻才能领会它的实质。好像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不可动摇、坚定不移的“治愈癌症的前景”,为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推动一个甚至不很情愿的国家向这个前景走下去。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176-217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28:25
。索尼娅·戈尔斯坦(Sonja Goldstein)两岁的儿子大卫,在1956年通过化学疗法治愈了维尔姆斯氏瘤。在她看来,这家诊所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既美妙又悲惨……难以言喻的压抑,同时无法形容地充满希望”。走进癌症病房的那一刻,戈尔斯坦写道:“我感到一种兴奋的暗流,一种(持续的)就要看到曙光的感觉,尽管一再受挫,却让我依旧充满希望。”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198-220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32:18
每天晚上,法伯会来到病房。他就像是船长,强力驾驶自己的无帆之舟驶过这片凶险未知的海域。法伯在每张床前停留,记笔记、讨论病情,也常常严厉指示身后的随行人员——住院医生、护士、社工、精神病医师、营养师和药剂师。法伯坚持认为,癌症是一个“总体性疾病”。这种病不仅从身体上,还从精神上、社会上、情绪上紧紧咬住病人。只有发动一场多方面、多学科的攻击,才有可能战胜这种疾病。他把这个理念称为“全面照料”。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409-241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4日星期五 上午8:31:06
李敏求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深刻但基础的肿瘤学原理——癌症治疗必须在每一种可见迹象都消失后,仍然继续保持系统的治疗。hcg水平——绒毛癌分泌的激素,才是它真正的指纹、真正的标记。此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试验验证了这个原理。但是在1960年,肿瘤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项提案。直到几年以后,人们发现李敏求用增加化疗次数治愈的病人再也没有复发,这才震惊了之前草率开除他的委员会。李敏求以自己的职业为代价,催生了第一例成人被化学疗法治愈的案例。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536-254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5日星期六 上午7:38:19
在科学的传说中,人们经常用心跳加快、异样的光辉来描述“科学大发现时刻”那激动人心、摒心静气的一秒,观察结果突然清澄透明,汇聚成一种新的形态,如同万花筒里的碎片,猝然成型。苹果从树上落下砸中了牛顿,也砸出了万有引力定律。阿基米德从浴缸里一跃而起,配平了方程式,导出了浮力定律。 但是,很少有记录记载另一种负面的、有关失败的“发现时刻”。它往往是科学家独自面对的时刻——患者的CT扫描显示,淋巴瘤复发了;曾被药物杀死的细胞又开始复生;一名患儿带着头痛回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665-266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5日星期六 上午7:55:43
但不论她有多么坚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尝试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无法面对这个明显的问题。主治医生坐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 比阿特丽斯最终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她耸耸肩,茫然地看着我们:“很抱歉,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终点。” 我们难为情地低头不语。我猜这并不是第一次由病人来安慰无计可施的医生。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2932-293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7日星期一 上午10:39:48
平克尔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儿童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不能再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了。我们不能再接受以缓解为目标的治疗方案。” 当然,他是在写给未来,但在一种更神秘的意味上,他也是在写给过去,写给那些曾深深怀疑白血病治疗,以及曾与法伯争论要让这些孩子“在平静中死去”的那些人。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060-306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下午6:58:57
宗教活动和教派活动往往基于四个元素:一位先知、一个预言、一部经书和一个启示。到了1969年夏天,抗癌十字军已经获得了四个元素里的三个。先知是玛丽·拉斯克,这位女士曾带领着这支队伍走出20世纪50年代的黑暗荒野,在仅仅20年后,就让它在全国备受瞩目;预言则是儿童白血病的治疗,以法伯在波士顿的试验为开始,以平克尔在孟菲斯的惊人成就为终结;经书则是贾伯的《治愈癌症》。最后缺少的那个元素就是一个启示,一个能预示未来、夺得公众想象力的标志。就像其他具有伟大启示的精神一样,这个启示也会出乎预料地神秘降临。启示,的的确确,将从天而降。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172-317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下午8:24:37
1969年,玛丽·拉斯克展示了她的战略天赋,提出创立一个“中立的”专家委员会,称作 “征服癌症委员会”(Commision on the Conquest of Cancer),为总统提出最有效的战略意见,以便发起对癌症的系统进攻。她写道,这个委员会应该“包括空间科学家、企业家、管理者、规划人员和癌症研究专家……委托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为美国国会描绘征服癌症的可能”。 当然,拉斯克确保了这个委员会(最后被称为顾问组)一点也不中立。它的成员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全部都是拉斯克的朋友、同路人和同情者,是一群献身于抗癌战争的男女。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269-327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下午8:31:51
这是一部畸形的法案,明显想讨好各个方面,但却无法满足任何一方。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364-336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8:52:19
作家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曾说过,“政治革命,通常都发生在宫闱禁地,在权力的交汇之地,既不在外,也不在里”。与此相反,科学革命则一般发生在底层,在远离思想主干道的偏远地带。但是,外科革命一定是从外科医学的内部圣殿开始,因为从本质上讲,外科医生是一种对外封闭的职业。就算只是进入手术室,也必须先用肥皂和水把手清洗干净,遵循外科传统。因此,只有外科医生才能改变外科医学。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385-338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8:53:38
但这个真相是不是真的?凯恩斯没有办法证明。直到20世纪30年代,临床试验的设计一般只能证明“正”结果,即疗法A优于疗法B,或者药物X优于药物Y。但要证明一个“负”结果——根治性手术疗法并不优于传统手术疗法,则需要一套新的统计衡量方法。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403-340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8:54:55
即便是距凯恩斯的发现整整40年以后,克莱尔也无法用试验来反驳霍尔斯特德的乳房切除术。医学中的等级制度、内部文化,以及被克莱尔戏称为“外科专业的圣经”的训练仪式都是抗拒改变和维持正统的理想工具。克莱尔发现他在与自己的部门、朋友和同事作斗争。那些他最需要的、能收集数据进行试验的医生,正是强烈地、甚至恶毒反对他的人。“Power”一词在口语中的“权力”之意,和统计学上的“效能”之意不谋而合。那些煞费苦心打下了根治性外科手术江山的外科医生,没有任何进行革命的动力。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419-342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8:57:56
手术室里的另一方令人兴奋地觉醒了。这一方就是手术刀另一端久久沉默、被麻醉了身体的癌症病人。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438-344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8:58:48
“临床医师,不管多么受到尊重,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经验,不管多么丰富,都无法被当作科学效力的指标。”费舍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愿意相信神的智慧,但霍尔斯特德理论并不是神的智慧。他直率地对一个记者说,“我们相信上帝,但其他人(必须)用数据说话”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448-345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8:59:48
1981年,试验结果终于公之于众。三个试验组的再生率、复发率、死亡率和远端迁移率在统计学上没有任何差别。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的那一组,付出了身体不健全的沉重代价,却没有在存活率、再生率和死亡率方面获益良多。 从1891年到1981年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大约有50万妇女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根除”癌症。其中许多人是自己选择的,也有许多人是被迫的,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意识到她们可以选择。许多人被永久性地毁形了;许多人视接受手术为万幸;许多人勇敢地忍受了它的折磨,希望极致的手段能彻底治愈他们。霍尔斯特德的“癌症仓库”超越了霍普金斯的局限,他的观点进入肿瘤学,渗透到它的词汇表里,进入它的心理、它的精神气质和它的自我形象。当根治性手术被证明失败的时候,整个外科手术文化也随之消融。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480-348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9:01:20
奥尔索普一针见血地指出,“拯救某个病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任务,虽然医生花费大量精力来拯救每个病人的生命,或者说至少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拯救某个特定病人的生命,而是要找到方法去拯救所有人的生命”。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567-356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9:09:18
对于陷入癌症死亡阴影的人而言,额外的一年可能包含了一生的意义。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721-372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下午4:36:35
如果我不能好转,你会赶我走吗? ——20世纪60年代一位癌症患者致她的医生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835-383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下午4:54:20
单词“姑息”(palliate)来自于拉丁语“托词”(palliare)——它提供缓解疼痛,被视为是掩盖了疾病的本质,掩盖症状而不是攻击疾病。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841-385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下午4:56:00
重建癌症患者理智和尊严的生活这一临终护理运动的浮现成形,不是源自痴迷于治愈的美国而是来自于欧洲。它的创始人是塞西莉·桑德斯(Cecily Saunders),一位曾经的护士,后来在英国经过再培训后成为医生。20世纪40年代末,桑德斯在伦敦曾经照顾一个来自华沙的因癌症而垂死的犹太难民。这名男子把自己毕生积蓄的500英镑都留给了桑德斯,唯一的遗愿就是“给她家开一扇窗户”。当20世纪50年代,桑德斯开始走进和探索被遗忘的伦敦东区的癌症病房时,她才亲身体验到那个神秘请求的意思:她看到绝症患者往往被忽视了尊严、缺少止痛的治疗,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护理。简直可以说他们的生活被局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桑德斯发现,这些“无望的患者”已成为肿瘤学的弃儿,在他们的战斗中,无法找到任何与胜利有关的修辞,于是他们像没用的伤兵一样,被弃之不顾,无人问津。 桑德斯发明了或者说是复兴了相反学科——姑息疗法,作为回应,回避了“姑息照料”。她写道,这是因为“照料是一个柔软的字眼”,永远不会赢得医学界的尊敬。如果肿瘤学家不能亲自向绝症患者提供应有的护理,就会求助于其他专家,如精神科医生、麻醉医生、老年医学医生、物理治疗师和神经学家,让病人无痛苦和优雅地死去。而她也会把垂死的病人从癌症病房里转移出去:1967年,她在伦敦创建了安养院,该院是为了专门照顾那些病危临死的患者而设置的,起名为圣·克里斯托夫(St. Christopher):不是死亡,而是以旅行者的守护圣徒命名的。 桑德斯的行动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传到美国,并渗透进充满乐观的肿瘤病房。一名病房护士回忆说:“向患者提供姑息治疗,遭遇到如此深层的抵抗,以至于在我们建议放弃拯救生命,转而拯救尊严的时候,医生甚至不会用眼睛看我们……医生对死亡的气息过敏。死亡意味着失败,和疾病斗争的失败——这是他们医生的死亡,是医学的死亡,也是肿瘤学的死亡。”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864-386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下午4:57:38
桑德斯拒绝承认临终关怀事业是在“挖癌症治疗的墙脚”。她写道:“提供……临终关怀,不应该当成孤立于抗癌斗争之外的负面做法。它虽然出现在抗癌斗争让人难以想象并且毫无收益的败退阶段,但在许多方面,临终关怀的原则,同那些其他阶段所需要的基础护理和治疗是一样的,虽然它的回报是不同的。” 这也是在了解敌人。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3997-399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下午5:08:28
贝勒和史密斯指出:“如果要在抗癌症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似乎很有必要改变研究的重点,从研究治疗转而研究预防……在我们进一步追寻总是难以企及的“治愈”之前,我们应该用客观、直接且综合的方式面对过去的失望。”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044-404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下午5:14:08
帕特的工作含义深远。如果引起阴囊癌的是煤烟,而不是一些超自然的神秘体液(根据盖伦的观点),那么必然有两个事实是确实的: 第一,外部介质而非体液的不平衡,一定是癌变发生的根基。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049-404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下午5:14:20
第二,如果外来异物是真正的诱因,那么癌症就是可预防的,没有必要净化体液。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085-408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下午5:16:17
香烟也像病毒突变一样发生了改变,以适应多样的环境。在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它成了地下货币;在英国的参政妇女中,它是一种反抗的标志;在美国郊区,它象征男子汉的粗犷气概;在叛逆的青少年中,它代表着与时代的分歧。在1850年到1950年的动乱世纪,世界充满着冲突、碎裂和迷惑,香烟却提供了与之匹敌,并正好相反的缓解物:友情、归属感、有同种嗜好的亲密感。如果癌症是现代性的典型产物,那么,其最主要的可预防的病因——烟草,也同样是现代性的典型产物之一。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091-409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下午5:16:45
我们对统计相关性的直观敏锐度,就像人类眼睛的敏锐度一样,通常在边缘部分表现最佳。当某一罕见事件与另一罕见事件叠加在一起时,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显而易见了。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716-472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37:20
HBV的发现使国家癌症研究所颇感难堪。该研究所花费了大量资金针对特殊癌症病毒项目,给数千只猴子注射了人类癌症提取物,却从没发现一种与癌症相关的病毒。反倒是一位研究原住民抗原的遗传人类学家发现了流传甚广且和常见人类癌症相关的病毒。布隆伯格敏锐地意识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尴尬处境和自己在研究中的机缘巧合。为了避免矛盾,他于1964年明智地离开了国家卫生研究院。他跨学科的好奇心触犯了“科研机构中学科划分的严格性”,而其中最严重的恐怕就是致力探寻癌症病毒的国家癌症研究所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723-472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37:49
但是布隆伯格没有时间反复思索这些冲突。他并没有用理论去研磨病毒与癌症的关系,而是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马上带领团队投入到HBV疫苗的研究之中。1979年,他的团队设计出一种疫苗。像血液检查策略一样,这种疫苗当然没有在癌症发生后改变它的进程,但它却能大幅降低未感染者的易感性。布隆伯格因此创立了从病因到预防的关键环节。他鉴定出了病毒致癌物,发明了感染前的检测方法,并且创造了阻挠其传播的方式。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733-473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40:35
但沃伦深信胃炎的真正病因是一种未知的菌种,依据医学信条判断,这种生物体不能在胃腔恶劣的酸性环境中生存。沃伦写道:“自大约一百年前的细菌医学早期开始,就教育学生细菌不能在胃内生长。当我还是个学生时,这个说法人尽皆知,不值一提。这好像以前人们所说的它是‘广为人知的事实’、 ‘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平的’一样。” 沃伦根本没有理会这个所谓“地球是平的”的医学信条。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776-477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41:36
制定预防癌症的有力战略显然来自对病因的深刻理解,鉴定出致癌物不过是迈向它的第一步。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781-478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41:58
癌症病因的多样性令人震惊,在所有的疾病之中绝无仅有。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804-480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46:11
很少有科学家像乔治·巴帕尼古拉(George Papanicolaou)一样,细致地研究了癌细胞的早期转变。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808-482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46:42
巴帕尼古拉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员职位,但这项工作也像卖地毯一样离谱:他被指派去研究豚鼠的月经周期,这种动物在经期既不会明显地出血,也不会排出剥落的组织。巴帕尼古拉学会了运用鼻窥器和棉签从豚鼠体内刮取子宫颈细胞,把它们以薄薄的水状涂敷到载玻片上。 他发现这些细胞像手表的分针,随着荷尔蒙在动物体内周期性地起落,豚鼠子宫颈内的这些细胞也周期性地改变形状和大小。巴帕尼古拉能够以它们的形态作为指导,准确地预测它们的月经周期,而且往往能够精确到天。 20世纪20年代晚期,巴帕尼古拉将这一技术运用到临床病人当中。(他的妻子玛丽亚,据称每日都接受子宫颈涂片检测,这无疑是其坚强婚姻的鲜明体现。)和豚鼠的情况一样,巴帕尼古拉发现,人体子宫颈脱落的细胞,同样可以预示妇女月经周期的阶段。 但是有人指出,所有这些不过是精巧却无用的发明。一位妇科医生狡黠地评论说 “灵长类,包括妇女在内”,大概都不需要靠涂片测定月经周期。在没有巴帕尼古拉的细胞学技术的帮助下,千百年来,妇女们就在预测自己的月经周期了。 这些批评让巴帕尼古拉灰心丧气,回到了自己的切片研究中。他已经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仔细地观察这些正常涂片;他推测,也许这些测试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这些正常的涂片,而是在病理状态下的涂片。如果他能够通过涂片诊断病理状态,那又将会如何呢?这些年来盯着正常的细胞或许只是一段让他有能力辨别异常细胞的序曲? 巴帕尼古拉由此进入了病理世界,他搜集了各种妇科疾病的病例切片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918-492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54:09
筛检的成功之路异常地漫长和狭窄。它必须在过度诊断和不足诊断之间寻找平衡,必须超越以早期检查作为目的的诱惑,同时必须渡过由偏见和选择造成的背叛的窘境。“存活期”这样简单直接的诱惑,不应该是它的终极标准。在每一个步骤,足量的随机取样都至关重要。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923-492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55:42
1963年冬天,有三人着手去验证运用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无症状妇女是否能减少乳腺癌患者死亡。这三个人各自退出了自己本来的研究领域,转而寻求研究乳腺癌的新方法。接受传统教育的外科医生路易斯·韦内(Louis Vent)希望发现癌症的早期形态,来避免行业内业已模式化的大面积损坏性根治手术。统计学家山姆·夏皮罗(Sam Shapiro)致力于设计新方法进行统计试验。菲利普·斯特拉斯(Philip Strax)是纽约的一名内科医生,他加入这项检测的原因或许是三人中最悲情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陪伴妻子渡过了乳腺癌最痛苦的末期阶段。斯特拉斯希望用X射线发现侵袭前的癌变,这是他个人的圣战,他要松开夺去爱妻生命的生物钟指针。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943-494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58:51
这项实验于1963年12月开始,立刻演变成一场后勤供给的噩梦。乳房X射线摄影检查非常繁琐,机器大如牛,底片小如窗,暗房里飞溅着有毒化学物。这项技术最好在专业的X射线诊房中操作,但是由于无法说服远在郊区的妇女长途跋涉去做检查,斯特拉斯和韦内只好将X射线设备移到一辆小货车里,停在曼哈顿中心,挤在冰淇淋贩售车和三明治小贩之间,为在午休期间出来的妇女检测。 斯特拉斯开始了锲而不舍的招募工作。如果被拒绝,他会打电话、写信、再打电话,说服对方参与。这个移动诊所以机器般的精确度,每天对数以千计的妇女进行筛检。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952-495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7:58:56
帘起帘落,门开门关,人进人出。检测像旋转木马一样从白天转到黑夜。经过六年的时间,三人小组令人惊叹地完成了通常需要二十年才能完成的筛检。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4985-499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8:00:57
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的热衷者震惊了。他们承认需要公正的再评估和重新实验。但是,该在哪里进行这样的实验呢?显然不是在美国——这里已经有20万妇女加入了乳腺癌筛检示范项目(不符合再一次实验的资格),而且学术界正对此争吵不休。整个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界在争论中茫然地蹒跚前进,进行过度的实验。他们不是在其他试验基础上进行有条理的再实验,而是发起了多项齐头并进、甚至相互阻碍的实验。1976年到1992年间,数量庞大的乳房X射线摄影试验在欧洲并行展开,分布在爱丁堡、苏格兰,瑞典的好几个地方:马尔默(Malm)、科帕尔贝里(Kopparberg)、东约特兰(stergtland)、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和哥德堡(Gteborg)。与此同时,在加拿大,研究人员自行发起了他们的随机化乳房X射线试验,叫作“国家乳房筛检研究”(National Breast Screening Study)。正像乳腺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样,乳房X射线摄影的实验转变成了一场军备竞赛,每一组都试图超越其他对手。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5022-503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8:04:39
最后,这样的争议终于在瑞典平息。2007年冬天,我访问了马尔默这个20世纪70年代晚期瑞典乳房X射线摄影实验基地。它靠近瑞典半岛的最南端,坐落在毫无特色的灰蓝色风景之间,是一个宁静的灰蓝色工业小镇。斯科讷(Skne)省广袤贫瘠的平原延伸到它的北部,厄勒(resund)海峡环绕在它的南部。70年代的经济衰退严重击垮了马尔默,这个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在近二十年里陷入停滞,城市的迁入迁出率令人惊讶地萎缩到不足2%。马尔默这个被遗忘之地,羁縻着男男女女,构成了无法逃离的队列,实在是进行这种困难重重的实验的理想之地。 1976年,共有4.2万名妇女加入了马尔默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项目。其中一半人(约2.1万名妇女)每年都在马尔默总医院外的小诊所进行一次筛检,另一半则不进行检查,从那时起,两组人就被密切地追踪观察。实验像时钟一样准确地进行着。“整个马尔默只有一家乳房诊所,这对于它的城市规模来说并不常见,”首席研究员英瓦尔·安德森(Ingvar Andersson)回忆说,“所有的妇女一年又一年都在同一家诊所进行筛检,因而研究活动高度一致,尽在掌控之下,这是最能令人信服的一次实验。
==========
众病之王:癌症传 (Siddhartha Mukherjee)
- 您在位置 #5042-505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8:07:16
乳房X射线摄影术,并不是乳腺癌妇女的真正救星。就像数据学家唐纳德·贝瑞(Donald Berry)描述的那样,它的效果“对于某些妇女而言是无可争辩的,但同样其效果之有限也是无可争辩的”。贝瑞写道:“筛检就像买彩票。赢家总是少数妇女……绝大多数妇女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但是她们要花费时间,承担着筛检的风险……50岁之后没有做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的风险就像是不戴头盔骑15个小时的自行车一样。”如果全国的妇女都选择不戴头盔径直骑车15个小时,当然会比起戴着头盔有更多的死亡。但是对于一周一次不戴头盔骑车去街角杂货店的妇女而言,她的风险根本就无足挂齿。 不过至少在马尔默实验中,人们并没有轻视这种细微的差别。原来的筛检组中,很多妇女已经死于各种原因,但是,就像一位当地居民形容的,乳房X射线摄影术“已经像是这地方的一种宗教信仰了”。一个冬日的清晨,我迎风站在门诊部外,看到成群的妇女(有些大于55岁,有些很明显要年轻得多)虔诚地走来接受她们一年一度的X射线检查。我想,这个诊所仍然在以它曾经的效率和勤奋运转着,在其他城市糟糕的实验尝试后,该城严格地完成了癌症预防史上最具潜力也最为困难的实验。病人们轻轻松松地进进出出,就像是午后例行公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