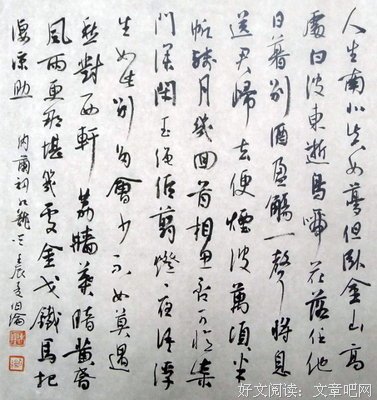当花侧帽说纳兰读后感10篇
《当花侧帽说纳兰》是一本由陈赋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当花侧帽说纳兰》读后感(一):字字玑珠
喜欢纳兰,喜欢他的诗心、痴心、慧心。认识陈赋,才知道喜欢纳兰的不止是那些痴心女子,更有这位不同于流俗的男子。读他写的《当花侧帽说纳兰》,字字玑珠,将纳兰的痴情、纳兰的忧伤、纳兰的义气、纳兰的悲哀淋漓尽致地分析出来。
《当花侧帽说纳兰》读后感(二):非常期待
曾经读过作者所著的《往事》和《吃茶去》,文笔流畅,案头功夫深厚,读来颇为有趣。偶见此书又是其之作品,何况又是讲纳兰若容,自是期待不已。期盼此书的上市!
另外,看这书的封面设计风格,感觉十分眼熟。但看出版社,哈!原来如此。找出手头那本《山楂树之恋》,果然果然,同是凤凰出版集团。嗯,这风格说来,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纳兰:冷暖无常看沧桑
文:周语
在清朝的词人里面,纳兰的词读来最亲切。关于纳兰的解读有N种,陈赋的解读属于心解,他并不严格遵循词的注解形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切入纳兰的生平,使读者在感受文字韵味之余,更能体会这位清朝词人的人生沧桑。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楞伽”二字让人联想到莲花与佛经。联想到他笔下的僧衣、夕阳和夜深人静时的清呗之音。陈赋品纳兰,得意失意流诸笔端,写出与众多词人不同的人生气象,内心世界。
文中的纳兰,总给人一种瘦弱的感觉,浑身散发着隐逸的气质以及入世的悲凉。
人情世故,权力场的角逐,让他感到疲惫而恐慌。或者对于纳兰来说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没有谁能给你最终的答案。
纳兰一生痴绝,是个有情人,诚如作者所写,“忧伤已经溶解在他的血液里”。大约这才是我们熟悉的纳兰:青衣紫佩,游走于宫廷与边塞,内心充满不堪的感伤。
陈赋写纳兰,是在都市里体会清代词人的孤寂。“无常迅速,念念迁移,石火风灯,逝波残照,露华电影,不足为喻”。纳兰到底是个真情人,在这世间沉浮之中,他半醉半醒,吟唱的词,让读者欲罢不能。月下纱窗,一壶茶,看纳兰词,只觉时光匆匆,双鬓半白。情到深处便是痛彻肺腑,而纳兰词初名《侧帽》,后顾贞观更名为《饮水》,则是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味道和感叹。
世间之事,千种纷杂,纳兰品尝了半生的聚散穷通、悲欢离合,此种幽艳哀断之意,流露在文字里,却始终不乏爱的热情,那是一种冷峻的慰藉。
注:此文为《当花侧帽说纳兰》代序
《当花侧帽说纳兰》读后感(四):唯有情难忘
在豆瓣参与凤凰联动的活动,很幸运,能成功申领到这本书。可是由于工作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看,整本书只是零散的看到了一半。好书,是不会被荒废的,争取抓紧时间读完吧!
纳兰词,独树一帜,自成一格,文明古今,就像是一千个读者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相信每一个读过纳兰词的人心中,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体会,对爱情、对事业、对人生,超脱了诗词,却又寄托于诗词。生活中不好言、不能言,皆可在诗中在词中去表达。这也是面临诸多困境、欲挣脱而不得的纳兰词作的来源之一吧!
整本书,挑选纳兰词作中的名篇,作者进行了解读,将他读纳兰的感悟和体会与读者进行了分享。文字简约、清澈,可以看出作者对纳兰词首先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喜爱,然后才能将心中的喜,化落笔端,篇篇精致,字字情真。行间字里都能看到纳兰词带给作者的深深影响。
作者不是简单的将纳兰词进行直白的翻译,而是将自己的个人体会和感悟全部展现出来。也为其他纳兰词的爱好者和粉丝,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角度。整本书,更像是一场诗词交流,更像是与其他的读者,其他喜爱纳兰词的人,分享着这诗词的内涵和独特魅力,期待着不同的声音,却有着同一种共鸣。
读纳兰,最动情处是他对妻子的深深眷恋,自古才子多风流,如纳兰的出身和地位,却能衷情如此,也可说是古今难觅了。因为爱情,这些动人的诗词传世。因为爱情,也让我们再生活困厄之中,心中还能怀有希望。
总的说来,这是一本好书。如果你也喜欢纳兰词,不妨读读这本书,或许,能找到另一个知音。
《当花侧帽说纳兰》读后感(五):走近,是一种幸福——读《当花侧帽说纳兰》
走近,是一种幸福
——读《当花侧帽说纳兰》
文:王玉洁
生命中有很多种走近,陈赋走近的是一颗大清绝世公子的心,藉着他所爱的纳兰词,他试图走近他,触摸他的灵魂,聆听他的爱与哀愁,纳兰变成了他隔世离空的知己。
非深爱而不能成文,非痴迷而不能走近。
他的痴绝、他的洁净、他的挚诚、他的婉转,是天地间第一等情种,他的词,不沾市侩卑俗,是身在广厦的鱼鸟之思,是红尘攘攘的世外仙株,是披肝沥胆的朋友情深,是坚贞如一的情爱缠绵。要想走近这样一颗心,读懂这样一个人的词,必得自己也有痴绝挚诚处,以一种痴绝去感知另一种痴绝,以一种至诚去抚摸另一种至诚,以一种洁净去贮望另一种洁净,以一种婉转去捕捉另一种婉转。
这似乎只有女子方能做到,然后,看完陈赋的《当花侧帽说纳兰》,我想,他做到了女子也不一定能够做到的,就像女子总是下厨房,而最好的厨师却总是男子,细腻感性是女子的特征,但一个文弱书生的笔下,却寥寥数笔勾勒出许多令人怦然心动的细致处。
米兰昆德拉说:“为什么上帝看到思考的人会笑?那是因为人在思考,却又抓不住真理。因为人越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个人的思想相隔万里。”陈赋在感知纳兰词的时候,可能感性更多于思考,所以,他选择一种感性的触摸比纯粹的思考更容易走近那个千年之前的多情公子,让读着的我们,也随着他感性的切入而沉入感性美的牵引中。
用感性美去解读纳兰的词,这不是陈赋的独创,似乎有安意如、苏樱在前,但,陈赋有陈赋的独特之处,安意如和苏樱是女子,陈赋是男子,而要解读的那个人也是男子,女人了解男人毕竟是隔了一层,而男人与男人之间,如果搭建一座感性的桥,似乎,更该是风光独好吧?
读过,方知,安意如适合在春日的草地上读,甜腻腻的,恰如拂面的香风。苏樱适合快速去读,读到喜欢处停下来细细品味。而陈赋的解读,不知不觉,仿佛是一个圈套,你被带进他预设的情感陷阱,“一道炊烟,三分梦雨,忍看林表斜阳”的羁绊于世事的无奈清愁,“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的宏阔与相思,“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深情追忆,“不辞冰雪为卿热”的热泪深情,他的一声轻叹“一片伤心画不成”,他劝姜辰英“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字字句句皆为心语……陈赋是带着自己的浓烈深沉的感情在读的,这种感情通过文字传导给了我们,我们便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一路走下去,走近纳兰,在他的文字里,喜着纳兰的喜,悲着纳兰的悲,伤着纳兰的伤,愁着纳兰的愁。
那一阙纳兰送别好友张纯修的词里,陈赋写道:“在聚散离合的烟水苍茫间,长袍宽袖,青衫磊落,隔着酒杯,飞觞相望,将所有的衷肠简约成杯中的酒,溢着香,埋着泪,不去想红尘的得失,不执着于一时的欢爱,明知醉得再多,哪怕是三万场,依旧是繁华世事落幕之前可怜的陪衬,却愿意在幕落之前,在花谢之前,微微笑着,想那俗世辗转千百回的你我,想那断壁残垣下路过时,手擎一杯喝下去内力炽热的酒,为你一饮而尽,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必说,“不用诉离殇”,是因为不说出来也懂得彼此的离殇。”这样用心用情的渲染,我们很容易便醉在了朋友分别是黯然销魂里。我想,文字的婉约唯美,是如此贴近原词的意蕴,甚至比原词更为婉转多情。
我一向认为,最好的解读就是用心灵真情地靠近,陈赋试图做到,也做得非常成功,一个人,一个梦,陈赋的梦里,一定有一个因为喜欢而走近纳兰的梦吧。
把梦尽量做到圆满,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花侧帽说纳兰》读后感(六):读《当花侧帽说纳兰》
读《当花侧帽说纳兰》
文:花邻
在时下泛滥的纳兰词解读类作品中,陈赋的《当花侧帽说纳兰》可谓清风扑面,该书对词本身理解是准确的,文字干净优美,不腻不柴不无病呻吟,很值得一读。
陈赋对纳兰其人其词的理解到位。对于纳兰的评价,他说,“人世间痴情女子多,痴情男子少。因为少所以可贵,纳兰短暂一生,对爱情痴,对朋友痴,是个血型好男儿,是个当之无愧的奇男子。”——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精炼和全面的。对于纳兰词的解读亦十分到位,《浣溪沙》有“此时相对一忘言”的句子,作者极其精致的解读到,“与佛对视,除了微笑,还能够说什么呢?你所想说的,佛都知道,你说不出来的,佛也知道,那便只有相对一忘言了。在与佛相对的时候,不出一言,却心领神会,已经明白佛旨所在。”我对照了其他的一些注本,都一带而过,语焉不详,基本上解作“此情此景让人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却忽略了“相对”二字,与谁相对呢?是佛像吗?是僧人吗?是同行者吗?本书作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陈赋的知识积累比较深厚,《蝶恋花》有“斑骓一系无寻处”,他指出该句化用李商隐的《无题》诗“斑骓只系杨柳岸”——这是对的。遗憾的是,《饮水词笺校》那样高级的本子也并没有注出啊。
——他写爱情时说,“造化有时就是如此捉弄人,明明不能相守的人,却要在最美好的时光里相遇相恋,然后,留一世隐隐的伤痛。”“那如繁花锦簇般的过往盛放在记忆最深的地方。我知,你在梦里最柔软的角落。”
——他写寂寞时说,“这样的寂寞伤感是如此空旷无边,前也茫茫,后也茫茫,找不到任何依靠和暖意,徒然心痛。人生最孤独的时候,往往目光所能及的地方,苍凉的景物,历历可见,触手可及。”
——他写风物时说,“江南,又最适合安放文人骚客的情怀之地,这里的风物美景、历史文化,无处不能找到与才子心怀对应的触情点。到了江南才知道,原来心里面最柔软的角落,一直等着江南的那只采莲的手轻轻撩开,从此,了无遗憾。”
… …
优美的文字,将“翩翩浊世佳公子”至情至性的情态真实、完美、生动的展现出来,能够帮助读者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一可爱的人物。
陈赋的文字富含哲理。“被人人争着去瞻仰,不如做人群中一个快乐的看客。”“到底,花真的不会老,月真的还会圆,但花非那时花,月非那时月。”“原来,景物是可以千年万年如此的,人不过只是沧海之一粟,在岁月的长河里,不过是一季的幻影。”“繁花是现世的烟花,灿然过后,便是湮灭。”“有时候,最深情的话不是山盟海誓,不是甜言蜜语,而是一句寻常话,寻常话里是只有彼此才知的情重,说得轻松,心里确是波涛汹涌。”寥寥数语即道出了人生的大道理,这样的文字虽非名言,确是实实在在的箴言,耐人寻味。
诚然,《当花侧帽说纳兰》一书也有值得商榷或不足的地方。作者数次提到“嫁作帝王妃的表妹”、“表妹入宫”、“恋人是康熙”,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表妹入宫是野史笔记的记载(顺带说句题外话:个人认为,纳兰有表妹这一婚前恋人,但不是入宫的表妹。)退一步讲,这其实也不算什么毛病,因为解读类文字毕竟属于随笔的体裁,不是学术研究,氛围没必要弄得那么严肃。不足的地方是校对,个别有错字现象,希再版时加以订正,使之更加完美。
(拙笔匆匆写于2011年11月15日凌晨1点)
《当花侧帽说纳兰》读后感(七):寄语落花须自扫,莫更伤春。
写这篇所谓的“评”时,我正在陪读——陪13岁的弟弟上国学课。瞧瞧,国学课!内容是诗经。让一小姑娘站起来复述诗经的第一首《关雎》的含义,小姑娘答得倍儿溜,但我说的是“复述”。
古人诗,莫说是孩子,便是成人能够真正读懂的又有几人,中国传统的文化文学,几乎快要在人们不断追求的钢筋水泥,纸醉金迷中湮没殆尽了。但这人世间总会有那么几个执着的笨蛋,这样的笨蛋不论面对怎样繁复的世界,都能保持一颗憧憬的心,不论自己如何成长如何成熟如何变得世俗,被打磨光了棱角,心中也总还有一块净土。
认识陈先生的人,或许会反应出来,我所说的这类人中,陈先生当排前几。
我总觉得,这不算什么“评”。只是一篇杂七杂八的字。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从小命题作文就不及格,所以只好请陈先生原谅。
拿到书的时候,看着陈先生的题字,心里还小小地窃喜了一下,约莫着日后这书会值一大价钱,故而好生收藏着。但这其中却不全因是他。更是因为他笔下的纳兰。
好吧,绕来绕去,总算绕到正题。
曾跟人谈起纳兰,年少时,与人争到面红耳赤,不许旁人说他一个“不”字,现下向来总也会笑自己。这世间向来没有完美,若那时爱纳兰,也只是爱幻想中那位如玉公子,爱他的满腹经纶,爱他的出淤泥而不染,爱他的文武双全,爱他的人间自是有情痴,却偏偏忘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理应有缺点,有不足,有懦弱。
陈先生笔下的,是最真实的纳兰,不避讳,不隐瞒,只求一种呈现。而不是凭想象意淫而成的翩然佳公子。那些言辞唯美华丽的误读者,却只狭隘而肤浅地关注他的爱情,他的才华,编造出一个又一个为世人所乐道的故事,可是那不过是为读者幻化出的海市蜃楼。严格来说,是对读者的欺骗。
以我所知的陈先生,应有足够的自信,为这本书题一篇自序。但事实上却没有,这多少让我有点失望,改日定要让他补一篇来。我更想通过书中的一切,看到一种个人的,公正的,客观的,直接的对纳兰词乃至纳兰其人的态度和认知。或许这其中有一部分个人原因。
多数人看纳兰词该是都缘于一个偶然,缘于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或是“一生一代一双人”。然后便声称自己视纳兰为知己,视纳兰为偶像,或是爱慕的对象。不可否认,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只是较之他们,我的时间长了一些,十年,大概还要再多些。可是却始终不能将其参透,长久地浮于表面,用虚华的背诵或是堆砌的辞藻来歌颂一段自我意识维系而成的完美。再后来的某一天,看着市面上泛滥的各种“纳兰词评”或小说,总也读不出自己想要的那个公子来。于是想,这大抵又是一百个“哈姆雷特”的道理吧。可是,“哈姆雷特”是谁,莎翁说了算。纳兰是谁,须得问问历史!
他专情么?那么为何会续弦,为何会在卢氏之后爱上沈宛?若是爱,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任何逃避推脱的理由,其实只是借口。他的确有才华,但他是懦弱的,屈从于皇权父命的重压牺牲在封建礼教的枷锁里,这样的他,若生于现世,你会爱上他欣赏他么?多半会被看作书呆子,怪物,甚至傻瓜。
不要盲目地说爱,你或许能够接受他所有的缺憾,但你依旧不能成为他的卢氏,他的沈宛,他的顾贞观。
所以,我请对纳兰感兴趣的人看陈先生的这本纳兰词评《当花侧帽说纳兰》。或许包装没有那么精美,辞藻没有那么华丽,名气没有那么显赫,但他是真实的。
你若真的钟情于纳兰容若,此书理应成为首选。
你备了那么多纳兰的词作,对他怀有的幻想从不比任何一个成书的作者少,但总该从旁人的叙述中找到真正的、以史为证的公子。便当是对自己负责!
与陈先生聊天谈及此,他只回了我说,你这是成熟了。
我想,或许吧。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这话,不仅顾贞观要感叹,怕是所有对纳兰给予了关注的人都会叹一声吧。可是我们不能回到百年前的渌水亭中,哪怕只是闻他低吟一首,抑或只是见他明眸含笑。大抵也只能是一段憾事。
也曾想前世与他并肩,不问繁花,不亲水泽,只把盏清风,策马河山,总也算成就一次梦寐以求的相遇。猜想,这想法也不仅为我一人曾有。
可有时又会庆幸自己并未经历过他短暂而绚烂的人生,如是便可不必在离别之际濡湿衣襟。这样想来会不会又有人跟我一样觉得卢氏更为幸运。
盖是一番小矫情,无用而空泛。
不过我总觉得,十年的坚持,即便是因为空虚,因为臆想而爱上,能够至今已属不易。
我不敢说自己如陈先生一般读他至深,我只知他的存在成就了我生命中不大也不小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并不致命,但失去却是一种灵魂的缺失。
我看纳兰,如梦中仙境,如临水洛神,如月华白练,知其缥缈,知其恍惚,知其所不可得,亦知自己身在何方,欲往何处。
如陈先生所说,该成熟了。
世情万千,不过了了。
写了数日终于完笔,再次感谢陈先生贻赠,不胜荣幸。
壬辰年正月初二
于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