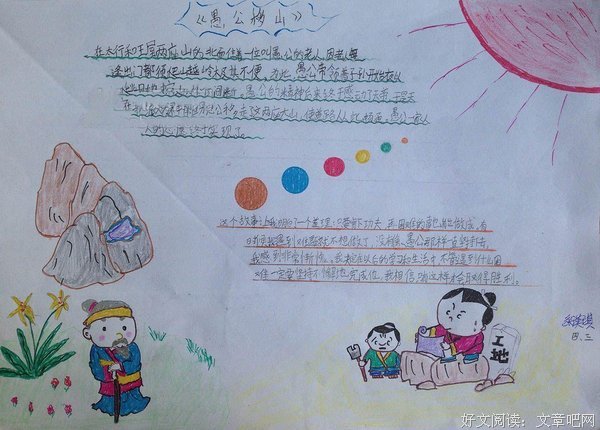礼是郑学读后感10篇
《礼是郑学》是一本由华喆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礼是郑学》读后感(一):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新见迭出,颠扑旧说。
十六字总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新见迭出,颠扑旧说。“入乎其内”表现在对文本一字一句的分析和简单平实的解说经义上,让读者真正理解经学关心的问题。“出乎其外”表现在研究方法本质来说是历史学和文献学的,不仅仅推文寻意,也注重历史环境分析和文献比勘。
如果以前读过皮锡瑞和周予同等人的经学史,阅读此书就是“不断被刷新认识”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些细节问题,郑玄与师友思想的差异、郑王之争、南北学之分、今古文之争和汉宋之争这些经学史的常识作者的解读都“新见迭出,颠扑旧说”。
但是,本书的核心论点如郑玄的纯理论倾向、王肃之后的实践性改革以及义疏学的衰亡,其实都来自乔秀岩的研究。同时作者经常对郑玄、皇侃和孔颖达等人进行思维复原和逆推,读来总觉得作者有时求之过深,尤其是先立下了郑玄体系严密的立场,凡有歧解必先辩护,虽然有时能找到足够的辩护理由,但这种态度与郑玄先立下了经书是不会错的,再四处找理由、时有牵强附会有什么不同呢?
《礼是郑学》读后感(二):《礼是郑学》提要
一是通过对佚存的郑注文本和学说分析,复原出郑玄的先建立以《周礼》为核心的三礼学——再以礼学为核心解释诸经并弥合经文异说——最终形成贯通群经诸纬的庞大经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框架;
二是通过对由汉至唐的经典诠释史的剪裁和梳理,勾画出一条郑学创立阶段——郑学的接受与回应阶段(魏晋郑王之争)——郑学的经典化和新诠释阶段(南北朝义疏学)的时间线索。
在以经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时代,经文本不容二解,但事实是诸经的矛盾和歧解甚多。在此背景下,郑玄的学术目标是“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郑玄以礼学作为标尺,对诸经牴牾之处进行裁量,结果是使诸经形成了庞大而严密的理论体系。我们需要在历史语境下理解郑玄注经的出发点,理解他的学术态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郑学并对其作出评判。
郑玄整理群经,其意并不在于调和或融贯今古,因此以今古学之集大成者看待郑玄失之片面。
魏晋复古重礼,郑玄纯理论的礼学由于不切实用遭到以王肃为代表的学者的挑战,但这不意味着郑王有是非或高下之分,而只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和不同的学术态度下造成的不同理解而已。
南北朝义疏学权舆,注重理论分析的学术风气回归,郑玄注从经文的诠释转变成被诠释的经典,而皇侃对郑玄注的诠释实则颇得郑玄学术风格之遗意。
宋儒以理学立异,视郑学为考订训诂、名物、制度之学,清人标榜汉学,尊崇郑玄,但对郑学的认识却仍未脱出宋儒的窠臼。
剥落这些成见,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真实的郑玄,而这也是此书对我最大的启发。
页161引《礼记正义》认为是《谷梁》家说(文详后),
《五经异义》中亦有此文,如下:
就是这条华喆引案:尹更始、刘向此说可能是存《左氏》说,《五经异义》其文如下:
全文案句读当以华喆为优。
前文《左氏》说明言“麟为孔子瑞”,尹更始、刘向等也认为是周亡之异?“以应孔子至。”
华喆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注释中说:“按《左传正义》卷五九亦引此文作:‘今麟为周异,不得复为汉瑞,知麟应孔子而至。’”
华喆或因为尹更始、刘向的身份,又据“石渠”字样,认为此条是《谷梁》家说(《汉书·儒林传》记“ 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郞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郞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看起来其是《谷梁》说应该不成问题。
但《春秋序》疏中明言尹更始受《左氏》于张禹,刘向亦习《左氏》,其于此用《左氏》反《公羊》也就不奇怪了。因此《驳五经异义疏证》中将其归入《左传》类。许慎大概将其附在后面也是这样的意思。
少龙案:在判断汉代经说中家师传承与具体人物经说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有清一代学者,在判断经说派别时,往往据其所学就断定其行文必用其所学,代表作就是《诗三家义集疏》,但这种判断已经被证明图样,虞万里在《 從熹平殘石和竹簡《緇衣》看清人四家《詩》研究 》一文中已经证明了这种“科学”方法的不可行,因此在操作中尤其要小心。
石渠阁会议上,刘向、尹更始等完全有可能暗戳戳借用《左氏》理论来打击《公羊》家,并且把这种学说伪装成《谷梁》家之说(这也是我脑补的,毕竟政治斗争要见血,我就想当然一下),甚至是直接运用《左氏》说攻击《公羊》说。因此《驳五经异义疏证》才直接说这就是《左传》类的。
以上我就是随便乱说一下,不要见得风是得雨,接到一个消息,本身要有自己的判断,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你把他说一遍,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礼是郑学》读后感(四):《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总结
quot;礼是郑学"这四个字出自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中的“禮是鄭學今申鄭義",原意是指《礼记正义》采用郑玄的《礼记注》,郑玄礼学有其完整的体系,故以阐释郑义为主。而在作者看来,郑玄是汉代经学发展的终点,又是魏晋隋唐经学演变的起点,在汉唐经典诠释中扮演主轴的角色,经典诠释围绕着实用性(王朝制度层面上的实践)和体系性(经学文本理论的完整)发生变化。郑玄伟大之处在于,建立起以《周礼》为核心的经学体系。郑玄作为纯粹的学者,没有官僚的身份,不追求经学的实用性价值,而是专注于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囊括各种异说。因此作者重点思考的是郑玄经学体系的内在逻辑,而不是简单判断郑玄注经的正误。
通过考察郑玄经注,我们可以发现郑玄经学体系的构造大致为“《周礼》一《仪礼》一《礼记》一诸经一诸纬”,即以《周礼》为中心,围绕三《礼》确定其他经书的内容所以郑玄三《礼》注成书在先,此后经注也多围绕三《礼》注展开,这种特点被学者概括为“以礼注经”。在第一章《郑玄礼学解析》作者通过对敦煌出土唐写本郑玄《论语注》进行考察,认为郑玄在为《论语》作注的时候参用《周礼》和《仪礼》,用三礼注论语,以至于有时会偏离《论语》文本本身的含义。郑玄注经带有强烈的理论研究色彩,并不考虑礼学是否能在实际生活中实践,完全沉浸于文本的世界里。所以用实践角度看待的话,郑玄的理论有时候会显得迂腐可笑。经学家都认为自己的解释最接近圣人的原意,别人的诠释都是错误的。如今已经不是经学的时代,我们自然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结谁对谁错,因为立场、视角不同。更可况,古代的经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书面的学问而存在,经学尤其是礼学更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文本理论构建越完美,那么在生活实践中可能越难以实现。但是如果一味地只从实践角度出发不顾文本内在逻辑也是不可取的。郑玄并非全盘继承两汉以来的解经传统,很多时候恰恰是在挑战传统。
第二章《郑玄和他的师友》,作者对马、郑关系旧说进行了检讨,郑玄所针对的不仅仅老师马融、同门卢植,更有贾逵、郑众等诸多前辈。与卢植、蔡邕等高官相比,身为布衣的郑玄一心沉浸在学术的世界里,并不喜欢为本朝不合经典的制度寻找礼学上的依据。接着作者借两汉《春秋》三传对“西狩获麟"的不同阐释,认为郑玄经学的纯理论倾向是郑玄倾动海内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最初董仲舒认为“西狩获麟"是孔子获得天命的象征,但是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王朝越来越需要塑造正统性和合法性,"汉家尧后"的理论应运而生,再也不提汉高祖以布衣身份手提七尺剑取天下了。于是在公羊家的附会下,“西狩获麟"不再是孔子获得天命的象征,而是汉德将兴的征兆。东汉的贾逵为了给《左传》争取官学的地位,更是主动迎合明帝、章帝,坚持认为《左传》有“汉家尧后”的理论证据。而郑玄在这个关乎本朝德运的重要问题上,却坚持认为麒麟是为孔子而来,与汉家无关。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随着汉朝统治的式微,朝代更迭,公羊家们把自己的学说和汉王朝的统治绑得太紧,以至于魏晋以后,不断走向衰落。而那些与时 政保持一定距离的,学说反而一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郑玄回避了与“汉制”有关的现实政治问题,使得其学说以一种纯粹的学术出现在礼崩乐坏的汉末,当汉魏禅让完成后,人们再也不会去关注汉制问题,郑学脱颖而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三章《魏晋学者中的反郑玄倾向》,魏晋反郑学确实是一个较为瞩目的问题,但是不同于传统学者认为王肃凭借外戚地位凌压挑战郑学的观点,作者认为反郑不过是对郑玄学说的回应和补充,再没有学者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经学体系,魏晋学者对郑玄学说也只能做些修补工作。相对不修古礼的汉王朝而言,中古时期则是兴礼制乐的时代。随着魏明帝景初制礼活动的展开,士人发现郑玄的礼学理论和实践存在矛盾,王肃反郑就是在王朝兴礼制乐背景下对郑玄理论的修补。中古时代王朝礼制改革的趋势是郑王杂糅,而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把郑王之争过度延伸到曹马之争上去则偏离了主题。西晋在复古改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国家礼制构建活动更是如火如荼。礼在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但是为了实现礼俗的平衡,也出现了很多学者和官员歪曲臆解经文的问题。西晋对孝特别重视,同时对士人不守礼制的惩罚之严厉堪称古今之最。 西晋对士人服丧期间的活动行为要求异常严格,嫁娶加冠等活动都会受到限制。面对礼制的严苛要求,官员不得不脱离经文之间的联系肆意孤立曲解经文。礼学和现实生活的矛盾是官学和学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魏晋学者反郑,也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南朝礼制问题不再突出,郑玄著作变成了被诠释和研究的对象。义疏学的兴起使得学者又开始注重分析经学文本,于是变成"礼是郑学"。
在最后一章《经学的棱镜 郑玄与经学史》中指出对待经学,我们要学会转换视角,不能再囿于清人建立的“汉学”、“宋学"框架内去认识郑学。中晚唐,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士人不再关注经学文本本身,而是去寻求经学中的"圣人之意",由此形成了新的学术风气,成为宋代理学的滥觞。宋儒探究的是圣人之理,关注的是前人未曾关注的领域。郑学也被宋儒分割成不同的内容。汉唐学者阐释经义一般都会立足为本,而宋儒可以直接抛开文本空谈义理。北宋以后的学者将经典诠释分为义理、历史制度和文本三个层次,郑玄的学术则被宋人归入到历史和文本层次,宋儒只是认为郑玄擅长考据,能帮助他们理解周代的历史制度,但是却不懂义理,读不懂经书。而所谓的清代学者,其实也一直站在宋儒的视角评价郑玄的经学成就。清代学者擅长考据、训诂,他们认为越古老的学术著作,训诂考据越正确,越能帮他们理解三代制度,所以他们反宋捧汉。经学不是历史,也存在多种解释,经学家不允许存在多解,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判断别人。而如今我们需要做的是理解他们的立场和逻辑,不是同古人一样单纯地判断谁是谁非。
《礼是郑学》读后感(五):回到棱镜之前
回到棱镜之前
——华喆《礼是郑学》读书札记
郑玄的虚影
我最初知道《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三联书店,2018年)的书讯,是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一则推送,内容是乔秀岩先生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乔文开头拿福柯的研究和经学研究作对比,令人耳目一新,接着他又说经学研究可以借助经文作为跳板,进入古人思维的过程,同样引人注目。经学在古代虽然居于学术的核心位置,但是随着中国近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出,西方思想的日益传入和渗透,今人对于经学已经充满了隔膜,常人读懂弄通经文已不简单,进入古人的思维过程,真是谈何容易!但当我读完《礼是郑学》全书,我对于乔秀岩在序言末对此书的盛赞深表赞同,整个阅读过程就好像一场“思维的历险”,在不同经学家的思想雨林中不停的穿越探索,作者在达成“进入古人思维”这个目标上确实已然“尽力”了。
《礼是郑学》的标题来自于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中的一句话,意思原本是虽然经文可以存在诸多理解,但郑玄注自有完整的体系,故孔疏仍以阐释郑说为主。作者声称借用此句话为标题,是想表达两重意思:一是本书的研究主题是郑玄及其学说,研究时段是以郑玄及其学说为主轴的汉唐时期;二是本书的研究方法是理解阐释郑玄的学术体系,还原其产生过程,而非简单的对错评判。
“郑玄”对于今人,可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这位经学大师曾遍注群经、尤精三《礼》,他的学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了经学的主流。自隋唐至宋明,纵使郑学逐渐不再是经学舞台的主角,但对于经学发展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清代随着乾嘉学术的兴起,郑玄作为“汉学”的代表人物再次成为了经学研究的重心。可以说,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来形容郑玄在经学界的地位,并不为过。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任何一部经学史著作中都必定提到郑玄,但对于郑玄形象和地位的认识却极其复杂和多样,甚至互相矛盾。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把郑玄视为汉学极致,而廖平却极力抨击郑玄毁坏汉学;晚清的经学史著作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把郑玄视为汉学的终结者,之后周予同等人认为郑玄是“通学”的开创者,再到后来《中国经学思想史》又提出郑玄只是东汉古文经学的继承者;有人说郑玄是一位“为经学而经学”的学者,也有人说郑玄学术和政治关系密切;真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郑玄”。
《礼是郑学》相较于前人另辟蹊径之处,正在于它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郑玄学说的结果,而是它的形成过程和内在体系。如果说郑玄是从汉代射来的一道光线,那么这道光线在穿越后世学者理解和叙述的棱镜过程中,已经被投散到了不同的光谱上,人们日常看到的都是郑玄的一道投射虚影,而《礼是郑学》所作的工作就是追寻穿越棱镜背后的思想之光最初的样子。
汉唐间经典诠释的变迁
《礼是郑学》全书包括绪论和终章一共分为六个章节,基本上都是每章分三节,每节又分成三小部分,从作者极其推崇郑玄学术的体系性来看,这种整齐分明的篇章安排恐怕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绪论部分主要是交代问题缘起、研究综述和全文安排;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全书的精华所在,第一章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郑玄《论语注》为突破口,纵向深入的剖析了郑玄学术体系的特点,第二章利用现存的辑佚材料,横向对比了郑玄和师友马融、卢植和蔡邕的学术差异,两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出色的郑学成立史研究;第三章重新讨论了“郑王之争”这桩经学界的公案以及魏晋时期郑学的变化;第四章接踵乔秀岩的研究,从具体经说分析皇侃、孔颖达对郑玄体系的不同诠释,描绘南北朝义疏学的特点及其衰落过程;终章则对唐宋以后郑玄的地位起伏和经学家们对郑玄的不同认识做了简单的勾画和分析。综合来看,作者尽心搭建了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的框架,同时又颇具野心的突破断代限制,试图写就一部郑玄研究的专题通史。
绪论部分主要是交代问题缘起、研究综述和全文安排,这是目前的学术规范,本来没有多少可供作者发挥的余地,但是在“源起”一节中作者却从京戏《连升店》中说起,提到隋唐时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组成孔门七十二贤的笑话竟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皇侃的经说,以此侧证隋唐时期经典诠释发生了变革,这不禁既让人想到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提到“层累说”亦来自于他喜欢听戏,又让人联系到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中提出的隋代学术革命。
第一章主要通过唐写本郑注《论语》来剖析郑玄的学术体系特色。总体而言,作者认为郑玄的学术体系特色有两大方面:一是以《周礼》为中心,兼采《仪礼》、《礼记》,以礼学来支配其他诸经的解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学体系;二是郑玄经注带有强烈的礼学理论研究色彩,在诠释过程中为了理论的完美经常牺牲礼的实用性。应该说这两个理论都并非是作者首创,杨天宇等长期研究郑玄三《礼》注的学者早已发现郑玄“以一持万”,《周礼》等礼学作品在郑玄经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现存的郑玄作品中又以三《礼》注数量最大,也很容易由材料导出这个结论;上个世纪中期加贺荣治在考察魏晋经学时便提出了“文献主义和合理主义”的二元划分,之后乔秀岩在讨论郑王异同时更加明确的将郑玄定位为一个关注“观念理论体系”的经学理论家。
但作者的创新点在于从具体经说入手,来还原郑玄的思考过程及他与其他经学家方法的差异,郑玄《论语注》和《论语集解》所引包氏对于“南牖”、“北墉”有完全不同理解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论语·乡党》中有一段称“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这是记载孔子在家中卧病养疾时,国君前来探视的情况,郑玄注认为“疾时寝室中北墉下也”,也就是说生病时孔子应该是躺在室内的北墉之下,头朝向东,但包氏却说“夫子疾,处南牖之下,东首”,包氏认为孔子应该躺在室中南墙窗户下面再头朝向东,两人的说法可以说“南辕北辙”。包氏的理由是皇帝亲自过来探视,虽然《礼记》中明确说了病人应该居于北墉之下,但为了使人君获得面南背北的尊位,故应该将病人暂时移动到南牖下。包氏的说法还有《论语·雍也》和《汉书·龚胜传》的支持,因为孔子和王莽的使者看望病人时,病人都是在南牖之下。但郑玄也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病人应该居于北墉之下《礼记》有明文,且根据《仪礼》,“室”是士人最私密的空间,君主是不应该入室内完成礼仪活动的,因此君主只需要站在室外,通过南边的窗户和室内北墉之下的病人对望就算完成探视了,在郑玄心中,君主只是一个永远符合礼制的符号,并不需要考虑万一君主突发奇想欲入室探望又当怎么办的情况。通过对这处经文歧解的分析,两种思考的路径一下子判然纸上,包氏设想的画面是具体礼仪实践的情境,而郑玄则总在考虑如何打通《仪礼》、《礼记》和《论语》的经说。
第二章接续第一章,作者认为正因为郑玄的路径与包氏等人有很大的区别,所以郑玄的很多经注实际上与汉代传统经说是针锋相对的,因此作者特别选取了郑玄的师友马融、卢植和蔡邕三个例子作为对比来说明这一点。马融虽然是郑玄的老师,但通过对比马融经说和贾逵《左传》注、《白虎通》等文献,可以发现马融的经学主要沿袭东汉旧有的经说,他解决经文内部矛盾的方法是简单的混同矛盾之处;卢植是郑玄的同学,他创作的《礼记解诂》主要是训解经文,方便读者理解,无意建立经学体系;蔡邕作为郑玄的同辈,却志在政治和撰史,他的《月令问答》非常留意古制和汉制,明显着眼于实用。郑玄则与他们都不一样,郑玄为了解决经文中互相矛盾的地方,有时将矛盾之处区别为不同时代的记载,有时又将矛盾之处区别为不同的制度,可谓用尽了手段,同时又试图使这种解释体系能够适用于全部经文。作者对于四者的比较构成了对之前郑玄历史定位的一个有力回应,郑玄是一种相对于汉学来说全新学术的开创者,但也并不等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或者二者的简单相加。
第二章第三小节同样是作者相对于前人研究的一大创新点,作者用了两汉春秋学常涉及到的一个问题“西狩获麟”作为例证,将“纯理论化的郑学为何能取代两汉经学”这个问题放在了一个汉魏嬗代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两汉的经学和政治密切相关,西汉的今文经学者将“西狩获麟”解释为孔子预知刘邦将要建汉、汉将受命的依据,东汉的古文经学者通过嫁接五德终始说使“西狩获麟”得以附会“《春秋》为汉制法”。郑玄对于这两种学说都不取,坚持从《礼记》和《论语》等经文内部找联系,认为“西狩获麟”与汉朝受命没有直接关系。结果,随着汉魏嬗代、东汉灭亡,今古文经学对“西狩获麟”的诠释同时失去了市场,而郑玄的纯理论探讨反而成为了后世学者研究此问题的出发点。
第三章核心焦点是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学者的反郑玄倾向。经学界讨论“郑王之争”可谓源远流长,议论纷纭,以往研究多从西晋的政治需要和王肃个人的学术观点两个角度来切入此问题。乔秀岩《论郑王礼说异同》可谓独树一帜,抽绎出礼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两个特点来分别定性郑玄和王肃。作者接踵其后,在两晋礼仪和经典诠释中找出了不少具体的例子来反映王肃之后郑学的变化和遭遇的挑战。杜预为了晋武帝的政治需要创造了“心丧”的新解;高崧、江彪为了儿子要服内结婚的现实问题调整了对丧服的解释;于氏为了求得养子不惜歪曲“为人后”的理解;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为了实用目的割裂郑玄创造的经学体系性。但是也正是为了反对郑玄,迫使魏晋时期的经学家开始深入的思考郑玄的经学体系。
第四章是以《礼记子本疏议》为中心再探南北朝义疏学的特色以及唐初义疏学衰亡的原因。但是这一部分也是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主要研究的范围,不过,当年乔秀岩创作博士论文时毕竟只能利用《子本疏义》的珂罗版复制本和林秀一书中模糊不清的图版,乔氏只是大概确认了孔颖达《礼记正义》大半袭取皇侃的《礼记子本疏义》,同时又删去皇侃科段、义例等附会之说,而作者则利用如今网络上已经公开的高清PDF图片,更加细化的研究孔颖达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在删改皇侃的作品,并总结称皇侃是在用郑玄的方法继续完善郑玄的体系,而孔颖达则更加尊重静态的文本,将超出文本外的推演全部排斥,并不追求经学体系的完整。
终章主标题为“经学的棱镜”,主旨在于探究唐宋以后的郑玄究竟处于什么的地位,这一章写的非常高屋建瓴、行云流水。作者认为随着义疏学的衰亡,中晚唐时期经典诠释方法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啖助、赵匡以至北宋理学兴起,“义理”在经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宋明理学对于汉唐经学发展的回望犹如一道棱镜,将一整束光线区分成了义理、制度(历史)和文本三个层面,而郑玄被归入了制度(历史)和文本的层面。清代乾嘉学术复兴,其实仍然延续宋学将经学三分的学术话语,只不过侧重点从义理转移到了历史和文本方面,只不过“把宋儒的功夫颠倒来练了而已”。在全书最末,作者提出“礼是郑学”的当代意义正在于回到棱镜之前,重视经学家和经学文献的内在逻辑体系,还原他们的思想原貌,“我们不再认为经书存在定解,而更愿意去倾听每一位经学家的声音,与他们的思想达成交流。”
如此一来,终章既是对前四章内容的延续和总结,又与绪论绪论中提到的“进入古人的思维”形成首尾呼应,使全书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闭环结构。
重新审视近现代的经学史研究
总结来说,本书的优点非常鲜明,堪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其内”表现在对文本一字一句的分析和简单平实的解说经义上,让读者真正理解经学关心的问题。“出乎其外”表现在研究方法本质来说是历史学和文献学的,不仅仅推文寻意,也注重历史环境分析和文献比勘。同时,作者对于最新经学研究成果的吸收非常丰富,如果以前读过皮锡瑞和周予同等人的经学史,阅读此书就是“不断被刷新认识”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些细节问题,还包括郑玄与师友思想的差异、郑王之争、南北学之分、今古文之争和汉宋之争等经学史的常识。
不过,这本书也并非没有问题。首先,作者在对比郑玄与马融、卢植和蔡邕等人时,非常强调他们的差异性,以此突出郑玄学术的革新,但是,现存马融、卢植和蔡邕的经注数量完全无法与郑玄相提并论,仅仅只是看到了辑佚材料中他们的差异,就说他们完全不一样,是否有“盲人摸象”之嫌呢?作者曾经批评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仅有皇侃、二刘、孔颖达、贾公彦等有限的几人或几部著作恐不足以代表南北朝义疏学发展,这个批评似乎也同样适用于此。
其次,作者全盘接受了乔秀岩对郑玄纯理论化倾向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很多结论的出发点,但是郑玄的这个形象是否也是一道棱镜后的虚影,学界的争议非常多。陈苏镇先生《<春秋>与“汉道”》就曾认为如果将郑玄置入东汉末年的政治和政治文化演进的背景,他的学说绝非是“纯学术”,同样具有政治意义,从郑玄的学说中也确实可以看到蕴含他对国家治术思考的内容。
再次,作者经常对郑玄、皇侃和孔颖达等人进行思维复原和逆推,读来总觉得作者有时求之过深。作者对郑玄脑海中画面的推理和想象,让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郑玄的想法还是作者自己的想法。即以郑玄与包氏的“南牖”“北墉”歧解为例,刘宝楠就曾站在郑玄的一方提出郑玄“北墉”说其实也有现实因素的考虑,郑玄就留下了这十几个字,刘氏的不同理解充分说明如果立场出发点不同,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最后,通览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有一个很明确的先行立场,那就是郑玄的经学体系是非常严密的,他的每一条经注肯定经过思考的,因此作者凡遇到郑玄与他人的歧解必会为郑玄辩护,虽然有时能找到足够的辩护理由,但这种态度与郑玄先立下了经书是不会错的立场,再四处找理由、时有牵强附会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以上的批评肯定带有旁观者的吹毛求疵,我们应该认识到,《礼是郑学》和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关于郑玄及其学说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方法。近代以来,研究经学史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历史学的方法,另一种是哲学的方法。以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经学,主要使用史传中关于经学的材料来搭建经学发展的骨架,拉出一个不同时期变化的大致线索,以版本考订和文献辨伪来确认经学作品产生时间和影响时段,同时非常重视同时代经学的整体特点以及后人的评价;以哲学史的方法研究经学,主要使用经学家的论述和著作来演绎经学体系,比较关注单个经学家的思想特点和超越性所在,在寻求时代之间的历史联系时重视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
但这两种方法研究经学史都有自己的弊端,往往最终得出的不是思想史,就是哲学史,归根结底二者都不是经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经学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有着自身的学术方法和研究范式;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体系受到西方影响极大,史学和哲学在吸收了西方的理论方法后相继独立成为现代学科,但由于西方的学科体系中没有经学,导致如今经学反成了史学和哲学的附庸。乔秀岩在《义疏学衰亡史论》中很明确的表示“前人治经学史,讨论注疏,其实皆不过经学学说史,未尝探索义疏家立说之意趣。”而华喆在某次论坛发言中也谈到在绝大部分经学史作品中“我们并不能有效地获知:某个时期的学者们在讨论什么问题?他们对经学问题的讨论有什么特点?体现了学者们怎样的方法?”
现代的经学史研究确实迫切需要找到第三条路——经学研究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吸收历史学和哲学中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必须要结合经学文献自身的特点和经学研究的特有理路。乔秀岩、华喆两位学者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值得更多的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