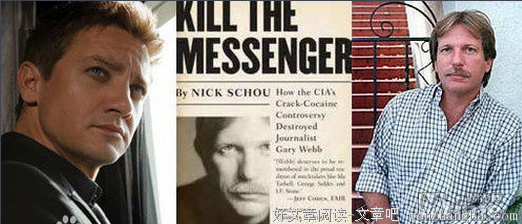《邮差》影评精选10篇
《邮差》是一部由迈克尔·莱德福 / 马西莫·特洛伊西执导,菲利普·努瓦雷 / 马西莫·特洛伊西 / 玛丽亚·格拉齐亚·库奇诺塔主演的一部传记 / 喜剧 / 剧情 / 爱情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邮差》影评(一):相識 也許不過擦過夢中
印象中的三个关键词,关于智利,狭长的天涯之角,高山荒漠,以及聂鲁达,伟大的诗人。《邮差》,在看完Antonio Skármeta的小说后翻出电影。他说,这是献给给予聂鲁达创作灵感的马蒂尔德•乌鲁蒂亚,也表达那些受益于聂鲁达是个的“卑微的抄袭者”对她的敬意。
电影中浪漫的意大利,蓝色的亚平宁的海水,半露忧伤半显欢愉的悠扬曲调,一切都在给这部电影添上诗的注脚。
不务正业,整日做着大胆的爱情美梦的马里奥,机缘巧合成为流放到岛上的诗人的邮差。像大多数人一样,他迅速为聂鲁达的诗情诗才所倾倒,并主动与他熟络起来。
而后酒馆遇见美丽的女郎,比阿特丽斯,她有着微卷的长发,丰满的胸部,热情奔放又带着可爱的狡黠。马里奥迅速坠入情网,他求助于诗人,并非为苦恋之解药。他想写诗,用各种暗喻,浓烈的,含蓄的,撩人的,忧愁的……诗人欣然相助。他坐在沙滩上与马里奥谈暗喻,与气冲冲护女心切的罗莎夫人见面,到小酒馆在佳人面前,亲自在扉页写下致辞——作为马里奥的第一本“诗集”。
朝涨夕落的海水,丝绸般泻下的月光,耳边来去自由地风,和那灵动的不可磨灭的诗句一起,见证了诗人与一位普通人的友情。
不可否认在这段友谊中,马里奥始终是主动的那方,这是由二人的身份地位决定的。诗人回国后,为铭记这段淡如水又醇如酒的深情,腼腆的马里奥将岛上的声音记录在磁带中,最后由妻子在他遭遇不测后转给聂鲁达。“第一,海湾的浪带,小小的波浪;第二,滚滚的波涛;第三,绝壁上的风;第四,灌木林间的风;第五,我爸爸忧愁的渔网;第六,教堂的钟声,还有神父;第七,岛上布满星星的夜空;第八,我第一个孩子的心跳。”一切都还美丽如斯。
书中提到Massimo Troisi“一看完剧本,就认为这将是他今生最成功的角色”,导演几次提醒他“一部电影不值得搭上一条性命”,他却说:“这部电影就是我的生命。”执意用所有的心力演绎邮差这一角色,到最后,旁人已分不清哪个是现实中的他,哪个又是剧本中的他。电影停机后十二个小时,他便告别电影,告别人世。仔细看电影中的他,苍白而瘦弱,然而眼神矍铄,嘴唇总是倔强地抿着,一句句诗意地念白,谁知他那时正在承受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阳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没有人不喜欢诗歌,或者说,没有人会真正讨厌诗歌。聂鲁达无疑是伟大的,难以超越的。他说:“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女人们为他的情诗痴狂着迷,劳苦大众从他的诗里寻找光明与希冀。不论前期以爱情、孤独、死亡为主题的浪漫主义诗作,还是苦闷时期的晦涩难懂以及后来达到鼎盛时期的铿锵有力,这些,都是聂鲁达心灵的歌。他用生命歌唱,绚丽多彩的意象,精巧动人的韵律,”复苏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亲爱的聂鲁达,无论是风光旖旎的黑岛,还是终年酷寒的合恩角,我都愿追随你,崇敬你。 “爱情如此短暂,而遗忘太长,”你说,那我愿“在这里爱你”,“今夜为你写下最哀伤的诗句。”
《邮差》影评(二):(memo)media、诗、言语、表达
索绪尔的理论认为意指和能指之间具有任意性,我们选择一个词指代某物都是偶然的。对于邮差来说,意指和能指是割裂的,他对聂鲁达说:“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感受,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长期的孤立,不能找到两者间褡裢的桥梁,即media。media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电影中的具体形象可以指代它。邮差=media
暗喻(言语)=media
聂鲁达=马里奥的media
小岛=孤立
渔夫=漂泊在广袤无垠的意义表面,打捞
没有淡水=强化没有media交流的孤独意象
父亲寡言=封闭的个体
婚礼=外界相融的界点,封闭的个体裂开小口,父亲第一次多言
当聂鲁达离开小岛,马里奥丢失了邮差的工作,失去了聂鲁达,却最终获得了语言的能力,建立起与外界的联系。他说:我以为你带走了所有的美好,可是最后发现你留给我很多东西-》诗
诗=media
聂鲁达在面对马里奥请求他解释他诗中词语解释时,说道“我不能用我的诗以外的来解释我的诗”。诗不能解读,只是以心传心,我只能解释我的心和你的心,而这中间的媒介有什么好解释的?如果你没有理解,就证明这个媒介无法抵达你。
邮差与言语在意义重合。可以把《邮差》看成献给语言的诗。(语言指人类的表达,言语指符号。)
这让人想到人类最早的情感表达形式就是诗歌。
《邮差》影评(三):第三只耳朵(《邮差》,Il Postino,1994)
1、
我所认为的幸福,就是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周末,拥着心爱的女人睡午觉。看《邮差》时,我忽然又酝酿起这个自中学以来便有的念头。
《邮差》是迈克尔·莱德福导演的一部意大利电影,它还有个我不太喜欢的名字叫《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讲述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意大利南部一个小岛上发生的邮差与诗人的故事。迈克尔·莱德福还导演过其他片子,其中包括改编自乔治·奥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
男主人公叫马里奥,是一名邮差,一天早上,他接到了一份工作——每天为流亡至此深受大家崇拜的诗人聂鲁达送信。他买来了一本诗人的集子,对着镜子一遍遍地练习:你能帮我签个名吗?我理解这种感受,大二那年,我曾负责全系的邮件收发,为了给一个心仪的女孩送一件别人写给她的信,我装束一新,等了半个小时,只见她穿着一件睡衣下楼,头发蓬蓬乱,这和马里奥见聂鲁达的情形类似。作为答谢,女孩递给我两只碧绿的青梅蜜饯,就像后来聂鲁达送给马里奥的些许小费一般。
2、
把女主人公取名“比阿特丽斯”很有意思,聂鲁达听到马里奥说出这个名字时愣了一下,脱口而出:但丁!传说诗人但丁毕生的挚爱也叫比阿特丽斯,然而后来比阿特丽斯嫁给了一个银行家,但丁娶了别人。
所以这注定是一部和诗有关的电影。它再次证明,一个热恋中的男人可以成为诗人。马里奥因为爱上比阿特丽斯而闯入聂鲁达的房间求救,他说:我坠入了爱河。诗人说:放心,这有解药。他说:不,不要解药,我要一直病下去!然后他求诗人帮自己写一首情诗,聂鲁达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他竟然第一次展现了聂鲁达颇为赞赏的自由意志,表达了自己的反抗:若这样的一首诗也能难倒你的话,你休想赢得那个诺贝尔奖。
在此之前,请聂鲁达签名时,马里奥并没有用到他反复练习的台词,而是问:您能令它与众不同吗?
3、
小岛是一个连自来水管都没有的偏远渔村,送水的补给船要一个月才来一次。一条不宽的阶梯连接着码头与村落,房子高高低低,颜色比陡峭的山壁浅,远处是通透的天空。渔民们忙于出海,海滩上人迹罕至,适合用第三只耳朵倾听,在这里,聂鲁达为马里奥朗诵了《致大海》。
比阿特丽斯的婶婶和教堂里的神父尽管竭尽全力阻止马里奥和比阿特丽斯在一起,但在他们的婚礼上,婶婶和神父依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正是我向往的适合午睡的好地方:人们斤斤计较,但很快就会忘记恩仇。
当后来马里奥在聂鲁达送给他的笔记本上,写下“赤裸的你如岛上的夜,群星躲在你的发间”时,马里奥已和诗人无异。最终,他完成了一部无与伦比的著作送给聂鲁达,目录是:海湾的波浪,灌木丛中的风,教堂的钟声,帕布力的胎音……
片中不容忽视的还有意大利作曲家路易斯·巴卡罗夫的配乐,吉他、小提琴等诸般乐器完全和风声海浪声等自然声响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交响合奏。马西莫·特罗西是饰演邮差马里奥的不二人选,他黝黑的表情羞涩真诚,他坐下时双脚内扣,大部分时间低着头。让人痛惜的是马西莫·特罗西在完成本片12个小时后,即因心脏病猝然离世。这部电影对于马里奥和马西莫来说,都是绝唱!
《邮差》影评(四):观影Il Postino
电影看多了,渐渐也产生了自己的分类标准。有一种分类方法便是: 绝世佳作看完之后留有余味,你会情不自禁去点评一番,与友人分享,下载BGM,甚至看好几遍还不断从忽略的细节中悟出新的道理或找到泪点。就好像第二次看Nuovo Cinema Paradiso的时候,开场,Toto的情人淡漠地说了一句:"有人死了——Alfredo",便倒头就睡。台灯熄灭,一阵响雷,透过Toto怔怔的眼神里,你就好似能够体会他的内心。这是第一次看时,显然会被忽略的情绪。还有一种电影,主要可能是看个热闹看个炫酷制作,电影的价值在放映完就燃烧殆尽,时间长了根本记不起来。因为太喜欢意大利电影了,有幸去了意大利将其兜底翻了个遍。归国后,好似大梦睡了20年的Rip Van Whickle下山一般,看魔都的高楼丛林和密密麻麻的人群觉得非常的绝望。“葛优瘫”,want a little more Italia,打开Il Postino,随着悠扬婉转的笛子声,便又回到了静谧的地中海上,晃晃悠悠。电影的节奏很慢,慢到你会质疑这究竟有没有神结尾值得如此期待,这一点也恰似对于人生的某种隐喻——你不知道等着你的会是什么,有还是没有,问题是你还愿意相信与否?
邮差皮肤黝黑,骨架在衣服之间晃悠着,眼睛凹陷,却总是充满着情绪——对于渔船上湿气的抱怨,对于无赖政党的无奈,对于正义的执拗,对于远方、对于Neruda和爱情时而提起的期待时而又不得不放下的失落,观影者也与之起起伏伏。而希望燃起的时候,老爷车车铃就响了起来。
和美国那种刻画无所不能之人的电影比起来,刻画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的电影似乎格外令人动心,因为它们选择去诠释人千万种心情中的一种不被看好的情绪,可能是负面的,可能是不愿与人说的。电影去放大它,去剖析它,教人体会与面对并有所领悟。意大利电影在这方面的刻画尤为细腻。这个电影也是有大人物的,Pablo Neruda, 但伟人和小人物互为补充,缺谁这个故事都是不完整的:没有邮差的聂鲁达,是不完整的聂鲁达;没有聂鲁达的邮差,或许也难以探索未知的自我。
这部电影若总结为若干关键词,可有“诗歌”,“友谊”和“爱情”。诗歌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为了吸引tutti donne,还是仅仅为了我的世界里最美的the one and the only Beatrice Russo?到底是帮助Neruda实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还是在于点亮了一种原本平凡无为的生活?这些都是答案。诗歌可以是灵魂的归处,可以是现世中的世外桃源,可以是痛苦的解药,可以是表达政见的利器,可以是生命的呐喊,可以是爱的邮差,可以是寄托。而Metafore是万事之间的联系,是让我们的情绪有所表达又不那么张扬,像是个秘密,等待真正灵魂相通的人去解开谜底。 诗歌文学属于任何人,理应不追求受众而是知音,无所谓语言技巧,无所谓创作者的出身。
再说Neruda和邮差之间的友谊,其实让人心驰神往。当我们看到Neruda拒绝邮差提出帮他捎生活用品的时候,我们或许心头会有一丝失望,然后又觉得无可厚非。大牌怎会有闲工夫搭理一个一无是处之人,情有可原。这种失望又一次出现在了电影后半段,Neruda归国后再无音讯,甚至不愿亲自提笔写一封信给邮差。邮差失落地读完没有提及自己一丝一毫的新闻报道,丈母娘说了句“别人只有在你有用时才想得到你,所有人都是这样,你别再期待”。虽然邮差至死也无以知晓Neruda多年后的登门拜访,但是我们不妨这样去思考:真正的友谊,岂在朝朝暮暮。Neruda对于邮差的点拨让邮差的灵魂觉醒,Neruda与邮差曾有的短暂相伴是邮差生命中最值得回忆的温情,Neruda帮助他懂得并获得这座小岛上最美丽的东西: Beatrice Russo,小海浪,大海浪,悬崖的风,父亲悲伤的渔网,钟声的撞击,岛上的星空,未出世婴儿的心跳。友谊的某种伟大的形式是给予彼此受益终生的东西,这何尝不比日日并肩更珍贵。邮差是懂得的,所以他录下了的自己给Neruda的诗歌,以海为隐喻。Neruda也未尝不从这段友谊中有所收获。人们害怕指引自己的星星有一天会在夜空中消失,但不论是否会消失,我们都要感谢它曾经的出现,也要懂得如何带着它给你的启示独立地走下去。
最后是爱情,虽然电影海报用得是爱情的元素,然这个电影中爱情应该并不是重点。虽然说理想主义让人在掉进现实了会碰得头破血流,不知有多少人会愿意在旁人的挖苦和现世阴谋论中,依旧去体会去相信自己的所爱。如Beatrice Russo那样,说出:“他是个正派的人”。
意大利电影太坏,总是给你许多笑点又在煞尾时给你一击。非常遗憾,邮差的扮演者在电影杀青时就因延误治疗而病逝。当艺术真正成为信仰,便与生命本身不分你我。
《邮差》影评(五):邮差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尽管许多愤怒的青年在大声抗议这喧嚣的都市、狡诈的人性、无情的工业化等等,尽管许多小资们正以各种解构和取消主义的态度在新兴的城市温床上吟唱,迷醉,一面享受现代文明,一面也发着各样的牢骚,可是本来没有经历过多少田园诗般生活的我们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些抗议,因为没有比较,也没有非比较不可的理由。然而,过去像透过帘帷的月光,依旧照进了我们的本来无辜的私房。只要有一点点蛛丝马迹让我们确信我们曾经或者应该生活得别样不同,我们的心就不再封闭了,这样的时刻我们甚至总是有些偏心的拿着现在的种种不好去比较过去在想象中被美化的部分,因此我们不得不不满起来,怀旧起来,孤独起来。 电影作为“想象的能指”,本身就具有半梦的性质,我们憧憬的许多幻想,都是从电影中来,而我们心甘情愿的陶醉在这样的梦幻里,也许这就为什么艺术可以成为人生的疗救。 意大利电影《邮差》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一个叫“下海湾”的小岛风光秀美,民风淳朴,但是常年缺少淡水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主人公马里奥是岛上一个渔民的儿子。他虽然能读会写,天生具有浪漫情怀却因为朴实害羞而不善于表达。他幻想着去那不勒斯、美国、日本等“大地方”生活。而务实的父亲却总是劝他先找到一份工作。 此时,智利著名诗人、共产党员巴勃罗·聂鲁达因政治倾向在国内受到通缉,流亡意大利,意政府将他和妻子安置在“下海湾”。意大利人热情的欢迎这位人民诗人,小岛上的邮政局为处理每天从世界各地寄给这位大诗人的众多信件,招聘临时邮递员专为他送信。马里奥接受了这份薪金微薄的工作。每天他骑着自备的单车翻越山岭到诗人的住处,诗人每次都给他一点小费。开始,马里奥不过认为聂鲁达是一个可以写出美妙情诗打动女孩子芳心的诗人,但邮政局的上司佐治却对诗人非常崇拜,受他的影响,马里奥买了一本聂鲁达的诗,请他签名,却打扰了诗人的思考,诗人并不情愿的草草签了名。马里奥感到沮丧,但是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读了一些诗人的诗,并鼓起勇气向聂鲁达请教。没想到诗人是个平易近人的老人,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为他讲解暗喻的使用,马里奥开始领悟了诗的奥妙。马里奥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诗人,聂鲁达建议他去海边漫步。一次,他们在海边散步,马里奥关于一切都是隐喻的想法打动了聂鲁达,他发现了这个渔民的儿子的敏锐感受力。一次,马里奥在小岛的小酒馆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少女贝雅特丽彩,但是由于不善于表达而受到了姑娘的戏弄。他跑去聂鲁达那里求他以马里奥的名义为她写诗,诗人和他一起到小酒馆里走了一遭,当着大家的面为马里奥签了名,使得马里奥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一次,聂鲁达的朋友为他寄来一盘录音带,马里奥听说这个东西可以将各种声音录下来,对这个老式录音机产生了兴趣,聂鲁达请他对着录音话筒讲一讲岛上的奇景,马里奥支吾了半天只说出了贝雅特丽彩的名字,姑娘将他的心完全占领了。为了获得她的青睐,马里奥不断钻研诗歌艺术,向聂鲁达学习,他将自己写的诗念给贝雅特丽彩听,终于获得了姑娘的芳心,尽管受到了酒店老板娘、贝雅特丽彩的姑姑的反对,两个人终于还是走到了一起。在婚礼上,聂鲁达作为证婚人即兴朗诵了诗歌,与此同时,他也收到了智利国内解除对他的通缉的消息,他可以回国了。 聂鲁达走后,马里奥仍旧负责照料他居住过的屋子,他每每去那里回忆和诗人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意大利此时正在筹备大选,共产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两不相让,争持不下,受到聂鲁达的影响,马里奥加入了共产党,并勇敢地站出来揭穿了社会党党徒为了邀买人心而谎称要在岛上修建自来水管道的阴谋。马里奥的家里人因为聂鲁达长久以来都没有消息,而认为诗人已经将他们这些乡巴佬遗忘了,只有马里奥坚信聂鲁达不会忘记他,忘记人民。贝雅特利彩怀孕了,马里奥给未出世的孩子起名叫巴比图,是聂鲁达名字巴勃罗的谐音。有一次,马里奥去聂鲁达的故居,发现了他留下来的老式录音机,萌生了一个为诗人留下纪念的想法。他找到邮政局的佐治,请他帮忙改造了机器,两个人将岛上海浪轻拍的声音、咆哮的声音、风吹过灌木丛的声音、风吹过山岗的声音、小教堂的钟声、父亲拉渔网的声音、还有小巴比图在襁褓中的声音等等都录制下来,作为送给诗人的礼物,好让他能够记住这个小岛,记住意大利。 多年以后,聂鲁达携妻子回到了岛上,来看望马里奥一家。此时,小巴比图已经五六岁了,长得和父亲很像,但是马里奥却离开了人世。贝雅特丽彩向聂鲁达讲述了马里奥的死,在一次共产党人的集会上,他作为工人代表被邀请上台讲话,而他要借此机会朗读自己写的,献给诗人聂鲁达的诗,不幸就在此时他们受到了当权者的镇压,马里奥牺牲了。诗人终于听到了马里奥为他精心录制的岛上的奇景之声,但是却再也无缘见到这位老朋友了。 影片的结尾,聂鲁达一个人徘徊在蔚蓝色的海边,根据贝雅特丽彩的叙述想象着马里奥牺牲的场景,耳边响起的是马里奥朴实的话语,诗人心潮起伏,赋诗一首纪念这位永别的故人。 影片的叙述平缓而带有轻松幽默的情调,直到聂鲁达走后,马奥对故人的思念犹如烟氲般逐渐升华,终于达到了诗一样的美好境界,而最后马里奥的牺牲将一个诗人和一位劳动群众的深挚友谊推向了高潮。然而即使是处理生于死这样的最适于煽情的范畴,影片依旧保持着哀而不伤的情调,诗人在海边漫步的彩色镜头与想象中马里奥在集会上牺牲的黑白镜头慢慢交替切换,伴随着轻轻的海浪声与马里奥的叙述,营造了诗一样美轮美奂的情调,特别是交待马里奥牺牲的镜头,一页诗稿在惊慌纷乱人群中缓缓飘落,意味着人虽终将归于尘土,而诗和友情却将历久常存。“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邮差》再一次展现了诗电影的巨大魅力,这里没有苦涩的思辨和艰深的哲学、没有残酷的暴露或华丽的粉饰、没有放任的搞笑和廉价的眼泪,然而没有人怀疑这是伟大的艺术,是只有意大利人才能创造出的艺术精品。或许是如此的佳作实在不可多得,主人公马里奥的扮演者马西莫.特罗西是意大利著名的喜剧演员和导演,在影片中他展现了高超的演技,此片拍摄完成后他突发心脏病逝世,在电影外给这部伟大的作品又添上了令人崇敬的色彩和使人叹息的魅力。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无疑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二次大战以后,饱受战乱之苦的意大利人渴望着新思想的解救和强有力民族复兴,此时共产主义作为全新的意识形态在意大利蓬勃的发展起来,5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已经在议会竞选斗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当权者运用国家机器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施以疯狂镇压。现在去探讨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得失已经成为了历史研究,影片的制作者也显然志不在此。故事更多的思考了诗艺术在人类存在中的不凡意义。这里的诗显然也不仅仅指出版物上刊登的诗作,“诗”在电影中作为一种存在方式而存在着。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聂鲁达自不待言,马里奥作为一个渔民的儿子,同样也具有着对诗的渴望和感受力,聂鲁达写作时遇到障碍,问他从渔网可以联想到什么?马里奥回答说,“忧愁”。可见“诗性”在每一个热爱美、追求美、全身心去感受美的人的心底都悄悄的存在——这是除友谊之外本片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即使是一个文盲、一个盲聋哑人,他们也可能具有诗的情怀,诗的本质决不是文字的能指,诗根源于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对美的追求,而文字只是表象和交流的手段而已。而马里奥最后不仅写出了诗,而且还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了用岛上各种自然籁声写成的诗,它比文字更真、更美。小岛居民拙朴自然的生活,憨厚直率善良的性格,小岛秀美的风光,与但丁恋人同名的美丽的女孩,这一切都以诗的方式存在着,向我们昭示着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理想。马里奥最后加入共产党,与其说是抱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还不如说是相信聂鲁达相信的东西一定也会像诗一样美好。诗不仅仅给人以美的感受,不仅仅将一个大诗人和一个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它可以给予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以斗争的勇气,并就此改变了他的一生,然而马里奥鼓起勇气当众诵读的不是政治宣言而是献给聂鲁达的诗,政治不是诗的方式,美才是诗的方式。郭沫若后期的说教口号诗之所以不成功,就是把这两种存在方式搞混了。而当代许多精英诗人从另一个极端狭隘的理解诗,他们太过个人化的诗作完全不理会那种人性中的普遍性诗的存在,倾向于不和读者交流,他们的方向也在离美越来越远。 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时代里,我们背负的苦痛与空虚已经足够沉重和乏味,因此,我们需要诗,需要梦幻,希望能够多一些这样宽容和热爱美的艺术家,为们创造出一剂止痛药,让我们可以敷好伤口,继续前行。
《邮差》影评(六):《我在这里爱你》 聂鲁达
我在这里爱你在黑暗的松林里,风解缚了自己
月亮像磷光,在漂浮的水面上发光
白昼,日复一日,彼此追逐
雪以舞动的身姿迎风飘扬
一只银色的海鸥从西边滑落
有时是一艘船,高高的群星
哦,船的黑色十字架
孤单的
有时我在清晨苏醒,我的灵魂甚至还是湿的
远远的,海洋鸣响并发出回声
这是一个港口
我在这里爱你
我在这里爱你,而地平线陡然地隐藏你
在这些冰冷的事物中,我仍然爱你
有时我的吻借这些沉重的船只而行
穿越海洋永不停息
我想我已被人忘却,犹如这些破锚一般
黄昏时分停泊
这些码头显得格外凄凉
我对这种饥寒潦倒的生活已经厌烦
我喜欢我没有的东西,你是那么地遥远
我的厌倦与那缓慢的暮色在争辩
但是黑夜来临,它开始为我歌唱
月亮转动起它那梦一般的圆轮
借助你的眼睛望着我,那些最大的星星
因为我爱你,风中的松树
愿意歌颂你的名字,借助它们那钢丝针叶
《邮差》影评(七):如诗歌一般的邮差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一定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这么说,不是因为它美妙秀丽的风景,也不是因为它独特悠久的历史,而是因为在这座岛上,曾经诞生过许多美妙的电影。比如意大利本土导演托纳托雷的“寻找三部曲”中就有两部的故事背景就放在西西里岛——《天堂电影院》以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又比如法国殿堂级的导演吕克贝松的《碧海蓝天》,更别说在这片土地上大量取景的影史上牛逼哄哄的黑帮片《教父》了。当然,还有这一部《邮差》。起初,我是不知道《邮差》也是发生在西西里这片土地上的故事的,只是在看这部电影时,所产生的感觉,让我顿时便想起了《天堂电影院》,那些古朴的而又逼仄的建筑,那些碧蓝的海水,以及善良的但却“自给自足”的人们。更何况片中伟大诗人聂鲁达和《天堂》中的放映员艾费多是由一个演员所扮演的。这一切都是我将这两部电影联系起来的原因,后来查阅资料,发现两部电影都是在西西里这片土地上完成拍摄的,我的一些猜想和疑惑便迎刃而解了。
而我就是如此的,像爱上《天堂电影院》一样,我爱上了这部《邮差》。来说说我是怎样的认识到这样的一部电影的吧?这么多年,看这么多的电影,那些浪漫情怀令我一直觉得,要是与自己的喜欢的人或者事物来次不平凡的遇见方式,定是件美妙的事。对于《邮差》,就是如此的。最初是我在看韩国电影《爱情小说》时,有一幕场景,剧中的三个男女主角一起相约在电影院看电影,当时电影的画面上是这样的,在一个房子里,一个痛苦的年轻人,搔头抓耳的对着我本以为是神父但其实是伟大诗人聂鲁达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恋爱了,我该怎么办?恋爱好痛苦,但是我想要继续痛苦下去。”我想我对这个场景印象深刻,可能不是单纯的因为这句台词而已,因为在《爱情小说》中接下来的剧情中,三位男女主角又再一次各自的复述了这句台词。其实,在电影《邮差》中,年轻人马里奥找到聂鲁达述说自己心中对感情的迷惑,寻求帮助的场景,并没有像在《爱情小说》表现出来的那样强烈,她是那样的静逸,带着一丝躁动,就像西西里人们的生活,以及那一片碧蓝的海。
“我恋爱了,我该怎么办?恋爱好痛苦,但是我想要继续痛苦下去。”马里奥在初识姑娘阿特丽契之后,对聂鲁达如是说。大致说来,初来的爱情,就是这样的感觉的吧。也许你不曾感觉到,不曾知道我的名字,但你的笑容,你的身影,已在我的心中翻江倒海了好像一整个世纪。马里奥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生在长在这片美妙而逼仄的小岛上,祖祖辈辈都是靠捕鱼为生,生活的苦闷把这个年轻人的脸拉扯的有些僵硬。他笨拙却又有一些温柔,渔网在他的眼睛里是悲伤的,他时常透过屋子的窗户看海的远方,他对父亲说想去伦敦或者纽约,但终于是没有去的。他的这一颗年轻而痛苦的心灵,几乎在一瞬间便令我想起了高加林,那个作家路遥的笔下,小说《人生》中的躺在麦垛上想象山的那一边不一样生活的年轻人。但不同的是,高加林是一个有着强大精神世界的知识分子,而马里奥只是这个小岛上识得几个字而郁郁的年轻人。假若没有聂鲁达以及聂鲁达的那些美妙诗歌,马里奥也许最终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悲伤的渔网下平凡的风景。
聂鲁达是上个世纪秘鲁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共产主义拥护者,在1948年,他被秘鲁官方通缉,辗转反侧流放到了西西里这片土地之上。某种程度上而言,聂鲁达就是马里奥的信仰。马里奥最初对他感到兴趣,是因为诗人身边总是伴随着一群姑娘,被许多的人爱戴着。他感到非常的不解,后来机缘巧合下,马里奥又成为了聂鲁达的“私人邮差“,他带着他的这些疑问,开始与诗人聂鲁达来往,他开始喜欢与聂鲁达讨论和请教诗歌,渐渐的两个人亦师亦友。马里奥一颗年轻的心,在与诗人与诗歌的接触下,渐渐的被影响着,那些情怀和暗喻在他的内心中慢慢的编织出了一个美妙的世界。而马里奥在爱上阿特丽契之后,通过向聂鲁达的讨教,最终也是靠诗歌虏获其芳心。
我之所以喜欢这部电影,不仅仅是这其中浪漫的爱情,因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在这个电影中所占的比分非常有限。我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故事, 喜欢的是她带给我的感觉,哀伤而又温暖,就像诗歌一样。电影的大多数场景,大多数配乐,大多数对白,总是令人欢喜而又轻快的,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他们生活中的困苦和被剥削,不要忽视马里奥在电影最终的动乱中死去的事实,不要忽视诗人聂鲁达是被流放在离自己祖国遥远的另一边。电影虽然没有极力的刻画这些现象,每每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这些苦痛和黑暗是那个时代也是电影故事发生的背景里真实存在的。但电影就像和煦的风一样令人温暖,她给人以希望,虽然在最终时不忍心的破灭了,但她给人的温暖却是绵长而又真切的。
聂鲁达在电影结尾时的四分之一处,在马里奥与阿特丽契的婚礼上,宣布自己已经被赦免,已经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对于马里奥来说,无疑代表着某种精神向往的崩塌。他丢失了自己那份”私人邮差“的工作,渐渐又回到了生活与理想的困顿与斗争之中,他无比的怀念与聂鲁达神交的日子,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做诗人的潜质。他在报纸上看到诗人采访,却并没有看到诗人念及西西里除美妙的风景以及淳朴的人们以外的什么,比如他的名字。他等待诗人的来信,就好像在等待着他信仰的回归。他想起曾经诗人要他介绍西西里岛上美妙的事物,他拿着那个收录机,走在西西里的各个地方,寻找美妙的声音。再困难而混沌的生活里,也总是有着我们喜爱的美丽。马里奥收录的声音是这样的。
“第一,海水流淌声,轻轻的;第二,海浪声,大声的;第三,掠过悬崖的风声;第四,滑过灌木丛的风声;第五,爸爸忧愁的渔网声;第六,教堂的钟声;第七,岛上布满星星的天空,我从未感受到天空如此的美;第八,我儿子的心跳声。
看着马里奥伙同邮局的老板四处收录这些他们早已习惯的声音时,我的眼眶莫名其妙就湿润了, 我始终觉得,美好的事物,哪怕再微小,再显而易见,总是值得去收藏和记录的。我始终觉得马里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寻找到了自己的心灵,从而坚定的想要做点什么,并且他做到了。在工人的集会上,他被邀请上台宣读自己的诗作。但在拥挤的人群中,他还没来的及上到台前,就遭遇了政府的打压,就那样轻飘飘的逝去了。白色的诗作稿纸在黑压压的人群中飘零,虽然没来得及朗诵,我却认为马里奥是无怨无悔的,因为他已经来到了他曾在窗台前凝视的远方。聂鲁达在四年后,回到西西里,听到阿特丽契说起马里奥的这些事情,平静的就如同轻轻流淌的海水声,我相信他的内心早已翻腾的犹如海浪。
最后感谢这部电影的这几个演员吧,首选感谢聂鲁达的扮演者,他就如同他在《天堂电影院》中的艾费多一样,温暖有爱;感谢马里奥的扮演者,他在电影拍完后的第12个小时里突发心脏病去世,感谢他带给我们如此美妙的绝唱;感谢阿特丽契的扮演者,她的心灵就如同她的面容和身体一样纯真而又美丽。
《邮差》影评(八):意大利式田园诗
意大利。美丽的小岛,隐去了生活的吵闹,留下的只有诗人的眼睛和海水的味道。悠扬的风琴,轻轻拍打的海浪,小酒馆里的一杯红酒,就是这里生活的旋律。
不安于像祖祖辈辈一样从事捕鱼的mario,由于接下了一份临时邮递员的,认识了流亡的智利共产主义诗人neruda。由于艳羡于大诗人的女人缘,mario对诗歌萌发了极大的兴趣,在向neruda请教诗歌的过程中,他们慢慢成为了朋友。借了neruda动人的情歌诗句,Mario终于如愿以偿娶到了他一见钟情的女人(那真是个标准的意大利美人)。
mario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青年,心怀幻想,却也没有一技之长,你甚至可以说他有点不切实际。憨憨傻傻,不善言谈,眼神闪烁,但是却有一颗纯净感性的心,一如日夜拍打海岸的浪花,平凡得你看不到他的存在。感性如他,他能感受到船只在文字上摇荡,大胆如他,第一眼就狂热地爱上了镇上最漂亮的女孩,卑微如他,neruda离开一年后寄来的秘书代笔信中没有留给他只言片语,他只会说,我是谁呢,怎么配得上neruda这样的人挂记,尽管眼里早已装满了失落。善良如他,为渔夫被剥削抱不平却反被责难,对他的诗人朋友坚贞狂热的爱着~
虽然neruda间接造成了mario的悲剧,但我们不能说相遇就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毕竟因为neruda,mario普通的生命曾经绽放了漫天繁星。
“(诗歌)当你解释它时,它就变得索然无味了。解释永远达不到诗歌能刻画的那种自然呈现的感觉。”它本身最具有说服力。
《邮差》影评(九):海浪的那一邊
記得畢業旅行的時候,三個哲學系的朋友坐在出租車的後排,窗外是內蒙呼呼的風和遼闊的原野。目的地尚遠,旅途像青春一樣長得沒有終點。我和B之間坐了姑娘Q,大家的話題隨著年齡流向了愛情和婚姻。自然又是哲學系聊天常見的套路:批判現實,抒發幻想。因為性別的差異,談話更是豐富多彩。在一番友好的唇槍舌劍後,X決絕地說:“現在的許多姑娘找男朋友都要看有沒有錢,家庭背景什麼的,而不看男生本身,這樣的人絕對不能交往。”我習慣性地反駁道:“你所說的‘人本身’是指什麼?為甚麼擁有的錢和背景不能作為其本身的一部分?才華或相貌,甚至性格,可以說是他的一部分嗎?內在和外在間的區分在哪兒?或者兩者間真的有區分嗎?”
Q說:“你又來了,你明知道這些問題討論不清楚的。我覺得X的意思是,不要讓金錢或權力侵入感情世界。”
B肯定地說:“對,最好這兩者不要侵入任何領域。”
我不禁笑道:“”倘若權力和金錢不侵入任何領域的話,它也就不稱作權力和金錢了。“
三個月後我換了個尚能賺錢的專業去美國念研究所。聽一些成本收益分析,人力資源分配之類的東西。一天下來,money和efficiency兩個字像兩隻蒼蠅般在腦中亂撞。然後我放下paper看了《郵差》:與世隔絕的小島,流亡詩人聶魯達,不想當漁民的年輕郵差,美麗的酒吧女郎,方興未艾的共產主義運動,因詩歌和死亡而不朽的愛情。我突然想起了從前的那段對話。心靈的觸碰,靈魂的共振,才是B想要的,其實我早也明白。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這份自然而然的相思,不恃於任何外物,也無法通過外物來獲得,大概就是內外的分野吧。至於詩歌,則如同滌蕩靈魂的海浪,使人飽受塵垢蒙蔽的靈魂,一時間看到美的光亮。
當這光降臨的時候,又有什麼能勝過它的呢?種種解釋、計算和考慮,於無所不在的燦爛中蒸發殆盡。顧城說:“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那些神的時刻,凡人一旦經歷便無法忘懷。詩歌、愛情和革命也正是因此而永遠誘人。聶魯達走後,郵差馬里奧伴著島上最美麗的姑娘,悶悶不樂地在廚房裡做工,耳邊是岳母的嘮叨和抱怨。他期待遠方的來信,為他帶來詩歌的魔力,為他帶回愛情最初的樣子。
馬里奧最終並未等來聶魯達的信,但卻以另一種方式和大詩人取得了聯繫。他錄下了島上最美麗的事物——小聲的海浪、大聲的海浪、懸崖上的風、穿過灌木叢的風、爸爸憂鬱的漁網、神父哀傷的鐘聲、島上星星滿布的夜空、兒子Pablito的心跳聲,為了一個塵封的願望。馬里奧已經可以用自己的眼光發現美。這個時候,他和聶魯達一同沐浴在繆斯神聖的光輝下,就像在曾經的海灘上。
故事的結尾,馬里奧在一次工人機會中準備朗讀自己寫的詩歌,他真的成了詩人。在他滿懷希望地擠向主席台時,遊行被軍警沖散了。他的詩歌落葉般被踏在人群腳下,如同他的命運。死的可真好。馬里奧摯愛的姑娘永遠不會老去,他說的對。
看完了,也寫完了,還能做些什麼呢?是不是抓緊時間洗洗睡,好去上明天的課程?看不見天堂並沒有什麼,感慨的是見到了天堂,卻發現難以久居。不知為何想到了老毛的“繼續革命”論,嗨,他可真是個浪漫到骨子裡的人。
《邮差》影评(十):如诗歌一般的《邮差》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一定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这么说,不是因为它美妙秀丽的风景,也不是因为它独特悠久的历史,而是因为在这座岛上,曾经诞生过许多美妙的电影。比如意大利本土导演托纳托雷的“寻找三部曲”中就有两部的故事背景就放在西西里岛——《天堂电影院》以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又比如法国殿堂级的导演吕克贝松的《碧海蓝天》,更别说在这片土地上大量取景的影史上牛逼哄哄的黑帮片《教父》了。当然,还有这一部《邮差》。起初,我是不知道《邮差》也是发生在西西里这片土地上的故事的,只是在看这部电影时,所产生的感觉,让我顿时便想起了《天堂电影院》,那些古朴的而又逼仄的建筑,那些碧蓝的海水,以及善良的但却“自给自足”的人们。更何况片中伟大诗人聂鲁达和《天堂》中的放映员艾费多是由一个演员所扮演的。这一切都是我将这两部电影联系起来的原因,后来查阅资料,发现两部电影都是在西西里这片土地上完成拍摄的,我的一些猜想和疑惑便迎刃而解了。
而我就是如此的,像爱上《天堂电影院》一样,我爱上了这部《邮差》。来说说我是怎样的认识到这样的一部电影的吧?这么多年,看这么多的电影,那些浪漫情怀令我一直觉得,要是与自己的喜欢的人或者事物来次不平凡的遇见方式,定是件美妙的事。对于《邮差》,就是如此的。最初是我在看韩国电影《爱情小说》时,有一幕场景,剧中的三个男女主角一起相约在电影院看电影,当时电影的画面上是这样的,在一个房子里,一个痛苦的年轻人,搔头抓耳的对着我本以为是神父但其实是伟大诗人聂鲁达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恋爱了,我该怎么办?恋爱好痛苦,但是我想要继续痛苦下去。”我想我对这个场景印象深刻,可能不是单纯的因为这句台词而已,因为在《爱情小说》中接下来的剧情中,三位男女主角又再一次各自的复述了这句台词。其实,在电影《邮差》中,年轻人马里奥找到聂鲁达述说自己心中对感情的迷惑,寻求帮助的场景,并没有像在《爱情小说》表现出来的那样强烈,她是那样的静逸,带着一丝躁动,就像西西里人们的生活,以及那一片碧蓝的海。
“我恋爱了,我该怎么办?恋爱好痛苦,但是我想要继续痛苦下去。”马里奥在初识姑娘阿特丽契之后,对聂鲁达如是说。大致说来,初来的爱情,就是这样的感觉的吧。也许你不曾感觉到,不曾知道我的名字,但你的笑容,你的身影,已在我的心中翻江倒海了好像一整个世纪。马里奥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生在长在这片美妙而逼仄的小岛上,祖祖辈辈都是靠捕鱼为生,生活的苦闷把这个年轻人的脸拉扯的有些僵硬。他笨拙却又有一些温柔,渔网在他的眼睛里是悲伤的,他时常透过屋子的窗户看海的远方,他对父亲说想去伦敦或者纽约,但终于是没有去的。他的这一颗年轻而痛苦的心灵,几乎在一瞬间便令我想起了高加林,那个作家路遥的笔下,小说《人生》中的躺在麦垛上想象山的那一边不一样生活的年轻人。但不同的是,高加林是一个有着强大精神世界的知识分子,而马里奥只是这个小岛上识得几个字而郁郁的年轻人。假若没有聂鲁达以及聂鲁达的那些美妙诗歌,马里奥也许最终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悲伤的渔网下平凡的风景。
聂鲁达是上个世纪秘鲁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共产主义拥护者,在1948年,他被秘鲁官方通缉,辗转反侧流放到了西西里这片土地之上。某种程度上而言,聂鲁达就是马里奥的信仰。马里奥最初对他感到兴趣,是因为诗人身边总是伴随着一群姑娘,被许多的人爱戴着。他感到非常的不解,后来机缘巧合下,马里奥又成为了聂鲁达的“私人邮差“,他带着他的这些疑问,开始与诗人聂鲁达来往,他开始喜欢与聂鲁达讨论和请教诗歌,渐渐的两个人亦师亦友。马里奥一颗年轻的心,在与诗人与诗歌的接触下,渐渐的被影响着,那些情怀和暗喻在他的内心中慢慢的编织出了一个美妙的世界。而马里奥在爱上阿特丽契之后,通过向聂鲁达的讨教,最终也是靠诗歌虏获其芳心。
我之所以喜欢这部电影,不仅仅是这其中浪漫的爱情,因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在这个电影中所占的比分非常有限。我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故事, 喜欢的是她带给我的感觉,哀伤而又温暖,就像诗歌一样。电影的大多数场景,大多数配乐,大多数对白,总是令人欢喜而又轻快的,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他们生活中的困苦和被剥削,不要忽视马里奥在电影最终的动乱中死去的事实,不要忽视诗人聂鲁达是被流放在离自己祖国遥远的另一边。电影虽然没有极力的刻画这些现象,每每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这些苦痛和黑暗是那个时代也是电影故事发生的背景里真实存在的。但电影就像和煦的风一样令人温暖,她给人以希望,虽然在最终时不忍心的破灭了,但她给人的温暖却是绵长而又真切的。
聂鲁达在电影结尾时的四分之一处,在马里奥与阿特丽契的婚礼上,宣布自己已经被赦免,已经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对于马里奥来说,无疑代表着某种精神向往的崩塌。他丢失了自己那份”私人邮差“的工作,渐渐又回到了生活与理想的困顿与斗争之中,他无比的怀念与聂鲁达神交的日子,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做诗人的潜质。他在报纸上看到诗人采访,却并没有看到诗人念及西西里除美妙的风景以及淳朴的人们以外的什么,比如他的名字。他等待诗人的来信,就好像在等待着他信仰的回归。他想起曾经诗人要他介绍西西里岛上美妙的事物,他拿着那个收录机,走在西西里的各个地方,寻找美妙的声音。再困难而混沌的生活里,也总是有着我们喜爱的美丽。马里奥收录的声音是这样的。
“第一,海水流淌声,轻轻的;第二,海浪声,大声的;第三,掠过悬崖的风声;第四,滑过灌木丛的风声;第五,爸爸忧愁的渔网声;第六,教堂的钟声;第七,岛上布满星星的天空,我从未感受到天空如此的美;第八,我儿子的心跳声。
看着马里奥伙同邮局的老板四处收录这些他们早已习惯的声音时,我的眼眶莫名其妙就湿润了, 我始终觉得,美好的事物,哪怕再微小,再显而易见,总是值得去收藏和记录的。我始终觉得马里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寻找到了自己的心灵,从而坚定的想要做点什么,并且他做到了。在工人的集会上,他被邀请上台宣读自己的诗作。但在拥挤的人群中,他还没来的及上到台前,就遭遇了政府的打压,就那样轻飘飘的逝去了。白色的诗作稿纸在黑压压的人群中飘零,虽然没来得及朗诵,我却认为马里奥是无怨无悔的,因为他已经来到了他曾在窗台前凝视的远方。聂鲁达在四年后,回到西西里,听到阿特丽契说起马里奥的这些事情,平静的就如同轻轻流淌的海水声,我相信他的内心早已翻腾的犹如海浪。
最后感谢这部电影的这几个演员吧,首选感谢聂鲁达的扮演者,他就如同他在《天堂电影院》中的艾费多一样,温暖有爱;感谢马里奥的扮演者,他在电影拍完后的第12个小时里突发心脏病去世,感谢他带给我们如此美妙的绝唱;感谢阿特丽契的扮演者,她的心灵就如同她的面容和身体一样纯真而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