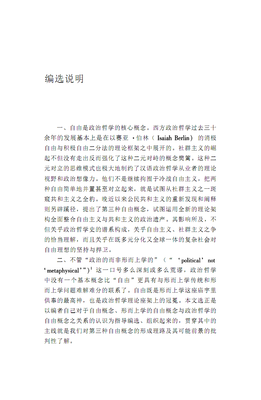第三种自由
▲Photo by Jules Marchioni on Unsplash
从前跟自己要好的朋友大概都被分配到了一个班级,而我却被独自分配到另一个陌生的班级。
全然的陌生,跟过渡性的、有熟悉之人与你一起分担(面对)这陌生,这两者不是同一概念。
想来我一向习惯忍耐,甚至是逆来顺受。如今这焦虑甚至是恐惧感,远远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范畴。于是我向家人求助,可不可以帮忙申请转换一个班级。
说不上是任性,因为据说这所学校向来有这个方式,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诉求,在合理的范畴下调换所在的班级。
眼看着身边那些同学大约都得到了答复,更换到另一个班级,或者从其他教室更换到这里。唯独只留下我。
那年我十三岁,这是我得到的答复。
拿出“几乎是视死如归”的勇气,走进校长办公室。得到的答复是,其实上面的领导是审批通过了,但是也需要各方力量的协商。
于是我知道了本质根源,卡在了目前所在的班级,那位班主任那里。
我在一个自习课上,冒着违规的风险,离开教室,去到那位班主任的办公室。他说,这里不大方便,我们去外面说。
教室走廊上,他一边抽烟,一边听着我的诉求。
我几乎用尽所有力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后把所要表达的意愿语句讲述清楚。
他只答复了一句,“是这样的,现在不合适。”
“就是......你不适合调换班级。”他还是面无表情,“从来没有这个说法的。”
“有的有的,王老师。隔壁班那个谁谁和谁谁谁,他们都已经调换安排好了。”
他终于叹一口气,“我这么说吧——其他人都可以,就是你不可以。”
我几乎崩溃。或者已然崩溃。
“因为你的入学成绩是班上的第一名。你是种子选手,你不可以离开这里。”
“你离开了,交换过来一名成绩普通的学生。其他班主任自然欢迎,但是我就丢失一名尖子生了。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决不允许。”
如果那时候我再勇敢一些,或者体能好一些,不至于“那么”被情绪所控制身体——或许我会多问上一句:那么到底是我的命运重要?还是你作为班主任的所谓业绩重要?
但是退回到如今的三十岁,我或许会在心底清楚地听到自己的答复:那位班主任,他的决策是对的;因为他的业绩,就等同于他命运的一部分。
以及,延伸出来给我的来日启迪是:就人生而言,重要的或许不是对错本身,而是关乎立场。
一个人越是在意什么,便会拼命维系(守护)什么。这不是是非题,是选择题,是价值导向逻辑。
从十三岁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写日记了。所以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那天晚自习下课,我一个人走到校园还在开发中的那片荒地上。山坡上一无所有,夏日的星空辽阔而闪烁。我痛哭到几乎心碎。
十三岁的掏心掏肺,是泪水可以装满整个海洋的那种。没丝毫的节制跟抑制。
我甚至不知道如何接住自己。
我只是在下坠,深不见底地下坠。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厌恶自己,是因为某种“优秀跟出众”,反而成为了我的束缚。
我恨极了自己,在那一刻。
大概哭泣了几日之后,我开始迅速梳理自己的逻辑线。即便那个年纪还没有“逻辑”这个概念。
但是因为我太害怕了——以至于我觉得,我必须跟我的命运之神,好好交谈一番。
我给自己两个选项——
放任自己,不顾学习,不再当好学生。脱离种子选手的赛道,让自己变得不再有价值。
那个时候,那位班主任就会觉得当初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说不定就放我走人了。
待我去到其他班级,再重新发奋努力起来。
这是第一。
我保持原本的学习作风,将这巨大的委屈收藏进心底,而后继续生活下去。
我只会在这里,这所学校生活三年。我要考出更好的成绩,离开这里,离开这些人和事。
这是第二。
如你所知道的,我选择了第二条路线。这条路线,是跟时间进行交易,而不是短视格局的自暴自弃。
没有人告诉我应该这样做。
“你喜欢我哪里?——那我改就是了。”
可是这个逻辑,放到其他领域,那是万万不可以参考,更不可以复制的。
因为——那可是你自己的命运啊!
如果一个人不够勇敢、自信、坚定,甚至在某些必要的课题上不够出众,那么你大可以向更好的方向走去。
可是反过来,如果是因为你在某部分领域的足够出众,以至于这种出彩会给的阶段性生活造成阻挠——你的第一反应不应当是配合环境,而是应当逃离那个“已经配不上”你的环境才是。
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有那个领域的出众者——这是由宇宙的正态分布法则所决定的。
而出众者,必然备受重视,重用,甚至是以各种名义的诱惑或者控制。
总之,如果你拥有某一部分的价值,你必然会受到重视。无论是学生、职业人、领袖,以及相关种种其领域中的领袖人物。
而一旦这种价值被某种外在体系认证,那么你就很难离开——无论是调换一个班级,还是更换一个部门,而行业杰出人物更是需要签订一份份“竞业禁止协议”。
那么问题来了,陷阱在哪里?
陷阱的诡异之处便是:成也价值,“城”也价值。
这“城”,便是一层层围墙。
你可以这样理解——
这世界有多少人正在努力解决温饱问题,就有多少已经“温饱自由”的那一类,在诉求更高级的快乐,甚至是理想。
不是他或者她不懂得珍惜生活,珍惜命运,珍惜已然拥有的。并且要说服自己,要学会满足。
问题的本质核心是,关于降服。
我始终觉得,真正的自我满足感,一方面来自于自我努力,二方面来自于创造性(包括有趣、享乐、停留都是很好的品质与能力),第三方面来自于对那条“上限”的认知。
而这第三样,是最为辛苦的。
一个女人,要赢得帝王的唯独宠爱。一个沉迷权力的人,试图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一个野心家,期待改变世界,甚至是整个宇宙。
这部分在一开始,其实就已经知晓结局了。
而满足感的奇妙之处,并不是来自于“你想要得到什么”,而是识别出“你不再失去什么”。
如果我知晓人性本质,我愿意迎接一切变化。这世间并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更多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你珍重此时此刻,那么你便拥有了永恒——因为就线性时间逻辑而言,绝对的永恒并不存在。
但是,某种永恒,是可以创造的。
就像我此刻,正在记录下这个年岁的启迪。只要文字不消亡,我的哲思便得以停留在永恒之河上。
于是,真正的降服,应当是这样的——
我有确定自己已经尽力,这种尽力建立在我已然拥有的资源之外,还投入了自己的主动性跟认知能力。
它(他们)总是劝服本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放下欲望,落入平庸;却同时又对所谓的平庸者指手画脚,诸多不满,“施舍”以焦虑感。
而你又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不会被劝服(或者诱惑)吗?
有家可回的人。
他或者她的诉求,已经得到,或者正在得到。
那些超出自己“围墙”的部分,也被隔离在山海湖川之外。
我不觉得这是所谓的得道之人,或者必须看破红尘,才可以换来这份“怡然”。我相信,并且我在自己的经历中,一直都在遇见这样的,大隐隐于市的智者。
生活如电影,转眼便是多年以后。
毕业第三年,春节假期准备回到深圳工作。我在客运站候车。我远远就看到了他,熟悉的影子。那位当年“为难”过我的班主任。
他送他的女儿去上学,听旧友说是某个外省的大学。他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孩子推着行李箱,他提着两个纸箱子,里面或许大包小包的东西,菜肴或者干货。
她的女儿跟我当年一样,懵懂而有些倔强。上车前假装平静。倒是父亲在多番叮嘱,唠叨着各种注意事项。
那几分钟,极为漫长。
不是我在纠结,而是在穿越。穿越回十三岁那年,那些身后无人,前途未卜的深夜。
某个瞬间他转过头,停留在我的视角。像是发愣,或者惊讶、疑惑。而后他很快扭转过头去了。
我看着他离开。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男人,操劳和费心的人和事,装满他的宇宙。他或许根本不再记得我。
从更大的本质视角来看待,他当年并没有做错什么。就像我在后来的人生里,总是可以用“他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这个“在其位谋其政”的逻辑,来安抚自己接纳所有的不顺。
我的委屈是真的,我被黑压压的人生推倒过是真的;曾经的“无人可依”之恐惧是真的;我在后来长达十余年的失眠跟惊恐也是真的。
我无法欺瞒自己,更无法说服她,去原谅这部分的“坠落”。
当年发过一个小小的誓言,等到来日,我学有所成,功成名就,必定要一一报复这些所有的人——以任何隐性或者显性的方式。
可是待到某个年岁,这些念头逐渐消失——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变得无足轻重,而我的世界也有了更好的生活。
于是按照佛家所言,这个阶段,当是“放下”一切了。
可是我还没有说完。
原谅(和解)的第二方面缘由,当然不仅仅是“我没有时间讨厌你”。
那就是,保持愤怒,方可不必愤怒。
保持愤怒,方可不必轻易愤怒。
“我想我还算年轻,还没到需要通过谅解万事万物,以便祈求老天换得多一些寿命。我还没有到这个领悟的年纪,或者阶段,所以我不打算扛起这份所谓的责任大旗。”
“我经历过一些死亡的边缘,我大概知道(甚至是确定),我挺不喜欢活着这件事的。所以我不奢求长命百岁,只求这一生尽我所能,有幸尝到过自由的味道或者感受。”
在某个夜里,我决定敲下这些话——以此来答复长久以来,一直“劝说”我要心怀广阔之心,包容万事万物才为“真正智者”的,某位“过来之人”持续不断的邮件围剿。
“我还没有到看山还是山的阶段——那也并非是我的诉求。我是一个平凡的写作者,这一生能够拥有情绪,接住我的感受,并将其记录下来。”
“这是属于我的降服上限,也是我的自我满足源泉。而这些于我而言,已经足够了。”
他后来再也没有给我发来邮件。
但是也务必记着:你的珍贵,来自于你的自我评定,而不是来自他人的诉求,甚至基于某种利益之上的立场。
保持愤怒,方可不必愤怒。
——说的是,我需要记得这种仇恨感本身,而并非针对那个人。
关于对自由的解读,从前的所得大概是两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也包括不必面对那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人。
这两类都需要“圈地”能力(或者资本)——前者是修炼自我、进行提升的能力,后者是提升进阶、逃离环境的能力。
而在那个春季假期的客运站,遇见了当年自己在年少时候第一个所谓的“灭霸式”人物——这一路过来的所有“仇家”,我大概都是这样的应对逻辑——
我不去复仇,不是我不可以,而是我不需要了。
我期待你也可以这样想。
以及逐渐行走于时间之河中,我觉得自己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自由地喜欢一些人,可以自由地不喜欢一些人。
这是第三种自由。
也就是,如果他或者她站在我面前,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难受,甚至想要逃离——而是——
“没有关系的,你存在于这里,并不会对我的心情,或者命运,构成任何影响与威胁。”
“因为老娘就是不喜欢你。”
我要告诉你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