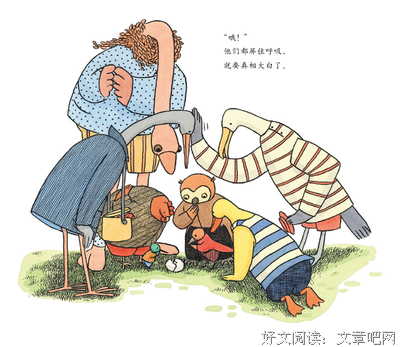《我们》的读后感10篇
《我们》是一本由[俄]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页数:2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读后感(一):没有我的我们
说实话看的挺艰难……期间多次睡着,并且是充满困惑的。当然是因为想凑齐三部曲而买来看的书,作为其中最早出版的一本,很多人都说它影响了《美丽新世界》,确实能感觉到里面有它的影子。 作者的想象力让人佩服,没有名字的号码们幸福地生活在“众一国”,住在透明的房子,吃合成的食物,被筑起的高墙保护,研究数学和理性即可,每天追求真理。没有个人“我”,只有“我们”。然而作为一名工程师的男主因为爱上了地下革命者而产生了混乱。经历过波动之后最终男主还是选择了做消除想象力的手术,并且没有内疚地出卖了其他革命者。 整个故事和描述感觉比其他两部反乌托邦都弱,可读性也差一些,有挺多地方都看得云山雾罩,万万没想到战斗民族有这样的文风……最后的讨论中作者提到,“错误比真理更有价值:真理就像机器,而错误是鲜活的。”竭尽全力让大家寻找真理避免错误的众一国,正是那个死气沉沉的地方,而I-330就是那个鲜活的错误。作者通过她的嘴告诉我们,不会有最后的革命,所有既定的“真理”都可能改变,保持怀疑、不畏强权,虽不易却是可以发生巨变的力量。
《我们》读后感(二):关于这本书
我现在在图书馆里,桌子上放着这本《我们》,就在几分钟前,我把它看完了。看这本书的原因很简单,我最近在学俄语,想了解一下俄国作家,在“俄国文学”的书架上,这本书封面最吸引我,如此而已。
《我们》叶普盖尼·扎米亚京的《我们》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被称为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 在阅读此书之前,我不知道乌托邦的含义,所以我特地百度了一下,百度的解释为“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 我以为这将会是一本描述未来美好生活的书。令我意外的是,在作者笔下,未来世界的众一国,每个人都只是号码,没有名字,绿墙里面的号码们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他们没有隐私,到处都是玻璃;他们的任何东西都是分配的,甚至性生活。每个号码赤裸裸地活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里,没有灵魂。D-503在有了灵魂之后,反而被认为是“生了病”。难道,没有自由的一致的能得到物质供给的几乎每人都一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吗? 我想,没有人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号码。
《我们》读后感(三):反乌托邦文学的意义
这次回国在书店发现,翻译作品非常繁茂,好几家大出版社都出了系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我买了三本。这是其中之一。扎米亚京的这本《我们》,和《美丽新世界》、《1984》合称反乌托邦三部曲,也是最早的一部,据说后面的两部均受其影响,所以带着几分崇拜开读。
不过也许是因为文字的角度是从一个数学家的视野展开,对于我等数学不好的人,很多以数学语言进行的表述,有点儿难懂。不过从整体的结构上讲,男主角的转变和反叛确实有些唐突,前一刻是忠心耿耿的众一国飞船的总设计师,赞美和欣赏各种现实制度,后一刻突然就不能自己的要反叛,据说是因为遇上了女主角……《1984》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女性角色……亚当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女性角色夏娃……联想起《窃听风暴》,那里面也有个类似的女性角色……女性可真是个Universal Solution。
从批判的角度说,我个人更喜欢《1984》,老大哥的格局设定比众一国的设定更有血肉,也更让人心惊。那本书真像一个“神算子”一语道破天机,我至今仍然记得阅读过程中的惊愕。那几乎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更像社会学家的预测和推论。
让人心惊胆颤不由得细思量,就是这种书的意义。
《我们》读后感(四):反乌托邦文学的开山之作
叶甫盖尼•扎米亚金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知名作家。1902年进入圣彼得堡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学,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两次遭流放。毕业后成为俄罗斯帝国海军的工程师,1916年曾被派往英国督造破冰船。扎米亚金十月革命前曾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秋回国,追随文豪高尔基从事十月革命后的文化建设工作。1923年,扎米亚金创作了他最出名的小说《我们》,由于在苏维埃俄国无法出版,第二年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问世。《我们》被誉为反乌托邦小说的开山之作,与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并称为世界文坛的反乌托邦三部曲。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小说虚构了六百多年后的公元26世纪,有一个名为众一国的国度,高度地整齐划一。人们的作息严格遵守《时刻表》,每天以六分仪般的精准在同一时刻同时起床,同时上班,傍晚数百万人同时下班;吃饭时在同一秒钟将汤勺放进嘴里;同一秒钟去礼堂,去纪念馆,去睡觉。众一国的男男女女没有名字,只有号码。散步时,在音乐塔播放的《众一国进行曲》雄壮的乐声中,成千上万的号码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制服,胸前佩戴金色的徽章——上面刻着每个人的号码,以四列纵队肩并肩地徐徐散步。众一国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私生活,有关机构给男女号码配对分发红色的票据,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凭票进行性生活。众一国的统治者叫恩主,号码们每年选举一次最高领导人,但只能投票给恩主连任。主人公“我”的号码是D-503,是位数学家,正在为众一国建造宇宙飞船“统一号”。配给他的性伴侣是O-90,她对D-503一往情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怀上了他的孩子。D-503却对I-330一见钟情,对她和其他男号码的来往非常嫉妒。I-330唤醒了D-503的情爱,也唤醒了他身上一种古老的、原始的欲望。在“统一号”即将试飞之际,I-330号召觉醒了的兄弟们打破墙壁,让绿色的风自由吹送;夺取“统一号”,飞向茫茫的太空。恩主对此洞若观火,逮捕了参与叛乱的号码。D-503被殃及,并被强制做了想象力切除手术,然后出卖了I-330。D-503眼睁睁地看着心上人I-330被恩主处以极刑。不久,城内爆发大战,尸横遍野,野兽横行。但恩主成功地筑起了高压电堡垒,他坚信哪能够镇压号码们的叛乱,理性终将取得胜利。
《我们》并不以故事情节、人物刻画见长,而是用笔记体的写作形式,通过象征、夸张、讽刺等手法,表达了作家的一些理念和对未来社会的忧思。在扎米亚金虚构的众一国中,人不是具有独立个性的“一”,而是渺小的、必须服从集体意志的“之一”。小说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即“我”就像是一克的砝码,而天平的另一头是象征了国家的“我们”的一吨的砝码。认为“我”相对于国家拥有某些权利,就像认为一克的砝码能压平一吨的砝码,这不是很可笑吗?“因此有了这一区分:权利归于吨。而义务归于克。从渺小到伟大的天经地义的途径就是忘记你是一克,而要认为是一吨的百万分之一”。
D-503因为爱慕I-330,产生了追求个体幸福的欲望,被瘦削如刀的医生讥讽为“病得不轻”,“有了灵魂”。但在主宰众一国的恩主看来,个人没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幸福是恩主赐予他的臣民的,条件是你必须放弃自由。在恩主的眼里,即使是原始社会的野蛮人,真实的代数意义上的人性之爱也不可避免地是非人性的,真相必有的特征就是——残忍,“正如火焰不可避免的的真相就是它会烧死人”。因此,用诗人R-13的话来说:“天堂里有两个人,被给予了两个选择:没有自由的幸福,或没有幸福的自由。没有第三个选择。”众一国的号码们不得不面对这人生的两难选择。假如有谁胆敢违背恩主的意志,去追求自由,显示个性,等待他们的就是毫不留情的镇压——被强制进行想象力切除手术。小说中有一段十分压抑的描写,有50个违反戒律的号码缓慢地沉重地走了出来,“那些不是脚——它们是僵硬的沉重的轮子,由看不见的履带驱动。他们并不是人——他们是人形拖拉机。在他们的头上飘扬着白色的旗帜,上面绣着一个金色的太阳:在太阳的光芒之间写着下面几个字:‘我们是先行者!我们已经做了手术!大家跟我们来!’”显然,失去了思想与个性的号码无异于行尸走肉。
扎米亚金创作《我们》时,已经退出了布尔什维克,他不认同苏维埃的审查制度,但如果将《我们》与斯大林的肃反及残暴统治联系起来,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这部小说面世的1920年代,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掌握苏联的政权。不过,小说中表达的反乌托邦的思想内涵,以及对幸福与自由、压制与宽容、个体与社会等关系的思考,依然令人深思。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但幸福若以放弃自由作为代价,则最多停留在物质层面。对于一个理想的社会来说,还是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
(此系本人原创作品,未经授权或许可,不得转载,否则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我们》读后感(五):扎米亚京《我们》
这本书的阅读完成标志着反乌托邦三部曲阅读计划的圆满结束。有趣的是,我的阅读顺序刚好是这三本书故事性的排序。《一九八四》最具故事性,《美丽新世界》次之,《我们》次之。《我们》的叙述方式很奇特,与其说是作者所标榜的日记式的记录,不如说像意识流电影式的碎片插入和镜头切换,加上译者比较忠实的翻译,让我读起来十分吃力,经常感觉到剧情的断裂和一脸茫然。好在篇幅不长,在我恍恍惚惚的艰难阅读之下,比较迅速的完成了这本书的阅读,对整个故事的脉络也有一点印象。 比起《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这本书的乌托邦社会可以说是很柔和了。没有《一九八四》里的过分监管、暴力,也没有《美丽新世界》里的高科技式洗脑、改造,作者最早主宰者的“恩主”甚至在选举大典上遭遇了暴动,甚至让“统一号”险些落入敌人之手。故事方面,三本书都从爱情入手。作为第一工程师的主角“D”爱上了反动集体领袖“I”,而故事中其他的男人们也大多是在“I”的诱惑下(应该是如此)背叛了社会,这不禁让我有点疑惑:这个女人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吸引技巧吗?巧的是,作为男主的“D”也有两个不求回报、默默付出的女人,夹在爱情故事之中的社会思考令人有些五味陈杂。无论如何,我同情“O”这种卑微付出的爱慕者。 故事的最后,因为觉得“I”不是真正爱自己的“D”出卖了反动集体,但作者并没有交代这个乌托邦社会的结局。也许,作者只是想告诉我们,在以数字计算的绝对理性社会之中,也会有最基础最原始最美丽的人性来反抗。但《美丽新世界》已经更进一步,消灭了人类的本性,靠超凡的科技。 “没有最后的数字,革命永不会停止”
2018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