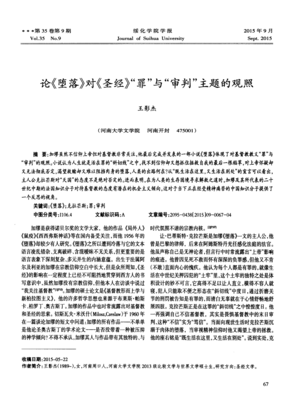堕落论的读后感大全
《堕落论》是一本由[日]坂口安吾著作,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出版的240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怀疑有很多被删减了
●安吾老师,霓虹文学界第一可爱的臭流氓。后半部分的作家论写得很好,是那种能把活人气死,把死人气活的好~
●仿佛一个醉酒又狂提精神的人在耳边絮絮叨叨磨磨唧唧东一嘴西一嘴的说着与他有关的一切,从社会现象到身边朋友的糗事,戳破了虚假的彩虹屁。看他的碎碎念惊呼终于找到了在同一个频率的人!可是,看他某些文章中反反复复的车轱辘话又很着急,他的表达配不上他的思想呀!要是他能写的再精确些,或许是一位改变文坛的人呢?
●果然,坂口安吾是对的上我的电波的www
●和太宰治半斤八两吧,颓废的立场不同,坂口更高傲些、更皮一些。
●片切鱼生的时候,刀很重要,要锋利。但更重要的是拿捏的厚度。要稳,要精,要准。 通篇看下来,刚开始感觉作者的刀是挺快的,没有那么多枯燥的形容词,很喜欢。 但时间久了有一点糟心的感觉,说好听一点,“不慕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 说难听些,他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世界就不再看了,选择了闭上眼。 同样他看问题也是,答案有那么多,但他只看自己想看的答案,就不再看了 中二之魂可能不光是燃,一多半得先把自己弄惨,骨子里你就得觉着自己就是待在一个特别惨的环境里,不然没法抗争,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抗争吧,反正不抗不足以显示我牛逼,不抗我就难受。 我想作者应该是有创造欲的,他也崇尚创造,但他只剩下了品味,品味是会拒绝其它人的。 所以他有些章节很有趣,有些也挺糟粕的 不过他的刀够快,看的不算累,好书
●坂口的美学是“闹剧”的美学。抓住牙医的手臂来上一句“能用原子弹转眼之间弄死上百万人,一个人的牙疼却镇不住,文明何在?混蛋!”。面对太宰治的死非要说人家是喝醉了被酒量好的情妇哄骗了。就连对新作剧派普遍的忧郁他都要调侃一番。完全是闹剧的美学。战时在电视台这种宣传口看了不少佯装正经的荒谬事,才能在战后把严肃、禁欲、忍辱负重捣碎了熬成了一碗教人堕落的毒鸡汤。不堕落就不是人,不允许人堕落的国家就是非人的集中营。
●丧逼的圣经。
《堕落论》读后感(一):《堕落论》坂口安吾
坂口安吾是跟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代表作家,只不过用三岛由纪夫的话说就是“太宰治被视为圭臬,而坂口安吾则渐渐被大家遗忘,就像石头浮在水面,叶子却沉下去的事情一样。” 《堕落论》是坂口安吾的随笔集,共17篇,在其中探讨自己对日本文化的看法、对青春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甚至对人的看法。 坂口安吾够锐利,不留情面地撕破那些人们自我安慰的虚伪假面。 既然是跟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大家想也知道他的风格,只不过越读越觉得其实坂口安吾跟太宰治还是不同的,虽然也有“想要回归乌有”的时候,但他大部分时候还是觉得人活着才是一切。 他不止一次在文章里面提到活着的重要性。 这本书的最后他写:懂得了这种绝对的孤独之后,至少要走完自己的生命全程。 他说自己无法乐观,但是字里行间却不停地在说要活着。 书中一篇随笔名叫《不良少年与救世主》,他这么评价太宰治:他到了四十岁也还是个不良少年,没有办法变成不良中年、不良老年。 他说:文学家的死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说死是随时都能做的事,这种随时都能做的事不应该做。 坂口安吾挺有趣的,颓中带点儿皮。
《堕落论》读后感(二):意外深沉的坂口安吾
四星半,这本书的加分部分大多在后半。坂口安吾挺啰嗦的,还皮的很,你要全神贯注咀嚼他的文字才能从中提炼观点,偶尔感觉索然无味,但好在其观点还算新鲜。他认为崇尚武士道精神、崇拜天皇,都是人堕落的表现——因为变得堕落,所以不得不给自己竖起了”道德“的标杆(想起卢梭所说的:人因社会契约而失去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一切对其有诱惑力和其所期待的事物的无尽权利);认为人生充满欢乐也是无趣的,因为当欢乐无处不在,那就等于没有欢乐,”活着就是一切“;对家庭和“良妻”与“恶妻”的看法很是鲜见;对夏目漱石“没有进行过诚实的自我追求”的批评也让我看的一愣。他百无聊赖的行文风格下居然还有深沉的存在呢?不过说起“百无聊赖“,太宰治比他更为严重,一篇《樱桃》已经使我对太宰治无可救药的无力感而感到绝望啦。 坂口安吾对于“闹剧”的解读倒是令我耳目一新。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喜剧的品格和精神要低于悲剧,至于闹剧,我甚至从没有注意过——那种狂欢乱舞的全员参与、故意夸大的不切实际的性格,种种巧合凑在一处的生拉硬扯,我总认为其太过粗糙而不予关注。但是读了坂口安吾对闹剧的理解,我的观念有所动摇了。闹剧之“闹”的程度拿捏不好,的确会降低它的文学价值,但若拿捏得当,却能将悲剧的泪水巧妙化解为欢闹的讽刺与捧腹,从而在作者那一视同仁的冷漠中,感受到其悲悯的态度。 坂口安吾在最后一篇随笔《关于男女交际》中讲到:”人生、生活就是从这种梦幻世界终结的时候开始的。实实在在的冷酷现实就是人生,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开始真正规划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虽此处的“梦幻世界”指男女爱情,但这话放到人生的任何一面都有其价值。我喜欢说自己“还是个孩子”,但我心里知道其实并不是那样,我如此说,只是对世界的逃避,就像音乐剧《如果爱》中的歌词:梦里有梦,都不要醒。
《堕落论》读后感(三):活着,然后堕落
1946年11月25日,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太宰治三人曾受邀参加一场文学座谈会。虽然织田作之助迟到两小时,到场时坂口安吾和太宰治早已喝醉,但三人依旧相谈甚欢,甚至三个人散会后又跑到银座重开续摊,大概就差盖上被子抵足长谈了。 那一年坂口安吾40岁,太宰治37岁,织田作之助33岁,时至中年的三人是当时“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人物。然而1947年织田作之助就因病去世,1948年太宰治也成功自杀,只有坂口安吾强撑到1955年。 三个同为“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又是“晚年”的至交好友,因此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三个人的堕落是相似的,一如我之前试图通过织田作之助去看清太宰治。 但太宰治和织田作之助是不同的,坂口安吾和另外两人也没什么相似之处。三个人唯一相同的只有向传统社会吐的那口唾沫,以及吐完唾沫后选择的堕落。 堕落或者颓废是“无赖派”文学的基调,是这群小说家去自虐自嘲、反抗传统的方式。然而地基相同,建筑物却可以千姿百态,三个人虽然都选择堕落,但眼中的“堕落”却千差万别。 在我看来,太宰治的堕落,是把旧文化、旧道德推进粪坑,然后紧接着把自己也溺死在里面;织田作之助的堕落,是趴在地上苟延残喘,寻找艰难生活中残存的幸福感;而坂口安吾的堕落,是把虚伪的旧观念、旧道德砸个稀巴烂,再去寻找更加积极度过人生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不同于太宰治和织田作之助选择用堕落去逃避现实或者苟且偷生。在坂口安吾看来,所谓的堕落是行与传统观念相违背之事,是与旧道德为敌的勇气,是挣脱旧社会束缚的方式。 坂口安吾看不上日本的传统文化,就像胡适看不上除墨家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大抵是因为两人都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而他们评判“实用”的标准,就是能否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所以胡适在《容忍与自由》里把老庄学说、孔孟之道都骂了个遍,因为老庄学说主张不问世事,而孔孟之道看不见民主和自由,全然不利于社会进步。 而坂口安吾则把枪口指向在日本传习千年之久的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思想。所以他先在《堕落论》里批判武士道,然后又在《续堕落论》里批判天皇制,而全书无一短篇没有透漏出他对日本传统文化的鄙夷。 在坂口安吾看来,这些所谓的传统文化都是政府为奴役人民而创造的违背人性的东西。他们把顺应传统的行为扣上“美德”的帽子,把违背传统的行为贬低为“恶德”,然后两极分化中,违背传统就变成“堕落”。 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从来如此,便对么?”,而坂口安吾看到这“从来如此”错的一面,所以在《堕落论》里呐喊“因为生而为人,所以才堕落”。 在坂口安吾眼里,传承千年的制度不过是蛊惑人心的骗术,天皇不过是统治者为使自己命令合法而创造出的傀儡,武士道也不过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创造的工具。它们都只是精心伪造的骗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 而且所谓的传统观念还充斥对人性的违背和对社会进步的阻碍,武士道鼓吹忠诚和为主而死,看不到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欲望。对女性贞洁的崇尚,导致禁止寡妇再婚却忽视性欲的需求。对吃苦耐劳的吹捧则导致技术停滞不前,因为是对效率而不是劳动的追求,才催生一代代的技术革新。当社会禁止人去满足欲望,妨碍人去寻求便利,选择堕落几乎就成为必然。 更重要的一点是,时代一直在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弊端会被不断地放大,传承已久的制度、观念、艺术、技艺都会逐渐无法适应变化的社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它们的存在就变成社会进步的阻碍。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两种,更新或者淘汰,但在卫道士眼里,无论哪一种都是对传统的叛离,都是堕落。 因为生而为人,所以才堕落。因为社会需要进步,欲望需要满足,所以坂口安吾的堕落是一种生活的必然。他的堕落即是对传统的反抗,又是对天性的解放。 所以坂口安吾眼里的堕落是社会进步的方式,是他的“实用主义”的结果,就像他在《青春论》里称赞宫本武藏的剑术不拘于形式,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去获取胜利,因而是进步的、实用的。 而堕落之于坂口安吾就像剑术之于宫本武藏,是抛弃无用的旧传统的束缚,去寻找更好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社会进步的契机就藏在这种可能性之中。
《堕落论》读后感(四):“堕落”又何妨
坂口安吾的“堕落论”在战后的日本显得惊世骇俗,他在《堕落论》一文中写道:“特攻队的勇士只不过是幻影,他们不是从成为黑市商人的时候才开始成为人的吗?圣女般的寡妇也不过是幻影,她们不是从心中思念新情郎的时候才开始成为人的吗?天皇或许也不过是幻影,真实的天皇的历史说不定会从他成为普通人的时候开始。该堕落的时候,必须实实在在地一头扎下去进行堕落。”而在今日,对于那些拘泥于传统和所谓“道德”的人来说,他的“堕落之声”也振聋发聩。
其实,坂口安吾所说的“堕落”,指的是遵循自然,释放天性。他眼中的人之常态应该坦荡、真诚:“人的、人性的正常姿态是什么?想要的东西就老老实实地追求,讨厌的东西就光明正大地讨厌。仅此而已。”(《续堕落论》)所以他鼓励神风特攻队员应大胆地去做黑市贩子,寡妇应该放手去思恋情人。相比在人性驱动下最终违背“道德”,还不如早早地甩开“道德”。这样反而显得更诚实,自始至终不存在背德——既不认同其为道德,又何曾背叛呢?
的确,对道德的认定值得商榷。道德产生于环境和时间,当二者发生改变,道德也随之变化,可能成为“恶德”。坂口安吾举“吃苦耐劳”为例,认为在科技和智慧尚无法改变的艰苦环境中依靠人力艰难跋涉,是无可厚非,值得推崇的;而在技术成熟,有机械可以迅速、优秀的实现目的时,还通过步履维艰的方式操作,并奉其为“美德”,则是在倒退,在欺骗。
美德之美在于内,而不在外。“为了美丽而美丽总会显得矫饰,归根结底无法称其为真实。那是空洞无物。空洞之物绝对无法凭其真实的空洞打动人,最终只能沦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他又提出了更令人咋舌的理论,认为法隆寺(寺内有世界现存最早木结构建筑)与平等院(日本著名木结构建筑)等日本古代建筑瑰宝悉数焚毁也“无关紧要”:“京都和奈良的古寺哪怕焚烧殆尽,日本的传统也照样岿然不动,连日本的建筑也照样毫发无损。如果还需要的话,可以重新再建,盖成那种简单的临时房屋就够了。”(《日本文化之我见》)
虽然坂口安吾的论调略显偏激,但他其实是在替人性和自由摇旗呐喊,用“过正”的手腕来“矫枉”。他大声疾呼是因为此前日本的人性被压抑、囚禁过久。特攻队员、守节寡妇、天皇被长期奉为典范,也因此深陷其中,但他们的本质都是人,当武士道、贞洁规范、神化偶像被时代的洪流冲倒,人的本来面貌则在洗刷之下显露出来,这时去指责人的本貌而赞美面具是虚伪、荒唐的。武士道、贞洁规范、天皇制度是反人性和反本能的产物,但同时又是参透人性和本能的设计,是编织的骗局:设计者正是认识到人会对制度和规则产生“背叛”,才制定它们以操控人的行为,给予人性强大的压力,使其困于桎梏。
然而,人不会永远困于制度和规则的枷锁当中。对此,坂口安吾有个形象的“鱼、网比喻”:“政治、社会制度是一张网孔很大的网,人是永远网不住的鱼。”(《续堕落论》)既然制度的制定建立在约束人性的基础上,那么也就埋下了人性突破制度的伏笔。人性的突破,或者归结到底的说是欲望的释放,可怕吗?毕竟,所有制度、规则、道德等“渔网”的编织,都出于对欲望的不信任,担心欲望泛滥后人类“永恒堕落”。
从《关于欲望》中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意在宣扬撕破渔网。他承认欲望要为制度和秩序做出牺牲,但反对隔离和恐惧(难道可怕的不是囚禁欲望的制度和秩序本身吗?)欲望的做法。在他看来,秩序应该不断修正,向满足欲望靠近,这时,文化与生活不但没有堕落,反而因为真实更显出人性的光彩。
对于“永恒堕落”,他在《续堕落论》中用悲观而又宏大的思考解决了这种可笑的担忧。他认为“人能够堕落的程度实际上出奇地有限”,因为“人并不具备足以无止境地彻底堕落的顽强精神”,更何况,在人类的永恒历程中,个人的生命是如此有限,“堕落”从根本上已没有“无限”的可能。在无限的时间面前,每个人的“堕落”充其量是对未来的轻微扰动,而坂口安吾为“堕落”而高呼的尝试,则只是扶起蜷缩一隅的人性,引起小小的“共振”而已。
如此来看,“堕落”是何等急迫,“堕落”一些又有何妨?
《堕落论》读后感(五):关于欲望——普列沃斯与拉克洛
我以前就对所谓家庭抱有疑问。也许想与所爱的人组成家庭是人的本能,但是否不管情不情愿,都必须心情压抑地至死守护这个家庭?这就是美德?为什么?我强烈地感到,这与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一样,与其说是美德,其实更近乎恶德。
许多人的家庭是个快乐的居所,而我更觉得它像间牢房。就跟吃苦能成为一种美德一样,人们已经被迫习惯了阴郁的家庭就是美德,习惯了忍受它的阴郁,习惯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就是从家庭的阴暗中找乐子。不过,我只觉得这是“被迫习惯”的。
我喜欢曼侬·莱斯科那样的娼妇,喜欢天生的娼妇。曼侬没有家庭、贞操这种观念,没有守护它们就是美德、破坏它们就是罪恶这种观念。她只想要奢华欢乐的每一天,无法忍耐阴郁的生活。
向男人献媚便是她的道德意识,甚至是她的辛勤劳动。她以此获取合理所得,因为她要维持每天的欢乐生活。
也许远古时期人们就是那样欢欢乐乐度过每一天的。大概是感到没有秩序难以共同生活,所以才出现了社会生活。我觉得,许多东西为了建立秩序而牺牲了,人们在物质、精神上相互争斗、相互影响,善恶美丑、灾祸幸福的本来面目都变得混沌难辨,最终形成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形态。人生是什么?或谓之曰:一言难解。可依我看来,是一言难断。我决不会断言家庭是丑恶的,因为我无法断言。这个问题在我有生之年大概解决不了。
总之,人类虽然需要社会生活的秩序,但秩序必然伴随着牺牲,因此不可能找到一种能公允平衡这二者的公式,只能寻找比现有秩序“更好的形式”。所谓绝对、永远的幸福形式是不可能有的。
我讨厌什么勤俭节约、吃苦耐劳。我认为劳动是为了玩乐,坚信对美好、便利、快乐的追求是人的天性,没有理由排斥或扭曲这种天性。不过近来我感到玩乐也非常乏味。真正能够抚慰我心灵的“玩乐”,我在现实中还没有发现,也不知道有没有。
《曼侬·莱斯科》的作者普列沃斯的本职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他这个思考上帝、绝对和人类幸福的神职人员去描写天生的娼妇,将那种恶德描绘成人间的最佳美果,我觉得也许是再合理不过了。曼侬的天性也是一般女人隐藏着的天性,在考虑天堂的幸福之前先追求地上的幸福很合理。然而,人几乎生来就是在为上天堂而不断牺牲着地上的自己,一个神职人员对这种训练、习惯和秩序的反叛和质疑,是思想正常发展的阶段,丝毫没有不合理。不质疑、不反叛反倒不可思议。
人的动物性不可能靠社会秩序这张网拯救得了,它无论如何都会从这张网里钻出来。我们因为无法靠这张网拯救这种动物性,所以将它称为恶德。然而,社会生活得以拓宽、文化得以进步,与其说是秩序使然,倒不如说更得益于恶德。
日本军部说欧洲文明是堕落也并非毫无根据。假如人类把重心放在人的社会性上,想要靠秩序将人完全绑住,那就会变成丧失个性、以制服来取代个性的武士道那样,变得像武士那样的统一制服中非人性的生物;或者像小笠原派礼仪中的武士女儿、妻子那样,变得既不是女人也不是人。人的欲望会被禁止,吃苦耐劳会变成美德,自我被强迫放弃,不得不对别人忠诚。这是蚂蚁的生活——战争中的确有军人命令部下要以蚂蚁为榜样,像蚂蚁那样去干活。
假如人开始思考自我,自然就会先思考自我欲望与社会规范束缚间的摩擦和矛盾。所有人都会思考,日本人也不可能例外。但人们一般都会觉得,是自己错误地怀疑了古老的习惯道德,他们会考虑“成熟的”做法,让自我欲望屈服,与古老的习惯、道德同化。他们觉得自己死心后的这种安宁兼具了真善美,是对人真正的最后安慰。
不幸的是我生来就无法这样思考。还没结婚,我就对家庭、老婆的阴暗感到绝望,心里琢磨着(像曼侬那样的)娼妓的魅力,非要搞清楚为什么娼妓是恶德。这种思考有失老成,傻乎乎地越来越偏离到秩序之外。但上述问题我并未搞清楚,至今仍然一头雾水。
普列沃斯发现的这种近代型娼妇至今仍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繁衍生长,连于洛男爵那样不惜自我毁灭地冲向这种娼妇的人物也出现了,作家们也主动对那种反动的淑德开始了新的探索。不过,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他虽然喋喋不休地舞弄传统观念,对所有背德行为横加指责,却由于“脾性”上的原因,无法更多地接触这种娼妇。所以他作品里的娼妇大都与日本一般常识中的一样,也是些由于贫穷而不得不卖身沦落于污泥浊水之中的苦命女子,也是些饱受摧残蹂躏的人。他笔下也会难得出现《赌徒》中的女大学生和勃朗西小姐那样的人物,但他对那种天生的娼妇性格并未从人自身的本质出发进行过真诚的探讨。他在脾性上很疏远这种女人,因而观念中有许多不严谨的地方。不过,当时的俄国到处是与现在日本一样的穷乡僻壤,大概现实生活中也还没有这种出自文化侧室的天生娼妇吧。然而,观念也不应该被这种现实限制。
在日本,美丽的是风景,是向庭园倾注爱情。而人的正常欲望被扭曲,清心寡欲取代人性成了日本人的第二本性,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更愿意把爱情寄托于风景而不是人本身。然而,对人来说,不可能有比人更美的东西。
曼侬虽然热烈地爱着她那个年轻情夫,但她本来就没把妩媚地蛊惑别的男人并出卖贞操看作对贞节的背叛。为了过上奢华欢乐的生活,妩媚就是最佳商品。曼侬有着最好的商业道德和良心——这良心就是出色的媚态,与贞操没有关系。贞操只存在于精神,作为物质则分文不值。娼妇的思维建立在彻底的物质主义基础上,对丧失贞操之事不会有罪恶感。它只是对“让男人无比高兴”这件事合理地要求高昂的报酬。曼侬·莱斯科直至其薄命一生的最后关头都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情人,这其实是普列沃斯神父对常识性道德的小小贿赂,因为世间的真实情况大都不会这样。曼侬的不贞不能用对一个情人始终不变的热情来将其道义化。假如能够道义化,也只能通过其自身的本质来体现。
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为这种天生的娼妇赋予了高贵身份(侯爵夫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对曼侬来说盲目的事情,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性,也就是说,这本小说描写的男女交往有爱情游戏这一明确的人生目的。在侯爵夫人看来,爱情游戏获得的满足不仅是肉欲的满足本身,它存在于漫长的游戏过程中使用的勾引手段、离间技巧和各种知识里,因此,她观察、研究了这所有一切。这本小说昭和初年曾被翻译引进作为限定发行量的淫书出版,对爱欲的追求越诚实,自然就越接近淫书的范畴,所以这部作品时至今日还无法预计何时会在日本公开发行。即使以前所有书都被我处理掉的时候,这本原版书我也保存得很好,可是小田原发的洪水却把它冲到太平洋里去了。
这种对人性的追求永远无法与“家庭”相容。虽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不道德的,但“家庭”究竟是什么呢?人们为了家庭就应该抛弃对这种游戏的欲望吗?想来,我们阴郁的家庭大概绝没有必须如此永远守护下去的价值吧。我们的家庭无论外表还是内涵都有不少应该改变的缺陷,不可能一发生有碍家庭稳定的事就意味着不道德。
通行的道德未必是美德。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有悖常理的“不道德”未必是不道德。与那种通行的道德义务相比,人性的真实里蕴含着永恒的生命,它是任何利器都无法杀死的。
为了秩序,欲望不得不做出牺牲,但有欲望并不是恶德。我们的秩序向满足欲望的方向靠近绝不是堕落。我反而觉得,在秩序向满足欲望靠近的地方,文化和生活会真实地成长,它或许意味着“追求人性”的文学目的也是一种有益于这种生活成长的反思手段。
人们厌恶肉欲、情欲的露骨展示。然而,既然它真的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就没有应该厌恶的理由。
我们必须先认真想一想,玩乐不是不健全,也不是不正经。就我自己来说,我虽然无法断言玩乐是人生的目的,但要我说出其他什么人生的目的,我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玩乐”本来就是“无所事事”的同义词,人靠玩乐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然而,我只能说,“想玩”表现出了人的欲望,这也是事实,只是这种欲望的实现未必会带来人真正的幸福。人想要的未必总是能满足,事与愿违的情况很多,曼侬和侯爵夫人也绝不是幸福的人。与无所事事的安稳幸福相比,满足欲望的事大概反而会带来比幸福更多的苦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也许是追求苦恼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