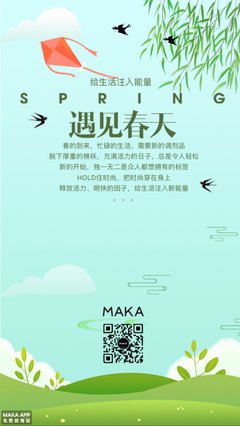误读的读后感大全
《误读》是一本由[意] 安伯托·艾柯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2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觉得有距离感。 要不是第一篇《乃莉塔》把我笑翻了,我估计都不会看下去。
●牙尖嘴利,不错不错
●你送我的这本,才拿出来好好看一遍。
●①哈哈哈哈哈;②艾柯是真爱纳博科夫啊,每本书不调笑他就不舒服;③某种意义上说这位也是个蛇精病短篇爱好者(#根本不用某种意义就是个蛇精病好吗#
●比带着鲸鱼去旅行更可读
●绝对的kuso神作啊,虽然提到的很多书都没看过= =辛苦译者了,拜
●真是误读,翻完了,除了第一篇章那个对OLD LADY有性幻想的年轻人的故事外,其他的篇章都不知道在说啥,而且完全无印象了。而且那个故事其实我也不知道在说啥。
●简直是群鸦的盛宴:)
《误读》读后感(一):一个误读
智力探险,炫技之作。此番屠龙之技,博学如博尔赫斯惯用此招,当然,这也不妨碍伍迪艾伦偶尔玩上一把,在《门萨的娼妓》里,他玩得可嗨了。
艾柯的同类人,一样渊博的钱钟书在《一个偏见》里说,“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 娱乐。”,把“偏见”换做“误读”,是很适合这种parody集子的。
多少读过他的书的朋友都知道,艾柯喜欢也善于在字里行间编织出巨大且精密的知识网络,并不时将各国语言、生造字和复杂的语法结构穿插其中。这不仅使读者常常难解其意,译者翻译时也是如履薄冰,苦不堪言,最终让人罹患知识密集恐惧症。而《误读》可谓是他作品里炫技的个中皎者。
《误读》里的文章多是1960年代所写,最近的不超过1972年。这时的艾柯正直壮年,处于锋芒毕露的时期,具有强烈的文学表达欲和讽刺欲,并在新先锋派的文学讨论中获得灵感(虽然艾柯暗示对其的仿讽,但显然他在写就的时候也乐在其中),因此我们在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到许多学术性的,对当前社会进行讽喻的实验性作品。
通常文人炫技容易让人厌恶,可是艾柯这样做却让人恨不起来。这倒不是因为他名声在望,而是这般文字只有艾柯的如椽大笔才能著就,称其是“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的学术集大成者绝不为过。对于这样“知识爆炸性”的大家,如果不尽可能的把学识倾囊而尽,想必会憋死吧。
事实上,相比于《误读》,我更倾向于艾柯90年代的文集《密涅瓦火柴盒》。尽管受体裁的限制(《快报》专栏),《密》的文字更加精简,无法像《误》那样展示其生花妙笔,但是二者立意的对比还是很好的体现了艾柯思想的转变。
在《密》里,艾柯的文字更加直白,甚少引经据典,文笔也趋于严肃犀利,对事看法也十分理性和透彻。而《误》作为早年作品,在体裁上不落窠臼,但更加随心所欲,甚至有些意识流。尽管其中文章讽刺意味浓厚,但对自己的观点的阐释却过于含混不清。在体裁虽颇吸引人眼球,但是行文到中间经常有些顾左右而言其他,虽引用大量华丽且有深意的典故,可主题思想又常为此所累。例如我最不喜欢的一篇就是《给儿子的信》,感觉行文似“为写而写”,堆砌感较重。
相比而言,《误》体现的更多是艾柯在学识上的渊博,远不是思想上的深刻。但这不能表明《误》是不成熟的,事实上,《误》的文章可读性很高,构思也十分精巧有趣,哲理也阐释的很有见地。虽然《误读》看似以诙谐之笔仿讽社会百态,学术兴味浓厚,但因为这算是艾柯的玩兴之作,纯粹以趣味作品来读也无妨。
《误读》读后感(三):艾柯,回声
安伯托 艾柯 在2016年的2月19日逝世,那一天是节气雨水。
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才发觉我有好几种艾柯呢,春节假期整理书柜,五六种正好和伍迪艾伦的几本放在一起。这俩老头在我脑子里有点混淆,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但是在荒诞不经下又透出真知灼见来。
买的第一本艾柯是三联的《带着鲑鱼旅行》。天马行空,脑洞清奇。后来陆续买了误读,别想摆脱书,玫瑰之名,开放的作品和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记得悠游小说林看过。但是这回整理没见,内容也不记得了。看他的介绍很多的头衔: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等等,因为先看的是带着鲑鱼旅行,看他的书怎么也正襟危坐不起来,总有点谐谑的味道。别人老生常谈的东西在他那里总有新的意思,历史的未来的杂糅。当然他著名的推理小说,玫瑰之名我只读了100页还是败下阵来,不读了。别想摆脱书是对谈,基本就是书籍印刷史了。
对他的纪念大概就是再读他的书了。误读不厚,只200多页,开本不大,正好可以在旅途中读。所以从2月23日起,这本书一直在我的包里。跟着我到杭州到南京到徐州,在高铁上在车站在旅馆都会拿出来读一点。但每次都读不多,一篇半篇的,看他戏仿纵论古今。乐不可支。也有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所以这本小书直到4月初的清明小长假才读完。
接触的越久,佩服与日俱增。不管他如何着笔,他身上的深厚学力在字里行间喷薄而出。我越读也是越伤感,原来古往今来一切都没什么 变。也许工具在变,但是人还是那些人啊。
印象最深的是《那东西》,当年的石斧不就是现在核弹?科学家对自己的发明束手无策,被蛮横的军人所用。哪个时代不都是那样?真是伤感啊。
是从《大限将至》看出不是胡说八道,不是逗你玩儿啊,他真的大学者写小文章,可是我觉得这世界真的不好了。越看越悲伤,哪里有什么新的希望有乐土!
也许是年龄大了。看什么也带着自己的有色眼镜了。
也许哪天我去尝试玫瑰之名。不过在我看完已有的艾柯之后。
《误读》读后感(四):让学术和流行文化狼狈为奸
依旧是艾柯,他最轻松得意的风格,或者说是懒散调皮的发挥,同《带着鲑鱼去旅行》一样,《误读》同样为1959年以来艾柯为“咖啡馆”杂志“小记事(Diario Minimo)”栏目每月写下的文章,内容皆为模仿,嘲弄和调侃他人作品,就社会和生活中的事情进行知识分子式的过度阐发,无一不是蓄意插科打诨,兼卖弄知识的玩笑之作。
读完此书,不得不服气大概也只有艾柯这样的人,热衷于把严肃的学术知识和肤浅玩笑的流行文化拼接杂糅在一起展示给读者,大名鼎鼎的《玫瑰的名字》便是一本借助悬疑犯罪小说的框架杂糅了20世纪学术界时髦话语,用自身擅长的符号理论为学术界奉献了一道轻松又不失内涵的文化大餐。自然,艾柯作为一个学者,并非是想要浮夸的表现自身掌握了多少知识,看了多少他人不知道的书,用别人不懂的观点和对生活中平凡现象的的过度阐释来彰显自己多么渊博和厉害,当然不容否认的是,他擅长并享受这种炫技式的写作,但更多得是,他想要用一种通俗文化和严肃学术杂糅的方式,以解构主义的风格来瓦解学术和知识的权威感,“幽默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他用自己对知识的蓬勃兴趣和从中得到的乐趣,来告诉普通读者,学术和权威并非那么不容侵犯高高在上,而生活中看似乏味平庸的小事也未必就没有内在的更多启示,换而言之,他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经过冲淡和包装来服务大众,仅仅是为了让人会心一笑。
然而普通读者也万万不可冲动就买了这本“幽默小随笔”,它很大程度终究还是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理想读者”而作,简单地说,他取悦的这样一类读者:他们热爱文学和艺术,对柏拉图到康德,从荷马到乔伊斯有着简单的了解,但并不深刻到通透,而是心中知道它们的某种“地位和牛逼之处”,他用你熟悉的文学和经典,熟悉的典故和哲学为材料,经过自身知识的加工和搅拌,奉献给你,这些文章充满了对你所熟知事物的吐槽,不断的在严肃和轻松之间撩拨你,让你在看到熟悉的人物和情节时会心一笑,并说:“太对了,我一直就是这么觉得的!”然而终究是本人的学识有限,对于其中诸多的学术界时髦话语,那些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的笑点并未能一一把握,而艾柯对于将学术和流行文化融合的尝试或许也并没有他所能想到的那么成功,或许是语境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这便不得而知了。
第一篇《乃莉塔》便是对经典轻松误读的优秀示范,艾柯把少女洛丽塔置换成了老太婆乃莉塔,原文故事大纲都保持着原有框架和逻辑,每一个熟知纳博科夫的读者想必都会为这种无伤大雅的调皮和小幽默所感染。《碎片》同样是一篇范例,将流行文化进行文化学上的过度阐释,满大街被知识分子不屑的流行歌成了《诗经》一般的古典名著,从中被挖掘出了诸多所谓的先民的生活图景,这是许多人在对经典暗自开玩笑时都有过的心态,但艾柯娴熟的把它变成了现实。《很遗憾,退还你的》更加疯狂,直接肆无忌惮的以现代商业文化的视角点评了《圣经》,《奥德修记》,《神曲》,《堂吉诃德》以及康德,卡夫卡等人的作品,《新猫的素描》则在形式和写作风格上完全模仿了格里耶的新感觉派小说。剩余的文章在我看来便不再如前面几篇如此轻松精彩,它们要么开始晦涩,诸如《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与性压抑》中对于政治,人类学,拓扑空间以及工业与宗教的巧妙描述,《大限将至》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对雅典文化的大众化庸俗化的阐发,《拍自己的电影》和《我的夸想》两篇文章对于不熟知诸多意大利大导演和乔伊斯《为芬尼根守灵》的人来说恐怕将是难以卒读的。而对于《苏格拉底式的脱衣舞》中对于社会和心理学的揭示,《天堂近讯》,《那东西》,《给儿子的信》里对于政治,战争的调侃都未免过于轻巧和简单,虽然也时时会心一笑,但并不让人眼前一亮。
艾柯始终坚持运用着自己擅长的文字游戏,为流行文化和学术之间搭桥,往往犀利幽默的对经典进行反意解读和庸俗化诠释,而对于流行文化也反其道而行之,进行高端的知识包装,不知他这样是否会产生一种异装癖般的顽皮快感。《误读》顾名思义是对经典文本和学术理念的故意歪曲和过度阐释,这样一种故意如同裂开的枝丫,对每一个充满“可被阐发性”的点进行解构,并生出更多分支,最终得到解构主义的目的,瓦解权威,释放压力,带着读者走向一个多元和衍义的开放文本世界,正如他本人所总结的:“这恰恰是反讽体的宿命:绝对不要怕走得太远。如果目标正确,他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极其庄严自信地向人们预示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而无须有任何愧色。”
《误读》读后感(五):小记事,大思考
没人在意白色封面上,一个简单的羽毛图案是怎样。重要的是安伯托·艾柯所记述的小记事之一《误读》。光看目录就能够让人眼花缭乱,这本书确实让人产生了不少思考。
艾柯一个细致入微的作家,从《玫瑰的名字》开始,就能知道这个作家非同凡响。他能够将虚构现实化,他用严格条令来约束自己的行径,对于每一个文字和场景化,都必须做到真实。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从桌子到桌子的距离,是五步还是六步,从桌子到人的一端是七步还是八步,他都会一一求证,并做出相对应的表述。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连楼梯的阶层,都能一一告诉你,从第一阶到第N阶之间的故事。
《误读》这本书,一共分为十五个篇章。从多个角度进行事件阐述和表明。用艾柯一贯的写作作风来诠释这个目录就是:乃莉塔、碎片、苏格拉底式的脱衣舞、很遗憾,退还你的......、新猫的素描、天堂近讯、那东西、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与性压抑、大限将至、给儿子的信、三篇古怪的评论、发现美洲、拍自己的电影、迈克·邦焦尔诺现象学、我的夸想。这已经把整个目录,赤裸裸地罗列出来。
这本小记事中,充满了各种名著和经典,亦有那些仿讽性、引用性。诸如《乃莉塔》就是仿讽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同时作者也在主人公名字上做了一番文章。艾柯的博学与直接简直高不可攀。他信手拈来的文本,多得几乎快装不下这本窄小的书本。隐喻性,也是他常用的技巧,还好有译者的备注与解释,否则光从典故和引用中,我们就得看上大半天。
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不过两百来页,但也绝非是一个下午能轻松对付的。里面充斥着艾柯最“严格”的批评和指点。对于某些经典书稿的品读,有其独特的艾柯思想。见鬼去吧,那些颠三倒四的文字,实在太不容易理解了,但显然,这并没有摧残人们阅读它的乐趣。
一个爱上“老妇人”的年轻人,这是多么反常态的一件事,艾柯也这样想,所以有了“乃莉塔”。
“碎片”中的记忆,让我把秘密图书馆这样的字眼给保留了下来。我喜欢这篇文本。
“很遗憾,退还你的......”的文章。里面讲述了艾柯在审稿过程中给的报告文,里面点评了包括《圣经》、《奥德修记》、《神曲》、《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泄露隐情的宝石》和《修女》、《朱斯蒂娜》、《堂吉坷德》、《约婚夫妇》、《追忆似水年华》、《实践理性批判》、《判决》、《为芬尼根守灵》等作品。作者点评得面面俱到、体无完肤,这些经典都被退回去了。
“新猫的素描”这就是那令人惶恐的精细。“从屋子的一角到桌子,6步。从桌子到后墙,5步。桌子对面有一扇开着的门。从门到你锁在的那个角落,6步......”慢慢领会艾柯的精细与微妙。这篇强势构建了一个房间地图,并伴随猫产生的故事。
“天堂近讯”一个牧羊人发现了一个记者的尸体,报社证实他是被派到某地执行特殊任务,但该报社拒绝透露任务的性质。国务院发布了新闻封锁条令。然后随着这个谜团展开了一系列故事。
“那东西”我无法诉说这个故事有多么精彩,但看得我心惊肉跳,尤其是最后的结局,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与性压抑”一些假说、遐想、现象悖论、对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解读。
“大限将至”关乎逻辑与艺术。
“给儿子的信”我们无法想象,艾柯竟然能在这里用一整页来从头到尾的来描写武器,他给儿子的反常规指导,也令人印象深刻。
“三篇古怪的评论”的确很古怪,先是对文化浪费与社会浪潮、审美消费等做了一个评点。其次是论《女性家庭杂志》,最后评点了D.H.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发现美洲”这是一篇访谈性文章,讲述了几个人在用自己的观点对发现美洲进行观点阐述和表达。
“拍自己的电影”,艾柯用大篇幅的文字,描写了电影脚本以及可变化的索引。
“迈克·邦焦尔诺现象学”毋庸置疑艾柯评点了一种“抄袭”的现象,麻醉剂这一词怎么样。
“我的夸想” 关于艺术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画像遭到嘲笑重新复制的一种虚构努力,艾柯评点了一些书籍,并进行了分析、假设。
好吧,我想我用了太多篇幅来描写,实际上没必要将目录一个个都写出来,但为了让你更了解这本书,我想我还是有必要大概的写一写,它们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感兴趣的人,定会主动去了解。艾柯在每一篇里,都穿插进了一些引人深思的话题,诸如年轻人爱上老妇人的伦理问题,关于图书保存的历史性问题,哲学经济学等相关问题......
如果,你喜欢写作,兴许你和我一样,能从里面看到艾柯的几条对我们的教诲。小记事,大思考。我还没彻底将它们读懂,有时候,我只是觉得我会不会是“误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