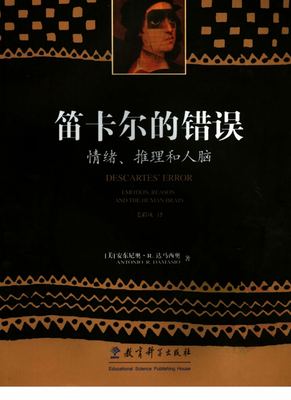笛卡尔的错误读后感锦集
《笛卡尔的错误》是一本由[美]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著作,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90,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继续刷第二本
●笛卡尔不知道演化论而已。偏学术,想提高情商改善生活直接读实操类的书吧。
●一般 写的乱
●原来以为是哲学类科普,没想到是神经认知科学的科普,也算是我会感兴趣的题材但基础太差看起来好像有点吃力
●好书,翻译减分,湛庐的书果然要三思而后买,毕竟不便宜。很多名词前后不一致读起来非常困惑。
●正如书名而言,本书主要围绕着心物二元论的错误展开。主观和客观一体,心不能脱离肉体存在,所以不存在一个抽象的自我,自我实际上是身体对于外界的映射的统觉。这本书对于主观唯心哲学家来说是一记重拳,哈哈,似乎名字改成黑格尔看招也完全不违和。扣分的原因是内容不过丰富和深刻,当然篇幅也不算多,所以时间浪费的程度也还能接受。如果你对具身认知和心物一体有疑惑,强烈推荐阅读此书。如果你都知道了,和我一样,泛读即可。
●我可以理解成,所谓的理性是不存在的吗?尤其是移植到社科领域的理性,毕竟理性所要实现的目标、利益最大化本质也是感觉、情绪等基本的动物精神所定义的。神经学领域所涉甚浅,有机会可以深究。
●新版。笛卡尔错在哪?他认为,哲学思考需要个可靠的基础,一个绝对的开端,所以开始怀疑一切,直到找出那个无可置疑之点。有怀疑,就有个什么东西来执行这个怀疑,这个执行者就是“我”,所以,怀疑证明了“我”的存在,也由此引出论断:“我思,故我在。”这个“我”是什么呢?本质上是思想,在笛卡尔看来,那其实就是个有欲望和感觉的小人,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它与人身体的接口在松果体,在此处操纵身体中作为活力的粒子,发号施令,身体则表现出具体的行为。这里有个巨大的漏洞,这个“我”,是如何操纵那些活力粒子的?(这个暂且不论)笛卡尔其实将人的心智完全与有机体的结构和运转分离开,在他看来心智是个自足的,无需物质支撑的存在。“即使身体不存在了,灵魂也不会停止 事实上,心智是身体和脑与物理与社会环境互动的产物…看书…
●日本人翻译的著作
本书写于90年代,到现在情绪的生理机制已经被人广泛接受了。在读这本认知神经科学著作之前,我已知道情绪与生理之间有极为紧密的互相联系,并以此指导着自己的诸多行动。这本书是用更系统的方式构建了统一大脑、躯体、心智的精妙体系,解释了情绪和感受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作者想要传达的机制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心智的实体就是躯体感受本身,大脑与躯体通过神经信号与化学信号的互相反馈,使人“感受”到情绪。情绪是人类进行生物调节的核心,通过躯体状态的标记来调配注意力,以积极或潜在的方式参与所有决策过程。 第一部分是motivation,稍显冗长。第二部分是本书核心,特别是第七章“情绪和感受”、第八章“躯体标记假设”,介绍了诸多基础概念和理论,初步提出了作者对人类认知生理机制的观点,即“躯体标记假设”。第三部分介绍了对假设的实验检验,并继续阐述了人类心智的形成(第十章)和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第十一章),个人读起来觉得最有趣的也是对相关实验设计的介绍。 后记部分很值得一读,对西方医学“身心分离”的反思和对“安慰剂效应”的探讨很有意义。第十一章和后记中对社会文化在情绪和感受中作用的探讨,也让人觉得有启发。《跨越边界的社区》中对“网络促进信任”的观点有过探讨,波尔兹认为集体中的个人会有更牢靠的相互信任,是由于:1,人们认为集体对个人的制约会带来长远的利益;2,如果你违背集体规则,你将被驱逐。项飙认为这两点解释的逻辑实际上有问题,至少没有讲清楚是个体之间的基本信任发生在前,还是集体的共同意志产生在前。本书阐述的社会文化机制对情绪生理机制的影响、继而对人类决策的影响,实际从非常微观的角度解释了上述奖励和惩罚机制。 个人的阅读体验上,作者对他论点的阐述使用了过多基础概念和解剖学专有名词,不够精炼,因此阅读时要建立共识会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对论点的证明过程又篇幅稍小,论证不足,说服力不够。也许是因为这是科普,输出观点更为重要吧。能够坚持读完,一方面是训练自己对社科类读物的阅读和知识摄取,一方面是生理性的解构情绪让人能够跳出当下自身的情绪状态,有意外的疗愈作用。
《笛卡尔的错误》读后感(二):在情绪中找到精妙的决策推理系统
关于如何理解人类的躯体与心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在20世纪之前,笛卡尔提倡的身心二元理论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该理论认为人的躯体与心智是不相联系的两个部分,心智完全可以独立于躯体而存在,所以才有了我们经常听到的、独立于躯体之外的“意识”、“灵魂”等说法。
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达马西奥躯体标记假说的提出如同一季惊雷,直指笛卡尔身心二元理论的弊端,在身心之间架起了切实可感的一座桥梁。
达马西奥,现就职于美国加州大学,是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及哲学家。他一直奋战在神经科学研究的前线,以情绪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研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从生物演化的角度重新阐述躯体和心智之间不可分可的关系。达马西奥提出了著名的躯体标记假说,被各个学科领域广泛引用,同时还启发了诸多欧美神经实验科学的研究。
在《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达马西奥通过对具体的神经疾病案例的研究,从躯体情绪的角度研究了情绪对决策机制的影响,验证了心智与身体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01神经疾病带来的启示
在神经科学研究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案例—盖奇的案例,盖奇曾经是一名铁路包工头,在一次施工爆破的过程中不幸被一根铁棍刺穿了头骨,幸运的是,经过治疗,盖奇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并且他的智力、思维能力看起来与以往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他却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令人尊敬的包工头了,他的性格发生极大的转变,经常口出污秽语言,做事情毫无头绪,他制定了很多关于未来和工作的计划,却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执行,更诡异的是,他总是积极地做出对自己毫无益处的选择,于是,恢复以后的盖奇成了一个浪迹街头的行为怪僻的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盖奇的案例似乎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大脑不同的区域对应着不同的功能,盖奇正常的智力、语言、和逻辑思维能力,表明他大脑内部的这些区域没有受到损坏,而相对应的与决策有关的大脑区域已经被损坏,才导致他总是积极做出错误的选择。
这些推测在汉娜 达马西奥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盖奇的搭配闹进行三维重建,汉娜 达马西奥得出结论,铁棍损害的是盖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这以区域刚好分管着他规划未来、行为和做出决策的能力。因此才有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惊人的转变。
02情绪和感受
情绪和感受是生物调节过程的核心,也是连接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的桥梁。达马西奥将人的情绪分为早期体验到的情绪和成人的情绪。
早期的情绪也被称为基本情绪,当人们感知到外界或躯体内部的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先天性的预期反应。比如,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感受到一个黑影飞过来的时候,即使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会自发地产生恐惧情绪,引起躲避反应。
早期情绪的感受可以让我们迅速而果断地采取决策行为,那么如果遇到复杂的情况呢?情绪是否一样可以影响决策的产生?回答是肯定的,不过这时候的情绪我们将之称为次级情绪。
所谓的次级情绪,就是当个体开始进行感受,并在物体、场景等之间建立系统的联系的过程。次级情绪明显比基本情绪要更加深刻,它可以对周围的一切展开深思熟虑的思考,然后产生相应的感受,最终影响决策。
达马西奥认为,情绪实际上就是躯体状态的的改变,这些改变被特定的大脑系统所控制,这写改变都可以被我们的躯体所感知,然后产生不同的决策行为。
03躯体标记假说
达马西奥认为,当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推理的时候,躯体会不自觉地体验不同的情绪,如负性的或者积极的,这就是躯体标记。
在面对负性情绪感受的时候,躯体会驱使我们注意结果可能带来的不良结果,并对我们发出警告,从而使我们的决策行为发生改变。如果是积极情绪则是相反的反应。
因此,躯体标记就像是一个自动检测系统一样,它可提前产生预期评估,举个例子:
为什么会有人熬夜加班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工作呢?
这就是因为躯体标记可以预知其在未来的积极反应,熬夜加班工作虽然暂时牺牲了身体健康,但是它可以让我们将自己的成果置换为金钱或理想的职位,这才有了愿意忍受当前不愉快,争取将来更高回报的决策行为。
而在我们前面说到的盖奇的案例中,盖奇的前额叶区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无法产生正常的情绪反应,因此对一切都显得满不在乎,无法产生正常的躯体标记,所以才有了决策行为的毫无根据。
虽然说达马西奥的这本《笛卡尔的错误》通过躯体标记假设理论,提出了情绪与推理机制的关系。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很有借鉴学习的意义因为生活中面临太多的选择,鱼与熊掌不知如何取舍的困难处境也是层出不穷,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根据情绪的反应,做出相应的决策,提高决策行为的效力。
《笛卡尔的错误》读后感(三):书评
接触过一点行为经济学的东西,也在发育生物学课堂上讲过大脑的发育,而且也算稍微了解过一点神经生物学的发展,我对这个领域还是很感兴趣的。这本书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的,想了想还是打出了5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我对大脑的认知。
ART Ⅰ 心智是大脑的躯体的结合体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反驳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最主要的观点就是“ 心智来源于人类结构和功能的整体,而非只来源于大脑 ”。
作者先提出躯体标记假设,论证了没有躯体就不可能产生心智。并用巧妙的电传导、赌博实验设计进行了验证。
躯体标记是次级情绪所产生的感受的特例。通过学习,这些情绪和感受被联结在一起,并用来预测特定情境的未来结果。当一个负性躯体标记伴随一个特定未来结果时,两者结合就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反之,当一个积极的躯体标记伴随着一个特定的未来结果时,就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但有时自动化躯体标记会对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从躯体标记假设和演化的证据上来看,没有躯体就不可能产生心智。但笛卡尔的“二元论”在我们的肉体和心灵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它将最精巧的心智过程与躯体分离了,这种观点一直主导着西方科学界和思想界,是时候颠覆它了。之后,反驳了“缸中大脑”的悖论
由于缺乏大脑到躯体的刺激来更新和调节躯体状态,此时无法触发躯体状态的改变,而躯体状态的改变恰恰是生存感的基石。有人会争辩,可以在神经层面精确模拟躯体状态传来的信号,从而使缸中之脑产生心智。这当然“可行”,我猜测这种情况下会有某种形式的心智产生,但更精巧的方案是直接构建某个躯体替代物。从而证实,对于正常心智最重要的还是“躯体输入”。不太可能做到的是,让这种“躯体输入”以现实的方式与大脑做评估时引发的各种躯体状态所呈现的组织安排相匹配。从进化生物学角度再次强调了躯体和大脑不可分割,
躯体在演化中居于首位,确保躯体本身的生存是大脑进化的首要目的,那么,当有心智的大脑出现时,它们会从更关注躯体开始。 大致上来看,大脑的全部功能就是知晓躯体其余部分,大脑本身以及有机体所处环境的状况,由此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可以获得最合适、最合适生存的协调。ART Ⅱ 自我的神经基础
作者对自我的认识也让我耳目一新
我之前一直对自由意识存在迷惑:可以说过去的每一个瞬间造就了现在的我,而且理论上可以将所有的意识解析到分子层面甚至原子层面,那真的存在“自由”意识吗?自我又是什么呢?
作者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自我的神经基础至少存在于两种表征的连续激活中,第一组涉及到个人自传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自我这一过去记忆和未来计划的结合体,其表象更新持续重新激活,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所理解的自我状态;第二组由个体躯体的原始表征构成。而且,更重要的是,
意识到这些庄重的人类行为背后有着生物机制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就降格为神经生物机制的附属产物。在任何时候,用相对简单的事物去部分地解释复杂事物都不意味着对复杂事物的诋毁。以上这句话真的是全书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了!一下子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ART Ⅲ 情绪
这里把这本书和《具身认知》做一个比较,在看待情绪这一件事上,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情绪的本质是一系列躯体状态的变化。《具身认知》也有讨论过身体对思维的作用,并提倡积极地看待身体的信号。最近也很注意引导自己的负面情绪:我有怎样的负面情绪?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负面情绪?我的身体正发出哪些危险的信号?我该如何做出应对措施?
情绪和感受的缺失同样会严重损害人的理性。而正是理性是人类独一无二,使人可以根据远景、社会习俗和道德原则作出决定。 情绪和感受上的缺陷会导致社会行为缺陷,冷血的推理过程使其无法对不同的选择进行权重赋值,从而使他的决策空间毫无起伏最初接触这个观点是在大一的通识课上,依我之见,所谓理性,也是以感性最大化为目的的。
ART Ⅳ 利他主义
这其实是书中很小的一个点,我把它单独拿出来,是为了整理到之前的认知体系里。
第一次看到对 “利他主义”的解释是在《自私的基因》里,人本来该是自私的,为什么会有利他主义的出现呢?利他主义是否是人的本能呢?
当时我的理解是,利他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基因的传递,总体来讲,人们可以在互帮互助中获利。另外一方面,极端的愿意付出生命的利他主义,其实是害怕死亡的另一个体现。我害怕死亡,所以会献出生命,并希望“获得永生”。
这里给出的解释也挺有意思,从情绪和感受角度解释了利他主义,
利他行为可以使利他者免受不作为带来的内疚和羞愧,不作为带来的痛苦感受相比危险带来的痛苦程度更甚。最后,我下学期一定选修神经生物学!
《笛卡尔的错误》读后感(四):五星好科普,趣味十足,文理兼收,而且深奥得很哦!
正文:
这是一本可读性非常好的脑科学科普书。
语言中性、精确,表现稳定。内容生动,行文流畅,阐述的对象形象鲜活,讲述的脉络由浅入深,深入浅出。我的兴趣一直被作者牵着走直到读完。这本书在写作层面上的完整性和乐趣性,堪比经典物理科普《汤姆逊先生奇遇记》(现在叫《物理世界奇遇记》)。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由著名的病例盖奇切入,逐渐为读者展开脑科学研究的对象。第二部分集中阐述脑科学研究的发现。第三部分作者以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为基础,对文化、哲学等领域进行了一番思索。
我觉得当下最该了解的,正是脑科学及相关研究。我们的感觉、感受、情绪、情感、思维的过程、脑中不断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意识、感性和理性、什么是“自我”等等,这些研究和发现真是太有启发了。智者总说“了解自己”,还有比脑科学研究更直接的吗?
而且,这本书不可避免地伸向了哲学。书名叫做“笛卡尔的错误”,可书里第一部分没有提到,第二部分只埋下一句伏笔,直到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才谈到这个题目。虽然我觉得作者这个人在给自己的书起名字的事上,品味有点难以捉摸,但读完之后感觉也并不为过。读到第三部分时,我脑子里不断闪现“哲学病”三个字。因为我以为当下大众流行中对哲学的追捧和喜好多少是病态的。我百度了一下,“哲学病”首先联系到的是维特根斯坦的那个说法。我还没有读过维特根斯坦,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说。
我毕竟是认真读过几本哲学书的。哲学在西方遥远的过去其实是一个大杂烩,但凡对世界的思考都会包含在里面,因而才被尊为高超的智慧。我以为它们既然能统称为哲学,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人对自然的认识毕竟有限,全写在一起也用不了多少字,所以那时候一个哲学家可以用自己一生有限的时间,将各种问题思考个遍。但历史的轨迹清清楚楚地显示,但凡受了数学工具点化的方面,在最近几百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地单干了,它们综合起来就叫做自然科学。我粗浅的看法就是这么粗暴:数学工具决定了一门学问的性质。社会科学到今天也不该被称为“科学”,因为它里面没有有效的数学应用(有也只是鹦鹉学舌式的),因而它仍然和目前的哲学难解难分。而当下这整个的社会科学和哲学搅合在一起,而且感染了文学和艺术,尤其是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现代艺术商业运作等方面,它们一起正在发生着“哲学病”。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我感到的“哲学病”只能用我十分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总说些脱离实际的话。有时候在某些专家、学者嘴里听到同样的话,我拍手称快。他们的表述自然精确很多,但意思都一样:总说些脱离实际的话。为什么自然科学值得信任?因为它以数学为工具,以观察-假说-预言-验证为方法。而更关键的是,无论如何,它总能付诸实际。费曼有一句至理名言:我们还造不出来,就说明我们还不理解。
一定会有人在此处想到“实证主义哲学”。总是有人在别人提到自然科学已然全面取代哲学最高智慧的地位、当下的哲学已经是一具没有生命的空壳、当下的哲学仅有作为哲学史研究的价值了……诸如此类的话时,要提到“实证主义哲学”。把实证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人,只能说明他两方面都不理解。实证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它仍然是哲学里的一种想法,和自然科学没有半点关系。实证主义哲学是在哲学内部对自然科学停留在表面的模仿,且它仍然是限于在哲学内部运用的,无论对象、方法都没有跳出哲学。所以它怎么能和自然科学相提并论呢?还是哲学内部换汤不换药而已。费曼还讲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南太平小岛上的原始部落,有一天意外看到了飞机;他们按照自己的印象,用木头和布搭了一架飞机,或者说飞机模型,然后每天祈祷神,让它飞起来。费曼那时候就是针对社会“科学”说的。
“哲学病”在我看来的核心症状就是,他们讲起“爱”、“情感”、“非理性”这样的词汇,完全只是符号操作。而这种脱离实际的符号操作,在本书作者看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其实很多人已经很清楚一件事了,每个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承认,理性本身没有基准,否则从古希腊直到今天讨论了两三千年还没有定论的事情缘何还在继续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显然不在他们的视野里,而他们似乎着了魔一样就是不向解决办法存在的方向看,简直病得荒唐。
自然科学,生物学,尤其是脑科学,显然指出了“哲学病”的解决方向。随着人类开始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意识现象,理性、非理性等等如今哲学还保有独一无二的使用权的题目也开始要分离出去了。这同时意味着,自然科学已经开始将哲学剩下的躯壳也要一并同化了。我不觉得这样不好。同化不等于替代,只是意味着,至少请钻研、热爱或仅仅是爱好哲学的人多学一学自然科学,受一受自然科学思维方法的锻炼。而且《笛卡尔的错误》的作者也说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二者我们都要学习。而且我相信,历史中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假如放在今天,一定会比他们的崇拜者更关心认知科学、脑科学。叔本华、康德、斯宾诺莎、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一上来的部分无一例外都是关于认知现象的观察。
:
有一个小问题我想分享一下自己的认识。书中多次提到研究对象的“复杂”,“复杂”这个词似乎我们不暇思索地以为自己是了解的。不,其实我们很可能并不了解。《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里提到:“请想象一下,有许多水上浮标被绑在一起,漂浮在水面上。当一艘船经过时,其尾流会形成一个个小波浪,从而使浮标一个个动起来。但是,每个浮标都无法单独‘行动’。因为每一个浮标都通过绳索连接着不同重量和大小的其他浮标,所以任何一个浮标的行动,都会带动其他浮标产生相应的行动。这些行动还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反馈过程,也就是说,浮标的行动会间接地影响到自身。于是,船的简单尾流,在这个复杂的浮标网络中引发了大量级联式的行动。如果船以其他方式驶过,比如以另一种速度或角度驶过,那么浮标的行动可能会完全不同。”想象一下,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组之类的我们似乎还可以应付,五元六次方程组呢?微分方程?我们的脑袋已经爆炸了。作者解释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何以形成的四个基本因素:吸积,交互,必须处理的例外情况、普遍的稀有事物。读着《笛卡尔的错误》,读者可以站在“复杂”和“复杂系统的成因”的角度来启发理解。
而如何理解“复杂”这件事,用《笛卡尔的错误》里讲到的直觉与思考的关系来说,也很有趣:我们一开始学习“复杂”这个词的时候,逐渐建立起了对“复杂”这个概念的直觉,然后不断运用着;但是我们应该不断地反思,在面对新的情况时,更新自己对“复杂”这个概念的认知,改善自己的直觉。对已经建立了直觉而不再通过反思而改善原来直觉的人,就是不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固执的人、主观成见的人、不具有开放性的人。还有一个更好理解的、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A问B读《红楼梦》吗,B说自己十年前读过。A劝B有空了再读一读,B果真又读了一遍,然后对A说:现在读《红楼梦》,感叹比十年前读时还要好得多啊。
《笛卡尔的错误》读后感(五):身心一体
一
Damasio提出对Descartes所谓身体和灵魂二分法的反对,包括这个观点的现代版本,即人的mind像一个软件,安装在大脑这个硬件上。Descartes的说法固然是沿袭古代把精神看作不同于物质的一种东西的设想,我不断提及Gazzaniga提到,我们有一种天生的二分倾向,把物质的看作一种东西,非物质看作另一种东西。我们直觉上会这么认定,从古至今都是如此。Jared Diamond在《崩溃》中曾说,万年前的原始人和我们智力差不多,就像那些土著的孩子一接触现代文明就能用电脑和开飞机。Mariano Sigman在《决策的大脑》中更是说,几万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智力基因基础都一样,差别只是文化而已。但是我印象中最近读过的几本书表示过不同的看法,即认为在文化影响之下,我们的基因必然也在进化,比如通过Baldwin effect。我的看法是,智力进化上差别如果有,或许也很小。土著人对于人的“活”也有很多观察和总结,我记得某本书提到,有些部落文化以为人的死和活之间差的是“体温”,有的认为是breath,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经验推理,到后来认为存在人形灵魂、一缕空气之类,或者存在松果体中,或者死去的人减轻21克,也都是新的想象或猜测。但是这些都代表我们猜测存在一种不同于物质的“灵魂”或“魂魄”。孔飞力写过一本《叫魂》,写清朝时候民间信仰关于摄人魂魄的巫术而引发的大规模恐慌;实不相瞒,我小时候也听说过叫魂这档子事儿。我在江南待过一段时间,曾看到一种符,是贴在外面,写类似“天皇皇, 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路过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之类。巧了,这种巫术,我在侯孝贤(《童年往事》?)的某一部电影中也看到过,不排除是当年大陆过去的外省人带去的巫术传统。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中,就写古代人信鬼神,现代人进步了信外星人,但是骨子里像老罗说的那样,别看今天的人开飞机玩手机,和古代人还是一样的笨蛋,害得道金斯在《最伟大的表演》中对西方人痛心疾首,惊呼都什么时代了还有半数以上的人信宗教信上帝造人。我以为,这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原装智力系统(Damasio先生,请听我解释)的锅,原装智力系统就是会迷信,就和原始人信巫术信神那样,是前面Gazzaniga所说的人的一些基本智力模块的自然结果。固然,我们看土著,就像普里查德写的赞德的巫术和宗教,马林诺夫斯基写的马兰尼西亚人的宗教和巫术,弗雷泽的《金枝》和泰勒的《原始文化》,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和洛维的《乌鸦印第安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和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会看到他们对巫术和奇怪神学的滑稽信仰,然而回过头看我们自己身边,谁身边没有几个穿红内衣、算星座、戴护身符、求神拜佛或算命的人呢?甚至拍电影、搞建筑的,都还祭天拜地,这些人和那些土著相比,有何不同之处呢?或者,你是否曾经在某件事上闪过一种迷信的念头?
Damasio的意思是,mind不是安装的软件,以计算机的比喻是不妥的。他说,身心一体。整个有机体,而不仅仅是大脑,是个巨大的计算器。当然,首先一点,就是说,人的智能,不是像软件安装在硬件上那样。我们看软件安装在硬件上,可以卸载,可以安装别的软件。但是有机体不一样,有机体不是硬件,有机体自身的组织方式产生了“mind”。就像是你把汽车零件散开在地上,就是一堆零件;安装起来,汽车会跑了,这不是说在“硬件”上安装了“软件”,而是硬件组织方式产生了一种“属性”。在某种意义,这就是功能主义的说法。只不过,功能主义走得太远,以至于给Searle一种印象(或有些人自己也说了出来),以为功能主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无论什么材料,只要合理组织,都能够实现对应的功能,比如把炭基替换为硅基照样产出生命。我认为这个说法基本没有什么错,但是不能说无论什么只要采取某种组织就能实现同样的功能,还要看基底材料的性质。此处是说,我们的mind不是安装在躯体硬件上,而是说,我们的躯体通过这种组织方式,产生了我们的“智能属性”。因此,我们的这个智能,不仅仅是来自大脑中脑神经的组织,我们的整个躯体的运行,也参与在整个智能系统之中。
智能就是一种收集和利用信息系统,目标是为了生存和繁衍。Damasio认为,智能的最基础的方式,就是把躯体的反应和外在的环境状况对应起来。躯体的不同的状态,驱动个体采取不同的行为。比如说当一个生命体看到天敌,引发躯体的躲避反应。就像小鸟小时候看到天上飞的大鸟,就会缩回窝里一样;当然,它们长大了,就不会对所有的大鸟都采取躲避反应,而是只对鹰隼类捕猎鸟产生躲避反应。Damasio说,这只需要两种过程,一种接受信号,一种发出动作信号。但是,随着有机体的复杂化,产生了更高级的系统。人类的系统就是如此,在最基本的系统之上,又增加了感受、情绪、理性等能力。这些能力似乎是通过两种机制实现的,一种是躯体神经反应,一种是对躯体神经反应的存储,相比低级智能,增加了更多中间过程。这种中间过程,最重要的元素是一种dispositional represetations,也就是说,对“知识”的存储,这种知识,可以是一种事实信息,比如对一个人的印象,是通过记录关于这个人的反应(来自early sensory cortices如视觉、听觉的神经反应),将其存储起来。躯体感受,是对躯体状态的一种表征,比如饥饿,当躯体处于某些指标降低的状态,躯体会触发饥饿的神经表征,个体就会感受到饥饿,从而引发进觅食和进食行为。情绪更为复杂,是一种外在信息触发的躯体状态,比如尴尬,在一般社交中,两个人相对而坐却无言,这种外在的情景会引发尴尬的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是这种场合信息引发了一种躯体状态的变化,个体感受到这种变化即呈现出尴尬情绪。情绪也可以看作一种自动反应过程,那么推理呢?就需要三前提,一个是躯体状态,一个是工作记忆,一个是注意力,来提供一种内在存储的知识(images)的展列平台,进行推理。
二
Damasio的对应研究和他的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带来了几种推论。Damasio说,他对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如Elliot的研究显示,这些人在各种智力、道德测试上表现和普通人无疑,但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做对“理性”的决策。在Damasio设计的赌博实验中,普通人会避开一个高收入但高风险的选项,甚至其他大脑区域受损的病人也是如此,但是Elliot却不是如此,而是倾向于高收入但高风险的选项,以至于赔到血本无归。Damasio的推断是,前额叶的损坏,导致“情绪”受损。对普通人的皮肤电测量显示,当他们在赌博中遭遇高收入但存在高风险的选项时,身体反应会逐渐增强,但是Elliot们展示出一种无动于衷的冷血。Damasio因此得出推论,在不确定的情况中,情绪会对远期风险提供一种警告。就像那些精神变态一样(Jonathan Haidt说每100个男人中就有一个这样的psychopath),他们通常毫无感情,仅仅根据自己的(短期)利益进行一种冷酷的计算,在这种计算中,阻碍他们的人,只会被他们看作和物体一样,仅仅是能够两腿直立行走而已(Haidt《The Righteous Mind》);Gazzaniga在Human中说,这些psychopath智商并不低,他们懂得社会规范,但是他们并不清楚不要伤害他人的规范和礼貌规范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对于残损肢体、受苦儿童的画面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反应。Damasio说,这些人强奸、杀人,并且会做一些害人害己的事,这都是因为他们缺乏感情。理性并不足以提供完整的思考判断,首先,理性是有限的,当面对复杂的、不确定的情况时,我们的思考能力不足,我们手头的信息也有限,所以我们的理性往往无所适从;其二,我们的工作记忆有限,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理性推理;其三,我们的理性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就像Kahneman等人的研究,以及Mercier和Sperber在《理性之谜》中对理性的分析。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完全理性的系统,就像计算1+1=2那样,能够用“纯粹”的理性来完成计算。我们在面对复杂的情况时,往往动用从上到下整个系统的帮助,而不仅仅是我们能意识到的理性层面,还包括下层的感受、情绪、本能和直觉这些系统,包括靠本能偏好推动和维持的working memory和attention两个工具。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机体运作,就是一种算法,我称之为生命算法(等于Dennett所提到的进化算法)。在Damasio的赌博实验中,对于普通人来说,感觉和情绪也在做风险和收益计算,并不是在理性层面上进行的。所以Damasio说,情绪或感觉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种预处理,作为一种偏向系统,已经预先处理了数据。在赌博实验中,这种情绪使得我们躲避高风险,但是额叶受损的Elliot失去了情绪处理系统,所以他不知道从长远或大框架上躲避高风险。注意,他确实知道躲避风险,但是仅仅躲避眼前的风险;即,每次受到惩罚,他都赶紧躲避。
躯体状态引发情绪,参与整个信息处理过程,这个说法解决了我上次提到的在街角的时候开始思考的那个问题,即什么为理性提供“心力”的问题。Damasio说,在赌博实验中,Elliot缺少情绪来提供关于长远目标(此处是高风险的损失)的考量,而总是屈服于眼前的诱惑。我们往往称之为一种willpower,意志力。那么,意志力是什么呢?从何而来呢?Damasio说,意志力,实际上就是远景所唤起的躯体的一种愉悦状态。比如说,一个胖子打算减肥,眼前放着美味的甜点,那么这个甜点会引发她的进食欲望。自从把Ta都用女她,以示我对女权的支持,然而常常感觉是在黑人。压抑这种欲望,就需要一种意志力,那么意志力从何而来?Damasio的意思是,想想自己瘦了的美,会引发一种躯体上的愉悦的状态,正式这种愉悦情绪,能够抵制当前的诱惑,此即意志力的来源和作用。这刚好能解决我所一直考虑的所谓“理性”如何战胜情感的问题。实际上,理性自身无法战胜情感。就像Elliot在实验室完成所有智力和道德测验,表现优异之后所说:生活中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也就是说,虽然Elliot能够在实验室,在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上,理性地运用知识,但是这和实际生活不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需要有一种驱动力,一种心力帮助我们做出选择。Elliot的心力,就像前面所提的,就是那些眼前的好处。他不在能“理性rational”规划,这里的理性,按照Damasio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明智”,比如一个胖子吃货节食减肥。理性实际上也要唤起情感,来战胜其他理性或非理性——在liberty of indifference中就是如此,比如给你两个同样的选项,比如……很难找出一个通用的两个同样的选项,用亚里士多德的例子吧,就是你现在缺水缺食物,让你选一样。你或许会感觉连两者都同样难以放弃,这是理性选择出现竞争的例子;前面减肥和吃甜点,是用理性战胜欲望的例子。最终做出选择,就需要一种“心力”,这种心力理性不能提供,只有感情能够提供。这里解决了我所谓的纯粹理性带来的道德律令如何不是作为“沉重的桎梏”,而是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原则的问题。
Damasio特意谈了自我的问题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他提到自我来自两个因素,一个自传体叙事,一个是对自我躯体状态的映射(双重,一种是即时映射,一种是存储的关于自己的躯体的信息)。他说,我们的自我在不断更新,所以我们能接受我们在镜子中逐渐改变的模样。他说,我们大脑在处理信息时,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自我感”。比如说,当我们看东西时,我们收到来自外界的信号,同时我们也收到我们“眼睛”相关部位的信号,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外界,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在用眼睛“看”。这导致了一种“自我”意识。我想说的是,实际上我们确实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更新的自我。我以前常举一个例子,当我们读一个谜语,知道谜底之前和之后,我们不是同一个人。知道谜底之前,我们会觉得这谜不好猜;知道谜底之后,我们会觉得这谜底不难猜。Kahneman曾提到这种现象,他说,事前和事后,我们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事前猪一样,事后诸葛亮,我们事后实际上无法再回到事前的状态。事后我们会觉得这容易,比如知道一场比赛的结果之后我们觉得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某队赢了或输了;事前我们会觉得几乎无法推断是否一定会赢或输——当然,有人很有信心,Annie Duke说,你跟这样的人打赌他就会犹豫了:既然她这么有信心,赌个1:100,你显然可以说就是打算白送她(因为她有信心稳赢)1块钱,她输了输100。写完这几句话我就不在是之前的自己。各位,我是另一个人。关于自由意志,Damasio认为Gage和Elliot这些人受伤后,失去了自由意志。很遗憾,Damasio关于自由意志的概念是混乱的甚至错误的。他把自由意志理解为一种rational ability,一种使得人不同于动物的、合理而明知规划和管理自己生活的能力。我认为这不是自由意志的正确定义。
二
Gazzaniga在Human中说,意识和注意是两码事。他举例说,给大部分人一本谈量子的书,不,给更多人一本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无论她们有多努力注意,但是如同读天书,这些文字背后的“含义”,永远无法进入意识。「我用女她,是有意纠正文化中男性偏见,就像人类是man,是human,不是woman,不是huwuman。有些人提出反对,那么不妨我们就都用女她好了。但是这没有意义。【我们灵智派看不起仪式派。关大眠在《佛教概论》中提到了佛教的分裂,即为这两派。我后来引申这个现象到各种流派中,无论是哲学、神学还是艺术。(只有科学不是这样,因为科学是可证的,没有人能浑水摸鱼,摸得了一时也摸不了一世,就像韩春雨事件。科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Mercier and Sperber在《理性之谜》中说,只有一种理性。科学表现得虽然和常见的理性的使用不同,即为自己辩护和说服别人,那可能是因为科学家面对的是更牛逼的听众,使得他们提高了标准而已;而且这可以从两点看出来,其一,科学家也并不具有一种可靠的理性方法,而也像艺术家一样更多是靠灵感,其二科学家也并不是孤独的推理者,牛顿在数学和物理学上的超级成就是由于他同时代也有许多出众的科学家,所以他为了说服他们得提出一种严密而可靠的论证,但是在炼金术上他的研究却是很滑稽,因为不仅他收集到的材料很有限而且周围也没有炼金术高手。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就像Damasio在本书中提出,和Evans的观点一样他认为也有两种理性,当然严格来讲不是两种理性是理性的两个领域的运用,即个人和社会领域,和非个人和社会领域。后者如做一道数学题。我以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种个性质,在科学推理的过程中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做这种推理的人或说科学家动机或心不纯罢了,也就是说,他们搞这个“科学推理”可能是为了名利,但是这动机一般并不参与这个推理过程,但是在韩春雨这类科学研究者身上,这种功利动机就参与了这个过程:他们造假欺诈。)所谓灵智派,我是指不在乎形式,而在乎内容。就像所谓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当然,人们要求形式,一个原因是因为,别人的内心我们很难确定,因此只有从形式上提出要求。但是,问题在于,形式可以伪装。从形式上讲,陶崇园的导师王攀就认为自己的“道德情操超越时代50年”;(但是等红绿灯不说明任何问题。Damasio、Haidt和Gazzaniga都提到,每100个男人中会有一个psychopath(Haidt),这种人从外表看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甚至更聪明和理性,但是他们缺乏“感情”,或说他们的情绪阈值非常之高,比如他们家暴殴打女性的时候,即使看到对方受伤和痛苦,也没有丝毫的情感波动,感受不到一点的同情,“自述“没有感受、冷漠无感”(Damasio),或许爱猫狗和帮助老幼病残是非变态的一个表征,他们知道所有的社会规范,但是“不要使用暴力”这条规则,与“和别人一起吃快餐的时候不用薯条蘸两次番茄酱”这条规则,在这种psychopath看来并无两样(Gazzaniga),而不是像普通人觉得你蘸了两次也算了,但是打人就很大条。他可以等红绿灯,说明他知道规则。但是他在给别人造成的损失上毫无后悔和内疚,或者可以说是急眼了给自己拼命辩护,或者就是对他来说,给别人造成的这种痛苦,根本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换句话,形式是外在的,是一种间接的信息或证据。Geerz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出一种thick description,所谓的“深描”,提了一个例子,说你看到一个少年眨眨眼,这就是表面,但是具体他为什么眨眼,你就需要深挖,或许他是模仿别人,或者他是有所暗示,有多种可能,所以你不能只是停留在“他眨了眨眼”上。David Sloan Wilson在《利他之心》中说,一个人作出某种行为,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可能有不同的动机或想法,康德曾提出一个商人童叟无欺,可能是出于善良,也可能是出于要维护自己一个良好的商业名誉,这就是一个不同动机或想法做出同样行为的例子,Wilson因此放弃了从动机或想法上来定义或推动道德行为的努力,再我看来这是对道德研究的一个巨大的失误。我把灵智派看作一种领会内在精髓,而仪式派是模仿外表的样子,如护球像亨利。】human和huwoman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其意义实际上体现在,男性和女性作为一种竞争对手,在利益上进行较量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把举例时说ta,Ta,TA,he or she,she or he,才有意义。我不得不承认,这种竞争真实存在,虽然在我看来滑稽。我本以为,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每一个男性和每一个女人都结了婚,按理说女人和男人,还有什么可敌对的?错在,我以为他们结婚是出于一种爱,一种相互的关怀。然后就发现我有点傻有点天真,很多人的结合并无爱情,或者并无“爱”。他们就是一种功能性的结合,受一种本能推动而结伴,像是一起做(繁衍后代的)生意,相互之间在利益上存在或明或暗的争夺,甚至存在算计、剥削、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感情虐待,婚姻和家庭竟然不是为了个人幸福,上演着多少人间惨剧。怪不得罗素有the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human beings。」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这本《笛卡尔的错误》,但是我并没有读懂Damasio所说的躯体反应在智能中所起的作用,没有读懂dis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s如何作为知识的对应物存在,以及“self”和subjective experience是如何在神经表征中实现的。多么神奇啊,我现在竟然读懂了。Damasio说,我们的“self”,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自我,每时每刻都在更新。你看,我的大脑就在更新。过去读这本书的“我”,读不懂,是那个时候大脑无法理解这里面的“含义”。但是,现在我的大脑已经变化,已经能够读懂其中的含义。
三
老罗在讲述自己心理素质差的时候说,在民风彪悍的大砍省,你瞅啥,瞅你咋地,这就能让双方找个地方一起切磋切磋,我没去过东北,但真看过一个你瞅啥视频。我记得有本书是关于南方还是西部的荣誉文化,老罗说他们那里也是一样原因。他说,年少的时候他也跟小伙伴一起跟别人切磋过,但是他心理素质差,往往还没开始衣服都湿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怯,打得更用力。他说,当时是在海边,当着阿狄丽娜的面揍人。听到他提阿狄丽娜,我就感觉很逗。老罗的幽默感不是盖的。我喜欢有幽默感的人,幽默感越好我越喜欢。就像王小波,他写道:
还有一段时间我戴着黑眼镜,假装是瞎子,在街上卖唱。但很少有人施舍。作为一个瞎子,我的衣服还不够脏。他们还说我唱得太难听,可以催小孩子的尿。后来我又当过看小孩子的保姆,唱歌给小孩子听,他们听了反而尿不出;见到雇主回家,就说:妈妈,叔叔唱!然后放声大哭。我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拖延了很多时间,来逃避我的命运。“喜剧性”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也是因为长久没有读这方面的书,所以还没有一个可靠的答案。但是似乎幽默感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级,最底层是滑稽,比如一些喜剧片里面演员装疯卖傻;更高级一些是抖机灵,机灵抖到最高境界就是玩深埋的梗,你没有足够的知识,你不知道阿狄丽娜是谁;当然,最高级是抖智慧,就像伍迪艾伦说,他被大学开除,因为在形而上学考试中作弊:I looked into the soul of the boy sitting next to me,偷看了旁边考生的灵魂。我以为这就是幽默的最高境界。我曾留意周星驰的喜剧如何高出其他人一筹,对比阿特金斯、金凯瑞,尤其是许冠文可以看出,其他人演喜剧往往是通过装疯卖丑,就像吴君如、楼南光、曾志伟,甚至其中相当出色的陈百祥这一票喜剧角色就是这种类型,这是编剧的锅,但是周星驰的不是,鉴于他巨大的创作力和喜剧灵感,他现场参与甚至指导了其他人的角色,疯丑的元素被他分配给了其他人比如苑琼丹的石榴姐,莫文蔚的火鸡,还有酱爆、田鸡、阿欢等等角色,而他自己的角色却总是在“秀”,陈独秀,秀儿。这不是“演”的,金凯瑞在美瑞儿斯特里普的庆祝宴上简直堪称神级模仿了Michael Nickleson、Robert De Niro和Bruce Dern。Jim Carrey,我希望有一天能跟他合作,帮他拿一个奥斯卡小金人。每一秒这个愿望都在getting older。但是更让我担心的,是Jim Carrey不满于和Jonnathan Haidt,韦伯、丹尼尔贝尔等人一样的对宗教倒台之后科学也没有能提供一个新的更高价值信仰,人们的生活流于世俗的物语带来的精神上的不满和空虚,而寻求精神寄托但是他好像误入歧途,越来越走火入魔,还相信了阴谋论说川普是什么reptilian illuminati,真是要让人操碎心。看来我得更加努力去完成我的文章了,也是为了Jim。
读书于我总的来说,是一件挺愉悦的事情。当然,是读那些写得好的书。Damasio说,推理的目的就是做决定,做决定的真谛就是从中做出一种选择。不是所有的书都写得好,甚至更多的书都是垃圾。因此,你就需要选择一些好书来读。to choose or not to choose,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不做选择,随便看,这是一种明显的不明智。当然,必须说,还有别的价值观,比如认为个人喜欢就好,萝卜青菜相对主义。这种价值观我以为是劣质的。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说,人人都追求幸福,不错;但是,不应该追求尘世的短暂幸福,而应该追求来自上帝的永恒的幸福。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说,确实有一些乐趣要更高级,比如追求知识就比吃喝玩乐更高级。这二位都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某种功利价值观,甚至还区分出了高级和低级的享乐,更别提我这种追随苏格拉底和康德的deotological价值观的人,我们完全不把幸福看在眼里,认为是低级的、不值得追求的。我相信我没有绑架苏格拉底,但不确定是否绑架了康德。既然烂书多好书少,自然也存在如何选择书去读的问题。我提及有一类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喜欢读就去读,这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你的喜好可能很不可靠,就像人们常说的“品味”,你的品味可能因为你不具有cultral capital,你没有文化素养、知识储备、没有思想能力,导致你仅仅跟随你本能和环境去寻求刺激,就像去读宫廷小说、看豪门恩怨,就像吸毒一样,用现代工具撩拨原始本能来获得快感而已。Damasio说理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作记忆有限,无法铺开用于完整的考虑,就像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沿着一个岔路前进,连续几个转弯之后,就会迷路,离主路越来越远,收不回来,工作记忆装不下已经溢出,最初想要写什么已经忘记了。我推想我不会活到能够做个生化改装,给我脑袋里再加一条内存的那一天了。
完了,我今天又到了mood disorder的抑郁态。 Damasio说,我们的智能系统有一个基础的运作机制,他成为躯体标识系统;就是说,躯体反应参与在人的智能计算之中。他说,有一种对应happiness的躯体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能够在大脑中更快产生images(可以理解为大脑运作更快),产生更多样的images(可以理解为大脑运作更丰富多样),并且推理更快。与之相反,在抑郁状态,大脑运作更慢,运作更单调,推理更慢。我刚刚探了一下大脑里面,就是发现空空如也。实锤了。意识状态实际上就对应一种大脑的生理状态。反过来说也可以。其含义是,我们能够通过意识改变大脑状态,同时也能够通过改变大脑的生理状态来改变意识的状态。就像在草原鼠和山地鼠的实验所展示的,草原鼠比较重感情,一夫一妻维持很久,但是山地鼠相反,态度随便,就像那个粗俗的说法“走肾不走心”。差别就在于,前者有较高的催产素oxytocin和vasopressin(vasopressin对应的基因片段相比较长)。古人一直寻觅爱情迷药,现代科学给了答案,这就是爱情迷药。就像在老鼠身上,阻断了vasopressin,就不爱了;提高vasopressin,就又爱了。所以曾经兴起过一股对oxytocin的风潮,但是实际上人们发现,大脑的系统运作要复杂很多,并非单单一种物质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以为,不妨走一走另外一条途径,即对付自己的大脑,通过有意调整自己的行为,来塑造自己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