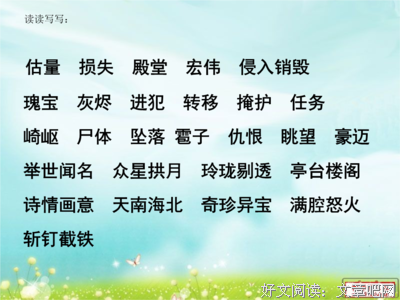天南读后感精选
《天南》是一本由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南》读后感(一):专题很不错
《天南》创刊号这期的特别策划做得相当不错,亚细亚故乡,视野很广阔。确实,这一块长期都有人关注,但大部分人都是忽略了的。读了之后会使人停下来思考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第一篇文章虽然作者是1999年写出来的,但通过此文反观我国的水利大跃进,仍然受益匪浅。
《天南》读后感(二):想随便翻翻的让道,适合静静阅读并且慢慢读。
刚刚看见这本杂志,印象还行,就是感觉自己阅历和知识面不够,读起来恐怕吃力,最终没有买。
但是还是有深度的一本杂志,下次会打算买。
现在还是不喜欢城市画报,氧气生活,壹周悦读,这些杂志了,因为深度不够,虽然比较有点文艺范儿,
万象杂志一直买,虽然有些内容自己还是吃不消,但是是纯粹的东西,
希望看到有自己独特观点见解,有深度,可读性强,的杂志。
《天南》读后感(三):鞭炮齐鸣
“老实说,做父母的像你们这样其实挺愚昧的。你们自己没有活得顺心自在,一辈子都把心思放在儿女身上,何必呢?难道你们就不是人吗?也可以说,我娶不娶老婆生不生儿子,既不关村里单位里那些三姑六婆的事,也不关你二老的屁事。但你们不操心这个还能叫中国人的父母吗?说难听点,你们总是操心各种各样的不关你们屁事的屁事。这就是你们的命,很贱的命,不怪你们。”
——《天南》01 《鞭炮齐鸣》曹寇
《天南》读后感(四):又是一个创刊号
今年小书店里一下子多了好多杂志。
没看过的《最小说》;有看的《鲤》系列、《独唱团》、《大方》。及。最近的《天南》。
发觉自己是一个装帧视觉控,摩挲粗糙的纸张更欢喜。
《独唱团》貌似被禁了。没有下期了。
《鲤》还在继续“来不及”。
《大方》属季刊,等夏天了。貌似安妮主笔杂志还是有些不习惯。
《天南》的文字不错,但全本看下来很累。视觉上的累。呵呵。
《天南》读后感(五):枯燥的天南
现代传播对《天南》的营销策略还是很成功的,有点苹果“饥饿营销”的意思了,上市没几天北京就断货了,越不给货读者越稀罕并纷纷重金求外援,难以免俗地,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期创刊号密度还算大,题材也是我灰常感兴趣的现代性与农村经济/农耕文明的问题,但略读一遍后却还是有“盛名之下……”的小怨念。
其一,刊名是Agrarian Asia,内容是”东亚,南亚,东南亚”,哪里就能代表“亚细亚”;不过中文刊名很有趣,“亚细亚故乡”听着就比“农业亚洲”洋气也兼有腔有调。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主编欧宁曾经有过诗人的生涯。
其二,版面实在枯燥,视觉冲击为零,中插的英文版打断了主题部分的阅读体验,刊首的诗歌和摄影就像组织上安排的婚姻,显然没有刊尾的那一对儿鸾凤和鸣得融洽。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版权页上没有美编。
其三,4-7页的摄影很像《城市中国》用过的旧图,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正文部分看不到朱老师的大作却在contributor页看到伊的大名。OH,I'M SORRY,翻到最后一页才发现那两张照片果然是朱老师版权所有。。。
无论如何,整体上这本创刊号在“杂志”与“书”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文字内容也很是精致深刻,我能想象也非常钦佩在这本杂志书背后编辑团队所付出的艰辛。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有人愿意做些有分量的东西就是好事,所以,我依然是以敬恕的心期待《天南》的下一刊。
《天南》读后感(六):芬芳散尽
一本杂志想要诉说的太多,也许成了一本书。
这本杂志是我在微博上看到的,有一阵还对它在市面上的难以购买很反感——装什么紧俏商品啊真是。买回来在家里一直放着(因为工作忙。。。),直到昨天晚上在飞机上才抽时间看了内容里的两篇(其余时间则在看机上娱乐节目——威廉王子的婚礼前瞻。。。啊哈哈哈)。今天飞回北京的路上则一直坚持着,把这本书看完了。
这本杂志带给我的,不仅是知识的分享(作为四川人的我并不曾知道陈子庄、也不知道中华民国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时区而“中原时间”是标准时区),也不仅是去研究几篇晦涩的“超现实”小说或者深读两篇文学研究,而更多的是情感的代入。
我觉得阅读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唤回我们早已淡忘的记忆。在间或放下书本,朝天花板望去的时候,会真的有昨天和今天同时在放映的感觉。那些已被深深锁进大脑里数不清的紧闭的房间里的过去,在这么多年之后,借了一本书、一段故事,悄悄的从门缝溜了出来和你说嗨。感动,哪怕只是那么一瞬间的似曾相识。
其实很多内容在本质上和我的记忆毫不相关,可真就在某个地方促我心有戚戚。我会莫名的从一两句无关的描写,联想起那一年从深圳回京的飞机上,我用三个小时对同事滔滔不绝复述了一遍《情书》之后重感冒一整个礼拜,也会想起高中第一年曾为之落泪的《北方的河》与《黑骏马》,我甚至因之想起了在极其遥远的幼儿园时期在饭堂端着小碗刨饭的时候一抬头看到的红砖屋顶上的结网蜘蛛。
感谢这本杂志(书),与我分享这24小时来回飞机上的4个小时,带我重新推开充满薄雾阳光的记忆城墙。
《天南》读后感(七):文学杂志的诗意化生存
初识天南,还是在《wallpaper》杂志的内页一角。当时只是有这么一则消息,告诉读者有一本文学类的杂志正在筹划出刊。封面就是印度恒河边上行走的人。
《天南》杂志出刊之后,获得大众好评。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在当今读图盛行的潮流下,成为一本颇具诗意化的文学志,每期的主题设置与探究历史的边缘、文学之外的社会文化相关,在文学和非文学的边界里寻求一份难能可贵的文化情怀。其英文名称Chutzpah,翻译过来是指“肆无忌惮的勇气”,“挑战成规的精神”。
其出刊后的主题,诸如:星际叙事、情色异象、离散之味,都呈现出一种挑战规则的意味,在既有的文学框架里,用一种侧边的角度去呈现杂志所要叙述的内容。让一切寻常的事物有了新的生机,并且期望能够以此挑战旧有的文学体系,重塑文学阅读体系。显然,这种方式获得了成功,在去年杂志出刊繁荣的市场环境下,博得了市场的青睐。
很多时候,文学只不过是人们的调味剂,在日益忙碌的社会节奏下,更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精神上的空虚需要一种更为快节奏的文学品加以慰藉,因此以图片为视觉导向的杂志纷繁而至。但这种模式在人们一遍又一遍的消费之下,咀嚼无味之后,便无人问津。
文学的写作本来就具有诗意的美感,而杂志的创作更应具有诗意的方向。用一本刊物塑造一种文学态度,打造呈现社会之下的种种生活。美与丑,善与恶,都应用细腻的关怀、贴切的精神慰藉来重新构筑社会本象,这方是一本文学刊物的生存意义。《天南》杂志里的作品虽然还具有一些严肃的气味,但形式上的创新和主题上的取舍已让人们看到了文学杂志未来新的方向。
《天南》读后感(八):新锐视野中寻求一柄量度现世戒尺
搭归地铁后走进书站,不免寻思着每本书每本杂志里面丰盛的饱满。一瞥《情色异象》,被震慑住于其争议的封面。
虽尚只阅读过《情色异象》一刊,限于高中学业里闲暇时间品味,茫然之际犹恍悟,自身视野狭隘,如井底之蛙。
仅凭疏浅学识发表些想法。
难能可贵的是现世纷呈斑斓的文化生活间有如此尖锐之匕首,新颖却不乏深度。文化杂志所定位的并不在于生活,在这本杂志上它有了更高的定位态度,它藉此杂志的媒体所传达出一种信念,我想用faith来表达这种东西。它不是宗教信仰,程度尚且没有信仰来的高,亦非世人倡导提议的一种精神概义,外乎上述两者,它更饱含的是来自于环境与人体自身两者在于特定时空所迸发出的一种理念。而此理念来自于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特殊背景(受西方宗教信仰、器物科技、资本文化等因素),国民渐趋于世界西方化的大潮,我们所提倡学习西方的所付诸的实践活动,都不外乎于至今仍在世界传播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便是我在这本杂志中感知到的理念。
古希腊先哲们主张的思想如“美德即知识”“有道德的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等,这些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精神的起源,至十四五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文艺复兴,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影响后世甚广。较之中国则是以儒学为主,道、佛、法等为辅的思想体系存于历史。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华夏大土盛着思想迸发的众多魂灵。
这本杂志有着许多凸显人文精神主义的地方,首期《亚细亚故乡》关注着亚洲农村历史和现实、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浪潮,二刊《星际叙事》一跃视角放到人类学识研讨自然宇宙中,三刊《诗歌地理学》主题放在中国八十年代诗人全国漫游把酒诵诗,四刊《情色异象》掠走呼吸的尖锐话题,到五刊《离散之味》讲述种种原因而离异的家庭的故事与关于流亡的话题。表现的是人如何与大自然对话下肯定自身的价值又给足大自然面子,即既不卑躬屈膝亦无桀骜纵然。这亦是人文精神主义发展到现在的深刻体现。如此理念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此杂志所传达出的人文理念便是现世中一柄量度事物的戒尺,亦是得以在百花齐放的文化市场中得以跳脱的关键。贩购架上如此多的书刊,《天南》所作的封面似乎我最不能忘记。
能与此般良识遇知,窥见另一片天地,实是欣慰。能在豆瓣上写些小见解,更是感恩。
《天南》读后感(九):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近几日只是乘得短暂的假期得以回家,出行前购得杂志《天南》创刊号一期,随编者所引进入的“亚细亚故乡”专栏又重新让我低下头俯身去审视脚边的泥土了。说起泥土,又回想起北岛一文《纽约变奏》里的场景——“纽约人是不会想到地平线的,这事儿生来就和他们无关。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话,那么在这儿肯定是纵向的。”现在置身于繁华都市上层惴惴不安的一十二楼,走出阳台宛若漫步云端,却正如父母不经意提到家中再难寻桂花香了。
杂志打开了一个入口,让读者再一次观看脚下这片土地,以开篇对大坝的议题抛出一连串问号,忙不迭的追逼斥责着读者的良心。好在编辑的善良,不仅用日本和泰国的纪实找回了人与大地的联系,还描摹出了“中国乡村建设者的群像”,给人以希望。
当初在阅读阿兰达蒂·洛伊对印度政府和社会的对大坝的控诉之时,我正坐在高速驶回杭州的大巴上,公路两旁是长三角富庶的农村景象,较之当年巴黎境内的火车窗外的景象毫不逊色。但是我清楚车窗外的风物在百里千里之外便大相径庭,去年清明火车北上帝都之时便看着火车车窗外颜色由绿至黄绿最后逐渐一切都被蒙上一层厚重的土黄色。我没有进入过中国,一直在边缘的地方游走仿佛置身自己于高阁之上;我希望进入中国,走进一个更加真实的非加工过的“中国”。中国二字在我的脑中定义更偏向似黄土地上蒙着风尘的农人形象,一如”锄禾日当午“,中国的男子的形象;而江南,或整一南方疆域则大抵是中国女子形象的缩影。
印度和中国相似之处很多,文中所提大坝——我已记不得文中涉及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水坝,都无外乎让我联想到三峡,联想到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文中的控诉通过这种自然而然的联想不断的晃动三峡大坝在我脑中的固有形象:新闻联播中兴奋的播报员和那些只留下背影的背井离乡的农人;大坝合拢时欢呼的工程师和黯然叹息的文人学者。这样的形象塑造无疑将大坝本身置于级贬的位置,显然有失公允,毕竟,未来如何还未成定数。但由大坝所见的并非人类妄图改造大自然的傲慢,而是人类离弃其生长伊始的根基和牵系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小川绅介所言的“吃米的人”一说很是赞成。简单说来,“吃米”本身就告诉你你不是“流浪者”,这正是前些日子提到北岛在外漂泊自觉流浪若萍的原因吧。电视前端时候报道水稻杂交新的成果事宜,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袁隆平教授的意思,只是时常会为土地本身担心:这一亩一亩的土地到底能被人类挤榨出多少价值。也许只有这些不懂得科学的感性的读书人才会幻想出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国度,而真正愿意为之付诸于行动的那些乡建者才理应是我们这些抱怨牢骚满腹的所谓愤青学习的榜样和标杆吧。
是的,那些只知发出怨艾国家、政党声音的年轻人自诩是高觉悟高文化的,却鲜有如梁鸿《行动在大地》一文中所涉及的任何一人的行动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我大学至今未能有一次完整支教经历当是让我深感遗憾的。走近产出生命的大地,走近离此泥土最近的孩子们的周围,切身提供教育的支援和帮助,这些都是支教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体悟;但不止于此,也许只有起码三个月抑或半年一年的与大地生活在一起的经历才能让你明白你所做的并不是施舍、奉献或付出,而仅仅是那么微不足道的感恩和回报。乡建是要去扭转这个已略畸形的社会结构,重新在人们(无论是农人还是城市人)心中根植下大地的这个概念。我想这应该是乡建真正的目的所在。
之后的四边文章仅读了前两篇回忆类散文。后面的小说就真不符合口味。这样的文艺类杂志在市面上愈来愈多了,倒也是件好事。
《天南》读后感(十):天南之后,再无天南?
《天南》停刊了,可叹可惜,可歌可泣。
作为为数不多的纯文学杂志,《天南》像是一个另类的存在,这本存活了三年零十个月的杂志硕果结满总计的十六期。而今因为营销的不成功,现代传播资讯有限公司敲下了停刊的法锤。
每两三个月一期,每期特定主题,整本杂志透出一股厚实,即便除去中间的彩页和刊中刊,淡黄的纸叶装订在一起也有约200P。外侧卡纸材质封面设计简洁,少数的文字表明它的名字、期刊号和本期主题,更多的是一条条黑色粗线之间的作者姓名。再加上冲击力强烈的封面图片,有其独特风格的《天南》甚是惹人怜爱。
从创刊之初,杂志主编欧宁便为《天南》定下了独特的原则:挖掘年轻作家,让文学视野更国际,杂志的品相也更有现代感。自外至内的全新编排,《天南》在开篇第一页便花不小的篇幅简介当期杂志的内容,各个栏目各篇文章题目串联起来,每行居中显示,作者全部用下划线突出。而后继续往下翻页,犹如进入了一栋房子,一片片门内承载全新的风景,依次进入欣赏,流连,幕落,See you next issus!事实证明,这些创新征服了大量读者。
《天南》的英文名为Chutzpah,源自意第续语,原意是“放肆”、“拽”,在传入英语世界后又发展出“肆无忌惮的勇气”、“挑战成规的精神”等意涵。正因如此,借用陈丹青先生之语“最可贵的无知和胆气”,《天南》成也在此败也在此,首当其冲后不可避免的陨落。
在《天南》主编欧宁看来,传统的、官方支持的刊物譬如《收获》和《人民文学》,办刊时间久,和大牌作家关系好,内容质量很高,但杂志产品形态落后,品相较弱,缺乏视觉冲击力。至于《最小说》《鲤》《文艺风赏》等一系列明星作家创办的杂志,其成功更多是商业运作上的,而非文学意义上的。
因此,《天南》进行了大量努力,以展现其所追求的真正的文学刊物。包括每期设定不同的主题,根据主题来选定优秀的稿件,而且大量的提携新人,以求还原一个真正的文学生态圈;包括每一期中的刊中刊,都会请国外的翻译家把原来的中文稿件翻译成疑问,以此来向国际推广中国文学,试图“与国际接轨”。
相比较国内的大多数文学期刊,尽管《天南》展现出了少有的文学时尚,也更加和国际接轨,但像《天南》中所刊登的文学归根到底还是要接地气,要让众多的读者看到他们感同身受的内容。《天南》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作者为中心,间接地忽略了读者的需求,以至于读者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很少有反应读者诉求的情况出现。
我本身接触《天南》不过两年,仅作为无聊之中的调味,几本一起的淘宝,断断续续的读着,因为是双月刊,发行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杂志确实良心,厚实得很——不仅在印装,更在于内容。
但在赞美之外,《天南》可以说太过于传统了,当下大互联数据时代,微博、微信一呼百应的案例数不胜数,遗憾的是《天南》并没有过度重视,文学产生于公众又回归于公众,不进到群众队伍中去,怎么能正确认识文学,又怎么能做好纯文学的杂志呢?
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天南》的停刊侧面反映出了社会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不能深入阅读,暂且不谈问题凸显的网络文学,通过微博和微信的传播来获取咨询虽然是简单快捷的方法,但是仅仅停留在表层的浅阅读根本上并不利于个人的知识储备和群体知识深度的发展,日益萎缩的阅读人群更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
所谓【晓】,就是带来梦想的拂晓。
有品·有范儿·有趣·有腔调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微信搜索【晓次元】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