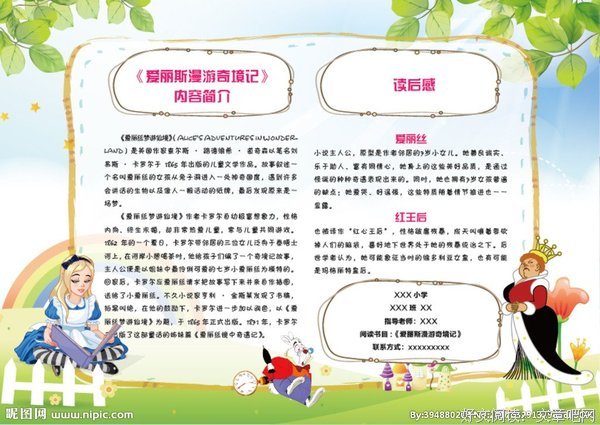French Absolutism读后感精选
《French Absolutism》是一本由Lublinskaya, A.D.著作,$ 58.76出版的2008-10图书,本书定价:368,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French Absolutism》读后感(一):一些吐槽
看了第六章,不得不说此书关于瓦尔特利纳问题的部分虎头蛇尾……第五章强调了这么久避免军事行动是因为缺钱,到黎赛留上台就忽然宽裕了吗?实际完全没有迹象啊,1624年底威胁走司法程序向金融家们敲诈1千万利弗尔,来年考虑到还有求于人减免了,之后无非还是卖官和管各省要钱而已。
然而就是在手头仍不宽裕的情况下,之前竭力避免的军事行动在1624年底搞了两次(埃斯特雷在格里松斯、莱迪吉埃尔与萨瓦盟军围攻热那亚),虽然作者强调是小规模的、不甚成功的,也总归是要钱的吧……何况如何保证这些小规模战事不会招来进一步的麻烦?
这些“小规模、不甚成功”的军事行动之后……就特么还是靠谈判啊!然后蒙松条约就签订了、瓦尔特利纳隘口的垄断权就回来了啊!WTF!作者你不是宣扬没有实力支持的外交没前途么!虽然你还是强调签这个条约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以至于要让大使以个人名义偷摸签,可坑的是道友不是贫道啊!
所以说西班牙到底为毛要签呢?!是了,作者你说他们现在麻烦多不想两线作战什么的,我去……十二年停战协定1619年就到期了好么,帕拉坦问题也是老早就存在了好么,难道1626年以前西班牙没这些顾虑如今忽然开窍了吗我去!作者你就这样丢下这堆问题去讲拉罗舍尔了你安心吗!
本以为此书能够给我一直以来想不通的瓦尔特利纳问题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现在看来果然还是不行……不过鲁布林斯卡娅也提到偏偏黎赛留执政初年的原始档案材料特别少,或许原因在此?话说回来从她的注释里看俄国图书馆收藏的关于17世纪法国的原始资料之丰富已经让我很惊讶和羡慕了。
《French Absolutism》读后感(二):前黎赛留时代冷知识集
列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17世纪初法国的经济概况(这个倒不稀奇,Tapié和勒纳尔的书里也都有)
·1621-1622年征讨胡格诺派的战役(详尽始末、作为背景的国际局势、一系列条约与谈判)
·瓦尔特利纳事件(政府不同阶段的决策及依据)
·鬻官制的一些有趣的副产品(伴随波莱税的强制借款、将牡蛎贩设为官职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裁撤官职意味着以金钱将其从持有者手中赎回等)
·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类目,三个年份预算的数据实例及分析
·包税制的具体运作流程
·显贵会议与三级会议的区别、1626年显贵会议的诸项议题及会议结果
·大量舆情小册子节录
·拉维厄维尔、埃菲雅等被吕伊纳与黎赛留的显赫政治生涯所遮蔽的“次要角色”,以及一个刚刚重返权力中心、尚未在三十年战争的舞台上创下伟业也尚未断绝内政改革构想的黎赛留本人
仍有一些概念是书中虽提及却未做具体阐释的。不过这也绝非坏事——正是拜那些曾令我苦思而不解的段落所赐,我终于有了动力去自己搞清楚什么是财政区行省和三级会议行省、什么是cens和censive、属地税和属人税的区别、supreme courts的范围、什么是巡回法庭以及lieutenant général de province、gouverneur和intendant三者的关系等等。
Lublinskaya在第五章用了不少笔墨对另一位前苏联学者Biryukovich的富于吸引力然亦颇有预设结论之嫌的理论进行了有理有节的质疑与驳斥,我虽对Biryukovich并不了解,读来倒也兴味盎然。自然,她自己在本书中的一些论点似也难完全让人信服,但大体上其运用史料的严谨态度我很是钦佩,选用的史料本身对我来说更是宝贵。不管怎么说,感谢她为1620-1629这个历来被遗忘的时段奉献的这部出色著作。
《French Absolutism》读后感(三):关于吕伊纳之后、黎赛留之前的内阁人事变迁
关于吕伊纳之后、黎赛留之前的内阁人事变迁,此书与卡尔莫纳的《黎赛留传》观点相差甚远:舍姆贝格去职,卡尔莫纳称是因其廉洁奉公而不见容于布吕亚尔集团,此书则归于其任期内糟糕的财政状况;布吕亚尔集团的倒台,卡尔莫纳称是因其侵吞公款行为败露,此书则将主因归于外交失利(西耶里在未经路易十三许可的情况下接受了教皇在关于瓦尔特利纳问题的谈判中提出的不利于法国的条件,后查出他及其子皮西厄还在其他外交事务中对国王多有隐瞒)。
相比卡尔莫纳我确实觉得鲁布林斯卡娅看起来更严谨可信,毕竟其观点通常都有事实和数据支持(无论是否充分)。比如关于布吕亚尔集团因外交失利倒台,她提供了以下背景作为佐证:当时法国外交部门的全体成员也一并遭到了清洗(这件事还真奇葩,虽说“全体成员”实际也就那么几个)。
同样地,关于拉维厄维尔倒台的原因,卡尔莫纳模糊地归于(在瓦尔特利纳问题上的)无能及黎赛留御用文人们的小册子攻讦,鲁布林斯卡娅则指出他在英法联姻谈判中擅自向英方提议将天主教信仰自由纳入条约,非但鲁莽,其独断专行更是犯了路易十三的大忌(他是否忘记了布吕亚尔集团是因何失势?)。最有力的论据是,路易十三在致各大使的通告与致巴黎最高法院的信里都给出了与鲁布林斯卡娅的论点一致的解释,在致驻伦敦大使的信里还特别强调日后诸事均需向他禀报。
在卡尔莫纳的著作中,这个时期法国面临的一切问题总是源于佞臣把持朝政而路易十三听之任之毫无作为,可这与他之前之后的行事作风都太不相符了。鲁布林斯卡娅的观点要有说服力得多——无论如何他从来也没有放任过臣下,布吕亚尔集团和拉维厄维尔恰恰都是由于未得命令擅作主张而被罢免。
当然鲁布林斯卡娅也未能解释黎赛留上台前政府对瓦尔特利纳事件的消极态度。路易十三其大臣们绝非不明白事件的性质,他们一直在做外交上的努力,却始终避免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行动。鲁布林斯卡娅给出的理由是缺钱(举出了鲁昂爆发的抗税暴动为证),但黎赛留上台后国库也不大可能立刻充实起来,政策明显转变的原因何在呢……
补上一个有趣的细节:拉维厄维尔被罢免后一度身陷囹圄,后逃出国外,于路易十三死后回到法国,并于1651年再度担任财政总监直至1653年去世。当时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而下狱的贵族如巴松皮埃尔等在黎赛留死后多得到赦免,此公却直至路易十三死后方敢回国,或可侧面印证他的悲剧的根源不在于挡了主教的路而在于得罪了国王……而再度担任财政总监的经历或许可以说明他在财政领域的能力即使谈不上出众至少也是胜任的。
《French Absolutism》读后感(四):拉罗舍尔阴影下的宗教战争
很多涉及17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史传著作,对1621-1622年间征讨南方胡格诺派的战事都甚少述及,在本就不长的篇幅里也以负面评价居多,好像这只是一场由国王的一时脑热发动、一班庸碌无能的官吏和军人们具体执行的劳民伤财而一无所获的战争;同时期爆发的瓦尔特利纳事件更是让他们乐于将针对国内胡格诺派的征讨指为可耻的外圣内王之举。有趣的是,多数史传作者对1625年的拉罗舍尔之围却不吝赞美之辞——但是,作为同一场战争的不同阶段,拉罗舍尔之围和1621-1622年的战事真的有本质上的巨大差别吗?胡格诺派“国中之国”的消失真的是主观上荒谬的动机却带来了客观上良好的结果吗?
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更细节化、基于事实而非传统偏见的考察,Lublinskaya的French Absolutism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它是我目前看过的所有同类著作中,对1621-1622年的战事分析最全面、最细致的一本,很少会陈述一两个简单的事实后便急于做出片面的论断,而是有相对充分的数据和细节来支撑其观点。拜此书第四章所赐,我终于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审慎的思考,多少也得到了一些确有依据、不那么武断的印象。
战争的肇始:无谓之战或顺势应时?
路易十三的宗教战争从来也不是针对保证胡格诺派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本身,而是它的附加条款。正是凭借附加条款,政府要掏钱维持拉罗舍尔的城防,胡格诺则派拥有独立武装、控制区内堡垒林立,享有税收上的特权。而这个附加条款最初也只有八年期限,之后由亨利四世和玛丽·德·美第奇两度延长,路易十三所要做的只是加以终止。
而法国胡格诺派本身在亨利四世死后,对政府始终存在不信任感。路易十三不同于他的父亲,自出生就是天主教徒且素来虔诚。他有时确实会对信奉新教的近臣表达希望其改宗的态度,但毫无迹象显示他不能接受新教信仰的存在。然而玛丽·德·美第奇摄政期间亲西班牙的政策与西法联姻使得胡格诺派大为恐慌,担心丧失在亨利四世治下享有的种种特权。他们在1614-1620年间王公显贵与王权的斗争中,倾向显贵而与王室敌对,甚至在路易十三迎娶奥地利的安娜时派出军队试图阻挠王室的迎亲队伍。
纳瓦尔和贝亚恩又是另一番情况。作为亨利四世的龙兴之地,这两个地区在他成为法国国王后却未能与法国合并,而是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路易十三即位后纳瓦尔和贝亚恩人担心政府政策的改变,选择与法国国内的胡格诺派联合以抗拒可能发生的归并,并参加了拉罗舍尔的宗教大会,此举在法国激起公愤,以至于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上递交的陈情表亦要求结束这两省的独立状态。同时纳瓦尔和贝亚恩作为比利牛斯山区邻近西班牙边境的地带,对法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由于不施行萨利克法,尽管路易十三也身兼纳瓦尔国王的头衔,一旦他和他的兄弟没有直系继承人,这片阿尔贝王室的领土将落入胡格诺派的领袖、素来有不稳迹象的罗昂公爵手中(凭借其祖母伊莎贝尔·德·阿尔贝的血统)。路易十三出生前,罗昂曾被纳瓦尔人认为是推定的继承人。
结合以上种种,路易十三在1620年驾临波城、从而引发长达十年的宗教战争,似乎并不能说成仅凭一己的宗教狂热发动的无谓之战。既然早在1614年(路易十三尚未亲政)的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而非教士等级)的代表就要求归并纳瓦尔和贝亚恩,那么可以说这基本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意的。1617年御前会议即已下达归并纳瓦尔和贝亚恩的谕令,只是迫于与显贵们和太后的战事未息而无法施行。而且国王谕令的内容绝不是取缔新教信仰,而是要求纳瓦尔和贝亚恩服从法国政府的统治、允许信仰天主教以及归还让娜·德·阿尔贝统治时期掠夺的天主教教产,他在波城建起一座高等法院及做弥撒即是表明这样的态度。
瓦尔特利纳事件:攘外必先安内一定是错误吗?
抨击1621-1622年战事的最佳理由莫过于瓦尔特利纳事件。瓦尔特利纳地区处于信奉新教的格里松斯联盟管辖之下,其本地居民却信奉天主教,于1617年发起叛乱,并向米兰总督求援,西班牙军队由是于1620年借机占领这一地区。由于该地恰是西班牙治下的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之间的交通要道,一旦落入西班牙的控制下对法国将极为不利,而依据亨利四世朝签订的条约,法国对该地区的隘口有着垄断使用权,西班牙的军事行动无异于对条约的破坏。
征讨南方的新教徒,还是将西班牙人逐出瓦尔特利纳?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法国政府在内忧与外患间选择先解决内忧,是否一定是对内严苛、对外软弱?
如前所述,占多数的天主教臣民与西南诸省及纳瓦尔与贝亚恩的新教徒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绝非国王一人的忽发奇想所致;早在路易十三亲政之前双方互不信任的种子即已埋下,之后自然只能是胡格诺派的分离主义和共和倾向日重,政府结束其“国中之国”状态的决心也日强。而瓦尔特利纳事件的爆发则要晚的多,更具有突发事件的性质。
面对这一事件,尽管并没有采用公开战争的形式,法国政府并非完全不作为或敷衍塞责。国王和御前会议的诸臣清楚事态的严重性,也确实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了努力。1621年初吕伊纳之弟(未来的肖纳公爵)出使英国,约定两国共同施压,迫使西班牙归还瓦尔特利纳和上帕拉坦(原属詹姆士一世的女婿弗雷德里希),同时要求英国不向胡格诺派提供援助,并谈及查理一世与法国公主昂丽埃特的婚事。但英国只关心上帕拉坦,为达到此目的亦在商谈与西班牙联姻;拉罗舍尔则不断遣使向英国政府及与其有商业往来的伦敦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求援;詹姆士一世故仅对法国做出模糊的许诺。巴松皮埃尔亦于1月出使西班牙并取得签订马德里条约的成果,依据此条约,西班牙应归还瓦尔特利纳并平毁所有1617以来建造的堡垒。事实上直到1621年4月国王仍在奥尔良逗留,前往靠近边境的里昂并进而发兵瓦尔特利纳或前往普瓦图并由此进入南方征讨胡格诺派皆有可能,正是条约的签订促使他下定决心选择了后者。
尽管巴松皮埃尔本人认为马德里条约对法国过于有利,对其履行持怀疑态度,但当时的局势下政府也唯有寄望于它能够得以履行。毕竟在天主教诸省与新教诸省交界,局部战事早已爆发;两派平民之间的仇杀渐趋失控,4月时图尔的新教教堂被焚烧,国王的法官判处天主教滋事者死刑竟因暴民骚动而无法执行;胡格诺派不顾国王的禁令在拉罗舍尔召开宗教大会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八大军区,在图卢兹、蒙托邦、卡斯特尔及下朗格多克诸市镇周边开始占领堡垒、劫掠天主教财产甚至截留地方税收。
而马德里条约终成一纸空文,也未必一定是西班牙的阴谋,考虑到适逢菲利普三世驾崩、与荷兰的停战协定行将到期,西班牙也正处在风口浪尖,归还瓦尔特利纳以换取法国对莱茵兰的不干涉也有合理性。或许最初确实是米兰公爵自行其是、而西班牙政府看到法国忙于对胡格诺派的战争便顺势利用了这一状况呢?法国选择进军瓦尔特利纳,倒要冒西班牙援助胡格诺派以致后院起火的风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1625年罗昂与西班牙代表经萨瓦公国作为中间人,在皮埃蒙特进行过谈判,他的秘使于1626年被逮捕;实际上罗昂与西班牙的接触早在拉罗舍尔之围以前,只是没有确实的证据,只在后来由一个曾与他关系密切的军官透露。
甚至1622年间政府也不曾放弃这种努力,曾遣使劝说格里松斯人对西班牙军队发起攻击,并派遣莱迪吉埃尔率军援助(尽管由于Lublinskaya的语焉不详,此次援助行动的具体情形无从得知)。
战争的执行:笨拙,但是否不可原谅?
在1621-1622年的战事中,王军的优势在于兵力、装备和资源,罗昂的优势则在于地形及素来出产佣兵的赛弗那山区可以提供给他的有经验的军官。双方也各有短板:王军的兵力优势在道路情况糟糕的南部山地难以施展,指挥官们经验不足,劳师远征需要耗费大量金钱,而17世纪的行军速度、易守难攻的坚城和无法开展任何军事行动的严冬也使得蒙托邦和蒙彼利埃两次围城战都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罗昂一方则要面对拉罗舍尔宗教大会的牵制、胡格诺派诸城中主和派的离心离德以及在极其有限的区域内征兵和筹集金钱的困难。
1621年王军确实犯下了许多错误。当时的法国军队久已未经战阵(与显贵们和王太后的战争过于简单,没有参考意义),下层军官们毫无纪律观念、对敌军的强固据点发起无脑冲锋,上层指挥官也时有自行其是的行为;军中缺少合格的工程师,仅有的一个意大利工程师的建议也时常不被听从,导致工事的修筑极为拙劣;时至8月中旬仍坚持围攻蒙托邦(但绕过该城同样需耗费时间),且对该城规模估计不足,导致以既有的兵力根本无法完成合围……加上瘟疫忽然爆发和寒冬的降临,围城宣告失败。
1622年的战役中王军已经吸取了前一年的教训,较1621年进展更快,但一些前一年归顺国王的城市已再度被胡格诺派占据、需要收复,而蒙彼利埃之围终于还是拖到了10月、难以在冬天来临前破城,加之瓦尔特利纳局势的日益严峻,最终促成了蒙彼利埃条约的签订和一次不彻底的胜利。
事实上,法军在1621-1622年的战事中表现出的种种笨拙之处,是他们之后的20年里也一直难于解决的。必须承认大孔代在罗克鲁瓦一战成名以前,法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天才,也从来没有军事理论上的革命性创建。但要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军事天才和军事理论的革命确实是极有利的因素,但从来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大孔代和之后太阳王时代强大的法国军队可以说正是从17世纪前期一场又一场笨拙的战役中成长起来的。而不管怎样,消灭王公显贵和胡格诺派的独立武装、平毁国内林立的堡垒,这些理念的方向是没有错误的,具体执行的过程固然远远谈不上出色,但也绝非不可原谅。
战争的投入与产出:劳民伤财而一无所获?
法国政府在筹备对胡格诺派的战争时确实面临着财政上的困难,急需增加一笔收入,而这笔钱的主要来源靠的是恢复征收针对官僚阶层的波莱税、向教士阶级强制筹款以及向金融家贷款,针对平民的盐税在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用来支付贷款的利息。波莱税作为广遭非议的税种曾于1617年被取消,而1620年恢复征收的波莱税为期九年,同时附加了新条款,不再确保官职的继承权而只确保在国王有意赎回官职时,官员的继承人可以得到一笔远低于该官职真实价值的补偿。此条款遭到官僚阶层强烈反对,以至于政府在与高等法院做了一番斗争后才付诸施行。鬻官制在法国由来已久,自有它产生的背景。而其诞生后出现了限制官职世袭的“四十天准则”,1604年又出现了既可供官员对抗“四十天准则”又可供政府增加收入的波莱税,可见官职鬻卖远非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17世纪的法国也不具备根除这一制度的条件,1620年的法国政府已经通过新条款尽可能减小其弊端了。
至于战争的成果,和之前与王公显贵们的战争一样,将纳瓦尔和贝亚恩并入版图以及终结胡格诺派的“国中之国”同样是对中央集权的增强,其意义想必也无须我再赘述了。确实,1622年蒙彼利埃条约签订后,政府仍然未能取得对胡格诺派的彻底胜利,一些史学家据此声称法国政府在2年的战争中毫无所获,最终还是要靠大量金钱买通胡格诺派的首领们归顺。事实是否如此?不妨看看蒙彼利埃条约的具体条款:依据条约,对南特敕令予以确认;平毁新修筑的堡垒;在除拉罗舍尔和蒙托邦以外的地区恢复天主教信仰;胡格诺派城市允许国王在城内驻军,国王宣布特赦,蒙彼利埃的城堡和新工事被夷为平地,该城的领事(consul)——一个天主教一个新教——由国王指派;罗昂被任命为尼姆斯、卡斯特尔、于泽斯和赛弗那总督,但不拥有驻军,政府为普瓦图总督职位拨出一笔6万埃居的年金,由罗昂支付。显然政府并不打算在2年的征战后回到原点,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己方的战果并防止胡格诺派死灰复燃。事实是至蒙彼利埃条约签订时,留在胡格诺派手中的城市已屈指可数,而在条约签订到拉罗舍尔之围间的休战期,政府也从未放弃争取胡格诺派贵族与富有市民改宗、操纵市政选举,尽管蒙彼利埃的城防已被拆毁,驻军也没有撤离。拉罗舍尔之围固然是伟大的胜利,但如果没有1621-1622年间对该城陆上一侧的彻底封锁(路易堡即为此目的修建)及在南方赢得的有利形势,只怕也是难以达成的吧。再回想一下1622年国王先去南特平定苏比兹之乱再前往南方围攻蒙彼利埃、同时还要考虑瓦尔特利纳的事态并向香槟一带派兵防御曼斯菲尔德的佣兵的窘境,不得不说一旦开始追究细节,就会发现很多看似“简单”的政治抉择都远不是后人们想当然的那样轻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