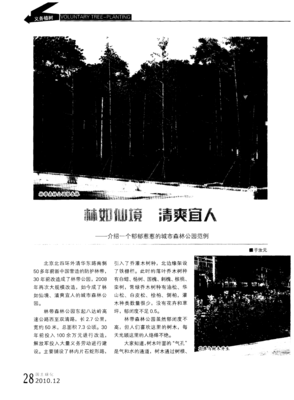防风林的外边读后感1000字
《防风林的外边》是一本由黄启泰著作,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元,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防风林的外边》读后感(一):被构建的“写作者”
对这种实验文学越来越失去兴趣。它完全不在乎情节构建,段落失去逻辑联系,人物角色形象不明确,甚至无法搭建基本意像。你可以用“内向世代”“后设”“内在风景”一些华美词汇来矫饰它,但因为我浅薄无知,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心理专业的作家在玩弄文字游戏。 唯一有点兴味的是数篇短篇小说一起构建出的的那个写这些小说的“作者”(不一定就是黄启泰本人,而是黄构建出来的那个写作这些小说的人)的形象,有点意思。 他名字可以是HS,苍白瘦弱…总之是对自己身体很不自信,还有隐睾这种生理性疾病,使他的气质是敏感、柔弱、内省的。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自身的“阴性”,使他对具有“饱满硬凸的胸脯”“肌肉发达”“粗硕的颈根”“宽阔的背影”“残忍性情”“健美的体格”“硕大性 器”的男性有着特殊欲望和偏好。当然,这种欲望是逐渐明确和坦露出来的。在他还年轻时候,他对“安静秀气”“消瘦纤细”“帅气”的年轻男人也会有自然的悸动和好感。我觉得,对后一种“天使类”男性的好感映射了那个“写作者”的自恋,而对前一种“魔王类”男性的迷恋是“写作者”真正欲望的投射。
所以这本小说集其实有三个写作者的形象:现实中的黄启泰;所有这些小说或多或少描绘出和共同构建起的那个半真实的“创作者”;还有就是《年轻计程车司机的海岸心事》等篇中的那个“写作者”。后两个,我想或多或少一定有作者的影子。
《防风林的外边》读后感(二):黄启泰自序:对镜
自序:对镜
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有一幅画:一位男子站在镜前,镜中却映现他的背影,而不是脸。因为镜台上的书本忠实地反射在镜中,表示他看见的倒影确实是自己。然而,如果镜子是真实的,为什么人和书本反射出不同的镜像?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时,有一种莫名的困惑,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男子,即使画中的背影转过身来,也无法证明镜中的脸是这位男子。如果镜子是真实的,一个人看到的却不是自己,而是他人的倒影,应该只有在自我否认和幻觉中才可能产生这样的扭曲吧?《防风林的外边》写于我大学和研究所求学时,或许可以比拟为这种自恋带着他人倒影的寻找认同纪录。
《防风林的外边》首次出版于 1990 年(尚书文化),书中作品大多是受已故作家林耀德的邀稿。《年轻计程车司机的海岸心事》是书中最早完成的作品,参加当时文建会举办的第 1 届青年文艺作品研讨会,长达十天的研讨会,每个学员的作品都会由两位文坛老师讲评,林耀德先生当时担任这篇小说的讲评老师(写到这段回忆,不禁想起热忱的承办人柯基良先生和苏桂枝小姐,柯先生已于 2017 年离世,作家袁哲生也是其中的学员)。往后几年林耀德先生陆续和我邀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导读》《魔王为父》《秋日盐寮海边》及《觅食者的晚宴》等文,刊载于《联合文学》和《幼狮文艺》等杂志,后面两篇发表时并由郑明娳和张惠娟两位教授撰文导读。《韩波的朋友》和《角力》是最后发表的作品,当时是 1997 年,接下来到英国求学后,就几乎没有作品发表了。2000年夏天,元尊文化计划重新出版《防风林的外边》和另一些未集结的作品《花与美神相食的存亡录》,编校完成后,一直没有上市,后来听到主编王淑慧病逝的消息。这些年来,我转换生涯跑道,不再挂记书稿下落,也许是刻意放手,且让这些作品随风飘逝、远离我的生活!转眼之间,《防风林的外边》出版将近三十年……朱岳先生去年来函表示有意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历经这些年迁徙,文稿早已不知去向,我回信敷衍回老家找找,沉寂了半年,朱岳先生请人在台北的范纲桓先生协助我扫描原书和杂志影本,转档为文字,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因缘际会,仿佛希望和读者见面的不是我,而是书,书自己本身有生命与其意志,这些年的荒废也许不是没有意义,让我有充裕时间从容离开过去的自己,让这些作品自身沉浸在时光流逝的安静中,经过许多年,我也该心平气和看待作品中的孤独和冲突了。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近三十年没有新作发表,或是什么时候准备拾笔重写小说,真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通常回说这辈子从事心理学研究的时间远超过写作时间,写作用的脑敌不过研究用的脑,表示大脑结构可能已被经验重塑。“用进废退”的说法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但与我的内心感受并不相符。我不确定其他写作者是否和我一样曾有过和未曾谋面的人神交的经验,我总觉得一个人一旦曾经立下盟誓投入创作,承诺要真诚对待生命,不管以后他是否踏上以创作为生的道路,那种决心会持续影响他在往后人生与世界相处的方式,让他觉得与喜欢的作家心灵相契,面对这些作家经历的痛苦特别敏感,仿佛是一起长大的朋友,一种无法确定何方而来的友情让我在精神上可以无忧地依附他们。今年 1 月份,我看了一部土耳其导演努瑞·贝奇·锡兰的电影新作《野梨树》,大学刚毕业、一心想成为作家的锡南,带着刚完成的小说《野梨树》回到家乡,寻找出版机会,有一幕锡南打开卧房的衣柜,导演引导观众注意贴在门背面的相片,我认出其中一张嘴角衔着烟的男子是卡缪,另外一幕锡南在暴雨骤至前跑进小镇的书店躲雨,当他走上二楼与本地作家展开侯麦(法国导演)式的冗长对话前,镜头停留在楼梯旁墙壁上的海报,我认出了几位作家的脸孔:卡夫卡、吴尔芙、雷莘、乔艾斯及汤玛斯 · 曼,卡夫卡深邃的眼神从我年轻时就一直以那种方式凝望着我,在那瞬刻间,不禁热泪盈眶,我强烈感受到和这些作家之间的心灵共鸣,觉得导演和我、以及这些逝者都是同路人,“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在时光的洪流中,仿佛有个生者与逝者隶属的无形国度,而这是我从事心理学研究多年不曾有过的感动。我知道年轻时的誓言和承诺并没有因为世故而消失,像小白羊颈项间的铃铛在山海交界处轻唤,维持着现实和想象的边界,一股良心般的力量始终支持着我。虽然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人生至此,我也没有再多可以逃避的借口哩!
这些年来,如果有些长进,或许是和自己相处得比较舒适,站在镜子前面,不再因为忧心镜中背影是不是自己而困惑。我学会用时光推进的方式,将玛格利特的画解读为未来式:仿佛有个迫不及待需要即刻前往处理的要事,也许太过于紧急,画家来不及让我们看到镜中的脸,男子就转身离去,因为太迅速了,我们只看到离去的背影。我想用诡辩来自我安慰,或许离开才是有益作品的健康,像埋在泥土里的果实,让它们不受干扰地分解、重新抽芽、即使因而被遗忘,其实都没有什么不好。在这些小说作品中,我写过自己,也描写过他人,有些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他们曾经进入虚构世界,有些人或许洞察到我的灵感来源,但尚未查证就已离开这个世界,把秘密带走,所以我是唯一知道这另一半秘密的人。如果作品完成后,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就脱离了,往后解读作品都是读者自家的事,容我把镜中的背影当作是作品,转过身后是不是镜前的人,其实就无关重要了。
《防风林的外边》读后感(三):小说测评《防风林的外边》|关于文学的文学,后浪挖来的遗珠
作者:Jay
校对:litcave 工作室
配图:Online
近几年出版的文学丛书中,能为中国内地市场带来巨大惊喜的,当数后浪的「华语文学」了。
去年年底,bilibili播出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其中第一集《书海编舟记》讲了后浪编辑朱岳推广袁哲生作品时的一些故事,朱岳的团队四处推广《送行》,却屡屡遭拒。
如此波折的经历,大概也是「后浪·华语文学」这个系列中每本书的缩影:读过的人叹为佳作,极力推崇;未读的人,不屑一翻。
对于当今中国大陆市场来说,何为经典,何为纯文学,似乎已经定型了。
但是,后浪这个系列文学作品的出版就像一只洪水猛兽,把内地读者的视野铺开到港台、马来西亚甚至更远的华语世界同时,也让那些遥远的、被忽略和遗忘的旅人回到「中国文学」这个古老的汉语家园。
之所以费尽笔墨做这个开头,是希求进入《防风林的外边》这本书测评时能让读者知道,这个系列的每部作品,亟需中国内地读者去阅读和接受却声响一直不大。真可谓缺乏「试金石」。
《防风林的外边》是台湾作家黄启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1990年初版于台湾。那个年代的许多文学作品,无论内地还是台湾,都在探涉文学书写的边际,作为「新世代」的领头羊,黄启泰当然不能回避这一挑战。
其作《防风林的外边》,便是「以书写的不可能来创造写作的可能」,防风林作为象征,既为沙滩和土地抵挡着海风的侵蚀,也阻隔了被垃圾填满的大海。
借由这一象征「先入为主」再进行阅读的话,要想读懂书中那些看似混乱、错位、甚至支离破碎的短篇,其实不算太难。
不过,也切忌一口气读完,毕竟11个短篇是作者不同时期所作,因而表露出对故事的驾驭程度也深浅不一。要想读出味道,千万别囫囵吞枣。
开头几篇有浓烈的浪漫色彩,《韩波的朋友》中,作者用兰波和魏尔伦作为主人公,以书信体形式创作。与其说这是在「重现」两位诗人,毋宁将之看成是作者想找一条艰辛的道路,跟死寂的知己对话和抒情。
而《少年维特的烦恼导读》始,文风突然冷冽,阅读过程真正进入了探寻的阶段。
这种小说被称之为「后设小说」,也即关于小说创作本身的小说,它读起来有一定难度:
一是要求读者关照的不是小说剧情和人物形象,而是文本的意象和隐喻,以及这一切所指向的作者本身的内在世界。
二是它通常打破了读者固有的阅读模式,以一种我们未知的、不确定的小说结构呈现,要想读懂,读者不得不集中精神摸索它的轮廓,并思考这结构本身的寓意。
就拿短篇《防风林的外边》来说,主人公是个写作者,他正展开一段旅程,旅程所见所闻蔓生出主人公将要写的小说,这一过程不断被作为读者和评论者的角色干扰,而主人公将写的「那篇小说」实质也是他的自我指涉。
这样的小说,就像开拓盘山小道般十分危险,一面是文字游戏的无底深渊,另一面是过于关照作者自我的坚固岩壁。
在这点上,黄启泰也算拿捏有度,他不会在叙事技巧上过于花巧而致使读者感到难读,但叙事的层级之间又有一定阶距,迫使读者停下来花心思去架接,去整合。
在表面上,每篇故事几乎都保持了传统小说的痕迹,欢迎任一读者的到来,然而能真正走到最深远处,和作者一样走到小说主体性危机的边缘那个位置的,恐怕寥寥无几。
总的来说,这不是一部能推荐给任何人读的小说,如果读者已经探寻过小说的荒芜之地,一定不可错失这部作品。倘若不明究里也冒然阅读,只会因迷失而感到困倦和沮丧。
《防风林的外边》读后感(四):黄锦树:关于海,与及波的罗列
《防风林的外边》黄启泰 1990年黄启泰的《防风林的外边》1990 年初版于台北,尚书出版社,距今已二十八年,台湾文坛记得这作者的人大概不多了。因为《防风林的外边》之后,作者几乎就从文坛消失,大概努力当一个学者去了。还记得这名字的,大概就几个写作的同代人。
《防风林的外边》在1999 年左右曾经有一次重新出版的机会,台北元尊出版社杨淑慧女士甚至找我为它写过序,后因杨女士猝逝而作罢。元尊原拟出版的黄启泰小说是两本,包含一本题作《花与美神相食的存亡录》的新著。其中有四篇(即《韩波的朋友》《觅食者的晚宴》《穿过记忆的欲望》《角力》)如今被移到简体版《防风林的外边》。尚书版《防风林的外边》收了八篇小说,除了《黑狗奇遇记》之外,其他七篇都重现于简体版。换言之,简体版《防风林的外边》是迄今最完整的版本。
《防风林的外边》 黄启泰 2020年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讲稿里提到,在《防风林的外边》集子里主要的几篇小说发表的1988 年间,恰也是同龄人骆以军(1967)初试啼声,在文学奖试身手的时候;比我们小两岁的赖香吟(1969)、邱妙津(1969—1995),比我们年长一岁的袁哲生(1966—2004)也开始发表作品了。但他受肯定是1994 年以《送行》得中国时报短篇小说首奖,比骆以军还晚了三年(骆1991 年以《手枪王》获同一奖项),我自己则比袁哲生还晚一年得该奖。而黄启泰,不是循文学奖路线登场(不知是没参加还是没得奖),受野心勃勃的林燿德(1962—1996)赏识,作为“新世代”的领头羊,作品得以顺利发表并快速出版。但书出版后文坛没任何反应,作品也很少被学界讨论。林氏鼓吹的“新世代”随着他早逝而烟消云散,迅速成为历史陈迹。学界一向倾向把目光投注在几个“明星”身上。那时的台湾文坛,张大春、黄凡是当红炸子鸡,同世代不过三十多岁的朱天文、朱天心也很被看好。其时,台湾刚历经政治解严,新思潮大量涌入,很快就会被学者宣布进入后殖民∕后现代时期;激烈的认同分歧即将成为常态,且遍及所有的领域,学潮、社运纷起。黄启泰的小说仿佛一开始就与这一切无关(可能也因为年轻),集中心力关注主体的内在风景。
我曾在《他者之声——论黄启泰的〈防风林的外边〉》那篇“废序”里,针对《防风林的外边》的主体篇章(《少年维特的烦恼导读》《秋日盐寮海边》《防风林的外边》),借用黄启泰的自白为引子来解释。他说:“我的构思通常凭着一种深刻的情绪状态,不事先拟定故事大纲,而是顺着故事的开头,慢慢地把那种情绪或是感觉,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来。”因此没什么故事性,像抒情诗那样,着意经营的并非情节。他又说,那些作品
“十分强调气氛的营造,尤其喜欢叙述单一景色,这景色不是纯然的客观现实,而是存在于人的心理状态的时空横切面;读起来好像是一幅幅的心理风景……也正因为我把故事建立在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模糊的边境,忽略了许多外界正在进行的有意义事件,过度专注内在视景的呈现,而不能从社会、政治、历史……等朝外的观点来剖析事件,而且由于这种建构故事的方式,主观成分非常强,使得正文本身变得不够透明化。”
这些自白相当准确地描述了那些作品的特性。抒情、唯美、图像化、内省——内在风景。从最早的《年轻计程车司机的海岸心事》那种单纯而不可救药的耽美抒情,到《防风林的外边》《秋日盐寮海边》较为冷冽的观照,经由一趟没有目的的旅程,我,及作为“他我”的流浪汉,看不出因果缘由的死亡,相似的场景(防风林,海边)、意象(木麻黄,尸体),甚至关键工具——照相机——摄取物象光影之物,机械之眼,《秋日盐寮海边》:“我努力微笑着走向前,对准镜头,按下快门。”在溺死者的相机内留下自己的影像,“这样一来,他便要将我永远摄入他底灵魂”,犹如跨越死生的另类自拍。《防风林的外边》更内嵌一个写作者作为观察者,于是小说乃自我指涉,叙事随旅程所见蔓生,不断被作为读者及评论者的角色干扰。于是小说正如其篇名所引的林亨泰的《风景No.2》所示:“防风林 的∕外边 还有∕防风林 的∕外边 还有”……仿佛可以无限延伸。正因为主观臆想还是客观现实的界 线并不明确,外在的旅程因而可能不过是内在的旅程。而主词位置的松动(我―他),文类边界的溶蚀(诗,小说),性别界线的混淆(常以人称转换的方式呈现),暗示了书写者及书写本身处于危险的状态,表达的不可能性悄悄吞噬它的可能性,写作和叙事本身均趋向衰竭——主体亦濒临消亡。
而年轻的黄启泰走得最远的地方,即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导读》。探索书写的不可能所导致的存在的不可能——仿佛只有书写的可能性可以保障存在的可能性。那造成了主人公(甯秀男)的精神分裂,失去自我,被想象的、曾经存活的强大的书写主体占据。那其实是复数的他者,主人公过度崇拜的对象,那位置,游移于三岛由纪夫,或三岛的妻子,或歌德之间。最后,这被他者侵占的意识,以伪主体的清醒目光回过头来,指称这小说不甚可靠的叙事者为威廉,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之叙述者“我”的收信人。《少年维特的烦恼》中为情所困,甚至殉情的主人公,那样的抒情主体,被植入“殉国”的妈宝三岛由纪夫,几种不同的“烦恼”被叠印为一种错体的“导读”。这样的小说常被归类为“后设小说”,但“后设小说”自20世纪80 年代中旬被引进台湾之后,常被小说家和学者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理解(视为“后现代小说”的技术指标),或视为对写实主义的彻底颠覆(尤其是张大春的小说)。然而,像《少年维特的烦恼导读》(1988)这样的小说,其实比黄凡《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1985)、张大春《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1986)更深刻地触及写作主体的存在危机。那已不是文字游戏,那样的小说暗示,写作的不可能,源于存在的不可能——因为,所有的写作者必然是个有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然而,作为“入戏太深”的读者,《少年维特的烦恼导读》的隐含作者发现,不止一切可写的都被“早行人”写过,甚至一切经验都曾经被经验过,“我”可能早已被“活”过。那个以为可以持有自我意识的“我”,其实早已是他人。
如此以书写的不可能来创造写作的可能,爆发出的或许是衰竭的灰色光芒。那仿佛是过于耽溺内在风景、长期蛰居都市、耽于阅读却经验贫乏的“内向世代”早衰的寓言。
由木麻黄构成的防风林是为了挡风,挡潮水,挡盐分,保护沙滩,保护土地。防风林的外边还有什么?当然就是海。真正深不可测,但即将被垃圾填满的大海。
2018 年 10 月 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