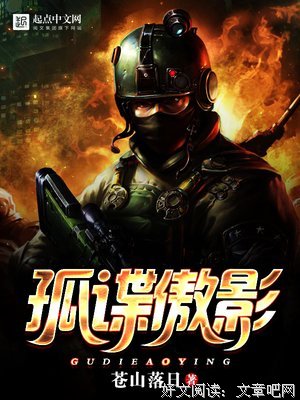《寒风孤谍》读后感摘抄
《寒风孤谍》是一本由John le Carre(约翰 勒 卡雷)著作,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0.68,页数:2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寒风孤谍》精选点评:
●会说人话的翻译对于一本书太重要了。同样是杰作,《锅匠》那本的翻译黄先生肯定是被故意请来黑勒卡雷的。。。
●情节过于简陋,结尾写得还不错
●20140115购买。结尾部分很出人意料。
●地摊2元钱入手,8新,开心ing
●间谍小说的问题与推理小说类似,作者必须在遮遮掩掩里给出暗示。勒卡雷试着将故事的重心向人物倾斜,却被自己枯燥的道德观绊倒了。
●啊还是看书解决的我最关心的问题......原来他们俩没好上也不影响整个计划...
●结尾的翻转出乎意料,好看。
●棋中有棋,故事棒呆!也有很多关于意义和人性的探讨。每个人都有自己跳脱不了的思维方式做事逻辑,能够看清这一点,也就能够操纵这个人了。
●此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柏林谍影》、新华社版《受冷漠的人》和珠海版《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故事还可以,人物也比较喜欢,结尾的一处情节安排得太假,翻译也真的不算太好!
《寒风孤谍》读后感(一):寒风孤谍
如同格林的小说,这里的老男人主角,也用其忧伤和冷峻打动了我。虽然为了了突出故事情节的惊险刺激,人的个性已经做了简化,变得扁平,而更服从于叙述路线的需要。
随便最初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崇高的理想,还是平实的谋生手段,掉进一个枯燥且危险的工作,再也无法脱身,视所得多少决定该牺牲多少,利益是唯一,人性是累赘。这样的斤斤计较,和另一个方面的满不在乎,冷酷的法则中,个人永远身为棋子,瑟缩于寒风中无能为力,越来越冷--如果你还有颗心的话,这样的情绪感染了我。至于所谓的爱情,为保护一点温暖和纯洁(一个傻姑娘的爱),最后付出生命代价,这一点煽情倒没什么了。
这是本最终能让人抽身出来的书。因为它告诉你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不提出疑问。不需要无谓的思考,答案就在此地。通俗小说一般总要这样,乐此不疲。
不由不想到《文静的美国人》,那本令我痛哭而不能出声的书。无法救赎的痛过于深重,难以理解,如果一部作品希望得到流行就得避开它,比如说,那个广受欢迎的《肖恩克的救赎》,实在是可笑的。
《寒风孤谍》读后感(二):李玛斯
李玛斯为什么会翻下高墙,回到死去的丽丝身边,去挨那些注定会将他打倒的子弹··············
此时的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人生经历过不幸,事业遭遇过惨痛的失败,最后一次行动,居然当了一枚棋子,任人摆弄,摆弄完了,还得自己爬回去。
当卡尔死的时候,李玛斯的状态并不好,他后来参与那个计划,要求他表达不满,装作愤懑,他酗酒,他潦倒,他消沉,他在扮演一个任务要求的角色,但那何尝又不是真实的自己呢———一个失败者。
是丽丝的柔情一点点感染了他,在他病倒时,在他于法庭之上,丽丝总是依恋他,总想帮他。他深知,这一切终将结束,如有机会,他还会做回自己,到那时候,除了丽丝,他还能依靠谁呢?
事业,残酷的事业,混蛋们编织的事业,他算是交差了,也腻烦透了,他此时可以抽身而去,然而自己爱的人却在最后一刻倒在了那面墙下,李玛斯的精神世界也在这一刻随之崩塌。
他清楚那句警告,也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在探照灯的强光下,他近乎本能地翻了回来,走到了丽丝身边,在枪口下走向了自己人生的终点···········
《寒风孤谍》读后感(三):像一头瞎牛站在斗牛场上
最初几章看的很是无聊,都不知道在讲些什么,到后来知道主管派他去做最后一个任务,这才来点兴趣,按照主管的要求开始堕落酗酒打人,吸引犹太人费德勒的注意,把自己以前在情报部门知道的东西筛选后告诉费德勒他们,制造出费德勒上司蒙特叛变是英国间谍的“假象”,利用他都手干掉他的上司,这就是李玛斯这次的任务,他很乐意去完成,因为他一手建成的情报网一个个手下就是被蒙特干掉的。 就在任务快要成功时,蒙特带来了证人丽丝,李玛斯的亲人,她对他要做的事一无所知,在一次次问话后,局势瞬间反转崩溃。李玛斯为了救丽丝费德勒,把一切都坦白了,蒙特成了胜利的一方。 忽然间他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是被安排操纵,他们故意把他瞒在鼓里,为了让他完美的演绎,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干掉费德勒,这位威胁到蒙特的人,因为蒙特真的是英国方面的人,是隐藏在东德反间谍机关内部的高级情报员。 读到这儿,我感觉自己和李玛斯一样被耍了,但兴趣被点燃了,因为忽然间有种柳暗花明的感觉,很妙。 李玛斯的任务完成了,他和丽丝也被安排逃走,正好第26章名为归来,我想这下可以圆满了,可是忽然出现柏林墙铁丝网这些字眼,和开头是那么相似,我神经绷紧,感到不妙,祈祷他俩安全回国。 结果,***,在墙上即将逃脱时,希望瞬间破灭,强光机枪,丽丝中枪身亡,李玛斯已经翻过墙了,周围有熟人让他快走的劝告,但那时李玛斯的精神世界已经崩塌,他从新回到墙这边,像瞎眼的公牛般来到丽丝身边,直到倒下。 一切是那么残酷,冷血,没有什么奇迹。 他们知道的太多了,他能保守秘密,可普通人丽丝能不能保守住就不得而知了,这是危险的,就像里麦克的情人一样,英国情报部门和蒙特是不允许的,所以她必须死。 他们其实和里麦克这些间谍一样,有时不是死在敌人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在高层眼里他们不过是棋子,没有利用价值后就会被抛弃,死不足惜。 在不同的时局中善与恶会对调,那些残忍可恶的人因为有用而得以生存,那些和善正直的人因无用而被牺牲,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大局。用李玛斯自己的话,这就是战争。
他走进寒风中,再也…… “以前我没读过间谍方面的书籍,因为我对这个词不感兴趣,自认为不好看,”张天星想了想接着说“不过我想现 | 豆瓣日记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700373235/
《寒风孤谍》读后感(四):转文
勒卡雷从来都希望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间谍世界,还有他对社会人生的真实看法,哪怕它只是一片灰色的阴影,哪怕它并不美好。
张 楠
2008年9月,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新书推出之前,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上先爆出了关于他的一个惊人故事。标题很耸动,说这位间谍出身的间谍小说家“差一点变节”,内容大致是冷战时期的他,对越过东西方的界限很是心动,只是最终没有实施。后来勒卡雷本人在伦敦的伊丽莎白女王厅为新书宣传作演讲的时候说,报道登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有点不确定是不是能够自由地来演讲了。
他很严肃地又给《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信更正,说自己只是理解和同情那种感觉,却并没有尝试要去做。“做这一行久了,就越来越靠近边缘。有时候只差那么一小步,似乎就可以一跃而过。”这句话被报纸大肆利用,后面加了点点点点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有趣的是,如果尝试以正面的角度去解读它,这句话可能恰恰反映了这位间谍小说家对自己曾经做过的工作的某种理解,和他创作的部分原因。
在1960年代前后,尤其是著名的双面间谍金·菲尔比叛逃前苏联之后,整个英美情报机构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气氛当中,勒卡雷称之为“大面积的妄想症瘟疫”,只要在某个级别以上,每个人都被怀疑是苏联派来的间谍。当时勒卡雷的一位同事到美国出差,每天都被强迫换一个房间。他说,每晚他回到宾馆前台,报出自己的房间号码要拿钥匙,服务员都会对他说,先生您记错了吧?您不住这间房,您住在几几几,这是您的钥匙。总是相同位置的房间,不同的楼层,而房间里的摆设,包括他自己的东西,都一丝不差地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他说除了CIA,没有人能做得这么精确。勒卡雷和他讨论为何他会有此待遇,他说:“他们怀疑我。于是给我施压,想让我精神紧张。”而的确,在英国的军情五处,上级也在对这个人进行彻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可怜的同事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总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越线的事?又或者,其实自己真的是那边的?
在冷战的日子里,东西方是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恐怕唯有这些间谍是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群,而外界的疑云和自己内心的不确定让东西边界真的模糊了起来。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从间谍世界里走出来的勒卡雷写得更好了,就像他自己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说的那样,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个主题我已经在好多部小说里讨论过了,最著名的就是《完美间谍》(A Perfect Spy)。”
今年10月1日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厅的演讲上,七十七岁高龄的约翰·勒卡雷同在场的书迷分享他的间谍与写作生涯,从那个外表衣冠楚楚内心却是流氓耍白烂的父亲说起,直讲到在瑞士学德语,又到汉堡当领事。讲到兴起,便从桌上拿起一本书读起来,说,你们看我早已经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某本小说里。这是真的,这位作家的每一段经历,待过的每一个城市,似乎都有那么一本或几本小说作为见证。从提笔至今发表的二十一部小说,就仿佛是他的人生记录,也是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忠实体现。
勒卡雷进入间谍机构工作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他亲身经历了柏林墙的修建和倒塌,而对冷战的深刻体会也直接催生了他的代表作《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这部同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金匕首奖和来自美国的爱伦·坡奖的间谍小说被誉为描写冷战最好的作品,而它以及其后的诸多作品,也真的与多数间谍小说的写法都不太相同。虽然广义上,间谍小说仍被划归到“犯罪小说”的大类别里去,勒卡雷却并不把“犯罪小说”所必备的悬念倾注于情节当中。相反,他给主人公的性格安插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他们往往矛盾彷徨,游走于理想与现实、责任与情感之间,有时候遵从了国家意志却远离了人本身的友谊与忠诚。人性的各种可能性构成了勒卡雷的作品作为类型小说,能够吸引读者的因素,而同时也让它们跳脱出类型小说的框子,成为与严肃文学最接近的间谍小说。
演讲中,读者数次问道他笔下人物性格和背景的复杂性,这是他们最喜欢他小说的部分,却也是最好奇的部分。他说:“如果每个人物都简单,你根本就完不成一个故事,至少我没办法。就像每个人都有个父亲,也都有过去。”“这些发生在不同的地方,昨天或者今天的故事,故事里的每个人都在尝试做着正确的事,可是每个人都失败了。”这几乎就是勒卡雷对间谍这份工作的理解和同情,他用这样一种基本的态度和书写方式,最大限度地描绘出了战后欧洲间谍世界的荒唐扭曲的本来面目。
冷战结束之后,推理小说评论家唐诺先生曾以《池塘结冰了,野鸭子往哪里去》来形容柏林围墙倒塌后间谍小说生存可能遇到的问题。东西对垒不复存在,小说家要写什么呢?然而世界本身很快就给出了答案,苏联解体,我们还有中东伊拉克;斯大林不在了,我们还有萨达姆本·拉登。后冷战时期,勒卡雷的小说不再局限于单一题材,而是将它们扩展到更大的地理范畴——譬如以色列巴勒斯坦(《女鼓手》)——或是更广泛的话题——譬如商业腐败丑闻(《永远的园丁》)。
在伦敦演讲的最后,勒卡雷对读者说他只写“今天”的事,他希望自己永远和“当下”相关联。所以到了2008年的新作《头号逃犯》(A Most Wanted Man),他开始讨论后911时代的恐怖主义,在通常比现实世界慢半拍的小说世界里,这是一个新得不能再新的话题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勒卡雷熟悉的城市汉堡,而这里,恰恰也就是911事件策划者的大本营。据说911事件发生的当天,勒卡雷本人就在汉堡;而五年后他又重返这座城市,并为当地电视台录制了一期关于911的节目。他在两个不同的时间走在以往熟悉的街道上,真实地感受到911事件之后,社会环境和氛围的改变。正是这些见闻,让他产生了写作这本小说的念头。比如在描写汉堡广场的时候,他说四周似乎多了许多不相干的人,而一旦有穆斯林面孔经过,他们就会立即进入戒备状态。就像六十年代以后的英美情报机构,在恐怖主义时代的西方世界里,伊斯兰教徒的生存环境忽然紧张了起来。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有俄罗斯血统的年轻穆斯林伊萨只身来到汉堡,身上带有明显的在狱中被折磨后留下的伤痕,不管在瑞士,还是在土耳其,他似乎都是头号逃犯。但与许多穷困潦倒的被迫移民者不同,伊萨随身带着一家英国私人银行中巨额账户的提取密码。他求助于当地一位女律师安娜贝尔,请她为自己处理移民和金额提取的事宜。同样卷进这桩事件的还有这家银行的拥有者,一位英国绅士布鲁。这样神秘的身份和神秘的财产当然引起了美、英、德三国情报机构的注意,经验丰富的德国间谍巴赫曼也因此和他有了直接的接触。大致上,勒卡雷把一个明显的悬念,即主人公的身份——尤其是金钱的来源,放在故事的一开头,而当情节逐渐展开,谜底一步步揭晓,却又有更多更广泛的问题被作者一一提出。譬如伊萨的过去在他的性格里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烙印?譬如对于站在西方立场的安娜贝尔和布鲁来说,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亦敌亦友的伊萨?来路不明的金钱是否可能最终用于正途?而那位真正的间谍,要面对的恐怕是间谍小说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对国家忠诚和对朋友忠诚的冲突中,你往往发现美好的人性在政治压力下,总显得如此脆弱不堪。
在推理小说世界里有一句名言,叫“人性哪里都一样”。纵观勒卡雷的小说,似乎不仅是人性,就连不同时期间谍世界可能呈现的样貌,政治的非人性化,以及主人公所承受的压力,从本质上说都无甚差别。与其说是读者一直在勒卡雷的小说里看到他目之所及的不同时代,不如说我们总在被提醒,一些矛盾冲突、一些悲剧在什么时候都无法避免,只是花样翻新而已。
或许是过去的经历使然,作为小说家的勒卡雷有着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他也是我所见过的、发表过最多政治观点的作家。2003年,他就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过题为《美国疯了》的文章,抨击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而本文开头提到那篇备受争议的访谈,也格外夸大了勒卡雷对美国政府的批评,让他很是担心美国读者的反应。在后来的信件中他说自己对整个美国的感觉并非憎恨而只是失望,但对美国政府过去八年来行动的批评却并未收回。至于英国部队对伊拉克战争的参与,更是他常常提起的话题。
西方媒体说,勒卡雷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的敢于挑战时事题材的小说家,所以对于他要涉及的话题,我们总有的期待。而就像早年冷战题材的小说,在它们间谍世界的外壳里面,掺杂的其实是在特殊环境下,作为间谍职业的“人”可能呈现的心理活动和与环境间的互动,他近年的小说里,人性的因素也从未消失。这说法或许有些突兀,但事实是,勒卡雷的小说在书店里可能一直都放错了位子,归到犯罪小说类的它们,其实与游戏性质为主的成人童话实在是两个极端。勒卡雷从来都希望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间谍世界,还有他对社会人生的真实看法,哪怕它只是一片灰色的阴影,哪怕它并不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