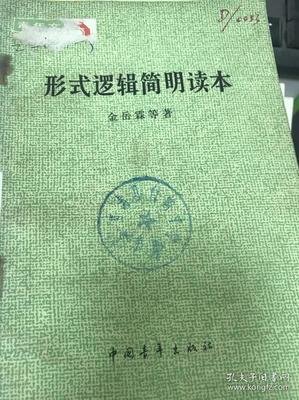《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读后感精选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是一本由叔本华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3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精选点评:
●本科论文时读的,基本忘光了
●叔之骂,威震寰宇、空前绝后、返璞归真,已超美学随笔和思想随笔中的零星碎骂。
●不错的译本。第一部分对于自由意志的形而上部分的论说很有启发,第二部分关于伦理学的构建,写的也很真诚。公正、仁爱——换位思考。
●两大经典论述
●不错
●没机会看了,也算是看完。
●第一篇:论意志的自由 将自由与必然性相连,最终得出人不存在哲学上的自由 第二篇:论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 先是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神学外衣 再是提出自己的道德基础,认为同情是道德的根源 最后才开始真正论述其形而上学部分。
●叔本华把"设身处地"写的老长,成一本书了.
●还不错
●叔本华30岁即写成划时代的哲学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二十年后又写成此书。此书延续了叔本华一贯的特点,通俗严谨,极具说服力。两篇论文的结论分别是,论意志自由:经验不自由、超验自由;论道德的基础:同情。第二篇论文难度显然大于第一篇,因为第一篇只是把先贤的正确观点更加清楚地说出来,而第二篇却是要反对近代、当代的权威,包括叔本华所尊崇的康德,叔本华也用很大篇幅来分析、批判康德的道德基础理论。最终的结论让人又看到了叔本华的佛学光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以种种方法同他融为一体;就是说,我自己与他之间的差距,那正是我的利己主义存在的理由,必须取消,至少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不就是佛教的“破我执”么?金刚经中说的“无我相,无人相”也是这个意思。原来康德、叔本华、佛经殊途同归。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读后感(一):一个啰嗦的小老头
人的天赋的性格决定了他要追求的目的,而手段决定于外部情况和自己的认识,手段高明与否决定于其知性水平,结果就是行为与最后的结果。不过叔本华没有解构道德主体与道德责任,而是把这些建立在性格与行动的决定论上。因为不同的性格导致了人在面对不同动机时的选择与最后的行动的发生,人必须对自己的性格负责。责任是唯一可以推断出道德自由的事实,所以自由就在人的道德之中。
然而在这里依然存在一个矛盾。虽然性格要为行为和行为的结果负责,也就是说性格所驻的个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既然性格是天赋的,凭什么人要为不由自己决定的性格负责任?就像钟表匠做出一块不准时的表,这块表怎么怨自己走得不准时呢?叔本华没有给我们的回答。这是一个尴尬的问号,道德主体在追问中还是不得确立。
心中有恨啊,伊抄了一大堆绵羊康的话。。。居然还那么啰嗦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读后感(二):记与读书的第三天
读《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第三天
前两天看到的主要是老爷子在搭建人类意识的理论框架,初步看来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内容太干,阅读进度太慢,忍不住去豆瓣看了下书评,结果有评论说老爷子的结论是否认意志自由(也就是前面说的道德自由)的存在,瞬间我就不淡定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反思(发呆),人类的意识动作是有自我意识和他物意识(认知)共同作用形成的,而认知又是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下不断积累形成的,也就是说一旦涉及到认知就不会有绝对意义上的意识自由(道德自由)。但是这一结论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所以我尝试换一种方式对意识自由进行论证说明。
首先认知是不能剔除的,人类的意识在剔除了认知以后就只剩下了单纯的“自我意识”或者是本能,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意识自由,就基本等于在讨论单细胞生物的意识自由,这是没有意义的。
在认知存在的情况下,认知本身就是受外界影响产生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自由论者会一味消极地排斥外界影响这一因素,这样就使得问题回到了上一段描述的情况,使得这一命题无法继续论述下去。
接下来就开始说一说我在篇头说的新思路。我们知道,外界事物对个体产生影响,并认知的形成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利用微分的思想来说,在一个特定极短的时间区间(时间点)下,外界事物对个体是无法产生影响的。
另一方面,自我意识的产生是瞬间形成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瞬间,外界事物对个体没有产生影响,而由个体的自我意识产生作用。讲这一极小的时间区间逐渐拉长,取他物意识即将发生作用的一段可感知的时间区间,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区间内形成的意志动作是自由的。
当然,我们要先定一个基准,我们接受了这个时间区间之前外界事物对我们产生影响而形成的认知。在这个大前提下,意识自由可以认为是存在的。
说到这里,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这样说来,认识自己,接受自己不就是自由的大前提吗?
所以纠结于过去,怀疑自己,陷入自我矛盾之中的人,是无法得到意识自由的。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读后感(三):记于读书的第三天
读《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第三天
前两天看到的主要是老爷子在搭建人类意识的理论框架,初步看来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内容太干,阅读进度太慢,忍不住去豆瓣看了下书评,结果有评论说老爷子的结论是否认意志自由(也就是前面说的道德自由)的存在,瞬间我就不淡定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反思(发呆),人类的意识动作是有自我意识和他物意识(认知)共同作用形成的,而认知又是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下不断积累形成的,也就是说一旦涉及到认知就不会有绝对意义上的意识自由(道德自由)。但是这一结论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所以我尝试换一种方式对意识自由进行论证说明。
首先认知是不能剔除的,人类的意识在剔除了认知以后就只剩下了单纯的“自我意识”或者是本能,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意识自由,就基本等于在讨论单细胞生物的意识自由,这是没有意义的。
在认知存在的情况下,认知本身就是受外界影响产生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自由论者会一味消极地排斥外界影响这一因素,这样就使得问题回到了上一段描述的情况,使得这一命题无法继续论述下去。
接下来就开始说一说我在篇头说的新思路。我们知道,外界事物对个体产生影响,并形成认知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利用微分的思想来说,在一个特定极短的时间区间(时间点)下,外界事物对个体是无法产生影响的。
另一方面,自我意识的产生是瞬间形成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瞬间,外界事物对个体没有产生影响,而由个体的自我意识产生作用。接下来换积分,将这一极小的时间区间逐渐拉长,取他物意识即将发生作用的一段可感知的时间区间,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区间内形成的意志动作是自由的。
当然,我们要先定一个基准,我们接受了这个时间区间之前外界事物对我们产生影响而形成的认知。在这个大前提下,意识自由可以认为是存在的。
说到这里,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这样说来,认识自己,接受自己不就是自由的大前提吗?
所以纠结于过去,怀疑自己,陷入自我矛盾之中的人,是无法得到意识自由的。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读后感(四):论自然的自由和智力的自由
看完了第一篇《论意志自由》,才发现叔本华在开篇对自由的划分有些偏颇,感觉作者对是为了将两种不易论述的概念从“意志”自由中剥离出去而做的强行拆分,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划分是否是在同一纬度进行的。
其结果也是显而易见,对自然的自由和智力的自由论述极其简单。而对道德的自由进行了详细得论证。
自然的自由,应该不属于“自由”这一命题,而应归属于自然科学,属于“能力”的范畴。
智力的自由的立意,只是为了解释在道德、法律标准下,“恶行”不被处罚的情况。作者认为,“智力不自由”的个体的不当行为,是基于其“不自由”程度,其罪行可以被适当原谅。
这一论述本身就已经偏离了哲学学术范畴,而走到了社会学、司法学的道路上。
这里举个例子,一个人的精神是错乱的(即作者所说的智力是不自由的),并有严重不当的行为,如果他在比较愚昧的年代,他可能会被认为是恶魔附体,处以火刑:而在当今社会,则会被道德和法律原谅。为什么同样的“智力不自由”,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同的对待,作者在文中并没有论述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讨论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对智力的自由的定义其实是不科学的,只是为了说明精神异常的情况,并自顾自地讲社会科学中道德评价、法律标准加在其中一锅煮。将哲学的基础理论的论述中夹杂了社会学这一应用学科的概念。个体的行为是个体意志的结果,而对其“智力是否自由”的判断本就包含了人的判断在里面,这样的论述显然是不严谨的。
假设人类不是社会性动物,那么精神异常的个体,将不会受到群体评价和审判,而是遵照这世间最弘大的规则生存下去,或许他在被野兽追捕时容易丧生;或许会精神恍惚,误食了有毒的果子而死亡。其实对于个体本身来说,这都是一种自身条件。
作者对智力自由的定义,本身就是夹杂了社会道德标准在里面,也就是夹杂了群体意志。也正是因为不同时期的群体意志不同,导致了“智力不自由”的个体,自己不同时期的审判标准不同。
所以就理论结构而言,应该以本能、认知、个体意识、群体意识理论框架进行论述。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读后感(五):人性的根本
十九世纪,叔本华对人性的研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令人万分吃惊,今日读来,仍有醍醐灌顶之感,结合自身,看到灵魂深处的身影啊。
人所有行为有三个源泉,分别是自利心,邪恶心和同情心,而每个人由这三个心以不同比例的组合形成各种动机,导致了所有的行为。自利心不需要解释,邪恶心是指看见别人受苦,不幸,有快感的那种心理,残忍那种心理,和利己无关,纯粹就是残忍邪恶,幸灾乐祸是最典型的这种心理。而同情心就是道德的基础,同情心也和利己无关 。
道德有两大基础行为,一个是公正,一个是仁爱,公正是指不损害他人利益,是元德,而仁爱则是看见别人不幸,就想施以援手,减低他的痛苦。公正往往和各类规则联系在一起,因此有了义务和责任的概念,因为你不尽这样的责任,直接就导致了对方的损失。圣经里旧约就是关于公正,有戒有约,新约就是关于仁爱,传播要像耶稣一样爱人如己。比如父母之于子女,因为父母未和子女订约,就把子女带到这个世界来,因此父母并不是说经子女同意今后要偿付什么责任才对子女负有责任的,父母天然就对子女有责任,如果不负责任,那么子女的利益就会受损失,甚至无法存活,而子女对父母在其负责任时有孝顺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随着责任的结束也结束了,此后是感戴,而感戴并不是义务,虽然忘恩负义是个很可恶的事情,但是感戴却不是义务,因为不感戴,父母也并未因此而损失,只是有点伤心而已,感戴是对父母超出责任的付出的感激之情。公正心的来源仍然是同情心,因为,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在同理心的情况下,就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因此是不被接受的,因此在违反公正原则的时候,人会有良心的不安,但是当损害利益的对象不是一个自然人,比如公司什么的,这种时候,人就心安理得的多,这时反动机是法律规定惩罚的制约,是自利心做出的反动机,而不是道德范畴的公正心。而仁爱则是受直接眼前的痛苦现象刺激引起的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帮助,在仁爱心上特别强烈的人,就是圣人,古往今来,都有很多对这样圣人的记录。 普通人的仁爱心也会很强烈,即使是个邪恶心很重的人,像那些打架闹事的人,也可能看到一个小动物,突然就触动了仁爱心。
一个人具有这几个心的比例是不变的,因此他的性格是天生的和不变的,自己也很难了解,只有当他做出了某些行为后才被检验知道了,但是因为不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些行为,因此他可以悟知自己的性格。
但是人的意志最终对哪些动机做出了反应,并形成了最终结果,还要通过媒介,那就是认识能力,认识能力把哪些动机传达给意志,是否完全,正确,也直接决定了最后的反应。比如说取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这是一个自利心下产生的动机,但是法律的惩罚就形成了一个反动机,事实上法律就是针对一系列未发生的犯罪行为的反动机,这两种动机通过认识能力反应给意志,同时还反映给意志逃避惩罚的可能性,让意志进行权衡,并最终做出反应。 很多胁迫,邪教洗脑,欺诈行为就是左右了人的认识能力,从而使人做出了他本不该做出的行为。
性格不可能改变,但是认识能力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所有的教育都是针对认识能力的,各种道德机制,宗教都是针对认识能力的,比如设计出来世今生的报偿,报应等等,利用人的自利心,来推进一些善事。
所以人有道德,可能是出于道德心,也可能是出于自利心,只有完全没有自利的任何目的的行为才是有道德价值的。
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你生就什么性格,就会对各种动机做出什么反应,从而采取什么行为,但是认识能力是自由的,可以通过不断地提高认识能力,把更多的动机,及对动机的认识,引入意志,来决定最终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