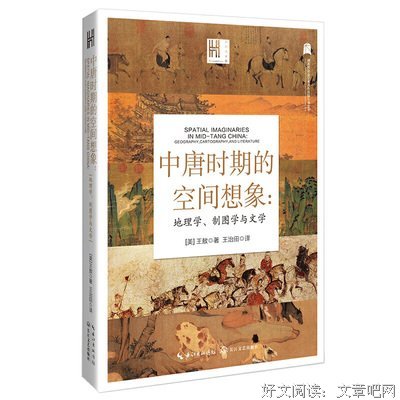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1000字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是一本由[美]王敖著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一):为什么网上AG只杀大赔小呢,你有没有知道AG的黑心骗局,远离AG
昨天我一个大学朋友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被骗了;我仔细询问得知,他是被网络AG骗了。但既然被骗了我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安慰他了,然后给他说了一下网络AG的内幕,现在他也已经醒悟了。
那么他们背后作假的内幕又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的这类游戏其实门槛是很低的,只需要随便弄个游戏网页程序就可以运行了。他们很多是没有什么实力和经验可言的。但当我们进入游戏大厅后;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气的平台。房间里热闹得很。
甚至一般都有上百号人在线,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不要怀疑,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只不过是他们设置的虚拟人气。为了引导真实玩家,他们会放很多的机器模拟人来陪玩家一起玩;从而到达更为真实的伪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平台忽悠,说他们这是澳门正轨的什么什么的;像这种更加不能相信,因为我国是不允许开设线上的。像现在出现的什么太阳城,金沙这些就是伪装的较真实地之一。网络骗局水真的很深,千万不要抱着好奇心去尝试;好奇心往往会害死人,不碰才是最好的!
永远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二):半个佳作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这句诗,应是本书最佳脚注。本作是一部研究集性质的作品,如果说的再通俗一些,更像是一个扩充版的毕业论文。站在此角度再阅此书,不难发现本书在创新性上的贡献。众所周知,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新数据、新方法、新问题(观点)”。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新数据实在难以取得。早年的研究尚有名家非名篇可以一读,随着时间的推移,广为流传的作品和广为流传的作者不再有可挖掘的空间,甚至连不那么有名的作品都被挖的一干二净。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完,后续的研究如何进行?本作恰好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既然没有了“新数据”也难有“新方法”,新观点、视角就成了最重要的法宝。本作恰是如此,作者选取了中唐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名家名篇为切入,使用了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文学视角与现实视角相结合,以由诗入画的方式撷取作品中与地图、方位有关的意象进行分析。最终将文学、地理学和制图学相结合,从空间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了解构。这一视角不可谓不妙。正如作者所言,中唐时期盛唐的尾韵,也是唐帝国版图剧烈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在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的同时也被政治生活所裹挟,或贬谪或逃亡,向蛮荒之地。另一方面,动荡的政治局势稍微平稳时期却又面临着外患,即使不是国破山河在的悲壮,于有家国情怀的文人而言也是心理上的巨大失落。心理版图的缺失与现实丈量脚步的扩展都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沃土。不同于盛唐时期作品的雄浑、浪漫,这一时期作品似乎更具“实用”性,这又再次反哺了制图学与地理学的研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并无清晰的逻辑链条,而“地理学”、“制图学”和“文学”这三个关键词的关系也无法判定。在某些情况下,是制图学影响了文学,文人们习惯地图视角下对所处环境进行分析。同时,也存在如图经般以文学服务于制图学、地理学的案例。更不乏后世抽丝剥茧般研究中发现的地理学和制图学痕迹。因此,这部作品并没能回答它自己的命题,我们依然不知道这三者间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低垂果实被摘取后研究中难以避免的一点。根据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观点,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因果性却并不普遍。证明因果性是研究的一大关键。在新观点的指引下,研究更多是在寻找什么可以研究,而难以找到值得研究的问题。本作品在一个新观点下,既不能纯粹的新瓶装旧酒也无法说明新事物间的真实关系。这就使得全书难免有跳脱和混乱之感。
因此,在早已没有低垂之果的情形下,如何找到视角切入又如何讲好故事,或许成为了当下绝大多数研究者面临的难题。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三):唐诗为什么这么辉煌,地理功不可没!
这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就是“地理决定历史”,尤其是近期中原大地汪洋千里,直接让人想到古时黄河不断改道,摧毁古人家园,以至于古开封埋在今开封地下数米,至于传说中的夏朝,更是被冲得无影无踪,好歹还有殷商留下,在安阳成功躲避了洪水,给后人留下了伟大的甲骨文。
历史和地理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跳出传统视角看待历史,总会有些重要的收获。近些年来,历史和地理的相结合,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广阔的历史空间,也提供了一个跳出政治、经济、文化视角下的历史解读视角。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就是这样一本学科交叉融合的书籍,乍一看书名,感觉比较小众,但是仔细一翻,一种磅礴大气扑面而来。为什么选择中唐而不是盛唐,这里其实蕴含了作者对中国历史转折点的惋惜与惆怅。盛唐时,万邦来潮,地理学或者制图,描绘的山川形胜有种“猎奇”的味道,地理学意识尚未浓烈,但是在中唐,尤其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出现藩镇割据、帝国边缘领土丧失等现实冲击,制图,在法理或者说政治层面展现名义上的大一统,就成了一种现实需要。
借曾担任宰相的李吉甫所言,制图的作用是“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可以屈就隐忍现实,不要里子,但是面子还是需要的。所以,也就很容易理解玄、肃、代、德、顺、宪宗6朝元老贾耽制作《华夷图》的良苦用心。后人根据残本推测,这应该是一幅亚洲地图,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天宝年间的“领土MAX”,只可惜,没有后来了。
当然,这种地理意识不是横空出现的,而是经过前人不断地积累,尤其是在最鼎盛时期,边塞诗人们在西域等内亚地区或行军或为官,写了《凉州词》《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名篇,通过脍炙人口的文字,加深着世人对边疆的情感,也成为后世情感认同的一种凭证。
所以在中唐,地理学与文学书写是相互印证和彼此成就的。当时的朝廷很多时候被宦官把控,很多著名的诗人如韩语柳宗元都有不如意甚至贬官流放的时候,中国的文人讲究入世与出世,仕途不如意总愿意寄情山水游目骋怀,为文学留下了诗歌和游记,更为地理学和制图留下了宝贵的文学文献。
比如著名的《捕蛇者说》,开篇就是“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把永州山水的险恶展现得活灵活现。还有白居易、元稹等人,很多诗歌和文章,不是诞生在南方,就是诞生在南方之南的南荒,这些都是帝国的边缘,直到近代才完完全全融入到中华的主流当中,如果没有文人雅客的记载,我们更难具体体会到对国家情感的血肉联系。
文学往往细致入微,能见微知著,感受到创作当时的时代风云,《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是一本奇妙的书,浪漫充满了激情,严肃中又展现了逻辑的严密。古人讲究诗言志,言自己的志是一种独特的表达,但要达到像杜甫那样“诗史”的程度,之前挺难的,但在细微的研究下,我们的思维通过诗歌,触达到时代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幸事。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四):文学和地理的浪漫相遇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这是“地理”一词最早的出处。单单从这句话来看,地理的最初诞生,便和文学脱不开关系。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是一本非常专业的研究书籍,书中含有大量的专业性名词和地理特有的概念。因此对于之前未曾接触过相关领域的读者来说,读时需颇费一番气力。
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用地理的思维去重新研究和解构文学,用地理研究的内在逻辑去研究相关文学作品的写作逻辑。而它对于经典篇目的解读,为我们在传统解读之外,提供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地理学科的解读。
而文学对于地理学的影响同样显著,文学家们用诗化的语言去描写描述常见的地理事物,所写就的作品又作为后世地理学家研究的重要史料。
而本书,也提及了诗人们在文学层面是对于地理学的理解和融会贯通。书本的第二章以杜甫《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为例,展示了一幅地图是如何在公宴聚会的场合引发诗学美感。书中提及,此诗的写作是在严武向宴请的宾客展示一幅蜀道的地图之后。
众人皆知蜀道之艰险壮美,但这幅地图,使得一直以来的文字描述图像化,使得观者为之震惊。而杜甫观图后所写就的这首诗,不仅将目光放在蜀地之内,更将目光投向了属地之外的神州大地。他借由这幅画,用俯瞰的姿态,将被战火分裂割据开的各个地区拼凑在一起,囊括四海,包举宇内,写出了一个完整的神州大地。
是地图唤醒了他的灵感,也是借由地图他表达了对于王朝统一的渴望。这是书中所例举的,地理和文学相结合的经典例子。 不同作家在描绘同样的事物中地理学知识运用与否所造成效果的不同也同样被他写在书籍中。通过对比来写出地理学科和文学学科之间所存在的互相影响,以及不同的诗人是如何巧妙的借用地理学知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当然,作者也写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文学家们借用的,大多是地理学研究的概念,同时对此有所超脱,常用文学的手法对客观存在的地理事物或距离进行夸张化的表达。
元白二人的互相唱和,更是地理学和文学的绝妙融合。他们在唱歌的诗歌中互相推断对方的所在位置,推断出来的位置竟与对方实际所在的位置相差无几。《水上寄乐天》一诗,通过对大量地理事物连续性的描写,表达了两人之间绵绵不绝的情谊。
书籍内容虽较为晦涩难懂,但在相关研究领域中是较为全面和有趣味的专著,获益颇多。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五):中唐文人地理学与文学知识的类同与互动
或许有“想象”的牵绊,王敖在尝试用新的视角探讨中唐时期文人在地图与文学之间遨游的境况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因偏向释读部分文人的文学作品(与地图相结合)而弱化了史学研究的取迳,容易让读者感到不适。在这本书中,他试图探讨中唐时期文人认识中的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并不笼统地归结为“相互影响”,而是实现者(文人)既拥有地图学的相关知识,也有制图的主动意识,文学又是其基本素养,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眼中的学科门类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实际上是类同与互动的。因而,王敖也试图强调以往被研究者们忽略的文人潜移默化于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意识的重要性,并试图填补历史中地理学与文学两大领域结合的思想碰撞的学术空白(史学已不再如此论述),然而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脱离文学研究范畴,但问题意识偏史学,因而读者容易以后者判断此书抛出之观点是否得当,不适感就在此。他的新作《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注定面世的同时就要面对争议。
在谈论中国历史前,我们需要有个认识,即所谓以学位分科的做法,源于西方。中国细分学科领域最早应在近代(教育体系)。而在中国古代,知识技能并不会如此明确细分,古人追求知识时也不会过分给自己设限,见面打招呼也要先问“您什么专业啊?”,我是文学,或者我只是地理学云云。不可能。对专业对学科的“不讲究”,反而凸显中国古代文人的全能,因而才有“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一说。因此,如果用当下的知识体系去认知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必定会有不适。尽管王敖试图解释中唐及以前地理学与文学并非泾渭分明,他确实又使用了当下的学科分类来论述中唐时期的地理与文学,历史现实与当下学科无法自然衔接,第二处让读者感到不适,或许也在此。
倘若在一些古地方志中,不难发现,古人划分地面界线,是以星象为标准。即夜空的哪颗星位于何处,以此界定地域的界线在何处。而古人在绘制地图时,注重地理功能大于赏玩性。我们在看某些地图时会发现它的不精确,实际却是强调哪些地理条件有益于他们当时的活动(军事或贸易等等)。地理与绘画之前的关系,东晋的王微已明确强调地图与文人画有所区别:前者客观描绘,后者体现画者情思。因此,在讨论制图学时,还需要区分绘者身份与绘制意图。比如皇者要求臣子绘制疆域图(版图),以此确认自己统治的规模(也有满足虚荣心的意图),或者制定军事策略、布防等等,这种制图虽也有其想象成分,实际又与王敖要论述的问题不同。
王敖将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结合展现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这其中有固定的对象,那就是文人。而这些文人个人经历虽大都相似,但相较于顺遂的朝臣和普通人,他们的经历又周折而“丰富”些。时代动荡加之自身身处的政治动荡,他们身体因际遇移动,在这过程中认识现实中的地理人文,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政治愿景,即王敖提到的“空间想象”。换言之,《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加入“文人”或许更贴切(《中唐时期文人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
古文人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融入绘画、描写女性的文学作品中尚属常事,融入地图中或许也如此,王敖只是打开了一扇窗,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把这一选题进一步深入研究,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六):青山绿水枉自多
跨学科研究,对于丰富和拓展当代知识库是一项功不可没的事情。或许是国民教育的缘故,兼顾文理的边缘性研究总是著作稀少,其实在看破与说破之间,往往只有一张薄纸的距离。拜读《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作者王敖通过对地理学、制图学、文学的综合考察,发现的蛛丝马迹,却也在无懈可击的描述中探寻研究唐代历史的“羊肠小道”,为读者展现了其穷尽真理的决心。 地理学与文学的交融互鉴,从学科沿革的角度分析,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相反,这一话题在近年跨学科研究中得到了重视与发扬。毕竟,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脱离了时空谈人的生存与发展,是无法“想象”的。王敖的发现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孤心苦诣,不如说是先知先觉,引领了研究者追问我们为什么存在,是从哪儿出发,又将走向何方。
尽管一个朝代可以从逻辑上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但是国内学者对于唐代的研究,不约而同地局限于盛唐气象的刻画与抒发,对于初唐、中唐以及晚唐则涉猎较少。仿佛除了盛唐,其余时期的研究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所幸,王敖以两副面孔和两副笔墨,打破了叙述的僵局,写诗时他是豪情万丈的诗人,著书时他是一本正经的学者。
从言之有序至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聚集于“想象”。之所以使用这种浪漫味极重的词语,一方面是在现代社会很难寻求唐代地图的原本,王敖即使想按图索骥,也很难得到科学的结论,正如“累石之台,起于平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想象”还是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想象不等同于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在王敖的视野中,通过诗歌信息所激发的灵感为辩识地图真伪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以韩愈、颜真卿、李贺、白居易等活跃在中唐时代的人物为经,以他们行走中国的所见所闻、所吟所唱为纬,既表达了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与力透纸背的批判力,也反映了一个时代所拥有的光茫是可以脱离空间而存在的。从更广阔的时空而说,不仅是中唐,不仅是中原,在世界各地,地理学与文学的交融互鉴在反映社会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总是令人热血沸腾的。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七):《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从游仙诗《梦天》寻找中国最早的地理记录
被《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吸引,是书中对于唐朝时期的地理、制图和文学方面的融合抒发,我突然觉得每个时代都有必然的空间想象,它投射在图像上,文字表达上,向后传承,源远流长。
平常人们说起盛唐的风华,仿佛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的确,那个时代的文化真是空前盛况。那真是文学最好的一个时代,留下了精美绝伦的诗词巨篇,放在今天吟诵,仍然美得令人心悸。我们平常读唐诗之美,却忘记了,文人写作本身也在新开发的帝国疆域建立了新的地标,这也反过来成为后世的地理学著作新的关注点。一旦把那些诗与地理空间相联想,就会发现古人在人文地理方面的许多延伸,而这一方向鲜有人研究,甚至古人地理学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特别是唐朝时期的人文地理,可以说《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的推出挺令人惊艳的,因为基于我的认知,它在我的世界里开辟了新方向,会让我脑海里的优美唐诗更有想象力和感染力了,丰富了其中的地理人文。
李贺的〈梦天〉是一首游仙诗。“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这样的:天色凄清,老兔寒蟾正低声呜咽,月光斜照,半开的云楼粉壁惨白。玉轮轧着露水沾湿了团围的光影,桂花巷陌欣逢那身带鸾佩的仙娥。俯视三座神山之下茫茫沧海桑田,世间千年变幻无常犹如急奔骏马。遥望中国九州宛然九点烟尘浮动,那一片海水清浅像是从杯中倾泻。
这首游仙诗写得真壮美,读来有无穷的想象。而其中的地理空间想象,似乎是诗词中最早运用大视野描绘天地山川,并赋予其地理意义的先驱。我猜我们常用的“九州”一词,在这首诗里变得更具象起来。三座仙山飘洒之下的沧海桑田,九州烟火下的人间风云。据记载,海上有三座仙山,指蓬莱、瀛洲、方丈,现实中仅蓬莱一地实存。九州最早是指“汉地九州”,最早出现先秦时期典籍《尚书·禹贡》中,是中国汉族先民自古以来的民族地域概念。
《华夷图》的木拓片也流失海外,作者提到美国馆藏中有此拓片。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有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此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一面为正刻的《禹迹图》,另一面为倒置的《华夷图》。图中注释显示,这两幅地图的刻记年代均为1136年。从这些资料记载连天烽火看,大中国的古人真的好牛啊。我们在那么早的年代,就已经知道画地图了。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很具有开创性,它把唐朝的文学与地理进行了架构,这一跨领域的联系对于我们理解文学与地理学两大领域,有很大的增强作用。至少我再读李贺的〈梦天〉,会觉得诗中的描绘能真实的落到自然天地之中,其磅礴之势,豪情万丈之意,皆有所指。那是诗人脑海中想象的地理概念啊。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八):地理学与文学的不期而遇
诗鬼李贺曾写下的《梦天》中有这样的诗句,“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俯视三座神山之下茫茫沧海桑田,世间千年变幻无常犹如急奔骏马。遥望中国九州宛然九点烟尘浮动,那一汪海水清浅像是从杯中倾泻。这两句诗写在月宫居高临下看人世的感觉,从非现实的世界冷眼反观现世,从而揭示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诗句用比新颖,构思奇妙,想象丰富,体现了诗人创作变幻诡谲的艺术特色。俯视人间,时间短促,空间渺小,寄寓了诗人对人间沧桑的深沉感喟。除了从文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读懂唐诗呢?翻阅《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此书,教授王敖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途径去领会唐诗。从地理学、制图学的角度去考察文学,实在是我以前没有想象过的视角,不知道这样子的梦幻联动能够擦出什么样子的火花呢?王敖教授打通了不同文学体式的壁垒,清晰揭露了中唐时期地理学与文学之间多样且流动的关系。中唐文学大师的佳作很多都被打上了“制图学之眼”的烙印,他们的作品中对地理的描写,使得不同地点与文本构成互动。
王敖教授首次研究的此种中唐时期的文学与地理学的奇妙联动关系是多重的。他通过对这两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汇与重叠情况的全面深入考察,意在指出在中国那个巨变时期两大重要思想领域之间的类同与互动的关系。中唐时期两大领域的大师在推进深入探索世界的同时,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情景空间,文学和地理两大领域的文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被广泛地生产与传播。两个领域的文本在空间呈现上可能会具有相似的视角,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交织,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王敖教授通过考察中唐时期的文学大师们的地理知识如何与文学感受共同作用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纷繁复杂的空间想象来研究空间如何透过中唐文人们的思想滤镜,变形成为映射在文学接受面上的影像。文学作品绝不仅是被过滤后地理世界的被动反映。经过文人独有的文学感受力的调和,空间想象拥有了一种能将各种地理学的测量和知识转化为人们的情感和想象的创造力,使得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因素充满生命力。除了在文学领域,此等方向还能运用到绘画、雕刻等各个领域。
本书的结构简单,思路清晰,一共分为五个章节的内容。首先介绍历史概览,侧重于地理学与空间想象方面,后续几章开始叙述地理学与文学的相遇,提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大唐文人们,我们将以另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他们眼中的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在大师们的笔墨与脚步之间,我们能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拔地而起。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九):中唐文人是如何让文学和地理学碰撞出时代的火花
唐朝根据时期划分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中唐时期是公元790年到820年,是大唐由盛转衰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唐朝的统治力下降,尽管安史之乱已经被镇压,但是各附属国和藩镇拥兵自重,入侵和叛乱时有发生。在盛唐时期的文化优越感和骄奢淫逸的那个时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文人集团致力于重建唐王朝的霸权的努力。
随着外敌入侵和叛乱的频繁爆发,中唐时期的许多人口迁徙到了那些“不毛之地”,迫使知识精英寻找更加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工具为人们导航。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文人的作品便不会再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而是弃笔从戎的文人“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或者是游仙诗“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这些包含着地理学的文学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文学地理学。
本书是通过分析中唐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关于地理学内容,探讨地理学展现出来的空间想象的灵感与文学作品的相互影响。作者认为地理学和文学的关系应该合二为一,也应该有一个同等的研究地位,单纯的研究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地理学知识是狭隘的,一个文学作品应该考虑是在怎样的地理空间中诞生。
选择中唐时期的文人作品来研究文学和地理学的关系,原因无他,中唐作为一个动荡的时期,承接了盛唐底蕴深厚的文化,这个时代多才多艺的文人们由于战争、贬谪、开发、游历等原因,用自己的足迹丈量这个伤痕累累的帝国,最终将地理学体现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
本书回顾了中唐以前的历史时期地理学和文学的融合,阐述了中唐时期的地理学发展,对于中唐文学中宏阔的意象引入制图学的思路进行解读。引用了《海内华夷图》、《元和郡县图志》以及颜真卿、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作品,考察中唐时期的文人对于不同区域地理的著作。现实中的地理学通过艺术手段的修饰、夸大,通过文人们的想象力的转化,最终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学的知识被赋予了生命,掺杂了人类的独特情感,反过来又升华了文学作品的空间感和内涵,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中唐时期的地理材料流传下来的甚少,作者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讨论了地理学和文学之间的类同性,这也成就了中唐时期文学所独有的空间想象之经验和美学背景。那个特殊的时期空前高涨的地理学知识的盛行,赋予了人们一系列的空间想象力,具备了丰富地理知识和想象力的文人们,建设性的将地理学融合在文学作品中,从文化角度构建了这个帝国的空间版图,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有了归同感。
尽管有学者认为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相似性被夸大了,但是作为重塑历史中地理学和文学关系的重要手段,其存在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不仅具有积极的艺术价值,对于构建那个时空的空间更是意义重大。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读后感(十):跨越地域,穿越时空:古人与今人的灵魂共振
历史上的中唐,具体说来代宗大历初至文宗太和末(766-835),共六十九年,是为中唐。在历经安史之乱后,这一时期历任君臣整顿赋税,平定藩镇,在形式上仍旧统一全国。我认为,文学中的中唐划定时期不能与史实中的中唐相提并论,很多时候它们并不重叠。因为历史是以具体历史重大事件或者有重大转折的战争等所注定的,而文学中划定时期则往往早于历史时期,因为文学具有很大的预见性和敏锐性,随着社会历史的极具推进,文学往往凝聚了一大批卓有远见的思想哲人,在特定历史时期,文人所特有的敏感会提早紧跟时代脉搏,把握时代浪潮,怀古讽今,指天说地,警示当代和后人。
所以,文学中的中唐时期概念我认为是以安史之乱后开始的。这一时期唐朝的政治形势重趋稳定,但中央集权衰落的大势却难以扭转。帝国不像初期那样拥有无比辽阔的疆土和开放的心态,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是在整个亚洲具有影响力的“天下帝国”。安史之乱导致的族群、人口和生活的大变动,在中唐时期引发了有关‘中国’地理空间的再发现和再定义,在这个变动时代,诗人或者文人们对于这种地理空间变化的惊讶、喜悦或困惑等诸如此类的复杂文学哲思,这些都是值得深层探寻的集历史风俗和人文地理的文化课题。
中唐时期是中国文学传统发生激荡变化和强力创新的时期。著名学者王敖的《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一书通过对中唐地理学、地图学与文学的综合考察,融合集地理学、制图学和文学的发散综合思维,为我们解读中唐文学乃至其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和方式。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批判性的视角,巧妙地使传统中国的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文学创作与地理--地图和知识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这是一项有重大贡献的研究。全书以批判的眼光和诗性的敏感,涵盖了不同的文学体式,全书着眼于中唐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在分析这些文本的过程中,他将文学、艺术、地理、地图学、生态学、哲学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揭示了一部丰富的知识分子探索的文化史,也是对中唐文学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新的解读和诠释。
全书历史材料广泛,史实考究,文献全面,观点新颖,论据充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合理又丰富的构想,富有超前的想象力和启发性,以文学展现地理,以地理丰富文学,多维想象的空间感,全方位展示了许多最杰出的中唐文人如何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重新想象他们的物理和文化环境,以产生新的空间想象。比如李贺的《梦天》、柳宗元的山水诗文、张祜运用大图视野欣赏古老画卷的诗歌、元稹和白居易富有地理信息的唱和诗等,这些作品都打上了“制图学之眼”的烙印。
总之,作者在《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一书基于对地理学的娴熟与热爱,使得历史文本与现实互动交换。不同地域之间、相同地域之间、旅行者与隐居者、得意者与失意者、今人与古人之间跨越地域、穿越时空,达到一种心有灵犀的精神共振和栖息。可以说,《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