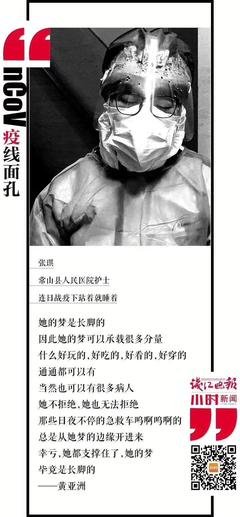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100字
《中国新闻舆论史》是一本由林语堂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新闻舆论史》精选点评:
●我读的第一本专业书
●大二读过,对作者是林语堂感到惊讶。
●近代部分有些单薄,古代蛮有趣,不过更多是集中士大夫视角,立场先行,借一位豆友所说,“学士将读书人阶层观点上传至皇帝处的一种集体行为,与现代意义上报刊的下达作用相去甚远。”
●到1936年成书为止,从笔者的考察来看,中国新闻史就是民间舆论和中国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古代时期比现代时期读起来更有意思。【当代新闻事业倒退包含着一个“悖论”,越是“强大”的政府,其新闻事业越弱小。】作者说了很多就算当下也有许多人无法直抒胸臆的内容,有一点是明确的,只有立法才能保护新闻真正的自由。
●把专业书写的很好看,绝了!从古到今其实我们还是在重复历史。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总还有道德和理想主义存在,即使一片黑暗。
●还是古代部分的舆论分析更见其意义。后面近现代部分尽是史料,还不及方汉奇那课本来得详细,不过,奇闻异事倒是诉说得详尽。另外,林大师论及的在中国古代媒介缺失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文人学士以及有识之士在舆论形成方面所坐的努力。只是,我的疑问是,书中论及的舆论行程,其实只是一种学士将读书人阶层观点“上传”至皇帝处的一种集体行为,与现代意义上报刊的“下达”作用相去甚远。而横向相比,外国报刊的兴起来源于商业之需,中国古代的舆论形成更有“文人论证”的意味。
●有几句话说的还不错
●公众对于国家事务的漠视是民主权利缺乏保护的自然和逻辑结果~
●翻译有槽点;内容的话,如果我是36年读到的会给五颗星。
●单薄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本比的确差很多
上海人民出版社,刘小磊译就比人大版本好很多。
这给人大这套系列敲了下警钟。这系列书价格方面本就不低,那就更需要注重质量了。虽然新闻学、传播学需要大量的引进国外著作,但译者的水平也同样很重要。千万别砸了这套系列的牌子。此书还是推荐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二):关于这本书的所提论点的一个专业疑问
还是古代部分的舆论分析更见其意义。后面近现代部分都是史料,还不及方汉奇那课本来得详细,不过,奇闻异事倒是诉说得详尽。另外,林大师论及的在中国古代媒介缺失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文人学士以及有识之士在舆论形成方面所做的努力。只是,我的疑问是,书中论及的舆论行程,其实只是一种学士将读书人阶层观点“上传”至皇帝处的一种集体行为,与现代意义上报刊的“下达”作用相去甚远。而横向相比,外国报刊的兴起来源于商业之需,中国古代的舆论形成更有“文人论证”的意味。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三):粗糙
手头没有英文版,仅凭常识来断定,人大版就有不少错误。
例如:
23页,谈古代歌谣,引了一首汉代歌謠“車班班,入河間……”,竟然发生串行,将接下来的几句作为另一首了。
28页,“东汉历史上曾接连产生了六个实际上统治着整个朝廷的女强人式皇后:涂皇后,(和熹)邓皇后、阴皇后、梁皇后和何皇后”
按,应作“窦太后、邓太后、阎太后”等。太后与皇后,可不是一码事。
30页,“正如儒家学说所倡导的‘讲’或服从的美德那样……”
按,什么是“讲”,莫名其妙。上海人民版作“礼让”。当以后者为是。
31页,“我们这里引用何容的案例……”
按:这里是在讲“何颙”替朋友复仇的故事。译者压根没核实过,上海人民版不误。
48页,宋度宗怎么称呼賈似道?人大版译为“相父”,误,当作“师臣”。
51页,第七章标题,人大版译作“明朝的宦官、新闻审查和东林党”,上海人民版译作“明朝的宦官、御史和东林党人”,观此章内容,压根就没有出现新闻审查的内容,御史作用是作为重点来讲的,故知人大版又误。
52页,朝廷御史官员实际上相当于现代公共信息员。什么是“公共信息员”,五毛党吗?莫名其妙。上海人民版作“时事评论家”,还说得过去。
60页,"一位道医被推荐来医治皇上的病",“道医”是什么东东,您听说过吗?核之以上海人民版,原来就是“方士”,真搞!
89页,“现任南京统一政府主席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三份日报”,于右任当过主席吗?根据于的履历,当作“监察院长”。
103页,“日本代表马上到北海约见褚恩堂,质问中国当局这种有损于中日友好关系的做法意欲何为。” “褚恩堂”看来是位中国方面的要人啊。起码应当是北平方面的头面人物,宋哲元级别的才对。但这又是本书译者捏造出来的人物。上海人民版译作“日本代表马上跑到北海居仁堂”,居仁堂是办公的地方,如同我们现在说“白宫”、“中南海”、“青瓦臺”。
127页,“商务印书馆经理汪先生认为”,当作王云五。
140页,“成舍我正在编辑由上海国际移民局出版的一份日报《立报》”,“上海国际移民局”这个机构很奇怪,核之以上海人民版,方得知是“租界”之误。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四):硬伤太多了
手头没有英文版,仅凭常识来断定,人大版就有不少错误。
例如:
23页,谈古代歌谣,引了一首汉代歌謠“車班班,入河間……”,竟然发生串行,将接下来的几句作为另一首了。
28页,“东汉历史上曾接连产生了六个实际上统治着整个朝廷的女强人式皇后:涂皇后,(和熹)邓皇后、阴皇后、梁皇后和何皇后”
按,应作“窦太后、邓太后、阎太后”等。太后与皇后,可不是一码事。
30页,“正如儒家学说所倡导的‘讲’或服从的美德那样……”
按,什么是“讲”,莫名其妙。上海人民版作“礼让”。当以后者为是。
31页,“我们这里引用何容的案例……”
按:这里是在讲“何颙”替朋友复仇的故事。译者压根没核实过,上海人民版不误。
48页,宋度宗怎么称呼賈似道?人大版译为“相父”,误,当作“师臣”。
51页,第七章标题,人大版译作“明朝的宦官、新闻审查和东林党”,上海人民版译作“明朝的宦官、御史和东林党人”,观此章内容,压根就没有出现新闻审查的内容,御史作用是作为重点来讲的,故知人大版又误。
52页,朝廷御史官员实际上相当于现代公共信息员。什么是“公共信息员”,五毛党吗?莫名其妙。上海人民版作“时事评论家”,还说得过去。
60页,"一位道医被推荐来医治皇上的病",“道医”是什么东东,您听说过吗?核之以上海人民版,原来就是“方士”,真搞!
89页,“现任南京统一政府主席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三份日报”,于右任当过主席吗?根据于的履历,当作“监察院长”。
103页,“日本代表马上到北海约见褚恩堂,质问中国当局这种有损于中日友好关系的做法意欲何为。” “褚恩堂”看来是位中国方面的要人啊。起码应当是北平方面的头面人物,宋哲元级别的才对。但这又是本书译者捏造出来的人物。上海人民版译作“日本代表马上跑到北海居仁堂”,居仁堂是办公的地方,如同我们现在说“白宫”、“中南海”、“青瓦臺”。
127页,“商务印书馆经理汪先生认为”,当作王云五。
140页,“成舍我正在编辑由上海国际移民局出版的一份日报《立报》”,“上海国际移民局”这个机构很奇怪,核之以上海人民版,方得知是“租界”之误。
《中国新闻舆论史》读后感(五):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
现在才想起来,寒假在晓风书屋里,抱着包括《光荣与梦想》这样的大部头在内的3、4本书时,拖着行李箱迟迟留恋,翻看这本橘红色封面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副标题,“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
原谅我成为眼球动物,书籍的装帧和CD的封面设计往往能成为吸引购买或者下载的主要因素。读完序言,最终还是放下,把炫目的颜色和刺激的副标题搁在那家书生气浓厚的书店。
回到学校,从图书馆借出来,读完……那时内心的涌动和文笔的喷张都荡然无存。现在所作的,只是自我的约束,给读过的书,写一两句话。
那是另一个版本,人大出版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封面不新不古,不俗也不雅。在图书馆见到时,只记得寒假有意于此,几天前又碰巧在《南风窗》看过了该书的书评,再读一遍序言。
今天慢慢往回想,一切才渐渐清晰起来。前文提到的“荡然无存”想必就是因为版本的差异,没有了“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的宏大叙事;“泛泛谈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作民主的真正基石。”这般真切大气的文本变成了“报刊新闻对我们而言是无意义的或者关系不大的,除非我们遵循新闻自由的理念,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报纸的业绩,进而通过以下路径把新闻自由构筑成民主的真实基础。”
诚如一些读者的留言,该书实为胆气之作。半个学期的《舆论学》课程里,千言道尽,也不敢说的话无非是作者在序言中的一句:“中国舆论史就是民间舆论同中国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
我赞同作者字里行间意欲表达的观念,好政府往往放开言论而难积起舆论的仇恨,坏政府却常以为自己在替民众考虑,不愿倾听他们的意见,渐而站到舆论的对立面。因此避开政治谈舆论实在虚伪。如我兴致勃勃地阅读此书,缘由里大概跑不掉素来对政治感兴趣却往往无解的无奈。
从古至今,两者构成了历史上不断延续的庞大舆论主体,以各种舆论形式进行斗争,复杂胶着,输赢无常。如非万劫不复、无可救药,得势者则往往是当权者。破除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也许只能是作者一以贯之,在末尾所提的“欧洲对整个人类的杰出贡献之一”。
我所理解的这些贡献,一为民主性的、法制化的制度保护,二为公众媒体的气节和无畏。
在林语堂先生看来,儒家学者的光辉篇章在于他们对国家事务无畏的批判活动,鼎盛于明御史制度。文官们前仆后继,冒死谏言,推动着一股源源不断的公众批评浪潮。近代的政治宽松时期,名记者名编辑的风起云涌,为新闻人心向往之。但这些舆论推动者的结果,非死既伤。其原因正在于当权者授予官员们批评的义务,却不给予官员自我保护的权利,言论免责,人身安全均为空谈。先生以为这些运动都是“徒劳的”,除非出现关于人权的合法保护。而这些期许中的社会政治环境,时至今日依然为一记幻象,记者们人人自危,新闻法终不见踪迹。待繁荣的政治批判精神复兴和现代新闻事业的崛起,尚需时日。
林语堂先生今时若开专栏,旁标注大概为“资深传媒人”。这位业内人士想必痛恶当时媒体的诸多作为,见利忘义或奴颜婢膝。他料想不到的是,几十年过去,“中国的新闻道德水平非常低”,“新闻界总是……不停的出卖自己”。封口费、车马费的潜规则成明规则,终酿波澜。理想信念和职业操守被至于低处,责任和努力被置之脑后。在拔河比赛的这一端,先是阉割成不完整的男人,进而堕落起来转身去做起了女人,终日娇滴滴的做所谓“网友”的传声筒。这是夜里的事情。太阳升起却又故作阳刚,一副肩挑使命的模样。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个呼喊着让无力者有力的行当而徒然无力。我们已经不信奉“斗争哲学”,但我们也不知从何改变。不大愿意读这样充满人文气息和理想气质的书本,因为终了往往悲观,甚至退化……难道我们只能自求多福,然后去坚信,“人类必将以文明的个人发展为基点而最终走向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