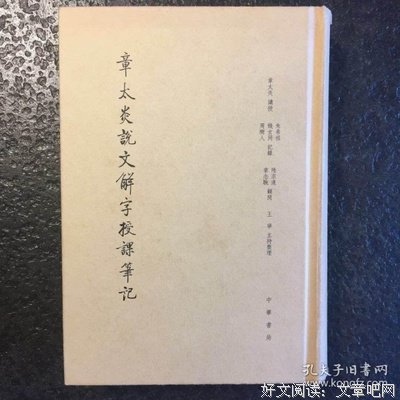《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读后感100字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一本由章太炎 讲授 / 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 记录 / 王宁 主持整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6.00元,页数:6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精选点评:
●貴在清晰,見微知著
●从版面到内容近乎无可挑剔
●也只是翻了翻
●研究对象
●15.7.13
●y
●对我来说晦涩了,第二本国学书,比读第一本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方便抓意根
●我准备再买本段玉裁的
●制作特别精致的书,定价八十多其实不贵。说了这么多年汉语,写了这么多年汉字,若是你问我某个字为什么那样说,那样写,我真的不知道。最近旁听古文字课,好好学习。 一直放在在读那块,都碍眼了。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读后感(一):普遍系联地比合对照
万献初在《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后记中说:
十多年前,虔心负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王宁师学传统语言学。听了一段课后,给我做的事情是:整理章太炎先生1908年在日本“始一终亥”三遍讲《说文》的笔记。记得背回宿舍的,是很沉的一大麻袋复印件,主要有朱希祖、钱玄同、鲁迅等人所作的笔记。同舍的同学很少来住,我排三张桌子摊开不同记录比对,再核对各种《说文》资料,翻来覆去地捣弄了整一年,还得师兄弟帮助,才弄成个老师不甚满意的稿子。后来,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这批材料为基础的《论章太炎的说文学》。
学,肯定是没怎么学好,倒是逼的我把《说文》翻找得比较快了,又看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太炎先生反复翻读《说文》原本,普遍系联地比合对照,讲起来总有他自己独到的想法,其字形的笔意构形分析总是与传世典籍中所载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意识特别强。这就使我明白了,《文始》字根词族的建立,正是他反复比合研究、讲解《说文》原本的结果。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读后感(二):讀後小記
學過現代文學都知道,章太炎在日本講說文的課很出名。因為事後很多當事者都提到了。但當時講啥了,怎麼講,沒幾個人知道。這書把幾個人的筆記整理了一下,讀者不妨假裝自己身在日本聽革命家講說文。
當時大概以段玉裁的注本爲教本,所以此書中的順序和某些字的篆書寫法和通行的大徐本不盡一致,讀者莫以為是抄錯了。
魯迅的筆記並不多。
錢玄同的筆記記得都比別人的調皮。比如調侃段玉裁說,老段如何,淺人段茂堂如何。能看到講課時因為有章老師這樣的牛人作為靠山的年輕人的自負。還有哈哈這樣的詞兒。同樣的內容,錢的筆記要容易得多,他思維很活躍。比如帶歪了帽子之類的話都有。錢的兩份筆記的差別不如朱的差別大。
朱希祖的筆記最嚴謹。朱錢對照就知道。朱的兩個筆記內容以朱2最精彩翔實。
大致說來,求本字和明通轉是筆記之中最注重的,這和黃侃的說文箋識所關注的很類似。此外,講授者還順帶提到了一些他對某些經典著作疑難字句的讀解。
套用某李的話說,此書毒性很大,讀者若沒有修習過古代漢語的課程,這書讀起來終覺得是雲裡霧裡的吧。
章雖然是小學大家,但此書若當成時下說文的入門讀物未免有點太濃稠了。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读后感(三):闲话太炎先生的《说文解字授课笔记》
一天午后读周作人的《泽泻集》,周二先生回忆他在日本跟章太炎学《说文》的事,说得扭扭捏捏:“中国文字中本有些朴素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地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进之也’的话很有些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的更好,而又拉扯上孔夫子‘屔’来说,所以显得不太雅训了。” 这欲说还休的语气,颇引起了我的好奇,但闲扫一过,也没太在意。后来读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余英时又引了周作人上一段话,还评说:“当时周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事隔五六十年,尚且记忆犹新,可见当时记忆深刻……”
——文字中仿佛透着一脸坏笑,我想,倒是什么能引得两位老头念念不忘了。处于俗媚的好奇心理,我先翻了《说文》,“尼。從後近之。从尸匕聲。女夷切。”段注引《释文》《释诂》《尸子》等说“尼,近也。”又写“開寶閒陳諤又改釋文尼爲昵”,但仍存“尼之本義:從後近之”一句。
后来买了《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得以一观余杭先生讲授“尼”字的原文。
尼字下朱希祖笔记:“《尔雅》训定,‘私之定也’。今俗骂人之肏字实即尼。即今云‘插屁股’尔。仲尼之尼字当做‘屔’。”钱玄同笔记:“盖今骂人之‘日你妈’之日字。古音尼,日音同。后作昵。尼字复以孔老头儿的台甫书作‘屔’,始不用本训,今都作昵。”
又见“尸臿”字注。朱希祖:“【尸臿】、尼、【尸旨】三字连属有义。”钱玄同:“从后头插进去。”
——原来许叔重的‘从后进之也’竟是这个意思,难怪周二先生年过八十,仍对当年的讲课念念不忘了。尼改为‘屔’是因为原意不怎么雅驯,避孔夫子讳而另造的字。想太史公《孔子世家》里一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也引得后来注家搔破头皮,为“野合”二字找个文雅的解释而曲为粉饰,都是蛮有意思的事。
以前读鲁迅,他在《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里摇头道:“前去听讲,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自谦哪。鲁迅在杂文《忽然想到(八)》里还记得“《说文》中‘淦’字是‘船底漏水的意思””;在小说《在钟楼上》还提到:“记得(太炎)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的‘州’,是女性的生殖器。”
章太炎讲说文,不避孔圣人的讳,也不避纲常人伦的讳,天马行空,洋洋洒洒。许寿裳回忆说:“太炎师据段玉裁的《说文注》,引证渊博,新谊甚富,间杂诙谐,令人无倦,亘四小时而无休息,我们听讲虽不得一年,而受益则甚大。”
士农工商,以识字的“士”为四民之首。识字的人占绝对少数,而掌握文字的人掌握着对现象的解释权。汉字所异于欧洲拼音文字的,在于它的贵族性。“子不语怪力乱神”,不雅驯的邑言村语被排除在以文字为符号的信息系统之外,这道选择加工的过程使被记载在文字里的大传统保留其纯洁与庄重。掌控文字者似乎在掌控未来。但是,被排除在文字信息系统之外的东西仍通过口口相传在民间留存。清末大厦将倾之际,贵族性的文字系统摇摇欲坠,章太炎对各地方言的研究把先前被文字遗弃的不雅驯的东西重拾回来。王汎森说,章氏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的影响,将六经历史文献化,故用世俗、朴素的社会人情为基础去解经,故一方面由六经中保存的史料,抉露出不少上古实况,连带的对六经性质的解释也随之一变。如从《易经》中得出“人情所致,惟淫欲搏杀最奋”,“《易》所常言,亦为婚姻刑法为多”,而古书中这些朴素的本意,多被后来学问家的“神圣化”而扭曲了。他的这种观点自然也带到他讲习《说文》的课堂里。他讲解《说文》里“州”“尼”“殿(太炎训作‘打屁股’)”等字时,那些司马迁所说“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话,也毫不犹豫地带到授课中来。这对当时听讲的学生来说,触动无疑是相当大的。旧学砖墙的缝隙就这样被渗入了,似乎可以预见到这栋墙的倒掉。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对《尔雅》《说文》倒背如流的钱玄同,成为改革汉字的旗手;周氏兄弟成为新文学的主将;在日本听课的学生中,只有黄侃等少数几人守候着旧时代。而章门弟子对旧学的倒戈,使白话文学的重要敌手反而成为了战友,章门弟子对白话文运动的推波助澜,让胡适、刘半农等小字辈遽获强援,虽然黄侃大骂钱玄同为“师门叛徒”,却已无力回天了。
这本书主要是朱希祖、钱玄同、鲁迅三人的笔记整理而成,其中朱希祖笔记最多,也最为认真,笔记中用语也相对持重,比较雅驯些。而钱玄同的笔记则不同,不时出现市井语言,嬉笑怒骂,别有一番狂狷之气(两人语气,比较上引的“尼”字笔记即可看出来),无怪鲁迅说他“十分的事情,偏要说到十二分”了。鲁迅的笔记看书影是工整的蝇头小楷,鲁迅先生留存的笔记不多,像钱玄同那样“出彩”的语言也少。通过看三人的笔记,不仅能读说文,又可看太炎先生的别出机杼,还可比较做笔记的人的性格语气,体味当时情境。真可谓一举多得了。
近日读费孝通《江村经济》,提到中国的书写系统异于欧洲拼音文字,出现“同字不同音”的现象,各地方言念法相异,反倒使方块字在东亚各地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中游刃有余,使汉字成为东亚大陆上各个民族间通行的书写文字,成了文化交流和地域统一的重要媒介。
我突然想起太炎先生在北大讲学,都用家乡话。他的浙江余姚话多数人听不懂,需要刘半农翻译,又因演讲中常常引经据典,钱玄同便在黑板上用板书写出。而章太炎在日本讲《说文》,虽然收受弟子甚众,但其中还是《民报》社“小班”弟子八人影响最大。这本《授课笔记》便出自其中三人之手。我们可以看看这八人都来自哪里:龚未生是浙江嘉兴秀水人,许寿裳是绍兴赵家坂人,钱家治是浙江杭州人,朱希祖是浙江杭州海盐县人,钱玄同是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朱宗莱是浙江海宁人。大家熟知的周氏兄弟则是浙江绍兴会稽人。
——不出所料,全都是浙江人。料来章太炎的余姚话这八个弟子听起来困难也不算大,而其余弟子,像较有名的黄侃(湖北省蕲春县人)、沈尹默(陕西汉阴人)、汪东(江苏吴县人)都非浙江人,虽说方言语音可以学而得,但终究有一层隔阂。章太炎纵是妙语解颐、诙谐间出,外乡人也总是有窒碍不通之处。而章太炎在日本所著的《新方言》,搜集方俗异语八百余条,考释惠州、嘉应州、潮州客话诸方言之来源,以古证今,以今通古,也是与日本讲学经历和方块字的这种独特性质有关的罢。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读后感(四):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史料新考
从新近刊布的钱玄同和朱希祖日记及《笔记》相关史料来看,章太炎的两次《说文》课程,分别以大成中学、民报社为主要授课地点,在时间和地点上始终错开。就笔记而言,朱希祖的笔记是三次不同授课的课堂记录,钱玄同的两套笔记则均据第一次讲课,并作了整理、校勘。
由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了解章太炎早年国学讲学的重要资料。从新近刊布的钱玄同和朱希祖日记及《笔记》相关史料来看,章太炎在日本期间,曾多次讲授《说文》,第一次在大成中学,从1908年4月至1908年7月,第二次在民报社,从1908年7月,约结束于1909年3月。这两次授课,在时间和地点上始终错开。就《笔记》而言,朱希祖的三套笔记是章太炎三次不同授课的课堂记录,钱玄同的两套笔记均是第一次讲课的笔记。其中,钱玄同第一套笔记,曾参考朱宗莱汇录的朱宗莱、朱希祖、龚宝铨、钱玄同、张敬铭五人笔记做过整理;钱玄同第二套笔记,当是直接据朱希祖记录的章太炎第一次讲课笔记做过整理。还原章太炎国学讲课的经过,梳理笔记所记录的讲课内容、校勘来源,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笔记的史料史料性质,并探讨章太炎早年的国学思想。
1908年4月起,章太炎先生在日本东京为留学生讲授《说文解字》,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2008年,《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整理出版,收录了钱玄同、朱希祖、鲁迅三家七种笔记,较为完整地保留了章太炎早年的《说文》授课情况。主持《笔记》整理的王宁先生,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前言》[1]中,详实地介绍了《笔记》的整理经过,并结合章门弟子的回忆,从章太炎的生平、革命思想与学术特点,梳理了《笔记》的相关背景和学术价值。参与整理的万献初,曾撰文记述《笔记》的原始面貌[2]。此外,汤志钧、周振鹤、侯桂新等学者,也围绕章太炎及章门弟子的交游、讲学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相关考察[3]。
正如王宁先生在《前言》中指出的:“这份《笔记》记录了太炎先生研究《说文》的具体成果,反映了太炎先生创建的以《说文》学为核心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思路与方法,也记载了三位原记录者向太炎先生学习《说文》的经历,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难得的原始资料。”但课堂记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部分材料的零碎和语境的不足:在学术语境方面,笔记包含了章太炎早期的《说文》研究,要结合章太炎同时期的语言文字研究来理解其讲课思路;在历史语境方面,《笔记》出版时,朱希祖、钱玄同的日记尚未完全整理刊布[4],学界只能依据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等章门弟子的事后回忆,事隔多年,弟子的追述难免在时间、地点上有失准确[5]。从笔记本身来看,朱希祖的笔记为三次课堂实录,钱玄同笔记则尚有辗转抄录的痕迹。本文拟结合朱希祖、钱玄同等听课弟子的日记,还原章太炎《说文》讲课的前后经历,并尝试考订《笔记》的源流,以期更好地认识《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的学术背景、学术价值。
一、章太炎在大成中学的国学讲学
1908年,正是章太炎在《民报》社担任主笔,写战斗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时候,章太炎缘何临席宣讲,为在东京的留学生讲授《说文》?钱玄同曾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说,“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6],周作人则追忆往民报社听讲,“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据钱玄同是年日记,促成者为钱玄同、龚宝铨(未生,亦作味生)和董修武(特生):
3月22日 上午与味生至太炎处,意欲请太炎来讲国学(先讲小学)。炎首肯。惟以今日有蜀人亦请其教,言当与蜀人接洽云。
3月25日 午后至太炎处,味生言四川人那边已接洽过,知太炎系令人看段注说文云。因与太炎讲及最好编讲义,用誊写版印之。太炎似首肯。太炎言程度较高者可看段注,次即看《系传》,一无所知者止可看《文字蒙求》矣。
3月29日 午后至太炎处,询讲小学事。言昨日四川人业已拟定。场所:帝国教育会;日期:水、土曜;时间:二时至四时。先讲小学,继文学。此事告成,欢忭无量。(浙人凡五:1余;2逖;3大;4复生;5未生。)
案,蜀人指四川籍的董修武。一开始,龚宝铨和钱玄同拟请章太炎讲授国学,后经与董修武的合议,章太炎决定编写讲义,并以小学开始国学讲授。钱玄同日记中的“欢忭无量”,正写出了他商定讲课之后的愉悦心情。
据3月27日的钱氏日记,初步确定的听课人员,有浙籍的五人,即钱玄同、龚宝铨、朱希祖(逖、逖先,亦作逷先),朱宗莱(大、蓬仙),沈钧业(复生)[7]。其余在大成中学听《说文》课的人员,还有范拱薇(古农)、张传梓(敬铭)、任鸿隽(叔永)等,均系章太炎早年弟子[8]。这一次《说文》的讲课,一周两次,时间一般在周三(水曜)、周六(土曜)下午,从4月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5日[9]。除了4月4日和4月8日的前两次听讲设在帝国教育会的清风亭外,从4月9日起,经董修武联系后,设在神田的大成中学[10]。
课程安排上,章太炎的讲授,是以《说文解字注》为底本。在清代《说文》学中,章太炎最推崇段玉裁的学术成就,在《訄书·清儒》中,章太炎盛赞“玉裁为《六书音均表》以解说文,《说文》明”。章氏的第一次讲课,即先讲授《六书音均表》及古音旁转、对转、双声诸例。在段玉裁发明古韵的基础上,章太炎进一步指出训诂音变还当以双声为标准。如《笔记》“铨”下,钱玄同笔记云:“权与垂非双声,故不可对转。凡可对转者,亦必双声也”,实即针对《段注》“权为垂之假借,古十四部与十七部合音”而发[11]。其后,章氏先讲授了《说文》叙,随后则是按照《说文》部首和正文的顺序,采用逐条讲授的方式。至7月26日,在大成中学的第一遍《说文》讲授完毕,现存的朱希祖第一套笔记,及钱玄同的两套笔记,就是对这一次讲课的记录和整理。
在结束了《说文》授课之后,章太炎每逢周三、六,仍在大成中学讲授国学。8月暑假期间,为避免下午天气炎热,改在上午进行(与民报社每周二、五上午错开),9月后恢复在下午[12]。从8月1日至10月31日,章太炎先后讲授了音韵、《庄子》、《楚辞》、《尔雅义疏》、《广雅疏证》的课程,涵盖了文学、诸子、小学的内容。但随后钱氏、朱氏日记失记,未见在神田授课的相关情况[13]。
二、章太炎在民报社的“小班”授课情况
1908年暑假起,章太炎在为钱玄同、朱希祖在大成中学讲授《说文》的同时,又在民报社章太炎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为朱希祖、朱宗莱、钱玄同、龚宝铨、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单独开设小班,讲授《说文》。
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回忆,“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这一次的“小班”上课,其具体时间是在星期日么?和大成中学的讲课的关系如何?在日记材料公布前,研究者多忽略了两次课程在时间、地点上的交叉进行。据朱希祖日记,二次授课的第一次开讲,乃安排在7月11日(周六):
八时起,至太炎先生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七人,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午后,至大成中学校聆讲《说文》,至女部完。
朱希祖的记载明确表明,上午的课程,在“太炎先生处”,讲授的是音韵学,同学连朱希祖在内共有八人。下午,朱氏仍到大成中学听课,续讲至《说文》女部结束。也就是说,当天的两门课虽安排在同一天,但时间、地点、内容不同。
随后,据两人日记,自7月14日起至9月8日,民报社的讲课一直安排在周二、五上午,与每周三、六大成中学的讲课错开。至于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所说的“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其实是九月之后的情形。是年9月11日,钱玄同日记记载:“因各人校课多有冲突,故今日停上《说文》课,容后再议。”到了9月20日(周日)起,章太炎恢复在民报社上课,时间改在每周日上午,每次大约四个小时[14]。
这一次《说文》结束于何时?据周作人、许寿裳回忆,大约均持续到第二年[15],而《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的整理者则根据朱希祖日记,推测课程结束于1908年9月[16]。实际上,《笔记》整理者的依据,即《尔雅义疏》的讲授,是大成中学班上的授课。据钱玄同日记,1908年11月1日,民报社的课程才到《说文》卷十的兔部。1909年3月3日,警局封禁民报社,3月4日(周四),钱氏日记云:“礼拜日之《说文》班,本应移今日,以昨晚事,今日辍讲。”这说明,1909年3月之前,章太炎仍在周日讲授《说文》,后来又改至周四。自第二周的3月11日(周四)起,章太炎开始在民报社讲《文心雕龙》[17]。许寿裳回忆,鲁迅曾在课堂与章太炎讨论“文学的定义”[18],并与章太炎就“有句读和无句读”、“文字与文学”有意见的不同。据钱玄同的《文心雕龙札记》[19],章太炎在这门课上,首先讲的就是“文学定谊”。这或即意味着3月4日前后,是最后一次《说文》课。随后,鲁迅继续在周四的班上听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此外,1909年4月,钱玄同曾向朱希祖借《说文》笔记。日记透露,钱玄同在课程结束前后,有过录同学的听课笔记的习惯。这也可以作为课程结束于1909年3、4月间的旁证。朱希祖的第二套笔记,就是对这次讲课的记录。
比较朱希祖第一次和第二次笔记中,也能看出章太炎讲授中,对考察本字、探求孳乳的学术认识的发展,如卷十二“戚”字下,第一套笔记云“亲戚不知由何假借”,第二套则云“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