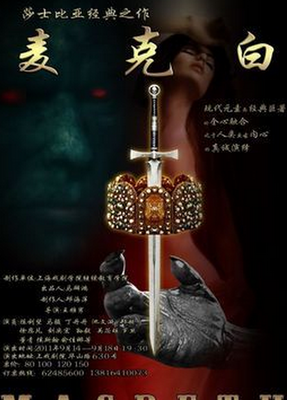巫师的读后感大全
《巫师》是一本由[英]罗纳德·赫顿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4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巫师》读后感(一):巫术的世界里并不是只有毒药和咒语
科技昌明时代,巫术隐形,巫师遁迹。但纵观人类发展史,巫术基本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且遍布世界的各个角度。
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从未见过巫术,也没见过巫师的仪式,但在潜意识中仍会有关于巫术的恐惧,就象我们对黑暗、对未知、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一般。
这部书,作者尽可能以广域而又纵深的视角,在世界范围内望向渐渐消逝的巫术时光,追求巫术的源起、发展, 考察世界各地人们对巫师及其他类似的信仰的态度以及巫师嫌疑人的遭遇。
巫术,从来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他更多的与当时当地的历史、政治、自然环境以及人文传统融合在一起,在人们恐惧和希望的夹缝里生存。巫术以其神秘的、带有诅咒性、超人类力量的属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有时,又与宗教、政权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翻云覆雨,掀起惊涛骇浪。
尽管以欧州为核心延展至世界范围的巫术,与我们的文化还有些隔膜,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静下心来,以慢阅读的方式,一点点去感受,你会发现这本书的趣味性,深藏于内,而它的文化属性,透过巫术打开的世界文化之窗,则需要慢慢感受。
巫术的世界里,并不是只有毒药、咒语,还有历史以及人心。
《巫师》读后感(二):邪恶与想象之间的使者,人类恐惧与欲望的投射
文/塞北1573
在大多信仰与相关创作中,神与魔,均借使者之名行事。在《使徒行传》中,是“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于各类魔鬼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是巫师。
从定义开始,《巫师:一部恐惧史》中,罗纳德·赫顿率先阐明书中“巫师”一词“遵循传统主流学术惯例指试用破坏性魔法的人”, 构成书中“恐惧史”的由来。梳理了巫师刻板印象的产生,产生的猎巫事件与巫师审判。从不断收缩的视角探讨近代早期从全球不同语境下的巫师比较研究,进入欧洲大陆的中世纪区域性魔法文化,最后落脚于大不列颠巫师形象的差别,及不同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演变,延伸至后来现代人广为熟悉的稍显“有趣”“轻松”巫师形象。
书本内容不仅是在广阔语境和深度视角中对“巫师”这一形象的追根溯源,更是各地民族文化、民俗内容的研究与补充。归根结底,巫师与猎巫的产生,是人们普遍相信魔鬼的真实存在与力量,且相信自身所处的正义性及与之抗争的必须性——这是千百年人类延续的根本——但却忽略了所谓的抗争是引发原因,以及抗争所维护的社会秩序下,究竟代表了谁的权益。更以“巫师”一角,掀开人类恐惧、女性困境与宗教政治的影响及行为。
随着对巫师及巫术内容的深入,我们发现,它们的产生、载体及作用,始终围绕着“人”运转。在神秘、随机、且伴随伤害和威胁的事件发生后,若无法用已知知识去解释,人类最容易归之为邪恶力量作祟。在不稳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变革的时期,也更容易发生巫师指控。基于疾病、猜忌、报复与政治性目的产生了不同巫术与巫师形象,直到魔王撒旦巫师新刻板印象的确立及传播。
而与之伴随的巫师指控与审判,也呈现出不同地区的态度差异,或同一地区不同时间出现的态度转变。如古埃及并入罗马帝国后,官方供养的读经者转为大众提供魔法服务,满足修习者或委托人世俗的愿望。由此产生了巫术概念和仪式性魔法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魔法莎草纸和通灵术。但在4到6世纪,基督教被普遍接纳后,埃及人此前对于魔法的宽容态度被根除殆尽。
从政治与宗教角度而言,巫师审判和猎巫事件的背后,也是西方信仰“万流归宗”,基督教在欧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渡。作者提到“近代早期猎巫行动的大多数受害者死于1560至1640年间”,在对巫师指控中,各地的传统和被记录下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如颠覆欧洲巫师指控“男少女多”的性别模式,在瑞典和挪威萨米文化影响下,出现了“男多女少”的特殊现象。
在大不列颠视角下的巫师研究中,作者着重介绍了妖精这一灵体样本的形象变迁及态度变化,从“欢乐生灵”到妖精王国传遍不列颠,最终到苏格兰。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期间,更在艺术作品和现实世界中中出现了“人假扮妖精或类似生灵”“犯人扮成妖精欺诈受害人,把财产和金钱弄到自己手中”等行为,逐渐消解了人们的妖精信仰,而这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导致英格兰和苏格兰对于妖精态度的偏差。在相较之下,凯尔特社会对于猎巫行为则因当地的信仰体系而行动较少。
在大量历史和前学术结论的举证或推陈出新下,罗纳德·赫顿在整本书的立论时可以说十分谨慎。关于特定时间和特殊案例的对比研究中,突显出历史长河中想象和信仰体系的成长与流变。时间依旧向前,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现代科学和先进政治制度出现,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宗教和审判之外的世界。那个年代里的“使者”或“受害者”也都湮没在历史尘沙中,而“恐惧”与“欲望”这两大主题,仍在现代甚至将来的社会中存在,再以各类想象与形式表现出来。
2020.11.23
大雪
《巫师》读后感(三):恐惧下的新视角
世界历史研究经常突破学科界限,将历史学与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甚至宇宙学等进行融合。1991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大历史”研究方法,探究强调作为类的人类,从不同尺度——微观的、全球的、世界史的、人类史的、宇宙的——来探究过去,思考人类身份的多样性。那么,我们从这本《巫师》也能看到作者从多视角来思考人类历史,确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巫师”一词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与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截然不同:《周礼注疏》有“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杜子春云:‘司巫师巫官之属,会聚常处以待命也。’玄谓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当按视所施为。”巫师为官方所承认之官员,主要是为国家祈福,且巫师是有组织的——包括“帅巫”(巫师的领导者)以及“巫恒”(类似于见习巫师);而在西方我们看到的是会魔法、伤害人的巫师形象,这便是文明视角。
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明更多将“天”这一概念拟人化,皇帝为天之子,巫师为上天的代言人,更多负责的是占星、预示和祈祷,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太平广记》当中有非常有趣的例子——中国如何处理祸害人的巫师?
第一,通过神明的处罚对巫师进行审判:
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常谓巫师为道人。初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门吏:“此云何所?”门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礼即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千百间屋,皆悬帘置榻。男女异处,有念诵者,吹唱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礼,礼怖走出。神已在门外,遂执礼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重。”付吏牵去。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燋烂,求死不得。经累宿,备极冤楚。府君主者,知礼寿未尽,命放归。仍诫曰:“勿复杀生淫祀。”礼既活,不复作巫师。(出《幽明礼》)
第二,由官方对邪术进行打击,重点为巫蛊之术。最为经典的案例便是汉朝的巫蛊之祸,我们在看很多宫廷剧都能看到巫术的影子,而一旦被发现他们的结局便是死亡,中国人对此非常忌讳,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但是,我们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巫师未成为反社会的因子,更多成为了官方的代言人,或者说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与西方文明有着明显区别。
回到书中,分三部分对“巫师”进行解释研究——深度视角、大陆视角和不列颠视角,不过还是以古代欧洲文明为中心进行。埃及、赫梯、波斯这些国家虽在地理层面上不输于欧洲,但在古代他们也属于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故而之间有很多的交流且有非常多相似点与共同之处。
“巫师”不能简单用“黑”和“白”来区分,历史研究应当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世上本就不是非黑即白,我们都是在两者之间徘徊。欧洲世界的巫师更多是以邪恶的反宗教者的形象出现,所以会有巫师恐惧和猎巫传统,这与基督教文明有联系,更类似于宗教层面的冲突。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在所有的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的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就如作者在本书当中引用的各个地区的巫师史实,便是在说明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理解,是与其本民族的文化相对应的,甚至能够形成比较大的区域传统,这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体系的拼凑,我们研究时不能忘却“文明”的功效。
魔法小说、玄幻小说、仙侠小说等等网络文学的传播,让我们对“巫”这一概念的认知得到了新发展:如魔法师经常会出现的灵宠——猫头鹰,手持魔杖、头戴法帽、身穿魔法袍,这成为了魔法师的标配。但是仔细去研究会发现,这一形象自古便已经有出现,我们只是将历史具象化,将之作为影视、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这本书并未将每个地区的巫师现象解释清楚,但是提供了一个大的框架、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能够激发其他学者进一步探索,取得各自不同的成果”。当一个个地区的巫师研究成果出现,之后再比较研究,便能够形成一个详细且有条理的巫师体系,本书还是更多在论述西方世界,对于东方文明以及印第安文明提及较少。
《巫师》读后感(四):《巫师:一部恐惧史》:关于巫术恐惧的全景扫描
提到巫师,你会想到什么?是电影哈利波特里的巫师世界?是动画里鼻子尖尖一身黑色斗篷的女巫形象?是童话里那些神奇或古怪的魔法?或者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猎巫行动?
也许这些都立马出现在脑海里,但很快会发现我们对巫师的想象其实如此的刻板和远离生活。《巫师:一部恐惧史》这本书则将巫师拉入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帮助我们了解与巫术有关的信仰,以及由巫术信仰引发的近代早期欧洲对巫师进行的审判。
该书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罗纳德•赫顿的巫师研究专著,梳理的内容庞杂,跨越时间很长,涉及地域更是辽阔,书中涉及的史实有理有据,素材详实,博大精深,是一本以巫师为主题的兼具学术本色及科普可读性的著作。
巫师的定义和特征
首先,作者先按照主流的学术惯例将巫师定义为所谓使用破坏性魔法的人。以与现在将巫师当成魔法使用者统称所区分开来。因为魔法使用者还包含另一种人群,这些人通常被当做术士、智者、药师、巫医等,他们将魔法用于善意目的,比如提供疗愈、占卜、消除巫术的影响、寻找遗失或被盗物品,或者引诱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等等。这类人被视作是服务型魔法师。
作者认为巫师具有五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对同胞构成了直接威胁,被认为以非物质和离奇手段给其他人带来不幸或伤害,人们甚至声称他们破坏了社会的宗教和道德基础。第二个特征是巫师伤害的是邻居或亲属,因此他们是来自社区内部的威胁。第三个是巫师的出现不是孤立事件。即巫术存在某种运作系统。第四个是巫师对社会带有强烈而普遍的敌意。公众自发地对他们带有愤怒和恐惧,常常认为巫师为害出于对人类社会的普遍仇恨,还与宇宙间的邪恶超人类力量结成联盟。第五个特征,人们认为巫师应该要被抵抗,也可以被抵抗,比如强迫、说服他们解除诅咒,或者攻击其身体杀死或者伤害他们等等。
猎巫行动仍在伤害现代社会
关于猎巫行动,有很多从犯罪学、心理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科学哲学等视角提供的真知灼见,也有的或许从社会政治权力结构、或许从女性主义不同的角度切入,这本书更多是尽量客观中立的爬梳和展示,把具有争议的观点一起介绍。比如对猎巫这一社会行动,作者将正反两种观点都叙述出来。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从理论上讲,猎巫在某些时候的确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对异常或反社会行为的阻止,它可以强化文化规范,从而加强社区团结。而另一种观点(也是本书作者更倾向于的),则认为猜疑和指控并没有解决恐惧和敌对,反而让它们更加激化,阻碍了社会内的友好合作。更恶劣的是,猎巫会使得社区四分五裂,留下持久的创伤和仇恨,大大加剧了因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造成的痛苦。
显然第二种才是更值得认可的,因为对巫师嫌疑人非正式和非法的暴力如今依然存在,残暴、残酷,仍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联合国官员的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里,全球范围内因巫术指控而被杀害女性的数量不断攀升。而书里也记录了一些近些年来的巫术指控事件。“针对嫌疑人的暴力行为(正如最近在非洲南部所发生的的那些)主要是由渴望在社区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贫困年轻人发起的,而且这些行为变得越发公开和极端。”“至2012年,关于儿童巫师的恐慌蔓延到刚果,据说有两万名儿童流落首都金沙萨街头,他们都被从家里赶出来了。”“2013年,新几内亚一名年轻女性在包括警察在内的数百名旁观者面前被活活烧死”,“2014年,两名男子在瓦努阿图的一个社区会堂内被公开绞死”,“2010年,加沙的一名妇女因被怀疑为巫师而遭到谋杀”……
女性与巫术的一些梳理
因为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我也特别留意了书中提到的性别部分。
“在1075年的科隆,1175年的根特,1190年和1282年的法兰西,1296年的奥地利,都有女性因为修习魔法而被处死。”猎巫行动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女性,只有在很极罕见的情况,即在17世纪挪威和瑞典的巫师审判中才出现意外,违反了“男少女多”的规律,因为当地萨米文化的魔法修习恶萨满教仪式主要与男性联系在一起。(萨米人在近代早期是令人敬畏的魔法师。)
书中提到20世纪一位中世纪魔法和巫术信仰的研究专家诺曼•科恩曾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者“普遍认为”仪式性魔法和巫术毫无关系,因为前者的修习者大多是男性,他们会试图控制魔鬼,而后者的修习者多为女性,他们是魔鬼的仆从和盟友。这算得上是极大的偏见了吧。
作者发现希腊人构想出来的使用危险魔法的神或者半神的人物,比如美狄亚和喀耳刻,都是女性。由此看来,那些将魔法定义为非法、不体面和不虔诚的活动,并将女性排除在政治和社会权力之外的文化,比如希腊和罗马,都倾向于将魔法和女性结合成一种“有威胁的他者”的刻板印象。
女巫师的形象被各种添油加醋的加工。比如偷牛奶,欧洲一些畜牧业经济区的民间传说中相信巫师会偷牛奶,在中世纪后期瑞典、丹麦芬兰、德国北部等一些教堂绘画中出现的偷牛奶的主要就是女性。到了近代早期,偷牛奶是波兰巫师审判中女性最常受到指控的罪行之一。中世纪爱尔兰文学也充斥着暴力和恐怖的女性,被翻译成英文时,她们就通常被描述为“巫婆”和“巫师”。
在有的社会,巫术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妇女针对男性的复仇行为,尤其是对那些婚姻不忠的男性。比如开普省的一些部落认为巫师都是女性,她们拥有很多奇特的动物,有一种甚至能变成英俊的年轻男子。她们还喜欢那些化身为蛇、狒狒和野猫的灵体,长毛的人形小生灵和复活的人类尸体……
书中涉及的内容实在太过庞杂,但个别的点也不失为有趣。比如p415提到的墨西哥的索西人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可以以动物形态存在的灵魂,不禁想到《黄金罗盘》、《黑暗物质》。还有书里简单提及的幽灵漫游、愤怒军团、夜间骑行队伍的超人类女性领队、将战场上被杀死的武士召集成军队且能穿越大地和海洋的女性骑者(女武神)等等……都是很适合出现在奇幻小说电影的设定啊。
《巫师》读后感(五):译后记
接到这份委托的时间是2017年,转眼三年多过去了。和ihuman各位编辑老师互动、接受帮助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胆子大,丝毫不知翻译之难,我是万万不敢接这份委托的。
不同于我见过的所有相关题材著作,作者罗纳德·赫顿将巫师和巫术放在全人类社会共同的境遇视野下,构建了一个“三层圆环”的论述结构。
在最外层,也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全球视野中的巫术和巫师形象。他利用广泛收集的全球人类学文本,总结归纳出巫师形象的五个特征,并将巫师与“服务型魔法师”区别开来,厘清了讨论的目标。
并从长时段切入,观察从埃及-希腊-罗马(+日耳曼)-中世纪,直到近代早期巫师形象的流变,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对于巫师的态度。
以及对巫师与所谓的“萨满教底层文化”做了辨析。
中间层,也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专注欧洲巫师形象的来源分析,论述了各文化中的哪些文本、那些民间传说被吸纳进“巫师是一种邪恶宗教”的刻板印象中。并进一步区分了依靠文本的上层精英魔法师传统,和主要依靠民俗、口耳相传的巫师传统。
还对欧洲猎巫最严重的时期,根据烈度做了地域性的区分,提出”近代早期巫师形象大拼盘“的形象比喻,具体分析民俗传统和社会权力结构等因素等对猎巫烈度、男女性别、社会阶层、指控原因……的影响,打破了以往对猎巫既有的一概而论的印象。
最里层,也就是本书的第三部分,专注于不列颠的巫师形象,介绍了德鲁伊与巫师在形象上的差别,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猎巫的差别,妖精形象在民俗传说中的变迁,家养小精灵形象的流变,魔宠(动物)与巫师的互动等。这部分尤其为英美流行文学和影视作品(指环王、哈利波特系列、梅林等)提供了颇有趣的学术背景。
由于地域跨度和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翻译起来难度真是特别大,尤其涉及古代和中古文献部分,只能上网检索与之有关的其他学术著作进行比照,力求对中心词的学术背景稍有掌握,勉力做功。希望各位方家、老师在阅读中多多体谅。
现附上我为本书作的译后记,为这项工作再稍作说明,如有碍眼之处,莫怪莫怪。
我与巫结缘始于2016年。该年的万圣节前夕,“万有青年烩”团队想就这一主题录制一期知识类的节目,我接受他们的委托,主要负责介绍与巫师有关的内容。为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动手查找中文世界中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资料,并撰写了上万字的文稿。
节目在万圣节前夜顺利播出了,从观众的反应来看还算不错,可作为参与者的我却像背上了一件沉重的包袱——太多的问题得不到解答。
比如,同样作为掌握了超自然力量的人类,哈利·波特世界里的魔法师与《灰姑娘》童话里变出南瓜马车的神仙教母有何不同?又比如,《指环王》里的白袍巫师甘道夫和非洲、拉美世界里的巫师一样受人敬仰吗?在早期近代席卷欧洲大陆的巫师迫害又是怎么回事?
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我。所以当ihuman的编辑询问可否接手《巫师》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时,我与另一位对巫师文化极感兴趣、也是合作多年的文史领域作者汪纯老师马上就答应了下来。我们商定,由我负责翻译本书的致谢、题记、导言、结论及第一部分、第三部分的八至九章,汪纯老师负责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的第十章,为了保证译文的统一,最后由我做统稿工作。
我们从未认为这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它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太多。正如作者所言,本书涉足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多个领域,既广泛引用了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至中世纪、近代的大量文献,又采用了大量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各民族人群的研究成果,对巫师文化做了全方位长时段的扫描。它介绍了埃及法老、罗马皇帝、北欧人是怎么看待巫术的,也探索了魔法咒语、德鲁伊和家养小精灵的定义和来历,最重要的,它从文化、历史等多个层面追踪了近代早期欧洲大规模猎巫和巫师审判的过程,并做了可信的对比、分析和研判。对于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内容极为丰富的巫术文化博物馆,而对译者而言,则如同“误闯”了一座茫茫的黑森林。
幸好,在探索的过程中,国内业已引进的相关书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南。我们参考了基思·托马斯的《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埃文思–普里查德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弗里茨·格拉夫的《古代世界的巫术》、沃尔夫冈·贝林格的《巫师与猎巫:一部全球史》、罗宾·布里吉斯的《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以及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研究巫术文化的专业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代历史著作和民间传说文本。而王铭铭主编的《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A. 曼古埃尔和G. 盖德鲁培的《想象地名私人词典》,以及必要的人类学、宗教学词典等则在人类学史、宗教学和西方民俗传说文本的理解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这么做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努力让我们的工作符合专业化的学术规范,避免让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耻笑和诟病。不过,考虑到本书的受众群体,其中应该不乏那些对时下流行的文艺作品中的巫师形象感兴趣的读者,因此我们也尽量将译本做得通俗,并在必要的地方加入了译者注,提供一些背景介绍,力求降低阅读难度,增加可读性。
这本书的最后能够成功翻译出版,还要感谢许多提供无私帮助的友人,尤其是,本书的德文词汇有赖于在德国工作生活多年的好友林海、朱敏,中东欧词汇的拼读则求教了博学的南蔻,关于植物学的生僻知识则叨扰了顾有容老师。感谢本书的编辑曾威智、周丹妮等,让这本重要的书不至于被我们粗陋的翻译所损伤。可爱的王恰恰同学,这本书没能赶在你离职之前出版,但我猜拿到书的你也应该感到十分开心。
2005年我在福建师范大学攻读世界史研究生。对于初窥学术门径的我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茫然。我的导师,基督教研究专家林金水教授不仅以无比热情和耐心向我展示了宗教文化的精彩和学术的魅力,还非常信任地将“罗马密特拉教”这个选题交由我研究。十多年之后,当我在这本书中看到那段关于“密特拉教神秘仪式”的论述时,就如同见到了许久未曾谋面的熟人一般亲切。希望读过这本书的您,也会在某一天涉猎巫师题材的通俗文艺作品时产生和我一样的感受。
赵凯
2019年10月12日
于福州飞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