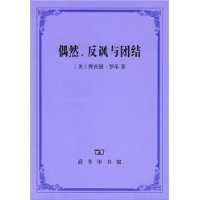《偶然、反讽与团结》读后感100字
《偶然、反讽与团结》是一本由理查德·罗蒂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2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偶然、反讽与团结》精选点评:
●没有人拥有真理 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别人正确地了解
●世界不说话,只有我们说话。只有语句才有真假可言;人类利用他们所制造的语言来构成语句,从而制造了真理。抛掉“真实的人”这个概念,就等于不再像康德一样,企图将自我加以神圣化,以取代神圣化的世界。
●反本质主义,团结赖于对他人经验的感受和理解,而非抽象的普遍的人性。从理论走向描述。至于追求自律的反讽者和追求公义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各自站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而不要试图从理论上统合两者,因为作者认为社会除了避免残酷不应该有别的目标,而反讽者所追求的自我实现其实于公共目标无益。对福柯和哈贝马斯的评论。
●清晰,流畅,态度鲜明。比起《筑就我们的国家》,这个罗蒂更让我信服。
●前面很不错,后面就...
●无法言语、唯泪流的惶惶巨著,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毒的特效解药。非在西哲岐路上牵绊、迷茫多年的人,不知这番解毒后的五味杂陈。读过的西哲书中,光芒位列个人榜单前三甲。恨这么晚才一睹。
●后半部分要求同等的知识背景
●期末论文参考,罗蒂在这里处理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哲学在共同体之中的地位。罗蒂将哲学放到与其他学科相同的地位,没有任何优越之处,反而提高了文学的地位,那么我们能走向一种类哲学的文学吗?
●与其说是一部试图调和反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术著作,不如说是针对若干哲学和文学内容的评论集,罗蒂自己也说,反讽主义哲学应该更像是文艺批评。其中纳博科夫与奥威尔、海德格尔与普鲁斯特的对比研究最为出彩,而罗蒂清晰生动的文风也是我所喜欢的
●若相信書裡的觀點,亦即把我們使用的語言、相信的「真理」皆視作歷史偶然的產物,而又把個人的目標設定為尋找自我的「終極語彙」,那我就是一位反諷主義者。
《偶然、反讽与团结》读后感(一):罗蒂
罗蒂去世,我写了一篇逝者发在杂志上
写这篇文章前,刚好在书店里买了本中华书局那套书中的罗蒂,发现作者刚好集中于罗蒂这本书的内容,对理解罗蒂的书很有帮助。
然后我又读了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之后那本哲学史
发现罗蒂对自己哲学的身体力行、否定哲学而倡导文化评论,并不是始自转到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而是更早,那家大学。
另外,为了表现文中有点个人评论,我说形而上学冲动是很难克服的。但是后来想想,罗蒂并没坚持要扫荡掉形而上学,他也是区分私域和公共领域,有一段就讲到海德格尔,你可以自己搞搞研究,但是不要把那一套付诸实践。
《偶然、反讽与团结》读后感(二):教条化和平主义对利益根基的伪装
所谓德国哲学的晦涩难懂其实是因为翻译腔,这翻译腔之所以中国人看不懂是因为它是用汉字写的,却不是贵国人的母语,而是两成的满大人语框架里塞了八成的日本国语。贵国人就只是货真价实的语言载具,幻想做语言屠夫,莫非真有能违反机器人三定律的铁疙瘩?那都是阿西莫夫对北京直立人的无耻恭维。/这就是白左圣母合理性的理论化,就是鸵鸟策略,刻意忽视义无反顾的繁荣是恐惧战争和毁灭的结果,怂得瑟瑟发抖却强装谈笑风生。此书应改名为《理论时尚的终结》。知识分子幻想的原子化好好先生解除武装,后果一定是被无产阶级虐得死去活来,三十年的全球化实践已经让欧美无根游士谄媚大众民主的破绽百出的多元化理论彻底破产。失去道德根基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诗性创造怎么可能被想象成普遍标准?欧美式中庸mediocrecy腔调展示了自由左派面对存在主义去神秘性后义正词严胡搅蛮缠般对内的志得意满和对外的鸵鸟政策。
《偶然、反讽与团结》读后感(三):诗化人生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书评
关于生,关于死;关于美,关于道;关于自我,关于他人。
要像写一首诗一样来度过自己的人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像复制品一样死去,这个意象可能是全书最打动我的地方。
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碎片很离散,也曾经自责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连续地去安排去规划去过一种不要总是浮在云端的生活。但是在阅读中渐渐明了,没有一种人生是绝对优于另一种的,没有一种生活状态是你应该要拥有的,所有的路和你的时空,生命可能的形态,都是可以创造的,而不是要你去趋近的。
一直觉得自己的念头转瞬即变,总是难以有一个连贯而清晰的自我,于是苦苦纠结于真实的自我,那个内心的本我是何面目。但是自由主义的反讽让我看到,不需要去纠结哪一个是真实,并没有一个内在的本质真实存在于世,对于自己,你不是要去寻找不是要去发现,而是要创造。于是瞬间释然,所以又如何,我就是创造了一个变幻不定的我,我的这首诗,就是要有不连续的韵脚,压同一个韵,只是一种格律,谁规定一定要用同一种格律,或者,谁规定一定要有格律呢。
宗教与哲学,其实是两种探讨终极问题的方法,罗蒂的哲学,事实上可以给我一个如何面死亡的答案,当然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答案,但是对我来说,我想此时此刻,会欣然于这样的答案,我所时常恐惧的,确实不是死亡带走了什么,不是失去,而是一种对成为复制品的恐惧,是当我离开时世界与我无关的无力。斯人将逝,罗蒂至少提供了一条途径,来面对这样的恐惧,至少指出了“我曾欲其如是”这样的意象,来说明如何避免这样的无力。
对于文学,我始终相信小说的字里行间,蕴含着可以让我面对一切的力量,始终相信活在故事之中,我就能抵御现实。在我人生低落或是阴郁之时,我也不只一次从小说中找到光芒,这或许是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深信,或许是一种偶然的坚持。但罗蒂让我更清楚地看到小说的作用,在他的语境中,小说或者说故事,或许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让我们将个人与社会结合,将个人追求与避免残酷相结合,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人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神经能接收到另一种生活的起落浮沉,于是我们能拥有更广阔的世界,心与万物同游。总是不被正统文化所重视的小说之中,原来蕴含着上帝已死,共同心性已逝之后,人类社会的希望。
会想到卡尔唯诺《看不见的城市》,不同的面向来观看,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会让人在同一座城市中看到完全不同的存在。我有时候以为自己跳出了盒子,其实还是在同一个盒子的不同区域思考,罗蒂的书其实是在扩大我们所认知的盒子,于是当我们想要跳出的时候,能实现更广阔的跃迁。
《偶然、反讽与团结》读后感(四):出家人慈悲为怀
因为最近着迷维特根斯坦,我又翻出罗蒂这本书,一些阅读记录和随意的想法如下:
1. 语言的偶然性继承后期维特根斯坦,世界或人类并没有一个内在的本质,所谓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我们更接近自然或人性的“本质”,而是我们选择用不同的语汇进行再描述,是一组新的隐喻诞生并逐渐被接受为本义的过程。这组新的语汇被接受,不意味着它更正确、更符合“真理”(因为只有语句才有真假,人通过语言制造真理,并没有什么脱离语言而自在的真理),新的语汇被接受仅仅是一系列时间与机缘的产物。
2. 如果可以像韦伯那样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结起来的话,那么现在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一定遵循着佛教伦理。罗蒂关于语言偶然性的说法也让我想起“诸法因缘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的教诲。
3. 自我的偶然则是相当存在主义的了。发现自身偶然性的自我害怕成为别人的复制品和仿冒品,因此要创造自己的语言,利用独特的隐喻在无趣的日常本义中重新创造自己。
4. 接受语言偶然性和自我偶然性的即反讽主义者,他对目前使用的语汇抱有质疑态度,不认为语汇之外有任何真实本质的东西。反讽主义者支持自由主义的原因是担心如果只认识相似的人,他们会陷入熟悉的语汇中,无法获得新的新的语汇新的体验来创造自我。
5. 然而罗蒂也意识到,“团结”很可能来自“媚俗”。大多数人不愿意被反讽主义者再描述,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熟悉的语言生活和理解世界,再描述意味着一种世界观的崩塌,对他们是侮辱,而侮辱是自由主义者最不愿见到的。
6. 那么反讽主义者如何成为自由主义者?解决方案是反讽主义者要将自己分为“私人的”和“公共的”两个部分,反讽主义者应当在私人有限的领域进行自我创造,而不是试图将这些语汇扩展到公共领域。海德格尔应当认识到,那些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词如“亚里士多德”“巴门尼德”“笛卡尔”,其实是和普鲁斯特小说中的“盖尔芒特”“贡布雷”“吉尔贝特”一样,只是他私人的东西而已。
7. 在公共领域,反讽主义者则依赖于“慈悲”,即对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同情来达到人类团结。阅读文学作品(如纳博科夫和奥威尔的作品告知读者人和社会可以如何残酷)是避免残酷的重要手段。最终通过对苦难的慈悲不断将“我们”的概念进行延伸,达到人类的团结。
8. 我非常理解与接受“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划分,人们总是希望在宏大叙事下获得安全感,所以我不愿从意识形态角度批评如《战狼2》这样的主旋律作品。但我怀疑,如果像罗蒂所说,海德格尔和普鲁斯特一样私人化,不需要超越性和普遍性,那哲学还有没有公共性可言。它甚至不如物理学,可以在一座建筑和桥梁中体现自身的公共性。
9. 罗蒂的自由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看上去像是民主政治、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的混合,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罗蒂的自由主义似乎只强调了避免残酷,但是否有一种虽然不存在对“他者”的直接侮辱,但却一样是让人“受苦”的自由社会?(例如那些生长在欧美“自由主义”社会的圣战主义者)
10. 罗蒂希望通过对苦难的慈悲,不断将“他们”变为“我们之一”,扩大“我们”的范围最终达到人类的团结。但如果没有“他们”怎么会有“我们”?“我们”是围绕“他们”建构起来的:那些异乡人、异教徒、女巫、不可接触者、移民、难民,所有这些 homo sacer ……只有当我们看见“他们”,才回头发觉“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偶然、反讽与团结》读后感(五):梁捷:纪念罗蒂
罗蒂在中国名气不可谓不大。他2005年曾来过中国的,不但在全国各地做了好几场讲座,还接受众多主流媒体的访问,甚至在华师大办了一场“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的国际会议,回答各式各样“罗蒂研究者”的提问,声势应该超过德里达和哈贝马斯。
而罗蒂的著作由多位不同的学者译成中文,其中不乏翻译名家。比如他的《哲学的自然之镜》是由李幼蒸教授翻译的,时间很早,应该是第一次把罗蒂的名字和贡献传递给国人;《后形而上学希望》以及是浙大张国清译的;《后哲学文化》是黄勇译的;《筑就我们的国家》是黄宗英译的,都是名家。可是,我最赞赏的一本罗蒂的书,《偶然、反讽与团结》,国内影响似乎要比上面那几本小很多,译者徐文瑞也不大为人所知,很让人想不通。
我觉得这本书的著、译俱佳,读来一气呵成,甚至有不忍释卷的真实体验。我坚信这本书是初识罗蒂的最佳入口。
罗蒂最终是在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的职位上去世的,但他当然是哲学家,多数人认定他是叛出分析哲学之门的政治哲学家。比如逻辑大师王浩先生颇不喜欢罗蒂,浸淫于欧陆哲学的张汝伦教授也是如此,多次以“复旦学生问倒罗蒂教授”的经历为豪。罗蒂早年确实编过“语言学转向”的文集,从而使得这个概念传遍天下。但罗蒂后来又接触了欧陆哲学以及其他各种哲学,处处批判,处处反讽,否认自己的根基,批评欧陆哲学也批评分析哲学,这才使得各派学者都对他感到恼火。
我读罗蒂后来的文集,看他也会重谈过去对戴维斯和塞拉斯的研究,同时分析普特南,分析丹尼特,这里面处处透出他的分析哲学基础。而且,分析哲学在近些年也纷纷转向“心智哲学”等领域,罗蒂一直在其中耕耘,算不得“叛变”。罗蒂在《偶然》一书中也说了,晚年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和海德格尔一样。
罗蒂自称“没有根基”,可研究罗蒂的学者好像多半都有些“根基”,所以导致研究出来的罗蒂都不大像我心目中的那个自由的罗蒂。罗蒂热爱海德格尔,罗蒂更热爱黑格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罗蒂也热爱杜威,热爱实用主义,热爱那一套千疮百孔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理论,这让很多人吃不消。再加上罗蒂热爱心智哲学,热爱当代政治哲学,热爱后现代解构主义,热爱文学批评,若是心胸不像罗蒂般开阔,很难体会罗蒂思想的个中三昧。
阅读罗蒂的时候,我正处于思想上茫然的时期,读罗尔斯,读哈贝马斯,读施特劳斯,也读德里达。我对一些政治哲学的立场当然有所亲近,但仍然怀疑它们的论证和结论。罗蒂的书让人过瘾,真是快刀乱麻,把各派分析的弱点清楚明白地揭露了出来。政治哲学的分析充满了偶然,不管政治光谱上哪一点的立场,都不见得是天经地义的,都有很多先在的假设和偏好。当时我读书体会,只觉得德里达虽然解构,却躲闪缠饶;伯纳德.威廉斯虽然解构,却文胜于质;只有罗蒂,是真正的诚实的解构,而且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实用主义,这是再诚恳不过的立场了。
我觉得《偶然》一书在结构和论证上真是精妙无比,文章嵌合得密不透风。罗蒂用三个主题词把书分成三个部分,每一部分三篇文章,又对应偶然、反讽与团结这三个主题,循环反复,趣味无穷。偶然是观点,反讽是论证,团结是希望,这三个词背后以实用主义一以贯之,构成了罗蒂整个一套思想。后来,罗蒂又用“希望”等概念来明确他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只是从这本伟大的文集里抽一段,加以发挥罢了。
罗蒂思想的魅力,是用一切思想对抗一切思想,让思想本身说话,让强大的思想散发魅力,让不完整的思想自我破裂。罗蒂就像一个居高临下的指挥,熟练地操弄各种思想。但他与德里达不同,他要严肃得多,毕竟他有不是立场的立场、不是哲学的哲学――“实用主义”。他不回避这个社会所遭遇的困境,他的最爱就是黑格尔。他讨厌康德,讨厌那种以为能够寻找确定、唯一的追求。他会用“反讽”的武器让这种思想自己出洋相,而历史的车轮不管它内部的思想,轰隆地向前滚去了。
罗蒂去世了。他的思想,必然随着历史车轮,留下自己的印记。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 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